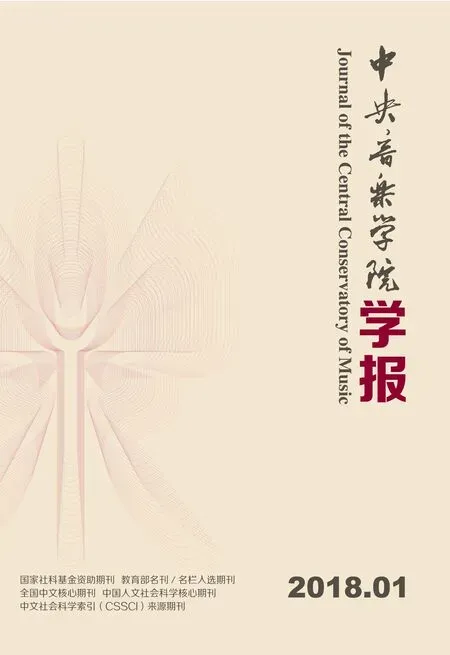《性别焦虑与冲突
———男性表达与呈现的音乐阐释》( 姚亚平著)
王丽君
引 言
随着当今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全世界各政治、经济、文化主体间相互交流、相互理解、相互协作的愿望变得空前强烈而迫切。音乐学研究作为文化研究范畴的一个专门领域,它的当下发展也毫不例外地呈现出这种趋势。鉴于中国在当今世界各领域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影响力,西方音乐学界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的音乐学术研究。同时,当今的中国音乐学者在探讨音乐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内容时,也开始更多地关心如何在国际音乐学术领域发出中国人自己的声音。尤其是对于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者来说,如何能够突破传统的研究模式,参与当代国际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学者们努力探索的目标。姚亚平的《性别焦虑与冲突——男性表达与呈现的音乐阐释》(以下简称“《性别焦虑与冲突》”)可谓这一探索的成功尝试。
该书秉承于润洋先生提出的“音乐学分析”的研究理念,基于作者多年来对这一理念的不断阐释、反思、实践和发展,借鉴当今国际学术界较新的研究视角、方法和观点,从法国作曲家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入手,以性别批评的视角,对作品中的性别隐喻进行了另类阐释,进而揭示出父权制意识形态下的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音乐文化中男性精英的性别焦虑和冲突。该书从实践层面反映出作者一直以来对西方音乐研究观念和方法的理论思考和探寻,以下笔者将结合书中实例从三方面对该书在理论上的主要建树进行评述。
一、对“音乐学分析”的实践阐释
本文最初始的研究工作正是受音乐学分析追求目标的影响和激励,在音乐学分析名义下开展的。(第32页)
这是姚亚平在《性别焦虑与冲突》的导言中表明的。该书可以说是从实践层面上对“音乐学分析”这一研究理念的阐释。
“音乐学分析”的概念是于润洋先生在他发表于1993年的论文《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中首次提出的①。它的提出被认为“对国内的西方音乐研究具有开拓意义”②。“它不仅仅从术语上填补了音乐学研究中的一个空缺,更重要的是它在方法论和学术观念上明确了一种符合中国传统的(因而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化的、较高层次的音乐学研究。”③与此同时,它“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文艺理论的观点不谋而合,在抨击形式主义,批评传统的传记、考证和文学史研究方法,要求把艺术置放于社会历史文化中来审视等方面立场很接近”(第32页)。
“音乐学分析”概念的提出在中国音乐学界引起很大反响,二十多年来它始终是学者热议的话题。学者们不断地对这种研究理念和方法进行尝试,有的则试图对其进行理论阐释。姚亚平在这两方面都进行着不懈探索并取得了卓然的成绩。他先后以《西方音乐的观念——西方音乐历史发展中的二元冲突研究》④《复调的产生》⑤,以及本文所谈论的《性别焦虑与冲突》等代表著述对这一理念进行实践,同时通过一系列文章对“音乐学分析”的学理进行努力探索,包括:《于润洋音乐学分析思想探究》⑥《什么是音乐学分析:一种研究方法的探求》⑦《关于“分析”的若干话题分析》⑧,以及《错觉图——游走于形式与形式之外的凝思游戏》⑨等。
《性别焦虑与冲突》一书是作者对于“音乐学分析”的理论探求在实践上的体现。该书以“音乐学分析”为理论基点,试图用具体的实践解决音乐学分析的一个重大难题,即如何“通过音乐这一具体的文化形式,阐释其中所包含的艺术审美之外的其他内容”(前言第2页)。而正如姚亚平在《什么是音乐学分析:一种研究方法的探求》一文中所述,实现这一目标“包含着两个最基本的要点”:
其一,注重从人的精神和社会环境的考察,从音乐之外的人类社会、历史和文化生活角度来解释音乐现象;其二,通过音乐本身,尤其是通过音乐的形式构成要素来说明音乐的社会性质。这两个要点构成了音乐学分析的两根支柱,互相依仗、缺一不可,有趣的是,它们一外一内,一虚一实——一个形而上:意识和观念的抽象;一个形而下:经验和实证的观察——而取得了某种均衡。”
也就是说,音乐学分析“必须要面对两种性质上完全不一样的文本,即音乐文本和社会文本。它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两件似乎互不相干的事物,如何化解这两种话语体系之间的隔膜,使其互相指涉、互相说明,最终到达从音乐的理解过渡到对社会和文化的理解。”
那么,在《性别焦虑与冲突》中,作者是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的?
如同姚亚平在上述理论阐述中说的那样,该书确实存在着两个一外一内、一虚一实、互相依仗的支柱。一方面是音乐作品的形式,即以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为代表的19世纪音乐形式;另一方面是性别意识,即以作曲家为缩影的19世纪父权制下男性精英的性别意识。作者正是通过环环相扣的论述,令这两方面实现沟通,从而实现以性别意识来解释音乐形式,以音乐思维来说明社会性别问题。
在该书的第一章,作者首先从揭示音乐形式分析无法解决的问题出发,从令学界争论不休的柏辽兹《幻想交响曲》的结构矛盾谈起,提出从音乐外部阐释音乐形式的可能性。接着,作者尝试着从这部交响曲的戏剧发展逻辑着手,找到了其中隐含的性别转换的线索,进而将戏剧结构中的性别转换假定为音乐结构的决定性意识,并结合实证材料和音乐分析对这一假设进行论证。至此,似乎音乐形式与音乐外部的要素已经建立起关联,然而这种关联似乎还不足以实现作者试图“通过一种具体的文化形式(音乐)了解和认识人”的写作目标。因为,揭示出《幻想交响曲》中所隐含的戏剧角色的性别转换,只是例示出一种现象,而如何理解这一现象的文化意义,才是实现研究目的的核心。
在接下来的第二章中,作者通过对女性主义双性同体理论的借鉴,对作品中所呈现的戏剧角色性别转换现象进行了另类的文化诠释,认为其体现出父权社会男性性别意识的冲突和男性的衰落。而在第三章中,作者进而以双性同体的理论来考察作曲家和作品所属的整个19世纪社会文化,认为女性意识的复苏是整个浪漫主义的集体意识,而柏辽兹作为其中的典型,他也是这种文化的参与者。在第三章最后一部分,镜头又从远距离拉至近距离,作者再次聚焦柏辽兹,对他作为父权社会的文艺青年的两面性进行了论述,认为:
柏辽兹的人格和音乐中具有双性合一的品质。一方面,作为父权社会的男性作曲家,他选择了这一时代最适合男人的表达话语——大型器乐,将日耳曼文化中的男性要素融入到在法国遭到抵制、并几乎无人问津的交响曲中,另一方面,他的音乐又极力冲破具有父权文化烙印的和声和曲式,无所不在地表现出男性中心主义的破坏和反叛。这种双性特征在他的音乐里表现为直接的冲突,两种对立因素互相支持,也互相削弱。(第57页)
在第四章中,作者以人类学、性别批评有关音乐思维的性别特征的理论为依据,并有所创见地对音乐思维中的性别隐喻进行了分析,认为调性音乐思维作为父权制社会在音乐中的印记,它在《幻想交响曲》中出现的种种变化的迹象,隐喻着男性的衰落。
在第五章,作者将目光投射向整个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从大型器乐和奏鸣曲式的衰落切入,揭示整个浪漫主义的阴性特质。而在第六章,作者“从和声的演化……始终不渝地反复重申本书的一个基本观点:音乐形式可以理解为一种具有性别意识的文化观念”(第278页)。
该书最终通过音乐内部形式与音乐外部的性别文化的不断互证,揭示出19世纪欧洲父权制社会男性自我的焦虑和矛盾问题,并站在男性立场上一鸣惊人地提出男性衰落的观点。
二、对西方性别批评的吸收、批判与补充
“音乐学分析”无疑是《性别焦虑与冲突》的理论基点,而将社会历史考察与音乐本体分析相关联是“音乐学分析”的独特性所在。然而,从上文可以看到,该研究的社会历史考察,不同于传统意义的社会历史考察,它以性别批评为视角,涉及有关人的新话题、新维度。根据姚亚平的说明,在这一点上,“它受益于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性别批评,接受上个世纪80、90年代以来以性别批评为主要特征的‘新音乐学’(new musicology)的一些重要思想,终归来说又与‘新音乐学’的后现代风格和意识相去甚远”(前言第2页)。
这里体现出姚亚平对于“音乐学分析”与当前国际新学术思潮之关系的思考和看法。他曾表示,“音乐学分析应该关注当代国际学术潮流的最新动向,但并不盲从,而是吸收一些有用的东西,并结合自身的文化环境和学术传统,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第32页)。他还表示,“社会-历史”这个概念在当下可以被诠释和拓展,他写道:
我们注意到,在当代,“社会-历史”概念正悄悄地被“文化”概念稀释、淡化而发生改变。对于这种现象,对传统的社会-历史学派来说不是坏事,完全可以吸收,以使自己的观察视角更加多元和宽阔。”
也就是说,“音乐学分析”与当代新的学术思潮具有很大的兼容性,这使得它的观察视角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正如姚亚平所说:
音乐学分析的表现形式、切入角度有多种可能,如传统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角度,20世纪心理和精神分析角度、新马克思主义角度、女性主义角度、文化人类学角度等等。这种种不同的音乐学研究派别虽然角度不同,思想方法迥异,甚至某些观点尖锐对立,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它们都反对传统实证主义,抵制音乐研究中的自律论,都主张以开放的姿态,将音乐视为一种与人、社会、历史有密切关系的精神文化现象,以在社会文化的语境中分析和研究音乐作为自己的努力目标。
那么,在《性别焦虑与冲突》中,作者吸收了西方性别批评的哪些方面,又对它进行了哪些批判和补充?
首先,姚亚平在该书导论中表明,该项研究接受了女性主义以下认识成果:
(1)迄今以来的人类文明社会本质上是男权社会,文明社会所指的人实际是“男人”,性别概念在很多情况下是人为和虚构的;
(2)所有的写作从理论上说都有“性”(gender)的烙印,因此很多文艺现象可以带着“性”的眼光来审视;
(3)父权制的所有意志都留在了这种意志的外泄对象——政治、法律、哲学、文学、艺术等人类文明的产品上;
(4)在音乐研究领域,原则上接受具有女性主义特质的、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音乐学”对音乐的性别批判和“性”的诠释。(第26页)
具体来讲,在该研究中,作者反对女性主义中的一种观点,即以男性的仇女意识来解读《幻想交响曲》,将其看作是一部“典型的‘控诉’型女性主义批评的范本”(第77页),认为这一视角仅仅“站在女人的立场上,把男人置于批判和控诉位置,它的重要特点是以生理性别为界限,将人类划分成男人和女人两种对立人群,强调性别矛盾和冲突,着眼女性的解放和战争。”(第77页)作者则与之不同,他站在男人的视角,更赞同社会创造性别的观点,认为不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是文化造就的。而且,他质疑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对于历史的推进作用。他承认,“至少自19世纪以来,父权制开始走向衰败”(第79页),但认为,“父权制的衰败,主要与男人的内部问题有关。”(第79页)
作者进而依据女性主义提出的另一种观点,即“双性同体”的理论,来解释男性的衰落问题。他认为“人类自始源上是双性合一的,文明社会造成了人性的分裂,而弥合这种分裂一直是人类不懈追求的精神目标。”(第82页)这里的所谓的“文明社会”主要是指父权制社会。作者称“父权制是以压制双性同体,推动性别分裂,凸显男性至上来维持自己统治的。……然而,由于双性同体原理,男性这个不正常和扭曲的主体,本能地一直努力试图恢复人性的双性本源,这个过程同父权制的男性观发生激烈冲突,并最终导致了男性的衰落。”(第93—94页)而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则被看作是体现这种男权意识衰落的代表作,作者认为,“交响曲中呈现出的戏剧角色性别转换是作曲家自己内心两种对立性别角色的轮换和迁徙”(第81页)。
那么,在从文化回到音乐形式的考察过程中,该书吸收了“新音乐学”的观点,“强调音乐分析的阐释性,把音乐语言视为文化和社会的符号反映”(第182页)。他赞同女性主义音乐批评的代表人物苏珊·麦克拉里(Susam McClary)的论断,认为“调性是男性的话语,是父权制的符号物证”(第323页)然而,他认为,“这一洞见并未得到充分论证:为什么调性是男性的?它在哪些方面体现为父权文化符号?”(第323页)他试图采取一种与“新音乐学”不同的方式对这一论点进行论证和补充。对此,他解释道:
新音乐学是后现代的,更为主观、随意和注重碎片式的表象;而本文的思想方法却很传统;它强调一种“过时”的整体观察,注重宏大的历史走向和深层次的思辨性论证。在某种意义上,本文是在弥补女性主义视角中的许多盲点,它从男性视角观察男性自身。(第182页)
由此,作者尝试以男性化思维对于调性音乐作为父权制符号进行宏观地思辨性论证。作者首先推论“父权文化必然在其文化产品上烙下印记,这个印记充分地体现了男人的意志”(第182页),而这种意志在音乐中体现为“结构与逻辑”(第182页)。作者从宏观层面着手,将19世纪前后欧洲的音乐语言与这个时代的思想观念关联起来,“在理性—男性—调性之间建立起可以横向关照的互文关系”(第182页),指出“这三个概念是同一思想意识在不同领域的体现,它们都体现为父权制文化的最坚实内核:理性是父权文化的思想基础;男性是父权文化的性别主体;调性是父权文化在音乐的符号体现。”(第182页)
三、对音乐形式观念语言学转向的回应
上文提到作者在对音乐的文化阐释方面吸收了“新音乐学”的观点,即“把音乐语言视为文化和社会的符号反映”(第182页)。作者吸收这一观点也同他对“音乐学分析”的反思,以及对音乐形式观念语言学转向的认识关系密切。正如作者在导论中宣称的,该书有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即“在音乐研究中实践语言学革命带来的新观念”(第36页)。也就是说,“音乐学分析需要对音乐形式的本质做出迎合语言学革命新形势的回答”(第36页)。那么,姚亚平对“音乐学分析”做了哪些反思,又如何认识音乐形式观念的语言学转向呢?
首先,他认为解决“音乐学分析”中音乐形式与社会文化相融合的难题的关键在于,对音乐形式的概念进行重新思考,转换以往的观念模式。正如他在《错觉图——游走于形式与形式之外的凝思游戏》一文中所论述的:
“音乐学分析”必须破解一个似乎难以逾越的难题:让形式与形式之外的事物对话和融合,以防掉入“两张皮”的困局。在我看来,破解这一难题的出路在于变换“形式—内容”二元对立的传统思路,探索在“内容”概念缺席下,形式话语自身蕴含的二重性,由此,必须思考一个很少被追问的问题——什么是音乐形式?
在此,作者清醒地认识到,当今对音乐形式的理解已经发生了语言学转向,形式本身作为符号具有了“形式之内”和“形式之外”的二重性。而这里所说的“形式之内”与“形式之外”与形式自律论和形式—内容二元论所说的形式和内容不同,它的前提并非建立在音乐形式具有“不依赖任何其他外在事物和影响的内在规律和逻辑”的观念基础上,而是认为形式本身便是观念或思想,正如姚亚平所论述的:
形式与形式之外是同一的,形式是观念的物化,形式与观念异质同构。一部西方音乐的形式史也是一部思想史和观念史,形式的逻辑也是思想或观念的逻辑,所有的形式的演进、变异、颠覆、更新都是思想和观念的演进、变异、颠覆和更新;形式和思想的关系,是错觉图的关系,不能说哪一幅是真实的,哪一幅是错误的,画面是两可的,不存在矛盾和逻辑混乱。我们也不能说形式表现了思想,而毋宁说形式就是思想。
姚亚平有关形式二重性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与新近阐释学派的观点吻合。两者都认为“文本之间是平等的,它们互相指涉、互相说明、互相影响。这就是新近学术思潮中常常提到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人们试图通过互文性来消解艺术文本与社会-文化文本的隔膜,解决艺术批评中的这个关键性难题。”在这种话语系统中,音乐文本本身就被看作是社会文本,而社会文本也被看作成为音乐文本,两者互相指涉,正如姚亚平论述的:
在这种阐释中,文本阐释不再是单向度的,不是一种文本决定另一种文本,而是双向甚至多向度,文本之间的相互交流;社会文化影响和指涉艺术,艺术也反过来指涉和影响社会文化;所有元素的边界都是开放的,不仅艺术文本对于社会文化是开放的,社会文化也对艺术开放着。在这样开放的阐释语境中,艺术并不是对立于社会,不是游离社会话语系统之外,相反,它是社会话语系统中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部分。很显然,这种阐释中艺术文本的话语地位得到了很大的强调,它不是被社会或文化所决定,不是结果,——作为符号或象征,它本身就已经被视为社会文化话语。”
那么,在书中,这种符号学语境下的新形式观念究竟是如何体现出来的?
在该书中,音乐形式被作为性别意识的象征和符号来研究,它本身具有二重性。在此,音乐的曲式、主题、和声等方面共同建构的音乐思维被看作是“形式之内”的,而性别意识则被看作是“形式之外”的。但这两者不存在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同一的,音乐思维被看作是性别意识的物化,两者之间存在着异质同构的关系。
作者吸收了麦克拉里的观点,认为调性是男权的象征,并认为奏鸣曲式“是这一原理的最高体现。”相对而言,调性的瓦解以及对奏鸣曲式的破坏则被认为具有阴性特质。在此基础上,作者还进一步论述了主题与和声隐喻的性别思维。他认为,主题具有男性思维特征,旋律具有女性思维特征;“前者是整体的、宏观的、连续一致的,后者是个别的、近距离和分散的;前者具有理性和逻辑性,后者则是感觉和经验性;前者是动力的、扩展的,后者是安静和停滞的。”就和声而言,线性和声逻辑与功能性的和声逻辑背后也隐含着两种音乐思维:“功能逻辑所信奉的乐音结构原则是关联原则,它是二元论思维,……关联原则符合理性主义的原则,包含超越、支配等理性意志,体现了西方父权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而线性逻辑体现的是并置原则,它是反二元论,与父权文化核心价值观相左”(第210页)。基于上述观点,《幻想交响曲》由于其结构上对奏鸣曲式的扭曲、“主题”思维被“旋律”思维取代,以及线性和声逻辑对功能性和声逻辑的破坏,被认为削弱了男性话语的表达系统,隐喻男性的衰落。
此外,该书在论述上采取双向度的方式,在音乐文本与社会文本之间互相观照、互相指涉。比如,该书的前三章通过由内而外、从音乐文本到社会文本的路径,解决了通过社会文化解读音乐形式的问题。而在后三章中,作者将考察的方式转变为由外而内、从文化到音乐的路径,目的是解决通过音乐文本说明音乐文化的问题。而且,在论述的过程中,焦距缩放自由,游刃有余。特别是由于宏观历史思维的加入,更使得符号话语体系的共时结构与传统史学历史叙述结合起来,从而使论述的向度更为复杂。
结 语
综上所述,《性别焦虑与冲突》一书通过具体的研究实践,对“音乐学分析”这一既独具中国特色又与当今国际学术潮流不谋而合的研究理念进行了新的阐释,使其与当前新的学术倾向更为紧密地呼应,而对于性别批评和符号学等新的学术研究视角、方法和观点,作者在吸收的同时,也对其提出批判性意见,并运用传统史学的宏观视角对其进行了有益的补充。
笔者认为该书对于中国学者的西方音乐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首先,它有效地解决了国内西方音乐研究中音乐与文化不能兼顾、或兼顾而不能深入,以及常见的“两张皮”现象。文中不论是对音乐文本的分析,还是对社会文本的阐释,都非常深入,而且在两者之间建立起水乳交融的联系。其次,它将新学术潮流中对阐释者主体意识的关注,与传统音乐史学中强调实证的倾向,巧妙地结合起来。文中的论述既处处闪现着创意的火花,又不乏严密的论证,可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此外,该书虽未涉及中国话题,也未刻意预设中国人的视角,但可以被看作是“中国视角”的西方音乐研究范本。作者作为一位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者从当代男性的视角,积极地对西方音乐发表看法,参与西方学者的讨论,“不是西方文化的旁观者,而是建设性的文化阐释者”,这本身就足以体现其“中国视角”。从以上意义上来讲,笔者认为,该书在理论上的探索意义更大于它在内容的创新。
① 论文通过对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分析例示了一种从音乐学角度分析音乐作品的研究理念和方法。这篇长文的发表以及这个概念的提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试图将音乐本体分析、审美批评以及社会历史批评融合起来。同时,它吸收了历史释义学和哲学释义学中的合理因素,来解决音乐作品意义的理解问题,主张研究者应将自己的视界与历史视界相融合,超越二者各自的局限,形成一种新的视界,来理解作品的意义。见于润洋:《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音乐研究》,1993年,第1期,第39—53页;第2期,第86—100页。
② 姚亚平:《于润洋音乐学分析思想探究》,《音乐研究》,2008年,第1期,第54页。
③ 同注②,第58页。
④ 姚亚平:《西方音乐的观念——西方音乐历史发展中的二元冲突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⑤ 姚亚平:《复调的产生》,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年。
⑥ 姚亚平:《于润洋音乐学分析思想探究》,《音乐研究》,2008年,第1期。
⑦ 姚亚平:《什么是音乐学分析:一种研究方法的探求》,《黄钟》,2007年,第4期。
⑧ 姚亚平:《关于“分析”的若干话题分析》,《音乐研究》,2010年,第4期。
⑨ 姚亚平:《错觉图——游走于形式与形式之外的凝思游戏》,《乐府新声》,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