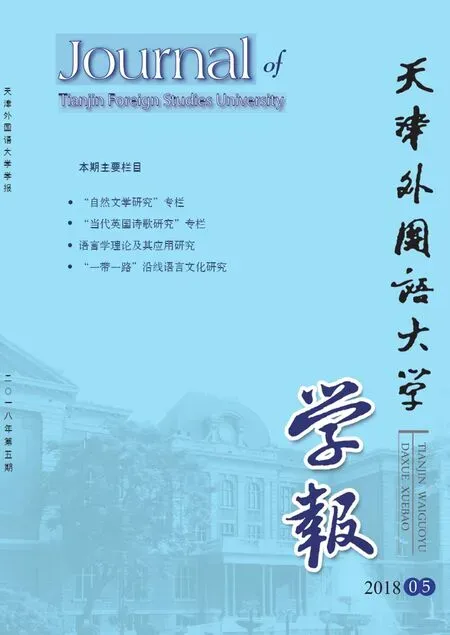高贵的野蛮人——R. S. 托马斯笔下普利瑟赫形象解读
姜士昌
高贵的野蛮人——R. S. 托马斯笔下普利瑟赫形象解读
姜士昌
(河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南新乡 453007)
在R. S. 托马斯笔下,以普利瑟赫为代表的野蛮人形象是人类与大地密切关系的象征,他们有着最自然的本性、最质朴的智慧和最顽强的生命力。与自然一样本真的生活赋予他们超乎常人的生存和自我修复能力,使他们成为人类创伤的医者和“新世界的第一人”。诗人希望通过揭示这些所谓野蛮人的本质表达对原始人性及其强大生命力的赞美,进而呼吁异化人类的人性回归。
普利瑟赫;高贵的野蛮人;人性;原始主义
一、引言
R. S. 托马斯(Ronald Stuart Thomas,1913-2000)是威尔士当代诗坛泰斗,20世纪英语世界最杰出的抒情诗人和宗教诗人之一。他一生共创作了24部诗集和五部散文与自传集,赢得过包括女王诗歌金奖(1964)在内的众多文学奖项,还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托马斯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在威尔士北部乡村教堂履行神职,退休后长期隐居于更为偏远的威尔士西部的利恩半岛尖端,是一位典型的隐逸诗人。托马斯终一生以自然和乡村的宁静与质朴来对抗现代世界的喧嚣与虚华。他反对现代应用技术及其一切衍生物,不但摒弃一切机器,甚至也容不下报纸的存在,他的一生几乎与现代化生活方式绝缘。诗人以这种常人难以理解和接受的离群索居的苦修生活坚定地践行原始主义(primitivism)的人生准则,而他的诗歌则是其生活与思想全面而真实的写照。
作为与现代主义完全对立的概念,原始主义思想的形成与“高贵的野蛮人”(the noble savage)形象的发现与发展密切相关。18世纪,包括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在内的众多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在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笔下“高贵的野蛮人”形象的基础上,结合古典文学及社会理想中一直在追寻的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共同塑造出一个“生活在‘纯粹自然状态’下,温和、聪慧、未被文明的罪恶所腐蚀”(Ellingson,2001:1)的具有普遍警醒意义的“高贵的野蛮人”形象。在此过程中原始主义也相伴而生。原始主义思想倡导野蛮人式的、远离科技文明的纯自然生活,反对奢华与复杂,坚信人类本性的善良和“文明世界必然的腐败”(Drabble,1993:789)。广义上来讲,原始主义至少有三个层面的含义,即人性、文化和文学的原始主义。人性原始主义是本原性的,当它投射于群体行为和文化形态时便成了文化原始主义,而文学原始主义是由内在人性与外在文化双重因素促成的。
托马斯的原始主义思想最直接的载体也是一位“高贵的野蛮人”形象——普利瑟赫。以该形象为主人公的系列诗歌是将人性与外在文化相结合的文学典范,其基本主题就是倡导扬弃现代文明,返归原始人性。这些诗歌以讴歌原始人性为出发点,谴责以英格兰为首的外部现代世界对威尔士民族地区的同化与开发,彰显威尔士人民为保护本土文化免受工业文明破坏而付出的努力,并进而揭示在强大的现代主义浪潮冲击下,传统民族文化与生活方式终难逃脱被毁灭的命运。托马斯共创作了19首以普利瑟赫为主人公的诗歌,与另外近20首描写不知名姓的农夫或农场工人的诗歌构成普利瑟赫系列,并指向同一类主题。
二、“不朽的老树”:原始人性的象征
对原始人性的讴歌是普利瑟赫系列诗歌的核心主题。在这些诗中人性的伟大是通过对近乎原始的威尔士北部山乡艰苦生活的描写反衬出来的。普利瑟赫的原型就出自这片山区。托马斯(Thomas,1997:52)描写了普利瑟赫第一次出场时的情景:“十一月份的一天,阴暗而寒冷,在去拜访山坡上一户农家的途中,(诗人)遇见了正在田间削甜菜的这家主人的兄弟。这一情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一回到自己的住处,他就着手创作《农夫》这首诗歌。这是他尝试着正视周围现实情景的第一首诗歌。”此景象在威尔士北部山区十分常见,也最终发展成普利瑟赫系列的典型背景,即山民孤独地行走于崎岖的山路上,劳作于乱石密布的田间,在狭小的世界里为生存而拼搏。普利瑟赫系列体现了突出的反田园诗特征。
在《农夫》中普利瑟赫被托马斯塑造成在自然状态下艰难求生的粗鄙、冷漠、迟钝的野蛮人形象,他养几只羊,种些甜菜,有点收获就“心满意足地/咧嘴痴笑”(5-6),他“空空的脑袋令人恐惧”(13),浑身还“散发着汗臭和牲口的骚味”(14-15)。这些描写延伸到该系列其他诗歌,如《一位劳动者》中“弯腰去拔/难扯的甘蓝”(5-6)的无名农夫那“无色的眼神”(7),《土壤》中行动迟缓、机械地挥动锄刀收割甜菜和甘蓝的主人公那“被篱笆圈定的/灵魂”(7-8),还有《亲缘》中身着“酸臭的衣服”(17),面带“莫名其妙的笑容”(17)的主人公。这种白描式的书写给人以苍凉悲壮的真实感,以至于“你不但能在山脊的田垄间看见他,还会去接触他……甚至于还会闻到他”(Rogers,2006:128)。你甚至还会从普利瑟赫们的笑容中寻找到一把解读人物的钥匙。普利瑟赫在面对收获时的确也会咧嘴痴笑,但这种笑容比“太阳撕碎/天空那憔悴脸庞”(《农夫》8-9)的次数还要少。诗人似乎在借此暗示就连微不足道的收获也不是常有的。而《菜农》中农夫的笑声不但罕见,而且沉重。
他的笑声
罕见得如撞开石屋上不堪
苔藓重负而下垂的窗户的声音。(5-7)
显然普利瑟赫们的笑具有双重内涵:一是罕见喻示生活的艰辛,二是乐观彰显生命的倔强。A. E. 戴森(A. E. Dyson,1981:297)分析说普利瑟赫及其族人在贫瘠土地上的辛苦劳作“不仅反映了威尔士农民的生存状况,更是所有艰难求生的人们生存状况的写照”。他进一步认为:“这种简约的生活……比起精明干练、老于世故更符合人性,或许这才是人类境遇的更为真实的写照。”(ibid.)事实上,诗人的确是要把普利瑟赫形象与普遍人性关联起来,从而将其升华为天然性情和原始生命力的象征。因为普利瑟赫就像深深植根于威尔士山乡的一棵不朽的老树,虽历尽沧桑却依然坚韧挺拔,顽强生存。
笔者认为,托马斯之所以重墨表现威尔士山民艰苦的生活境况,主要目的并不是要唤起读者的同情,而是要给与读者更高层次的训导。普利瑟赫形象的典型意义就在于他固守根本,而那些背离简约生活方式而转向物质享受的所谓文明人则丧失了人之根本,是异化了的存在。文明世界的虚华与造作使诗人更加向往普利瑟赫们的简约生活和天然性情,普利瑟赫形象也因此成为诗人对抗现代社会物质主义的有力武器。更重要的是,野蛮人般的普利瑟赫以顽强的生命力彰显着自然状态下人性的伟大,表现出比文明人更为高贵的品质。
三、“坚固的堡垒”:来自原始的力量
普利瑟赫的率真与质朴成为托马斯用来抗击文明世界虚伪与造作的有力武器。这是诗人创作普利瑟赫系列诗歌的目的之一。年复一年的辛苦劳作榨干了普利瑟赫的思想,仅存的似乎只有生命和沉默得有点迟钝的情感。《农夫》中劳作了一天之后他“枯坐在椅子上/纹丝不动,偶尔倾身把一口痰啐向火中”(11-12)。普利瑟赫这种木讷得几近原始的性情显然是长期艰辛生活的必然结果,也肯定会唤起读者的同情。但诗歌的主旨绝不在此,而是要表达更高层次的主题,即对原始生命力的肯定与赞美。普利瑟赫的木讷、粗鄙、身上的汗臭以及牲口的骚味不但没引起诗人的反感,反倒被认为是质朴本真的体现,它们直接冲击着“那文雅/却造作的感官,自然无遮掩”(15-16),是人类原始生命力的象征。
这就是你的原型,他,一季又一季,
与雨的围攻抗衡,与风的消耗战对峙
保卫他的种群,一座坚固的堡垒
即便在死亡的混乱中也牢不可破。(14-20)
第二人称的突然出现暗示出上述语义的攻击目标,即那些文雅却造作的所谓文明人。其确切所指可有不同解释,既可以理解成对诗中叙述者本人的指责,也可以假定是针对读者。如果是后者就不仅是泛泛地指责所有文明人矫揉造作的一面,更可能是把矛头指向了那些小觑威尔士文化传统的英国人。“种群”一词包含有血统、世系、家畜等多重意思,这里可能是在讲普利瑟赫的羊群,更可能包括他本身,尽管他只不过是个脑袋空空的皮囊。这个字眼无疑暗含着普利瑟赫与牛羊家畜品格相通、略无二致之意。可以想见作为一位农夫,普利瑟赫虽然“与文化和诗歌绝缘,甚至也与宗教绝缘……他生命中却蕴藏着令人羡慕的本真与能量”(Dyson,1981:294)。诗中的另一个意象坚固的堡垒寓意更深。首先,诗人似在暗示正是由于普利瑟赫的精神空白才使得它坚不可摧,甚至死神也无法把他毁灭。这个颇具反讽意味的逻辑表明这不是所谓文明的胜利,而是原始生命力的胜利。其次,这一意象还暗含着诗人对威尔士乡村传统得以延续的愿望。
威尔士乡村传统的延续或再生产一直是托马斯诗歌间接表达的主题。《乡下孩子》中描绘了一位乡下男孩从降生开始一步步成长为一位典型的威尔士农夫的过程。这首诗歌虽没直接提到普利瑟赫之名,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男孩就是普利瑟赫,至少在他的身上看到了普利瑟赫的影子。就像这位男孩一样,所有的威尔士农夫的青春都曾在他们的脸庞上做过短暂逗留,但很快又在“肆虐的寒冷风暴”(4)和灰麻鹬的哀鸣中迅速褪色。这成为威尔士乡民的成长模式。诗人有意将威尔士农夫的成长经历普遍化,目的是要揭示威尔士民族与历史的再生产过程和以普利瑟赫为代表的威尔士乡民持守根本的毅力和韧性,并进而将这种认识推及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再生产。
毫不快乐从贫瘠的子宫坠落,
渐渐成熟,父母却日渐老去;
……
就这样,日子将漂入月,月漂入年,
铸成他沉默的口,抚犁的手。(1-8)
在《埃古·普利瑟赫》中坚固的堡垒演变成了新世界的缔造者。普利瑟赫形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诞生的,这时的世界需要弥合满目的疮痍,摆脱核爆炸和核威慑带来的恐惧,在旧世界的废墟之上重建一个新世界。按照托马斯的设想,这个新世界不但要彻底驱散战争与核爆的阴霾,还要解决机器文明所带来的生态危机。普利瑟赫或如他一样“用大地的法则”(10)指导自己生活和信仰的人就成为执行这个伟大的再造工程的丢卡笠翁和皮拉①,是“新世界的第一人”(12)。他们反对都市化、工业化和一切生活中的虚华,过着天然、本真的生活。他们最贴近自然,具有最原始的感受力和创造性。他们知道自然界的一切如何运行,表现出与自然一样的、超乎常人的生存和自我修复能力。托马斯认为,普利瑟赫和他的族类不但要承继悠久的威尔士乡村传统,也注定要成为灾难中的世界的拯救者。普利瑟赫形象的核心价值不仅在于他是威尔士传统乡村文化的代表,更在于他的持守根本及由此表现出的无穷生命能量对人类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
四、“真理面包”:人性认同的吁求
托马斯塑造普利瑟赫形象的另一目的是要寻求人性的普遍认同。诗人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存在基础:原始人性。也就是说,无论是文明人还是野蛮人,本质都是一样的。原本一样的人类如何走向不同道路,最终产生巨大隔阂,《埃古·普利瑟赫》揭示了其中的原因。
啊,埃古,我的朋友,无知的人们认为
你是你族类的最后一个,因为你从黄金时代带来的
所有财富就是粘在你鞋子上的
牧场鲜花散落的黄尘。(1-4)
诗人暗示人类走向不同道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对财富的不同认知与选择。野蛮人把从黄金时代延续至今的黄尘(即泥土)视作最大财富,因为它是人类生存的根本和原始人性得以延续的保障。普利瑟赫之所以像《那位劳工》中“一颗坚挺的野树”(16),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就是因为他像神话中的大力士安泰一样坚守根本,“双脚定在了泥土之中”(18)。诗人以此告诫读者人类要持续发展,就要像普利瑟赫那样敬畏根本,回归自然和质朴生活,决不能弃本求末。然而,无知的人们(泛指所有文明人)却为了满足对物质的贪欲而走向了歧途。他们无视原始生命力的价值,背弃人性,抛却根本,远离自然与土地,走向了所谓文明的道路,当然也无法公正看待生活在自然状态下毫无文明素养的普利瑟赫和他的族类。
诗人认为,要想召唤文明人回归根本,首先就要让他们正确认识并接受普利瑟赫形象的真正内涵,消除文明人与普利瑟赫形象之间的冲突与隔阂。诗人强调普利瑟赫与所有文明人之间的认同,并使其不断强化。《那位山民说》中的山民竭力强调:“听,听啊,我如你一样,是个人”(5);《亲缘》中普利瑟赫与文明人共享一片星空:“他也是人,同一颗星星/指引你回家,也照亮了他的心灵”(18-19);《那位劳工》里的劳工虽双眼迷离,亦如其他人一样受同一颗星星的引领:“不,不,他和你一样,是一个人,只是汗滴模糊了/眼睛,看不见指引你的那颗明星。”(14-21)布朗(Brown,2006:24)认为,诗人的反复呼吁是在向读者强调普利瑟赫与文明人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异。
既然普利瑟赫和文明人之间并没有本质差别,为什么不能坐在一起交流呢?托马斯构想了一个有点不可思议的情景,即一场发生在哲学家康德和野蛮人普利瑟赫之间的辩论。他将康德的术语“范畴”改头换面饰以“绿色”,写出了诗歌《绿色范畴》,以象征这些野蛮人固有的乡土气质,颂扬和捍卫他们世界观的高贵与尊严。诗中康德和普利瑟赫之间展开辩论,但均未能说服对方。最后的结果是两人居然凑到一起,“在一颗星星蓝色的火焰上分享(他们)的信念”(23)。有学者认为,这样的结果似乎暗示了两种悬殊观念的彼此妥协,而笔者更愿意将其解读为包括康德和诗人在内的文明人向野蛮人的妥协。因为在托马斯的观念中野蛮人甚至比文明人拥有更多的真理。托马斯之所以持此观点,是因为他认为本真是通往真理的必经之途,顺应人性,葆有本真,才能拥有真理,而违背人性,丧失本真,便意味着远离真理。
托马斯进而用两种境界来说明本真与真理的关系。像康德那样心存本真的人属于第一种境界。对他们来说只要拥有《仆人》中“清澈的眼和自由的手”(24),寻求真理不过是在身边事物中信手选择而已。以普利瑟赫为代表的野蛮人则属于第二种境界,他们秉持本性,天人合一,无需选择便已拥有真理。
对你来说不是(选择),
而是种子,播撒在一颗心
浅薄的土壤里,那里并不肥沃
但能够种植一种作物,
亦即我掰开的真理面包。(26-30)
对于普利瑟赫来说,作为生命根基的唯一真理就如同种子,播撒并成长在他的心中,那是带有宗教神圣感的至高真理。诗人这种典型的直觉主义观点直接针对的是普利瑟赫与康德之间的观念对垒,希望借此进一步强调自己的认识论。康德固然心存本真,拥有“清澈的眼和自由的手”,但他选择真理仍需要依靠理性思辨。普利瑟赫却无需这么复杂,他仅凭直觉就能够实现对真理的认识。这种观念类似于华兹华斯和爱默生等浪漫主义者的思想,也是托马斯认识论的基础。正如罗素(2003:235)对卢梭笔下野蛮人的评价:“野蛮人(无论何时都)不能理解主体论的证明,然而(他们)却是一切必要智慧的宝库。”托马斯的普利瑟赫无疑就是这样的野蛮人,他知识不比康德,信仰不比身为牧师的诗人,却不但不比他们卑下,甚而还更高贵、更智慧。因此,文明人应以野蛮人为师,而不是将其作为鄙视嘲讽的对象。
五、逝去与复活:普里瑟赫形象的宗教化
通过上面论述我们已然发现托马斯对普利瑟赫形象的塑造是从两个层面展开的:一是将他作为现实人物来描写,以强调他的真实性,增强人物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二是将他逐步升华为一种象征,以彰显其普世性精神价值。作为前者,普利瑟赫要不断成长,如常人一样慢慢变老,直至死亡;而作为后者,他又必须像耶稣基督那样,经由复活而达到永恒。在该系列后期诗歌中普利瑟赫渐渐被神秘的宗教氛围所笼罩,预示着神圣主题的降临。无论托马斯本人的信念多么坚定,随着在机器世界强力冲击下威尔士乡村传统的全面崩溃,他的普利瑟赫也难逃消亡的命运,诗人不得不为普利瑟赫准备后事。该系列的最后一首诗歌《逝去?》就像一篇写给普利瑟赫的悼词。
他们会否在将来某个场合,
看着被践踏的耕地说:
这就是普利瑟赫的家乡?(1-3)
这是诗人以一贯追求的质朴、冷峻的风格为普利瑟赫家乡书写的一首挽歌。诗人在诗中为传统威尔士乡村的消失而哀叹,这是在哀挽一个传统的终结,也是在追索代表这个传统的普利瑟赫的最终命运。诗人无奈而悲凉地看着那些乡民“咧嘴微笑/以回报那些花在他们身上的/钱”(13-15),而他们中间再也寻找不到那位洒着汗水默默地接受生活,满足于“贫瘠的土地、黑色的荆棘和空旷的天空”(21)的普利瑟赫。这篇悼词并非仅仅是针对普利瑟赫个人,而更多的是针对他的家乡。正如克里斯托弗·摩根(Morgan,2003:114)所说,最终逝去的“不仅仅是昔日的这片土地,甚至也不仅是曾经劳作于这片土地上的族类,而是两者的合体以及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关系”。
树篱连根拔除,
围墙也不见了,一个移动的民族
乘着飞快的拖拉机
来去匆匆;林立的天线
仿佛悄悄入侵的舰队,
未被察觉,锚定在
受财政资助的山涧。(4-10)
普利瑟赫是否真的已经逝去,就诗人本人塑造该形象的动机与目的来看,这的确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普利瑟赫和他的族类的确也必须脱离那个已经由机器主导,被物质主义裹挟的威尔士乡村。因为那里篱墙已经不见,土壤已然枯竭,昔日的一切全变了模样,他们传统的栖居之所已经消失。如果是动物,不迁徙就意味着灭亡,而作为人类的他们可能迁徙,更可能就地选择另一个灭亡的方法,那就是变成彻头彻尾的新人,融入到人类异化的洪流,湮灭于机器与物质世界之中。果真如此,普利瑟赫便是从肉体到精神的全面死亡。但事实上诗人在诗歌中给出的种种暗示却让读者联想到普利瑟赫的复活。因为基于先前对普利瑟赫的反思与重新认识,诗人对普利瑟赫的敬仰之情越来越强烈,他不愿也不会让普利瑟赫以脱离人之根本的方式逝去,而是竭力把他的逝去描绘得如基督受难一样神圣而肃穆,以暗示其精神的长存。
普利瑟赫诗歌中的宗教气氛是在诗人的一步步铺垫中渐渐展现出来的。诗人从没有简单地将普利瑟赫的沉默寡言归结为愚昧、无知,反而就沉默本身的内涵展开思索。这与诗人的宗教诗歌中对隐身上帝的思索相契合,从而将人性探讨与追寻上帝联系起来,赋予普利瑟赫形象神秘的宗教色彩,如对《最后的农民》中那位农民脸庞的描写。
他的脸总是从外面被照亮,
白天是太阳,夜晚是红红的炉火;
内里却黑暗空洞。(11-13)
这黑暗空洞的脸庞是极度沉默的表现,它作为普利瑟赫的典型表情一直延伸到诗歌《面孔》之中。这首诗预告了普利瑟赫的死亡,因此可被解读为诗人与普利瑟赫的告别辞。诗中的普利瑟赫颇像受难时的耶稣,被撕裂的手暗喻耶稣被残忍钉上十字架,普利瑟赫与其一样肉体虽遭残害,精神依然永存。而无所期待的目光再次暗示极度的沉默,让我们联想到耶稣受难时失色的眼神和他向上帝发出的最后呼唤。无所期待可以解读为无需期待,因为让耶稣绝望的上帝其实就在他身边。
我能看见,他无所期待的
目光,跟雨水一样无色。
他的双手被撕裂,但精神
依然存在。(19-23)
绝望即必然,乃耶稣履行使命的必然途径,也就是说耶稣必死,也必复活。因此,耶稣所需唯有信念,而不是期待。这也恰恰是诗人对普利瑟赫的期望,普利瑟赫的生活境况(包括他的持久苦难和些许快乐)是自然(或上帝)的赋予或命定,是他持守人之根本的必然途径。如基督一样,普利瑟赫也面临着人生的必然,唯有信念,而无所期待。普利瑟赫的坚定信念及其与基督的认同在该诗下文得到了强化。
他会继续下去,肯定会的。
……心灵画廊的
墙上,那张以荒山为画框的
脸,虽不光彩照人,
却坚定如土地。(25-30)
鉴于这首诗歌被收录于诗集《皮亚塔》(Pieta意为圣母怜子像,是圣母玛利亚怀抱圣子尸体的景象),其中描写的荒山无法不让人联想起诗集的标题诗《皮亚塔》中那座圣山。诗中画面的远景是起伏的山峦,它们“簇拥在天边,/远远注视”(3-4)近处这静穆之景。
高耸的十字架,
阴森,无人
思念身后
处子柔怀中的
圣体。(6-10)
在这些宗教隐喻中,普利瑟赫像圣子一样蒙受着上帝的荣光,葆有的不是肉体而是精神。在《坟墓》中普利瑟赫终于如耶稣一样,以肉体的消失赢得了精神的复活。普利瑟赫虽然已被埋葬,在那碧草下面变成一堆白骨,但却又让他化作“历史风景中的/一颗树”(14-15),在“年轻希望的/绿叶中复活”(15-17)。树的意象得到了升华,它不仅象征着强大的生命力,而且象征着普利瑟赫的死而复活,从而进一步将普利瑟赫身上所体现的原始人性神圣化、永恒化,表达了诗人对原始人性永不泯灭的坚定信念。
六、结语
崇尚应用技术和过于发达的物质文明扭曲了原始人性,导致了整个社会的精神萎缩和生命力的缺失,而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人们之所以在灵与肉两方面都纯粹强健,充满活力,是由于他们更为贴近自然,并与现代文明保持相当距离,原始人性未遭泯灭。普利瑟赫及其族类虽谈不上完美,却因为葆有原始人性而在多种层面上表现出比文明人更为高贵的品质。首先,他们是自然的守护者和再生产者,而来自文明世界的人们却只想掠夺资源,消费自然;其次,野蛮人性情淳朴,知足常乐,因而内心世界宁静平和,而这正是那些被物欲挟持,在喧嚣和焦虑中挣扎的文明人无限渴求却很难寻回的境界;再次,野蛮人率真、质朴的性情也是对文明人矫揉造作的强烈回击;最后,他们在严酷的环境中培养成了坚韧、顽强的品质,使他们在面临困境甚至灾难的时候表现出比文明人更强大的生命力。野蛮人的上述高贵品格是他们持守人性的根本结果,他们的生命实践告诉我们人性即真理。
注释:
① 古希腊神话中宙斯用洪水毁灭了人类,幸存的丢卡笠翁和皮拉夫妇受神谕用向身后抛石的方法再造了人类。
[1] Brown, T. 2006.[M]. Cardiff: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2] Drabble, M. 1993.[Z].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Dyson, A. 1981.[M]. London: Macmillan Press.
[4] Ellingson, T. 2001.[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5] Morgan, C. 2003.[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6] Rogers, B. 2006.[M]. London: Aurum.
[7] Thomas, R. 1997.[M]. J. Davies (trans.). London: J. M. Dent & Sons.
[8] 罗素. 2003. 西方哲学史(下)[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Noble Savage: The Prytherch Figure in R. S. Thomas’s Poetry
JIANG Shi-chang
Prytherch, a savage-like Welsh hill ploughman, is depicted by R. S. Thomas as a symbo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land. Nature endows Prytherch and his kind marvelous living and self-mending ability, making them the healer of human trauma and the rebuilder of a new world. The poet aims at the praise of human nature and the primitivity of life to appeal to the return of humanity of the alienated people.
Prytherch; noble savage; humanity; primitivism
2018-07-04;
2018-08-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空间理论视阈下英国田园诗歌研究”(13BWW051)
姜士昌,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比较文学
I106.2
A
1008-665X(2018)5-007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