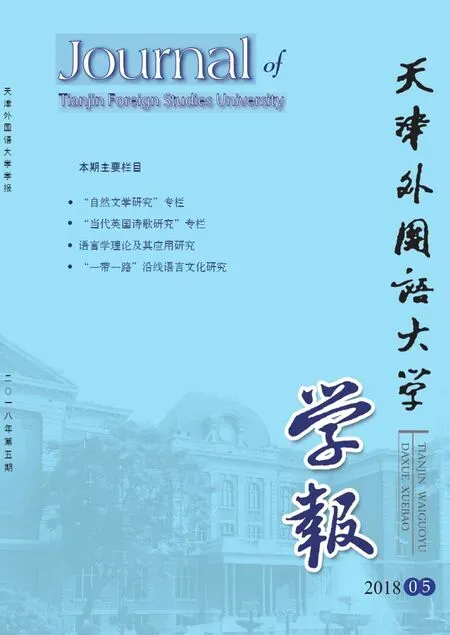美国自然文学中的水世界——溪流与海的生命书写
赵晓霞
美国自然文学中的水世界——溪流与海的生命书写
赵晓霞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70)
美国自然文学中有关水的写作深受田园传统、超验主义和东方文化的影响。无论是湖泊、溪流还是海洋,以水为对象的写作强调动静结合,意图呈现自然之景形态的丰富和音乐的美感。此类作品在自然文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并延伸了荒野的内涵,体现了荒野的价值。水世界中蕴含着自然的声音,给予人们心灵的启迪。从亚利桑那出发,经由弗吉尼亚到马萨诸塞,选取大峡谷、汀克溪、科德角的河海之景,分析经典水主题的写作,进而将个人生活置于一个更为广泛的背景下展开探索。溪流绵延数里,海洋广袤无垠,从美学和伦理的角度提示着人类如何在多变的现代社会中寻求一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
美国自然文学;荒野;水;三维景观
一、引言
美国自然文学(nature writing)作为一种文学流派受希腊田园文学、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影响,在超验主义思想指导下吸收了东方文化和现代科学理念,植根于美国本土,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向纵深发展,日趋繁荣。美国文坛涌现出了大批自然主义者和博物学家,其中集大成者包括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约翰·缪尔(John Muir,1838-1914)、玛丽·奥斯汀(Mary Austin,1868-1934)、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887-1948)等。作家们深入自然,撰文结社,引领文学文化思潮,促进了公众意识的觉醒以及社会的进步。步入20世纪下半叶,爱德华·艾比(Edward Abbey,1927-1989)、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1907-1964)、劳伦·艾斯里(Loren Eiseley,1907-1977)、劳伦斯·比尔(Lawrence Buell,1939-)、安·兹温格(Ann Heymond Zwinger,1925-2014)、安 妮·迪拉德(Annie Dillard,1945-)等当代作家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进一步扩充了自然文学的内涵,使其呈现新特征,蕴含新希望。
在美国自然文学中荒野是一个重要概念。对于早期移民、探险者、旅行家来说,荒野是和人相分离的,它慑人心魄,神秘莫测,似乎待人发掘,又拒人于千里之外。在新大陆的天地中人们感到喜悦振奋却又迷茫不安。受到自然的感召,具有审美意识的作家深入荒野,用细致和诗意的笔触描绘自然。作家们或在沙漠里感受孤寂,或在花园里流连忘返,或在乡村里观鸟,森林间与树为伴,深山中聆听郊狼嚎叫。而在亲近水域之时作家怀有出世之心,逐渐实现了自然和人的融合。借助科学事实和设备作家们仔细观察,结合自身阅历,运用想象,将溪流与海拟人化,向读者传达水世界的信息,引发读者共鸣和联想。在西方传统哲学的框架下,美国自然文学作家借鉴东方视角,结合神话传说,在池塘小溪旁聆听自然之声,在河流海洋中思索文明之疾,从美学和伦理学的视角展现了意蕴深厚、相互交织的声景、心景和风景,并将人类传统伦理道德观扩展至动植物、大地以及居住的地球①。自然文学充分体现了文学的连续性和适应性,丰富了文学的美学价值和道德内涵。
学者程虹(2015:13)认为:“我们通常说,文学就是人学。但是自然文学不同于其他文学形式,在自然文学中,人作为主人公的概念被淡化,作品焦点是农村和荒野,而并非城镇和都市。”在小说中河海是主人公生活和际遇的主要场域,为事件发展和人物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背景,而在非虚构类作品中河流和海洋成为了作家主要描写的对象。通过篇章安排、写作技法组合以及语言创新,文学作品中的水世界精彩纷呈。学者们尝试对河海书写进行了归类探讨,克里斯·布洛克和乔治·牛顿(Chris Bullock & George Newton,1992:73-74)在《河流荒野:北美河流写作》(A Wilderness of Rivers: River Writing in North America)一文中指出:“河流主题写作呈现多种结构,总体来说,按照松散的时间顺序或直接连贯是最常见的结构安排。”“河流写作中最有趣的闪光点在于将运动的体验、流动的快意、界限的消失诉诸于语言。”查尔斯·道森(Charles Dawson)在博士论文中分析了北美河流写作中的重要作家。科学研究拓展了人们对海洋的认识,更加关注地球面临的生态问题,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参考。随着国内外对河海研究兴趣不断加深,经典文学文本重回视线,如梭罗所著自然文学经典作品《瓦尔登湖》(,1854)营造了澄澈纯粹的净土,亨利·贝斯顿(Henry Beston,1888-1968)的代表作《遥远的房屋》(,1928)传达出自然壮阔的声响,艾比的《漂流而下》(,1982)对比荒野的生机与城市的没落,卡森笔下的海洋三部曲(,1941-1955)②则显示出水世界的磅礴多变。
追溯自然史题材作品,作家详尽地描述了实证洞察的过程,语言多是描述性的。在当代自然文学中作家往往通过美术、地理、历史、生物、人类学等跨学科知识表现水主题。而聆听音乐家的作品则让自然文学家从情感、理性、指示、内涵等方面寻得共鸣和紧密联系,呈现出自然文学的音乐性以及别具一格的审美趣味。在跨学科的视阈下,自然文学家热诚地投身荒野,通过诗意的语言为读者呈现具体的水世界的同时,无形中展现了一种广阔视角下充满道德选择的人类行为。熟悉法国文化的贝斯顿、擅长风景写生的兹温格以及充满奇思妙喻的迪拉德笔下的水世界具有异同之处,展现了荒野的引人入胜、变幻莫测以及生命的特征和自然隐含的法则。本文跟随上述三位自然文学家的脚步,从自然文学的三维景观:风景、声景及心景(程虹,2015)出发,分析河畔写生、海边独居的文本,探讨作家和水不同形式的互动,试图呈现作家笔下水的流动美感以及灵动之声,总结与水相关的作品在文学表达中的内在韵律,探索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途径,从美学层面关注水主题写作的音乐性和诗意表达,从道德层面关注水主题写作对人类生活精神世界的影响,促进公众环保意识的提高。
二、水之身影
贝斯顿、兹温格、迪拉德三位作家对自然都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善用类比阐释自然,尽管受到荒野条件的制约,他们仍然深入未知的自然,结合对星体、光、风、岩石和其他自然物的具体观察,构筑了一个个五光十色、变幻莫测、吐纳万千的水世界。
1 深入峡谷
从一年冬季到次年秋季,兹温格在其获奖③作品《深入大峡谷》(,1995)中技法娴熟地向读者展示了精彩纷呈的科罗拉多大峡谷的河流世界。借助作家本人在书中精心绘制的地图以及传神的线条勾勒,读者开启了非比寻常的河流之旅,获取了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作家对自然现象的科学解释使之在美国自然文学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一席之地。兹温格描写了大峡谷秋季的河流阶地④和乌卡⑤三角洲(river terraces and Unkar Delta)。从麓原的构造和形成年代可以读出科罗拉多河流经的位置和高度。兹温格(Zwinger,1995:216-217)向读者解释了河流的侵蚀和沉积作用,系统地刻画出大峡谷的环境:“广袤无垠的大峡谷充满着横扫一切的力量。无论多么优雅,视域宽广的图片都不足以传递河流风景的精髓:水流的畅快,柿子树和薰衣草的芳香,货运车般哐当作响的激流,或者是沙堆的沉静,鹪鹩的欢鸣。春天沙滩的凉爽,松脂灌木在指尖留下的余味,流水的刺骨,岩石的灼热,每一刻都充满变化。在这里,风景是灵动的:向前行进,调动变换,累石积土,从不回头,人们被太阳烤灼的视网膜上留下了闪回的丰富图像,而脑海中只能记住它绵延不断运动过程中的片段或剪影。”根据考古学家在1966-1968年的艰苦研究,兹温格(Zwinger,1995:218-224)划分出公元900-1150年间三角洲人类定居的四个时段,每个时段伴随狩猎、采集、农耕文明的发展,留下了独特的建筑和工具,改变着峡谷的地貌,与气候产生相互影响。作家在古人类旧址久久停留不愿离去,怀古思今,在脚下的土地留存了生命的印记,顺着流水的方向,寄托了对未来的展望。
2 溪畔朝圣
迪拉德的目光则被汀克溪的景象深深吸引,在《汀克溪的朝圣者》(,1974)中湍急的河水倒映着河岸的枝条,斑驳褪色,像水蛇般颤动不停。迪拉德(Dillard,1988:2-4)在开篇便创设了一种神秘的氛围,在弗吉尼亚蓝岭(Blue Ridge)的溪谷中,作者伴随着清晨的阳光醒来,却发现猫爪在身体上留下了玫瑰般的印记,像是徽章,又像是污渍,使作者联想到神秘、美丽和暴力。在她看来,汀克溪的每一秒都是鲜活新奇的,含有神秘而持久的创造力,隐含着天意,这里充满了前景的模糊、命定的恐怖、当下的逝去、自由的镣铐与完美无缺的理想化。可以推测作家带着患病的躯体走进自然,感受到的水之风景并不那么令人愉悦,但是在水畔她得到了和兹温格相似的启示。她引用了一句拉丁名言:“抓住当下”(Carpe diem),说明自然中的奇迹转瞬即逝,珍贵非凡,应该倍加珍惜。在自然中迪拉德的双眼成为放大镜,通过她的描述读者得以在细微之处品味自然。她还对时间和空间作出了新的诠释,认为“流动的活水和光影构成了一个无尽的世界,源头是如此的神秘,使其不断更替,持有崭新的面貌”(ibid.:104)。在水中人们能够借助光的折射看见彩虹,这兴许是上帝的旨意在人间的显现,提示人们不要忘记同上帝的约定。迪拉德在书中引用了梭罗、卡森、爱德温·韦·迪尔(Edwin Way Teale)、瓦莱丽·艾略特(Valerie Eliot)、托马斯·默顿(Thomas Merton)的作品,展现了丰富的文学传统。书中还含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亚瑟·斯坦利·爱丁顿(Arthur Stanley Eddington)、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洛伦·艾斯利(Loren Eiseley)等科学家的论点,文学与科学相结合使作品更具现代感和严谨性。
3 海边独居
前面两位当代作家以女性特有的视角书写溪流,而要客观全面地了解水世界,前辈作家贝斯顿及其朴素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不容忽视。罗伯特·芬奇(Robert Finch,1943-)在1988年再版的《遥远的房屋》序言中写道:“贝斯顿善用语言凸显自然事件的特质,呈现海洋史诗般的英雄事迹。”(Beston,1992:xxi)作家巧妙运用如诗般文字的韵律唤起读者的感知力,带给读者想象和思考的空间。“梭罗带着笛子在瓦尔登湖畔生活,而贝斯顿则把风琴带去海滩”(ibid.:xiv)。作家采用季节交替的顺序进行描写,含有丰富的隐喻,风格和意象的运用充满了力量。毫无疑问科德角的一年是对原始仪式感的寻访、追忆和再现,体现了自然的周而复始与生生不息。
在“冬季、海洋和鸟类”一章中,通过海浪的嘶吼贝斯顿感知到冬天的来临。海滩上作家为鸟类机械一般精妙的行动力所震撼,进一步指出人类不应自恃甚高,用自身的文明去衡量动物界,古老的动物远比人们想象的要进化完整而成熟(ibid.:23-25)。在“壮美的海滩之夜”一章中作家反省现代文明排斥自然的倾向,在机器时代人们选择与自然的夜间为敌,原始时期人们害怕的只是夜间动物和不为人知的力量,而到了现代社会人们似乎更加厌恶夜晚本身,变得更为胆怯。从时间层面来看,夜晚和白天一样,正如车轮的两面。脱离夜晚则无法品尝夜的诗意,感受夜的性格。从空间层面来看,结合海滩的夜间见闻贝斯顿发现不同于海洋的热闹,沙丘如同丝绸一般华丽柔顺的运动则是无声的。在风的作用下沉默的土地和有声的大海形成了鲜明的比照,但却相互依偎,无可分割,构成了一个完整立体的系统。海滩、泻湖、斜坡、高地与远方的天际、下降的太阳和起伏的沙丘浑然一体,动静结合,高低相依,形成了有机的生态整体。而群鸟在天际留下的运动轨迹正是自然难以抗拒的一致性和整体性的一种暗含解释(ibid.:165-174)。贝斯顿质朴的生态整体观对后世作家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心灵感知
以上三位作家对溪流和海的描写不拘泥于自然形象的刻画,而是深入结合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自然进行着心灵的互动,让思绪徜徉在水世界中,借助神话引导读者领略自然界无形的魅力。
1 神性意旨的文字传达
作家进入荒野,用独特的心灵感受自然,笔下的水世界是带有浓厚的精神色彩的。兹温格和迪拉德作为女性作家拥有过人的胆识和智慧,同时也更善于表现自然的千面多姿。兹温格和贝斯顿忘我地投入到荒野之中,不顾环境的艰苦,甘愿忍受孤寂,坚定而充满勇气地追寻生命的美好与感动,记录自然界的奇迹,充满智慧地表达生活的意义。而迪拉德和贝斯顿沿袭爱默生超验主义的文风,从哲学和神学的角度描写自然现象,行文中带有隐秘和微妙的特点。三位作家创造性地运用语言,深入浅出地阐发了自然传达的观点。
如同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达芬奇,兹温格从科学和艺术的角度热忱地钻研自然的模式和过程,对自然的解释图文并茂,客观明了,推动了人们对大峡谷的了解、对自然的认识,为科学考察作出了贡献。而她在这一过程中以文学家的身份探讨动物实验、水坝修筑、干预捕食等人类行为,流露出与自然难舍难分的深厚感情,显示了道德的力量。在大峡谷蜿蜒的流水中兹温格受到了雅典娜女神的眷顾,充分发挥了人类的智慧和技艺。
《日晷》()杂志于1840年7月1日首次出版,集中体现了超验主义的文学成就,倡导浪漫主义对灵性、精神以及内在真理的追求。而迪拉德的语言风格自由,注重文本的前后呼应。其文风受到超验主义的影响,承袭了爱默生玄妙的说教风格,又显示出如同孩童般天真而大胆的新特点。当她在汀克溪畔朝圣时仿佛受到了黛安娜女神的眷顾,使其免受疼痛的困扰。她直言按照四季的变迁书写自然平淡无奇,并试图从正反两极去观摩、探寻自然。
梭罗在《康科德和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1849)中实践了超验主义观点,坚持艺术和生活进行融合。“艺术不应是普通意义上驯服的体现,自然也不是普通意义上野性的象征。人类理想的艺术作品要么是野性的,要么是自然的,关注的都是生活的积极面。”贝斯顿承袭了梭罗的艺术观点,在科德角的海滩上犹如和象征着力量、勇气、意志的罗马神赫拉克勒斯(Heracles)亲密交谈过,将野性十足的自然淋漓尽致地呈现给读者,为人类生活注入了精神的活力。
2 栖居自然的美学体验
在栖居自然的过程中,人类文明的痕迹弱化,产生了一种清新的美之体验,对人们的生活和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如果说兹温格的作品表现了彩虹崇拜,迪拉德和贝斯顿的作品则分别表现出对月亮和太阳的崇拜。随着河流源源不断从四面八方汇入海洋,海洋又以各种形式同陆地进行着能量交换,融合风景、心景的水世界得以立体化。
约翰·德怀特(John Dwight)在《美学论》()⑥中指出:“美是含有灵魂和道德意义的,它指向人的内心世界,是一种区别于物质世界的精神实质。”艺术来源于“艺术家将自我提升到超我的需求,试图与宇宙以及与难以言说的存在融为一体的需求”(Koster,1910:29)。自然文学家笔下河海的影像正是一面反映人精神境界的镜子,给人以美的体验。他们并没有逐条提出刻板的美的标准或者范式,时而婉婉道来,时而直抒胸臆,刚柔并济地唤起读者对自然之美的感受力,流露着道德的启示。
3 多元共存的伦理延续
水的形态多样,被各国文化赋予了圣洁的含义,如西方世界的洗礼、具有净化作用的印度恒河水、观音玉净瓶里的圣水等。河流不向高位,和泥土共存,滋养了万物的生命,它的灵魂虽然无形,但人们总是试图去感知。当陷入迷宫一般的千丝万绪中时,河流会指引人们重返宁静和纯洁的精神世界。而被视为生命起源的海洋隐秘幽深,博大难测,吞吐万物,给人一种无形的约束和无言的警示,彰显着多元力量的平衡与再生。
美国俄亥俄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哲学博士科尼利厄斯·威廉·布朗尼(Cornelius William Browne,2001)在论文《自然文学的经验:实用主义文学生态与20世纪美国自然文学》(Nature Writing as Experience: Pragmatist Literary Ecology and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n Nature Writing)中阐述了20世纪美国自然文学的实用价值,认为自然文学家深入冷静地思考作者、读者以及物质世界之间的关系⑦。纵观水主题文本,作家通过物质性描写、个体经历以及文化寓意书写体现了与荒野保护一脉相承的思想,推动了文明的进步。
四、水之乐音
文学的雅趣如同春风化雨,浸润身心。通过书写溪流与海之歌人们把握自然的脉搏。透过作家的文字倾听自然之声,人们在文明中求得身心平衡。
1 叙事组曲:河流吟唱的超验之歌
兹温格将四周的动植物视为朋友,充满好奇地展开探访之旅,书中不乏亲昵、自由、浪漫的语调,而对鸟类歌声的描写更像柔和的旋律跃然纸上。作家在孤寂中发现美,沐浴在阳光之下,参与自然的盛典。
河流通过叙事曲调告知作者季节变换,动植物迁徙,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它们幽深的另一面则传达了寂静之声,河流在人们的心间流淌,正如艾比(1991)所说:“像河流一样去感觉”,即放低自己,换一个视角感触世界,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充分体会自然界的其他物种优于人类的特质,进而认识到人的局限性,摒弃自大、自负的心态。在沉静中体会物我合一的境界,用心聆听河流无声的诉说。历经春种冬藏,沧海桑田,仍然记录着世间的平静与流畅、变动与阻塞。如果人类对河流的经验之歌置之不理,仅从自身利益、好恶出发,就会打破自然顺序,干扰自然界的平衡,最终危及自身的生存。在河流的世界,时空是连续而充裕的,人们可忘记尘世的烦恼,静静地感知和冥想。作家们对人类活动产生的作用进行解读,潜移默化地让读者领悟河流的诗意以及自然是精神之象征的超验思想。
2 变奏歌谣:溪畔演奏的异幻之歌
迪拉德在溪畔的朝圣使她仿佛化身为一只目光锐利的鹰,观察着奇幻的世界,聆听着多样的声音。书中描写了蝗虫的吵闹、鸣蝉的不休、鹑声的哀怨,展示出自然粗糙、阴暗、可怖的一面。作者没有忽视青蛙、蛇、螳螂及其他小昆虫等并不太招人喜欢的生物。它们是自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蕴含着神秘的力量,使人们为之警惕。
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曾说:“没有人能够两次踏入相同的河流”,强调了变化是宇宙万物的规律。迪拉德在《汀克溪的朝圣者》中描写了自然界无情而凶残的一面,在表达人与自然的矛盾时,她使用传统的《圣经》典故诺亚方舟以及鸽子、洪水的意象,说明这对矛盾古已有之,只是在当代技术革命的背景下形式发生了变化。作者在第九章中写到洪水之后旺盛生长的蘑菇既可以被看作自然的预言,也可被看作自然的谜语(Dillard,1988:149-160)。迪拉德的言辞智术犹如乔治·格什温(George Gershwin)的蓝色狂想组曲(),展现了人与自然易变的一面。
《汀克溪的朝圣者》和《在康科德与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两本书中均含有作家对河流进行的诗意解读。作家诉诸悲伤的力量,试图唤起读者的共情能力,在困苦和荒凉的环境中寻得存在的价值,在充满危险和消亡的世界中重获生存的安定。人们无限膨胀的好奇心和欲望推动着现代技术日新月异的变化,但同时生存环境也存在着一些不稳定的因素。此刻水世界是笼罩在迷雾和朦胧月光中的,读者置身于正反两极交织的漩涡中,产生怜悯、敬畏之情。此时文字犹如飘散在空中的安魂曲一般对亡灵予以慰藉和敬意。
3 交响乐章:海洋谱写的和谐之歌
以海洋为伴的作家将孤寂视为精神疗愈的良方,同时也是一种有意的选择。在《遥远的房屋》中贝斯顿注重表现荒野磅礴的气势,模拟海洋的声音,使读者仿佛置身于宽广的礼堂,聆听着声部交织、气势恢宏的交响乐。贝斯顿的文风同德彪西(Claude Debussy)谱写的海洋三部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充满史诗感,似乎重现远古的战争,使人们的身心为之颤动。“自然界最基础的三种声音由雨声、原始森林中的风声和远海的声音构成”(Beston,1992:43),而人们则在此基础上编织着自己的声音。《遥远的房屋》构筑的不是一个只存在于纸上的世界,而是一个充满立体声环绕的多维景观。相比河流之声的细腻、隽永,海洋之声则更为粗犷、浑厚。
贝斯顿融入海洋的世界,从中袭得吟游诗人的气质,通过展现海洋不同声部谱写了一曲充满普世价值的交响乐,对当世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维持生态平衡予以无限启迪。海洋的另一端似乎遥不可及,奇异难测,引人遐思。迥然不同的文明被海洋所连结,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海洋传递普世之爱的协奏曲得以传颂。
五、结语
自然文学家感情真挚地为自然发声,说明荒野与文明密不可分。而水的足迹和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它不仅是人类生活必不可少的物质,而且在精神上带给人们洗涤或冲击。梭罗和艾比将河流视为手足相连的兄弟,迪拉德和兹温格将河流视为一面还原世界的镜子,贝斯顿和卡森凝视海洋的包容性,充满了严肃的问题意识。贝斯顿、兹温格和迪拉德的经典作品既有各自的特点,又有相通之处。从写作风格来看,三位作家独树一帜。兹温格的作品充分体现了人类的智慧与艰苦卓绝的探索,迪拉德的作品充满了变动的不确定性,体现了物质世界中个体为生存而奋斗的状况;贝斯顿的作品则充满了原始的仪式感,用语自然,风格雅致,呈现出戏剧般跌宕起伏的文学品味。从写作内容来看,作家们着重表现荒野的形式和精神,体现了对自然的热爱。写作的初衷或许都是为唤起人类对赐予生命之水的珍视。
人们欣赏风景之美,聆听自然之声,塑造生活的心境。兹温格和迪拉德通过神秘而美丽、凶残而仁慈的河流告诉人们既要充满敬畏,学会克制,同时又需要人类的智能,使世界充满善意和美好的欢愉之声。贝斯顿则提醒读者海洋和上古的联系,连接了人与自然。芬奇指出:“《遥远的房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经久不衰的原因在于它强有力地提醒人类,在电器化时代,人类仍然无法脱离地球深层的、持久的韵律,我们赖以为生的,正是地球母亲基础性的完整与镇定。”(ibid.:xxviii)。作家们正是精准地传达出或隽永或宏大的自然之声,不约而同地发出呼吁,从生态整体出发共同守护我们的地球家园。
作为一个开放的文学流派,美国自然文学在当代仍然充满生机。自然文学家的经典作品历久弥新,其审美意蕴和伦理指示得以持续发展。当代自然文学引入生态学的概念,成为自然文学的一个新特点。进入新世纪现代人开始关注在人工智能盛行的当代社会技术方案能否完全解决人类生存所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人口快速增长、化石能源使用、气候变化等社会、环境议题使得自然文学家进一步探索荒野,作为人类行为的参照。
浩瀚的宇宙中充满生命力的地球面积有七成左右被水覆盖。作为地球社区的成员,人类和其他生物一样无法脱离水而生活,与水拥有相通的灵魂。自然是人类的灵魂伴侣,人类的感性和理性以及智力、道德、良知使其能够察自身不足,从而洞悉自然,与之和睦共处。水的音乐和人类的音乐是一致的。如果人类善于倾听生命之水的召唤与声音,沿袭自然,学会与自然融为一体,或许能够减少物质世界的藩篱,求得精神境界的升华,通过感知万物灵性的存在接近和谐、健康、稳定。
注释:
① 参见利奥波德的《沙乡年历》(,1949)。
② 分别为《海风下》(,1941)、《我们周围的海》(,1951)和《海之滨》(,1955)。
③ 美国西部图书奖创意非虚构写作类。
④ 河流阶地即由河流作用形成沿河谷两侧伸展且高出洪水位的阶梯状地形。阶地高度由阶地面与河流平水期水面间的垂直距离来确定。
⑤ 作者随后在书中解释“乌卡”一词来源于印第安派尤特语,意思是红色溪流或红色石头。
⑥ 伊丽莎白·皮博迪(Elizabeth Peabody)时任编辑。
⑦ 可参考美国康奈尔大学英语系的迈耶·霍华德·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教授写于1953年的《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
[1] Abbey, E. 1991.[M]. New York: First Plume Printing.
[2] Beston, H. 1992.[M].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3] Browne C. 2001. Nature Writing as Experience: Pragmatist Literary Ecology and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n Nature Writing[D]. Ohio University.
[4] Chris, B. & N. George. 1992. A Wilderness of Rivers: River Writing in North America[A]. In S. Zeveloff, L. Vause & W. McVaugh (eds.)[C]. Nevada: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5] Dillard, A. 1988.[M].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6] Koster, D. 1910.[M].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7] Zwinger, A. 1995.[M].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8] 程虹. 2015. 宁静无价:英美自然文学散论[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9] 程虹. 2015. 自然文学的三维景观:风景、声景及心景[J]. 外国文学, (6): 28-34.
Water World in American Nature Writing: Life Writing of the Creek, the River and the Sea
ZHAO Xiao-xia
Writing on water in American nature-oriented literature is influenced by pastoralism, transcendentalism and orientalism, which is an extension of wilderness theme and demonstrates the value of wilderness. Ponds, lakes, rivers, oceans speak and spark in nature writing, creating a moving world of tranquility, diversity and musicality. In the water world, we can hear the sound of nature to give us an endless stream of inspiration. The examination of writings on Grand Canyon, Tinker Creek and Cape Cod offers us a chance to place our personal life in a larger context. From Arizona, through Virginia to Massachusetts, the classic writings about water can provide people an insight into the problem of how to maintain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with nature in an ever-changing modern society from the ethical and aesthetic perspectives.
American nature writing; wilderness; water; the three-dimensional landscape
2018-07-31;
2018-08-26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态文明价值导向下的美国自然文学研究”(18WXB007)
赵晓霞,硕士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美国自然文学
I06
A
1008-665X(2018)5-00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