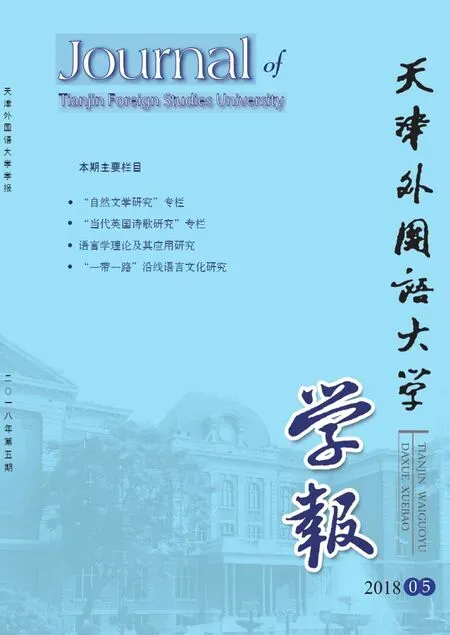北美原住民自然思想基础上的群体表演艺术——后殖民现象下的回望
陈彦君
北美原住民自然思想基础上的群体表演艺术——后殖民现象下的回望
陈彦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70)
北美原住民自然神话传说基于大地母神、万物有灵论、动物图腾观和能量守恒等理念传达出原始部族对自然的感恩与崇敬,并强调人将自己的身体与自然融为一体,用群体表演的形式回馈自然。可溯源至远古时期的群体表演艺术同样承载着北美原住民朴素的人与自然交流观。从当代原住民文学创作来看,针对后殖民现象,其生活现状和身份认同迫切需要从原住民神话思想和仪式艺术里探寻欣赏自然、尊重自然和维护自然的合理途径,置于全人类亦如此。通过探索自然、人类和艺术三者之间的关系来重新审视群体表演艺术在当今人与自然对话中的价值也显得颇有意义。
北美原住民自然思想;群体表演艺术;仪式;后殖民;身体对话
一、引言
北美原住民在人与自然的相处中衍生出了他们自己的一套法则。古老的自然神话理念在其传统的仪式中得以一一展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界限在这种交融和表达中得以不断消解。当今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仪式群体表演也就架起了人与自然之间对话的桥梁。因为人以身体行为和身体绘画等为呈现手段告知自然得以继续生产作息,而自然也借此融入人的生活中,并强化自己的身份感。
对于原住民的自然理念价值,众多自然文学家都有提及。文学作家玛丽·奥斯汀曾在她的著作《少雨的土地》中赞美了印第安人与其所处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可以说“为工业化社会缓和文明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提供了借鉴”(程虹,2013:151)。加里·斯奈德也向来推崇原始文明(陈小红,2008)。“巴特拉姆、威尔森及奥杜邦等人都赞美人与非人类自然之间的亲缘关系,也因此向美国文学引入了一种原初的生态情怀。”(胡志红,2015:118)爱德华·艾比也强调“维系人类与自然的原始联系”(程虹,2013:283),而这种原始联系就可以从北美原住民自然思想中探寻。这些文明“没有西方那种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也没有指派人类统治非人类世界”(艾布拉姆斯、哈珀姆,2014:199)。由此可见,其古老的自然思想至今都备受关注和肯定。作为他们与自然交流的主要形式之一——群体表演艺术不仅有其思想基础,更有其现实意义。
随着当今殖民统治时代的结束,作为殖民主义的对立面,反殖民主义也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以文化对抗关系为主的新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的反抗延续至今。当代后殖民主义语境下,语言、宗教等文化因素如何影响旧殖民地的土著文化是后殖民研究中的重要领域(任一鸣,2008:4),其中存在许多反对新殖民的呼声,关于流放和寻根的话题也此起彼伏。
原住民(indigenous peoples)作为有过被殖民历史的群体,其文化也逐渐在与定居者(settler peoples)的主流文化博弈中被边缘化,具有跨文化背景的原住民后裔的“身份认同成了一个问题”(Bell,2014:26)。尽管当今他们以及学界在极力以原住民和定居者的关系处理双方的文化冲突问题,但难以避免的是历史上的旧殖民政治压迫已经转换为现在各种形式的新殖民经济和文化压迫。而这种对部分人的压迫又体现在对所处自然环境的压迫上。新殖民的这些特征也是后殖民概念外延里重要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今人类因为发展现代化工业的需要和传统人类中心价值论的影响,对自然界万物长期不合理霸占和利用的行为是人对自然的变相后殖民。后殖民已成为一种世界现象(任一鸣,2008:4)。但人与自然本是平等互利的双方,动物和人类都是这个世界上的主人和资源共享者。正如朱峰(2012:131)所说的物种主义是一种范围更大的种族主义,是一种人对自然的歧视。
由此将后殖民的概念迁移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中去也有了可探究的切入点。从广义上来说,面对后殖民现象,尤其是自然为环境所替代的情况,不仅要关注后殖民社会中人的生存环境问题,还可以在环境公正批评阶段把握住后殖民批评中的占用、身份认同、对话平等和寻根等理念,并将其推广至全球化语境下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我们需要给予自然更多的话语权和空间,因为重新审视自然能促进人类环境的优化。有殖民历史或正受着主流文化和边缘文化冲击的当代原住民作家无论是以强调自己身份的形式,还是以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式,都在他们的后殖民文学作品中反复涉及了上述有关自然和生存环境的类似观点。因为许多北美原住民被迫离开自己原有的住所,经历“身体的空间流放”和“心理流放”(任一鸣,2008:13),他们正通过文学途径找到自我身份和传统,抑或是从古老的自然理念出发弱化自己的边缘危机。全人类都有责任去关注自然,重学古老传统,“保持和传递给后人一个宜居的、多样的、令人愉快的世界”(艾布拉姆斯、哈珀姆,2014:201)。不管是社会形势还是人类呼吁都在发出善待自然的诉求,而源远流长的群体表演艺术或许可以作为一个着手点,联结自然与人类,从古老文明中为原住民后裔文学和全人类的生存,也为当代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汲取养分。
面对这样的局势,“现实生活中的我们依然渴求着能够触动心灵,激活我们感官知觉的形象与故事,饱含情感的话语”(石海毓,2012)。而集中体现群体思想价值,即建立在北美原住民深厚的自然思想积淀之上的群体表演艺术很有可能满足这一需求。“以审美角度出发感受自然需要我们充分调动知觉感官浸入自然。”(Roholt,2017:65)这种规约的艺术正是通过在身体上描绘自然物景,用身体演示自然现象和生产活动等形式,为人类浸入自然提供了一个实体角度,并倡导通过人类的身体实现风景的体验、精神的沟通、情感的交流,特别是感恩与敬意的传达。先从身体知觉出发,再调动人对自然的意识,而不是一味灌输式的说教。原住民仪式研究学者维克多·特纳(Turner,1991:7)指出,他们通过表演“带有一定风格的肢体动作、歌唱具有隐含意义的乐曲来促进他们对这种行为的理解”。
本文以北美原住民神话里的自然思想为基础,结合其在当代原住民文学中的理念绵延和后殖民现象中的人类生存现状,挖掘其蕴含着生态整体主义和生态平等主义的传统信念,包括大地母神、万物有灵论、动物崇拜、图腾制度、能量守恒观以及萨满教信仰影响等,主要探讨北美原住民自然思想的集中体现——群体表演艺术在当今后殖民语境中为人类与自然提供身体对话机制的可能性,旨在说明这种群体表演艺术以北美原住民神话传说中的自然理念为行为根基和活动指南,以身体为艺术载体和交流介质,是与自然展开情感交流与灵魂沟通的有效方式。该身体艺术作为自然理念的具象化表现传递并升华了他们的自然思想,又反过来作用于实际的生产活动。而原住民的后殖民文学不断聚焦于自然神话和现实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群体表演艺术也可以为其文学创作提供新的灵感来源和现实选择。该艺术不仅给自然赋予了新的内涵,也为自然和人类搭起了彼此深入了解的渠道,更可以推进当今人类与自然之间新的相处模式的产生。
二、北美原住民神话文学的自然理念
北美原住民神话文学和古希腊神话、古埃及神话以及北欧神话有着同等的重要性(Bastian & Mitchell,2004:ix)。其自然神话故事因部落种族和地域气候的差异而丰富多样。对比其他神话,其神话传说无过多文字记录,大部分为口头流传至今,所以更需要受到重视和保护。不管是自然现象的解释也好,还是对自然万物的探索也罢,神话中的概念表达了北美原住民的自然观。这种早于殖民时期的自然理念还尚未受到入侵与改造,因此具有探索与保护意义。
动物是血缘同胞,其神力于人类有恩,这种自然观深刻地影响着北美原住民。神话中描写了大量具有神性的动物。原住民敬慕动物身上的神力,认为动物与人一样是大自然的邻居与资源的共享者,具有人形,可以说人话(周柏冬,1984),人和动物之间可以相互转换、成亲,血脉彼此相连,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关春玲,2006)。达尔文也认为,动物和人类一样具有情感和记忆,能够推理判断。原住民神话中有许多与北美西部原野上的郊狼(coyote)有关的故事传说,纳瓦霍人(the Navajo)和基奥瓦人(the Kiowa)对此也各有特定叫法。郊狼往往被视为具有魔力可以自由转换的文化英雄,许多原住民部落相信郊狼将火带到人间,划分出四季,教会人们如何捕捉、烹熟鲑鱼,并让人们劳动作息,承受苦难,还与欧洲人的起源关系密切。原住民神话还赋予郊狼掌控死亡的力量,以避免人类过度繁衍(Bastian & Mitchell,2004:77)。原住民对于死亡这种生命现象的解释也颇具现代科学意义。在其他故事中郊狼还是人类性愉悦体验的启蒙和惩治邪恶力量的正义使者。他①通过神力创造了山川河流、峡谷瀑布和岩石河岸,还根据动物特性给其他动物命名(ibid.:78-82),可见郊狼这一形象在原住民神话中的地位。不同于现代社会对龟的普遍看法,在原住民神话里龟代表着极具力量的守护者和驱逐怪物的勇士,这和萨满教文化有关。神话中聪慧的龟一路高歌哼唱,振奋士气,在最后的时刻机智挣脱了敌人的牢笼(ibid.:212-215)。斯奈德也因崇尚原住民文化中龟的精神,以与原住民同样的视角将美国称为龟岛。还有神熊能预料人类行为,风之马(wind horse)为人排忧解难等。图腾文化中人兽成亲也常常会出现,“将特定的自然物看作同胞”,多是“近似父亲、祖父那样的存在而亲近的习俗”(山崎正和,2014:34)。
在北美原住民眼里动物便是具有超力量的化身,人与动物可以相互转化,动物创造了世界,帮助人类更好地生活,也可以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而人可以从动物身上获利,只要听取动物的建议,但不能过度滥用。他们并没有狭隘的唯动物至高无上的二元论思想。周柏冬(1984)指出:“印第安文学的另一特点是现实与超自然紧密结合在一起”,他们并不是无端地对超自然力量盲目崇拜,而是扎根于现实生活。对动物的这种态度也体现在他们的图腾文化里以及身体绘画上。鉴于这种自然与人平等互助互通的神话立场,另一个自然理念——万物平衡,即要遵循规律,取之有道,用之有节,与此也大有关联。
切罗基人(the Cherokee)流传着关于雪松的神话故事。人们向造物主祈求取消黑夜,而黑夜真的消失后人们却因为白天的燥热争吵不断,于是又请求造物主收走白天,留下黑夜,而这却导致许多饥寒交迫的人一个个失去生命。这些逝去的人的灵魂便被放入雪松之中。人们意识到自己的过错,积极祈求恢复日夜更替的自然规律。由于各族之间的地域环境差异,同一个物种在另一个部落却有着不同的含义。曼丹部落(the Mandan)的雪松传说与感谢美国北部造物主有关。一个开创了美国北部的独行者(Lone Man)在护送因欲望膨胀而要去赴一场盛宴的人类的过程中披荆斩棘,除恶护良,而最终自己变成了一棵雪松(Bastian & Mitchell,2004:95-97)。在切罗基人的神话故事中自然是无恶意的,人类是允许试错的,但是人类应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主动以自己的诉求和行动再次改变这个状况恶化的自然世界。“人类既然可以错误地造就生态危机,就应当也可以正确地重建生态平衡。”(高歌、王诺,2006)曼丹人也通过神话向族人传达要恪守节制,莫贪婪自大,要对自然感恩戴德。“所有的采集和狩猎都必须以保护平衡的方式进行。”(王诺,2011:140)因为一草一木都是恩赐,都住着圣洁的灵魂与神,人应在获取恩赐之后以仪式表演回馈自然。这与北美原住民的万物有灵论又大有关系。
万物皆有灵,与人平等,大地是北美原住民的精神载体。“万物有灵论是印第安文明最核心的宗教信仰,是印第安文明的基础。”(张明兰,2010)大自然中的万物都有自己内在的灵性,都具有某种人类难以解释的力量,每一种细微的自然现象则是来自神的暗示。土地在原住民心中则是大自然综合体的表现,寄托了世世代代原住民部落的精神信仰。“我们是大地,大地也是我们。”(王诺,2011:137)这种信仰在原住民与自然的关系上不是刻意疏远,而是敬而不疏。“印第安人认为人与某种动物、植物或非生物有一种特殊的亲族关系,每个氏族都源于某种动物、植物或非生物,那个根源物就是图腾。”(同上:136)人与图腾之间似乎存在一种能被客观感知到的相似性,而“动物有可能大致相当于祖先”(斯特劳斯,2012:95)。正是因为把自然万物视为自己的血脉同胞,同时又秉持取用有度的原则,原住民身上才得以体现出对自然深沉的爱以及和自然融为一体的庄重感。安德森(Anderson,2005:127)在《探索荒野自然》中指出,人类与动植物的亲密关系表明了他们在收获和庄稼管理上的经验,而这些实践又给生态上的和谐指明了道路。原住民与自然的关系在保持密切联系的同时还维持着生态的和谐发展理念。不论动物还是植物都有灵性,诸如许多神话文学中出现的玉米神、马铃薯神等。作为美洲的五谷妈妈,玉米女神由玉米穗等做成,还穿上妇女的服装,受到礼拜(弗雷泽,2013:662)。陈小红(2018)提出“植物也有一种看不见的能力”。美国西南部部落在面对政治问题时会通过某种仪式和舞蹈让动植物参与到民主权利事项中来,因为它们也被看作是人类。一切抽象的神都“披上了具体人形的总倾向”,树神自然也具有了人形。这些都说明了原住民眼中的动植物具有人的形象,就好像“山像静脉,身体像溪流”(陈小红,2018),万物与人之间的相互转化已然变成了不可分割的同体存在。而作为广大原住民信仰的萨满教中的萨满便是充当了人和自然之间灵魂与精神沟通的桥梁。这种圣化大地的整体神学观从人的内心深处奠定了自然伟大和不可随意侵犯的基础。
三、基于其自然理念的群体表演艺术
原住民的群体表演艺术体现在他们各式各样的庆典仪式上。北美印第安人时常关注他们与灵魂世界的关系。他们以典礼和祈祷的方式来敬拜灵魂,与灵魂沟通,表明他们的感恩之情,同时也希望通过这种形式能过上一种“平衡而又谦卑”的生活(詹纽尔里,2009:14)。正如“阿伊努族人说:‘听说鹿、鲑鱼、熊喜欢我们音乐、着迷于我们的语言,所以我们打渔狩猎的时候,会为它们唱歌、和它们说话并奉献感谢的祈祷。’”(山里胜己等,2014:15)。出生、成人、死亡、战争、婚姻甚至修建房屋——日常生活的每一方面都可以用舞蹈来演绎,对于他们而言,舞蹈是生命的本能(王晓燕,2009:136)。
受大地母神观、万物有灵论、动物崇拜观、人神转化概念以及自然要素能量守恒的领悟等影响,北美原住民的生产生活工具和饰品中有许多能反映他们自然理念的事物。而具有研究意义的群体仪式表演也能集中体现他们这些自然思想,因为它寄托着原住民对自然变换中四季更迭的感激、对温饱平安的祈求和对部族传统的敬重等。比如,普韦布洛印第安人踏着整齐的节奏,“四十多个男人组成的队伍……边歌唱边合着大鼓的鼓声踏着厚重的柔软的脚步,走向大地中心”(山崎正和,2014:101),借此抒发对大地的崇敬之情。这种祈求还不是纯粹的苦苦哀求,而是将打猎的技艺融入歌舞表演之中,为光电风雨等自然现象的到来跳起精心设计的舞步(哈里森,2015:15)。他们通过戴面具、唱歌、跳舞和演戏等表演形式来反复纪念这份对自然的敬重,重申动植物不可侵犯的神性,宣扬部族祖先的英勇往事,传授为人处世和辨明善恶的真谛。
这种调动感官知觉的身体参与不光是出于自然理念的集体规约,更反过来不断提醒了表演者对自然的意识认知,也使得仪式观看者通过可视的动作领悟其中的奥秘。这种群体表演仪式不仅在选址上和大自然的构造息息相关,仪式的用具、身体歌舞都尽是自然元素。其中广泛用到的面具可根据场景需要在人脸和神形之间变化,一则再次验证了北美原住民关于人神可相互转换的观点,二则也是为了让表演中的人物特征为大自然神灵所知晓(詹纽尔里,2009:36)。可以看到他们在承受来自“群体地位、财富、性别以及其他与自然、文化有关的因素上的差异时,所带有的谦卑和耐力等”(Turner,1991:189)。大平原地区的印第安部落坚持着太阳之舞的传承,用自己血肉之躯参与仪式,跳起鬼舞来与殖民统治作斗争,西南地区的霍皮印第安人在冬至来临之际便会举办活动敬拜他们的玉米女神,他们的狂欢节直至今日也热闹未减。
群体表演艺术成为北美原住民和自然之间的一种对话机制,原住民可以在进行生活劳作之前获取自然的恩准和旨意,从而有节制、有约束地适当索取资源和神力,抑或是在五谷丰登、消灾辟邪之际感激自然的馈赠。就好比是一场联姻,这种人群的汇聚是自然与有组织的人员安排之间的对话(ibid.:140)。他们在脸上和身上绘画,用整个身体去阐释灵魂,表达感情,用色彩和图案融入自然,愉悦自然,人和自然的身份地位得到体现。这些仪式表演不仅是“每个男人、女人、小孩得以保护尊严、自由和身体存在的一种手段”(ibid.),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人在与自然互动过程中的积极性。北美原住民的自然思想便由他们的群体表演展现得淋漓尽致。人类与自然借助艺术传递感谢、释义、请求、困惑和敬仰。在这种基于一定自然理念并强调交流的群体表演仪式中,不管是群体还是个人都在“调整自己的内心世界以适应外在环境”(Turner,1988:158)。人类与自然在展开对话,这可以让自然看到人类的诚意,而人类用自己的感官和肢体也在这种“大集体中丢弃日常的一切慎行,沉浸在心醉神迷中乱舞狂喜地度过时间”(山崎正和,2014:39),从而伸展身心,忘却烦忧。自然与人类便借此融为一体,不分你我。
对于这种群体表演艺术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它在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关系。艺术被德谟克利特和柏拉图等古希腊哲学家定义为一种摹仿。但是原始时期的群体表演艺术以身体为载体,却不是完全出于摹仿,“而是为了创造和重温情感”(哈里森,2015:24-25)。而关于身体山崎正和(2014:106)提出了三个分类:一是作为生理过程的身体,二是作为行为平台的身体,三是作为人生目的的身体,即“在”意义上的身体和“做”意义上的身体。人类在现实生活,包括这种群体表演中,往往是三者的复合体。这种仪式表演强调经验(experience),而经验需要身体的亲历,通过这种经验人就可以得到来自认知上(cognitive)、情感上(affective)和意志上(volitional)(Turner,1988:55)的收获。“表演仪式上的歌唱、舞蹈、宴会、奇异的穿扮、身体绘画、酒精和迷幻药的使用等,使得生物的生命变得高尚、规范变得充满情感意义。”(Turner,1987:55)通过以上种种集体规约式的呈现来实现自然意义的再现(representation),使经历者和观看者都更加容易联想到自然与生活生产。而在获取的同时原住民也在给予,因为这种身体表演在集体仪式上讲究身体激情与欲望自然而然地流露和宣泄(哈里森,2015:18)。在原始群体表演中舞蹈占据了很大一部分,而“舞蹈,最基本的概念是用自己的身体去表达内心的情感”(蒋勋,2015:55)。具备了情感传达和联想刺激的这种群体表演也就起到了艺术在生活中的一些作用。
面对自然世界,个人的身体也可以“为其他人所看到,为所有目击者可见”(杨大春,2007:271)。依据梅洛-庞蒂的看法,他人依靠身体在维护客观性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因为个人虽然不能直接感知他人的意识,但可以通过直接感知他人的身体体会真正的“在世存在”。也正是这种感受使得个人不会陷入唯我论的漩涡,更能以世界参与者而不是唯一主人的身份参与到这场与自然的对话中。通过这种“可见的身体的独特说服效果”(同上)为身体通往精神打通渠道。
综上所述,人既有收获又有给予,并且还能通过他人感受到客观实在,身体就作为个人参与群体仪式表演的一种载体为心灵上体验的加强和人与自然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因人而异、各有特色的通道。身体不再是机械式的肉身,而是充满灵性的存在。在自然中身心合二为一式的体验也有了实例基础。这种艺术哲学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地位便可见一斑。
四、原住民文学文学与艺术的出路
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落幕之后一些霸权国家通过科技和经济等不同方式对欠发达地区和国家实施新殖民主义。后殖民研究主要针对包括这种新型殖民行径等现象展开。后殖民概念较之新殖民概念更为动态和广泛。一些后殖民国家和地区的人经历过被殖民历史,也正经历着新殖民式的经济冲击和后殖民现象下的文化冲击。有受驱逐历史的北美原住民后代尽管更适应以定居者和土著人的身份对话,但是依然难以避免被纳入后殖民研究范围而带有后殖民色彩。
在美国成立之前北美印第安人就受到来自欧洲定居者的殖民统治,他们生活的区域也可看作是后殖民地区。如今其后裔也正经历着后殖民语境下边缘文化与中心文化的对峙交融。就其内部后殖民现象来看,一些主流文化代表者以发展的美名掠夺原住民的自然资源,垄断其经济命脉,剥夺其政治地位,并弱化其本土本族文化意识和身份自豪感。遭受这种涉及教育、经济、宗教、语言等多方面的实体和非实体入侵的原住民承受着心理流放和文化错位,他们也通过各种方式探索从边缘走向中心的途径。在这种原住民的后殖民现象中纯实用主义和唯理性主义之风盛行,人类的古老传统受到挑战,艺术价值受到忽视,而原住民的生活环境、自然风光也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土地被剥夺后,其神圣性也受到工业材料的污染(扬,2008:51),野生动物被驱逐出自己的家园。原住民的自然理念和部族特色的仪式传统也逐渐被淡忘,身体参与自然也渐不为人重视。人类“做”的身体逐渐规格化和技术化,而“在”的身体逐渐被丢掷一旁和遗忘(山崎正和,2014:107)。艺术和自然连同人的身体心灵就成了遭受同样境遇的弱势者。这种时局也就催促着这三者走到一起。
为了改善这种境况,原住民当代文学创作竭力从寻找本族文化根源的尝试中找到发声出路。由于原住民文学往往具有多元复合文化背景,他们的作品具有后殖民文学特征。北美原住民的当代文学经历了从同化、回归再到文化杂糅的三个阶段(邹惠玲、郭继德,2008)。从一开始渴望通过白人语言获得白人社会的肯定到传统民族意识觉醒,争取政治话语权力,批判白人文化,再到从原住民自身文化与后殖民文化的既有杂糅现象中探讨原住民群体的合适位置与发展路径,以树立自身文化魅力,当代原住民文学创作者在认清后殖民语境现实中不断重建自身民族的文化价值意蕴,尤其是为宣扬自然价值,维护环境正义而作出了持续的贡献。“他们的贡献主要包括反抗文学,有时候用其他最公开的方式,如非虚构报道和政治宣传手册,也有更间接的形式,如小说、诗歌和戏剧。”(哈根、提芬,2012)其中诞生了许多原住民女性作家,她们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在作品中常常穿插着传统的神话传说。这种文学创作上的性别差异特征还引起了人们更多的关注(Boehmer,1995:216),关于原住民后殖民生态批评的诉求也在日益增大。著名原住民作家路易斯·厄德里克(Louise Erdrich)在《爱药》()中便深刻揭露了印第安人在居留地遭受白人文化侵蚀下的精神空虚与迷茫现象。另有一些作者则引用了诸多本族的古老传说与神话,从侧面反映了后殖民现象,并重申了自然思想。波拉·甘·艾伦(Paula Gunn Allen)在作品中以新的形式复述了古老纳瓦霍人“变之女”(Changing Woman)的传说。安妮塔·恩德雷泽(Anita Endrezze)的作品《太阳祖父与月亮脸女人的爱》()则是引用了雅基族(Yaqui)关于日月的神话(Wong,Muller & Magdaleno,2008:197-203)。除了从原始神话中汲取创作力量表达对自然的关怀和对人性贪婪的鞭挞,更有直接从生态角度出发来探索原住民生存方式的作品。路易斯·欧文斯(Louis Owens)的《狼歌》()传递了对土地的崇敬。琳达·霍根(Linda Hogan)在《灵力》()中呼吁动物崇拜传统的回归,斥责对动物的滥杀无辜行为。原住民后裔试图通过这样一种文字传播的方式来唤起族人的清醒,重拾部族自然思想价值。他们还通过种种重构来增强自身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原住民不仅在作品里重申了自己的身份,回归了原始自然思想,还因为语言文字使用的混杂和文体叙述手法的独特等原因走出了有自身特色的一条文学道路,极大丰富了世界文学。这也是后殖民文学的一个不同之处。
面对这样的现实条件和文学出路,加之群体仪式表演艺术在继承北美原住民自然思想上的重要作用,以及当代原住民在文学中对传统自然神话思想重视的不断加强,再次认识群体表演艺术的价值和意义不仅能够给原住民文学带来新的创作灵感,还可以为他们在现实中实现与自然的对话和接触提供可行的路径。而将原住民后代这一群体的呼声诉诸于全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找寻一条合理应对当代机械工业过度泛滥,自然环境恶化,人类缺乏对自然的敬畏与交流等问题的有效途径就显得尤为重要。而首先应该做的大概就是从感觉和情感角度出发,先学会欣赏和感激自然。为了达到此目的,我们可以尝试从艺术入手,“人类所拥有的对娱乐的狂热和艺术的才能其实是对这个星球的一种生态贡献”(山里胜己等,2014:15)。尤其是群体表演艺术作为软文化中的一环能重新唤起我们对“在”的身体的关注,唤起我们的感情和感觉,以对抗当今社会里纯功利主义的做。因为表演艺术关注身体本身存在的价值和美,而不是它能够创造多少实际利益。群体表演艺术启迪人类将直接利用自然的单一想法抛掷一旁,转而注重与自然的灵魂交流和情感对话。这是原住民自然思想里人与自然对话的一种介质与桥梁,在重塑当代自然观上亦可以协助人类更好地欣赏自然,从而尊重自然,最终得以维护自然。这意味着人类要懂得感恩,并用身体去对话自然。
艺术可以拯救我们的精神荒原,而群体表演艺术可以拯救我们自然理念的荒原。我们主张探讨能动性和为自然辩护的精神(赵建红,2014),要尝试“以平等的身份去接近自然,经历自然,融于自然”(程虹,2013:148)。走近自然的一种方式便是把自己的思想融入自然,用自己的五官感受自然,将自己的身体浸入自然,以便可以为自然呈现我们的回应与礼物。而我们的身体与灵魂也在这种以表演为形式的交流对话中成为自然中动态的一景,因为“表象即世界,表象即自然”(山里胜己等,2014:86),我们也本就是自然中的一员。这些坦诚而亲密的举动对于自然而言即是一种肯定的感激与恩德。
五、结语
无论是大地母神、万物有灵论、动物崇拜还是图腾制度、能量守恒观以及萨满教信仰,内涵丰富的北美原住民自然理念广泛而深刻地在他们的生活中蔓延。我们看到的是北美原住民的生态整体主义和生态平等主义人与自然交流观。人与自然万物血脉相连,同根同源,还可以相互转化,互帮互助。北美原住民通过歌唱、舞蹈、身体绘画、人造物和自然物的使用等形式不断向自身及族人传达和加深了自然理念的印象,人与自然平等互惠,人可以进入自然的精神世界,每一次向自然索取都要心怀感激。这样一种以群体身体为呈现载体的活动充分展现了北美原住民的古老智慧,通过对生产活动和自然万物及现象的再现他们向自然表达了自己的身份话语和情感因素,并积累族人的自然经验,而自然也借此看到他们各自的特色和交流的诚意。我们不仅要为了自己的感受进入自然,也应该忘却人类的身份,站在自然的角度,为了让自然可以看见我们而进入自然。身体作为客观实在的感知体验存在借助群体的相互对照调动并不断启发人的内在精神意识。身心的历史边界被打破,人与自然的对立也得到消解。这种群体表演活动既有艺术价值又有哲学内涵。广义上也可以说艺术架构起了人类与自然的联结,身体成为了基本的交流和对话介质。
而在当今后殖民现象中,艺术、自然和人类三者命运紧紧相连,我们回望这种群体表演艺术就十分有必要。北美原住民后裔正经历着身份认同危机,他们的后殖民文学创作也不断地在向原始自然传统中汲取精华和认可,探寻民族特性,以彰显身份个性,增强差异,或是挖掘人类共性,以在后殖民语境下从边缘走向主流,弱化差异。不论哪种途径,解放身体回归自然的群体表演艺术传统不仅可以为他们在文学创作上提供灵感和启迪,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自然神话,也可以为他们的现实生活带去宽慰和平静。对于全人类而言,在经历了从生态中心主义环境哲学到环境公正主义批评阶段的转变后,也可以尝试抓住后殖民现象下的寻根、占用、身份认同和对话平等的概念,将其迁移回归至人与自然的大主题下加以反思。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群体表演艺术的作用和价值,即背后的自然理念、艺术体验和哲学内涵。由原始文化发展而来,又有着丰富自然思想内涵的群体表演艺术在当今完善人类与自然关系上是可取的。我们应该在自然中投入自己的身体,让身体表达感情,对话自然,把握好节拍,与自然共舞。
注释:
①原文中使用的是he,虽有性别色彩,但为保持原文的准确性,在此沿用原文用法。
[1] Anderson, M. 2005.[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 Bastian, D. & J. Mitchell. 2004.[M]Santa Barbara: ABC-CLIO, Inc.
[3] Bell, A. 2014.[M].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4] Boehmer, E. 2005.[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 Roholt, T. 2017.[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6] Turner, V. 1987.[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7] Turner, V. 1988.[M]. New York: PAJ Publications.
[8] Turner, V. 1991.[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9] Wong, H. D. S., L. Muller & J. Magdaleno. 2008.[C]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0] 布兰登·詹纽尔里. 2009. 印第安艺术与文化[M]. 简悦译.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11] 陈小红. 2008. 加里·斯奈德与印第安生态智慧[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6): 18-21.
[12] 程虹. 2013. 美国自然文学三十讲[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3] 高歌, 王诺. 2006. 北美印第安神话中人与自然的关系[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 24-29.
[14] 格莱汉姆·哈根, 海伦·提芬. 2012. 后殖民生态批评的发展观[J]. 张慧荣译.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 145-149.
[15] 关春玲. 2006. 美国印第安文化的动物伦理意蕴[J]. 国外社会科学, (5): 62-69.
[16] 胡志红. 2015. 西方生态批评史[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7] J. G. 弗雷泽. 2013. 金枝[M].北京: 商务印书馆.
[18] 简·艾伦·哈里森. 2015. 古代艺术与仪式[M]. 刘宗迪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 蒋勋. 2015. 艺术概论[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 列维·斯特劳斯. 2012. 图腾制度[M].北京: 商务印书馆.
[21] 罗伯特·J. C. 扬. 2008. 后殖民主义与世界格局[M]. 容新芳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2] M. H. 艾布拉姆斯, 杰弗里·高尔特·哈珀姆. 2014. 文学术语词典[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3] 任一鸣. 2008. 后殖民:批评理论与文学[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4] 山里胜己等. 2014. 自然与文学的对话——都市·田园·野性[M]. 刘曼, 陶魏青, 于海鹏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5] 山崎正和. 2014. 世界文明史——舞蹈与神话[M]. 方明生, 方祖鸿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6] 石海毓. 2012. 生态文学的现实价值[J]. 山东外语教学, (2): 79-84.
[27] 王诺. 2011. 欧美生态文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8] 王晓燕. 2009. 古美洲生活[M].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9] 杨大春. 2007. 语言身体他者——当代法国哲学的三大主题[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30] 张明兰. 2010. 从《摇篮曲》解读印第安人的文化生态观[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 203-205.
[31] 赵建红. 2014. 从对话到建构——读《后殖民生态:环境文学》[J]. 外国文学, (6): 145-160.
[32] 邹惠玲, 郭继德. 2008. 后殖民理论视角下的美国印第安英语文学研究[J].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2): 327-332.
[33] 周柏冬. 1984. 拉丁美洲古代印第安文学[J]. 外国文学研究, (1): 124-130.
[34] 朱峰. 2012. 发展、环境、动物:评《后殖民生态批评》[J]. 外国文学, (5): 129-135, 160.
[35] 朱刚. 2015.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The Art of Group Performance in Rituals and Ceremonies Based on Northern American Natives’ Minds on Nature: A Recall with a Postcolonial Background
CHEN Yan-jun
Native northern Americans’ mythology and legends contain mother goddess, animism, totems and energy conservation etc. and conveys their gratitude and respect towards nature. They also reciprocate nature with group performance by integrating their bodies into nature. The art of such forms offers them a way to communicate with nature. In the case of postcolonial background, especially for some natives’ writings, there are continuous and urgent needs to find a way to appreciate, respect and preserve nature from their myths and the art of performance in light of the unsatisfactory living conditions and vague self-identity, and so do all humankind. It’s significant for us to reconsider the role of the art of group performance in contemporary dialogues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through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nature, human and art.
northern American natives’ minds on nature; the art of group performance; rituals; post-colonization; body dialogue
2018-07-31;
2018-08-26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态文明价值导向下的美国自然文学研究”(18WXB007)
陈彦君,硕士生,研究方向:美国自然文学
I106.7
A
1008-665X(2018)5-0021-12
——评《后殖民女性主义视阈中的马琳·诺比斯·菲利普诗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