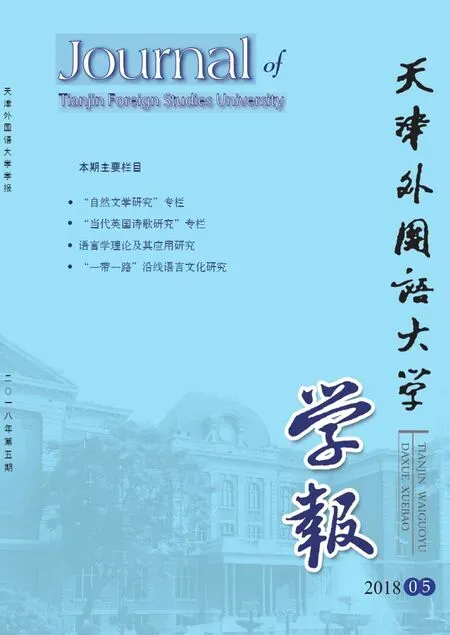荒野中的荣光——论约翰·缪尔的神性自然书写
余 青
荒野中的荣光——论约翰·缪尔的神性自然书写
余 青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70)
19世纪中叶,美国日益激变的工业化发展严重冲击了自然发展的平衡。寻求个性解放和探索精神世界的文学领域则因超验主义思潮的异军突起而充满了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约翰·缪尔作为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的先驱和自然文学作家的典范通过自身广泛的旅行考察,试图在自然中寻找“神性的力量”,将对自然神性的信仰有意识地融入到客观自然的表现中,并赋予了其自然文学作品以神性的品质。他不仅以一种科学的精确性再现了自然的外在肌理,而且以一种强烈的精神力量阐释了自然的内在价值。他的神性自然书写对当代转折进程中探索人与自然的张力关系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约翰·缪尔;神性自然;荒野
一、引言
约翰·缪尔(John Muir,1838-1914)是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美国自然文学及环境保护领域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以深入美国西部荒野的切身体验为素材,写出了近10部既优美又饱含深刻生态哲思的自然文学散文、生态传记等。他凭借与生俱来热爱荒野的品性,以强烈的激情、诗意和博爱回应荒野自然与生命,从大自然的每一处角落挖掘潜藏在万物之间无形又无处不在的神性力量和震撼力,不仅艺术地再现了客观自然的外在肌理,而且以一种炽热的精神品质展现了自然的内在价值,从而使客观自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灵性,用“知行合一”的姿态给予读者以情感上的共鸣和思想上的启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2009)曾称大自然是“博大的灵魂,永生的思想”,其中蕴含着无所不在的宇宙精神和智慧(wisdom and spirit of the universe)。而缪尔则从泛神论的出发点去体察大自然的神性(the divinity of Nature),在其自然散文和大量书信日记写作中表达了“上帝与自然合一”(divine unity)的观点。
近年来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和不断严峻引起了人们对生态人文的广泛关注和深切反思。王宁(2005:18)明确指出,针对生态危机生态批评家试图以自然生态环境为研究视野,并借助文学的力量来呼唤人们自然生态意识的觉醒。深层生态学家们则认为,如果人类希望可持续性地生存在地球上,必须进行深层生态转化(程相占、布依尔,2010:13)。而国内外学者对美国自然文学领域、自然保护运动的杰出代表——缪尔及其文学作品的研究热度也日益攀升,现已逐渐发展成为美国自然文学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米勒(Miller,1999:67)曾评述缪尔在加州、阿拉斯加和落基山脉区忍受寂寞热心探险的经历,称他的作品将精确科学与诗意表达相结合而有种特殊吸引力。马永波(2011:62)则将缪尔及其文学作品的贡献概述为给人类对荒蛮自然的激情、荒野的意义提供了直率的文学表达。耿菲琳(2015:3)在《荒野之子的山间哲思——〈夏日走过山间〉中的山性、神性与科学性》一文中着力探讨了缪尔神性自然的表现,详细解读了自然神性在《夏日走过山间》一书中的灵魂地位和鲜明特点。事实上,缪尔对极为奇妙的神性自然的倾力书写始终贯穿了其大多数作品及大量日记和书信之中。提姆·弗兰德尔(Tim Flinders,2013:20)在《约翰·缪尔:精神书写》()一书的导言部分“约翰·缪尔的永恒之光”中就特别强调了“神性自然”(sacred Nature)作为最重要的主题贯穿了缪尔的作品及书信中,使他“逐渐将自然界看作是揭示神性的天书(came to view the natural world as a revelatory scripture to the Divine)”。夏承伯(2012:29)明确指出,缪尔的荒野自然观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也几乎像他对荒野自然的顶礼膜拜的虔诚一样浓厚,鲜明地点出了缪尔笔下的自然神性特征及其与荒野自然不可分割的关联。而目前从荒野自然或神性自然的视角对缪尔的作品进行系统性审视和研究尚存有不少拓展空间。
荒野自然作为人类生存不得不面对并发生关系的对象不仅与美国自然文学有着深厚的渊源,而且已发展成为美国自然文学的一个热门研究主题,被自然文学作家们给予了广泛关注和充分解读。美国自然文学正是以描写自然为主题,以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内容,展现出一道亮丽的自然与心灵的风景,重述了一个在现代人心目中渐渐淡漠的土地的故事(程虹,2011:2)。荒野即荒凉的原野,是我们生活之外的原始大自然,是一种蛮荒的存在。孟宪平(2013:28)指出,对自然荒野的兴趣不专属于风景画家,整个社会在文明创造过程中都与其发生身体和精神上的联系。荒野自然就如缪尔思想根底中的一块基石,是他思考问题的出发点。由此可见,缪尔经历了从客观自然荒野向精神观念荒野(包括荒野文化、荒野保护和荒野审美等)的心智变迁过程,为“走进荒野其实是走向内心”作出了鲜明而深刻的文化注解。
二、神性的孕育
客观自然与自然的神性之间存在着极为奇妙的张力关系,早在古希腊哲学的人类学时期人们就发现了这一点,从而产生了神性的自然观,而这(自然的神性)正是缪尔作品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缪尔的荒野世界里我们感知到的是荒野的野性、神性与灵性的交相辉映和生机勃勃,它凝聚了“大自然的造化之功和万千宠爱,与我们印象中的荒野完全不同”(耿菲琳,2010:12)。
缪尔的神性自然理念的孕育或产生与缪尔的成长历程和生活环境密切相关。1838年他出生于英国苏格兰东洛锡安的邓巴镇(Dunbar),1849年随父母迁至美国威斯康星州伯蒂奇附近的农场,在这两处以自然景色闻名的地方成长让缪尔深受荒野自然的眷顾,并直接催生了其对大自然的最初兴致,使他对那里的一山一水和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深厚的感情。缪尔曾在个人传记《我的青少年生活》中描述了他在一次与祖父的短途旅行中发现的奇妙景象,至今仍让他兴奋不已。
当缪尔还是个孩子时“就十分喜爱一切野性的东西”(缪尔,2015b:1),他骨子里与生俱来的野性沿着自己辉煌的轨道前行,如同天空中不可征服、无法抵挡的繁星一样,这种对荒野景物的热爱由来已久,并伴随了其一生,而且有增无减。缪尔天生就属于荒野自然,被其尊为心灵导师的珍妮·卡尔(Jeanne Carr)最早发现了他的这一天赋异禀,并称其为具有“内在的眼睛”(eye within the eye)的人(Flinders,2013:7)。在认识自然的深度和本质方面,缪尔仿若洞察自然的精灵,无疑是最具敏锐目光的。正是大自然的绚烂景致开启了他内在的眼睛,他能看见自然的美之所在,他的灵魂能感应到自然神的存在,从而感叹大自然的美源自造物主的鬼斧神工,这为缪尔充满神性的荒野审美提供了必要条件。
从孩提直至青年时期,缪尔的家庭,尤其是缪尔的父亲丹尼尔·缪尔(Daniel Muir)对其清教思想的启蒙教育和性格的培养为他踏上自然之路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缪尔的父亲是虔诚的新教徒,其执着、节俭的品性影响了缪尔的一生,其颇为严格的精神约束与艰辛的农场劳作之令,缪尔在自传中将其称为老苏格兰人的鞭子,也为他出走孤寂的荒野提供了绝好的契机,使得他在充满野性和青翠草木绵延的威斯康星荒野中挖掘到了无尽的快乐(ibid.:5)。每日晚饭后的《圣经》背诵是缪尔家庭教育的必修课,每逢安息日做礼拜也是缪尔在威斯康星州农场劳作的日常。
自然文学家们对荒野自然之赞美与细致入微的描绘也增强了缪尔到没有学校和书本的神秘荒野中畅游的渴望。苏格兰传统文化中深深的恋土情结(land complex)给予了缪尔自然写作风格的传承,而“那光辉的威斯康星荒野”(that glorious Wisconsin wilderness)热情地拥抱和传授了缪尔辉煌的荒野经验,成为了他荒野行吟的高歌之地。缪尔在威斯康星大学接受了自然史教育和自然文学作品的广泛浸润和熏陶。他从自身的荒野体验出发,将客观自然和神性元素与理性、科学联系在了一起,孕育出了神性自然,“展现了荒野自然的美丽神奇与叹为观止”(夏承伯,2012:29)。至此缪尔的神性自然观便水到渠成地在其作品和环境保护行动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
三、荒野的荣光
缪尔笃信置身于自然的神圣殿堂会使自己的自然神性得以升华,故而他极力崇尚与赞美自然,用尽浑身解数来展现自然山林保护区和天然国家公园的壮美万能的内在价值,以此来激发人们走进荒野,亲近自然。几十年跋涉于美国西部荒野的缪尔由起初的模糊印象到后知后觉的体悟,目之所及之处皆是闪动着神性的光辉和生命的律动。正如弗雷德·怀特(Fred White,2006:x)在《至关重要的缪尔》()的导论中所表述的那样:“他(缪尔)所观察到的每一处,皆是自然揭示它的光辉(Everywhere he looked, nature revealed its glory.)。”这种精确的观察与崇高的光辉之间独特的呈现方式都在缪尔的心中留下了美妙和超凡的印象,并给予他对自然更多的人文关怀。
事实上,“荣光”一词是缪尔最喜欢的一个语汇,也是最能传神地攫住缪尔深入荒野时那种愉悦近乎狂喜的情感。雷蒙德(Raymond Barnett,2012)在《约翰·缪尔与神性自然》(John Muir and “Godful” Nature)一文中揭示了缪尔将自然看作是充满神性的所在,“他(缪尔)公开呼吁上帝的美与爱存在于美国的荒野之中”。弗兰德尔(Flinders,2013:15)指出:“缪尔在1873年搬到奥克兰(Oakland)居住并重拾记者事业,由此将他的神性自然的热情向更广大的人们当中传播去。”在《阿拉斯加之旅》(缪尔,2015a)中对极光的描写令缪尔感到无限的满足与快乐。缪尔曾和负责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的查尔斯·萨金特(Charles Sargent)教授一起登山,哼唱着“荣耀在一切之中”(武尔夫,2017)。“荣耀的荒野,好像在用一千种如歌的声音呼唤”,暴风雨中的树木“充满了音乐与生命的脉动”(缪尔,2014)。缪尔笔下的荒野是充满野性的、生机勃勃的,同时也是充满人性的。“神圣的风从令人震惊的广阔天空中旋转而来……(他们将风景视作有生命的、独立存在的景观而欢庆)(divine the cut of the wind and the shocking immensity of sky that it swirls out of…)(and they celebrate landscapes as animate, existing on its own)”(Zwinger,1994:x)。缪尔认为,在内华达山的荒野中全是充满灵性与感情的生物。所有的一切,无论山峰、岩石、冰川还是森林、草原、瀑布,甚至云朵、天空与风,都具有一种顽强的生命力,自然万物就在神光的普照之中拥有了神性。《大西洋月刊》的编辑埃勒里·塞奇威克(Ellery Sedgwick)在阅读了缪尔的《夏日走过山间》的手稿后曾激动地说:“我感到仿佛发现了宗教。”(Wolfe,1981:233)我们不妨说这本书可谓是一部高山岭大传,书中所描写的岩石地貌、植物、动物 、山峦、瀑布无不在缪尔的笔下熠熠生姿,眉目传情(赵白生,2003:299)。
缪尔的神性自然不仅延续甚至升华了古老的博物学传统,而且还为自然文学中的荒野书写注入了一脉新鲜的活力。正如安德烈娅·武尔夫(2017)在《创造自然》一书中所写的那样,缪尔眼中的自然是充满神性的,他们(洪堡和缪尔)将自然视为神圣的存在,也正如缪尔所信任的那样,他们的神就在森林中。缪尔与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自然神性精神产生了共鸣,洪堡看到的是内在于自然的创造力,而缪尔找到的则是神迹。有“光之山脉”(the range of light)之称的内华达山脉就处处布满了神迹,缪尔在此生息、布道,沉浸在对热带植物缤纷景象的想象中。缪尔曾说:“长久以来,我都被上帝创造的南方的热带庭院吸引着。”(Bade,1916:XVIII)对他来说,研究神性自然是一项十分虔敬的事业,心灵的情感聚集成为一种自然与创造之间的融合点。
四、神性的展现
缪尔在荒野中发现了上帝的存在,认为荒野显现着人类的希望,这就是对神性的最透彻阐释,同时也是缪尔的生态哲学观之体现。神性几乎贯穿缪尔的所有自然作品之中,并糅合了他自己的精神信仰。在山间徒步旅行,在荒野中发现上帝,对自然的敬畏便是对上帝的虔诚。赵白生(2003:300)认为,缪尔将科学与文学、观察与想象、自然与人彼此交融,互相滋润着。缪尔无疑最热心于从神性自然的角度来展现自然的内在价值。他从内心已经把自然界中的万物当成与自身平等的成员了,这些成员平等地分享着自然的博爱与神圣,并对自然赋予的这份和谐之美心存感激。自然的神性主要通过缪尔发现上帝存在于自然之中、近乎朝圣般的自然探索和亲身体验自然神迹这一过程得以展现。
首先,缪尔对俗世基督教教堂的反叛促成了其寻找并发现上帝在自然中的存在。缪尔的父亲深受勤奋工作、严于自律的清教徒道德伦理的浸润,培育和教导缪尔拥有一副敬畏上帝和热爱自然的仁慈心肠,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我的青少年生活》(缪尔,2015c)一书中缪尔试图唤醒一种青少年时期的回忆,回顾着父亲把花园装扮得像个伊甸园,敬畏又兴奋地欣赏着姑姑种植的百合花。童年时男孩的那种野性而又善良的脾性造就了缪尔日后对荒野的无穷痴迷和热爱。他在自传中描绘了原野在耳边回响的时刻,大自然呼唤我们到旷野中漫游。他满心期待着没有书本的美国荒野,到达威斯康辛州后,由于农场的事务,缪尔未能进入传统学校继续读书,他那由衷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突然投进这纯粹的荒野,在大自然温暖的怀抱接受洗礼。他在后来的作品中也如实表达了大自然带给他的无边馈赠。
其次,神性自然是通过描写内华达山脉中散落在一切自然物上的光辉来体现的。在《夏日走过山间》中,“在优圣美地的圣庙里,他们从鱼的生死苦痛中寻乐,而上帝本人却在布道,他的经文就是那最崇高的水和石。”(缪尔,2014)“大自然——上帝的水石经文,这是穆尔发自内心的咏叹调。”(赵白生,2003:301)上帝借助水石经文向他创造的大自然(包括人类本身)向人们揭示自己的光辉。缪尔又把内华达山脉称为“光之山脉”(缪尔,2015c),他提出如果要给内华达山脉重新命名的话,也许应该称其为光之山,而不是所谓的雪之峰。因为这里有着最晴朗无比的天气,这里的阳光能够多角度地、庄严而自由地挥洒而下,让内华达山脉整个沐浴其中。还因为这里有着冰川打磨过最闪亮的岩石和美丽瀑布闪烁着彩虹光泽的水花。塞拉山上由银冷杉和银色原松树形成的闪亮的森林以及这里的点点星光、如水月色也是使得塞拉山成为光之山的理由。
最后,神性还表现在缪尔本身及其在山中所体验到的自然神迹上面。缪尔骨子里闪现着一部分神性,他那种对自然执着的热爱和强烈的归属感无疑都是神性的体现。在奇妙之旅中缪尔就记述了一件他本人的灵异事件(缪尔,2015a)。他在深山中静坐,忽然预感到他的老朋友巴特勒教授(William Butler)就在下面的山谷中。虽然他自称从小就对招魂术、神秘预感和鬼故事等都不感兴趣,因为大自然是如此开阔、和谐,它的旋律是如此美妙,充满了阳光和日常的美,相比之下,这些超自然现象就显得多少有些别扭,但他还是决定到下面的山谷中去尝试寻找教授。令人惊奇的是,他的预感竟然应验了,他竟然真的找到了巴特勒教授。这件具有超自然启示的事情显然没有办法用科学来解释,我们只能认为是大自然赋予了这位宠儿以一种神奇的力量,令他在自然当中能够较凡人发现更多的美,亦能够感知到朋友的来临。而他感到过多地提及和琢磨这件事实在是很愚蠢,因为与这些所谓的超自然现象相比,我们日常所见的自然要更加神奇与神秘。
五、神性的启示
作为19世纪后期美国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念的重要代表,缪尔一方面继承了浪漫主义者和超验主义者对荒野的那份热爱,另一方面自身的荒野探险经历及其对大卫·梭罗(David Thoreau)等人超验主义思想的吸收使得缪尔摒弃了传统的功利主义自然观,从而变成了一名自然价值论者。缪尔坦言造物主创造出动植物的首要目的是要使它们中的每一个都获得幸福,而不是为了其中一个的幸福而创造出其余的一切(缪尔,1999:3)。这就体现了普遍的神性启示和自然博爱的特征,这一点也深深影响着缪尔的思想。在研习自然的广泛考察中缪尔还经常将《创世纪》中的篇章与他所切身观察到的客观自然所蕴含的思想加以比较,这就无疑决定了他的自然文学作品具有相当程度的宗教神秘色彩。他笔下的每一个自然物都表现出了最为生动、美妙的神秘感,这些作品所彰显的自然元素与自然神性的完美结合是无法用语言文字来描述的,留给读者对生命和自然的无限思考。
缪尔的伟大成就离不开荒野自然的锤炼与熏陶,用脚步朝圣荒野,并发现自然神性的特别之处。在缪尔眼中充满神性的大自然中有一切美与爱的典型特征,具备人类无法比拟的神性与优点。“我能听到每一个水晶和每一粒沙子的心脏的跳动,能够在他们的产生、形成和流动中看到一种聪明的计划。所有的事物都依据神圣的音乐在跳舞。”(同上:211)自然的灵动之美和外在神性在他的笔下一览无遗,意味着物质性与神性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张力关系。缪尔还精心描绘了山川、树林、岩石等,山川象征着坚定的信念,而树木则寓意着希望。缪尔特别喜欢岩石,因为它证明了大自然的巨大力量,“大教堂岩,或岩石切割而成,或地陷所致,高山仰止,恍若山谷中一座神秘而庄严的殿堂”(孙重人,2017:105)。对缪尔而言,自然的一切是上帝的象形文字,他激动地说出上帝无处不在的肺腑之言。他笔下描绘的各种风暴、激流地震、山崩地裂以及宇宙灾变等无论最初它们看上去是多么神秘、多么无序,它们都是大自然创造之歌中的和谐音符,是上帝表达爱意的不同形式,是广袤大自然的无止境延伸。缪尔曾发自肺腑地讲述自己只能在这片令人喜爱的壮阔山峦中漂泊,心甘情愿地在神圣的大自然中当一名谦卑至微的仆人(同上:101)。缪尔的自然文学作品并不局限于如实地呈现自然景色,而是更进一步以自然的客观元素为载体聚集了一种对上帝敬畏的感情,突出大自然的庄严和雄伟,反映人类置身于大自然怀抱时所表现出的渺小和心灵的谦卑。
缪尔之所以被认为最具神性自然特征的代表,还因为他笔下的自然拥有一种超凡的力量,一种在光与影、准确的细节与崇高的光辉之间独特的观察与呈现方式。追寻着缪尔的足迹我们常常犹如悬浮在半空中俯瞰山景,感受自然的空冥之美。对缪尔而言,研究自然这一上帝的创造物是一件虔诚的事,而我们常常感动于他对自然永远不息的描绘。在观察自然和与自然发生关系时,他的技巧是在借助文字的同时也借助于视觉表现,从日志中数量众多的素描可见一斑(布兰奇,2014)。缪尔不断地扩充着这些想法,并逐渐相信自然万物都具备神性的优雅。他所寻求的精神元素虽然有时也是十分令人费解的,但是内在的神性力量却震撼着无数观赏者的心灵,这种神性自然的元素也为当代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一种具有哲理性的思考方式。他在1873年的日记中写道:“组成世界的所有个体‘事物’或‘存在’都是神圣灵魂的火花,表现为形态各异的叶片或坚硬的岩石。(all of the individual ‘things’ or ‘beings’ into which the world is wrought are sparks of the Divine Soul variously clothed upon with flesh leaves, or that hard tissue called rock)”(Flinders,2013:23)这种源自荒野的觉察不断地滋养着缪尔的思想内核,自然界无论动物、植物以及岩石都闪烁着神性光辉的启示。
六、结语
神性自然是对工业革命以来的科学理性的拒斥,但它既不等同于基督教观念中的自然,也不是简单地回归于古代文化中万物有灵的自然,而是一种新型的自然思想,它在大自然的形象里渗透着朴素的美德,使之与人的心灵形成共振和感应,启迪着社会生活中被资本主义金钱关系所异化的人们对真善美的向往。神性自然意识自始至终都深深扎根于缪尔的荒野行吟与自然书写中。在我们集体性的想象力中把攀登树梢的缪尔定性为永远的年轻人,这对他来说也许是一种荣耀。和梭罗一样,缪尔经常启迪我们追求理想所需的各种各样的必备要素——顽强、野性、独立和自信。
缪尔完美诠释了生态文学的使命,即发现自然的和谐,培养人的生态情结,让人真正地融人到生态交响乐之中。缪尔的生态书写表达着一种与现代生态伦理相契合的科学主张,以文学形式真实地再现了自然的生机与活力,重新给予了自然以神性的尊严,以此构画出了人类诗意栖居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感人画卷。在缪尔看来,神性的自然观把自然与神性直接联系在一起,同时也间接地把它与人性联系在一起,体现了自然的神性表现和人性进程的连续性和一致性。缪尔用对大自然宗教般的虔诚谱写出了与自然的心灵对话成果,其作品不仅赋予人类对荒蛮自然以敬畏之情与责任意识,而且还为荒野存在的价值意义提供了最为直率的文学表达与寓意。缪尔笔下自然神性的演绎传达出了他对自然生命深厚的人文关怀,也为开启深层生态保护和拉近当代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最契合的交流方式。
[1] Bade, W. 1916.[M]. San Francisco: Sierra Club Books.
[2] Barnett, R. 2012.[J]., (3): 266-288.
[3] Flinders, T. 2013.[M]. New York: Orbis Books.
[4] Miller, S. 1999. John Muir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J]., (1): 8-21.
[5] White, F. 2006.[M]. Berkeley: Heyday Books.
[6] Wolfe, L. 1981.[M].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7] Zwinger, A. 1994.[M]. Boston: Beacon Press.
[8] 安德烈娅·武尔夫. 2017. 《创造自然——亚历山大·冯·洪堡的科学发现之旅》[M]. 边和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9] 程虹. 2011. 《寻归荒野》[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0] 程相占, 劳伦斯·布依尔. 2010. 生态批评、城市环境与环境批评[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5): 12-16.
[11] 耿菲琳. 2010. 荒野之子的山间哲思——《夏日走过山间》中的山性、神性与科学性[J].荆楚理工学院学报, (3): 11-15.
[12] 马永波. 2011. 荒野中的朝圣者——论约翰·缪尔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J]. 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 (2): 62-67.
[13] 迈克尔·P. 布兰奇. 2014. 奔走于世界的约翰·缪尔——1911-1912年的南美、非洲旅行[A]. 野田研一, 结城正美. 越境之地:环境文学论序说[C]. 于海鹏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4] 孟宪平. 2013. 荒野图景与美国文明[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15] 王宁. 2005. 文学的环境伦理学:生态批评的意义[J]. 外国文学研究, (1): 27-29.
[16] 威廉·华兹华斯. 2009. 华兹华斯诗选[C]. 杨德豫译. 南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7] 夏承伯. 2012. 大自然拥有权力:自然保存主义的立论之基——约翰·缪尔生态伦理思想评 介[J].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 (3): 28-33.
[18] 约翰·缪尔. 1999. 我们的国家公园[M]. 郭名倞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 约翰·缪尔. 2014. 夏日走过山间[M]. 邱婷婷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 约翰·缪尔. 2015a. 阿拉斯加之旅[M]. 马永波, 张伟译. 北京: 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1] 约翰·缪尔. 2015b. 我的青少年生活[M]. 马永波, 王雪玲译. 北京: 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2] 约翰·缪尔. 2015c. 加州的群山[M]. 马永波, 王雪玲译. 北京: 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3] 赵白生. 2003. 生态文学三部曲[J]. 世界文学, (3): 297-308.
[24] 孙重人. 2017. 荒野行吟:美国自然文学之旅[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Glory in the Wilderness: On John Muir’s Divine Nature Writing
YU Qing
In the mid-19th century, the increasingly cataclysmic industrializ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seriously impacted the balance of development of nature. The literary field which seeks the liberation of individuality and explores the spiritual world is full of religious mystery because of the emergence of transcendentalism. John Muir, as a pioneer of the environment conservation movement and a model writer of American nature writing, tries to find the divine strength in nature by means of his extensive excursion inspection, consciously integrates the belief in natural divinity into the manifestation of objective nature, and endows his natural literary works with divine quality. In his works, he not only reproduces the natural external texture with a scientific precision, but also explains the intrinsic value of nature with a strong spiritual power. His divine nature writing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tens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 the contemporary turning process.
John Muir; divine nature; wilderness
2018-07-31;
2018-08-27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态文明价值导向下的美国自然文学研究”(18WXB007)
余青,硕士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美国自然文学
I06
A
1008-665X(2018)5-00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