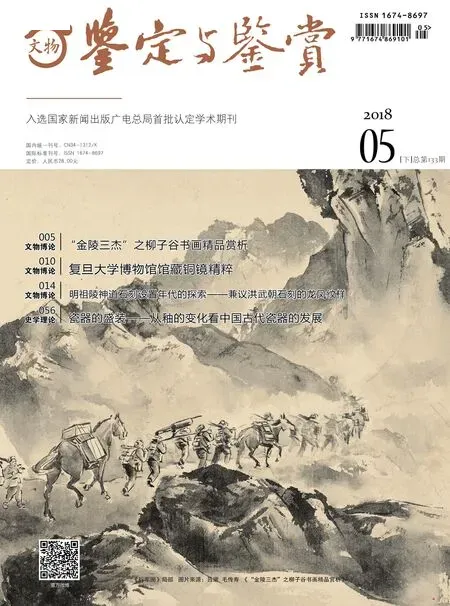法必师古 意从我出
——浅谈中国古代书论中的“通变论”
陈凯
(阜阳市女书家委员会,安徽 阜阳 236000)
中国书法发展的过程从本质上说就是一个“通变”的过程,书法之所以能称为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也正得力于“变”。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通变论”是一个重要的命题,“通”与“变”也是两个重要的概念。在中国古代书法创作论中,“通变论”也是重要的规律之一。从中国书法字体的不断演变,到技法体系的不断完备、流派的形成,再到书法家个人风格的确立,无不是在“通”与“变”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促进中来实现的。一部中国书法史就是不断“通”与“变”的过程,也是“通变论”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
关于“通变论”,早在《易经》中便有“生生之谓易”的发展观,“生生”即指事物的不断发展变化,“易”也就是“变”的意思。《易·系辞下》云:“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系辞上》云:“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又云:“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干,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又云:“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在文学史上,最早提出“变”的观点的是西晋时期的陆机。他在《文赋》中说:“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在这里,陆机的意思是说做文章要吸取前代的优秀成果,但前代的成果毕竟如昨日之早上已经绽放的花,不能沉浸其中不能自拔,要想开出属于自己的鲜花,一定不能重复,必须自出新意,不践古人。在这里,“变”是主旨,同时他又构成了一个新的命题——“通”,“通”是“变”的基础,这样“通变”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命题。之后梁朝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将“通变”单独列出,对“通”与“变”之间的关系做了详细的论述。《议对》篇云:“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当今。”《神思》篇云:“至变而后通其数。”《物色》篇云:“古来辞人,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尽而情有余者,晓会通也。”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说:“通变之术,要在‘资故实,酌新声’两语。缺一则疏矣。”近代著名学者黄侃先生说:“美自我成,术由前授。以此求新,人不厌其新,以此率旧,人不厌其旧。”从刘勰《文心雕龙》开始,这种“法必师古,意从我出”的通变观即成为我国古代文学艺术理论中的重要命题。
在我国古代书法理论中,梁武帝萧衍《答陶弘景书》中最先提出了关于“工学之积也”“且古且今”的论述,南朝梁文学家、书法理论家庾子慎《书品论》中也有“阮研居今观古,尽窥众妙之门,虽复师王祖钟,终成别构一体”的论述。这些论述应该是中国古代书法理论中关于“通变”的最早论述。之后,经过各朝代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的不断实践、总结、发展、深化,逐渐形成了一个完备的理论体系,是一个具有完整内涵的书法理论命题。
中国书法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了篆、隶、揩、草、行等几大书体,并且每种书体都有相对完备的、独立的技法体系。要想深入了解书法之真谛,首先要通过的关口就是“通”其基础技法。并且要明白,虽然各字体都有相对独立的结构和用笔规律,但归根到底它们之间又是相互促进和贯通的。清代沈曾植对书法各体之间的“通变”之理作了论述,他把篆书、隶书和楷书、行书之间的关系做了论述:“楷之生动,多取于行。篆之生动,多取于隶。隶者,篆之行也。篆参隶势而姿生,隶参楷势而姿生,此通乎今以为变也。篆参籀势而质古,隶参篆势而质古,此通乎古以为变也。故夫物相杂而文生,物相兼而数赜。”李瑞清亦提出了有关碑学的“通变”之说,特别指出篆书、隶书在书法创作中的重要地位:“书法虽小道,必从植其本始,学书之从篆入,犹为学之必自经始。余尝曰‘求分于石,求篆于金’,盖石中不能尽篆之妙也。”由此可见,书法各体之间是相互关联的,而不是相互割裂孤立的。比如通晓楷书技法之后,又精通其他书体之法,进而将诸法融合为一体,才能达到“通”的境界。宋代蔡襄在《佩文斋书画谱》中说:“古之善书者,必先楷法,渐而至于行草,亦不离乎楷正。张芝与旭变怪不常,出于笔墨蹊径之外,神逸有余,而与羲、献异矣。襄近年粗知其意,而力已不及。”清朝傅山《霜红龛集》中说:“楷书不知篆隶之变,任写到妙境,终是俗格,钟王之不可测处,全得自阿堵。老夫实实看破,工夫不能纯至耳,故不能得心应手。若其偶合,亦有不减古人之分厘处。及其篆隶得意,真足吁骇,觉古籀真行草隶,本无差别。”在这里,“通”的关键是由貌到神,由得笔法而会笔意,故“若通其变,五体皆在笔端,了无阂塞,唯在得其道而已”,此时之“法”便是“我意”之载体了。唐代孙过庭《书谱》所说的“规矩”与“从心所欲”“平正”与“险绝”的关系,其实质也反映了“通”与“变”之间的关系。所不同的是,它是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对通晓古法而又能化出新意的阐述罢了。
中国书法的学习和其他学科略有不同,其要求后世书家必须深入传统,挖掘经典,入古才能出新,否则一切都是枉然。一个时代对传统了解的程度,决定了这个时代在书法上达到的高度;一个书家对经典的把握程度也决定了他在书法上取得的成就。古代有成就的书家无不是在除贯通前贤书法艺术的基本技巧外,深谙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书法家的特殊艺术旨趣,在更高层次中求“通”,化古为今,变得新意。在书法艺术中,基本技法是最基本的条件,而领悟古代书法大家如何运用技法去表现其特殊的审美追求,则是较高的意识层面上的“通”。其实,历代书家之“体”以及“其体”所用之法,已经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审美典型。而通晓其“体”,了悟其“法”,也便是在神采和意趣上的一种“得”。
中国古代书论中论及某家之“源”,又观其所“变”,正是从“通变”的角度来审视某家、某体,乃至一个朝代的时代风尚。晚唐书僧释亚栖《论书》曾说道:“凡书通即变。王变白云体,欧变右军体,柳变欧阳体。永禅师、褚遂良、颜真卿、李邕、虞世南等,并得书中法,后皆自变其体,以传后世,俱得垂名。若执法不变,纵能入石三分,亦被号为‘书奴’,终非自立之体。”在这里,释亚栖举了王羲之、欧阳询、柳公权、智永、褚遂良、颜真卿、李邕、虞世南等之所以能够艺传后世,正是因为他们都能在汲取前代书家精髓的基础上,融会贯通,自出新意,故能立于世间。若是“执法不变,纵能入石三分,亦被号为‘书奴’,终非自立之体”。这也对后世书家特别是当今习书者敲响了警钟:若一味摹古、泥古,终究只是“书奴”;若要自成一家,必须要“通变”。只有这样,方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书家。
从学习书法和创作的角度而言,书法艺术中的传统修养越高,积累越丰富,对后代人“通”的要求就越高,而“变”的可能性也越小。同时,“变”的基础越广博,其创新品位就可能会更高。书法传统的作用就在这里。米芾在其《海岳名言》中说:“吾书小字行书,有如大字。唯字藏真迹跋尾,间或有之,不以与求书者。心既贮之,随意落笔,皆得自然,备其古雅。壮岁未能立家,人谓吾书为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从中我们可以看米芾在青壮年时尚在“集古字”,但他擅长“取诸长处,总而成之”,让人不知道其所宗,终能“自成家”而留名千古。欧阳修在《欧阳文忠集》中曾经提到自己的学书的感悟:“余始得李邕书,不甚好之,然疑邕以书自名,必有深趣。及看之久,遂为他书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笃。譬犹结交,其始也难,则其合也必久。余虽因邕书得笔法,然为字绝不相类,岂得其意而忘其形者邪?因见邕书,追求钟、王以来字法,皆可以通,然邕书未必独然。凡学书者得其一,可以通其余。余偶从邕书而得之耳。”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欧阳修从学习李邕书法中悟到“凡学书者得其一,可以通其余”的道理,看出了李邕书法的字法从钟、王而来,“皆可以通”,对于后世学书者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部书法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书家不断深入传统、化古为我而最终“自成家”的过程,也是书家们如何由“通”而“变”的历史。对于当今有志于书法学习的爱好者而言,要想在书法史上留下自己浓重的一页,必须要明白“变”的重要性,同时还要明白“变”要以“通古”为基础,要以“通古”为起点。
书法之所以能成为一门艺术,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书法家主体精神和个体情感在书法中的体现。只有寄托了书法家个人情感的书法作品才能打动世人,只有充满了书法家情感内容的书法才能真正获得艺术的生命和价值,正所谓“能移人情,乃为书之至极”。在中国古代书论中,除了“通变论”,还有“神采论”“寄情论”“人格象征论”等一些重要理论。这些观点虽然有着各自的理论内涵,但却有着一个共同的宗旨,即强调书法艺术创作中书法家的主体精神,这也是书法艺术充满活力、生生不息的原因所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能传世的书法作品都是既有深厚的传统修养又有着强烈的个人符号,作为书法史上的经典之作,其也就转化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因此,个性和共性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生发和转化的。个体特性既要与群体审美取得某种一致性,又不能在其中迷失。欧阳修的“其学精而无不至”、苏东坡的“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强调书法之“不可学”,陈槱强调“通变”要“各自有一种神气”。刘熙载认为书法“由不工求工,继由工求不工”,有“观物”和“观我”“我神”和“他神”的变化。这些都说明一个问题,即书家个人创作与时代特性相互影响并相互转化,个性化既要与时代性取得某种一致性,又要突显个人特色。这种既互相影响而又不能彼此取代的关系,其实是一种悖论,也是摆在历代艺术家和理论家面前的难题。而古代书法理论中则用“通变”对此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即明代董其昌提出的“妙在能合,神在能离”。他在《容台别集》中说:“盖书家妙在能合,神在能离。所欲离者,非欧、虞、褚、薛诸名家伎俩,直欲脱去右军老子习气,所以难耳。哪吒拆骨还父,拆肉还母,若别无骨肉,说甚虚空粉碎,始露全身。晋唐以后,惟杨凝式解此窍耳,赵吴兴未梦见在。”从这段话中我们就能看出,一个书家要想有所作为,必须在“合”的基础上“离”。所谓“妙在能合”,即通晓传统书法的基本技法、神采和意趣,亦即“临古不可有我”。这时的“不可有我”,其实是将“我”融入到书法艺术的传统中去,汲取书法的共性养分。但即使如此,也仅仅是达到“妙境”,要达到“神”境,还要能“离”,从“无我”变为“有我”,由“他神”入“我神”,这要通过“通变”才能达到。但这时的“我”是在充分吸取了传统书法审美经验的“新我”。所谓“临帖不可不似,又不可徒似,始于形似,究于神似,斯无所不似矣”。书法创作能将共性与个性统一,“术由前授,美自我成”,最终与古人“合于形骸之外”,既通古人的法度和艺术精神,又变为个人面貌与精神,从而达到“神离”之“妙合”。其创作也就是一种由“古”而“新”,是“通篇意气归于本家者”的真实性情的表现。对此,古人也精赅地总结为“入古出新”。
对于一些只知道摹古泥古、食古不化的顽固派,梁同书《频罗庵论书》中有以精妙的论述:“帖教人看,不教人摹。今人只是刻舟求剑,将古人书一一摹画,如小儿写仿本,就便形似,岂复有我?试看晋、唐以来,多少书家有一似者否?羲、献父子不同。临兰亭者千家,各不相同。颜平原诸帖,一帖一面貌。正是不知其然而然,非有一定绳尺。故李北海云:学我者死,似我者俗。正为世之向木佛求舍利者痛下一针。”妙在能合,神在能离。能“合”就是要能得古人的“妙处”,能领会古人的“精神”;能“离”就是要能脱离古人藩篱,把自我的意识表达出来。如果仅仅会“将古人书一一摹画”,那就真成了梁同书说的“向木佛求舍利”了。梁同书所要表达的无非就是要求创作者要有自己的主体精神,要有一己之意,要有自己的面貌。
“通变论”作为我国古代书法理论中的重要命题,不但是书法学习和创作的重要依据,也是一切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之一。千百年来一直在指导着一代又一代的书法家创作实践,并且通过他们在书法实践中的“通变”和“入古出新”,才使中国书法在不同的历史朝代和不同的人文环境中焕发出不同的艺术气息,才使不同的书法家个体创作出极具自己主体精神的书法佳作,共同构成了一部灿烂绚丽的书法史。与此同时,“通变论”也激励着当今书法爱好者以“通变”的思想承担起为书法这一古老的中国文化艺术增光添彩的历史使命。■
[1]黄惇.书法篆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2]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3]崔尔平.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
[4]王镛.中国书法简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5]欧阳中石.书法与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