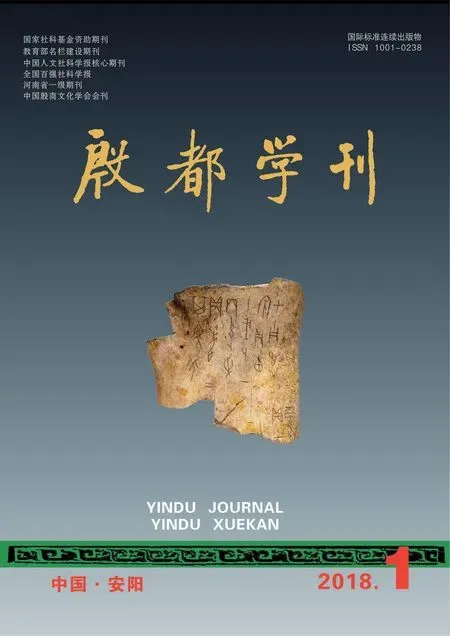《关雎》传播初期应属王室房中之乐
陈 宁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引言
《关雎》列于《周南》首篇,同时也是“诗三百”的首篇,汉代以后形成的经典文本一直如此。历代经学家都借该诗大力阐扬诗教,比附文王太姒之德,甚至还宣扬其为“王道之原”“天地之基”。[1](P164)但是,笔者通过爬梳先秦传世文献,有关《关雎》文本之论仅寥寥数语,最为有名的便是《论语》“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2](p30)和“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2](P82)了。而这两处言论,笔者更以为不仅是对诗文本的评价,更有乐评掺杂其中。试简论如下:
所谓“《关雎》之乱”的“乱”,肯定单指音乐结尾。宋人吴仁杰之《两汉刊误补遗》有载:
诗者,歌也。所以节舞者,曲终乃更变章乱节,故谓之乱。按昭谓:歌诗节舞于理则然。若曰:曲终变章乱节则事正相反。《乐记》言《大武》之舞复乱以饰归,《正义》曰:“乱,治也。复,谓舞曲中舞者,复其行位而整治。”盖舞者,其初纷纶赴节,不依行位;比曲终则复整治焉,故谓之乱。今舞者尚如此,诗乐所以节舞者也,故其诗辞之终,亦谓之乱。《商颂》辑之乱是已;乐曲之终,亦谓之乱,闗雎之乱是已。[3](P180)
依吴氏按语可知, “乱”本是古时舞蹈动作最后一步,曲终时,则“不依行位”舞列开始复位而整治,其用于歌诗,于理亦然。故而,“乱”当是乐之将终,众音毕会的状态,所谓“洋洋乎盈耳哉”,也当指《关雎》的音乐效果。关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程树德《论语集释》引郑樵《通志略》云:“人之情闻歌则感。乐者闻歌则感而为淫。哀者闻歌则感而为伤。《关雎》之声和而平,乐者闻之而乐其乐,不至于淫;哀者闻之而哀其哀,不至于伤。此《关雎》之所以为美也。”[4](p257)很显然,郑樵是将《关雎》作为“和而平”的乐曲清音来评价的。程氏不只是例举《通志略》一处为证,所引《论语骈枝》更是明言:“诗有《关雎》,乐亦有《关雎》,此章据乐言之。”此解将先秦诗乐合一的艺术体例一语点明。程氏不但认同早期诗乐本为一体的观点,更认为例证不只限于《关雎》,《葛覃》《卷耳》同样符合这一特点。由上可知,孔子的《关雎》之评,当更掺杂有《关雎》的音乐之评。笔者借此想说的是,这两处评论,不仅是全部《论语》的《关雎》之评,也是全部先秦传世文献的《关雎》之评,并且是融入音乐之评的《关雎》之评。战国中期以前对《关雎》文本的轻视由此可见。
既然汉代将《关雎》列为《诗经》首篇,并作为重点阐释对象,为何先秦传世文献对其文本的阐释却又如此寥寥?在传世文献难觅其踪时,幸而出土文献带来新的视域考量。上博简为战国中后期的入土文献,[5](p2-3)其《孔子诗论》评《关雎》云(依马承源简序,李学勤释文):
第十简:《关睢》之改,……曷?曰:童而皆贤于其初者也。《关雎》以色喻于礼……。
第十一简:……情爱也。《关雎》之改,则其思益矣。……
第十二简:……好,反纳于礼,不亦能改乎?
第十四简:其四章则喻矣。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6]
由简文可知,《孔子诗论》时代的《关雎》文本与目前通行本已经无大差异。这个时代,对于《关雎》的评价已经初成体系,不仅仅是对文本表面的解读——“情爱也”,而且已经深入到礼学阐释范畴——“《关雎》以色喻于礼”“反纳于礼”,深掘出以礼约情的诗义内涵。由此可以看出,《关雎》的文本分析从春秋到战国中后期是一个逐渐丰富的过程,这和它在“诗三百”中的地位演变是相互关联的。笔者因此生发出关于《关雎》文本形成、地位演变等等一系列诗学问题的思考。
一、关于文本形成:《关雎》在战国中期之前并非有乐无辞
笔者大胆假设:《关雎》在战国中期即上博简之前是否无文本传世,而仅以音乐的形态示人?是否也因为这个缘故,孔子才多从乐理角度来评判《关雎》,而其他诸子对于《关雎》文本更是不置一词?在讨论这个假设之前,需明白的一点前提便是诗与乐的关系,也即是为何这两者能放在一起讨论。在上文中,已经简单论证过孔子对《关雎》的评价应该是评述其乐曲意涵,这里面已经潜在包含了当时诗乐共体的特殊艺术形态。这在许多文献中已有印证,前人张西堂以《诗经》为本证,摘出许多材料可明诗乐相合,现略录几例:《四牡》“式用作歌,将毋来谂”;《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四月》“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崧高》“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张氏论道:“所用歌诗二字,直若毫无判别。二《雅》本是乐歌,而说‘作为此诗’‘其诗孔硕’‘矢诗不多,维以遂歌’,足见当时所谓之‘诗’,都是可以被之管弦的乐歌。”[7](P16)当然,可证文献不止于此。《墨子·公孟篇》“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8](P455)之言早为人所熟知,虽说这诵、弦、舞的三百诗是否为同样的三百篇还需详证,但是诗与乐舞的紧密关系可以窥明。又宋人郑樵《通志·乐略》有云:
自后夔以来,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八音六律为之羽翼耳。仲尼编诗为燕享祭祀之时用以歌,而非用以说义也。古之诗今之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诵其文而说其义可乎?不幸腐儒之说起,齐鲁韩毛四家各为序训而以说相高,汉朝又立之学官,以义理相授,遂使声歌之音,淹没而无闻。[9](P883)
虽说郑樵此文尚有许多可商榷处,但是其诗乐关系之述当是确论。宋人程大昌《考古编·诗论》将“南”归于乐调一种,更是成为之后学界共识。[10](P12)近人顾颉刚《论<诗>所论全为乐诗》[11](P301-342)一文更是认为“诗三百”全部可入乐。上述可证,诗乐共体在先秦时期确为《诗经》事实。既是如此,《关雎》便不可能一直只是一支乐曲而无文本记录。
诗乐关系虽然紧密,但两者并非一定是同时创作。从“歌咏言”到“歌咏诗”之间可能还有一段历史需要连接,大致便是民间谣词佚诗改编入乐的历史过程。故在诗与乐还未如后来那般匹配成一套完整礼仪程序之前,上古古乐是有可能只有乐而无辞的,《汉书》有云:
昔黄帝作《咸池》,颛顼作《六茎》,帝喾作《五英》,尧作《大章》,舜作《招》,禹作《夏》,汤作《濩》,武王作《武》,周王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招》,继《尧》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华茂也。《六茎》,及根茎也。《咸池》,备矣。……国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学歌九德,诵六诗,习六舞、五声、八音之和。[12](1038)
既然是“歌九德”而“诵六诗”,只用于“歌”的古乐里可能便没有诗文本存在,很有可能是一些表达庄严肃穆之情的引吭之音调——这些单纯的“德音”带有浓重的道德内涵。那《关雎》有无可能就是这种诗乐共体前的纯古乐存在?笔者认为不太可能。从上述古乐名能看到古乐名大都可概括其乐之宏旨,即便在《汉书》正文中不太能理解,藉由颜师古注也能窥明其义。如颜注有:“勺读曰酌。酌,取也。”“夏,大也。二帝谓尧、舜。”“韶之言绍,故曰继《尧》也。”“咸,皆也。池,言其包容浸润也。故云备矣。”(《汉书》卷二十二)凡此种种,皆是说明古乐名能直括主题——并且非一般主题,都是战功或者盛德一类之宏伟叙事。《关雎》之题也必其来有自,不管是乐曲主题还是文本主旨,都应该与《关雎》题目相关。然从《关雎》题目看来,不能表达如古乐乐名一般史诗叙事,且此题目与上述乐名用词也不太相仿,故而《关雎》也不太可能是上古纯古乐之流传。还有,从《乡饮酒礼》“工歌《鹿鸣》……乃间歌《鱼丽》,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燕礼》“遂歌乡乐,《周南》、《关雎》、《葛覃》”(阮元本《仪礼注疏》卷十一)可看到,《关雎》在后世已有演奏,并且还有专门乐工来“歌”。王力先生《古汉语词典》解“歌”有一义项为“能唱的歌曲或诗”,引《吕氏春秋·音初》“乃作为‘破斧’之歌”为例证。[13](P539)同时,“歌”也引申有动词义,便是歌唱歌曲或诗。《吕氏春秋》与《礼记》相去不远,其间常用词所含意义也不应大相径庭,所以“歌《关雎》”之《关雎》,此时应是有诗歌文本存在的。故“《关雎》在战国中期前一直有乐无辞”的假设不成立。《关雎》文本在先秦一直存在应无需质疑。
二、关于《关雎》地位演变及传播范围问题
(一)多评乐少评诗不是先秦人的学术批评惯例
在文本存在的时代,《关雎》被“忽略”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提出的假设是:先秦时代对于诗乐共同体的学术批评是否多集中在“乐”而少在“诗”?是否因为这个缘故,才致使今日所见之先秦传世文献鲜少对《关雎》诗歌文本进行评论。笔者核查相关文献,发现并非如此。
先看儒家。《论语》中涉及到《诗》评十余处,谨举为人熟知的二例。《学而》篇有云:“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思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其中孔子与子贡师徒关于《诗》的对话已经彰显出儒门对于《诗》文本本身的意旨内涵探讨。《八佾》篇云:“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以与言诗已矣。’”此章所含儒门的阐释理路意味更浓一些,这也能够说明孔子及其弟子面对《诗》的时候,无论文本还是乐曲,都在其学术批评视域之中。
再如道家。道家著作中引诗较少,主要在《庄子》一书。明引诗句在《庄子》中亦少见,只《杂篇·外物》记载了一句逸诗:“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褥,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顪,汝以金椎控其颐,徐别无颊,无伤口中珠!”[14](P927)此句逸诗讽刺儒者的虚伪,刻画得很深刻。这也是由《诗》之文本出发,进行意涵解构的演绎。《天下》篇更有“《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庄子集释》卷十下)之论,其中明言“《诗》以道志”而非“诗以歌志”,确能看出庄子或其道家弟子,对《诗》文本的深刻内涵已有准确体会和把握。说明道家对《诗》文本也并非熟视无睹、不予置评。
墨家亦是。《墨子·兼爱下》云:“且不为《誓命》与《汤说》为然,《周诗》即亦犹是也。《周诗》曰:‘王道荡荡,不偏不党,王道平平,不党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厎,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视。’若吾言非语道之谓也,古者文武为正,均分赏贤罚暴,勿有亲戚弟兄之所阿。即此文武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於文武取法焉。不识天下之人,所以皆闻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又云:“先王之所书,《大雅》之所道曰:‘无言而不雠,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即此言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不识天下之士,所以皆闻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 (《墨子闲诂》卷四)从这两段文字可窥,墨家引《诗》也大多作论据用,符合每篇之章旨意涵。“王道荡荡,不偏不党,王道平平,不党不偏”“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等诗句都很显白地佐证了墨子的“兼爱”观点,可说墨家亦对《诗》文本有很清晰的解读思路。
后看法家。《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云:“诗曰:‘不躬不亲,庶民不信。’傅说之以‘无衣紫’,缓之以郑简、宋襄,责之以尊厚耕战。夫不明分,不责诚,而以躬亲位下,且为下走睡卧,与夫掩弊微服。孔丘不知,故称犹盂。邹君不知,故先自僇。明主之道,如叔向赋猎,与昭侯之奚听也。”[15](P264-265)韩非子用儒家常引之诗反来驳斥儒家,认为若君主事事躬亲,则君臣职分不明,且将失去君主之“势”。另《说林上》载有一件趣事:“温人之周,周不纳客,问曰:‘客耶?’对曰:‘主人也。’问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问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谓非客,何也?’对曰:‘臣少而诵《诗》,《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则我天子之臣,而又为客哉?故曰主人也。’君乃使出之。”(《韩非子集解》第二十二篇)韩非子引温人略带戏谑口吻之语说明了周人诗乐礼教的迂腐,以诗反诗,足够证明法家在对《诗》文本的应用上手拈来,也不存在在学术批评领域故意忽略《诗》文本的情况。
更为人所熟知的是,《左传》所载春秋鲁僖23年(前637)至鲁定公4年(前506)132年间外交场合赋《诗》、引《诗》、歌《诗》就达279次,其中仅称引《诗》句以说理就达181次184首,《国语》亦称引26次38首,且每次称引都精准确切、说理深刻,更可窥见当时权力上层和知识分子对“诗三百”文本已有相当高的掌握水平。
以上例证足以说明先秦的学术批评绝没有忽略“诗三百”具体篇章文本,相反,时人对于《诗》文本本身都有着独特的把握和深刻理解,并纷纷自觉运用“诗三百”这一学术公器来武装自身的论点。因此,关于“先秦学术批评惯例多评乐少评诗”的假设,也是不成立的。可见,《关雎》被“忽略”绝不是因为学术方法和视域问题,其传播初期诗学地位的形成更应有其他因素。
(二)《关雎》当为王室房中之乐
经过对上述问题的讨论,我们已将探讨问题的可能范围大大缩小了。《关雎》在先秦应该是诗乐共存的状态,没有经过亡佚或人为删减,在诸家学术批评视域中,也不存在诗与乐偏废的情况。故而,先秦传世文献中,仅有寥寥数语涉及《关雎》最为可能的原因,很可能是《关雎》之诗和乐只在小范围、特定人群中流布,未能得到广泛传播。汉代被列为《诗》文本首篇后才骤然重要起来。
笔者以为,《关雎》很有可能是房中之乐。这样推测,有以下理由。
首先,《房中乐》在经书上确有明载。《仪礼·燕礼》:“若与四方之宾燕……有《房中之乐》。”郑玄注:“弦歌《周南》《召南》之诗,而不用钟磬之节也。谓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讽诵,以事其君子。”(嘉庆阮元刊刻本)《关雎》属《周南》,当在此列。故此,《关雎》传播范围已经限于权力高层间,是其用于享乐的专属曲目。但是,既属演奏曲目,便不可能不会向外流传,且《周南》里《卷耳》《兔苴》等篇目在《左传》里皆有记载,可证《关雎》不可能仅因为属于权力高层便在文献中销声匿迹。《房中乐》在《仪礼》经文和郑玄注文中可窥其用于两种场合:一是宴请四方之客,二便是郑注所云“后、夫人之所讽诵,以事其君子”。此种情况在后世《汉书》中更有详载,《汉书·礼乐志》云:“汉兴,乐家有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大乐官……又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乐》,至秦名曰《寿人》。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汉书》卷二十二)这段文字详尽记录了刘汉王朝取得天下后,对于诗乐礼制的因袭传承,可见《房中乐》之礼制应该也与先秦一脉相承。笔者以为,《关雎》与其他《周南》《召南》稍有不同处,可能便因为它属于后妃专诵之曲,而对象也只有君主而已。至于前述《乡饮酒礼》《燕礼》中明载有演奏《关雎》之事,笔者以为,这说明《关雎》在君主专属到后世广为流传中有一个过渡过程,而由君主专乐变为燕乐,也正属于这个渐变过程。笔者猜想,这个过程应该出现在战国中晚期,大致与上博简所在时代相同,《关雎》已经有所经学化而非君王专属之“房中情歌”了。而先秦末期诸学后人对《关雎》一方面是还不甚了解,另一方面是关于其文本评论,还无师传先例,加之战事纷争,经学化后的《关雎》主旨并非迎合时宜。由是,这个局面直至汉时才得到极大改变。
其次,查今本《关雎》内容,“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此类种种应是极为符合“后妃所诵”“所事君子”的历史场景,文本多涉及男女情窦初萌,表达情绪有约有节,贴合房中所歌的要求。并且文本中“君子”“淑女”“琴瑟”“钟鼓”等字眼实非普通民间场景之描述,可见描绘的乃是权贵欢情享乐之画面。这也调和了历来关于《关雎》属于民间还是贵族的矛盾,它应是属于贵族幻想朴素民间情爱的王室专属乐歌。
再次,证《关雎》乃王室房中乐,《论语》中孔子之论亦不会有所龃龉。孔子精通音律,传世文献记载翔实。《论语·阳货》:“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八佾》:“子语鲁太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子罕》:“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上文种种皆说明孔子对音乐是造诣深厚的,并且他晚年身处鲁国顾问高位,能接触到权贵专属乐曲也属正常。
最后,《关雎》的分章也值得注意。《毛传》分为三章,首章四句,后二章各八句。郑玄可能以为此分法有违《诗经》各章句数相等之例,改分为五章,每章四句,然而他的重分又违背了章句对应之例。根据翟相君先生的看法,以为是三章,每章八句,排列如下: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16]
翟氏这一思路应该引起重视。若翟氏推论成立,《关雎》确存在残佚,那么便说明《关雎》在先秦流传不广,否则是不太会出现残佚而无人增补现象的。这也证明了《关雎》极有可能属于宫廷私人之物,才致使在流传过程中少有人知其原状,导致最终残损数千年而无人察晓。也只有是贵族高层的私乐才能在鲜少关注流传的情况下还能大致完整地保留下来。在孔子时代,《关雎》应该已经在社会上层流传,但其地位应该不高,最重要的证据是《左传》里被称引或赋诵的诗句达数百条,但却无一涉及《关雎》。而且先秦诸子也对它鲜有评价。直至战国中后期,《关雎》可能经过经学化后,才慢慢成为如上博简主人这般贵族的阅读之物。
结语
《关雎》文本在先秦至汉数百年间,地位和传播范围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此间有许多假设和问题需要推敲探讨。在对“有乐无辞”“先秦学术批评惯例”“王室房中之乐”等等假设议题一一推敲论证之后,最终认为《关雎》为君主专属私乐的可能性较大,逻辑也能自洽。但是在更新材料出现之前,有关先秦的学术探讨都存在有转圜和补充的余地,《关雎》的诗学讨论更是如此。其作为《诗经》开篇阐扬诗教之重点,学界对它的关注焦点不应再仅仅限于其对后世诗学阐释的影响上,更应把目光拓至其初期流传阶段,重视《诗经》文本初始传播和汇集形成中的流变现象,这对于以后《诗经》更广视域的研究当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韩婴 撰,许维遹 校释:韩诗外传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3]金开诚 董洪利 高路明 校注. 屈原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6.
[4]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5]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6]李学勤.诗论说关雎等七篇释义[J].齐鲁学刊,2002,(2).
[7]张西堂:诗经六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8]孙诒让 撰,孙启治 点校:墨子闲诂[M].北京:中华书局,2001.
[9]郑樵 撰,王树民 点校:通志二十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5.
[10]程大昌 撰,刘尚荣 点校:考古编·续考古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1]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2]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4]王力.古汉语字典[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5]郭庆藩 撰,王孝鱼 点校: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
[16]王先谦 撰,钟哲 点校: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
[1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8]翟相君:《<关雎>系脱简残篇》[J].北京师院学报,198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