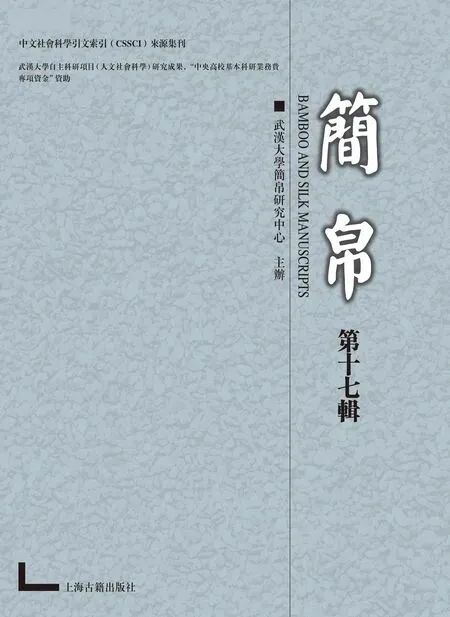時令説的展開
——北大漢簡《陰陽家言》與銀雀山漢簡“陰陽時令、占候之類”
[日] 湯淺邦弘
關鍵詞: 陰陽家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 銀雀山漢墓竹簡 時令説
序 言
2015年9月,《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叁)》得以刊行。(1)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該套書中,首先於2012年12月刊行了(貳)(内容爲《老子》),後於2014年12月刊行了(伍)(内容爲《節》《雨書》《揕輿》《荆決》《六博》)。本書則在其後,與(壹)(内容爲《蒼頡篇》)同時出版。
在第三分册中,收録有《周馴》《趙正書》《儒家説叢》《陰陽家言》等四種文獻。本稿即以其中的《陰陽家言》爲主進行探討。“陰陽家”,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被列爲諸子百家的首位,但是並未留下完整文獻,因此其實態尚有諸多不明之處。(2)《史記·太史公自序》中爲“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此外,據《漢書·藝文志》記載,其中含有《鄒子》49篇、《容成氏》14篇等,共計21家,369篇,現皆已佚失。因此,本稿將通過解讀《陰陽家言》,對其中陰陽家的思想,特别是對時令思想的形成與發展進行考察。
一、 《陰陽家言》的概要
首先,根據《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叁)》釋文注釋的“説明”,先將本文獻的概要總結如下。
原釋文的整理者爲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的朱鳳瀚氏及陳侃理氏。竹簡共17枚。完簡長29.5~29.6釐米,寬0.9釐米,綴合爲12枚,推測尚有缺簡。未發現篇題,“陰陽家言”爲根據内容所起的擬稱。
全體押韻,大致可以分爲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第一簡~第九簡)爲天人感應,論述了政治違反時令,人君的事業不切實際時,會帶來怎樣的災異。第二部分(第十簡,第十一簡)與“四時改火”有關,論述了順應天時。第三部分(第十二簡)論述了天氣地氣如何産生風、雨、霧等自然現象。其中,論述災異的段落中,有與銀雀山漢墓竹簡《人君不善之應》相類似的句子,大致與《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中的“陰陽家”内容一致。
但是,在原釋文中也稱,儘管整體上提出了第一簡到第十二簡的排序方案,但因爲竹簡殘缺較多,右側的三個段落在原書中位於何處尚且不明,因此該竹簡排序僅供參考,在編連上或有其他的可能性。
二、 竹簡排序的問題
原釋文爲何在竹簡排序上提出如此不自信的見解?其原因在於竹簡背面的劃痕。所謂劃痕,或是爲了防止竹簡的誤脱,而在背面所劃出的傷狀斜綫。第二分册的《老子》在公開之際,其劃痕狀況與《老子》文本的走勢高度一致而引發關注。另外,在其後公開的《節》《雨書》《揕輿》《荆決》《六博》《蒼頡篇》等文獻中也同樣發現此類劃痕,在竹簡的排序上,起到了極大的輔助作用。劃痕成了將散亂的竹簡進行復原之際的有效指標。换言之,也可以説,無視劃痕存在的重新排序是無效的。
但是,在《陰陽家言》中,由圖版之後附載的“簡背劃痕示意圖”可見,第三簡、第四簡以外的竹簡的確可以看到劃痕,但是從其狀態而言,可以明顯確認連結的,僅第五簡與第六簡,第十簡與第十一簡而已,其他劃痕未見具有連續性。儘管如此,在原釋文,對第一簡至第十二簡進行了排序,還將全體分爲三個段落,例如,認爲第一簡至第九簡基本相連,爲第一部分。但是,對於其排序與劃痕狀況基本不對應的問題,並未進行任何説明。
此後,對於竹簡的排序問題,學者們提出了一些徹底的修改案。例如,王寧氏《北大簡〈陰陽家言〉1~9簡的編連問題》中,對於第一部分提出了以下的重排方案。(3)王寧: 《北大簡〈陰陽家言〉1~9簡的編連問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2015年12月20日,http: //www.gwz.fudan.edu.cn/Web/Show/2684。
第一段 1……4+5+6……8
第二段 ……2……7……3
第三段 ……9……
此外,龐壯城氏在《北大漢簡〈陰陽家言〉編聯問題》中,還提出以下的重排方案。(4)龐壯城: 《北大漢簡〈陰陽家言〉編聯問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2016年2月9日,http: //www.gwz.fudan.edu.cn/Web/Show/2741。
第一組 1,□,□,2,□,12
第二組 3
第三組 4,5,6
第四組 □,7,□,8,□,□,11
第五組 9
第六組 10
之所以出現此類修正案,其根本原因還是原釋文的竹簡排序與劃痕狀況不符。王寧氏將内容分爲與原釋文不同的三個段落,龐壯城氏又將文獻整體重編爲六組,皆爲苦心之作。但是,即使如此重新排序,全體文獻的通讀也依舊困難重重。如上兩者的排序方案之中,在現存竹簡之間,還必須假設具有“……”或“□”等未見竹簡,否則排序方案無法成立。
因此在本稿中,在尊重原釋文以及其後的重排方案的前提下,暫且對此排序問題進行保留。爲方便起見,首先按照原釋文的排序,對竹簡逐一釋讀之後,再結合劃痕狀況,重新對排序問題進行綜合考察。
三、 《陰陽家言》釋讀
以下,將按照原釋文的竹簡排序,對竹簡逐一釋讀。並以“原文”“現代文大意”“語注”的順序羅列如下。“原文”,是在尊重原釋文的基礎上,加以綜合考察後確定下來的内容。對於原釋文進行重新釋讀的文字,將在“語注”中進行解説。01、02等爲原釋文的竹簡編號。[ ]爲抄寫之際誤脱之字,【 】爲原釋文對竹簡不明之字加以復原後的文字。
原 文
春氣作生,君氣作仁,不仁而張,六風王王,公門改行,中壟之殃。夏氣作緩,不緩而張,01
實者榮,國家失情,必害卿正。冬氣宜藏,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者生,宜蟄者【鳴,宜】02
實者榮,國家失情,必害卿正。宜冬不冬,萬物皆[失其]龍。宜春不春,萬物皆失其倫。宜夏03
甚張,誅殺甚明,萬物銷亡,公門改行,國有大喪,中壟之殃。故天子動樂,讋春三04
旬,讋秋三旬。此謂與天地同和。人君好藏,掌窌十年而弗發,則地奪之財。好治宫05
室,十年而不息,則天奪之時。昔耤斂無義,使令不時,則民奪之謀矣。人君好埵爐,06
反山求金鐵,則地不能凍,水不能恒,宜死者生,宜蟄者鳴,宜實者榮,國家失情,07
野有熯者,歷八時,則妃主崩,國妖死,多女喪。人君好水居漸臺,行舟飲酒移居,08
大臣,則天下覆。參,則大臣疾,榮芋零,苴多螣,山多螟,大兵起,天下訖。九,則君卒矣。秋09
之火,秋食金燧之火,□於□□十二室,十二竈而月迭鑽燧易火,而必食歲之所美,10
是故天氣發,地氣弗應,則爲風。地氣發,天氣弗應,則爲霧。天地相應,則爲雨,雨者12
現代文大意
春氣引發“生”,君體引發“仁”。(如果君主)不仁而擴展(事業),則强風大作,朝廷大事迫於更改,中央的墳丘遭遇災禍。夏氣引發“緩”(緩和),(如果君主)不緩而擴展(事業),01
宜結果者開花,國家失去常態,必有害於重臣。冬氣宜“藏”。宜藏而不藏,濕氣溢出,宜死者生,宜蟄伏者鳴叫,02
宜結果者開花,國家失去常態,必有害於重臣。宜冬而不似冬,則萬物皆失其調和。宜春而不似春,則萬物皆失其秩序。宜夏 03
過於張,則誅殺大爲盛行,萬物消亡,朝廷大事迫於更改,國家將有大喪(衆多人民死亡),中央的墳丘將有災異。因此天子發動音樂,相當於春之三04
十日,秋之三十日。此謂與天地同和。若人君喜好收藏,倉庫的管理官十年不開放食糧,則地將奪走其財寶。若(人君)喜好宫05
殿的建設,十年也未停止,則天將奪走其時。若(人君)喜好收奪,耕作徵税毫無限度,所發指令不合時宜,則人民將奪走其謀。若人君喜好埵爐(製鐵的工具)06
挖山以求金鐵,則大地(冬季)也不會上凍,水也不會正常流動,宜死者生,宜蟄伏者鳴叫,宜結果者開花,國家失去常態07
草原發生火災,經過八時(九十六日),妃主(天子的嬪妃或女兒)崩亡,國中子女多有亡故。若人君喜好臨水居舍以及觀景樓臺,浮舟飲酒,移動居所,08
……大臣,則天下翻覆。若持續三次,則大臣病倒,花草枯落,麻上多有螣(食葉昆虫),山中多有螟虫,發生大規模的戰争,天下也會終結。若連續九次,則君主將會亡故。秋09
……之火,秋季之食以金燧之火(加工食品),□於□□十二室以及十二竈而每月變更鑽,更新火種,則必定可以吃到當年的美味。10
易火,而發火之正。人君消費金屬以及木炭,(喜好)製鐵的工具而燃燒金石。達其神髄者,能製其命。達其法者11
因此若發動天氣,而地氣不應,則成爲風。若發動地氣,而天氣不應,則成爲霧。天與地相應,則成爲雨。所謂雨12
語 注
(1) 春氣作生,君氣作仁: 原注中指出了,《爾雅·釋天》的“春爲發生”,《論衡·變動》篇的“使物生者,春也”,《鹽鐵論·論災》篇的“故春生,仁。夏長,德。秋成,義。冬藏,禮”等。由此,可知“春”“生”“仁”的關係。此外,在《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篇中也有,“東方者木,農之本。司農尚仁”,可知在漢代,已經意識到五行中,東方(木,春)與仁的對應關係。
(2) 不仁而張: 若不具備春君之氣的“仁”而擴張事業。因爲“張”與春之特性的萬物發生有關,因此其本身並未被否定,但“不仁”而“張”則不善。另外,《爾雅·釋詁》有“張,施”,若援引之,則還具有君主不具備仁德而施行政策、事業之意。
(3) 六風: 原注指出,在《周禮·春官》保章氏“以十有二風”的賈公彦疏中有“風即氣也”,在《漢書·律曆志》“天有六氣”的顔師古注中有“張晏曰: 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另外,還指出在《春秋左氏傳》昭公元年中,也有“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
(4) 王王: 原注釋讀爲“遑遑”或“荒荒”。王寧氏指出在《廣韻》中有“王,大也”。總之,是指發生異常天氣。
(5) 公門改行: 公門,原注指出,在《春秋穀梁傳》莊公元年“主王姬者,必自公門”的范寧注中有“公門,朝之外門”。在此,並非是指“朝之外門”的建築物本身,而是暗示了朝廷及中央政府。而“改行”,或是指使該朝廷大事被迫更改的災禍。
(7) 夏氣作緩: 《淮南子·時則》中有“孟夏始緩,孟冬始急”,其高誘注中有“緩,四月陽安。急,十月寒蕭”,由此可知“夏”與“緩”的關聯性。此處也爲提示了夏氣的“緩”(緩和)。
(8) 不緩而張: 王寧氏從與春之句的對應上,認爲此處存在誤脱,認爲本應爲,“夏氣作緩,君氣作德,不德而張”。若春夏之句嚴密對應,則其説較妥。
(9) 實者榮:“實”爲果實,指植物秋季結果。“榮”指花開。《吕氏春秋·仲秋紀》中有“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大恐”,《管子·七臣七主》篇中有“草木夏落而秋榮,蟄蟲不藏”,《禮記·月令》篇中還有“孟秋……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由此可知,竹簡第二簡的該部分,在論述與秋有關的時令以及違反時令時的狀況。因此可以判斷,“夏氣作緩,不緩而張”與夏之事項中途完結的第一簡與該第二簡並未直接連結。而且,該句也見於第三簡中,參考第七簡的“宜死者生,宜蟄者鳴,宜實者榮”,則此處也同樣有可能,本來在“實”之前存在“宜”字。從此點上,也不得不對第一簡與第二簡的連接加以否認。
(10) 卿正: 原注指出《周禮·天官冢宰》中“一曰正”的賈公彦疏中,有“六卿稱正”,以“正”爲“長”之意。在此,意爲君主違反時令,結果造成了國家重臣爲災害所襲的後果。
(11) 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者生,宜蟄者【鳴,宜】: 原注指出《管子·輕重己》篇中“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者生,宜蟄者鳴,不藏之害也”,《管子·七臣七主》篇中“宜死者生,宜蟄者鳴”等類似句。若違反冬之時令,則會引起濕暖之氣上升,冬眠的動物開始鳴叫等異常現象。“蟄”,《吕氏春秋·孟春紀》中有“蟄蟲始振”,本來爲“孟春”的現象。“宜蟄者”之後,原釋文補入“鳴宜”二字。該二字在竹簡上難以辨認,但的確存在有兩個文字,第七簡中也有“宜死者生,宜蟄者鳴”,因此,如原釋文所推測或具有復原的可能性。但是,第二簡能否與第三簡連接則是另外一個問題。因爲,假設可作如此補充,則第二簡記載了冬之事項“宜死者生,宜蟄者鳴”,但是第三簡爲説明秋之事項的“宜實者榮”,季節順序發生逆轉,文意也無法通順。因此,第二簡與第三簡的連接,尚須加以慎重判斷。總之,在此《陰陽家言》中,“不仁而張”“不緩而張”“宜冬不冬”“宜春不春”“人君好藏”“人君好埵爐”“人君好水居漸臺”等,具有類似句不斷重複的特徵。此點同樣見於論述時令説的其他傳世文獻之中,具有按照季節重複記述類似句的傾向。因此,僅憑類似句,還無法立即判斷竹簡是否連接。
(12) 萬物皆【失其】龍(和): 原釋文隷定爲“萬物皆龍”,並讀“龍”作“讋”,作“忌”之意,文意略有不通。王寧氏也指出“讋”字不當,從與後文“萬物皆失其論(倫)”的對應關係上,推測此處誤脱“失其”二字,認爲本來爲“萬物皆失其龍”。並指出,《廣雅·釋詁》中有“龍,和也”,認爲此處爲“万物皆失其和”之意。此處以該推測爲妥。
(13) 萬物皆失其倫: 原釋文隷定爲“萬物皆失其論”,並讀“論”作“倫”。因字形類似,所以推測較爲妥當。原注中對於“倫”的字意並未特别言及,在此,當爲“倫序”(秩序)之意。
(14) 萬物銷亡: 《莊子·天地》篇有“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因爲違反時令導致物事消亡。
(15) 天子動樂,讋春三旬,讋秋三旬: 對於天子與音樂的關係,原注指出《禮記·樂記》篇中的“大樂與天地同和”,鄭玄注有“言順天地之氣與其數也”。“”,原釋文隷定爲“春三旬,秋三旬”,並讀“”作“讋”,但是原注並未特别言及文意。若如前記按“忌”取意,則略有不通。王寧氏,如前記讀作“遘(遘)”,並指出《説文解字》中有“遘,遇也”,認爲此處爲“天子動樂要在春三旬和秋三旬”之意。天子通過音樂與上天溝通的思想容易理解,但於春秋各三十日這一點頗耐人尋味。或爲對整年沉湎於音樂的否定。“三旬”,《吕氏春秋》十二紀中,常見將“三旬”作爲因遵守時令而帶來恩恵的期間的例子。例如,“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季春紀》《孟夏紀》),“行之是令,而涼風至三旬”(《孟秋紀》)等。而且,在《吕氏春秋》中,有關音樂的篇章集中於“夏”。此外,第四簡與第五簡在文意上極可能接續,但是第四簡背面並無劃痕,僅憑劃痕狀態尚無法判斷。
(16) 掌窌: 原注指出《荀子·議兵》篇中有“必發夫掌窌之粟以食之”,楊倞注中有“地藏曰掌,掌窌,主倉粟之官”。此處並非在説“掌窌”官職本身,而是在説人君吝嗇而固執於收藏,不願打開穀物倉庫。
(17) 好治宫室: 原釋文隷定爲“好治宫窒”,讀“窒”作“室”。《晏子春秋·内篇·雑下》中有“晏子辭曰:‘吾君好治宫室,民之力弊矣’”。意爲異常喜好宫殿建築。其結果,《晏子春秋》中爲民力疲弊,而此處爲“天奪之時”,具有特色。
(18) 昔耤斂無義: 原釋文以“昔”字爲衍文。王寧氏則釋讀“昔”爲“索”,推斷脱落了“人君好”。前後句均有“人君好”,因此該推斷較爲妥當。總之,是指喜好收奪,無限度徵税等君主的不當行爲。
(19) 人君好埵爐: 原釋文隷定爲“人君好垂盧”,並讀作“人君好埵爐”。如原注所指出的,銀雀山漢簡[貳]《人君不善之應》中可見“人君好垂(埵)盧(爐)槖,抏金盧,反山破石,磿(歷)二時,五穀椅橋”等類似文句。(5)以下銀雀山漢簡各篇皆引自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 《銀雀山漢墓竹簡[貳]》,文物出版社2010年。意爲君主喜好製鐵鑄造,於是爲了得到礦石原料不斷過度挖掘山地。若從此文義,第六簡可能與第七簡接續,但是竹簡背面的劃痕錯位,由此尚難以判斷兩簡必定接續。
(20) 反山求金鐵: 如上所示,銀雀山漢簡《人君不善之應》中可見類似文句。而且在銀雀山漢簡《禁》中,也有“定秋下霜,毋以聚衆鑿山出金石”,作爲秋之時節的禁止事項,舉出了動員大衆開闢山地,挖掘金石。
(21) 水不能恒: 此處從原釋文讀法。王寧氏讀作“水不能凝(冰)”,與前句“地不能涷(凍)”,認爲均指冬季的異常事態。但是,“恒”也可解釋爲水(川)如通常一樣不流動。
(22) 野有熯者,歷八時: 原釋文隷定爲“磨八時”,並將“磨”讀作“歷”,意爲違反時令導致自然發生的火災不斷。“歷八時”,在銀雀山漢簡《人君不善之應》中有“歷八時而國亡”。此外,銀雀山漢簡《三十時》中,有“五時,六十日”“十時,百廿日”“十四時,百六十八日”等,整理者還指出十二日爲一時,認爲一七四四簡簡首爲“【八】時,九十六日”。傳世文獻中未見“歷八時”的用例,參照《三十時》的記述,則可理解爲九十六日。時令説一向多以四時(四季)爲主,因爲“十二”是天文曆法的基本數,所以可以認爲或存在基於十二的其他系統的時令説。但是若如此,在該《陰陽家言》中,以春夏秋冬四時爲基礎的思想,與將十二日作爲“一時”的思想並存。另外,王寧氏推測,在銀雀山漢簡《人君不善之應》的類似問句“磿(歷)六時,則林有□者矣”的缺文中當填入“熯”字。“熯”爲野火(山野的自然火災)之意。
(23) 妃主崩: 原注解釋“妃主”爲“后妃和公主”,王寧氏則注目於“崩”(原釋文隷定爲“傰”)字,指出在《禮記·曲禮下》篇中有“天子死曰崩”,此處“妃主”當爲“王(皇)后或國君的正室夫人之用事者”,並指出了傳世文獻中多見“女主”。
(24) 國妖死: 原釋文隷定爲“國訞死”,並讀“訞”作“妖”。王寧氏指出《管子·七臣七主》篇有“民多夭死”,推測此處“國”之後脱落“多”字。並且,此前簡文的“野有熯者”“妃主崩”均論述了陽氣過盛時的災害。陽氣過盛則陰氣衰亡,由此而引發屬“陰”的女性死亡。
(25) 人君好水居漸臺: 原釋文隷定爲“人君好水居湛臺”,並讀“湛”作“漸”。“漸臺”爲池中所設的觀景台。原注舉出銀雀山漢簡《人君不善之應》中“人君好水居漸臺,極舟飲酒游居,磿(歷)二時,五穀湛涂”,以及《漢書·郊祀志》中“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泰液”等,顔師古注中“漸,浸也。臺在池中,爲水所浸,故曰漸臺”等。此外,若根據劉向《列女傳·辯通·齊鍾離春》中,“漸臺五重,黄金白玉,琅玗籠疏,翡翠珠璣,幕絡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則“漸臺”不單是建筑物,也是君主奢侈的象徵,其構築過度將會使人民疲憊不堪。此處也是在論述,君主喜好戲水游船,脱離政務,而在池中所作高殿中終日遊玩。
(26) 榮芋零: 原釋文隷定爲“榮芋令”,並讀“令”作“零”。“零”爲零落,草花枯萎之意。“芋”字,從原注讀作“華”。
(27) 大臣,則天下覆。參,則大臣疾,榮芋零,苴多螣,山多螟,大兵起,天下訖。九,則君卒矣: 對於該節,王寧氏舉出銀雀山漢簡《爲政不善之應》中“爲正(政)壹擾則虫,再則蛾,三則冥(螟),四則踲,五則螣,六則兵作,七則君”,“爲正(政)壹暴則胞(雹),再則如垸(丸),三則盈握,四則穿屋,五則如杚,六則兵作,七則君”等,認爲該處有文字省略,本來全文應爲“【爲政壹□則□】大臣,【再】則天下覆,參(三)則大臣疾,【四則】榮芋(華)令(零),【五則】苴多螣,【六則】山多螟,【七則】大兵起,【八則】天下訖,九則君卒矣”,爲論述災害程度逐漸增加的一節。但是,若參考銀雀山漢簡《爲政不善之應》,推測此處也是設定爲從“壹”至“九”的階段,則略有疑問。若如此,則爲何此處只記述“參”與“九”?另外,在銀雀山漢簡《爲政不善之應》中,將君主死亡的最壞事態設定爲“七”,而此處爲“九”。因此,此處難以設想只是單純漏寫了其他數字。銀雀山漢簡與北大漢簡均使用了類似文句,但道理卻不同。例如,此處僅見“參”與“九”,並非是漏寫了其他數字,或爲“參”與“九”本身即具有極大意義。“參”,不只是三次之意,也表示數次、多、常常之意。而“九”也同樣,特别是表達了究極之數。若如此,則此處並非誤脱其他數字,而可能爲,“參”的結果導致從“大臣疾”到引起“天下訖”,而“九”的結果則導致了“君卒”。
(28) 苴多螣,山多螟: 原注舉出《管子·七臣七主》篇中“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苴多螣蟆,山多蟲螟”,《詩經·小雅·大田》中“去其螟螣”,以及毛傳中爲“食心曰螟,食葉曰螣”。“螣”“螟”均爲禍害穀物、植物的害虫。
(29) 之火: 從後文“秋食金燧之”推測,在其之前或可考慮存在有如“春食□□”等四字。但是第十簡上端與第九簡下端並無缺損,因此第九簡並未接續第十簡,或另存在其他一枚下端寫有“春食□□”之句的竹簡。
(30) 金燧: 原釋文隷定爲“金遂”,讀“遂”作“燧”。“金燧”爲從太陽取火之器。《禮記·内則》篇中有“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鄭玄注中有“金燧何取火於日,木燧鑽火也”。在此則論述了“秋”季進餐用火應由“金燧”取之。
(31) □於□□十二室: 原釋文隷定爲“□於□□十二窒”,並讀“窒”作“室”。王寧氏根據擴大的紅外綫照片以及文意,釋作“□於【作之】十二窒(室)”,認爲可補充“作之”二字,未詳。
(32) 月迭鑽燧易火: 原釋文隷定爲“月佚鐫【遂】昜火”。原釋文重視竹簡的“鐫”字與“易”字之間有一字左右空白,遂在此補充“遂(燧)”字,釋讀爲“月迭,鑽燧易火”。王寧氏以句讀位置有異,釋讀爲“月迭鑽燧易火”,取“根據時令按照月份更迭鑽燧改火”之意。另外,在《論語·陽貨》篇中有“舊穀既没,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其《集解》引馬融之説爲,“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按四季“改火”。在此,因爲有“月迭”,所以變爲按月採火的工具(打火石以及捻鑽錐),爲重新取火之意。
(33) 抏金炭: 原注舉出銀雀山漢簡《人君不善之應》中有“人君好垂(埵)盧(爐)槖,抏金盧”,推測其下方的“盧”字或爲“炭”字之誤。若參考前文以及《人君不善之應》,則此處也可以理解爲指違反時令的君主的行爲,但其與前後的文意接續未詳。
(34) 埵爐橐,鼓金石: 如原注所指出的,在銀雀山漢簡《人君不善之應》中可見“人君好垂(埵)盧(爐)槖,抏金盧,反山破石”的類似文句。且在第七簡中也有“人君好埵爐,反山破求金鐡”,所以,可能在“埵爐橐”之前脱落了“好”字。此外,“鼓”字,在《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中有“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顔師古注中有“如淳曰: 鑄銅鐵,扇熾火,謂之鼓”,因此,所謂“鼓金石”,即以鞴煽火融化金石之意。
(35) 天氣發,地氣弗應,則爲風: 原注指出,在《易緯乾鑿度》卷上有“陰陽升,所謂應者,地上有陰,而天上有陽,曰應”,“動於地之下,則應於天之下。動於地之中,則應於天之中。動於地之上,則應於天之上”,在其鄭玄注中有“天氣下降以感地,故地氣升動而應天也”。此處論述了風的産生機制。
(36) 地氣發,天氣弗應,則爲霧: 原注指出,類似文句在《爾雅·釋天》中有“天氣下,地不應曰雺,地氣發,天不應曰霧”。此處論述了霧的産生機制。
(37) 天地相應,則爲雨: 原注指出,《太平御覽·天部》所引《春秋元命苞》中有“陰陽和而爲雨”,《周易·睽》中有“往遇雨則吉”,其孔穎達疏中有“雨者陰陽交和之道也”。此外,對於第十二簡,龐壯城氏認爲,第一簡、第二簡均屬於第一組。但是,第一簡、第二簡的内容論述了“春氣”“夏氣”“冬氣”等四時,與第十二簡内容有異。廣泛言及自然現象一點上或有類似,但在竹簡接續的可能性上不得不説未詳。
四、 《陰陽家言》的構成與論理
以上,爲方便起見,對各簡分别進行了釋讀,由此,可總結如下。
第一,竹簡連接的問題。從文意及劃痕狀況態上均可判斷相互連接的,爲第五簡與第六簡。另外,雖然從劃痕上無法判斷,但是第四簡與第五簡連接的可能性極高。“讋春三旬,讋秋三旬”等語句的段落不可忽視。因此,可以確認第四簡,第五簡,第六簡相互連接。此點,王寧氏與龐壯城氏也均認可。
除此以外,是否還有直接連接的竹簡?從劃痕狀況而言,第十簡與第十一簡也似乎連續。的確,兩簡均言及“火”,在該點上具有類似性。王寧氏對其連接予以認可。但是,第十簡末尾的“而必食歲之所美”與第十一簡開頭部分的“易火而發火正”,在文意上是否連接尚不清晰。另外,第十一簡“人君抏金炭”以下的文意與“易火而發火正”如何連接也頗爲難解。因此,龐壯城氏認爲兩簡並未接續。此點暫且保留。
另外,劃痕也並非分毫不差連續標示。在其他北大漢簡上,也存在數毫米的誤差。在標示劃痕之際,竹材本身也會發生上下錯位。也可能雖然劃痕本身並無錯位,但其後由於竹簡上下端發生略微破損,因而導致錯位發生。劃痕確爲竹簡排序的有力證據,但如果過度重視劃痕的連續性,或固執於數毫米的誤差,反而會引起錯誤排序。對此點應該充分注意。
第二,思想特色的問題。從該文獻的擬稱“陰陽家言”可知,整體上大概論述了陰陽家的思想。只是,若詳細分析便可知,其中並存數種不同的理論論理。
首先,第一簡、第二簡、第三簡中論述了四時與人爲(君主行爲)的關係。認爲若不按照時節行人事,就會引發災害。第一簡言及“春”,第二簡言及“冬”,第三簡言及“冬”與“春”(末尾還可見“夏”字)。其相當於以四時爲基礎的時令説的思想(詳情後述)。
其次,也存在雖然未明示與四時的關係,但依然論述了因爲政者的不善而引發災害的内容。第四簡“甚張,誅殺甚明,萬物銷亡,公門改行,國有大喪,中壟之殃”中,與第一簡語句類似,但其後爲“故天子動樂……”,即其主體並非爲“君”而是“天子”。而在其後的第五簡、第六簡中,主體重新成爲“人君”,論述了人君與“天”“地”“民”的關係。第七簡雖未明示主體,或以人君的行爲當作問題所在,並記述了因其不善而引發災害。第八簡以“人君”的不善爲問題所在。雖然均未觸及春夏等四時,但在導致災害一點上卻是同樣。
此外,如前所述,需要注意第八簡的“八時”一語。若如同銀雀山漢簡《三十時》爲“九十六日”之意,則此處所設定的,是與四季以及月相異的“十二日”的時間標準。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對“陰陽家”進行説明稱,“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陰陽家的時間標準似爲四時,但在《漢書·藝文志》中,將陰陽家定義爲,“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其時間的標準並未僅限於四時。《陰陽家言》的“八時”,倒不如説與《藝文志》的定義相一致。
另外,與上述内容具有若干理論差異的,爲第九簡。如上述“語注”中所解説的,在此,通過“參”與“九”等表示程度的詞語,來表示不正的累積。在君主的不善招致災害一點上,與其他相同,但是,此處則主要是對(程度)過度時進行的論述(此點的思想史意義容後詳述)。
而第十簡,則更與第九簡不同。其内容,論述了四時與“改火”以及“食”的關係。在論述四時一點上,與第一簡、第二簡、第三簡等類似,但在此,並非論述了違反時令時引起的災害,而是論述了應該按照季節,或者按月改變火,當然,在其前後,尚有可能存在記述了違反如此“改火”而導致災害的竹簡,因此僅憑從該竹簡尚無法定論。
最後,第十二簡論述了風、霧、雨的發生機制。龐壯城氏將其與第一簡、第二簡共同分爲第一組。因爲第一簡、第二簡論述了四時與人爲的關係,所以便認爲第十二簡論述了其前提條件的自然現象的發生。但該觀點尚感唐突,因爲至少在其内容上並未與第一簡以及第二簡相連。
經過如此考察得知,在《陰陽家言》中,至少並存有四類理論。第一,論述了四時與人爲的關係。第二,不提與四時的關係,而論述了爲政者的不善導致災害。第三,特别論述了不正行爲的不斷積累,逐漸帶來極大災害。第四,論述了風、霧、雨等自然現象的發生機制。但是,其先後關係未詳。而且,各自的論述也欠周詳,如王寧氏所指出的,在《陰陽家言》中,必須假設尚存在數枚未見殘簡。僅此十二枚竹簡顯然無法構成一篇完整文獻。
對於《陰陽家言》而言,其竹簡連接以及段落分配尚無更爲確切的證據,因此,當前還是暫時停留在以上四類理論並存的理解上較爲妥當。雖然分爲四類,但該文獻的基調還是天人相關思想,尤其是論述了以四時爲標準的時令一點,是其最大的特徵。
五、 銀雀山漢簡“陰陽時令、占候之類”與《陰陽家言》
那麽,《陰陽家言》的思想特徵以及的歷史地位該如何理解?以下即以銀雀山漢墓竹簡爲綫索進行探討。
1972年,從中國山東省臨沂銀雀山的漢墓中出土了竹簡。1985年,《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公佈了其中的一部分。(6)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 《銀雀山漢墓竹簡[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一輯所收録的是銀雀山漢簡中的《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尉繚子》《晏子》《六韜》《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等。此外,還預告了將在第二輯中收録“佚書叢殘”,在第三輯中收録“散簡”“篇題木牘”“元光元年曆譜”等。
2010年1月,刊行了《銀雀山漢墓竹簡[貳]》。其内容爲第一輯中所預告的“佚書叢殘”部分,整體上,類别爲“論政論兵之類”“陰陽時令、占候之類”“其他”等三個部分。這三個部分在内容上並無緊密關聯,僅對在第一輯中偶爾漏編的部分進行整理後加以收録。其中,特别對與本稿有關的“陰陽時令、占候之類”加以關注。
在上文三的“語注”中已經提及的銀雀山漢簡《爲政不善之應》《人君不善之應》兩篇文獻,均分類在“陰陽時令、占候之類”之中。以下重新對其與《陰陽家言》的類似點進行整理。
首先爲《爲政不善之應》(一九二二簡~一九三一簡),如下文所示,共十一條。
爲正(政)壹擾則虫,再則蛾,三則冥(螟),四則踲,五則螣,六則兵作,七則君。
(一九二二簡)
爲正(政)壹暴則胞(雹),再則如垸(丸),三則盈握,四則穿屋,五則如杚,六則兵作,七則君。
(一九二三簡)
内容從“一”至“七”論述了君主的不善逐步積累的過程,各條最後的“七”中,均爲君主的死亡。如“語注”中所考察的,王寧氏以此爲根據,提出了《陰陽家言》第九簡的“【爲政壹□則□】大臣,【再】則天下覆,參(三)則大臣疾,【四則】榮芋(華)令(零),【五則】苴多螣,【六則】山多螟,【七則】大兵起,【八則】天下訖,九則君卒矣”復原方案。但是,在《陰陽家言》之中特别重視的是“參”與“九”,與《爲政不善之應》的理論有别的可能性,已如前述。
其次,《人君不善之應》(一九三三簡~一九四四簡),由“人君好”一條開始,在各條開頭均添加墨點“·”,明顯可以確認“·人君好”的,有五條。特别是以下兩條,與《陰陽家言》的關係引人注目。
·人君好水居漸臺,極舟飲酒游居,磿(歷)二時,五穀湛涂。磿(歷)四時,山出泉。磿(歷)六時,則石辟(劈)而出泉。磿(歷)八時而國亡。
(一九三三~一九三四簡)
·人君好垂(埵)盧(爐)槖,抏金盧〈炭〉,反山破石,磿(歷)二時,五穀椅橋。磿(歷)四時,大火焚臧(藏)。磿(歷)六時,則林有囗者矣。磿(歷)八時而國亡。
(一九三五~一九三六簡)
在此,與《陰陽家言》的類似句多處可見。同時,還需要注意“二時”“四時”“六時”“八時”等時間標準。如“語注”中所考察,在銀雀山漢簡《三十時》中,一時爲十二日,《陰陽家言》的“歷八時”,也可理解爲九十六日。若兩者相同,則在時間的標準方面,兩者也具有共同之處。
因此,北大漢簡《陰陽家言》與銀雀山漢簡《爲政不善之應》《人君不善之應》,君主的不正不斷積累並會在各個階段引發相應的災害,最後導致君主死亡或者國家滅亡,在此論旨上具有共同之處。而且,還可見到具體語句的重複。兩者的先後關係能否明確尚屬未詳,至少可以説在漢代初期,此類思想及語句已經廣爲思想家所共有。
但是,《陰陽家言》的理論,如前所總結的,至少有四類。其中,以“四時”爲標準的時令的思想具有特色。對此,《爲政不善之應》《人君不善之應》僅論述了爲政者不善的積累,其中並未介入季節的問題。
那麽,在銀雀山漢簡“陰陽時令、占候之類”中,是否具有四時及五行的要素?銀雀山漢簡殘缺較多,無法確認内容的文獻較多,以下即從該觀點,對於除《爲政不善之應》《人君不善之應》以外的分類在“陰陽時令、占候之類”中的主要文獻作一概述。(7)以下的各文獻名稱從《銀雀山漢墓竹簡[貳]》。
·《曹氏陰陽》: 從陰陽之氣對四時加以定義,並分對遵守和違反的情況分别加以論述。例如,“秋冬,陰也。春夏,陽也”(一六二三簡),“春之陰,正月三月。正月者刑”(一六二四簡),“夏之陰,五月也”(一六二五簡),“秋月者,諸物盡反(返)陰,以此徙,與物倶入静,吉。若以春夏徙,厥陰之陽散,有死之徒也”(一六二六簡)。
·《禁》: 按照四時的禁忌加以論述。例如,“春毋伐木,華生。夏毋犯火,精薪豐。秋毋犯金,當銀昭。冬毋犯水,甘泉出”(一六九七簡)。此内容,與《管子·七臣七主》篇所述的“四禁”類似。但是,如“故守國無禁,必傷於民。土無禁則年不長,木無禁則百體短,火無禁則物不豐,金無禁則筋”(一七二簡),爲“土”“木”“火”“金”之後若有“水無禁……”一句,則反映了五行説。
·《三十時》(擬稱): 如前所記,有“五時,六十日”“十時,百廿日”“十四時,百六十八日”等,並以十二日作爲一時。此外,如“【八】時,九十六日,霜氣也,殺氣也。以戰客勝。攻城,城不取,邑疫”(一七四四簡),在論述時節與軍事勝敗的關係一點上具有特色。
·《迎四時》(擬稱): 論述了天子迎四時之際的事項。例如,“故距冬日至【□】六日,天子迎春於東堂……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樂也。距春分卌六日,天子迎夏……”(一八八~一八八一簡)。如整理者在原注中所指出的,與《尚書大傳》的内容類似。
·《四時令》(擬稱): 記載了各月的天子的發令。例如,“七月朔日,天子出令,令西輔入御,令曰: 趣賦斂,興力事,審關市,斬伐勿禁,弋射田獵勿禦”(一八九六~一八九七簡),“十月朔日,命北輔入御,令曰: 繕甲厲兵,合計爲兵”(一七九七~一八九八簡)。如整理者在原注中所指出的,與《管子·五行》篇的内容類似。
·《五令》(擬稱): 舉出“德令”“義令”“惠令”“威令”“罰令”等五個政令,並與自然季節相對應,若違反則會發生災害。例如,“德令者,求諸孤幼不能自衣食者,廩餼之,以助生。毋壅塞川澤,發令者有咎,民多腸疾”(一九一~一九二簡),“故德令失則羽虫爲災”(一九一簡)。
·《不時之應》(擬稱): 若四季之中,不合時宜之事不斷積累(從一至六),則會在與之對應的階段上發生災害。例如,“春三月,一不時,孟種不熟。再不時,二種不熟。三不時,三種不熟。四不時,四種不熟。五不時,五種不熟。六不時,不出三歲降如脊”(一九一四~一九一五簡)。
如上所述,在銀雀山漢簡“陰陽時令、占候之類”中,明確可見以四時及五行爲背景的時令思想。本來,“陰陽時令、占候之類”也只是一個權宜之稱,分類於此的各文獻的成立狀況也尚未明暸。但是,可以明確得知的是,至少在漢代初期,廣義上的“陰陽家”的各種思想已經並存於世。可以認爲“陰陽時令、占候之類”,以及北大漢簡《陰陽家言》也是該思想之一。
六、 時令説的發展
那麽,與《吕氏春秋·十二紀》以及《禮記·月令》篇中典型的時令説之間的關係,又該如何考慮?在此,重新將《陰陽家言》中與時令説有關的部分列舉如下。
01 春氣作生,君氣作仁,不仁而張,六風王王,公門改行,中壟之殃。夏氣作緩,不緩而張,
02 實者榮,國家失情,必害卿正。冬氣宜藏,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者生,宜蟄者【鳴,宜】
03 實者榮,國家失情,必害卿正。宜冬不冬,萬物皆(失其)龍。宜春不春,萬物皆失其倫。宜夏
雖然竹簡的連接性尚未確定,但是在第一簡中有“春”與“夏”,第二簡中有“冬”,第三簡中有“冬”與“春”等語句,並記述了於各個季節違反時宜時帶來的災害。明顯是在論述時令的思想。
但是,若與《吕氏春秋·十二紀》以及《禮記·月令》篇等的時令説進行對比,便可發現兩者的相異點相違點。在此,作爲典型的時令説的代表,首先來看《吕氏春秋·十二紀》(正確的説法爲《十二紀》的各首章)。首先看開頭的“孟春”的記載,爲方便起見,在原文前添加①~⑤的號碼。
①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蔟。其數八。
②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齋。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
③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繁動。王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④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以從我始。無變天之道,無絶地之理,無亂人之紀。
⑤ 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槁,國乃有恐。行秋令,則民大疫,疾風暴雨數至,藜莠蓬蒿 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霜雪大摯,首種不入。
①論述了孟春之月的天文氣候等狀況。以及基於五行説,日則爲甲乙,帝則爲太皞,神則爲句芒,動物則爲鱗之類,音則爲五音内之角,律則爲太蔟,數則爲八等。
②論述了與之對應應當實施的宫中的各類大事,以及國家的政務等。在此也以太史之言,謂該月相當於五行之“木”。③爲有關農業的指示。此處也表達了對以五行爲基礎的方角“東”的重視。
④指出該月不可進行的事項(具體上如挙兵),如違反則會引起天災。另外,在⑤中,則論述了若在“孟春”行夏的政令,或行秋的政令,或行冬的政令時,將會引起何等災害。如上記述,被分爲十二個月,記述在十二紀的各首章,進行了極爲有序的編集。在《禮記·月令》篇中亦然。
由此可知,與此類典型的時令説進行比較,北大漢簡《陰陽家言》的特色爲,第一,幾乎未見有五行説的要素。在以上的十二紀中,基於五行説,列舉了天體的狀況以及音樂,方角,數字等,而在《陰陽家言》中,僅可見到與春之“生”相對的君德之“仁”的描述。
第二,十二紀以及月令,正如其名稱所示,通過一年十二個月來表示時令,而《陰陽家言》的基本框架卻爲四時。在此點上,倒是與《管子·七臣七主》篇的“四禁”的記述相近。但是,對於“歷八時”,雖解釋各異,卻很可能是以“十二日”爲單位的。若如此,該點也是一個較大的差異。
第三,是有關違反時令時的災害的記述。在以上的孟春紀中,在論述該月不得舉兵的同時,還個别記述了在孟春施行其他季節的政令時的災害。但是,《陰陽家言》的特色在於,論述了若違反季節會引發何等災害的同時,還記述了(與四時無關)若爲政者重複不善,則會段階性地發生何等災害這一點。
如此看來,可提出以下的一個假説。即,與《吕氏春秋·十二紀》中整然有序的時令説不同,在漢代初期可能並存有各種型態的時令説。在銀雀山漢簡“陰陽時令、占候之類”中,含有以“陰陽”,“四時”爲標準的,以“十二日”爲標準的,以及反映了五行思想等的數種文獻。另外,在北大漢簡《陰陽家言》中,也並存有以四時爲標準的理論以及其他不經過四時來論述天人相關思想的數種理論,難以認爲反映了强烈的五行思想。在與四時及五行無關的,因爲政者的不善而帶來災害一點上,不如認爲其論述了素朴的天人相關思想。
向來認爲,時令説的形成與五行説具有密切的關係。這是以《吕氏春秋·十二紀》以及《禮記·月令》篇爲標準的推測。在這一點上,《管子》的《幼官》篇、《四時》篇、《五行》篇和《淮南子·時則》等篇章相同,對於時令與五行説的關係進行了詳細論述。(8)久保田剛: 《時令説の基礎的研究》,(廣島)溪水社2000年。均在四時以外放置“中央(土)”,顯然,其中明確地反映了五行説。但是除此之外,還並存有與此類整然有序的時令説不同的,未必含有五行説,甚至不含四時的多種多樣的類型。通過北大漢簡以及銀雀山漢簡,便可以找到此類痕迹。
結 語
最後,就本文中所涉及的北大漢簡《陰陽家言》以及銀雀山漢簡“陰陽時令、占候之類”的成立時期進行確認,並對由此導出的時令説的發展狀況進行總結。
首先,北京大學西漢竹書的出土地以及埋葬時期不明。因爲在數術類竹簡中有“孝景元年”(前156)的紀年簡,所以竹簡的年代推定爲西漢中期,多數爲武帝時期(前141~前87)書寫。而銀雀山漢簡則推定書寫於西漢文帝、景帝時期至武帝初期。兩者均爲漢簡,又書寫於武帝時期之前,因此文獻的形成更早於此。同時,《吕氏春秋·十二紀》,其“序”推測記於秦王政六年(前241)。(9)參看陳奇猷: 《吕氏春秋校釋》,學林出版社1984年。
如此,則《陰陽家言》以及“陰陽時令、占候之類”被書於竹簡的時期尚在《吕氏春秋·十二紀》的寫成之後。但是,《陰陽家言》以及“陰陽時令、占候之類”所收文獻的形成時期尚無法斷言是在《吕氏春秋》以後。也有可能爲,思想成立於戰國時期,至漢代初期才被書寫。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在漢代初期還有與《吕氏春秋·十二紀》等典型的時令説不同類型的時令説並存。
但是,此類時令説並未流傳後世,可以説是被時代所淘汰了。其原因之一,可以舉出《禮記·月令》篇的成立。伴隨與五行説有密切關係的時令説完成版的登場,其他的思想便開始趨於消亡。
那麽,是否可以認爲,《陰陽家言》以及“陰陽時令、占候之類”等作爲被淘汰的思想,在思想史上並無多大的意義?的確,此類文獻在其後並未得到流傳而是最終消亡。但是,若爲政者的不善不斷積累,則其災難也會逐步增大的觀點,使人聯想起董仲舒的災異説。其思想的結構爲: 若爲政者違反天意施行不善,則天作爲警告而降下“災”害。爲政者見之必須反省,若無視警告繼續施行不善,則天最終會降下“異”常現象懲罰爲政者。(10)《春秋繁露·必仁且知》篇有“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這與《陰陽家言》中,對“參”以及“九”的不正階段的論述,以及“陰陽時令、占候之類”中,對從“一”至“七”的積累的論述,具有類似的觀點。當然,其繼承關係未必明朗,但是與董仲舒的災異説一脈相承的觀點本身,可能自古即有。這也是我們從新出土文獻中學到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