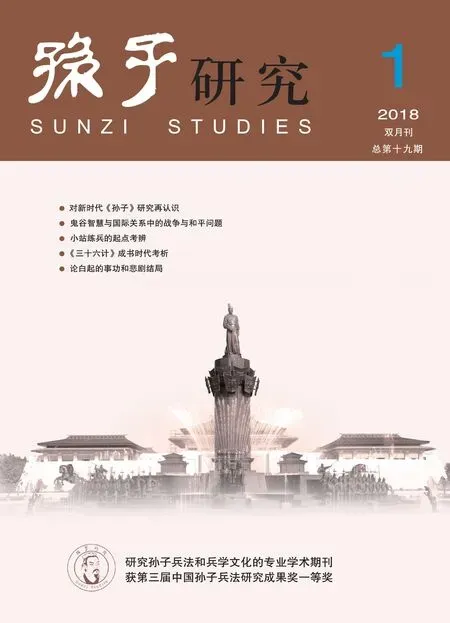《孙子兵法》的“中”之美
“中”,是从中国远古文化衍生出来的美学概念。“中”原是中国远古的仪式地点,人们在“中”的图腾杆下集合,议事,断决,誓师;在中杆下仰望天空,与天空对话。远古的仪式地点,经过千年的演化,最后成了帝王君临天下的行政中心,凸显了“中”在中国文化、中国美学形式中的核心地位。
对此,张法《中国美学史》作了系统阐释:“‘中’,意味着中心与四方的天下观念,‘中’是一种中国式的空间图式;‘中’,意味着日月运行有一个中心,春夏秋冬的往来围绕一个中心,历史兴衰循环有一个中心,‘中’又是一种中国式的时间图式;‘中’,意味着一个政治/地理/时空中心,一个中国式的帝王和以帝王为中心的等级制度;‘中’意味着一个居中的主体,居中而观天地、而理四方,表现为一种中国式的天地人合一的模式;‘中’,表现为以制度为标准的不偏不倚、不过不及的中正的社会/政治思想,表现为以自然为规律的阴阳相生、五行相成的中和的宇宙/哲学观念,从而‘中’,也是中国美学的核心。从时空和宇宙模式来看,这个‘中’是‘无’(天道),从政治/社会来看,这个‘中’体现为有(圣王);‘中’呈现为有无相生;‘中’体现为美学形式的时候,最好体现了‘中’的有无相生的文化意蕴。”
《孙子兵法》的“中”之美,既可以从远古文化、远古美学的这种演化发展轨迹,及其精髓要义中找到源头,同时又以个性化的魅力生动诠释了远古文化、远古美学的生命力、影响力与发展脉络。
一、中正之美
“中”字,作为一个词,它有不偏不倚、适合正好的意思,这是其义项之一,是其美学体现的主要方面。《书·吕刑》曰:“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蔡沉集传曰:“咸庶中正者,皆庶几其无过忒也。”朱熹指出:“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常行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至也。”这种不偏不倚,强调的是既不太过,又无不及,不要片面,不要偏激,不要太趋向和执著于某一端。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在解释《易经》时说:“事物若要臻于完善,若要保住完善状态,它的运行就必须在恰当的地位,恰当的限度,恰当的时间。《易》的卦辞、爻辞,把这种恰当叫做‘正’、‘中’。”这种被冯友兰叫做“正”、“中”的“恰当”,如果通俗地来理解,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正好”。战国时期楚国著名才子、辞赋家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中曾经描写过东家美女:“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宋玉“赋”中的这位绝色佳人,迷人之处就在于她的身材与容颜“恰到好处”,体现的就是一种“正好”。
无限风光在涯巅,前挪一寸是深渊。真理向前一步,就是谬误。《孙子兵法》贯彻和体现了“中正”、“正好”的理念,在军事思想、战争学说中具体而生动地诠释了“中者,天下之正道”,“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中”的内涵。
(一)把握“好”的尺度,谨防优长变劣点。《孙子兵法》重视将帅品德修养,《计篇》提出“智、信、仁、勇、严”的五条标准;《地形篇》提出“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的明确要求。同时,《九变篇》又提出戒“五危”之说,认为:“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从修“五德”到戒“五危”,孙武给人们传递了一个怎样的信息呢?那就是做事情不能过分“求好”,过了就会成为“癖”,甚至会走向事物的反面。在孙武看来,奋勇杀敌是必要的,但要反对孤注一掷的匹夫之勇;保存自己是没错的,但要反对那种偏重保存实力、保护自己的消极怠战行为;战场上义愤填膺、同仇敌忾是对的,但要防止情绪失控、落敌圈套;保持廉洁的美名无可厚非,但要防止为名分所累、被敌人所用;爱民是应该的,但不能一味“爱民”影响整体和大局,而使国家和人民遭受更大的损失。
(二)把握“高”的尺度,谨防消化不良症。食量适中,营养够用,裨益健康;胃口过大,就会消化不良,损害身体。同理,战争中在作战目标的确立上,如果胃口过大,也会出现消化不良的问题。抗美援朝战争中,特别是在战争初期进展比较顺利的情况下,志愿军部队出现了盲目乐观的情绪,严重低估了美军的战斗力,作战目标往往定得过高,以致该攻下的阵地攻不下,让本该可以围歼的敌人溜之大吉,造成了不该有的重大损失。后来,志愿军吸取教训,缩小胃口,适度确定歼敌目标,比如有的用一个军打敌一个营,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孙子兵法》主张在作战目标的确立上,要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反对贪大冒进。《谋攻篇》强调:“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老子曾经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又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军争篇》主张“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讲得虽然有些绝对,但也体现了适度、留有余地的目标追求,是一种作战目标、作战追求上的“知足”,也就是“知度”不“过度”。
(三)把握“得”的尺度,谨防一味盲目“趋利”。利害常相依,得失常相随。凡事有利就有害,有得就有失,趋利就意味着容害,而且往往是求利越大,随害也越大。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在利与害的相权中找到一个平衡点,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以谋利的“正好”实现获利的最大。就像足球比赛,加强场上的进攻,势必要弱化场上的防守;反过来说,进攻往往又是最好的防守,防守往往也是最好的进攻(防守反击)。因此,至于投入多大的攻击力量,投入多大的防守力量,需要根据球队的实力和对手的情况,具体而灵活地部署与调整,而这里的核心与关键就在于保持攻守的平衡。这就要看主帅的场上指挥调度水平与队员的领悟应变能力。《孙子兵法》主张“趋利”与“避害”两相虑、一体权,在“趋”与“避”的平衡中求“中正”,反对不计其害一味求利、不计成本盲目逐利。《军争篇》指出:“故军争为利,军争为危。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为此,《九地篇》强调:“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
二、中和之美
由和两极而得中,我们称之为中和之美。《礼·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这里,中和是一种儒家哲学。《荀子·王制》曰:“公平者职之衡也,中和者听之绳也。”杨倞注:“中和谓宽猛得中也。”在这里,中和是一种方法论。《孙子兵法》的中和之美,主要体现在战略层面。在战略博弈方式、战略对决形态上,中和之策表现为三个层次,也就是《谋攻篇》讲到的“伐谋”、“伐交”、“伐兵”。
第一层次,“伐谋”。就是通过强有力的战略威慑,挫败敌方的战略意图,让其主动放弃战略诉求,取消作战行动企图与计划,被迫服从我方的战略意志、满足我方的战略诉求。《虚实篇》曰:“敌虽众,可使无斗。”1948年10月,我解放军攻克东北重镇锦州后,国民党营垒人心动荡,军心涣散。蒋介石急于挽救连连受挫的被动局面,想出了一个毒计,准备偷袭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企图摧毁共产党的最高统帅机关。为此,蒋介石还亲自飞到北平督战。当时西柏坡只留有一个警卫连的兵力。石家庄虽已解放,但无部队驻守,实际是一座空城。敌人兵力已集结保定,而保定距石家庄也不过150公里,10万机械化装备的蒋军如果突进石家庄,西柏坡就危在旦夕了。面对十万火急的情势,毛泽东从容地拿起笔,于10月15日、26日、30日亲自撰写了3篇新华社电稿:《蒋傅匪军妄图突击石家庄,我军严阵以待,决予歼敌》、《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匪军进扰》、《评蒋军傅匪军梦想偷袭石家庄》在全国播发。毛泽东一方面发表3篇电讯迷惑敌人,一方面急调主力部队救险。蒋介石听到电台播发的消息后大吃一惊:自己的如意算盘竟被毛泽东轻易看穿,再偷袭已失去了意义。正犹豫间,迅速赶回的我先头部队已与敌接上了火。国民党损失官兵3700余人,汽车90余辆,还有一大批作战物资被我军缴获。得到情报,再思量新华社的3篇电讯,“剿总”司令傅作义也怕凶多吉少,只好急急忙忙撤军。偷袭计划就这样流产了。蒋介石还很庆幸地惊呼:差点又上了毛泽东“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当!
第二层次,“伐交”。一方面,就是通过外交手段,破坏敌方的联盟,让敌对国失去挑战我方的实力与资本。另一方面,就是通过外交上的运筹博弈、讨价还价,实现利益交换、双方共赢,消除敌意、和平共处,甚至变敌为友、为我所用。《九地篇》曰:“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战国后期,六国都面临着被强秦吞并的危险,本应同舟共济、联合抗秦,但有些国家并没有看到这一点,仍在相互争斗和残杀,而这正是秦国所期望和追求的。纵横家苏秦敏锐地看清了秦国的野心及六国面临的灭顶之灾,并勇敢地担当起合纵六国的重任。然而,秦国早就看破了这一点,充分利用六国各打各的“小算盘”的弱点,有针对性地实施连横之策,六国“合纵”联盟不长时间即被瓦解,秦国便轻轻松松地实施了各个击破的战略,一举创建了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封建帝国。
第三层次,有分寸、有限度的“伐兵”。《九地篇》强调:“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像解放战争时期的攻打天津之战,战役的最高企图不是夺取天津城,而是为了尽快实现北平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还有上面举例讲到的毛泽东以“伐交”为主要手段,破解石家庄之险的诸多措施,也包括坚决有效的“伐兵”行动。
三、中心、中枢之美
中心、中枢是“中”的当然义项。指挥中心、中枢,是现代战争的产物,是因应战争规模的日益扩大、组织指挥的日趋复杂而构设的决策指挥机构。然而,在2500多年前孙武就着眼于战争的发展趋势,以及对决策指挥提出的崭新要求,在作战指挥上勾画了现代作战指挥中枢的雏形,构成了战争指挥的核心。
《孙子兵法》倡导的中心、中枢,就是国君,就是这个国家利益的代表者。一方面,“将受命于君”,将要“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要为“国之辅”,要“辅周”而使“国强”,要一切为了“安国全军”;另一方面,要给将帅以临阵的临机处置权,要“将能而君不御”,不能“患于军”,要允许“君命有所不受”;主将要善于“择人而任势”,实行君王领导(授权)下的将帅负责制。孙武眼中的这种指挥中枢,分工明确、责任明确、关系明确,流程简捷、运转顺畅,有利于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有益于决策指挥水平与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愿望与要求的实现。这种指挥中枢,极具前瞻性地揭示并顺应了作战指挥发展的规律,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既彰显了孙武的远见与智慧,又彰显了“中”的军事功能与美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