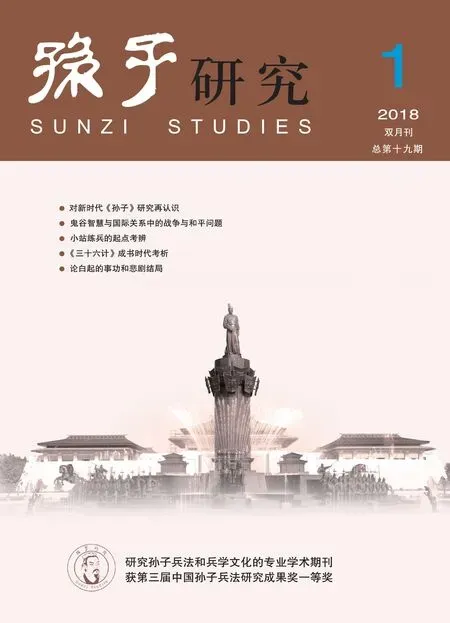小站练兵的起点考辨
小站练兵是我国近代军事史上极为重要、影响巨大的历史事件,也是天津地方史研究中的“制高点”之一,它在各个方面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都相当深远。小站练兵的发生地——小站镇,坐落在天津市东南陲(今津南区),面积仅有六十余平方公里,但其在历史上的名气可不“小”。天津小站曾是近代中国最主要的军事基地,从那里走出了北洋政府的四位总统: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曹锟,一位临时执政者段祺瑞,以及九位总理和三十多位督军。正是由于小站练兵历史地位的重要性,从专家学者到民间人士,关注这个历史事件的人很多,学术界对小站练兵的研讨也成果颇多,有关论著从许多方面对其进行了研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小站练兵”这四个字已经成为天津历史文化中的一张底蕴丰厚的名片。但是,关于小站练兵的起点究竟是哪一年,学术界却始终存在着几种截然不同的看法,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为了维护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我们认为,对小站练兵的各种观点以及所依据的历史资料重新进行梳理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本文拟从几个方面对此问题进行考辨。
一、学术界对小站练兵起点问题的四种主要观点
归纳起来,目前学术界对小站练兵起点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四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以袁世凯1895年编练新军为起点。相当一部分学者的作品持此看法,其中尤以专门关注北洋历史及人物的论著和文章居多。譬如,李宗一在《袁世凯传》中,将小站练兵作为一个专门章节,并将时间明确标注为1895年起①李宗一:《袁世凯传》,第43页,中华书局,1980年。;马平安也提出:“1895年,练兵的基地又从马厂转移到小站,开始了所谓的‘小站练兵’。”②马平安:《袁世凯的正面与侧面》,第20页,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此外,也有部分通史、专题史著作采用了这种说法,南京大学版《中华民国专题史》中称:“1895年,朝廷正式敕派袁世凯就任练兵大臣……该军从定武军的营址马厂迁到了天津小站,并正式更名为‘新建陆军’,也称‘北洋新军’。是为‘小站练兵’之开始。”①马振犊、唐启华、蒋耘:《中华民国专题史·第三卷·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与外交》,第3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另外据报道,“2015年12月16日,由津南区小站镇政府、津南区旅游局主办,天津市小站练兵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北京出版集团协办的‘纪念小站练兵12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徐世昌日记》首发仪式’在津南区小站练兵园举行。市区政协文史委、市社联、天津社科院、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及国内史学界知名学者莅临小站练兵园进行学术研讨。”②据《天津日报》2015年12月17日第8版载。2016年底,“津南区小站镇练兵园与文体站举办了小站练兵121年、彰德秋操110年学术研讨会”③据北方网2016年12月28日讯。。此前的2014年,某房地产公司也在小站办过一次会议。这其中的学术会议,有不少业内人士与会,有关发言围绕袁世凯小站编练新军及北洋历史文化,大都集中提及“小站练兵120年”“小站练兵121年”云云。笔者所在的天津兵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的学者均未受邀参加上述三次会议,有关资料未能取得,有些情况不得而知。但笔者认为,经过认真讨论后,如果某位学者甚或是某些学者均持此观点,都是应当得到理解和尊重的。但是,在会议开始之前,尚未进行深入研究时,就把“纪念小站练兵120周年”作为预设的结论,则似乎不够严谨和慎重。会后,笔者就此问题曾与友人、也是后两次会议的主要承办者之一周醉天先生进行过交流。据他告知,这两次会议采取1895年这种说法是因为该结论已“约定俗成”,而且袁世凯的练兵在民间“老幼皆知”,影响巨大。他说的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是即便如此,经过反复思考之后,笔者仍不能同意小站练兵的起点为1895年这一说法。
第二种观点是以胡燏棻等于1894年开始编练新军、1895年移驻小站为起点,这种看法以张博等学者的文章为代表,周醉天开始也持此说。张博在文中称胡燏棻为“被淡忘的小站练兵第一人”,④张博:《被淡忘的小站练兵第一人》,载《天津日报》2011年4月18日。而周醉天《小站练兵史话》一书中“第五讲”的题目就叫“小站练兵始于胡燏棻”,他提出“1895年,由于马厂兵营不够用,胡燏棻率定武军移驻津南小站,所以说小站练兵始于胡燏棻”。⑤周醉天:《小站练兵始于胡燏棻》,载《今晚报》2015年12月7日副刊版。事实上,袁世凯来小站负责编练新军,也正是接替胡燏棻的工作,但由于胡燏棻在小站练兵持续时间较短(仅一年左右的时间),因此过去多不为学术界所重视。这种观点的意义在于,正确地指出了在袁世凯小站练兵之前,已有人先期在此练兵。但是其不足之处则是,所论胡燏棻为“小站练兵第一人”之说不够精确。
第三种观点是从第二种观点延伸而来的。近来,有人将汉纳根的建议、策划与胡燏棻练兵共同作为小站练兵的起点。如周醉天认为“小站练兵的源头是清末编练新军,而这个建议是汉纳根最先提出的,最先负责这项工作的是胡燏棻。”⑥周醉天:《练兵策划人是汉纳根》,载《今晚报》2015年12月2日副刊版。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虽然在细节上与第二种观点有一些异同,但其优长之处和存在的问题是一样的。
第四种观点是以周盛传1875年率盛军赴小站地区驻屯为起点,这种看法以来新夏、谭汝为等先生的文章为主要代表。来新夏的文章中说:“一般认为小站练兵是袁世凯独有的业绩,实际上,上起同光之际淮军将领周盛传的盛字营就在此屯田练兵,下至民国九年(1920年)段祺瑞在小站编练的振武军被遣散,前后近半个世纪,小站一直是练兵之地。其间甲午战后袁世凯的编练‘新建陆军’,名声显著,成效最大,影响极巨,对此后30余年中国政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人们常把‘小站练兵’与袁世凯联系在一起。”①来新夏:《名镇小站》,见《不辍集》,第371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谭汝为也将小站练兵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即:“1875年,淮军将领周盛传率盛字军在小站练兵拉开序幕;1895年,袁世凯在小站操练新建陆军;1920年,段祺瑞在小站训练的振武军被遣散。历时近半个世纪。”②谭汝为、刘利祥:《小站练兵旧遗址 营盘地名今扎堆》,见《天津地名故事》,第26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此外,天津市津南区政协编辑出版的文史资料《清末天津小站练兵》一书认为:“清末天津小站练兵……是以公元1875年(光绪元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调遣淮军著名将领周盛传率领所部从河北青县马厂移屯今小站北侧的潦水套,设‘亲军营’开始小站练兵,又经胡燏棻练兵、袁世凯练兵、张之洞练兵、段祺瑞练兵,时至1920年为止,历经近半个世纪的一段史实。”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津南区委员会:津南区文史资料总第十一辑《清末天津小站练兵》(上),序言部分,2005年。由津南区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津南区志》中则记述为:“小站练兵……是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委派袁世凯接替胡燏棻在小站建立操练新建陆军——北洋军阀胚胎时期为中心,上自光绪元年(1875年),淮军将领周盛传率盛字军在小站练兵,下至1920年,段祺瑞在小站训练的振武军被遣散,历时近半个世纪的一段史实。”④津南区地方志编修委员会:《津南区志》,第797页,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对于上述关于小站练兵起点的四种说法,笔者均不能赞同,试考辨如下:第一种观点相对影响较大,漏洞却最明显。事实上,在参加“小站练兵12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学者中,有不少人在另外的场合表达了不同看法。张诚认为,“小站练兵分为四个时期,一是甲午战争之前盛军,一是甲午战争至庚子期间的练军和定武军,一是庚子之后的新军。”⑤张诚:《关于小站练兵》,《小站练兵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孙树芳在文中提及,“小站当初是由一个军事据点发展而来的,由盛军屯田始。”⑥孙树芳:《军旅文化与小站人风格的形成》,《小站练兵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罗澍伟先生也指出:“清王朝为什么选择天津小站训练现代军队?……因为小站是中国人最早感知西方军事文化的训练基地”,而这个“最早”,则是“天津教案爆发后,李鸿章率淮军来到天津……淮军是中国最早采用现代装备、最早参照德国营制的军队,率先建立了克虏伯炮队,一般士兵也改用洋枪,并聘用西方军官进行操练”。⑦罗澍伟:《从小站练兵说近代天津的历史地位》,《小站练兵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等。而第二、第三种观点之不能成立已见前述。其实就前三种观点而言,它们均存在着对史料挖掘不够深入的缺陷,因为无论是小站镇的建立时间还是周盛传在小站地区的练兵时间,都要远早于汉纳根、胡燏棻、袁世凯的编练新军。就小站地区而言,汉纳根、胡燏棻、袁世凯的练兵实践,均不具有开创性。相反地,他们都继承了周盛传之前在小站练兵宝贵的物质基础、部队基础和精神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对天津小站练兵起点问题进行研究时,以上三种观点可以先期被排除掉。
而第四种观点貌似最接近真相,其实却并非如此。首先,一部分持此说法的论著或文章只提观点,但并没有举出足够有力的根据,所论亦难以服人。其次,周盛传所部在小站地区的活动达七八年之久,只笼统而简单地说小站练兵始于周盛传,而不明确指出始于哪一年,这显然是不可取的。再次,有些论者将小站开始建镇的时间与小站练兵的起点混为一谈,殊为不妥。
由于小站是大批北洋军政人物的成名之地,备受关注;加之后来的袁世凯等人编练新军在规模上远远超出之前周盛传在小站操练盛军。人们往往更倾向于将历史事件的兴盛阶段作为历史事件的对应点或起点,但实际上这种做法是不合理的。
二、周盛传在天津小站练兵的实践考述
因周盛传的有关活动已见诸不少作品,故本文仅简要介绍之。
周盛传(1833-1885年),字薪如,安徽合肥人。在乡时,周盛传及其诸兄周盛波等共同办团练对抗太平军,历任把总、千总。清同治元年,周盛传随周盛波加入淮军,担任亲兵营哨官,在江浙地区战功卓著。同治三年,加提督衔。后战于河南、山东、皖北等地。同治六年,授广西右江镇总兵,击败东捻军。同治七年,参与在直隶、山东等地击败西捻军的军事行动。后驻湖北。同治九年,随李鸿章赴陕西镇压回民军。是年秋,李鸿章移督直隶,疏调周盛传率所部屯卫畿辅。同治十年,移屯青县马厂。光绪二年,正式调任天津镇总兵,在津南小站地区移屯兴工,操练盛军。光绪八年,擢升湖南提督,仍留镇训练士卒。光绪十年,丁母忧,回籍病死。其谥武壮,建专祠。著有《操枪章程》十二篇。①详见《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后人整理有《周武壮公遗书》。周盛传多年征战南北,戎马倥偬,而其在天津小站的时期,则是他一生中唯一能够较为安定地守卫一方、实践其练兵理想的时光。
(一)小站练兵的物质基础来源于周盛传的练兵实践
小站地区原是一片斥卤之地,积潦纵横,盐碱低洼,芦苇丛生,土旷民稀,在周盛传率部来到这里之前,它被称作“南大洼”、“潘家坟”、“潦水套”。面对着这样一方条件欠佳的土地,在此实行屯垦是需要相当大的决心的,它之所以能成为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与周盛传及其所属部队的努力是绝对分不开的。小站“南扼祁口,东控大沽,声气相接,以张远势”②周家驹编:《周武壮公遗书》,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九辑》,(台湾)文海出版社,第87页。,是马厂—小站—新城—大沽这一海防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在小站军屯练兵,也是周盛传海防思想的重要实践体现。倘若没有周盛传兴修马新大道(马厂到新城),“四十里设一大站,十里设一小站”,随后修筑“新农镇”(即小站镇),就根本不会产生“小站”这个地名并广为流传;倘若没有周盛传率领盛军挖通经过小站地区的马厂减河,用“石水斗泥”的南运河水,引淡涤碱,使滨海数百里斥卤尽成膏腴,小站地区也难以生产足够的水稻来供养后来的驻防大军。当年清政府为表彰周盛传开发小站的功绩而建立的周公祠,历经百年沧桑,虽已毁坏残破,但经天津市津南区文广局委托热爱兵学文化的企业家门前刚先生在原址重建,至今依然矗立在小站镇会馆村,成为了这段历史的重要实物见证。另外,后人可利用的还不仅仅是盛军将滨海弃壤改造成“小江南”的这一大环境,资料显示,胡燏棻、袁世凯在小站地区编练新军时,仍沿用了老盛军的营盘。①关捷等:《中日甲午战争全史 第6卷:人物篇》,第184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周盛传及其所率盛军在小站及其周边的多年经营,则无后人在小站大规模练兵之根基。
(二)盛军并未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部分军队为北洋军所继承
周盛传的盛军在小站开始的练兵举措之所以被某些学者所忽视,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认为盛军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盛军的历史到此中断,与后来的北洋军没有传承关系。②详见郭鸿林:《清代小站屯垦述略》,《古今农业》1991年第3期,第35-41页。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并不正确,经对有关史料详加考证后,笔者发现盛军实际上并未消亡,而其部队最终为北洋军所继承。甲午战争期间,卫汝贵率盛军与马玉昆所部毅军共同肩负朝鲜大同江沿岸布防,曾一度取得“船桥里之战”等战斗的胜利。但平壤溃败后,卫汝贵随叶志超弃城逃走,他的不堪行为,相当程度上降低了人们对盛军的整体评价和关注。此后,盛军残部陆续撤回国内,这时尚存相当于原有人数约八成的兵力,后改由聂士成接统。
日军进入奉天后,聂士成所部盛军陆续参加了摩天岭、连山关等战役,颇有斩获。1895年,聂士成调防京畿,将盛军余部统带入关,后与其所统辖的武毅军等同编入武卫前军,盛军编制从此被取消了。1900年庚子之乱后,武卫前军余部被改编入直隶淮军,归袁世凯统率。③详见徐平:《甲午战争·中日军队通览 1894-1895》,第57页,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当年盛军的残余血脉,随之化入了北洋军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一脉相承的。
(三)周盛传小站练兵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并被后来编练新军者所继承
周盛传在练军的过程中,特别推崇德式装备和德式操法。他强调现代武器的重要性,而且对当时各种先进的新式武器装备都相当通晓,曾一再向李鸿章推荐和要求购买德国克虏伯大炮及林明敦式、斯奈德式等新式来复枪。他所著《操枪章程》十二篇,对武器的构造、保养和使用分析细致入微,并将其用于各部队的训练。1870-1871年普法战争之后,德国陆军名扬天下,这对周盛传的触动也很大,他于1879年以从德国留学归来的查连标教习德国操法。至1884年李鸿章聘了一批德国军官来华充当教习,德员李宝等检阅盛军“炮队三营步伐止齐,似尚许可”,“至所演洋枪(队),经该员阅视,据称现在德新式微有不同……似大同小异,俟德弁到后稍事变通无不合度”。不久,德员康嚆克等到营,每营拨弁勇十二名,交该洋员教习,“伊等教操不过七、八日即可成熟”。“操规无须更改”,“窥该洋弁之意,亦知卑军习操已非一朝,不过量为指授,以完教习之责”。可见盛军操法照德国陆军操法相去不远。④陆方、李之渤:《晚清淮系集团研究——淮军、淮将和李鸿章》, 第157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周盛传及其胞兄周盛波还提倡新式军事教育。在中法战争期间,他们建议李鸿章仿照西国武备书院之制,设立学堂,遴派德弁充当教师,挑选营中剽健又粗通文义之弁目到堂肄业,学业西方军事技术,以期造就将才,“为异日自强之本”。天津武备学堂就是李鸿章采纳他们的建议成立的。天津武备学堂为清末编练新式陆军提供了大批军事人才。⑤陆方、李之渤:《晚清淮系集团研究——淮军、淮将和李鸿章》, 第157-158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周盛传等率先使用德式装备和德式操法的做法,无疑是具有开拓性的练兵举措,这也被后来的北洋新军将领所接纳。从之后胡燏棻、袁世凯等人练兵时聘请德国教官汉纳根等,又用德国陆军操典、德国营制乃至德式军歌等元素训练新军的史实来看,当年周盛传崇尚德军训练方法的思想和实践对他们也是有着深远影响的。
三、“小站练兵”的起点究竟在哪一年
通过上述考辨,笔者对目前“小站练兵”的研究情况有了大致了解。“小站练兵”的肇始者,并不是袁世凯、胡燏棻、汉纳根等人,而应是为后来者奠定物质基础、部队基础并留下宝贵精神财富的周盛传。那么,这场享誉中外的“小站练兵”,起点究竟在哪一年呢?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应当从“小站”、“练兵”两词入手进行分析。
许多史料中均提到,1875年周盛传率盛字军由马厂移驻天津小站。《周武壮公遗书》中所收录的《磨盾纪实》(即《周盛传年谱》)提及:“光绪元年……二月,留马队驻马厂,余拔队移屯天津之南洼,地名潦水套,即今新农镇也。”①周家驹编:《周武壮公遗书》,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九辑》,(台湾)文海出版社,第87页。(仅有少数资料显示移屯时间为1876年②“于1876年3月除马队留驻马厂外,各营移屯小站,分别筑墙垒营房,另开引河引甜水绕于旁。”见王景云:《周盛传与周公祠》,载《津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第35页;“1876年(光绪二年),调盛军于天津镇,移屯兴工”,见《肥西县志》,645页,黄山书社,1994年。,可能是将周盛传正式调任天津镇总兵的时间误作移屯时间。③“1876年,周盛传调任天津镇总兵”,见《安徽近现代史辞典》,第39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另,李鸿章于光绪二年(1876年)正月二十六日的奏折中,仍称周盛传为“遇缺简放提督直隶天津镇总兵”(见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7·奏议七》,第16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即此时仍为候补。可见周盛传正式调任该职时间应晚于1876年正月。)那么,周盛传及盛军究竟是何时正式开始在小站地区“练兵”的呢?
通过阅读有关史料并进行分析后,笔者觉得将“小站练兵”的起点定为光绪三年(1877年)较为符合历史事实。现列出其理由如下,以供学术界讨论。
(一)据《盛字全军屯田图》反映,小站镇及其周边土地收购工作直至1876年才基本完成,次年方有条件开始系统的“练兵”
据考证,“小站建镇之初,镇街实际是为军人们提供生活资料的集市。初建的一条东西街,叫‘行营买卖街’,两端各有城楼一座,称为东门和西门。城门洞上有横额刻碑,刻有新魏书‘新农镇’三字。其形制和北京的城门差不多,当然没有那么高大。然则一般民房也只够到它的半腰。这东西两座城楼已于1956年拆除。”④刘景周:《沽帆远影》,第41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14年。小站镇中必要的设施和民众的聚居,为小站练兵提供了有力的后勤支撑。小站镇的建成,反映了周盛传在小站地区购买、开垦土地、扎营等工作的基本完成,以满足“近万人日需两万斤粮”。⑤刘景周:《近代史上的小站》,天津社科院出版社,2008年。而只有当所有这些工作都完成后,盛字军才有在此开始练兵的可能。
另外,练兵活动还需要教官、武器、装备等一一到位,特别是必须有足够的军粮供给,那一定规模的屯田就是必然的配套之举。即便在1876年内基本完成了土地收购并进行了全面的平整、开垦,最快也要到来年才能收获种植的“小站稻”。
据《周武壮公遗书》记载:“光绪元年……先是营地本海滨沮洳之地,居人寥寥,负贩绝迹,勇夫购物于数十里外,道途仆仆,稽察难周,爰就营前隙地,购材筑屋,以止商旅。既成,命之曰新农镇。”史料中仅提到光绪元年开始建设新农镇(小站镇),但是并没有其建成的准确时间。笔者认为,尽管盛字军在1875年已开始移驻小站地区并陆续进行相关营房修建、屯田、新农镇(小站镇)建设的准备工作,但实际上,新农镇(小站镇)的建成肯定不会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相当一段时间,因此其实际建成的时间肯定要稍晚于1875年。
天津博物馆现藏有《盛字全军屯田图》,这是一幅绘制小站开垦的原始图。它是周盛传当年统一改造津南土地时,从地户手中收购土地绘图契约总录,其可靠性和史料价值不言而喻。此图由八轴六尺的条幅组成,图上标明小站垦区和新城垦区收购的每块屯地,方法是在图上标明地块四至、地名、亩数、价格、业主姓名、居住地及购置手续完成时间。图中没有注明成图时间,但图中近百笔收买荒地的年份,只有一笔是光绪五年(1879),其余大多在光绪二年(1876)及其以前。①况清楷:《珍贵的〈盛军屯田图〉》,《今晚报》,2010年10月27日。从这个情况看来,小站镇及其周边土地的收购工作应该基本上完成于1876年,在此之前想要大规模地、系统地进行练兵是不具备空间条件的。至少在1876年以后,小站才有了开始练兵的可能性,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标志性年代。
(二)1877年哥老会成员哗变之后,盛军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裁军,并发布了整军指令,是为周盛传小站整军、练兵的举措之始
在当年盛军兵士传唱的《盛军勇歌》中,描述了所谓“当勇十妙诀”,其第一项就是“莫结哥老会”。由是可见,哥老会成员掺杂入营,借机煽动闹事是当时盛军面临的最大危险。哥老会是当时的民间秘密结社,以反满倾向著称,清政府视之为“会匪”,在江南、西北等地声势很大。光绪三年(1877)正月初一,盛军逮捕了哥老会成员何松桂,混入盛军中的其他哥老会成员不甘坐以待毙,于大年初三凌晨,结伙沿北潮河大埝道自北而南,焚烧了仁军营、盛军左军右营、中军前营、前军右营营房外的柴火垛,焚掠了小站的行营买卖街,然后向南逃遁。周盛传对此采取了果断的应对措施,他命令留驻马厂地区的马队实行包围攻击,同时亲率军士百数十人,由甜水井、大苏庄,渡娘娘河,沿途追击,并于次日下午追到小韩村,全歼逃犯。②周家驹编:《周武壮公遗书》,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九辑》,(台湾)文海出版社,第92-93页。此次军队哗变发生在距离京城不远的天津,且是淮军的精锐部队盛军,李鸿章不得不亲自上书解释情况,“近年淮军各营饷源枯竭,每岁仅能发饷九关,弁勇苦累实甚。盛军驻防津沽附近地面,操练既勤,又累岁修筑新城炮台各巨工,继以开河屯田,终年不少休息,筋力过劳,口粮又少,故会匪易于煽惑”,并为周盛传开脱。光绪帝高度重视此事,将涉及哗变两营之营官二人革职,对周盛传表示“姑念追剿尚为迅速,著从宽免其置议”,但“仍责令该总兵整饬营规,严加钤束,倘再有溃散情事,立即从严参办”,且认为随哥老会散去之兵勇不止所报“百余名”之数,要求进一步查明下落。③李鸿章:《剿平煽勇滋事之会匪折》(附 光绪三年正月十八日寄谕),见《李鸿章全集 奏议 第7册》,第298-300页。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周盛传于光绪三年正月初十日、十六日陆续发布《严整营规谕》《再整营规谕》,规定“出入稽查务须认真严密,不准借故到咸水沽、葛沽一带行走。如有赎当,可派差弁持票代赎,勿许再当。各站盘查,必有公事,持营官护照始准放行”,“即有公干必须遣弁赴本总统处挂号知会卡巡以备查考,每次关饷务须点名,戥足匀包亲自发给,米粮勤加检秤,每发必督各哨算清,勿任侵减粮饷”。①周家驹编:《周武壮公遗书》,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九辑》,(台湾)文海出版社,第950-952页。依靠严格规定出入制度和粮饷分配并不能完全保障部队的正常发展。当时盛军已和刘铭传所部铭军并列成为淮军前两名的大枝营头、主力部队,而盛军所驻扎之地的富庶、丰腴程度,远不如铭军。事实上,盛军面临的最大威胁并是不来自于哥老会成员的蛊惑,而是由于部队过于庞大,导致“饷源不济”,供给严重不足,军心难免离散。
为了破解这一难题,从光绪三年(1877)开始,盛军实施裁军精简工作,所有部队根据去弱留强的原则,“集阅诸勇,惟汰老弱”,然后重新整编,先是各军统一减员二成。后又遣散仁军一个营,裁汰前军正、左、右三营,左军、右军皆裁掉其左营,周盛传所部盛军、仁军共计裁撤了六个营。②周家驹编:《周武壮公遗书》,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九辑》,(台湾)文海出版社,第98-99页。原先合计十五营的盛军、仁军,至此已裁去其三分之一强。据有关资料统计证明,自1877年开始的这次裁撤,是盛军发展历史上的第一次裁军,也是同时期淮军各大枝营头最大的一次裁军。③详见《淮军勇营数及大枝营头变迁表 下》,樊百川:《淮军史》,第435-43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经过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裁军精简,盛军甩掉了老弱病残的包袱,去除了哥老会余党的威胁,摆脱了供给不足的负累,真正成为了一支精锐之师。笔者认为,这次裁军与盛军正式开始“练兵”,是有密切关联的标志性重要事件。而在1875至1877年之间,盛军并没有任何相关军事方面的大动作,多是在购买土地、开垦田野、开挖疏浚水道、修建城镇,这些只是练兵的准备和基础性工作。对于周盛传在小站地区的军事实践来说,裁军整军才是与“练兵”因果相关的主要内容。因此,将1877年作为小站练兵之始,笔者认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正确表述。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如果没有小站镇(新农镇)的完整建立并正常运转,就不具备练兵的基本条件——根据地,甚至没有这个地名;但仅仅有了小站之名是不够的,必须有军队在此正式进行具有相当规模的军事训练活动,才称得上是名副其实“小站练兵”的开始。
说得更具体一点,构成“小站练兵”的两个要素缺一不可。1875年,周盛传率盛字军移屯于此,在一个小站的基础上开始建镇,收购土地,招民领种,修路架桥;1876年,完成了大部分土地收购,挖河引水,去碱种稻,同时制定章程,解决人员、经费、装备等,为进行一定规模的练兵提供了可能;1877年,由于发生了哥老会哗变,盛军开始了大规模的裁军整军活动,逐渐形成一支精锐之师。在清光绪三年(1877)之前,“小站练兵”要件不完整,条件不具备。1877年,基本条件具备,稻粮开始收获,一切准备就绪,既有了“小站”之名,又有了“练兵”之举,两个要素的齐备使“小站练兵”有了可能性。如此说来,将1877年定为“小站练兵”的起点是合理的。
结语
必须承认,周盛传的小站练兵无论在规模上、档次上,都与之后胡燏棻、袁世凯等人的练兵实践有一定差距。但是,面对史实,我们仍应当清楚地看到,至1877年,周盛传在小站地区的军事活动,已经具备了“小站之名”、“练兵之举”的两个关键要素,事实上构成了“小站练兵”的起点。
把1877年作为小站练兵的起点,这种观点之所以此前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未能获得学术界一致认同,是因为对相关史料缺少全面而深入的分析。如果此说能够成立,将给“小站练兵”这一历史概念构建出更为准确的定义,对于推进相关历史研究是大有裨益的。进一步说,如果此说法能够成立,则2017年是小站练兵开始的整整140周年。从兵学文化研究的角度、从弘扬地方历史文化的角度而言,笔者认为,这个时间段恰恰有必要开展隆重的纪念活动,更好地探讨、研究小站练兵的历史,对相关概念进行厘清和健全,为小站练兵的历史文化根基“正本清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