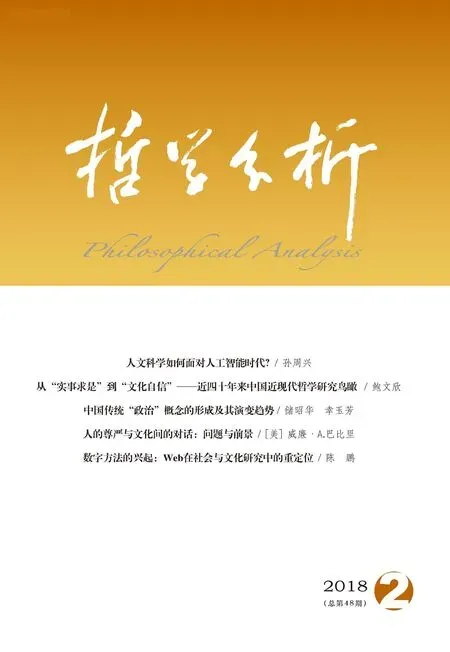“第六届中德科学技术哲学论坛”综述
张 帆
科学哲学自逻辑经验主义奠定以来,就一直跟随着时代的脚步“起承转合”。20世纪70年代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理念一炮打响,给科学哲学的研究增添了历史的维度;20世纪80年代,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以及哈金的《表征与干预》的出版,科学哲学的“理论优位”的理念受到了挑战,自此开始关注经验,并以此为基点重新审视科学与技术的关系……今天,当引力波已经被探测到,当“阿尔法狗”已经连续将李世石和柯洁挑落马下,试问我们该如何理解科学、技术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围绕上述问题,2017年6月11至14日,“第六届中德科学技术哲学论坛”在德国达姆施坦特工业大学哲学系举办。这次论坛的主题是“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艰难整合”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Perspectives on an Uneasy Relationship)。来自德国的汉诺威大学、比勒菲尔德大学、达姆施坦特大学、勃兰登堡大学和来自中国的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大学、中国科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专家学者出席了这届论坛。
论坛的承办者德国达姆施坦特工业大学哲学系主任阿尔弗雷德·诺德曼(Alfred Nordmann)教授在开幕式上指出,科学哲学一直在探索思想与实在之间的关联,而技术在这个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工具”的角色。如何最大限度地消解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界限并找到其共同发展的基点,的确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问题。围绕这种整合之路,与会代表的报告可划分为两大块:一是基于实践传统,围绕技能、自动化认知及其专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二是基于科学技术史,围绕科学、技术与艺术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
一、技能、自动化认知与专家
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成素梅教授报告题目是“‘熟练应对’的哲学意义” (The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of “Skillful Coping”)。她在报告中指出,“熟练应对”概念是德雷福斯推进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现象学进路的一个核心概念,意指当技能学习者从新手提升为专家乃至大师时,所具备的娴熟地应对局势的一种直觉能力。这个概念的提出,不仅升华了海德格尔的哲学主张,提供了对人类智能的一种新的理解,而且引发了学界对相关的哲学基本概念的深入讨论。德雷福斯关于“熟练应对”的观点正是在回应劳斯、塞尔、柯林斯等哲学家和知识社会学家的质疑中进一步发展起来的概念,也是德雷福斯推进现象学进路的一个核心概念。熟练应对的现象学强化了对人类智能的直觉应对能力的思考,为我们重新理解认识论、心灵哲学、行动哲学、社会科学、认知科学以及伦理学中有关人类行动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域和新的概念框架;也为我们重新理解人类智能的本性提供了另一种可选择的理解方式;也有可能为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整合提供一条思路。熟练应对意指应对者能够娴熟流畅地应对局势的一种直觉能力。学习者达到熟练应对的过程是逐渐摒弃慎思行动的过程,是融入世界的过程。熟练应对是由世界或域境本身诱发的。这种诱发不是原因,而是一种挑战。熟练应对者与世界的互动是直觉互动,而不是表征互动。直觉互动本身不是在寻找原因,而是在专注地应对挑战。诱发相当于整个系统产生的一次涨落,这种涨落会导致系统创造出新的形式,形成新的活动焦点。熟练应对活动所蕴含的关于人类活动的哲学假设,建立在主客体融合的基础上,而不是主客体二分的基础上。在熟练应对活动中,应对者对世界的可理解性是实践理解,而不是理论理解;应对行动的意向性是基于身体的意向性,而不是可表征的意向性。
达姆施坦特工业大学的凯瑞斯·冯·伊柯斯蓝德(Cheryce von Xylander)博士的报考主题是有关自动化认知(automated cognition)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的报告风格别具一格——在她的整场报告中,没有出现一个字,完全是通过图片的形式向人们展示了她所要表达的观点: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是不同的。表面上看来,这两种信息处理方式是类似的。然而,前者的劳动关系依赖于自身,后者则取决于自动化。这种区分对于公共领域的规范价值有着深远的影响。现在已经越来越难区分计算机创造的和人所创造的艺术品、翻译,等等。由于工具的拟真设计(skeuomorphism),模拟智能工具使得机器的行动越来越拟人化。那么,我们怎么样去重新认识意识?这个问题敦促哲学家必须站在一个新的舞台上去理解认识,因为自动化时代已经到来。
华东师范大学的王不凡博士的报告是有关“技能型知识” (skillful knowledge)的。他认为,从科学哲学史来看,关于知识形成的哲学探讨出现了两种主流区分:一种是理性主义,一种是社会建构论。关于科学知识表征的探讨,也出现了两种主流区分:一种是明言知识,一种是意会知识。在从知识的生产到知识的内容表现所反映出的二元区分中,二者存在微妙的联系。通过比较“理性—社会”二分与“明言—意会”二分的内涵以及研究进路发现,关于知识的“理性—社会”二分的理解对“明言—意会”分化的理解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然而“明言—意会”的分化面临着概念模糊和关系不清的问题。为避免走向诸如“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等二元对立的极端局面,他的报告提出“技能性知识”这个概念,对知识的明言与意会维度进行了整合。
“专家”之所以成为专家,从认识层面分析,其根源并不在于明言知识而在于“技能”的部分。因此,沿着上述两位学者对于技能话题的分析,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张帆博士分析了当前基于对专家的知识和技能的研究所形成的“专长哲学”(philosophy of expertise)研究的两条进路:首先,她强调社会评价专家的标准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完全相信并遵从专家的意见;“第二次浪潮”揭示了专家意见的非理性机制,同时使人们认识到社会因素是专长拒斥不掉的认识论特征;“第三次浪潮”在技术层面上要求回到对专长本身的讨论上来。其次,她概括了当前对专长哲学研究的两条进路:以德雷福斯为代表的“个体主义”和以柯林斯为代表的“集体主义”进路。二者虽然都抓住了“身体”这条线,开展了“经验研究”,但是德雷福斯研究的是日常经验,而柯林斯研究的是科学经验。这导致二者在看待涉身性和意会知识等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这两种进路分别站在了专长哲学的两极,如何弥合二者的分歧,在介于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找到中间道路,将是专长哲学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
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戴潘博士在其报告中首先介绍了克拉克和查尔默斯提出的功能等同性论证:当我们面对一些任务时,如果世界中的一部分所起的作用和在头脑中所起的作用一样的话,那么我们毫不犹豫地承认,世界的这一部分构成了认知系统的一部分,并构成了认知过程的一部分。接着,他又介绍了保罗·斯马特的“网络延展心灵假说”:大规模的信息网络的技术和信息元素在某些环境下可以构成行动者心灵状态和过程的物理基础的一部分。但是,很多学者对这一点并不持乐观态度。因为,今天的互联网的发展依然非常原始,特别是它的被动性与日常我们和世界交互方式的分离性以及非个人化特征,无法满足克拉克和查尔默斯对延展认知所提出的三条标准。斯马特提出,未来两个主要的技术发展,即数据网络和真实世界网络技术,能够帮助互联网实现延展心灵所需要的标准。
迈克·史托茨(Michael Stöltzner)博士的报告讨论了“其余情况均同”定律(Ceteris Paribus Laws,简称CP定律)。史托茨博士强调,应用科学有一个正常性的前提,所以它需要有CP定律,因为CP定律的意思就是“其余情况均同”。在皮多斯基和雷(Pietroski & Rey)的CP定律中,他们提出了“存在量化”( existential quantification)的理念。史托茨博士认为,这种CP定律的观点对应用科学来说是有诱惑力的,存在量化可以对应于认识论中的信任。因为科学是有社会分工的,我们不必完全知道一个定律背后需要有哪些潜在条件它才能够成立,我只要知道它存在就可以了,至于具体涉及哪些条件,可以让其他领域的人来确定。所以,史托茨博士强调这种“存在量化”的CP理论是有道理的,是可以应用于对应用科学的叙述的。
二、科学、技术与艺术
德国汉诺威大学的霍宁根—徐宁(Paul Hoyningen-Huene)教授的报告对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加以辨析。他说,通常我们都认为技术取决于科学,但事实并非如此,在17世纪以前的西方传统一直是以技术为主导的。直到19世纪之前,技术的发展都是独立于科学的。他特别列举了吉萨金字塔(公元前2570年)、希腊战船(公元前 630年)、雅典卫城(公元前 430年)、水道、嘉德水桥(公元50年)、罗马斗兽场(公元80年)、罗马万神殿(公元120年)、荷兰风车(源自13世纪)、穹顶、机械钟(源自13世纪)、挖掘和造船技术的例子,来说明在17世纪之前技术传统是独立存在的。17世纪之后,科学开始确立,科学中出现了技术的身影,但此时的技术也并不是以一种科学的“附属品”的姿态出现的。之后,他又举了三个科学中的案例对技术如何引导科学的产生加以说明:(1)1816年,在全球范围爆发了所谓的“没有夏天的一年”的大饥荒,此事件促使化学家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从1840年开始对植物生长的条件进行系统的研究。他发现过磷酸钙中的磷溶于水,易于被植物吸收。于是1846年,第一家磷肥公司成立,它极大改善了19世纪后半期直至今天的营养学。(2)1856年3月,18岁的化学家威廉·亨利·珀金(William Henry Perkin)偶然发现了一种有机苯胺染料。1856年8月,他申请了专利,这是染料工业的开始。这项发明使合成染料工业首先在英国发展起来,然后传到了德国(从1863年开始)。1857年,珀金开设了第一家染料工厂。从此,合成染料代替了天然染料。(3)电力产业是在没有任何科学背景的条件下产生出来的。1879年发明家爱迪生首先发明了灯泡。1881年至1882年之间,英国和美国首先在街道上装上了灯。科学(物理)对电力产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上海大学王天恩教授的报告题目是“科学和技术:人与世界相互作用中的模型和因素”。他在报告中用了“树”的模型,通过对由知识到认识再到实践的过程的阐释,强调了科学与技术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首先,他强调说,就像笛卡尔哲学是西方近代哲学的肇始,笛卡尔的知识之树是现代知识论的出发点,但笛卡尔的知识之树把形而上学作为所有知识的基础,不仅导向无限循环,而且始终不可能摆脱怀疑主义。必须由形而上学再进一步,进入作为其基础的思维规定。由于思考必须建立在一些基本的思维规定基础之上,而基本的思维规定总是一些基本假设或逻辑预设,这意味着随着认识的发展,必须更新甚至替换一些基本思维规定,这就有了“反映” (reflection)所意味的轴对称的知识论结构,即围绕对称轴构成的双向循环知识发展结构和机制。其次,他认为,在这个知识论结构中,具体条件范围的扩展意味着认识范围的扩大。认识具体条件范围的扩大,始终是依靠人类建立在层次越来越高的认识基础上的想象,并以作为自己身体器官延长的技术手段与对象世界相互作用得以进行的。如果思想实验代表科学,那么技术就代表行动体(agent)作为人类因素与其他因素进行相互作用,通过这种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效应建立起理论或数学模型。这些模型的价值就在于:它们能在一定条件下得到实践回应。总之,科学理论不是外部世界的镜像写照,而是从形象的几何模型到抽象的数学模型,这些模型的意义不是来自它们对外部世界的真实写照,而是在人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中,通过技术这一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得到某种实践回应。辩护越来越只能被理解为人类通过实验用技术探针向外部世界发问的实践回应。这种回应可能来自不同的世界图景,就像同样的功能可以来自不同的结构。科学和技术的关系就是科学模型通过技术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不断使知识论合理化,这种合理化过程最终通过思维规定的更新实现。由于思维规定与人类学特性密切相关,因而当代知识论的人类学进路顺理成章。
中国科学院的方在庆教授对“技性科学” (Technoscience)的理念进行了阐释,并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给出了一种关于技性科学的中国式解读。方在庆首先解释了“技性科学”一词的起源——该词首先是法国哲学家的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所造,其同胞拉图尔(Bruno Latour)将其引入到科学技术的社会学研究当中。拉图尔在“实验室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技性科学研究揭示了科学家“实际上”是如何展开工作的。他试图把技术的社会建构向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建构扩展。技性科学强调了科学本身的物质性,但并不意味着以技术为中心导向或者技术优先于科学。它是以一种去中心化的视角来看待今天科技的发展。库恩启发我们用历史的、动态的、批判的眼光去看待科学,而技性科学的科学观使得我们能将科学、技术、社会、经济等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用“技性科学”来描述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是非常好的一个手段。但“技性科学”并没有消除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差别。“以任务为驱动”的中国科技政策,恰好混淆了这一点。李约瑟问题和爱因斯坦的回答表明,“技性科学”概念可以更好地说明古代和现代人类的成就,但不能更好地解释变革的根本原因。“技性科学”可以作为一个良好的现象学描述,而不是最好的动力学解释,这要求我们重申基础研究的至关重要性。
德国勃莱登堡工业大学的苏珊娜·阿布珊卡(Suzana Alpsancar)认为,当我们在理性的范式和知识的有效性的范围内来讨论科学实践,就会发现似乎技术与知识无关。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从发现的语境和辩护的语境来看的话,似乎科学与技术的界限是模糊的。因此,她回顾了哈金、莱茵贝格尔和拉图尔在对科学实践的论证中对技术所扮演的角色的解释。阿布珊卡博士认为,尽管哈金和莱茵贝格尔都认为技术是科学实践的必要工具,但拉图尔区分了调解者和中介,它们转化和转译了与物相关却又被转化了的其他东西。在此理论背景下,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技术:仪器和基础设施稳定和再现的过程、能力和知识,以及介质的能量效应。
技术的发展不但与科学相关,而且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技术与艺术之间的界限也在变得越来越模糊。在传统的理解中,技术多被看作改造世界的手段和工具,艺术则被看作对现实世界的再现与表征。来自上海大学的周丽昀教授则强调,数字技术/艺术的发展不但扩展了时空范围,打破了虚拟和真实的界限,还引发了一些新的交互形式,比如人与机器/技术的交互、观众与艺术家的交互、作品与实践的交互、个人与公众的交互等。在现象学的视角下,似乎可以重新理解技术与艺术的界限问题。实际上,不存在客观的、外在的技术与艺术的划界标准,对技术物还是艺术品的判断取决于身体主体与技术物/艺术品之间的关联。这种关联源于不同情境之中的不同主体的知觉与体验。周丽昀教授认为,我们可以从具体的情境出发,去区分技术与艺术。对“界限”的超越,或者通过“界限”进行超验层面的思考,一方面意味着技术与艺术要进行跨界合作,对“界限”的质疑与由此而来的挑战与超越,恰恰是创造力的源泉,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对跨界的程度保持一种反思的态度。艺术需要发挥超验层面的审美追求,审慎地反思技术的统治逻辑,警惕技术的滥用、入侵和过度扩张带来的可能的危险,从而使人达到一种本质的回归。
比勒菲尔德大学的科内利斯·门科(Cornelis Menke)博士的报告是有关“统计测试作为归纳推理和研究技术”的。2015年,“开放科学合作组织” (Open Science Collaboration)公布了一项复制研究结果:在100项刊登在顶级专业刊物的心理学实验中只有少量实验能够被复制。通常,对显著性水平的解释是:在心理学上,把显著性水平定义在5%,它代表在特殊的水平上、纯粹基于偶然获得“统计显著性”的可能性。这是内曼和皮尔森对显著性试验的假设,但是他们并没有说概率一定是5%。这就给我们留下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将5%作为一个标准?最早的显著性假设是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设计的“卡方检验” (Chi-square-test of Goodness-of-Fit)。所谓“卡方检验”是统计样本的实际观测值与理论推断值之间的偏离程度,实际观测值与理论推断值之间的偏离程度决定了卡方值的大小。卡方值越大,越不符合;卡方值越小,偏差越小,越趋于符合。若两个值完全相等,卡方值就为0,表明理论值完全符合。为了解释卡方值,皮尔森设计了一个卡方值,假设偏差完全是由偶然性因素造成的,他把它叫做“p值”——卡方值的特殊值或极值或假设实验结果完全是由偶然性造成的。这样,就需要区分实际的p值和显著性水平。如果试验是可重复的,p值是在实验中获得的(它取决于数据),显著性水平侧重于获得实验结果。以5%作为一个标准的背景来看,如果要达到更高的标准,比如1%就要做更多的统计实验。要完成更多的实验,就会有更大的误差,实验成本也会更高。也就是说,虽然统计的误差小了,但是其他误差会增加。
比勒菲尔德大学的约翰尼斯·伦哈德(Johannes Lenhard)博士的报告是有关20世纪90年代德国工程专业中的数学教育。在报告中,伦哈德博士指出,20世纪80年代,德国的工程师们都反对工程教育和研究的组织方式,即反对现有的实验室设施和数学教育。历史文献反映出这样做的原因是:数学教育与实践需求之间存在差距,它是提高学术和社会声誉之需。伦哈德博士认为这两点理由都是有效的,但未必合理。他强调,把数学作为一种工具在工程师的教育中常常是被忽视的。特别是作为工程师代表以及后来的柏林技术研究院院长的阿洛伊斯·莱德勒(Alois Riedler)认为,数学只是一个工具(辅助科学),而他的反对者、来自哥廷根的数学家菲利克斯·克莱恩(Felix Klein)则申辩说,数学不是一个工具,它为所有科学提供了一种基本的结构。在介绍二人的争论过程时,伦哈德博士特别介绍了卡尔·冯·巴赫(Carl von Bach,1847—1931)这位斯图加特的机械工程教授的工作:他把数学作为平衡各种对立观点的工具(辅助的和等级的),将数学建模融入实验室和实践,对后代的工程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都师范大学的朱慧涓博士认为,针对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的争论,应当在科学史的语境下来理解。以现代宇宙学为例,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有两条促使该学科建立的独立进路。第一条进路与宇宙理论的发展有关,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为这一理论奠定了基础。但在提出广义相对论的过程中,爱因斯坦完全没有考虑过宇宙学的问题。另一条进路与现代天文技术的发展有关,特别是天体物理技术的发展。其中,大型望远镜和相关的观测技术将人类视觉延伸到了太空的深处。正是因为这两条进路的最终汇合,才有了现代宇宙学的建立。
中国科学院的雷煜博士分析了中国宋代工匠地位转化失败的原因。首先,他分析了宋代官营手工业中工匠的组成情况——包括厢兵、战俘与囚犯和被强制雇佣的工匠。其次,他分析了士大夫主张限制工匠与手工业的原因。对此主要有两种解释:其一,宋代时期商品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于是限制奢侈的观念便受到了挑战与打击。一些士大夫在面对这种情况时,认为有必要重新对工匠们制定管理规定。其二,一些士大夫认为,与农业相比,手工业应该居于次要地位,应帮助农业发展。雷煜认为,中国宋代手工业地位的崛起是受到来自农业的影响。
三、结 语
此次会议的主题是“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艰难整合”,这里的“艰难”对应的英文单词是“uneasy”,这用来形容“中德科学技术哲学论坛”也十分贴切。本论坛初建于2011年,在中方主席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素梅研究员和德方主席汉诺威大学的霍宁根—徐宁教授的共同推动下,在国际和国内的影响力逐步扩大,这个过程实属不易。到本次论坛为止,已经分别在德国召开三届,在中国召开三届,下一届将于2018年在北京召开。随着信息技术、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许多相关的哲学问题将既与科学哲学相关,也与技术哲学相关。对这些相关问题的研究将会给未来的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发展带来怎样的变革,也是未来的“中德科学技术哲学论坛”需要进一步思考的一个“不容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