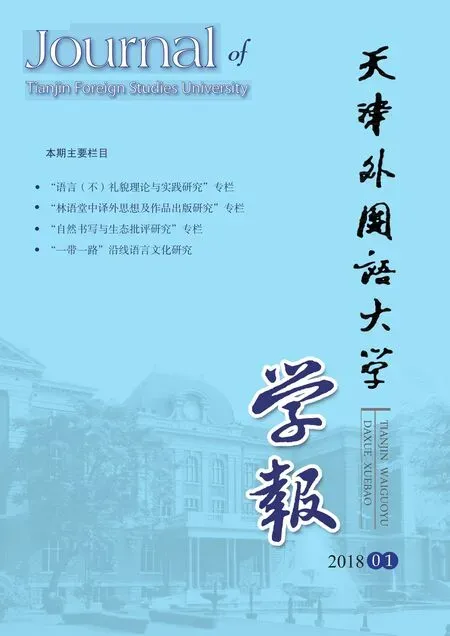民族意识下的不同文化认知及多重阐释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林语堂文本在日本的译介
邢以丹,陈煜斓
(闽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漳州 363000)
一、引言
林语堂的作品首次进入日本是1935年6月,《中国文学月报》第四号登载了他的小品文《笑》。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林语堂文学活动的高峰期,随着佳作不断涌现,国际影响力逐渐加大,日本对他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当时中日两国矛盾日益突出并最终爆发战争,以日本战败收场。在这样敏感的时局下,林语堂文本在日本的译介传播特殊而复杂,有许多值得挖掘的侧面。本文致力于挖掘林氏文本在日传播中所隐藏的操纵者的意识形态要素,给传播的选择性和阐释的引导性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二、逐渐升温的译介盛况和时过境迁后的淡出
最早将林语堂的作品译介到日本的是中国文学研究会。该研究会是 1934年 3月由当时东京帝国大学支那哲学支那文学科的毕业生竹内好、武田泰淳、冈崎俊夫等发起成立的,是当时唯一专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团体(熊文莉,2010)。研究会的骨干们对鲁迅、周作人的评价很高,而对林语堂的介绍力度并不大。冈崎俊夫在《中国文学月报》首刊上发文时提到过林语堂,但他个人不欣赏林氏过于自由的个性,只是介绍他为中国小品文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理念上与鲁迅、胡风等人产生分歧而受到后者的批评。武田泰淳倒是对林语堂的幽默文学大加赞赏,将其比喻为“美式的、开放的新鲜血液”(河村昌子,2007)。但由于林语堂逐渐转成英语写作,在专门翻译、介绍中文作品的《中国文学月报》上就基本没再出现他的文本①。
1938年,日本掀起了翻译出版林语堂作品的高潮。当时的翻译和出版非常及时,几部代表作的原著出版时间和译著出版时间很接近。最突出的例子是Moment in Peking,原著1939年底出版,鹤田知也的译著在1940年初也在日本出版了,而且出版社就有15家。他高兴地称自己的译著在“这场世界翻译大赛中最先出版,连中文版都还没完成呢”(林语堂,1940:1)。The Importance of Living同期有两个版本,而Moment in Peking同期有三个版本问世。译者的身份也相当多元,除了有翻译家、评论家外,还有政治家、芥川奖获奖作家、社会统计学家、社会活动家、语言学家等。
以下数据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发行的盛况。1938年12月,新居格在《我國土·我國民》的改订版序文中写道:“《我國土·我國民》的译著公开销售是在七月一日,一个多月里初版的三千部就售完了。”(林语堂,1938)《有閑随筆》是1938年7月发行的,到1940年4月发行了13版。《北京の日》于1940年2月18日发行,2月20日再版。《支那の知性》1940年6月发行,到次年的8月已经发行了16版。可以说林著在日本的翻译、出版与发行呈现出百花齐放、你追我赶的火热局面。
当时对林语堂文本的评价呈现出相当大的分歧。拥护派冠之以各种头衔,阪本胜称林语堂为“眼界开阔的国际人士”(同上),永井直二称他为“难得一见的名文家”(同上:306),三木清称他为“现代的蒙田”、“东方优秀的道德家”(同上:1),笠间杲雄称他为“语言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诗人和忧国的志士”(大井浩一,2004:56)等。当然也不乏反对的声音。阿部知二、中野好夫、松本正雄等认为,林语堂其文及思想都是空洞的,甚至是危险的。尾崎秀实、中村雅男等则属于比较平和的中间派。日本战败后,林语堂写的《给日本的忠言》成为日本媒体重视的世界文化接纳自己善意之声的代表。由于林语堂的政治思想与当时中国大陆的追求背道而驰,被加以抵制,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他也慢慢淡出了日本国民的视线。在林语堂文本传播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日本民族意识形态始终作为一个隐含的主宰者,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翻译的篇目和评价的方向。
三、实用性的解释与最贴近林语堂原貌的良知论
实用论可以算是当时日本学界对林语堂作品的主要评价。评论家新居格称《我國土·我國民》不仅是评价中国及其文化的好书,而且书中“精确的见解”对今时今日的日本极为重要。“著者描写自己的祖国,却有一种外国人般冷静明澄的客观性”,“但又不会像真的外国人或者外国长大的中国人那样,缺乏对自己国家的了解”。“我觉得好像打开了很多扇新的窗户。原本思考起来笼统模糊的东西,都得到了恰当的解说”,林语堂的书真可谓“他山之石”(林语堂,1938)。政治家阪本胜说读了《生活の発見》,“你一定会吃惊,因为中国人的人生观,完全出乎日本人的意料”,“日本将成为中国新的领导者,所以此书必须要读”(同上)。社会统计学家安藤次郎和农民运动家河合徹认为,《支那に於ける言論の発達》的内容让人感觉面目一新,“通过言论的历史进行政治批判”,“给人以很多启示”。本书“通古言今”,揭示了“中国舆论的特异性和多舛的命运”,是“极好的参考资料”(林语堂,1939)。Moment in Peking的译者藤原邦夫称作品“能够让人更正确、更艺术地体会中国人的肉体和心灵,直到阴翳的每个角落”(林语堂,1940:2-3)。芥川奖获奖作家小田嶽夫认为,此书可以与《三国志》、《水浒传》、《红楼梦》齐名,“不仅是中国的生活之书,甚至是人生之书、宇宙之书”(同上:2)。林氏同时参照东方和西方的思维方式,避免一叶障目,令人感觉亲切又耳目一新。这对于日本文化人来说既有共通的文化底蕴,又有崭新的视角,领悟颇多,倍感实用。实用论者关注的是日本民族通过林氏文本对世界和自我的认知价值。
日本法文学家吉村正一郎则在《支那のユーモア》后记里指出,贯穿于林氏随笔和评论的思想就是“良知的哲学”。这里所说的良知包含理性的意思,要有能力辨别真伪,但不那么严肃;也包含常识的意思,要对人类生活起作用,但不需要墨守成规,也不欣赏卑俗和没有经过反思的随声附和。良知是“理解事物的、合理的精神”,是“实证的精神”。吉村正一郎认为,虽然我们还不清楚良知能产生什么样的积极作用,但起码它能起到一点消极的好作用。良知可能“让人变得不再勇往直前,但能让人不再做愚蠢的傻事,享受更多的和平”(同上:192-194)。吉村认同林语堂消极自由主义的活法,顺乎本性,则身在天堂。林语堂赞赏孔子的幽默和近情,儒家哲学让他扎根于烟火人间。林语堂对信仰的批判和重申让他的思想里充满了人间的理性,包含着对常识的保护。这是对日常一种免受疯狂的意识形态侵害的精神向度,与日本民族传统中的强调日常、人间性、理性的良知精神不谋而合。
林语堂小说的浪漫主义基调也是对人们的心理日常免受严苛现实侵袭的一种保护,即使是像Moment in Peking这类战争题材的小说,林语堂还是用大量的笔墨来描写历史和幻想,描写人物的生活细节,体现浓郁的文化情调和哲理意味。林语堂的小说“是一种情感世界的自然和自由状态,一种舒放、奔流和飘逸的情感意向”(王兆胜,2016:313)。这种美学选择和江户时代国学家本居宣长(1730-1801)的物哀论不谋而合。本居宣长(2014:1)在《紫文要领》和《石上私淑言》等著作中一再强调物哀和知物哀就是知人性、重人情、可人心、解人意,富有风流雅趣,要有贵族般的超然与优雅、女性般的柔软细腻之心,从自然人性出发,不受道德观念束缚,对万事万物包容、理解与同情,尤其是对思恋、哀怨、忧愁、悲伤等刻骨铭心的心理情绪有充分的共感力。良知论大致可以概括为日本人在林氏作品中发现的自身民族传统的自我确认。
无论是实用论还是良知论,都把林氏文本当作一种日本民族认识自我、认识世界的他者性工具。就实用论而言,它是所有民族自然而然的一个倾向;就良知论而言,则是最贴近林氏文本的合理阐释。
四、东方意识承载者的盛赞与危险人物的诋毁
三木清身为京都学派的哲学家,在《有閑随筆》的序言中称该作表现了中国日常生活的哲学,这也是中国人民族性的哲学,其真髓可以统合为东方人文主义。日本人和中国人思想上虽然有不少差异,但是都注重日常生活。读了林语堂,日本人“可以发现作为东方人的自己”,并产生共鸣(林语堂,1938:2)。共产主义评论家尾崎秀实在《支那の知性》序言中认为,林语堂的思想糅合了东西方文化特征,极高明地把握住了东洋(中国)文化真正的价值。他“确信只有日本人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人的知性”(林语堂,1940)。东方论是以中日两国传统文化情怀的一脉相承为基础提出的,提倡中日不分彼此,兼而有之。阪本胜则更加强调这种东方意识对西方白人哲学的冲击性,指出这是用一种悠远的中国思维的方式“戳中了白人思维的虚无”,是对白人哲学“大胆无敌”的冲击和反抗。其中代表性的作品是《続 生活の発見》,它讽刺挖苦基督教教徒,又针锋相对地反驳尼采、苏格拉底的思辨。林语堂好像“慢慢卡住白人的脖子一样,那种令人恼火的镇定,带着受虐狂式的魅力向你逼近”。“山上宝训②、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林语堂要冲破这三者构成的三次元世界。他像晴朗秋日里的野鸭一样,拍着翅膀,要从白人思想的泥沼里展翅飞起,探索四次元的世界。”(林语堂,1938)这显示出林语堂阐述的中国老庄哲学可以与白人哲学分庭抗礼。
林语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和依恋对西方哲学远离人生、不近人情的嘲讽及对欧洲文明道德缺陷的警告均见解深刻,锋芒毕露。这也让一直处于西方文化权威压制下的日本文化人感觉酣畅淋漓,扬眉吐气。日本明治时期的思想家、美术史学家冈仓天心(1863-1913)也曾经盛赞东方文明:“亚洲的精神在于具有活力、强健并且温厚的、富有人情味的和谐思想。”(蔡春华,2011)冈仓热爱佛学,到印度和中国考察风土文化,看到19世纪中叶以来亚洲各国被欧美列强入侵,或沦为殖民地,或签订不平等条约,或割地赔款,不仅政治上饱受蹂躏,连源远流长的亚洲文明也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威压下苟延残喘,令人痛心。他以博大的爱的名义批判以蒸汽和电力为代表的西方物质文明,主张要建立对亚洲文明的信心,提出亚洲一体论,呼吁团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只有日本才能够担当重任,领导亚洲复兴。这些见解与林语堂有几分相似之处,但不同是处于军事、政治、经济上升途中的日本民族显现了与传统的强势白人民族争雄的野心。日本学界的这些溢美之词重视的是东方,是新的思想和势力,而进一步的潜台词则是日本作为东方领袖的崛起。
而另一类声音则给林氏贴上了危险的标签。小说家阿部知二是较早批判林语堂的学者,他在《东京日日新闻(晚报)》(1938年9月20-22日)上发文《林语堂的“支那”》里写道:“在《我國土·我國民》里,他朴素真挚地探求‘支那’本身的真相,但是到了《生活の発見》里,他乘着前者的成功之势,利用的是半真实半理想化的、由他的脑袋想出来的支那,这是别有用心的一本书。”(河村昌子,2007)阿部否定了林著的实用性和借鉴意义。等到长篇小说Moment in Peking出版以后,当时的英美文学翻译泰斗、评论家中野好夫在《文艺》八卷二号上发表文艺时评《文学、宣传及其他》(1940年2月),断然否定该小说的文学价值,称其为“看起来最不像宣传文学的宣传文学,甚至可谓国策文学”(同上)。他抗议作品中充满了对日本的诽谤,但也无奈地承认并忧虑作品对西方社会具有强大的说服力。Moment in Peking在日本翻译出版时内容被动了手脚,大大弱化了反日气息,译者们也自欺欺人,力图辩解。《北京好日》第三部的译者松本正雄就强调了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小说的第三部“只是贯穿整部作品的‘历史’的一部分,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从来就没有摆脱过战乱——内乱与外患,只是碰巧发生于小说结束部分的那个战乱正好是日支事变(即中日战争,笔者注)而已”(林语堂,1940)。但随着战局的扩大,林语堂书写的时政评论不断出现在美国的报刊杂志上,声援中国,谴责日本。日本国内舆论开始转向,畅销作家等头衔被弃用,林语堂新的身份是“排日宣传家”(大井浩一,2004:61),是对欧美有强大影响力的危险人物,A Leaf in the Storm等也未翻译出版。
但日本没有停止对林语堂动向的关注,仍不时会有少量报道。林语堂1943年出版《啼笑皆非》,批评西方的科学定命论以及地缘政治家奉行的强权政治,倡导亚洲复兴。1944年又出版游记《枕戈待旦》,向西方介绍中国政府的抗战近况,并呼吁美国的支持。日本的报刊媒体在报道林语堂这个时期的著作以及在各地的会议和演讲时,多强调林氏批判欧美诸国对亚洲的不平等待遇和种族歧视,提倡亚洲民族的独立,开始和追随英美的中国重庆政府唱反调。日本媒体抹去了林语堂所有抗日言论,日本国民了解了林语堂的真知灼见,以亚洲大局为重,向西方社会据理力争,对日本也没有太多恶意。
由此可见,日本传播界对林氏文本中与其民族利益相冲突的部分是反感的,他们进行了有利于自己的阐释,选择性地翻译和介绍林氏的一个侧面,有时为避免相反的阐释,则干脆屏蔽之。无论是盛赞林氏的东方意识还是斥责林氏的危险与虚假,都是明显地为伸张和维护日本利益服务的。
五、被崇尚的林氏《给日本的忠言》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9月26日的《每日新闻》头版一整面刊登了林语堂的《给日本的忠言》③。后来赛珍珠(美国作家)、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开国总理)、安德烈·莫洛亚(法国作家、评论家)撰写的《给日本的忠言》也陆续登载。在日本百废待兴的节骨眼上媒体把林语堂请出来,排在首席亮相,重视程度之高应该是有其原因的。这可能与上文所述的日本媒介一直关注并强调林氏批评西方的科学定命论及强权政治,批判欧美诸国对亚洲的不平等待遇和种族歧视,提倡亚洲民族的独立等口吻密切相关。这种宣传一直持续强调林氏对日本的善意。“在信息统治加强的日本国内,通过媒体接触到的林氏的言行,让当时的日本人对林语堂的印象产生微妙的改变,他不再是‘排日宣传家’,而是倡导‘独特的重庆批判’和‘亚洲独立’的宣传家。”(大井浩一,2004:65)林语堂由危险人物变成了亲日派,选择他来发表战后重建的忠告对日本国民来说代表了先进的国际化观点,值得信赖。
更重要的是林语堂在《给日本的忠言》里所释放的善意,指出日本当前正处于重建国民生活的最困难时期,需要条理清晰、冷静透彻地思考。日本国民必须通过自己国家的自由主义领袖对自身进行再教育,下定决心努力合作,以达成波茨坦宣言的目标。日本的第一要务要认清历史,清除军国主义思想,进行立法改革、政治改革。不要再相信征服的战争及“神圣民族”这类毫无意义的观点。必须和所有的现代民主国家一样把权利移交给由人民选举出来的统治机构,清除与君主制有关的神秘主义思想。国民当然应该敬慕、恭奉天皇,并服从其命令,但是不应该把天皇当成狂热崇拜的对象。今后建立的政府必须进行社会和经济改革,要让众多的小商人、农民、劳动者都能得到更好的机会发展。林语堂还阐明不需要通过共产主义民主政治就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从《给日本的忠言》可以看出林语堂一贯坚持的自由主义者的姿态,他抨击军国主义,也不赞同共产主义。他对天皇制的建议非常符合其本人的中庸思想和人文主义思想。
林氏的善意与当时最主要的战胜国美国的民意是有较大不同的。1945年 6月29日《华盛顿邮报》刊载的民意测验结果表明,对昭和天皇主张判处死刑的占33%,主张审判的占17%,主张判无期徒刑的占11%,主张流放的占9%(关捷,2006:602),可见西方主流民间社会对日本人所崇仰的天皇倾向于采取比较严厉的惩罚。但林语堂却考虑到了日本的国情和民族情感,具有前瞻性地提出了在一定条件下保留天皇制的可能性。林氏的《给日本的忠言》尤其强调了日本民族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更新,给予新日本以充分的信任,给彷徨中的日本指引了一个容易接受并具可行性的发展方向。日本社会抓住了这个善意的声音,各大报纸纷纷转引和论及。1946年,鱼返善雄和土屋光司将林语堂的旧著翻译出版,他们均提到了该文,当时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毫无疑问,日本对林氏的《给日本的忠言》的重视是由于林氏《给日本的忠言》中的善意最能保护日本民族意识中对天皇的敬仰,是对待战后日本最宽容、对日本自我更新最信任的一种声音。它的传播是和日本对自己民族意识和利益的守护密切相关的。
六、结语
林语堂文本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日本的译介经历了最初的平静、之后的繁盛,最后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这其中有拥护派的盛赞,也有危险派的批评,还有对其善意的及时把握。在意识形态盛行的时代,某一作家文本的传播并不是一个客观全面的引进和介绍,而是在民族意识形态的主宰下呈现出不同的文化认知和多重阐释。最为客观的实用论派是基于对他人和自己的认知来介绍林氏文本的,而良知论派则是基于对自己民族意识在他者那里的自我确认来阐释林氏文本的。东方意识论派阐释林氏文本则有着明显的张扬自我作为东方领袖的意图,而给林氏文本贴上危险标签的阐释和过滤则是为保护日本利益服务的。对战后林氏《给日本的忠言》的大力传播则基于对其善意的把握和扩大。虽然日本民族的意识形态是隐含着的,但通过分析不难发现它是不容置疑的传播操纵者。这本身只是一个个案,但一个典型的个案对文本的传播、对民族意识形态乃至其他意识形态都有着可以普泛化的认知价值。
注释:
① 除了《笑》之外,《中国文学月报》第六号(1936)和第三十四号(1938)上分别刊登过林语堂的《小品文之遗绪》和《好莱坞谈》。
② 山上宝训是指《圣经‧马太福音》第五至七章中耶稣基督在山上说的话,其中最著名的一段是“八种福气”,被认为是基督教徒言行的准则。
③ 中国国内的论著没有提及林语堂《给日本的忠言》一文。本文参照了大井浩一著《メディアは知識人をどう使ったか——戦後「論壇」の出発》第51页报纸复印件以及http://linyutangstudy.webnode.jp/上的《補遺/日本への忠言》。
[1]Lin Yutang. 1935.My Country and My People[M].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2]Lin Yutang. 1939.Moment in Peking[M].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3]Lin Yutang. 1943.Between Tears & Laughter[M].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4]林语堂. 1938. 我國土·我國民[M]. 新居格译. 东京: 丰文书院.
[5]林语堂. 1938. 生活の発見[M]. 阪本胜译. 东京: 创元社.
[6]林语堂. 1938. 有閑随筆[M]. 永井直二译. 东京: 偕成社.
[7]林语堂. 1939. 支那に於ける言論の発達[M]. 安藤次郎, 河合彻译. 东京: 生活社.
[8]林语堂. 1940. 北京歴日[M]. 藤原邦夫译. 东京: 明窗社.
[9]林语堂. 1940. 北京の日[M]. 鹤田知也译. 东京: 今日の問題社.
[10]林语堂. 1940. 北京好日[M]. 小田嶽夫等译. 东京: 四季书房.
[11]林语堂. 1940. 支那のユーモア[M]. 吉村正一郎译. 东京: 岩波新书.
[12]林语堂. 1940. 支那の知性[M]. 喜入虎太郎译. 东京: 创元社.
[13]林语堂. 1938. 続 生活の発見[M]. 阪本胜译. 东京: 角川文库.
[14]王兆胜. 2016. 闲话林语堂[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5]河村昌子. 2007. 戦時下日本における林語堂の邦訳[J]. 千叶商大纪要, (45): 51-64.
[16]大井浩一. 2004. メディアは知識人をどう使ったか——戦後「論壇」の出発[M]. 东京:劲草书房.
[17]本居宣长. 2014. 日本物哀[M]. 王向远译. 北京: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8]关捷. 2006. 影响近代中日关系的若干人物[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蔡春华. 2011. 从“理想”到觉醒——冈仓天心的亚洲一体论的构造及其悖论[J]. 中国比较文学, (4): 68-79.
[20]熊文莉. 2010. 中国文学研究会にとっての「翻訳」[J]. 朝日大学一般教育纪要, (36): 1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