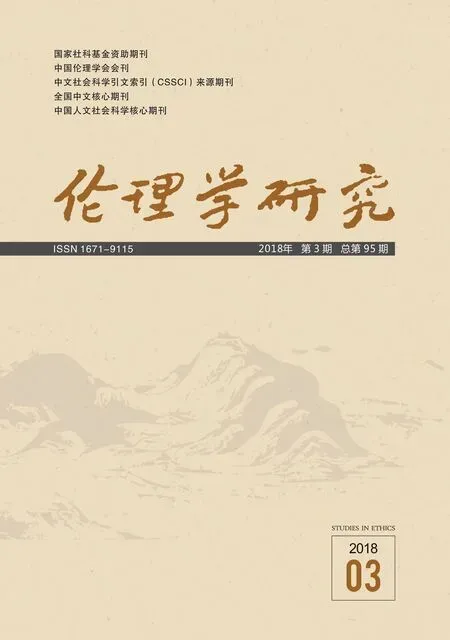“消费主义”观念影响下的网络音乐的伦理辩析
袁 茜
“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1](P2)“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看到物的生产,完善与消亡的却是我们自己。”[1](P2)这是当代社会学家让·波德里亚对当下社会环境的判断,他提出当代社会已经进入到以消费主义为中心的消费社会。在消费社会中,物品的使用价值被忽略,取而代之的是物的消费价值,人们消费物品“主要不在于满足实用和生存的需要,也不仅仅在于享乐,而主要在于向人们炫耀自己的财力、地位和身份。因此,这种消费实则是向人们传达某种社会优越感,以挑起人们的羡慕、尊敬和嫉妒”[2](P200)。在此过程中,物品成为了可以标识某种身份、地位、财富等社会象征意义的符号,人们通过消费行为获得自我确证。
消费主义是消费社会倡导的一种生活伦理和价值观念。从经济层面来说,消费是推动生产的必要手段,但消费主义主张消费至上,其实质是商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诉求,在这种状态之下,“需要”不再由社会个体本能地或主动地产生,而是在“应该需要”的刺激下被激发出来,所有的一切都掌握在利益的操控之中。从文化意识来看,消费主义主张消费是社会个体自我确证的重要甚至是唯一手段,人们通过物品消费的等级来分化人的社会地位和等级。商品是一种含有文化标识的符号,人们不需要商品的实用性,需要的是消费商品获得的安全感、认同感和自我意识,换言之,人们通过消费以获得情感快乐、梦想和欲望的虚幻满足。消费主义正形成着它对社会的统治,当文化被纳入消费体系之中时,文化与经济的合谋使得文化呈现出世俗化、时尚化、大众化等一系列消费特征。正如王岳川教授所言:“用消费主义理念支撑的社会,完全有可能成为大众媒体与世俗文化主导的世俗社会。”[3]
说到“大众媒体”和“世俗文化”,网络音乐是典型代表之一,它是当下音乐存在最为普遍的形态。一般对网络音乐的定义分为两种,广义而言指通过网络媒介传播的音乐,狭义而言指通过网络媒介和电子信息技术创作生产并传播的音乐,即在信息网络中生长并留存的音乐。文化部《关于网络音乐发展和管理的若干意见》首次对网络音乐的名称下了定义:“网络音乐是音乐产品通过互联网、移动通信网等各种有线和无线方式传播的,其主要特点是形成了数字化的音乐产品制作、传播和消费模式。“媒介文化”概念的引入使得网络音乐的文化特性被重视。所谓媒介文化,是指在我们的现实文化中,媒介不但广泛地制约着我们的观念、价值和意识形态,而且使人处于一种越来越依赖媒介的交往情境之中[4](P349)。信息网络的及时性、交互性、开放性和无中心性等媒介特征改变着人们的音乐行为和音乐观念,大众的广泛参与使得网络音乐更加具体直观地反映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在“消费主义”观念的消极影响下,网络音乐文化呈现出世俗化、时尚化、大众化等消费特征。因此,本文所论述的网络音乐是人们利用信息网络进行传播和建构的具有大众文化消费特质的音乐,它是音乐在网络中传播的主体,也是当代大众文化意识的承载体。
自古以来音乐文化就有着重要的社会伦理担当,音乐与伦理的亲缘性决定了在音乐文化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人们伦理观念的折射。网络音乐从创作到传播都具有最广泛的大众参与性,大众的伦理意识十分鲜明地投射在网络音乐的伦理价值观中,而与此相应的是,音乐作品中隐含的伦理价值观念也会传递给受众,从而影响着人们的伦理价值观。因此,在当代消费主义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在网络媒介带来的文化冲击下,重新审视音乐的伦理价值,探讨音乐伦理与大众意识的联动关系,是一个敏锐又鲜活的议题。
一、世俗与高雅——网络音乐的伦理价值取向
对于音乐文化来说,世俗和高雅是两种相对立的伦理价值取向。世俗化的音乐通常以直白的生活素材为创作内容,其形式结构往往没有固定的传承模式,而是以“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为主。而高雅化的音乐通常恪守创作传统,以文化的积累和沉淀为使命,虽取材于生活却提升出历史厚重感。从文化品位来说,世俗的音乐以取悦大众为目的,融现实生活中的嬉笑怒骂于音乐创作之中,倾向于通俗化和娱乐化。高雅的音乐恪守严肃、典雅、崇高的品性,追求意境的深远和意义的升华,具有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从传播效果来看,世俗化的音乐往往得到大众的拥戴,传播范围较广,但是鲜有经典传世。高雅化的音乐往往曲高和寡,其受众大多是有较深音乐修养的专业人士和品位较高的音乐爱好者,即通常所说的文化精英,因而高雅化的音乐传播圈子较小,但容易沉淀出精品。从创作动机来看,世俗化的音乐创作者或为名利,或是为了表明自己对生活的态度;高雅化的音乐创作者一般都是为艺术而艺术,把对艺术的追求看作人生的信仰,表达的是对社会对人生的思索和终极关怀。
在历史进程中,世俗和高雅的文化争夺表现为大众和精英的文化话语权的争夺。在大多数情况下,精英们占据着文化的制高点,他们所推崇的高雅音乐以精湛的技艺和崇高的艺术追求获得了权贵阶层的青睐,从而成为社会的音乐价值标准。而世俗化的音乐以其生活化的审美趣味流行于巷道坊间,也有其活跃的阵地。在二者的交流碰撞之中,文化精英们试图通过审美标准的建立将世俗化的音乐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而世俗化的音乐则通过争取广大的受众获得话语的对抗,并以世俗化的审美价值观消解经典。在此消彼长的进程之中,媒介技术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印刷术(音乐纸质媒介)到音乐录制技术(声音媒介),再到广播电视(电子媒介),媒介技术的每一次革新都推动了音乐传播的大众化——媒介技术使音乐的受众范围扩大了。而作为信息媒介的网络技术以其无可比拟的传播能量将音乐的大众化推向了极致。在此种情形下,作为大众文化标识的世俗音乐获得了颠覆高雅的契机。
与此同时,现实社会的经济环境和人文环境也发生着剧烈变革。消费主义的盛行使得音乐的世俗性得到空前发展并越来越趋向于低俗化,音乐的审美价值转变成了消费价值,音乐的文化使命变成了大众娱乐和休闲。因此,网络技术和消费主义环境的合谋使得世俗化成为的网络音乐的文化标识。一时间网络音乐时空风起云涌,从第一批网络歌曲“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大学生自习室”,到第二波的“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再到后来的“江南Style”“最炫民族风”“小苹果”,等等,都以直白地描述生活和爱情,或者调侃讽世为特征,再有大量对于经典音乐的篡改、拼接和恶搞,例如“刺激”系列、恶搞红色经典系列等,掀起了世俗颠覆高雅的全民狂欢。
世俗化是当前网络音乐的发展趋势,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得到印证:第一,从网络音乐的社会功能来看,娱乐和休闲成为音乐的首要功能;第二,从网络音乐的内容来看,反映都市生活的琐碎的情感题材成为主要内容;第三,从网络音乐的文化品位来看,粗鄙、戏仿、反讽的市民化趣味成为主流;第四,从网络音乐的流行规律来看,感官的刺激和时尚的诱导是音乐流行的激活代码;第五,从网络音乐的作品案例来看,某些低俗、庸俗的音乐作品一度成为网络热点。这些特征不但表明网络音乐的世俗化乃至低俗化趋势,还充分印证了消费社会的庸俗价值观。消费主义打着“人性解放”和“精神自由”的旗号不断地将世俗化甚至庸俗、低俗、恶俗的音乐作品复制扩散以谋取利益,而那些艺术性较强的高雅音乐作品成为了被忽视甚至被嘲弄的对象。
不仅如此,为了扩大音乐的消费版图,技术与市场合谋将高雅音乐以一种不被察觉地方式纳入消费体系。马尔库塞的这段话也许可以作为参照:“今天的新奇之处是通过消除高层文化中对立的、异己的和超越性的因素——他们借助高层文化而构成现实的另一种向度——来消除文化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对立。清除双向度文化的办法,不是否定和拒斥各种‘文化价值’,而是把他们全部纳入已确立的秩序,并大规模地复制和显示它们。”[5](P47)马尔库塞认为,高层文化具有一种否定现实和超越现实的特质,他与现实始终保持着一段距离,但在当代工业社会发达地区,文化却因为屈从世俗化趋势而具备了商品的形式[6]。马尔库塞的观点在当前高雅音乐的商品化发展中得到了印证。在网络背景音乐、网络广告音乐、网络游戏音乐中也常常引用经典音乐作品,但是这些音乐作品已经失去了往日高雅的艺术特质,成为了文化时尚的附庸,或是消费商品的增值内容。如果说高雅音乐由于其精湛的技艺和优雅的品味曾经一度成为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身份象征的话,处于网络社会中的高雅音乐已经沦为了一种供人娱乐的消费符号了。
二、生活与艺术——网络音乐的伦理价值归属
“为生活”还是“为艺术”?对于这个命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读。第一层涵义是音乐家的事业信仰问题;第二层是音乐的价值归属问题。在音乐传播的历史进程中,音乐家从来都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他们的创作理想常常受到社会权力、经济环境、文化思潮等多重因素的制约。例如,在19世纪以前的欧洲,音乐家们大都依附于权贵而生存,他们的作品也多为讨好宫廷贵族而作。音乐家们一方面为艺术理想屈就于权贵趣味而感到沮丧,另一方面又感恩于贵族阶层对自己的资助和扶持。查尔斯·H·H·帕里(Charles H.H.Parry)写道,“甚至贝多芬在采用一种音乐形式(奏鸣曲式),并把它带至高峰态度也是矛盾的,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不仅因为其中带有他的时代的习惯的趣味,而且也明显地表现出他喜爱自己所不属于的和由于他的民主坚定信仰而反对的社会圈子:贵族。”[7](P65)18世纪末期随着资本市场的兴盛,音乐家逐渐从对权贵阶层的依赖中解脱出来,获得了一种遵从市场需求的自由职业。“前所未有的商业机会的增长散布于音乐的多个方面,诸如复制、雕版印刷和印刷,使无数具有独立精神作曲家和演出者不用求助与传统类型的赞助而从事他们的职业。”[7](P75-76)由此可见,市场在发展初期对于音乐家的职业自主起着积极的作用,它在经济上解放了音乐家们依附于贵族的生活状态,提高了音乐家的地位,为音乐家的艺术自由提供了宽松的环境,这是市场对于音乐发展积极的一面。与此同时,市场对音乐家的控制也悄然滋长,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和成熟,经济利益法则再次将音乐家的命运绑架在市场需求之下,为了迎合市场的需要,音乐家们不得不“生产”出违背艺术理想的作品,音乐家和工人们一样,成为了创作生产的机器。在消费需求的驱使之下,音乐市场常常“拒绝那些先进的”作品[7](P86)。在以消费经济为主导的现代社会,作曲家面临的处境更加严峻,因为大众的音乐消费是建立在音乐体验和官能刺激的基础上的,世俗化的审美趣味、惊颤的音响效果是吸引大众眼球的重要手段,而这与音乐家的艺术理想是格格不入的,于是音乐家们再次陷入了“为生活?为艺术?”的两难境地。
毋庸置疑,网络的出现为音乐的大众化发展开拓了新的领域,网络技术营造的民主氛围成为市场推进音乐消费的完美理由。自2001年网上推出《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始,网络歌曲呈逐年递增的发展态势,其中2010年至2016年间每一年都有风靡网络的“神曲”诞生,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流行狂潮。从各类“神曲”的音乐内容和风格特征入手,可以获得这些作品的流行密码:第一,浅显的、通俗的歌曲可以获得较高的传唱度,例如《小苹果》《大王叫我来巡山》等,这些作品旋律简单歌词易记,听过几遍就能随口哼唱。第二,贴近生活题材的音乐作品可以获得广泛的受众共鸣,例如《爱情买卖》《剩男之歌》《马上有钱》《江南Style》等反映的是生活中的爱情观和金钱观。第三,指涉社会热点事件的歌曲因符合大众的戏仿和调侃的心态而常常伴随热点事件持续发酵,如《我不想说我是只鸡》(反讽“禽流感”事件)、《买房国际歌》等等。由此可见,“生活”已然成为了网络音乐创作的核心,这与消费主义的“让生活更美好”的意识推广是不谋而合的。
为生活?为艺术?——网络音乐给出的答案是为生活,而生活的意义在于消费,通过消费人们才能获得自我确证。消费在社会生活中获得了一种神奇地位,人们把消费作为幸福来体验[1](P7-8)。消费主义倡导的幸福感是建立在欲望的满足的基础之上的,是审美生活化、世俗化、娱乐化的价值体现。消费社会试图将所有事物纳入消费体系,用“生活高于一切”消解音乐的艺术性,在追求个性和自我的网络空间,生活对音乐艺术的解构表现得尤为明显。从音乐的内容上看,占据主导优势的网络流行歌曲几乎是社会生活的素描,有些歌曲甚至赤裸裸地反映浮躁、低俗的社会生活现象或事件。当然,对高雅音乐抱有成见的人可以用“音乐不应当为了艺术而艺术”“音乐来源于生活”进行辩驳,倡导审美日常生活化的人也可以说“音乐的价值在于对生活真实的反映”。但是音乐毕竟不能完全等同于生活,它与生活的区别恰恰在于其艺术特性。它对生活的反映应当具备三个特征:创造性、多样性、思想性,因而音乐应当艺术地反映生活。这既符合音乐艺术的创作规律,又能够适应人们全面的音乐需求。因此,消费主义倡导的网络音乐的症结在于,把人们对于音乐的多层次的精神需要单一地设定为娱乐快感的满足,由此获得精神消费的价值最大化,在此过程中,作为消费主体的人的欲望被无限放大,享乐和占有成为了人生追求的主要目标和最高价值,音乐成为了人们娱人娱己、调侃生活的工具,这样的音乐消费不但不能够给人们带来深层次的幸福体验,反而让人感到精神空虚和麻木。在所谓的以生活为核心的价值判断中,网络音乐成为了迎合低级趣味的消费品,与此同时作为消费主体的人也逐渐沦为丧失审美能力的精神乞丐。
三、功利性与艺术性——网络音乐市场的伦理价值评判
艺术的生存需要资金的支持。在商品经济出现之前,音乐家通过获得个人赞助或社会机构的支持来坚持艺术创作。随着音乐商品化的发展,音乐家逐渐成为市场中音乐商品的提供者,获得了经济和身份的双重独立。与此同步,音乐的使用价值逐渐被市场开发,最终超越艺术价值成为音乐价值的核心。消费社会的形成是物质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的成熟阶段,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音乐作品使用价值被极度挖掘以实现商品利润的最大化。音乐的价值在利益的驱动下被重构,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第一,音乐作品的艺术性向实用性转变;第二,音乐艺术价值向音乐消费价值的转变;第三,音乐欣赏行为向音乐消费行为的转变。这三个转变的深层动因是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音乐的艺术性向功利性的让渡。“文化工业引以为豪的是,它以自己的力量,把过去艺术中无法改变的原则纳入到了消费领域之中,并剥离了艺术的强制性和天真的特性,将之提升为一种商品的质性……文化工业取得了双重胜利:它从外部打碎了真理,并在内部以说谎的方式无限制地把它重建起来。”[8]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市场的存在形式变得灵活多样,借助于虚拟的网络空间,市场不再需要依附于真实的地点和场所,商品的信息化拓宽了市场的运营范围。就网络音乐而言,音乐产品以数字化信息的形式存在,人们通过下载或在线播放进行消费,付费方可以是产品使用者本人,也可以是第三方(如广告商)。网络信息传播的高效与便捷使得一首音乐作品可以在极短时间内获得广泛的认知,而对于市场来说,消费群体的规模意味着利润的空间。因此,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制作和推广能够引起关注的音乐作品是音乐市场最重要的生存法则。这其中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将网络推广放在首位,不论音乐产品质量如何,好的网络营销就成功了一半,例如我们常常看到病毒营销、恶意炒作等现象。第二种是看中音乐作品本身的商业价值,根据消费者的喜好投其所好地制作音乐产品,提前预测消费者的心理预期,迎合或刺激消费者的消费欲望。这两种方式常常结合在一起,共同点是将音乐的艺术性放在次要位置,音乐作品成为了获取利润的工具,只要获得市场认可、能够取得高额回报的音乐作品就是好的音乐作品——市场成为了衡量音乐价值的唯一标准。遗憾的是,这里的音乐价值早已背离的音乐本身,吸引消费者眼球的往往是娱乐、新鲜、刺激等消费价值,而这些价值正是传统音乐观念所鄙视的。
在网络音乐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推动下,人们的音乐理念也发生了转变,人们对音乐的欣赏不再是为了获得美的心灵感悟,而是为了消遣和娱乐。像Pen Pineapple Apple Pen这类滑稽搞笑的作品的风靡证明了这一点。这是一首由日本搞笑艺人Piko-Taro创作的“神曲”,全曲主要内容由Pen、Pineapple、Apple三个单词组成,利用单词拼读和浮夸的表演产生滑稽的效果。这首MV被放到YouTube上不到一个月便被播放700多万次,并在世界范围内疯狂传播,两个月点击量已破亿。对于艺术欣赏和消遣娱乐这两种心理,本雅明曾做过绝妙描述:“关于凝神专注和消遣作为两种对立的态度可表述如下:面对艺术作品而凝神专注的人沉入到了该作品中;他进入到这幅作品中,就像传说中一位中国画家在注视自己的杰作时一样。与此相反,进行消遣的大众则超然于艺术品而沉浸在自我中,他们对艺术品一会儿随便冲击,一会儿洪流般地蜂拥而上。”[9](P288)当今网络音乐作品的短期走红和迅速离场证明了大众的消遣心态,人们对音乐的艺术敬仰转变为对音乐商品的用度,音乐与其他货物一样成为人们唾手可得随时可弃的消费品,音乐的艺术价值被市场消解。
人们的消遣心态影响着音乐的价值取向,反过来音乐价值的变化又影响着人们的音乐消费观。在此过程中,市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市场出于功利的目的忽视和消解着音乐的艺术价值,将功利化的游戏规则应用于音乐创作与传播之中。人类的精神世界因此受到了市场消费的侵蚀,人类不再具有崇高、伟大、深刻的精神理想,而是疲惫地在娱乐享受和感官刺激中游荡,人类的精神根基受损,最终将如富有洞见的学者们所预言的“人类自身异化为消费物”“人最终消费的是自己”。
四、暴力与性——网络音乐的伦理价值导向问题
波德里亚在其著作《消费社会》中论述了“身体”的消费现象:“在经历了一千年的清教传统之后,对它作为身体和性解放符号的‘重新发现’,它(特别是女性的身体,应该研究一下这是为什么)在广告、时尚、大众文化中的完全出场……今天的一切都证明身体变成了救赎物品。在这一心理和意识形态功能中它彻底取代了灵魂。”[1](P120)波德里亚认为身体在消费社会是作为一种消费符号呈示的,人们从物质性和功用性来看待身体,并生成了“身体关系新伦理”,而在“各处指导着身体之‘重新发现’及消费的,就是性欲”。[1](P125)在当代社会的大众文化中,身体的出场是必不可少的,并且似乎只有将自己置于在身体的符号系统之下,文化作品才能够积攒足够的人气。网络音乐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身体消费”理念的感召,将身体因素融合于音乐创作之中。从具体表现来看,当前网络音乐的身体化倾向有两种,一种是“性”,一种是“暴力”。
网络歌曲的走红需要一些吸引眼球的特质,如果没有足够的艺术水准的话,内容刺激的低俗创作被认为是条捷径,这正符合了文化市场竞争中的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法则)。不少以情感为主题的网络歌曲为了增加“曝光率”“刺激度”,其歌词内容往往包含暧昧的性暗示,例如《香水有毒》《冲动的惩罚》《伤不起》《爱火》等。更有甚者,从歌名来看简直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性展示:《少女的初夜》《纵欲》《飞向别人的床》《那一夜》等等。还有不少歌手在表演时通过裸露身体或暧昧动作(Lady gaga是典型代表)吸引眼球,这些表演视频同样是网络歌曲“性展示”的一部分。这些歌曲出于功利的目的通过“性的展演”走红网络,不但抹杀和颠覆了音乐的艺术气质,对于传统的爱情题材的歌曲也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力。爱情是人类的美好感情,也是人伦常情。爱情题材的音乐通过对爱情或纯真朴素或崇高伟大的描绘,表达着人们对真爱的向往和追寻。这本是人类真实可贵的情感,却在当今的网络歌曲中褪了色。部分低俗、浅薄的网络歌曲以爱情为由放大情爱内容挑逗着人们的感官,把性的暧昧等同于爱情。在这种精神垃圾的污染下,人们无法从音乐中体会爱情的圣洁崇高,人们的爱情观受到了侵蚀。这便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为什么在情爱文化泛滥的社会,反而会诞生爱情悲观主义了。
网络音乐中另一种形式的身体出场是暴力。暴力是力量和欲望膨胀的展演,是背离道德规范的一种身体释放,因此精神世界的暴力幻想能够带给人一种身体膨胀和释放的快感。消费时代的经济是以“体验”为消费特征的,它以身体自由和解放为噱头,建立起一套以“刺激-反应”为基本模式的类似于生理活动的感官体验系统。在当前流行的网络音乐作品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暴力因子的存在,从重金属摇滚中嘶哑的吼叫,到游戏音乐中震耳欲聋的音响轰鸣,再到演唱者狂放粗野的表演形式,无不激发着人们内心如恶魔般蛰伏的情绪猛兽。更有甚者,一些网络歌曲中包含着赤裸裸的暴力化歌词内容,例如《被逼的》《牛逼的天津》《粗口成脏》等等。这些歌曲用类似爆粗口的方式发泄情绪,是以音乐为工具的暴力展演。网络歌曲的暴力化倾向是对人的负面情绪的一种迎合,或者说为了获得消费价值而刺激和夸大受众的负面情绪。在这些歌曲中音乐早已成了配角,满载怨愤情绪的声响、表演、语义才是卖点,暴力体验早已超越了音乐体验。道德的意义在于通过人的自我管理来获得内心的平衡,不良情绪的疏导应当在真善美的体验中实现,音乐正是承载着“美”的道义。如果连音乐都成为了暴力展演的工具,人类怎能面对人生中的精神困境?又如何通过艺术完成自我的精神救赎?当前在网络中流行的粗鄙作品不但抛弃了音乐的精神使命,反以自由解放为借口,诱导和刺激着人们的心灵之恶,冲击着人类道德文明的底线,既背离了音乐艺术也背离了人类自身,是艺术品性的堕落也是文化伦理的失守。
结 语
消费主义是当代社会盛行的生活伦理和价值观,其核心是将一切物质与精神都纳入消费体系,以消费逻辑重构人类文明。网络音乐是大众文化的代表,大众的消费意识和价值观念影响着网络音乐的创作和传播,使网络音乐呈现出以消费为中心的伦理价值导向,表现为网络音乐的低俗化、生活化、功利性和“身体展演”等多个方面。同时,网络音乐所包涵的伦理价值观念又反过来参与着大众精神文明的建构,进一步推动着消费主义对于社会伦理的统治。因而,网络音乐文化与社会人文环境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联动关系,以当下消费主义的社会环境为背景来研究网络音乐的人文特征和伦理价值,可以更加清晰地观察当代社会环境对于网络音乐伦理观的影响,以及网络音乐对于社会伦理价值观形成的作用。网络促进了音乐的传播与普及,本应更好地发挥音乐的娱乐、教化和心灵净化的功能,但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之下,网络音乐出现的低俗化、功利化的趋向,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必须对其进行必要的制约,引导网络音乐正向发展,进而构建健康和谐的社会人文环境。
[1]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王宁.消费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3]王岳川.消费社会中的精神生态困境—博德里亚后现代消费社会理论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7).
[4]周宪.视觉文化的转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08.
[5]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6]向玉乔.后现代西方伦理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7]伊沃·苏皮契奇.社会中的音乐:音乐社会学导论[M].周耀群,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
[8]仰海峰.法兰克福学派工具理性批判的三大主题[J].南京大学学报,2009(4).
[9]本雅明.经验与贫乏[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