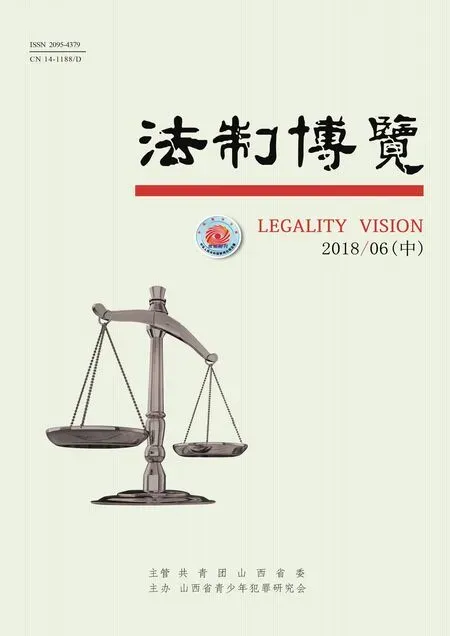唐代刑讯制度的技术优越性与人治并存的缺陷
张 傲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 武汉 430000
惩罚犯罪行为人的罪行一直是古今中外所认同的,从刑罚的目的来看,就是惩治和预防犯罪。那么,在已掌握一定证据与线索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让罪犯认罪伏法,或是使无辜之人摆脱嫌疑,就是十分重要的环节。
为了实现这一环节,从古至今,我国的刑法制度中采取了多种的手段,如秦代云梦睡虎地出土竹简中《封诊式》中《讯狱》篇就规定了笞讯的方法。汉承秦制,沿袭前代,并进一步发展,只规定三种刑讯方式,“掠者唯得榜、笞、立”,将刑讯手段减少,规范化。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分裂,隋朝重新统一全国,隋文帝颁行《开皇律》,废除了许多酷刑,规范了笞杖徒流死五刑,完善了“八议”、“官当”封建等级司法特权,确定了封建法律中的“十恶”,成为唐律的重要基础。
一、对于年老年少者和孕妇的刑讯
断狱六——八议请减老小,“诸应议、请、减,若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者,并不合拷讯,皆据众证定罪。违者,以故、失论。若证不足,告者不反坐。”对于年龄在七十岁以上老者,十五岁以下的孩童,不能进行拷讯,否则,以故意或过失论罪,要是证据不足,诬告之人也不会受到刑罚。三句话,就精简明确的规范了四类主体,两种处理方式,即年老者、年幼者、为官者、错告之人,和定罪以及是否反坐的惩罚方式。
断狱二十七——拷决孕妇,“诸妇人怀孕,犯罪应拷,及决杖、笞,若未产而拷、决者,杖一百;伤重者,依前人不合捶拷法;产后未满百日而拷、决者,减一等。失者,各减二等。”即孕妇犯罪后应施杖、笞刑的,监官在她生产前或产后不满百日施刑的,要处杖一百或是处流徒之刑,致重伤死亡的,则判加役流。以上两条充分体现了唐律中人道主义的方面,体现了统治阶层对于弱势群体的恤民之心。
二、对于普通囚犯的刑讯
(一)刑讯对象的认定
在一件刑事案件中,最主要的主体就是被害人(原告),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古代似乎没有区分),其次是证人。古代官僚统治阶级占据着绝对优势的地位,采取的是典型的纠问式诉讼,本质特征是官员主动依职权追究犯罪,原告和被告都没有诉讼主体地位。[1]可想而知,前面提到的三个主体都会成刑讯的对象。首先是被告人,在古代,被告人在有罪推定的法律传统下,几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囚”的身份特征,其口供作为证明犯罪的重要证据,对其刑讯就成了官员们最寄予希望的断案捷径。其次是证人,证人一般不会被讯问,但是,较为健全的唐代法律制度没有忽略掉证人作伪证或是知情不报的情况,虽然唐律中没有专门的对证人刑讯的条文,但是在“八议请减老小”中《疏议》对此的表述是“以其不堪加刑,故不许为证”,可知,对于“堪加刑”的证人来说是可以刑讯的。[2]
(二)刑讯程序的规范
断狱八——讯囚查辞理,“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察辞理,反覆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官员讯问囚犯前,一定要审慎了解案件情况,反复考究,在经过言辞质讯之后,罪犯仍然不招供或者审判人员“认为”其招供不实,案件的判决“犹未能觉”,这时,才能适用刑讯。
断狱九——拷囚不得过三度,“诸拷囚不得过三度,数总不得过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过所犯之数。拷满不承,取保放之。”[3]这是对刑讯手段数量与次数的硬性规定,因为刑讯是通过对讯问人施加痛苦而使其对犯罪行为产生悔意与对刑法感到恐惧,从而招出所犯罪行,但反之,屈打成招的例子也不在少数,所以对于刑讯杖责等手段加以量化性规范是刑讯程序的一大优点。
断狱十四——决罚不如法,“诸决罚不如法者,笞二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如法,即依法,这是依法治民的重要体现,虽说在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社会,人治高于法治不可避免,但是将人治的手段制定成成文法去实施,也是法制文化的一大进步,有利于让百姓去接受律令。
关于官员错判、错罚的责任制度也有规定,这里就不再一一说明。唐代处于我国古代政治经济高度发达的一个历史时期,法律制度完善,文化环境也较为宽松,所以产生了完备的刑讯制度,包括人道主义思想以及不同主体在刑讯中的不同义务与责任。同时,当事人权利的缺失与审判官员的主观随意性和优势审判地位,也注定了刑讯制度的不公正性和残酷性,为后世刑讯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制度土壤。
从以上条例的分析来看,可以说,唐代的刑讯制度保留了前代的基本框架思想,[4]也融入了盛世独有的文化,具有人道主义与法律技术性并存的特点。
[ 参 考 文 献 ]
[1]张小海.论被害人在程序法上的地位与完善[J].中国律师,2012.
[2]蒋雪智.论刑事诉讼被害人的地位及权利保障[D].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硕士),2004.
[3]谢波.唐宋刑讯制度传承演变考论[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
[4]胡元元.唐代刑讯制度研究[D].安徽大学,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