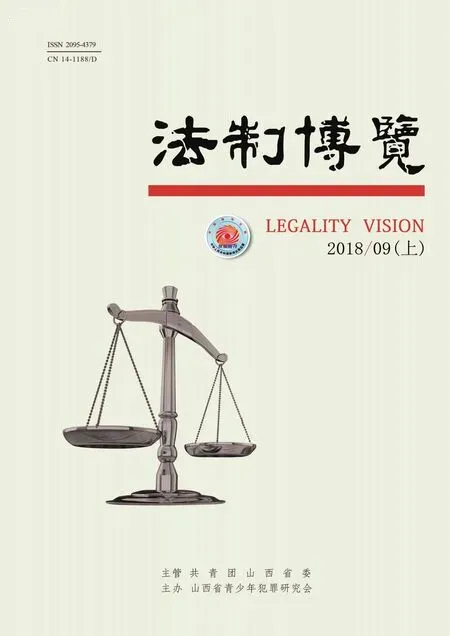被胁迫杀人行为的法理分析
王志鑫
黑龙江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一、案例的引出
被告人刘某、岳某、冯某和陈某等人为了勒索钱财,一起绑架了某集团董事长章某。之后,刘某、岳某持刀、枪反复威胁章某某,令其答应在2016年3月之前交付赎金1亿元人民币。为了能够确保章某不报警并按期交付赎金,刘某等人胁迫章某与他们一起用绳索将一名女性被害人杀害。在杀害的同时,刘某对整个杀人过程进行摄像记录作为威胁依据,之后将章某释放回家准备赎金。
二、案件争议焦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如何定性章某的行为,虽法院未对章某进行处罚,但分析章某的行为在刑法学领域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此学界存在着几种观点。
如果将其行为认定为有罪,则章某属于胁从犯。此观点认定章某构成犯罪,但因其参与犯罪是被胁迫的结果,故可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如果将其行为认定为无罪,通说存在三种观点:紧急避险论、阻却责任的紧急避险论(来源于德国刑法对紧急避险的二分法)、期待可能性理论。
但是,我国刑法仅存在着胁从犯和紧急避险两个范畴。有观点认为,“被胁迫行为在我国刑法体系下应当是紧急避险与胁从犯二选其一的情形。”[1]这样的观点难免显得有些狭隘。通说还认为紧急避险中被侵害的法益应小于被保护的法益。所以,本案之所以会存在着诸多争议,原因有以下几点:(1)章某遭受的是生命威胁这样的重度威胁;(2)本案中被胁迫者的行为侵害的法益与所保护的法益价值相等;(3)本案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
三、对争议焦点的分析
(一)从胁从犯角度分析
“胁从犯,通说认为是指被胁迫参加犯罪的人,即在他人的威胁下并非完全自愿地参加共同犯罪,且在共同犯罪中起较小的作用(次于从犯作用)的共同犯罪人。”[2]胁从犯是我国独创的概念,其依附存在于共同犯罪之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本案中,章某被刘某等人胁迫实施犯罪行为,符合二人以上这一条件。然而,很难确定章某与其他犯罪分子存在着犯罪故意。
不过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胁从犯的判定应只限于心理性强制而不是物理性强制,处在物理性强制下的身体动静本身就不是刑法上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该行为不能成立犯罪。”[3]章某当时被刘某等人用管制刀具等凶器进行威胁,从一般人的角度来讲,当时章某并未被束缚身体,对于杀人行为的危害后果也有着一定的认识,是可以自己做出选择的,也就是他并未受到物理性强制,仅是心理性强制,所以并不能以这个理论来为其脱罪。
综上所述,章某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而危害他人生命的行为与刘某等人属于共同犯罪,成立胁从犯。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来进行处理: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二)从紧急避险角度分析
如果能够认定被胁迫者的行为构成紧急避险,则章某不成立犯罪。本案中,章某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权益而侵害他人的生命权益,这两个权益在本质上是相等的。“如果所引起的损害等于或大于所避免的损害,就有悖于紧急避险的意义和目的,成为对社会有危害的行为,也就失去了合法性。”[4]
根据以上的分析,从衡量法益的角度进行判定的话,章某的行为并不能构成紧急避险,也就无法阻却其行为的违法性。
(三)从期待可能性角度分析
所谓刑法上的期待可能性,就是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是否可以期待其做出适法行为的可能性,如果有这样的可能,则可以判定行为人是存在着犯罪故意的,也就是成立犯罪的。
本案中,章某完全可以用钱来保护自己和被害人的生命安全,因为犯罪分子的目标只有钱。生命具有平等性,章某不能为了自身的安全选择牺牲其他无辜者的生命,所以说不能用期待可能性的理论为章某不成立犯罪作辩解。
四、结论
通过前文的分析,笔者认为本案应认定章某成立故意杀人罪的胁从犯,并在量刑上根据其犯罪情节的严重性来从轻处罚或减轻处罚。这样才能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维护法律的正义性和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