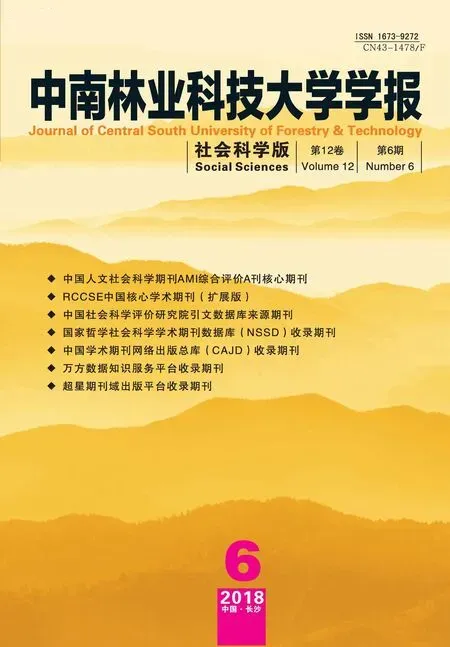顺从—征服—尊重: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伦理梳理
曹康康
(同济大学 人文学院哲学系,上海 200092)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人同自然的关系史呈现着不同的伦理特征。在“前农业”文明时期,人类秉持着崇拜于自然、依附于自然的伦理态度,饱受着自然界强大“异己”力量的对立威慑,依靠“其动物式”求生的“本能”过着“采集—渔猎式”的相对散漫生活;在农业文明时期,人类逐渐呈现出利用自然、依赖自然的伦理属性,但他们依旧怀揣着对自然界万物生灵的敬仰崇拜,依靠其日益健壮的“体能”和“人类手脚简单延伸”的粗劣工具过着相对简单的“封建庭院式”生产与再生产生活;可是在工业文明时期,人类疯狂的展现出控制自然、利用自然、征服自然的反伦理倾向,此时“人类神”战胜了“自然神”,自然万物由“图腾崇拜”演变成了“上帝诸神”的馈赠,人类依靠其日益成熟知识文化技能,尤其是利用机器延伸了的“手与脚”过着上天入地下海的“资产阶级”奢靡生活。然而,当人类步入“后工业化”社会的历史阶段时,日益蔓延的环境污染、资源匮乏、生态失衡等全球性生态问题集中展现在人类面前。人们不得不开始重新反思“人在自然中到底处于什么位置”“人与自然的真实关系是什么”“人在何种程度上达到与自然和谐相处”等等问题。当人类怀揣着种种疑惑发问之时,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为伦理表征应运而生。
一、肯定阶段:“顺从自然”的伦理表征
当人类处于古代前农业文明和农业文明时期时,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大体呈现出“顺从自然”“仰慕自然”“依附自然”等的伦理表征。总体来说,这是由当时人类主观依附意识的强烈和客观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决定的。一方面,社会生产水平低端决定着自然生态系统受外界干扰因子的影响较小,从而使生态系统依旧保持着其良好的自组织特性、保持着其系统结构合理性、保持着其系统稳定性。另一方面,依附自然的强烈意识决定着人类不可能对自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这对于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演化,保持自然、社会以及人类的“低度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如何理解这样“低度和谐”的境况呢?从实质上看,人与自然之间认识与改造关系是和谐平衡的;从数量上看,人与自然之间认识与改造能力是低端滞后的。在古代前农业文明和农业文明时期,造成这般“低度和谐”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方面,从人的主观愿望上看,人类追求“天人合一”。从原始巫术宗教到部落图腾崇拜,再到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封建传统文化,无不宣扬人依附于自然、人受命于天地的伦理主张,在这种“伦理范式”支配和影响之下,人类逐渐萌发了“顺从自然”的主观思想意识,诞生了“依附于自然”的道德品质。另一方面,从自然的客观实际来分析,人类被迫顺从依附于自然。由于人类认知与改造客观自然界水平的低端落后,生产力因素与科技手段的无足轻重,从而客观上彰显自然客体“异己”力量的异常强大,很大程度上使得人的能动性让位于受动性,从而客观上致使人类不得不顺从依附于自然。因此,人类“顺从自然”的伦理品质是主观意识与客观实际双重互动整合的效果展示。“顺从自然”的伦理品质具有以下两大方面表现:
第一,人类“顺从自然”的伦理品质表现为“人”层面上对自然的“寄生性”。一方面,维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物质生产消费资料的需要寄生于自然。就原始采集渔猎时代或农业文明而言,人类社会以及自身发展的快慢与好坏直接决定于自然生存条件的优劣与否。一般而言,自然地理气候条件好的地方,人类依靠“体能”也许勉强可以求得温饱而延续人类生命存在;而对于自然地理环境恶劣的地方,人类随时可能面临饥饿灾荒而终止繁衍。换言之,人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人本身“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生存发展的物质前提,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人要靠自然界生活”[1]另一方面,人类的精神发展需要也寄生于自然。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西方世界,都不乏寄情于山水的“士大夫阶层”,他们热爱自然,称颂自然,甚至超然于物外,中国的庄子和陶渊明可能是最好的例子;同时也不乏寄喜乐悲伤于天地的寻常百姓阶层,如若他们喜迎乐事,定会焚香祷告,跪谢天恩;如若他们遭受悲痛,更会祈福免灾,安定人心。因为此时自然被人们供俸成“神”或“天”。总而言之,此时人的主体属性淹没于自然客体属性之中,人的自由属性也沉浸于其必然属性之中,从而表现出“人”层面上“人顺天”伦理特性。
第二,人类“顺从自然”的伦理品质表现为“物”层面上的自然“衍生性”。一方面,从生产发展水平看,无论是从石器到铜器再到铁器的劳动工具,还是供人类生产灌溉或日常生活饮用的沟渠、水井等人工设施,还是维持人类生存需要的谷物、果蔬以及家禽等劳动产品,无不透着“物”层面上的自然“衍生性”。另一方面,从消费流通层次水平看,普通民众服饰主要以粗麻、棉布为主,日常生活饮食主要以种植谷物、驯养家禽为主,绝大部分农户住宅自然而简陋,正常的交通出行则以步行、牲畜车为主,由此可知,当时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都显示出了“物”层面上的自然“衍生性”。正如马克思指出那样,“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1]。自然界是物质生产的原料库,人无法创造出“新物质”,人只是有大脑的“搬运工”而已,在自然原有“旧物质”基础上创造着现有的“新事物”。换言之,此时人工“创造物”基本保持着自然再生属性和自然层理结构,没有打破自然原始机理与天然平衡,从而表现出“物”层面上的古代的“人顺天” 伦理特性。
二、否定环节:“征服自然”的反伦理倾向
随着近代工业革命展开,人类社会开始由手工工场时期进入了机器大工厂文明时代。在这资本文明的冲击下,人类主观利己主义的欲望日益膨胀,人类客观科技生产手段的日渐精进,可是这种膨胀和精进的同时“利用自然”“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反伦理劣迹日益凸显蔓延。此时,人类活动打破了原始生态平衡,生态系统自组织功能严重遭受破坏,自然、社会以及人类之间不和谐因子高涨,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倾向也大体呈现出“征服自然”的反伦理特征。恩格斯告诫我们“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绝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2]。马克思不仅向我们剖析了“人与自然的矛盾根源在于资本逻辑”[3],还要求我们“站在社会历史视域考察自然概念,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行完全的变革”[3]。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种“反伦理”特性呢?总的来看这种“反伦理”特性具有两方面蕴涵:从其“质”的角度看,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的方式是不和谐的;从其“量”的层面考察,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的能力是发达的。一方面,从主观上解析,人类日益膨胀的反伦理物质欲望需要从自然界中获取大量的物质与能量来满足自我无限度欲望。此时,物质主义战胜了禁欲主义,“自然当做一种绝对的东西来代替基督教的上帝”[4],人类求知欲的扩张客观上也加速人们“金钱观”的膨胀,生产消费欲望越是高涨,马斯洛“塔底”越发壮大,“天人”矛盾越发尖锐。另一方面,从客观上解析,人类能够且可以从自然界中获取大量的物质与能量来满足自我无限度欲望。此时,科技文化战胜了蒙昧无知,生产力发展也大大延伸人类手脚,“异化”形式的生产手段越是先进,自然神的面纱越是明晰,人与自然之间越是失和。因此,“利用自然”“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反伦理特性是主观欲望膨胀与客观手段延伸双重驱动的结果呈现。“征服自然”的反伦理特性具有以下两个方面表现:
第一,“征服自然”的反伦理特性表现为“人”层面上的与自然“对立性”。一方面,从思想上看,人类秉持着肆虐自然的“反伦理”理念。无论是英国实验科学始祖培根“对万物建立自己的帝国”[3]的口号,还是法国唯理论哲学家笛卡尔“人是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的主张,还是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人为自然立法”的思想[6],还是直观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等等,他们都是站在主客分离的立场上,宣扬“人类中心主义”,这种伦理倾向是“等差式”伦理范式支配下的“极中心”主义伦理思维,因此无不透视出思想上人与自然的“对立性”。另一方面,从行为上看,在绝对主体统治意识支配下人类日益暴露出肆虐自然、制用自然的“不道德”行为,对森林、草场、矿产等资源疯狂掠夺造成了资源短缺;对废气、废水、废渣等废弃物肆意排放造成了环境污染;对穿山甲、大象、犀牛等野生生物大量捕杀造成了生态严重失衡,这些“反生态”、“反伦理”的劣迹处处昭示行为上人与自然的“对立性”。总而言之,人在思想和行为上都透视着近代的“人制天”的反伦理属性。
第二,“征服自然”的反伦理特性表现为“物”层面上的自然“异生性”。一方面,自然生态环境的灾变带来了天工“自然物”异变。无论是“肿瘤水果”,还是“变异蔬菜”,还是“长着外星生物脸的鳗鱼”等等,这些都是由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对立而呈现的“外化”形式,这些自然物“异生”发展与人的反伦理倾向紧密相关联。另一方面,自然生态环境的灾变带来了人工“自然物”异变。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客观上加速人类自身的进化,同时也客观上推动社会机体的演进,然而科技自身的天然对立性也客观上带来了无形的隐患和后续的弊端,比如人工“创造物”异生发展,无论是转基因的植物或食品带来的健康或安全隐患,还是克隆动物或者克隆人带来的社会或伦理问题,都值得人对科技创造物“异生性”进行深刻反思。总而言之,此时无论是天工“自然物”还是人工“创造物”一定程度上都失去了其固有的自然存在状态和基本构造,处处皆昭示着物的异生“非善”、反伦理特性。
三、否定之否定阶段:“尊重自然”的伦理特性
现如今,人类社会正处在后工业文明加速前进的特殊历史阶段,人类享受工业发展带来的现代福利的同时也饱受着工业发展带来的环境恶果,此时人类渴望通过科技、伦理、法律等具体措施来缓解环境系统中不和谐的熵,尤其是要重新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来恢复自然生态系统昔日之平衡,从而使自然、社会以及个人趋向“高度和谐”的发展状态。这种“高度和谐”的发展状态同样是“质”和“量”的统一体,其发展方式是和谐的,但与农业文明阶段相比,其发展水平是高端的。倘若从主体人的角度看,表现为人类真化自然、善化自然、美化自然的伦理倾向;倘若从客体自然角度看,表述为自然用绿色育人、用绿色成人、用绿色护人的伦理特征,在这双重倾向的伦理关怀最终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利互济、和谐共达。与此同时,“尊重自然”的伦理属性还表现“人”层面上的“和生性”与“物”层面上的“仿生性”,简言之即生态人格的成功育成与绿色物品的满目琳琅。总而言之,当代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伦理属性的最终目标是使自然生态系统达到“生生、协变、臻善”[6]的绿色和谐状态。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的发展状态不是没有可能性的理想状态而是具有可能性必然性的现实状态。
首先,从理论基础层面看,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中国化为实现人与自然“高度和谐”发展状态提供了理论基础。比如说,毛泽东“属意自然”的自然观、“增产节约”的经济观、“大地园林化”的美化观、“统筹兼顾”的方法论[7];邓小平“在人与自然关系的主体方面,主张控制人口,主要涉及绿色发展的人口与资源协调发展观;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客体要素方面,倡行植树造林,内含了绿色发展的生态安全观、群众主体观和持续绿化观;在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支撑条件方面,强调科教对经济建设和环境建设的先导作用,突出立法建制对环保事业发展的保障作用,蕴含有绿色发展的科技观、教育观和法制观”[8];江泽民的“可持续发展观”;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塑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观、“促进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生态经济观、“弘扬法治理念与红线思维”的生态安全观、“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民生福祉”的生态民生观[9]等等,这些都是中国一代代共产党人对人类同自然关系的深刻探讨,这对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其次,从社会文化层面考察,人与自然“高度和谐”发展状态日益成为一只有生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从主观意愿看,自然优先、民本至上、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理念日益渗透到社会运行发展的各个方面和环节,人类已经深刻认识到只有秉持“自然优先、民本至上、和谐共生”的伦理理念才是化解“自然报复”预言的最佳途径,才是传播“自然正义”声音的时代号角;从客观手段看,现代生产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致使“从生态中求生产,在生产中存生态”的双向互动发展成为了可能,用科技生产力维护生态,用科技生产力补偿生态,反过来,从自然环境中谋持续,从生态系统中谋发展,这样双向双赢战略都日益被采纳;此外,《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美学》等环保著作的面世为其提供了知识向导;环境科学与绿色技术等日益成熟为其提供了科技支撑,绿色经济应用以及生态文化传播为其提供动力之源。因此,整个社会都吹响了人与自然关系协调发展的号角。
最后,就制度实践层面而言,人与自然“高度和谐”发展状态正在如火如荼地被践行和推广。西方绿党政治、各国环保游行以及抵制污染等运动日益兴起,环保事业日益成为一项伟大的全球公益事业,它不仅得到了越来越多环保人士的支持,而且在实践上证明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此外,人类已经开始探寻“人和天”的绿色和谐发展之路,世界各国相继制定绿色和谐发展路线,比如,英国的《气候变化法》《低碳转换计划》《可再生能源战略》和“绿色产业振兴计划”;日本的“福田蓝图”和《建设低碳社会的行动计划》《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草案;美国的《美国复苏与投资法案》《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等等。当然中国也不例外,绿色发展战略稳步推进,胡锦涛曾在中国科学院与工程院大会的讲话中就首次明确提出了“绿色发展”的概念;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要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三大发展方式;紧接着十三五规划中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由此可见,世界正朝着绿色发展迈进。相信在人类不懈努力和美丽追求之下,怀揣“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伦理美德,人与自然之间“生生、协变、臻善”的绿色和谐一定能够实现。
四、结语
一切发展的过程都包含着发展的起点或原始的同一(正题)、对立面的显现与分化(反题)、“正反”二者的统一(合题)三个辩证环节。同样,人与自然辩证关系史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它势必也应该经历一个从“同一”到“分化”再到新的“同一”的辩证圆圈。换言之,“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进程,发展环境不会一成不变,发展条件不会一成不变,发展理念自然也不会一成不变”[10]。因此,笔者认为随着人类认知的不断深入、人类实践的不断推进和人类价值取向的不断成熟,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将沿着“正—反—合”的伦理进路不断趋向“臻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