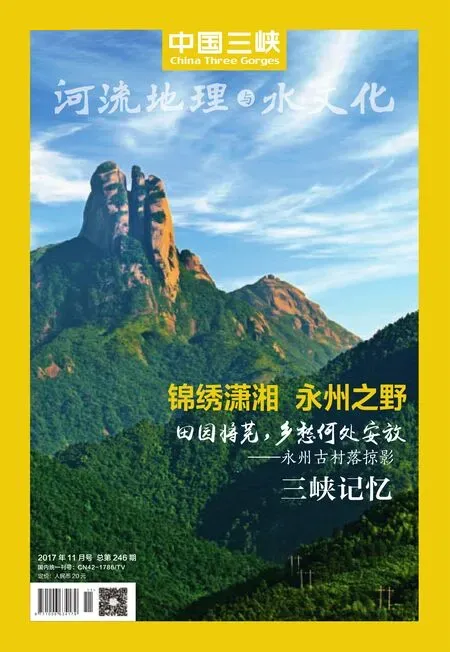我的腾冲:诗人与战争
◎ 文、图 | 杨碧薇 编辑 |田宗伟
我有太多的话语,太悠久的感情……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穆旦《赞美》(1941年12月)
一
我睁开眼睛,飞机正飞越高黎贡山。大片大片的云朵翻卷着、舒展着。多自如又灵逸的云呀,阳光为它们镶上了一条条金边。而云朵之下,高黎贡山的一道道褶痕,像是被大地的手轻轻聚拢起来的伤口。
KY8251次航班,昆明至腾冲。整个飞行过程只有一小时,我刚打了个盹,醒来时,飞机已开始下降。
下飞机后,并没有见到机场摆渡车。我跟着人群往前走了不到二十米,就直接步入航站楼了。看来驼峰机场名气虽大,却十分袖珍。出了机场,十二月的阳光热烈地挥洒着,身穿薄毛呢大衣的我,竟冒出细细的汗——没错,这里是温暖的滇西。看着道路两旁绿意盎然的树木,在裹着草木清香的暖风里,我有点恍若隔世的错觉。腾冲——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你好!
二
这次来腾冲,是因为穆旦。
对现在的人来说,“穆旦”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了,说起他的另一个名字“查良铮”,也不见得会有多少人响应。这个世界上,热爱文学的人本来就不多,懂诗的就更少了。
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做的是穆旦诗歌研究。在论文完稿的一个多月后,碰巧有一个合适的机缘,于是我就想到腾冲看一看。
我想知道,这个远征军曾走过的地方,离我心里的穆旦有多远。
1942年,24岁的穆旦参加了远征军。
那个时候的穆旦,已是一名小有成就的青年诗人。1940年,他从西南联大毕业,留校担任外文系助教,两年后,他便投笔从戎,在杜聿明兼任军长的第5司令部,以中校翻译官的身份,随军进入了缅甸抗日战场。
在那血流成河的岁月,穆旦在热带丛林里接受了生死考验。他不仅要面对致命的传染病与漫长的饥饿,还要承受遍野白骨带给人的震撼与悲愤。后来,他经过野人山,进入印度,1943年结束军旅生涯,从印度乘飞机返回昆明。
三
这一次,在滇东北长大的我来到了滇西南,想去感受一下穆旦的足迹,也想看看此地如今变成了什么样。
这个温暖的城市里,举目是勃勃的绿意,玉石店不计其数,人们坐在街边小摊上,悠然地吃着大救驾。傍晚,行到了一条余晖苍茫华美的公路上,当地的朋友说,沿着这条路一直往西走,就能进入缅甸境内。他还告诉我,现在腾冲的文学事业并不景气,人们都忙着赚钱去了。这里地处边境,有得天独厚的边贸机会,玉石买卖尤为兴盛。近年来,腾冲的旅游也走出了云南省,它的热海、银杏村、顺古镇,吸引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们。
当然,也有一些人是为追溯远征军的历史而来到腾冲的。中国西南边陲的腾冲,是远征军活动的重要据点,也是兵家必争之地。1944年的腾冲之围尤为惨烈,那年,远征军光复滇西,腾冲成为光复第一县。所以,腾冲也吸引了不少军事爱好者。
而像我这样,因为一个诗人而特意来到这里的,恐怕不多罢。
12月底,银杏村的树叶早就落光了,我本也没打算要去。和顺、热海温泉我都去了,至于博物馆与国殇墓园,则是我此次行走的重点,可我并不指望它们给我多大的冲击。我知道,历史是很难还原、更难以抓住的,在历史中沉浮的一个诗人,作为渺小个体,他的一切更是难以留住。但同时,我内心深处也有隐微的期盼,幻想能收获一些意外的感动与震撼。
怀着这样的心情,我去了抗战博物馆。
博物馆不允许拍照,我只好收了相机。一进大厅,一千顶抗战军士的钢盔就闯入眼帘,我是个军事盲,但还是看得出这些钢盔比我想象的重得多。它们挂满了墙壁,首先在视觉上就给我一种冲击,将我带进严肃的沉思氛围中。越往里走,洞天越大。我看到了野人山的土著使用过的生活器具,他们用人的头盖骨盛水喝。在一张慰安妇的照片前,我驻足许久——她已是个老态龙钟的妇人了,紧闭的嘴唇压抑着血与泪的控诉,一刀刀深深的皱纹是抚不平的伤疤。她的眼神紧紧地抓住镜头,仿佛要把镜头抓下,也要把观者的眼珠抓下。我还见到了日军进行活体实验的一些医疗用具:在解剖活人的手术台前,整齐地摆放着一把把寒光凛冽的手术刀,还有容得下三个成年人的大锅,这口锅里煮熟过许多活人。我打了一个又一个寒颤,以前在历史书上看相关的图文介绍,我并没有这种感觉,但当我站在这堆毫无温度的器具面前时,却觉得身后有一股明显的凉气,正悄无声息地踱着脚步,轻轻贴到我的后脚跟处,然后“嗖”地一下蹿起来,贯穿了我的脊柱,直到我的大脑发出轰轰的回响。

远征军名录墙
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我看到了穆旦。这是一个玻璃橱窗,远远地,我就看见一张熟悉的照片,走近一看,果然是穆旦。照片下面有对他的介绍,还附有他的一首诗,《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这首诗我很熟悉,胡康,在缅语里意为“魔鬼居住的地方”。中国远征军第5军撤退时,曾进入这片区域。1943年,远征军与日军在此发生激战。穆旦在诗里说“欢迎你来,把血肉脱尽”“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关于穆旦在胡康河的经历,他的恩师吴宓,曾在日记里如是记录:“铮(即穆旦)述从军的见闻经历之详情,惊心动魄,可泣可歌。不及论述。”而他的好友、翻译家王佐良这么写道:“那是一九四二年的缅甸撤退。他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给死后的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毒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有想到人能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几乎还在空间——之外,胡康河谷的森林的阴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带着一种致命性的痢疾,让蚂蝗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达八日之久。”由于战争太过于残酷,穆旦反而很少向朋友们提起他作战的经历。不过,从他的诗里,我读出一种扭结的痛苦,这种痛苦不断拧紧,拧紧,扼着他的喉咙,每一秒钟,他都可能会死去;每一秒钟,他都要忍受肉体与意志的折磨。
作为一名诗人,关于自己的军旅生涯,穆旦只留下了《森林之魅》等只言片语。我能理解他的沉默,真正沉重的东西往往是难以言述的。我读过日本作家远藤周作的《深河》,书中写到一名曾参加战争的日军战士,他在战场上饥肠辘辘,只好学别人一样,把死去的士兵身上的肉挖来生吃了。因为没有其他选择,他吃掉的是一名亲密战友的尸体。战争结束后,这件事成为他一生的心理包袱。
没想到,在腾冲,我会以这样的方式邂逅穆旦——其实,仍然是通过他的诗,别无它路。诗歌,把不同个体的命运,在不同的时代联系到一起,这种隐秘的追溯与承续,有着展望的无限可能性。一个诗人,在沉浮的大时代,命运常常是无常的。正如谢冕评论穆旦时所说“在偏见的时代,天才总是不幸的”,经历了远征军作战的九死一生后,穆旦回到国内,几年后去美国继续深造、结婚。上世纪50年代初,他谢绝了国外一些知名大学的入职邀请,与夫人周与良一起,历经辗转和坎坷,迫不及待地回到新中国参与建设,但没多久,他就被打倒了。
因为曾担任远征军翻译官,他成为“历史反革命”,长期受到管制、批判、劳改和思想改造。他在上世纪40年代响亮的诗名不再被人提起,诗歌写作也被迫停止。尽管如此,他仍坚持着外国文学的翻译。
1977年春节,59岁的穆旦在病痛的折磨中,默默离开了人世。1979年,穆旦被平反。
1976年——离世前不到一年,穆旦曾写下这样的诗句:“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是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四
参观完博物馆后,我去了旁边的远征军十万将士名录墙,最后,去了国殇墓园。时为午后,安葬着远征军、美国飞虎队、南洋机工等英烈的墓园很安静。我静静走着,只见一些花环在阳光下倍显灿烂,有的墓碑旁摆着祭奠所用的腾越老烧酒。我注意到,许多墓碑是没有名字的。
我强烈地感觉到:我们遗忘历史的速度是多么快。埋葬在这里的人们,难以想象今天日新月异的生活,一切的享乐与他们无缘。但是他们早就知道——正如穆旦诗里所说,“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这足以构成他们抗争与牺牲的理由。
和风吹过来,松影摇摆,一切是轻柔的,恬静的。在没有冬天的腾冲,我抱着双腿坐在一块墓碑旁,想起腾冲当地老人说的一句话:
“对你们而言,战争已经是模糊的概念了,你们摸不到它,听不见、也看不见它。
但是,对我们腾冲人而言,战争意味着——每一片树叶上都有三个弹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