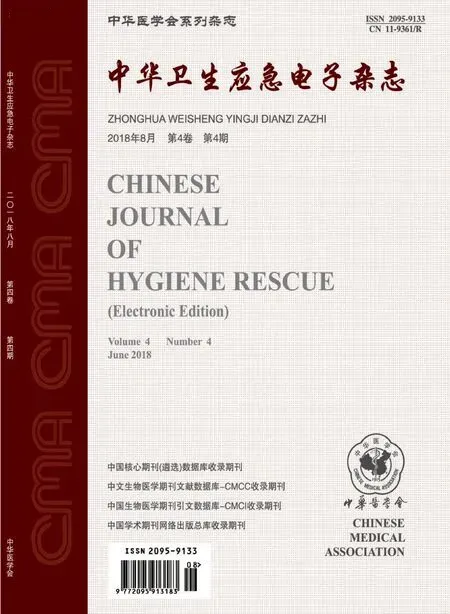白介素-10家族成员IL-10、IL-22与脓毒症的关系
郑燕华 吴莹莹 冯凯 司少艳 张建中,3
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伊斯兰哲学家Ibn Sīnā就识别了脓毒症并将其定义为血液和组织的腐败并伴有发热[1]。但对于脓毒症的定义始终混乱,直至1991年人们才达成共识,认为脓毒症是微生物感染引起的发热(或体温过低)、心动过速、呼吸急促和血液白细胞改变,即全身性炎症反应(SIRS)[2]。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和医疗实践的增加,脓毒症已不再是一种直接危及生命的疾病,却是一种慢性危重病,通常与长时间的炎症、免疫抑制、器官损伤和无脂肪组织消耗有关[3],存活下来的脓毒症患者在出院后仍有持续的死亡风险以及长期的认知和功能缺陷。尽管随着医学的进步,脓毒症的住院死亡率已有明显的下降,但使用免疫调节剂的疗效仍然令人失望。同样,没有一个生物标志物可以明确诊断脓毒症或预测其临床结局。因此,改善脓毒症结局依旧任重道远。
脓毒症的病理生理学特征是在感染过程中机体的免疫调节功能出现异常,产生并释放了大量的炎症介质并因此而引发全身性炎症反应[4]。脓毒症涉及到了多种细胞类型、炎症介质和凝血因子,最近的研究更是集中在了固有免疫系统和T细胞在脓毒症中的作用。细胞因子是有效的炎症介质,几乎参与了免疫和炎症的各个方面。在感染过程中其血清水平明显增加,导致了其他炎症效应分子的水平也发生变化。大量的研究表明,白介素-10(interleukin-10, IL-10)在脓毒症进程中起重要的负调节作用[5-9]。另外,IL-10家族的其他成员也在脓毒症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如IL-22[10-13]等。因此,笔者着重介绍脓毒症的免疫学特征以及IL-10及其家族成员IL-22在脓毒症中的研究进展,探讨IL-10家族成员IL-10、IL-22与脓毒症的关系。
一、脓毒症的免疫学特征
1.细胞因子风暴
脓毒症从根本上说是由固有免疫系统激活介导的炎症性疾病。目前,在脓毒症中发现有固有免疫反应激活的两个重要特征:(1)脓毒症通常是通过由负责免疫监测的补体及特异性细胞表面受体同时识别多个微生物产物和内源性危险信号来启动的[14];(2)这些多信号通路的激活最终导致炎症、适应性免疫和细胞代谢中涉及的几种常见基因的表达,包括与炎症相关的细胞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 TNF)、IL-1、IL-12、IL-18及I型干扰素(interferon,IFN)等以及由这些细胞因子启动的其他炎性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包括IL-6、IL-8、IFNγ、CC趋化因子配体2(CCL2)、CCL3和CXC趋化因子配体10(CXCL10)[3],这些炎性介质的产生和释放可引起脓毒症初期的系统性炎症反应特征[15]。在脓毒症发展的早期发生了过度炎症状态,通常被称为细胞因子风暴[16]。“细胞因子风暴”一词生动地反映了免疫系统的紊乱和炎症反应的失控。与细胞因子风暴相关的炎症在局部部位开始,并通过血液循环扩散到全身。
2.淋巴细胞凋亡与免疫抑制
免疫抑制在脓毒症进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脓毒症患者血液循环中淋巴细胞减少、出现未成熟中性粒细胞(多形核)、单核细胞丧失产生炎性细胞因子和抗原呈递的能力、以及中性粒细胞样髓系来源的抑制细胞(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MDSC)数量增多等[3]。对脓毒症患者的尸检研究表明,细胞凋亡是固有免疫和适应性免疫抑制的潜在驱动因素[17]。淋巴细胞的凋亡性减少是免疫抑制的直接因素,导致了重度脓毒症患者中淋巴细胞减少[18]。淋巴细胞凋亡程度与脓毒症的严重程度有关,而持续的淋巴细胞减少可预测脓毒症死亡率[19]。凋亡细胞也通过与其他白细胞的相互作用来抑制免疫功能,例如,凋亡淋巴细胞的吞噬导致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释放抗炎细胞因子如IL-10和TGFβ。该过程还在基因转录水平上抑制了促炎细胞因子的产生,从而导致了脓毒症中固有免疫反应无力[19]。从药理上或基因上干预脓毒症诱导的细胞凋亡可明显改善脓毒症动物模型的存活率,再次证明了脓毒症诱导的细胞凋亡的功能性后果。
循环中未成熟的中性粒细胞和中性粒细胞样MDSC分泌多种抗炎细胞因子,包括IL-10和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进一步抑制免疫功能[20]。在循环中未成熟的髓细胞具有抗菌活性缺乏、粘附分子的表达降低以及捕获病原体的胞外诱捕器减少等特征[21-22]。此外,脓毒症导致抗原呈递细胞(APCs),包括树突状细胞和巨噬细胞,失去表达活化的HLA-DR的能力。循环中的抗原递呈细胞上HLA-DR的丢失与反应性降低相关,且单核细胞无法恢复HLA-DR水平,预示着脓毒症的不良结局[23]。在脓毒症的进程中,反常的免疫抑制和感染并发症相混杂,伴随着血培养阳性率的增加以及向机会性感染的转移[24]。与非脓毒症的对照组相比,脓毒症患者的潜伏病毒再激活率显著升高,42%的脓毒症患者的血液中可检测到病毒DNA(非脓毒症的危重症患者仅有5%可检测到病毒DNA)[25]。尸检结果发现,80%的脓毒症病例中存在持续感染灶和微脓肿[26],证明脓毒症患者存在免疫抑制状态。而脓毒症患者淋巴细胞产生促炎因子和Th1细胞因子的能力仅是非脓毒症患者的10%[27],进一步证实了脓毒症进程中免疫抑制的存在。因此,针对淋巴细胞凋亡和脓毒症引起的免疫抑制的干预研究结果非常令人期待。
在细胞因子风暴发生之后,循环中IL-10的大量产生是免疫抑制的一个标志,由此可见,IL-10在脓毒症的进程中起到关键性作用。近年来,人们逐步开始关注IL-10家族成员在脓毒症发生发展中的作用,也取得了一些研究进展。
二、IL-10家族
1.IL-10家族成员
近年来,与IL-10相关的细胞因子陆续被发现,并将IL-10家族成员扩展为9个,包括:IL-10、IL-19、IL-20、IL-22、IL-24、IL-26、IL-28A、IL-28B和IL-29,其中IL-28A、IL-28B和IL-29又称IFNλ2、IFNλ3和IFNλ1,统称III型干扰素[28-30]。IL-10家族成员的基因是联系在一起的,其分子结构具有高度保守性,并因此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共享受体。IL-10、IL-24和IL-26由活化的单核细胞和T细胞产生,IL-19和IL-20由活化的单核细胞产生,而IL-22主要由活化的T细胞产生[31]。IL-10家族成员与它们的特异性受体分子的相互作用引发了一系列广泛而多样的信号,并介导了不同的生命活动,包括免疫抑制,增强抗菌和抗病毒免疫,抗肿瘤活性,并促进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自我耐受性,并影响许多免疫机制[29, 32]。除IL-10外,IL-10家族其他成员都发现得比较晚,故目前人们仅关注IL-10和IL-22在脓毒症中的作用,而其他家族成员与脓毒症的关系尚未见报道。
2.Ⅱ型细胞因子受体
IL-10家族成员的受体均为异源二聚体结构,由不同的II型细胞因子受体组成[30],包括IL-10R2(CRF2-4)、IL-22R1(CRF2-9)、IL-22BP(CRF2-10)、IL-20R1(CRF2-8)和IL-20R2(CRF2-11)[33]。然而,家族成员并非直接与受体复合物发生相互作用而引发下游通路,而是先与其特异性受体亚基相结合之后发生构象改变,然后与另一个受体亚基结合,激活下游信号通路。IL-10是通过IL-10R1和IL-10R2形成的异源二聚体信号发挥有效的抗炎作用。IL-10R1主要表达于造血细胞,包括T细胞、B细胞、NK细胞、单核细胞和树突状细胞,而IL-10R2则是广泛表达的。与IL-10不同,家族其他成员的特异性受体亚基(IL-20R1、IL-20R2和IL-22R1)在造血细胞中基本不表达,这些受体主要表达于各种组织的上皮细胞和间质细胞成纤维细胞上[34]。由此可见,新的IL-10家族成员在造血和非造血细胞之间的通信和相互作用中起到桥梁作用,而这一作用与IL-10的免疫调节功能截然不同。
3.IL-10与脓毒症
IL-10是一种重要的免疫调节性细胞因子,通过抑制由各种免疫细胞引起的促炎症反应,限制了在感染期间引起的组织损伤和免疫病理学改变[35]。有研究表明,IL-10 -1082G/G基因型与烧伤患者血清IL-10水平升高有关,且与发生脓毒症相关[5]。Berg等[36]在急性内毒素休克模型中发现IL-10基因缺失小鼠的LPS致死剂量比野生型小鼠低20倍,提示内源性IL-10决定了小鼠的LPS耐受量。由于IL-10在脓毒症的免疫抑制中的重要作用,学者们尝试使用IL-10重组蛋白来治疗脓毒症。通过小鼠盲肠结扎和穿刺(CLP)模型研究IL-10对CLP小鼠存活率的影响,发现在脓毒症诱导6 h后给予1 μg或更多的重组小鼠IL-10治疗可显著降低脓毒症小鼠的死亡率,并可抑制脓毒症后血液循环中TNFα的升高。然而,在建模的同时或建模前6 h给予相同剂量的IL-10治疗却对CLP小鼠的存活率没有明显影响[37-38]。但是,在以葡萄球菌肠毒素B(staphylococcal enterotoxin B,SEB)诱导的致死性休克小鼠模型中,IL-10在诱导前或与SEB同时给药均能以剂量依赖的方式阻止小鼠的死亡,但在诱导后给药效果不明显。由此可见,IL-10介导的保护作用是明显的,可作为治疗脓毒症和脓毒症相关的多器官衰竭的潜在候选物,但在给药时机上仍存在争议。
4.白介素-22(IL-22)与脓毒症
IL-22是除IL-10之外研究最多的IL-10家族细胞因子,主要调节上皮细胞的稳态,并诱导产生抗菌素和β-防御素,在固有免疫中起重要作用。IL-22由淋巴细胞产生,通过IL-22R1/IL-10R2异源二聚体激活下游信号通路。IL-22R1是IL-22的特异性受体亚基,主要表达于肝、肺、皮肤、胸腺、胰腺、肾脏、胃肠道、滑膜组织、心脏、脂肪组织、乳房和眼睛等器官[39-48]的基质细胞和上皮细胞,但在造血细胞上不表达。IL-22的特异性受体除了膜受体IL-22R1外,还有一个游离型受体IL-22BP(IL-22结合蛋白),该蛋白是IL-22/IL-22R1轴的拮抗剂,对IL-22/IL-22R1轴的功能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12]。有广泛的证据表明,IL-22在实验模型中介导上皮组织的保护和再生,包括肝炎,胰腺炎,结肠炎,胸腺损伤等模型[39, 43-44, 49]。然而,IL-22并不是在所有的模型中都是起保护性作用的。IL-22也可以诱导促炎因子的表达,包括IL-1、IL-6、IL-8、IL-11、G-CSF、GM-CSF和LPS结合蛋白[43, 50-51]。由此可见,IL-22可以是组织保护的也可能是促炎的,这两种作用并不互相排斥。
近几年,人们开始关注IL-22在脓毒症中的作用,并证明了IL-22在脓毒症进程中具有负面影响的。Weber等[12]发现,CLP腹膜炎模型小鼠的肾脏和脾脏中IL-22水平是升高的,而CLP建模后抑制IL-22的表达则能增强细菌清除率,促进吞噬细胞募集,减轻器官功能障碍,并降低IL-10的表达。同样地,CLP大鼠模型中也发现血清IL-22水平升高[52]。单中心研究对16例腹部术后脓毒症患者的研究表明,与健康志愿者和非脓毒症手术对照组相比,脓毒症患者的血清IL-22水平也显著升高,且脓毒症患者的血清IL-10也显著增加[10],表明IL-22和IL-10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它调节细菌负担和宿主免疫/屏障稳态之间的临界平衡。
三、总结与展望
脓毒症与宿主免疫功能的异常有关。细胞因子风暴和免疫抑制是脓毒症的发展进程中的两大免疫学特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53]。IL-10是脓毒症免疫抑制的一个重要标志,对于检测脓毒症患者的免疫状态具有重要的作用,而IL-22在脓毒症患者血清中的水平升高,并与IL-10水平具有相关性,也证明了IL-10与IL-22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然而,IL-22在脓毒症中的作用机制目前尚不清楚,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IL-10家族的其他成员在脓毒症中的作用目前尚未见报道,可能与其发现较晚有关。目前,也有学者尝试着通过干预细胞因子风暴和免疫抑制来治疗脓毒症,然而,由于脓毒症的复杂性,对于脓毒症的治疗方案和效果仍待进一步的发展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