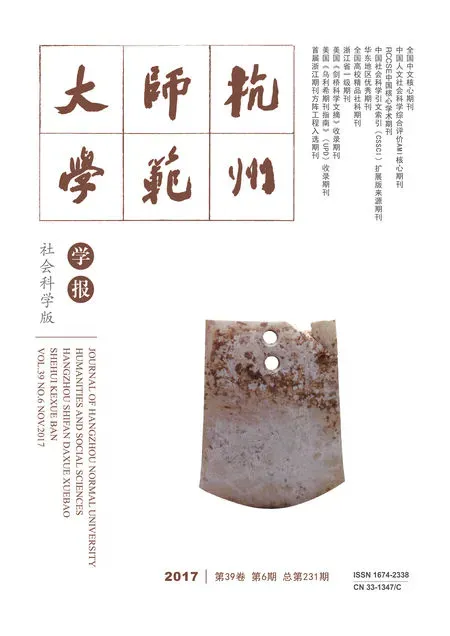略论中国“古典禅”与《维摩经》
龚 隽
(中山大学 哲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主题研讨中国哲学的真实建立之九
略论中国“古典禅”与《维摩经》
龚 隽
(中山大学 哲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以《维摩经》对中国八世纪中期之后古典禅思想的影响为中心,可分别见出禅宗思想史上初期禅到古典禅的典范转移,及其对经典应用方式的变化;特别是从古典禅的“语录”与灯史对《维摩经》的使用上具体阐明这一时期禅宗与《维摩经》之间的复杂关系。
古典禅;语录;灯史;《维摩经》;维摩
一、从初期禅到古典禅
历来禅宗被视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一流,这一点在中国八世纪中叶之后古典禅时期似乎更具有代表性。不过,有关禅宗思想史的研究表明,中国禅宗从初期禅(从五世纪末到八世纪中期)到八世纪中后期兴起的所谓“古典禅”的法流,都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使用或诠释着经典。①“古典禅”(classical chan)是借用西方禅宗研究的说法,约指八世纪下半叶起,即从中唐到宋初这段时期的禅宗阶段。与初期禅比较而言,可以说是禅宗的中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禅风与初期禅有了明显的变化,特别是马祖道一及五家分宗各派所开创的禅风,开创了以“语录”与“机缘问答”为主的说法形式,这一初期禅相对于经教的那种方便通经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参见John R.McRae,Seeing through Zen-Encounter,Transformation,and Genealogy in Chinese Chan Buddhism,Berkel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75-77。日本禅宗学人忽滑谷快天所谓“禅机时代”,也与古典禅时期相类似而略有提前,通指神秀、慧能之后到宋代之前的禅宗发展时期。参见其著《中国禅学思想史》,朱谦之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5-11页。本文主要以“古典禅”的划分来加以阐明。禅师虽然很少像义学僧那样对经教进行系统的论述与注疏,但无论是其宗风之“遵教慢教,随相毁相”二流,都程度不同地以“六经注我”的方式广泛应用和引述经论。宗密发现,初期禅宗的传承都是显、密并传:所谓密者即是“默传心印”,而显者即是“藉教悟宗”,借经教来勘证心法。宗密说:“其显传者,学徒易辨,但以言说除疑。况既形言,足可引经论等为证。”[1](PP.402中,405上)永明延寿也提出类似的洞见,指出禅门大都借经明宗、分别以“显了”与“秘密”两说来阐明宗义,所谓“各据经宗,立其异号”。[2](P.427上)我们应该注意的现象是,从初期禅到古典禅的流变,其应用经典的宗趣与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维摩经》对中国中古佛教义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六朝到隋唐的佛教义学中,有关《维摩经》的注疏可谓法流众多,盛极一时。唐以后中古义学中的维摩经学已经走向衰微,并逐渐让位于禅宗了。中国“初期禅”大都以“方便通经”的方式会通不同的经典,为禅法寻找教义方面的依据。以往学界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初期禅的发展经历了由《楞伽》到《金刚经》的转化,以致胡适说《金刚经》革了《楞伽经》的命。[3](P.129)其实这只是有关初期禅宗思想史的一个过于简单的叙事。实际上,《维摩经》对中古禅宗史的思想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维摩经》“以不思议为宗”,恰恰被看作是禅门“秘密之说”的经教依据。[2](P.427上)禅师们以各种形式使用《维摩经》的观念,甚至在禅师的偈颂中也出现了以维摩为主题的“五更转”。*“维摩五更传”,详见田中良昭、篠原寿雄编《敦煌仏典と禅》,东京:大东出版社,昭和55年,第268-269页。而在古典禅门下的灯史书写中,维摩在禅门的系谱中已经被塑造为直续七佛的核心人物了。
禅门对经教的会通,向来与经论师不同且显示了另类的法流。禅师重于心法的印证,其与经教的融合也是在心法优先的前提下才得以展开的,这就是所谓的“方便通经”。于是,他们对经教的使用,从形式到内容方面都不必因循传统经论师所定的规矩。禅师们重视的是“观心释经”,强调“以心宗之衡以准平之”的原则。[4](P.264中)可以说,他们倾向于以一种“行事的”(performative)原则,实用性地运用经典,以此完成心法所设定的目标,而非一味阐明经中原义。[5](P.149)对经教的引证,他们大多也是断章取义,绝不用文字束缚心法的体会。
对《维摩经》的融通,中古禅宗也显示了自己不同的作风。初期禅对《维摩经》的使用,重在以经教阐明宗义。从达摩到东山法门,以至北宗及曹溪门下的作风,都广泛且频繁地用《维摩经》来讲解各宗禅法的意趣。他们并没有系统地注解经义,而是摘取经中若干语句进行禅解与贯通。禅师之会通经教与经论师不同,他们甚至批评说经论师的解经只是虚妄的分别意识所为,而没有结合心法。如保唐禅系的无住就认为义学经论师的解经是“以流注生灭心解经论,大错”。他引《维摩经》“佛国品中”的“以无心意无受行,而悉摧伏诸外道”的方式,以此说明解经应该是“达诸法相无挂碍,稽首如空无所依”。[6](P.298)此即是一种离言悟教的禅门经解。
八世纪中期以后,古典禅时期的禅师们对《维摩经》的阐释益发偏向“行事”化的风格。他们主要不是以“方便通经”,而是更多地以“语录”和“机缘问答”等形式自由地随意发挥经义,在思想倾向上也表现了对经教的轻忽。在他们的“机缘问答”中,古典禅的禅师们习惯于对经论师进行勘破。我们从早期禅宗灯史的记载中可以找到很多的例证。《祖堂集》里的赵州禅师即是如此勘破《维摩经》的经论师的:“师问座主:所业什摩?对云:讲《维摩经》。师云:维摩还有祖父也无?对云:有。师云:阿那是维摩祖父?对云:则某甲便是。师云:既是祖父,为什么却与儿孙传语?座主(无对)。”[7](卷15,P.392)《祖堂集》又载马祖门下的归宗智常“乃深穷《肇论》,洞达《维摩》”。他对经论师也予以了同样的破斥:“时有江州东林寺长讲《维摩经》并《肇论》。座主神建问:如何是触目菩提?师乃跷起一脚示他。座主云:莫无礼。师云:不无礼。三个现在,座主一任拣取。座主不会。”[7](卷18,P.342) 《景德传灯录》里也有不少的例子。如《景德录》卷15载筠州洞山良价禅师对《维摩》经论师的呵毁即是一例:“师问讲《维摩经》僧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识识,唤作什么语?对曰:赞法身语。师曰:法身是赞,何用更赞。师有时垂语曰:直道本来无一物,犹未消得他钵袋子。”[8](卷15,P.321中)《景德录》卷17又编撰了洪州云居道膺禅师是如何点醒一位《维摩经》学僧的故事:“有一僧在房内念经。师隔窗问:阇梨念者是什么经?对曰:《维摩经》。师曰:不问《维摩经》,念者是什么经,其僧从此得入。”[8](卷17,P.321中)这些例证都旨在表明,由初期禅到古典禅,虽然它们都保留了别出于教门而会通《维摩》的风气,其轻教的倾向却是越来越分明了。
二、以“语录”与“机缘问答”为例
中唐以后,中国禅进入了所谓“禅机时代”(八世纪后期到九世纪后期)。这一时期的禅风大变,可以说“古典禅”的形成及其禅机时代在思想方面形成了以“语录”而不是以经典为中心的方式。古典禅不再像初期禅的时代那样惯于“方便通经”、依据不同的经教思想来阐明禅法,而是自抒心法、以“语录”为中心,逐渐削弱了书写为主的经典传统。古典禅的禅师们将初期禅所会通的经典尊之为一种历史的价值,而不再作为宗门或心法传承的必要前提了。柳田圣山在《中国禅佛教的语录》一文中认为,随着马祖禅创造了“语录”的新形式,体现传统书写性的经典地位受到动摇,口语化的语录注重个体化的事实和事件。他们对经教系统完全没有兴趣;“语录”对通经的替代表明,经教不再是“宗教立场的逻辑基础”了。*参考柳田圣山《禅宗語錄の形成》,John R.Mcrae译,the Recorded Sayings texts of Chinesech’an Buddhism,出自:Early Ch’an in China and Tibet,Ed.Whalen Lai and Lewis R.Lancaster,Berkeley:Asian Humanities Press,1983,P.185-205。
于是,传统经典的权威性便让位于一种更生活化和在实践生活场域中具有对话风格的“语录”或师徒间的禅机问答了。这种典范的转移也影响了古典禅师对《维摩经》的使用方式。“古典禅”对《维摩经》的使用与他们对待其他经典的态度一样,具有更浓厚的行事与活动的性质,而远不像初期禅那样需要仰赖经典来融通宗义。从他们的语录与机缘问答的一些片段中,我们可以察识出他们对《维摩》通经以致用的门风。“古典禅”的资料大都经历了后代不断制作的过程,相当多的内容直到宋代才得以成型,因而我们很难完整了解唐代“古典禅”的思想原貌,只能从早期灯史,如《祖堂集》(952)到《景德传灯录》(1004)及宋代集撰成的各类“语录”中进行大略的阐析。
八世纪后中国禅的法流中仍然流传着对《维摩经》的参究,但从内容到形式方面都出现了一些鲜明的变化。初期禅广泛地应用《维摩》,而在心体的阐明上还是以四卷《楞伽经》的“诸佛心第一”为主流。从东山法门到北宗的一流,都坚持了楞伽宗的传统,如神秀依然“持奉《楞伽》近为心要”。[9]南宗对以《楞伽》传心印的法流颇多轻视,慧能与荷泽系都倾向于般若,特别是以金刚般若来阐明心要。“古典禅”对心法的阐明,明确体现了《维摩经》的影响。黄檗论如何调伏其心,所引经证即是《维摩》。《宛陵录》中载:“一切众生轮回生死者,意缘走作心于六道不停,致使受种种苦。《净名》云:难化之人心如猿猴,故以若干种法制御其心,然后调伏。所以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故知一切诸法皆由心造,乃至人天地狱六道修罗,尽由心造。”又说“如今但识自心,息却思惟,妄想尘劳自然不生。《净名》云:唯置一床寝疾而卧,心不起也。如今卧疾,攀缘都息,妄想歇灭,即是菩提”。[10](P.386中)马祖门下的大珠慧海延传初期禅的《楞伽》传统,同时也鲜明地将之融会于《维摩》之中。《顿悟入道要门论》卷上讲到心法时,即把《维摩》与《楞伽》并举:“云何知心为根本?答:《楞伽经》云:心生即种种法生,心灭即种种法灭。《维摩经》云: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即佛土净。”[11](P.18上)
以马祖道一为代表的“古典禅”倾向于以《维摩》的空性观破除对法的执持,并将之会通于其禅法所主张的无修无证的一流中。如他对《维摩经》“菩萨行品”之“不尽有为,不住无为”的说法,即是从空性的意义上加以理解的。他认为:“有为是无为家用,无为是有为家依。不住于依,故云如空无所依。”[12](P.94)另外,马祖主张“夫求法者,应无所求”,[12](P.2)此即出于《维摩经》“不思议品”:“若求法者,于一切法,应无所求。”[13](P.546上)他在解释“无一法可得”时,也援引了《维摩经》“弟子品”之中“不坏于身,而随一相”的说法。[12](P.50)此外,道一在解释其著名的平常心是道的观念时,也引用《维摩经》“问疾品”中之“非凡夫行,非圣贤行,是菩萨行”来讲平常心的“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12](P.93)从马祖一系所留传的“语录”看,他们对经教的引证越来越少,且对引经教的风格也进行了更多的自由发挥。
中古禅门中存在着“依教”与“离言”二流,可以说古典禅比初期禅更倾向于不立言说这一面,因而其对《维摩》的应用也特别强化了经中静默主义的观念。《维摩经》“入不二法门品”中文殊与维摩诘关于语默议题,成为古典禅门下参究玄机的一个重要公案。禅门灯录与语录所载此类公案甚多,略举几例为证。仰山慧寂禅师与门下共参此义:“师共一僧语,傍有僧曰:语底是文殊,默底是维摩。师曰:不语不默底莫是汝否?僧默之。师曰:何不现神通?僧曰:不辞现神通,只恐和尚收入教。”[8](卷11,P.282上)福州雪峯义存禅师的门风也类于此,《景德录》中载:“问文殊与维摩对谭何事?师曰:义堕也。僧问:寂然无依时如何?师曰:犹是病。”[8](卷16,P.327上)曹山的宗风是这样的:“僧问维摩默然文殊赞善,未审还称得维摩意么?师曰:尔还缚得虚空么?僧云:恁么则不称维摩意也。师曰:他又争肯。僧云:毕竟有何所归?师曰:若有所归即同彼二公也。僧云:和尚又作么生?师曰:待尔患维摩病始得。”[14](P.531中)
《维摩经》的言默观念经过古典禅门的提倡和发挥,深刻影响了晚唐宋代禅门的思想发展。晚唐之后,禅门仍然保留了对这一公案的参究风气。晚唐宋初禅宗门下参究《维摩经》,大多也是就其不二法门中的言默关系进行论辩的。如玄沙师备说:“十地魂惊,语路处绝,心行处灭,直得释迦掩室于摩竭,净名杜口于毗耶。须菩提唱无说而显道,释梵绝听而雨花。”[15](P.29下)法眼文益也指出,从佛陀、维摩直传到达摩的禅宗法流即是不言一语,默然心传的:“廓不可得其际,湛兮或存。妙不可得其名,灵然自照。释迦以此而掩室,净名以此而杜辞。少林九年,垂一则语,诸人还体悉得么。”[16](P.385下)《古尊宿语录》也保留了许多禅师对这一公案的参究案例,如《古尊宿语录》卷24 潭州神鼎山第一代湮禅师语录云:“释迦掩室于摩竭,净名杜口于毗耶。三乘教外,一句别传。”[17](P.158中)该书卷25筠州大愚芝和尚语录中有“问话且住,净名杜口,犹涉繁词。达磨西来,平欺汉地,放一线道去,也放个葛藤处”,[17](P.163中)又卷26首山省念禅师语录云:“释迦掩室于摩竭,净名杜口于毗耶,三乘教外一句别传,敢问大众作么生是别传底?试对。”[17](P.228下)卷35大随开山神照禅师语录载:“不闻道,释迦掩室。净名杜口,须菩提无说而说,释梵绝听而听,此事大难。”[17](P.251上)又卷38洞山第二代初禅师语录:“问:释迦掩室于摩竭,净名杜口于毗耶,犹是中下之机。向上一路,请师说破。师云:玄玄无倚靠,逈逈勿人知。”[17](P.795上)
另外,东山法门的分流,对见闻觉知与悟道的关系有完全不同的阐释。如保唐、北宗的禅法对《维摩》的理解是离见闻觉知而入道,南宗的意见则认为即见闻觉知而当下无染,鲜明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法流。古典禅不立言说,对此问题的解决却另有发明。他们在言默关系上不立一义,而是在可否之间,以非一非异、两可两不可的公案形式逼使学人在陷于两难悖论的疑情中去各自参究,最终得以道断言语与行思。这也是古典禅鲜明的教学方法之一。道一的门风对《维摩经》的阐释即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宗镜录》卷第一“标宗章”载,大义禅师不断地以《维摩经》见闻觉知的说法勘验学人:“鹅湖大义禅师因诏入内,遂问京城诸大师:大德,汝等以何为道?或有对云:知见为道。师云:《维摩经》云法离见闻觉知,云何以知见为道?又有对云:无分别为道。师云:经云善能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云何以无分别为道?”*《宗镜录》卷第一“标宗章”(《大正藏》第48册,第418页上)。此处所引经文出自《维摩经》“佛国品”中偈云:“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大正藏》第14册,第537页中。《景德录》也记载了大珠慧海引《维摩》而破相的说法,如说“无一法可取,无一法可舍,不见一法生灭相,不见一法去来相。遍十方界无一微尘许,不是自家财宝。但自子细观察自心,一体三宝常自现前,无可疑虑。莫寻思莫求觅,心性本来清净。……又《净名经》云:观声实相,观佛亦然。若不随声色动念,不逐相貌生解,自然无事去”。[8](卷38,P.440下)古典禅对《维摩经》的使用,无论在思想倾向还是使用风格等方面,都与初期禅形成了明显的分离,从而显示了新一类典范的逐步形成。
三、“古典禅”灯史中的维摩
中古禅学各宗的发展,以“藉教悟宗”和“方便通经”的方式,程度不同地融会《维摩经》的思想来阐明心法。从初期禅到古典禅的流变中,禅门各家对《维摩经》的应用可谓各出手眼,变化多端。随着禅宗的形成,不同类型的宗门灯史陆续出现,禅宗内部试图透过历史编撰与叙事的方式来“重构”其各宗门的思想形态和传承谱系。经过三个多世纪的酝酿成熟,禅宗灯史不同形式地会通于《维摩经》,并别有深义地参与塑造了新的维摩形象。
八世纪后中国禅门内部的宗史编撰,从北宗灯史如《传法宝纪》(713)、《楞伽师资记》(712-716),到反映四川一系的《历代法宝记》(775)以及代表南宗门下的《宝林传》(801)、《祖堂集》(952)等,他们都从各自立场出发建构了法流众多的禅门史述。直到《景德传灯录》(1004)问世,意味着由帝国钦定的第一部禅门灯史登场,从而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特别是《景德录》“采诸方之语录,次序其源派,错综其辞句”,[8](序,P.196下)试图系统地建构禅宗历史的系谱,在吸收唐五代以来禅门灯史成果的基础上,别有创制地确立了宋以后禅宗灯史的新典范。
初期禅门的灯史偏重融会经教,特别是早期北宗灯史大量地引述不同教典进行论述。我们仅以《维摩经》为例,从《楞伽师资记》的书写来看,《维摩经》对这一初期禅门史书就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师资记》“自序”明确援引《维摩经》以明“托悟在中”;其论及“独守净心”的意味时,也以《维摩经》之心净国土净来阐发其义:“善法尚遣舍之,生死故应远离。《维摩经》云: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也。身虽为之本,识见还有浅深。”[18](PP.62-67)古典禅的风格深刻地影响了晚唐到宋代古典禅门下的史书编撰。这一时期,由南宗不同宗系所编禅史也体现了以“语录”为中心的特点,致使传统经教大量减少、甚至有退隐的迹象。“语录”以人为中心,于是人物逐渐取代了经典而成为灯史的主角。以《维摩经》来说,与初期灯史相比,后期灯录所引经中文句少了很多,而活生生的人物——维摩诘的故事似乎取代了《维摩经》并成为古典禅时代灯史的重要议题。由思想到人物的变化,是古典禅思想史研究中一个需要重新讨论的议题。
有关维摩诘的形象,有一个可圈可点的问题是,在《景德录》问世后,禅宗史上的维摩诘出现了一个深刻却不为人注意的历史叙事,即《景德录》创造性地建构了一个由佛陀开制、维摩接续的新的禅宗历史图式。《景德录》卷一“七佛天竺祖师”章,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这样一种说法:“古佛应世,绵历无穷,不可以周知而悉数也。故近谭贤劫有千如来,暨于释迦,但纪七佛。案《长阿含经》云:七佛精进力,放光灭暗冥。各各坐诸树,于中成正觉。又曼殊室利为七佛祖师,金华善慧大士,登松山顶行道,感七佛引前,维摩接后。今之撰述,断自七佛而下。”*《景德传灯录》卷1,《大正藏》第51册,第204页下。又,《景德录》卷27中有善慧传,其中就记录了这个传说:“善慧大士者,婺州义乌县人也,齐建武四年丁丑五月八日降于双林乡傅宣慈家本名翕。……陈天嘉二年大士于松山顶遶连理树行道,感七佛相随。释迦引前,维摩接后。唯释尊数顾共语,为我补处也。”《大正藏》第51册,第430页上、下。
我们不能以简单的附会旧传来看待这一故事的创制。《景德录》号称是一部“校岁历以愆殊,约史籍而差谬,咸用删去,以资传信”的严肃的宗史编著,[8](序,P.196下)这个以善慧傅大师的定境为证,看似有点虚构的禅宗历史故事是如何逐步形成的,我们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勘证。不过,这一建构的历史图式表明,在北宋时代的禅宗史撰中,维摩及《维摩经》的地位已经非同寻常地超越了初期禅宗传统所建立的《楞伽》与《金刚经》传统,从而具有标示性的意义。维摩形象在禅门中的抬升,从另一侧面说明古典禅的思想与行事风格也发生了典范性的变化。经中的维摩诘在思想上具有不依传统,以破显立的作风,并强调了佛法超越言说而入于不思议的法流。为此僧肇说,《维摩经》“语宗极则以不二为门,凡此众说皆不思议之本也”,[19](P.327上)这些恰恰都是古典禅师们所心仪的理想宗师的形象。《景德录》只是创立了一个基本的法式,后续的灯录仍然有所延续。
我们从宋代灯史的形成史中可以探究出一点相关线索。南宋的灯录《联灯会要》(1183)继承发展了《景德录》的基本图式,在“七佛”与“西天祖师”之间增加了“竺乾诸大贤圣”章,专录印度佛教史上的诸位著名大士,如文殊、天亲、善财等,维摩诘也成了其中重要的一位。《会要》“诸大贤圣”章,从《维摩经》中所录有关维摩的故事占有相当大的分量,其中包括维摩与文殊论“入不二法门”,维摩与须菩提的对话以及舍利弗与天女的对话等。这些都是《维摩经》中的著名故事。[20](PP.16中-17上)集宋代灯录之大成的《五灯会元》(1252),不仅有意识地全盘承接了《景德录》所确立的“七佛引前,维摩接后”这一传说,*《五灯会元》卷1中叙述“七佛”置前,完全抄录《景德录》中有关七佛启前,维摩接后的一段文字。见《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80册,第28页上。且重新整合编排了北宋以来的灯录传统,特别是将《会要》“诸大贤圣”章的内容进行了整删、进而形成了“西天东土应化圣贤”录一章(卷二)。该章把维摩单列于天亲菩萨章;对《会要》中有关《维摩经》的选录部分,它只保留了维摩与文殊说不二法门这一节。《五灯会元》卷二载:“维摩会上,三十二菩萨各说不二法门。文殊曰:我于一切法,无言无说,无示无识,离诸问答,是为菩萨入不二法门。于是文殊又问维摩:仁者当说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维摩默然。文殊赞曰:乃至无有语言文字,是菩萨真入不二法门。”[21](P.65中)有趣的是,宋代灯录有关维摩形象的塑造更加趋向于静默主义的法流,《五灯会元》有意识地强调了《维摩经》“入不二法门”离言悟禅的一面,这恰恰体现了“古典禅”以来中国禅宗思想的流变。
[1] 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高楠顺次郎等:《大正藏》第48册,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大正年间(1922-1934年)。
[2] 延寿:《宗镜录》卷2,高楠顺次郎等:《大正藏》第48册,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大正年间(1922-1934年)。
[3] 胡适:《楞伽宗考》,《胡适学术文集-中国佛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4] 志磐:《佛祖通记》卷26,高楠顺次郎等:《大正藏》第49册,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大正年间(1922-1934年)。
[5] Bernard Faure.ChanInsightsandOversights:anEpistemologicalCritiqueoftheChanTradi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
[6] 柳田圣山:《初期の禅史Ⅱ——歷代法宝記》,东京:筑摩书房,昭和51年。
[7] 释静、释筠编:《祖堂集》,吴福祥、顾之川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
[8] 道原:《景德传灯录》,高楠顺次郎等:《大正藏》第51册,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大正年间(1922-1934年)。
[9] 张说:《唐玉泉寺大通禅师碑铭》,董诰:《全唐文》卷321,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10] 黄檗:《宛陵录》,高楠顺次郎等:《大正藏》第48册,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大正年间(1922-1934年)。
[11] 大珠慧海:《顿悟入道要门论》,《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63册,京都:京都藏经书院刊印,明治三十八年至大正元年(1905~1912)。
[12] 马祖:《马祖语录》,邢东风编校,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
[13] 维摩诘:《维摩经》,高楠顺次郎等:《大正藏》第14册,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大正年间(1922-1934年)。
[14] 曹山本寂:《抚州曹山元证禅师语录》卷上,高楠顺次郎等:《大正藏》第47册,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大正年间(1922-1934年)。
[15] 玄沙师备:《玄沙师备禅师语录》卷上,《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73册,京都:京都藏经书院刊印,明治三十八年至大正元年(1905~1912)。
[16] 宋师明集:《续刊古尊宿语要》第2集“法眼益禅师语录”,《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68册,京都:京都藏经书院刊印,明治三十八年至大正元年(1905~1912)。
[17] 赜藏:《古尊宿语录》,《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68册,京都:京都藏经书院刊印,明治三十八年至大正元年(1905~1912)。
[18] 柳田圣山:《初期の禅史Ⅰ——楞伽师资记·传法宝纪》,东京:筑摩书房,昭和54年。
[19] 僧肇:《注维摩诘经》“序”,高楠顺次郎等:《大正藏》第38册,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大正年间(1922-1934年)。
[20] 悟明:《联灯会要》卷1,《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79册,京都:京都藏经书院刊印,明治三十八年至大正元年(1905~1912)。
[21] 普济:《五灯会元》卷2,《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80册,京都:京都藏经书院刊印,明治三十八年至大正元年(1905~1912)。

GONG Ju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un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山 宁)
2017-05-26
龚隽,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佛教思想史研究。
B946.5
A
1674-2338(2017)06-0034-06
10.3969/j.issn.1674-2338.2017.06.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