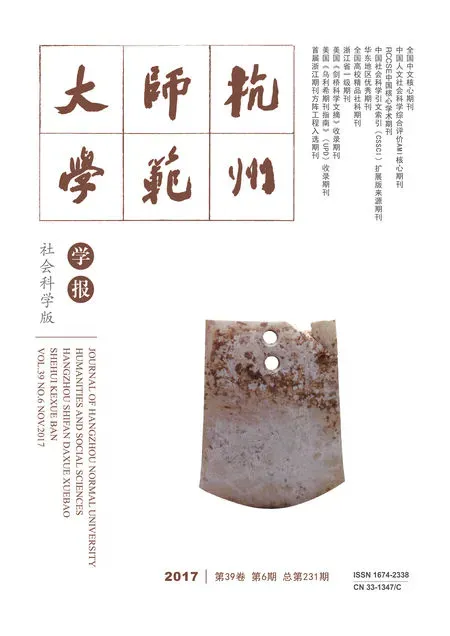毛奇龄评点《西厢记》的“心学”意蕴
杨绪容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文学研究
毛奇龄评点《西厢记》的“心学”意蕴
杨绪容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古今不少学者认为,毛奇龄经学研究的核心是心学研究。他壮年时期完成的《西厢记》论释,具有浓厚的心学意蕴,与他晚年的经学研究在思想价值、文学观念等方面密切相通。可以说,《西厢记》论释是毛奇龄经学研究的预演和准备。以往的看法是,文学总是被动接受经学的影响。而从毛奇龄的《西厢记》论释与经学研究的思想逻辑而论,则体现了文学对经学的滋养作用,从而揭示了经学与文学关系的另一个侧面。
毛奇龄;心学;《西厢记》
著名经学家毛奇龄被视为清初心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门生邵廷采曰:“至先生而发阳明之学,乃无余蕴。”[1](P.316) “‘致良知’三字,实合致知存心于一功。……如吾师直标宗旨,即今无第二人。”[2](P.310)《四库全书总目》称:“奇龄历诋先儒,而颇尊其乡学,其直指知本,仍王守仁之良知。其主诚意,则刘宗周之慎独也。”[3](P.315)不少现代学者也把阳明心学视为毛奇龄经学的核心。杨向奎认为,毛奇龄是“以经学就王学”,[4](P.227)台湾学者陈逢源将毛奇龄的学思历程定位为“理学与经学的会通”。[5]於梅舫说:“在毛奇龄本人或同时学人的认识中,阳明心学才是其学术核心,为其一生心血结晶”,[6]其概括尤为明确。
毛奇龄博学多才,其经史文学固多建树,其戏曲成果也颇受人重视。他最具代表性的戏曲成果是对《西厢记》的校注和论释。其书原名《毛甡论定〈西厢记〉》(五卷二十折)(以下简称“毛本”),卷各四折,康熙十五年(1676)学者堂刊行,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①本文所引《西厢记》正文、序跋皆出自《毛甡论定〈西厢记〉》,清康熙十五年学者堂刊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有特别说明的除外。毛甡是毛奇龄的曾用名。本文所引毛奇龄《西厢记》评语也均出自该书,为方便起见,只注明某卷某折某条,一律不标明页码。毛奇龄的《西厢记》论释之思想与文学观念具有浓厚的心学意蕴,与他的经学研究呈现出一种互为补充、互为呼应的关系。
一、毛奇龄论释《西厢记》所体现的心学观念
朱熹讲“性即天理”,[7](P.325)只谈“性”不言情。而心学则强调“人欲即天理”,②参见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一《语录》一“爱问‘道心常为一身之主’”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页。与宣扬“存天理、灭人欲”[8](P.224)的理学大异其趣。从王阳明的“良知”说到罗汝芳的“赤子之心”,再到李贽的“童心”说,都主张人要率性而真地表达自己的合理欲望。泰州学派还进一步把人情物欲世俗化、生活化。王艮主张“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9](P.10)李贽肯定“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10](P.4)在阳明心学的影响下,百姓日用成为晚明文学的重点和核心内容,其波澜延及入清以后。一生服膺心学的毛奇龄,于是在《西厢记》论释中表现了对世态人情的密切关注。
(一)对“情理”的重视
在《西厢记》卷三第二折【朝天子】“近间面颜……病患、要安,出几点风流汗”、【四边静】“怕人家调犯”两曲后,毛氏夹批云:
“病患”以下,皆使气语,言何必太医也,只恁足矣;且亦何必问病也。既怕调犯,则万一破绽,大家不安,遑问甚病乎?只赚人上竿而掇梯看之足矣。此以反激为使气语,最妙。初最爱王伯良解,但过于奥折,且曲白不对,又与尔时情理稍有未合,今并参之。
在此,毛氏特地拈出“情理”二字,并据此作为论释《西厢记》的评价标准。
在笔者看来,在明清《西厢记》评点家之中,毛奇龄最为重视“情理”。《西厢记》论释中几乎每条批语都被揆以“情理”,并最终形成独特新颖的意见。如卷三第二折【醉春风】“半晌抬身,几回搔耳,一声长叹”后,毛氏夹批云:“‘半晌’三句亦只是懒,而继以长叹,则其情可知耳。”此“情”指莺莺相思中的慵懒情状。毛奇龄不言“情理”而合于“情理”的批评更为普遍。如卷一第二折【幺篇】“若共他多情姐姐同鸳帐,怎教他被铺床。将小姐央,夫人怏,他不令许放,我独自写与个从良。”毛氏夹批云:“此以调红为调莺语。‘央’者,央说许放耳。‘怏’,不肯也。……言倘夫人不肯,不教小姐许放,我独写与从良券合耳。‘许’属莺,‘令’属夫人,‘令许’二字俱有着落。俗作‘夫人央’,平韵不叶,王本欲改‘勉强’之‘强’,亦谬。”对于“从良”,不少《西厢记》评点家谓张生“有得陇望蜀之意”,希望既娶莺莺为妻,又娶红娘为妾。而毛奇龄则认为张生其实表明了爱惜红娘、不愿其做奴婢之意,其观点新颖而中肯。卷一第四折【乔牌儿】“大师年纪老,法座上也凝眺”,【折桂令】“大师难学,把个发慈悲脸儿来蒙着”,毛氏参释曰:“初云大师‘凝眺’,后又云‘难学’,似矛盾。不知以‘凝眺’之师,能假覆以慈悲之脸,故‘难学’也。”意谓众人皆惊艳于莺莺之美,惟普救寺住持法本大师则能“以慈悲之脸”相掩饰,没有显露出张生及众和尚的狂乱状,所以“难学”。其他《西厢记》评点家均未把“难学”之意解释得这么深细。
毛奇龄还批驳了前人《西厢记》批评中存在的诸多不合情理之处。卷一第一折【赚煞】“饿眼望将穿,馋口涎空咽,这透骨髓相思怎遣”,毛氏夹批云:“‘相思怎遣’,诸本作‘相思病染’,‘染’字属廉纤闭口韵,固非。若朱氏本改作‘病蹇’、王本改作‘病缠’,则亦非是。初见而曰‘病缠’、‘病蹇’,情乎?且【赚煞】第三句末二字须用去上,‘病缠’为去平,终是误也。旧本‘怎遣’,最当。”其意是说,张生初见莺莺,用“病缠”、“病蹇”很不合情理,用“怎遣”最恰当。卷一第四折【驻马听】“侯门不许老僧敲,纱窗定有红娘报”。毛氏夹批云:“‘侯门’二句,则因莺未至,而急作揣度之词,言僧众固难通,梅香应报知也,此时当至也。‘报’是报莺,故云‘纱窗’;王伯良解作红娘应报长老,误矣。”其意是说,张生推想,红娘应把法场开始的消息报给莺莺,莺莺即将来到。这样的理解细致而恰当。
(二)对爱情的赞赏
爱情也是人情的一部分,甚至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例如,袁枚在《答蕺园论诗书》中宣称“情所最先,莫如男女”。见《袁枚全集》第2册,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年,第1022页。毛奇龄在《西厢记》论释中,对“崔张”爱情体会细致,表达了不少独特的意见和评价。如卷一第一折【后庭花】“若不是衬残红,芳径软,怎显这步香尘底样儿浅。且休题眼角留情处,则这脚踪儿将心事传。见慢俄延,投至到栊门儿前面,刚那了一步远。刚刚的打个照面,风魔了张解元。神仙归洞天,空余杨柳烟,只闻得鸟雀喧”。毛氏夹批云:“‘且休题’以下,却又从‘芳径’上写出一层,言不特眼角留情也,只此‘芳径’中有心事焉。何也?其踪迁延,不忍远也。及到入门处,因门有栊,刚此一步差远耳,余俱不然。芳径具在也,心事如此,却又刚于入门时打一照面,岂非眼角留情乎?因此‘风魔了’也。”该条批语说明,莺莺以眼角留情、以脚踪传心事,正是张生“风魔”之因。卷一第二折【耍孩儿】“当初那巫山远隔如天样”、【五煞】“则是年纪小”、【四煞】“夫人忒过虑”三曲后,毛氏参释曰:“此三曲反复红语,紧承上‘回头一望’、‘老母威严’二意,以申其缠绵之情,步步转变。”其意是说,张生所唱三曲,【耍孩儿】言莺莺本欲传情于己,而畏惧夫人威严;【五煞】其意一转,言莺莺之所以惮夫人者也,是由于年少性刚,未领略风流况味之故;【四煞】其意又一转,言夫人亦过虑耳,我岂妄想耶?郎才女貌,正相当也。三曲有三层转折,细致地展示了张生对莺莺的“缠绵之情”。卷四第三折【幺】“你与那崔相国做女婿,夫荣妻贵,但得个并头莲,索强如状元及第”。毛氏夹批云:“‘年少’以下,又承‘别离’来,言年少薄情,始多离弃,全不想我辈情深,非是之比,不容离也。然且今必离者,得无谓与相国作婿,不招白衣,必夫荣妻贵而后已耶?以我言之,但得并头已足矣,何必尔尔也?此节从来误解,致使莺口中,突作无理夸语,可笑已极。而陋者又复盱衡抵掌,谓从来妻以夫贵,而此则夫以妻贵。嗟乎!哀家梨已蒸食久矣。”一般批评家解释这段《西厢记》原文,认为莺莺以相国女婿、“妻荣夫贵”为由,不愿张生因科考而分离,其意颇为牵强。而毛氏则指莺莺因“情深”而不忍为功名暂别,且与“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之意甚相符合,语言简洁明快。卷五第二折【三煞】“则这天高地厚情,直到海枯石烂时,此时作念何时止?直到烛灰眼下才无泪,蚕老心中罢却丝。须不比轻薄子,弃夫妇琴瑟,拆鸾凤雄雌”。毛氏夹批云:“‘天高地厚’二语,莺情无尽也。‘烛灰蚕老’二句,感莺无尽也。情感如是,而犹疑为弃夫妻继别姻,何也?”毛评申明张生不别继良姻之意志,肯定了“崔张”二人深厚而坚定的爱情。
毛奇龄仅仅依据“情理”,实事求是地分析《西厢记》字里行间所隐含的“崔张”爱情意蕴,虽很少直接评价,但能让人明白感知他肯定和赞赏的态度。毛奇龄对爱情的肯定与赞赏,尽管未能达到晚明同情“心学”的一批优秀文学批评家(如提倡“童心”的李贽、宣扬“情至”的汤显祖、推崇“情教”的冯梦龙)那样的高度,但在观点与态度上是一脉相承的。
在生活中,毛奇龄也有过一段爱情佳话。他在京任翰林院检讨期间,曾娶丰台卖花翁女阿钱为妾,更其名为张曼殊。有人一度劝年轻貌美的张曼殊离开年迈贫困的毛奇龄,但她誓死相从。两人的忘年恋轰动京师。张英、周清原、陈维崧、汪楫、汪懋麟、施闰章、任辰旦、方象瑛、王嗣槐、乔莱、李澄中、龙燮、李铠、丘象升、吴陈琰、张鸿烈、潘耒、梁清标、尤侗、冯勗、汪霦、彭孙通、阎若璩等皆感怀赠诗。数年后,24岁的张曼殊病死,京师诸公悲其遇,又争作挽吊,其中尤以周清原的《续长恨歌》最知名。毛奇龄特作《曼殊葬铭》,录诸公吊词于其中。[11](卷96,P.90)这段爱情经历,折射了毛奇龄学术人生的一个精彩侧面,对我们理解毛奇龄的《西厢记》论释不无帮助。
二、心学影响下的戏曲文学观念
毛奇龄论释《西厢记》的主要成果是戏曲评点,借此表达了不少受心学影响的戏曲文学观念。
(一)“艳体”亦风雅
毛奇龄特别肯定了“艳体”亦即情词的文学地位。毛本卷首《论定〈西厢记〉自序》云:
或曰:“《西厢》艳体词,其词比之经之《风》、骚之《九歌》、赋之《高唐》、美人诗之《同声》《定情》《董娇娆》。宋子侯以下,其在词则《江南》《龙笛》等也。”虽不必尽然,然绝妙词也。
《西厢记》作为“艳体”,上接诗骚传统,乃是“绝妙词”。毛本卷首吴兴祚《序》亦云:“如《西厢》之经文纬质,出风入雅,粹然一归于美善,仍所罕有。……世有以《西厢》为艳曲者,吾不得知。”吴兴祚是毛奇龄的好友,两人都拿《西厢记》比附“六经”之一的《诗经》。
对“艳体”的积极评价,体现了毛奇龄个性化的文学观。孔子在《论语》中说“郑声淫”,主张“放郑声”。朱熹易“郑声”为“郑诗”,提倡“淫诗”说,认为郑卫之风多是男女淫奔之辞。毛奇龄针对朱熹的“淫诗说”进行了尖锐批评。他分辩说:“三百五篇皆可施礼义者也,皆弦歌者也。向使为淫奔诗,则不惟礼义所绝,几见有淫诗而可弦之歌之者?且淫诗何诗,谓可以合之舜之《韶》、武之《武》,与夫在朝在庙之《雅》、《颂》耶?”他为了证明“郑诗非淫诗”说,特地把《论语》所说的“郑声淫”解释为“声溢于诗曰淫”。[12](PP.405-406)毛奇龄的“郑诗非淫诗说”,与论释《西厢记》的“艳体亦风雅说”,相互贯通,相得益彰。
(二)元曲为“一代文章”
在毛奇龄看来,“艳体”尚且接续“诗骚”,那非“艳体”又如何呢?当然后者更具有积极的教化作用。他为《何孝子传奇》作《引》云:“昔元词以十二科取士,原有忠臣烈士孝义廉节诸条,不尽崔徽丽情也。读《孝子传奇》而不知其有裨于世也,则请过勾栏而观之可也。”[11](卷58,P.616)毛氏在顺治末曾作“连厢词”两部:名曰《不卖嫁》《不放偷》。其《自为墓志铭》云:“予少好为词,至是无赖,取元人无名氏所制《卖嫁》《放偷》二遗剧,而反其事,作《连厢词》,谓可正风俗,有裨名教。”[11](卷101,P.126)由此可见,借戏曲创作倡导教化是他一贯的主张。毛氏倡导戏曲的“教化”功能,对戏曲价值与地位的提升当然是有帮助的。
心学一脉总体上对戏曲等通俗文学评价甚高。王阳明说:“今要民俗反朴还淳,取今之戏子,将妖淫词调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13](P.113)王学中之泰州学派代表李贽《童心说》云:
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14](PP.98-99)
李贽把《西厢记》《水浒传》、唐传奇、金元院本等与秦汉古文、唐代近体诗并称“古今至文”,大大提升了戏曲小说的地位。毛奇龄也有这种倾向。他在《拟元两剧序》中言:“予思曲子昉于金而盛于元,本一代文章,致足嬗世。”[11](卷55,P.485)毛氏明确把戏曲作为元代文学的代表,与诗词文等传统文学中的正宗和主流等量齐观,体现了卓越的文学史识。此说对焦循“一代有一代之所胜”[15]和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16](P.413)之说不无启发。
(三)肯定戏曲文学的通俗性
毛奇龄在《西厢记》论释中肯定了“俗”文学的积极意义,但不反对必要的“雅”。其《西厢记》论释中有不少对俗语、俗文化的解释。如他指出,卷二第三折【殿前欢】“‘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系俗语”,卷五第三折【斗鹌鹑】“‘谢肯’勿作‘问肯’,系俗礼,今尚有之”。一方面,毛奇龄明确肯定了戏曲语言的通俗性。毛本卷三第一折【混江龙】后,毛氏参释曰:“‘灭门绝户’句,亦元词成语,如《蝴蝶梦》剧‘那里便灭门绝户了俺一家儿’,勿诟其俗。”卷四第一折【村里迓鼓】【后庭花】诸曲后,毛氏在夹批中引曹受可之言曰:“‘浑身通泰’,甚俗。然与‘医可九分不快’句相应,正‘十分’也。不然前欠一分,无谓耳。”另一方面,对《西厢记》的部分唱词及说白中的诗词,毛奇龄也提出了“雅”的要求。卷五第一折,叙张生中举,寄信报捷,莺莺回信附诗云:“阑干倚遍盼才郎,莫恋宸京黄四娘。病里得书怀旧事,窗前览镜试新妆。”其中“怀旧事”三字,俗本一般作“知中甲”,毛氏认为“既不对,又不雅,可恨”。总体而言,相对于“雅”,毛奇龄更重视“俗”。
毛奇龄特别强调不应以雅俗分高下,曰:
古乐有贞淫而无雅俗。自唐分雅乐、俗乐、番乐三等,而近世论乐者动辄以俗乐为讥,殊不知唐时分部之意原非贵雅而贱俗也。……故设为雅俗之辨,欲使知音者毋过尊古,毋过贱今,谓当世之人为今人不为俗人,谓今人之声为人声不为今声,则于斯道有庶几耳。[17](PP.326-327)
毛氏这段引文虽是从乐曲的角度立论,但与其文学及戏曲批评多有相通之处。晚明以来,“心学”对百姓日用的关注,引发了明代文学艺术尚俗的潮流,李开先、袁宏道、冯梦龙都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毛奇龄在论释《西厢记》中认可必要的“俗”,正是这一潮流的延续。
(四)具有宗唐倾向的文学理论范畴
唐诗和宋诗不仅是两个朝代诗歌的总名,而且代表了我国诗歌史上两种诗风和诗法。唐宋以后,历代诗歌派别之 宗旨基本上体现为“宗唐”或“宗宋”。历代文学批评家论唐诗,多偏重性灵、兴趣、意象、神韵、格调、趣味,论宋诗则多偏重理趣、才学。毛奇龄在《西厢记》论释中,使用了一些文学理论范畴,诸如性情、兴会、意象、传神阿堵、刻画等,这些术语体现了毛氏宗唐的文学倾向。
1.性情
毛奇龄认为,戏曲创作要抒发性情。他晚年接受洪昇邀请作《长生殿院本序》云:“才人不得志于时,所至诎抑,往往借鼓子调笑,为放遣之音。原其初,本不过自抒其性情,并未尝怨尤于人,而人之嫉之者目为不平,或反因其词而加诎抑焉。然而其词则往往藉之以传。”[11](卷47,P.409)毛氏认为,像《长生殿》这样的优秀戏曲作品乃是作家性情的自然流露。
毛氏把“性情”的主体归因于天赋异禀的才子。《西厢记》卷四第二折【幺】“你与那崔相国做女婿,夫荣妻贵,但得个并头莲,索强如状元及第”。毛氏夹批引赤文之言曰:“为相国婿,便夫荣妻贵,不惟作者无此陋词,莺亦定无此秽语。且通体转折,俱断续不合,不知向来何以能耐此二语,不一体贴也?《西厢》词世人能诵而不能解,其中多有未安处。经此论定,俱涣若冰释。谓非此书之厚幸不可矣。文章有神,千古文章自当与千古才子神会,西河之降心为此,或亦作者有以阴启之耳?”这就是说,戏曲批评也需要“神会”。“赤文”是一同论释《西厢记》的好友,称毛奇龄为“千古才子”,称毛氏的论释是与《西厢记》这部“千古文章”的“神会”。从中,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认识“才子”与“兴会”的关联。
2.兴会
在古代文论中,“兴会”主要指偶有所感而产生的意趣。毛奇龄认为,诗歌即源于性情与意绪的“兴会”。其作《张禹臣诗集序》云:“诗有性情,非谓其言之真也,又非谓其多愬述少赋写也,当为诗时,必有缘感焉投乎其间,而中无意绪即不能发,则于是兴会生焉。乃兴会所至,抽思接虑,多所经画,夫然后咏叹而出之,当其时讽之而悠然,念诵之而翕翕然,凡此者皆性情也。”[11](卷47,P.402)毛氏认为,性情与意绪的统一,抒情、赋写、描画的结合,都需要借助“兴会”,如此才能产生艺术审美意趣。
毛奇龄把“兴会”用在戏曲的解释与批评上。毛本卷首《〈西厢记〉杂论十则》云:
卤略者以不求解而存《西厢》,敏悟者以好解而反亡《西厢》。何也?以解之不得,则改窜从此生也。《西厢》犹近古,正由其耐由绎耳。今请翻《西厢》者,勿先翻《论释》,只就本曲字句寻求指归,志意相逆,文词不害,徐而罔然,又徐而涣然,然后知以我定词而词亡,不如以词定词而词存也。世实多真解会人,鄙识弇促,妙义层累,岂无补苴所未备、疏辟所难通者?踵事增华,是所望于嗣此者尔。
“解会”就是指人对“兴会”的理解。毛氏提倡做《西厢记》“真解会人”,要依据“本曲字句寻求指归,志意相逆”,反对强解和妄改。“志意相逆”,语出《孟子》:“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18](P.288) 毛氏把孟子“志意相逆”作为“兴会”的内涵,要求立足原典字句,达到解注者之意与原作者之志的妙合。
3.意象
卷五第一折【逍遥乐】“何处忘忧?看时节独上妆楼,手卷珠帘上玉钩,空目断山明水秀,见苍烟迷时树,衰草连天,野渡横舟”。毛氏夹批云:
“何处忘忧”七句,但一路填词,而意见言外,如云必欲忘忧,除非望远,但空见尔尔,则又何能忘忧耶?“空”字内有止见此而不见人意,此正如昔人所称王龙标诗:“外极其象,内极其意”,此填词最高处。且亦本董词“无计谩登楼,空目断,故人何许?”并“楚天空阔、烟迷古树”诸句。而或者訾为填句,无理。且“手卷真珠上玉钩”出李璟词,“凭高不见,芳草连天远”出王和甫词,竟痛加涂抹;谓“珠玉”等字随手杂用,则病狂甚矣!他可勿复道耳。
在唐代,“意象”是颇具特色的诗歌范畴之一。王昌龄历来被视为唐代诗人中运用“意象”技巧的典范,其《诗格》甚为关注“意”、“象”及其会通之“境界”。明末陆时雍《诗镜总论》云:“王昌龄多意而多用之,李太白寡意而寡用之。昌龄得之椎练,太白出于自然,然而昌龄之意象深矣。”[19](P.203)毛奇龄在此借用“意象”概念,凸显了崔莺莺抒发离愁的景中之境、言外之意。毛氏把“意象”概括为“填词最高处”,对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揭示元曲最佳处在于文章有“意境”之论[20](P.74)当有所启发。
4.传神“阿堵”
毛奇龄在《西厢记》论释中数次用“阿堵”表示“传神”之意。卷三第二折【普天乐】“晚残妆,乌云散,轻匀了粉脸,乱挽起云鬟”,毛氏夹批云:“不曰‘晓妆’,而曰‘晚妆’,以宿妆未经理也,前言‘云乱挽髻偏’故也。此言‘乌云散’则髻解将理矣。又曰‘乱挽起云鬟’,则因见简帖而又仓卒绾结也。此正模画入阿堵处,而不知者以为重复,何也?”其意是说,“乌云亸”与“乱挽起云鬟”,细致地表现了莺莺见到张生来信前后发饰的变化,不仅不重复,反而十分生动、传神。在《西厢记》卷五第二折前,毛氏“参释曰:此与前折作对偶,俱用虚写。盖未合以前,则以传书递简为微情;既合以后,又以寄物缄书为余思。皆作者阿堵也”。毛奇龄认为,卷五第一折叙莺莺寄信物给张生、并一一说明其用意,第二折张生收到莺莺信物、又一一猜中其用意:这两折都是在“崔张”结合之后,采用虚笔。而在前面卷三中,第一折叙张生寄信给莺莺表达相思之情,第二折和第四折叙莺莺寄信给张生邀其赴约:这三折都是在“崔张”结合之前,属于实写。《西厢记》虽然用了五折篇幅表现寄信场景,但在重复中又有变化,因而都是传神之笔。
5.刻画
“刻画”也是毛奇龄论唐诗的关键词之一。《西河诗话》云:“自无学者谓唐诗笼统,不知唐诗最刻画。”[21](卷6,P.553)毛氏还曾例举李商隐、张谔诗为“刻画”的典范,曰:“唐诗刻画如李商隐《和韦潘先辈七月十二日》诗:‘桂含爽气三秋首,蓂吐中旬二叶新。’其赋七月十二日便镂琢至此!先兄曰:‘初唐《九日》诗有 “绛叶从朝飞着夜,黄花开日未成旬”,其镂琢倍于韦诗,且赋九日只一句。’”[21](卷6,P.554)“镂琢”是指特别精细的刻画。
《西厢记》卷四第一折叙“月下佳期”,毛氏在【混江龙】一曲后参释曰:“前七曲一节,后十曲一节,俱极刻画。”其意是说,本折前面从【点降唇】到【寄生草】七曲叙张生等待莺莺的情景,后面从【村里迓鼓】到【煞尾】十曲叙张生莺莺相会的情景,刻画极为细致生动。同折【幺篇】叙莺莺幽会时的情态:“半推半就,又惊又爱,檀口揾香腮。”毛氏夹批云:“‘揾’者,以手抆物,如‘揾泪’之‘揾’,从手;此推就之际,似羞其不洁而抆口在颊,真刻魂镂象语。”“刻魂镂象”,是指把虚实景况都刻画得细致生动。
总之,毛奇龄在《西厢记》论释中引用了不少唐诗,其作者有李白、杜甫、白居易、李贺、李商隐、陆龟蒙等,但他同时也引用了范仲淹、苏轼、李清照等人的诗词,对唐宋文学皆有所取。然而在文学观念上,毛氏却有强烈的宗唐倾向。毛氏明确把“刻画”、“意象”概括为唐诗的重要特色,而性情、传神、兴会历来亦被公认是唐诗特色。《西厢记》是曲词,与诗词关系非常密切。毛奇龄把这些诗词术语运用于戏曲批评范畴,由此显示了他的思想宗唐的文学倾向。
在毛奇龄诗学观中,“尊唐”与“抑宋”是彼此相通的两个侧面。毛奇龄对宋诗的厌弃甚至都不需要说明理由。他曾说:“诗以雅见难……亦以涵蕴见难……又以不着厓际见难……然则为宋诗者亦何难何能何才技而以此夸人,吾不解也。”[21](卷5,PP.547-548)在他的意识中,优点都属于唐诗,缺点则归于宋诗,后世学宋诗之人亦毫无所取。他只要有机会,便毫不客气地贬抑宋诗。其自叙云:
尝在金观察许,与汪蛟门舍人论宋诗。舍人举东坡诗“‘春江水暖鸭先知,正是河豚欲上时’,不远胜唐人乎”?予曰:“此正效唐人而未能者。‘花间觅路鸟先知’,唐人句也。觅路在人,先知在鸟,以鸟习花间故也,此先先人也。若鸭则先谁乎?中水之物皆知冷暖,必先以鸭,妄矣。且细绎二语,谁胜谁负?若第以‘鸭’字‘河豚’字为不数见,不经人道过,遂矜为过人事,则江鳅土鳖皆物色矣。”时一善歌者在坐,观察顾曰:“诗贵可歌咏,若‘河豚’句似不便咏吟。试倩善歌者歌之,能脱嗓否?”各笑而罢。[21](卷5,P.548)
汪懋麟喜欢宋诗,绝口称赞苏轼,引起毛奇龄不满,当场反驳说苏轼“此正效唐人而未能者”。毛奇龄的意见得到其好友、江南按察使金镇的当场呼应。
毛奇龄诗学研究“尊唐抑宋”的倾向,与其经学观的“尊明抑宋”态度是一致的。毛奇龄的经学研究专门攻击朱熹,大力维护阳明心学,因此他对宋学痛加诋毁。宗唐是明代诗坛的主流,在晚明受心学影响的诗人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如前后七子、竞陵派都倾向于尊唐。因此说,毛奇龄“尊唐抑宋”的文学观与“尊明抑宋”的经学观是互为表里的。
综上所述,作为清初心学代表人物之一的毛奇龄,其对《西厢记》的论释与心学研究,在思想价值、文学观念等方面密切相通。他壮年论释《西厢记》,晚年才专注于经学研究,其学术思想、治学方法与理念实际上是首先形成于《西厢记》的论释中,然后才运用于经学研究的。从此意义上来说,毛氏的《西厢记》论释尤其值得关注。就经学与文学的关系而论,以往的看法是,文学总是被动接受经学的影响。而从毛奇龄的《西厢记》论释与经学研究的思想逻辑而论,则体现了文学滋养经学的认知规律,从而显示了经学与文学关系的深层内容。
[1] 邵廷采:《答蠡县李恕谷书》,《思复堂文集》卷7,祝鸿杰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
[2]邵廷采:《候毛西河先生书》,《思复堂文集》卷7,祝鸿杰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
[3]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37《四库全书总目·〈四书索解〉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4]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
[5]陈逢源:《毛奇龄经学论著及其学思历程》,《东吴中文学报》,2000年第6期。
[6] 於梅舫:《从王学护法到汉学开山——毛奇龄学说形象递变与近代学术演进》,《中山大学学报》,2014 年第1 期。
[7]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8]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1册卷13,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9]王艮:《语录》,《王心斋全集》卷1,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
[10]李贽:《答邓石阳》,《焚书》卷1,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11]毛奇龄:《西河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12]毛奇龄:《白鹭洲主客说诗》,《续修四库全书》第6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13]王守仁:《语录三》,《王阳明全集》上册卷3,吴光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14]李贽:《童心说》,《焚书》卷3,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15]焦循:《易余籥录》卷15,德化李氏木犀軒刻本,清光绪十二年(1886)。
[16]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王国维遗书》第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17]毛奇龄:《竟山乐录》卷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经部第22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18]孟子著、阮元编撰:《孟子章句》卷18《万章章句上》,影印十三经注疏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19]陆时雍著、李子广评注:《诗镜总论》,《中华经典诗话本》,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20]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王国维遗书》第15册,影印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
[21]毛奇龄:《西河诗话》,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420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
TheConnotationofMindStudiesinMaoQiling’sInterpretationonTheRomanceofTheWestChamber
YANG Xu-ro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Many ancient and modern scholars think that the core of Mao Qiling’s study on Confucian classics is Mind Studies. His interpretation onTheRomanceoftheWestChamber, which was completed in his prime of life, has a strong connotation of Mind Studies and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his later studies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aspects of ideological values and literary concepts. Therefore, the interpretation onTheRomanceoftheWestChamberis a rehearsal and preparation of Mao Qiling’s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The previous views hold that literature is always passively influenced by Confucian classics. However, from Mao Qiling’s interpretation onTheRomanceoftheWestChamberand the ideological logic of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literature nourishes Confucian classics, which reveals another aspec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an classics and literature.
Mao Qiling; Mind Studies;TheRomanceoftheWestChamber
山 宁)
2017-08-08
杨绪容,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攻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代表作有《〈百家公案〉研究》《王实甫〈西厢记〉汇评》等。
I206.2
A
1674-2338(2017)06-0103-07
10.3969/j.issn.1674-2338.2017.06.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