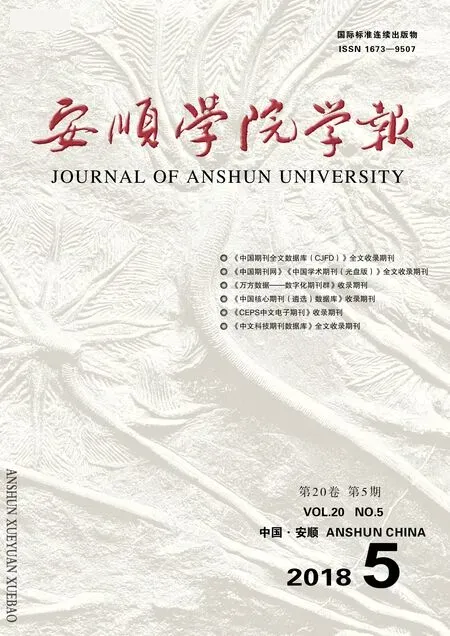从张惠言的词学主张看词之“本色”
(河北大学文学院,河北 保定071002)
词之本色问题,在欧阳炯《花间集序》已有所表述。宋初诸家不离花间宗风,至苏轼为一变,作豪气词,自是一家。其本质乃是文人将诗家意趣和笔法融入词的创作之中,成为“以诗为词”的士大夫之词,开启了词由歌者之词到文人之词的演变之风。有清一代,被称为词之中兴。这期间作者辈出,并形成诸多词派,浙西词派、云间词派等先后主导词坛,词之创作,一时间蔚然成风。就创作而言,浙西词派标举姜、张之清空骚雅,阳羡词人则以苏、辛为尊,推崇豪放;但就理论而言,二者均未能形成完整的创作理论体系。直至常州一派出,力除两派积弊,成为清中后叶的一大词派,影响深远。张惠言作为常州词派的创始人,其词学主张,在与其兄弟张琦所编《词选》序文中已可见一斑。本文试从张惠言的词学主张出发,回到词之“本色”,对词的“本色”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一、意内言外的立意根本
言意关系之探讨,先秦已有。《易传·系辞上》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1]爻辞并不能表述全部思想,因此圣人通过卦象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张惠言早岁治经学,他在《虞氏易事序》中写到:“夫理者无迹,而象者有依,舍象而言理,虽姬孔靡所据以辩言正辞,而况多歧之说哉!”[2]40他认为理本是没有踪迹可寻的,只有通过有所依的物象,才能表现不可寻的义理。他也说:“夫民有感于心,有慨于事,有达于性,有郁于情,故不得已者,而假于言。言,象也。象必有所寓也。”[2]18文字不仅是言语,更是由文字组成的意象。显然,他对汉代经学的言、象关系的接受,对他的词学主张有很大影响。《词选·序》云:
《传》曰:“意内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3]1617
关于《传》所指为何,一般认为是许慎《说文解字》。许氏此书作于东汉,而词作为一种文体则兴起于唐五代,所以许氏所说的词一定不是后世普遍认为的韵文体式,而是指语词之词。张惠言在此基础上仍用“意内言外”来解释词,显然不是混淆之误,而是故意为之。此“词”非彼“词”,不过借他人之言来阐释个人理解。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以“言有尽而意无穷”[4]7来形容盛唐诸人诗文的高妙,使文艺创作和批评注意到主客、虚实、象外、物外的艺术辩证关系。可见将言意关系用于文学批评,是有其渊源与传统的,并不是张惠言的拈来之语。“意”是什么?张惠言说是“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3]1617。从屈原“香草美人”开始,文人士子便有以男女爱情暗指君臣的寄意传统。张惠言在《词选》中共收录唐宋44家160首词,其中被他认为有“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者,约40首,不能自言之情均被张氏认为是温柔敦厚,美刺忠君。如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中,张惠言认为“照花”四句有《离骚》“初服”之意,含感世不遇之情。后人对此颇有质疑,清代另一位大词学家王国维就曾对此提出批评,“固哉,皋文之为词也!飞卿《菩萨蛮》、永叔《蝶恋花》、子瞻《卜算子》,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3]4261他认为张惠言解词太“固”,太过死板固执,这些作品都是兴到之作,没有什么不能自言之情。
然而,张惠言“意内言外”的词学主张并不是凭空臆造。诗歌是直接感发、不加掩饰的情感表达,具有直接性。而词与诗不同,它不是直接的感发,而是感情的沉潜,当作者产生创作动机,沉潜在内心的感情便自然而然流露于纸上。它不一定是感世不遇之情,也不一定是故国之思、家国之悲,但它真实存在于词人内心,虽去留无迹,难以捕捉,却不可忽视,只能通过所言所写之事、所描所咏之物才能够体悟感知。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内在情感,所以词人看山已不单是山,看花已不单是花,眼前的景象都打上了“意内”的烙印。词人的个人际遇、生平遭遇,所接受的诗学、禅学、儒学思想,都是意的累积。我们常说,评价诗人词人的创作风格,不能固守眼光,只抓住他的一些作品进行判断,要注意阶段性、流动性,正是因为诗人词人在不同人生阶段有不同的遭遇,接受不同的思想,所以才会有不同风格的作品。张惠言强调“意内言外”,是对词内核的关注,“意内”影响作者语言的表达,所能看到的表面的“言外”,是因先有“意内”的存在而存在的。这种意内言外的立意根本,不在于意境是否高远阔大,语言是否庄重高雅,而在于直抵词人内心深处的情感诉说,这也正是词之所以为词的本色。
二、幽微隐约的美感特质
谈到词的美感特质,不能绕开的就是花间词和花间词人。这批词人尽柔艳绮靡之能事,以绮筵公子、绣幌佳人的生活为写作素材,以女性形象和女性语言开创了清切婉丽的花间词风,对后世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故东坡称少游为今之词手;后山评东坡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5]婉约与豪放,素来被认为是词的两种不同风格,其中婉约风格正是对花间词风的承袭和发展,似乎婉约便是这类词人一以贯之的美感特质;继而苏轼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6],开豪放之先河,似乎豪放便是其作品的美感特质。
张惠言在《词选·序》中谈到最多的就是词的美感特质。特即特别的,特殊的,质就是品质,那么词的美感特质就是说词作为词的特殊的美好品质。他说道:“低徊要眇,以喻其致。”[3]1617低徊,出于《楚辞·九章·抽思》“低徊夷犹,宿北姑兮”[7]171,王逸注云:“夷犹,犹豫也……言己所以低徊犹豫,宿北姑者,冀君觉悟而还己也。”[7]172低徊表明感情的反复回荡、萦纡,如孤鹜南飞,低掠水面而盘旋不忍离去。要眇,则出于《楚辞·九歌·湘君》“美要眇兮宜修”[7]72,王逸注云:“要眇,好貌。修,饰也。”[7]73要眇就是经过修饰的,容貌姣好的样子。洪兴祖《楚辞补注》[8]59则说“要眇宜修”是形容娥皇的“容德之美”,容德,容貌与德行,自然就包括外在容貌和内在心灵,是说女子容貌与心灵统一的美。另《楚辞·九章·远游》“质销铄以汋约兮,神要眇以淫放”,洪兴祖释云“要眇,精微貌”[8]168,则是精巧微细的样子。因此,低徊要眇就是缠绵萦纡且精巧微细的美。通过雕琢这样一种精微细致而又缠绵之美,来达到所追求的词的极致。这在张惠言看来,正是词独特的美感特质。
王国维在 《人间词话》中谈到词的定义:“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3]4258同样用“要眇宜修”四字为词做了最基本的定义。词的内容与形式决定了它缠绵悱恻,低徊要眇的特质。一种难以言状、沉积在词人心底深处的情感,“兴于微言,以相感动”[3]1617,使得千百年后人读之,仍能感受到这种情感的力量。
就词之本色而言,当然不能以某一类词的某一特色为标准,只有词共同具有的特质,方可成为评判是否为词之本色的依据。婉约词为词,豪放词也为词,融汇在两者之间不显为人所见的共性,正是它们的本色所在。
苏轼以诗为词,用词书写个人怀抱,开豪放之先河,南宋辛弃疾更是以文为词,将一腔热忱与志向倾注于词,遂分词为婉约、豪放两派。以苏辛为代表的豪放派摆脱了花间以来以女性和爱情作为写作内容的倾向,赋予词同诗一样的“言志”功能。近年来,对于婉约与豪放两派的划分,学者不断提出新的质疑。如历来认为苏轼是豪放派,而苏词中绝大多数作品却属婉约之作。吴梅《词学通论》中就说道,“余谓公(苏轼)词豪放缜密,两擅其长,世人第就豪放处论,遂有铁板铜琶之诮,不知公之婉约处,何让温韦?”[9]51他认为苏词中的婉约秀丽之处,比温庭筠、韦庄等花间词人不差分毫。笔者在此无意对豪放或者婉约词派划分进行辩驳,而是意在说明本色之幽微隐约的美感特质,无关豪放与婉约之分。五代宋初的词作,作者没有有意识地创造幽微隐约之美,表现于词中的这种美感特质,是作者心灵中细腻美好品质的自然流露。而到苏、辛等人,他们有意识地抒情言志,作豪气词。然而,在这样的作品所展示出的广阔视角中,仍然同婉约词一样,具有幽微隐约的美感特质。豪放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初读只感到无尽豪迈之情,再读便体会到词人在看似豁达的语言之下,隐藏着难以言状的无奈之情。在词中苏轼没有直抒胸臆,而是用豪放的语言表达曲折深隐的内心情感,何尝不是一种幽微隐约之美?何尝不与“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有异曲同工之妙?
王国维说“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3]4246。此处应说,词之幽微,在神不在貌。一首词是否具有幽微隐约的美感特质,不能一概而论,婉约词作中有许多语言富艳而无内质,或者纯粹描写闺阁女子,淫靡浅露、缺少中国传统之美的浅薄之作,这样的词虽有婉约之貌,却难有婉约之神,实在难称为词之本色。同样,豪放词作也不只是流于叫嚣,豪放词佳作所蕴含的幽微隐约的美感特质,也是不可忽视的。词之本色,无关风格,而在于一首词是否具有词之特美,即幽微隐约的美感特质。
三、比兴寄托的创作追求
“比”“兴”二字,上溯《诗经》,在“诗六义”中,“比”与“兴”并称,是诗歌创作的传统表现方法。《周礼·春官·大师》郑注云:“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10]而朱熹则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11]5,“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11]2。可见,“比”和“兴”不单单是诗歌创作的表现手法,更是具有美刺劝诫含义的表现手法。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近矣。”[3]1617
张惠言论词之“比兴”,与“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并提。“变风之义”“骚人之歌”是张惠言对于词之“比兴”的进一步理解和说明,可见他认为词之创作,也应该同《诗经》《离骚》这样的作品,具有美刺比兴的意义。如何实现词的美刺比兴?正是要通过寄托,有所指发,有所寄托,是意内言外,是深美闳约,是贤人君子的“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
除在理论层面提倡作词要“比兴寄托”,张惠言更是将这一主张运用到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如《水调歌头·春日赋示杨生子掞》其五:
长鑱白木柄,劚破一庭寒。三枝两枝生绿,位置小窗前。要使花颜四面,和着草心千朵,向我十分妍。何必兰与菊,生意总欣然。
晓来风,夜来雨,晚来烟。是他酿就春色,又断送流年。便欲诛茅江上,只恐空林衰草,憔悴不堪怜。歌罢且更酌,与子绕花间。[12]
上阙以纤细柔婉的笔调,描述春之到来,欣欣向荣,而下阙笔锋忽转,“晓来风,夜来雨,晚来烟”,环境突变,“是他酿就春色,又断送流年”,外在环境成就了春天,也葬送了春天。看似在说外在景物,实则以景物比喻人生,以“风”“雨”“烟”来象征经历的磨难和挫折,接着指出面对风雨忧患,仍应有济世之心,最后“与子绕花间”的安然自得,带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内在感发。全词的比兴寄托,是通过“长鑱”“诛茅”“江上”等中国传统文学中特有的语码来完成的,这些语码在前人的作品中形成的容易引发联想的寓意和内涵,使得读者在读到这首词的时候,产生出相应的联想,此时,作者的比兴寄托才得以实现。另外,张惠言还通过选本《词选》表达了自己的创作追求。前文已提到,张惠言在《词选》中共收录唐宋词44家160首,其中有“兴寄”,即所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者,约40首,占到全书的四分之一。虽然有的解读被后世认为过于牵强附会,但也确实从一个层面反映了张惠言对于创作中“比兴寄托”的推崇。
词在产生之初,是歌筵酒席间助情遣兴的曲子,这样情况下产生的词,当然很难具有比兴寄托的深意。但随着词从歌者手中转到了文人手中,在创作时,文人难免将个人的所思所想流露于词中,自此,词就自然而然带有了比兴寄托的创作动机。任二北《词学研究法》“比兴之确定,必以作者之身世、词意之全部、词外之本事三者为准。”[13]他认为有无寄托之意,应当从身世、词意、词外之本事三方面去考量,将时代和作者以及作品联系在一起,才能判别一首词是不是有寄托的作品。而笔者认为,一首词是否具有比兴寄托,穿凿附会,深究每一词每一字的寄寓,自是不可取也不可为,而全词之兴寄,无处可寻却令人回味无穷,才是比兴寄托的最高境界,作者或有意为之或无意为之,在创作时将内心情感表露于有形无形之中,使得词具有了幽微隐约的美感特质,从而回归到词之雅正的根本,这才是张惠言“比兴寄托”创作追求为我们提供的本色新视角。
总而言之,张惠言的词学主张有深厚的思想基础,意内言外的立意之本、幽微隐约的美感特质和比兴寄托的创作追求三个方面不仅是他的个人主张,更体现了词本色的最高理想。从张惠言的词学主张入手探讨词之本色,打破了传统本色观对豪放词的偏颇见解,将本色视角更微观地放在词所具有的深层意蕴上,对此后的词体创作和词学批评都有重要影响。
——以张惠言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