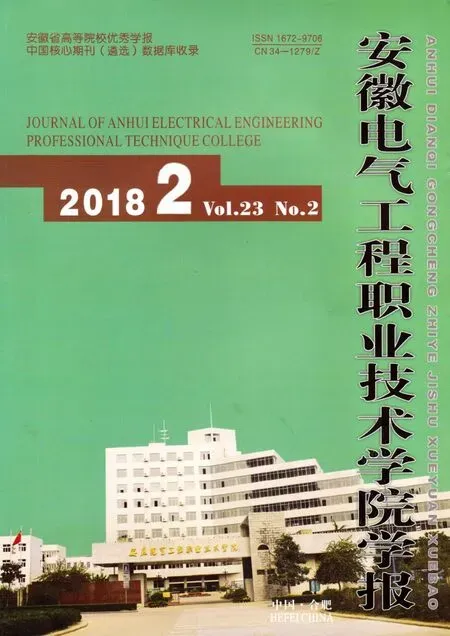论政府与市场关系视阈下证券监管权限的配置调整
——动态演进论的视角
程 威
(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 201620)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证券监管因“新兴+转轨”的特殊背景要求而较多以严格性、冲动性、敏感性的部门立法方式得以运作,对于实践中生成的金融创新采取适度放开的保守路线,对危及投资者利益的证券违法行为课以严格的责任负担。该种立法与执法风格需放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结构性制度背景之下予以理解。政府与市场关系是现代社会运作的基本参数,前者通过在“全能政府”与“小政府”之间的权限选择和权力运行实现社会结构的整体平衡,后者通过放任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而组合不同的社会交易行为并扩大其影响边界以实现社会产品的归属稳定。然而,随着“全能型政府”和“全能型市场”的制度示范模型被经济逻辑摧毁,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交叠诱发局部性经济危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开始暧昧不清,如何能在具体的制度事项安排上有效地结合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通过政府与市场的不同组合方式达致一种相对稳定而合理的权限分配,成为迫切待解的问题。
在日常权力的运作场域,证券监管权因其涉及金融体系的安全防范和财富流通的有序组织,而受到普遍的关注,在制度检讨环节,证券监管权也最适合从政府与市场的双重维度上进行理解和解释,本文结合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的反思性调整,从时间(过程)维度、空间维度、主体维度对证券监管事权的安排进行重构。
二、政府与市场关系视角下的监管理论及其挑战
监管思路的变迁直接促成监管规则的重构。从证券监管权限分配的维度思考政府与市场关系将反过来对监管思路的调整产生积极影响,因为从宏观与微观的制度互动而言,中国证券监管属于典型的行政治理推进模式,从与市场的持续沟通中得出的反馈来看,政府主导的治理规则开始面临相当程度上的不适应局面,需要重新理解政府与市场关系并获得启示。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重述*政府与市场关系是经济资源配置的关键话题,也是决定权力配置的重要因素,在日渐放松监管强度和力度的制度背景下,天平偏向前者则预示着权力的毛细血管仍在施加控制,天平倚向后者则表明对市场精神的尊重。
有关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讨论,其原点在市场失灵。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揭示,市场供需双方的力量博弈能够使得资源流向其价值实现最大化的方向,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佳方式。而在现实的经济运作过程中,诸如公共物品的消耗、自然垄断的形成、外部效应的溢出、信息不完全的误导等等市场失灵问题使得市场之手难以实现其最优目的[1]。政府由此介入的目的正是在于对市场自发秩序形成过程中出现的收入分配不公平、贫富差距扩大化等现象的补救,政府通过行政手段的积极应用调整跨时期的资源分配,比如对公共品的过度消耗,政府从维护整体利益出发,除了主动提供公共产品之外还会对公共品的使用采取建章立制、有法可循的方式抑制使用者的消费需求;对自然垄断造成的竞争失效局面,政府会通过法令对非法垄断采用切割、嫁接等方式保证市场充分竞争、价格足够合理;对负的外部性现象,政府也会加大惩处力度使企业将外部成本内部化,从而减少过度的资源使用;对信息不对称格局,政府会要求信息优势方在不损害自身经营损失的情形下披露信息,保持市场信息充分,减少沟通、磋商成本等等。
然而,随着政府行为的扩大化,其因理性局限以及统筹信息功能不足所造成的政府失灵现象开始凸显。哈耶克在较早的一篇论文中评价社会主义总体统筹经济规划的制度安排会遇到三个根本的问题:人际之间的效用不可比较、数据不可得到、很难恰如其分地去奖惩人们的行为。而经济体系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变化的问题,关于变化的知识(knowledge)永远无法集中在一个统一规划的人手中[2]。政府试图为公共利益计量从而施加管制的行为存在先天缺陷[3]。政府经济职能的发挥、干预经济活动的有效性是建立在政府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的假设基础上的。但事实上,政府的行为目标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是有差异的。政府官员是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政府机构具有内部性,政府行为的目标之一是实现预算最大化[4]。在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政府并不是完全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政府,它往往为有影响的利益集团左右。政府机构效率低下、角色错位、政策的滞后性以及政府干预空间与市场自治空间的冲突等等均对微观经济机制的运行产生损耗。
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反复无常验证了经济社会的不确定性风险,只有在政府与市场之间保持一个动态的平衡和合理的把握才能妥善处理好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资源错配。而此二者之间的定位从知识论视阈来看,知识论把“政府是否应当干预市场”的价值判断问题,转化为“政府与市场的获取知识能力”的事实问题,这可以提升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的科学性。科学的解释固然重要,但必须升华到实践层面才有意义[5]。
(二)证券监管理论及其挑战
根据政府与市场的不同定位衍生出不同的证券监管理论如公共利益论、监管俘获论、监管经济论和监管辩证论等,但这些理论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现实挑战。
公共利益论的逻辑起点是法律父爱主义,即法律因在社会建构过程中所具有的独特功能决定了在对社会对象的适用中需保持审慎、公平、均衡化的要素考量。*关于法律父爱主义的逻辑框架下行政执法者的基本管理模式,可参见孙笑侠、郭春镇:《法律父爱主义在中国的适用》,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为了维护证券市场这一共同体内部异质利益的妥适分配和和谐相处,必须以利他主义为出发点,*关于利他主义的经济理性及反思,参见何国卿等:《利他主义、社会偏好与经济分析》,载《经济学动态》2016年第7期。方能对证券市场施加有效监管、弥补市场失灵从而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然而,公共利益在利益纲目中的宽泛定义使其具有模糊性、变动性、阐释性、适应性等特点[6],如何有效、准确界定公共利益的涵摄范围成为公共利益论的“阿基里斯之踵”。即便政府高举维护公共利益的大纛且其行政行为也趋向对各方利益的妥当考虑,但其自身能否代表公共利益、其管制行为的边界如何确定等仍备受质疑。特别是,伴随着官商合谋(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丑闻曝光、政府寻租现象导致监管效率低下的直接恶性后果显现,公共利益论的监管逻辑式微。
监管俘获论来自于经济学家斯蒂格勒(Stigler)基于供求分析模式对政治市场上的管制行为所进行的探讨,由于利益集团通常控制和利用大量的资金和专用技术,对政府和公众施加影响,迫使监管者成为俘虏对象,扭曲了监管格局[7]。该理论强调,监管仅仅是被监管者俘获的产物,受监管的利益集团对监管者有特殊的影响力,监管者存在各种利己动机于是容易成为被监管者俘获的对象。但在解释中国证券市场时,因我国是典型的“散户市场”,个人投资者在投资者中占比远远高于机构投资者,长期范围内,中小投资者并无充分议价和左右市场的能力,所以俘获监管者的可能性并不存在,反而是因市场监管机制建设不周,中小投资者权益受损严重且获得救济的机会要小得多。此种情形下,监管俘获论的解释空间相对而言并不适用。
监管经济论整合了前述两种证券监管理路,将政府监管作为内生变量纳入到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内,运用监管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相互关系解释了监管影响资源配置的方式以及监管实施的方式。监管供给产生于对利益集团的政治支持的渴望,监管需求产生于利益集团对政府监管带来优势的追逐,故而在监管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会产生人力、物力、财力的损耗,而且有的监管行为甚至会阻碍被监管者创新行为的服从成本和被监管者寻租的成本。基于效率的考虑,监管者必然根据成本收益分析进行监管规划以服从其“经济人”身份特性[8]。而在我国的证券市场因处于有效市场假说的弱式有效市场类型,市场价格不能准确反映证券价格信息,为了谋求高额利益回报产生诸如虚假陈述、信披缺漏、暗箱操作等现象,在资本市场风险传导与扩大的特殊机制之下,市场秩序陷入困境,故而监管经济论所奉行的监管规则因过于强调“经济性”缺乏稳健的市场建构考量而显然面临不足的态势。
监管辨证论从动态的角度解释了监管过程中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机制,认为监管是由利益集团自己要求的,需求的存在产生了政府或政治集团供给监管的激励。虽然被监管集团首先要求监管,但监管实施的效率和达到目标的程度,随着环境的变化、目标的冲突、金融机构不遵守监管行为的不可检验性等原因而较难达到[9]。监管与逃避监管的矛盾冲突、持续互动,监管漏洞的存在使得逃避监管的行为迭生,而又引发新一轮的监管创新和制度轮替,如此交互作用推动整个证券市场发展。然而,在中国证券监管的现实样态下,监管结构发育的缓慢、监管能力低效、监管政策变易不居的制度约束使得监管辨证论无法有效回应金融创新,其结果可能会导致监管滞后而不加限制的金融创新绕开监管规则危害实体经济。特别是资产证券化等创新产品模糊了机构界限,监管归属如何明确、风险定价和交易规则如何规范等等是监管难以协商定论的屏障。面对日新月异的金融创新,监管层往往反应滞后,难以招架,现有的监管供给远不能跟上技术娴熟的创新主体,监管滞后负面影响可见一斑。监管辨证论的理想化追逐模式在中国证券监管领域将铩羽而归。
三、证券监管的事权重构
证券监管权的运作空间是政府与市场关系角力的典型场合,基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变革尤其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制度背景,证券监管权的分配亦随之重构。在构想权力分配重构的具体逻辑之前,需要理解转变政府职能的经济学含意(implication),因为政府何以转变职能以及政府职能本身的转向是决定确权的基础。
(一)转变政府职能的经济学分析
根据威廉姆森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严格分析,“任何一种关系,无论是经济关系还是其他关系,只要它表现为,或者可以表述为签约的问题,就都能根据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概念作出评价”[10]。交易成本政治学由此“把交易成本分析扩展到政治交换过程中”[11]。*证券监管权限的分配调整主要受控于转变政府职能认知的观念转向,设若以大政府小市场为政府认知判断,则极度压缩证券市场活跃度,假如小政府或服务型政府观念占据主流,则为证券市场繁荣创造了监管背景。
根据交易成本政治学的理论框架可以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是由政府自身利益驱动的,但经济社会组织也会就政府在经济社会事务治理中的边界进行再协商。其中,经济社会组织的相对议价能力确定了经济社会组织与政府进行政治交易的可能性,政治契约被治理的可能性也影响了再协商的结果。如是,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是一个政府利益最大化,经济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政治交易达成的可能性以及相对议价能力三者互动的结果[12]。
政府职能转变是其对经济社会事务管理职责履行的范畴调整,实质上是制度变迁的过程,根据政府终极目标在于其预算最大化的基本假设可得知,转变职能所诱发的制度变迁成本只有低于其所获收益才能刺激政府理性缩减其监管权限。从政府与市场的“双向运动”来看,区分经济政府与市场主体、政府配置与市场配置就是强调两类主体、两类配置要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并在经济治理上辨证施治,解决资源配置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13]。政府必须切割分离它配置效率并不高的领域,积极为市场在经济社会中配置资源的主体地位让路与铺路,使得政府本身成为支撑市场运行、维护市场秩序的守护神,而非积极干预市场、非理性强化政府功能的主体。
(二)证券监管权限重构的逻辑与应用
政府与市场分权应用到证券监管领域,其主旨从应然的规范分析而言,政府干预倾向于市场安全和秩序规范,市场主体主要是倾向于活跃市场、缔造金融创新,事实上从两种价值取向上保证市场本身能在安全的边界内实现效率提升,而理念的落实有待时间实践的操作。“一个好的法律环境可以有效地保护潜在的资金供给者,使他们愿意为金融市场提供资金,从而推进金融市场的发展”。*Lopez-De-Silanes, Florencio, et al. Law and Fina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6.6(1998),pp.113-115; and See Porta, Pafael La, et al, Law and Finance,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106.6(2001); pp.113-115.刷新监管体制的过高成本可能会遏制甚至侵损原有的体制福利和经济效率。从证监会与交易所、中央与地方两个维度,围绕证券监管事项安排对证券监管权限重构是目下监管权安排的基本因循。
1.证监会监管权限下放,交易所加强一线监管*日前我国交易所不断强调的加强一线监管体现了对市场精神的适度尊重。
美国证监会在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监管失败清醒地印证,格林斯潘氏所谓金融机构自身的认知、克制与修正这样一种“巨大弹性”与其说是监管者对市场本身的自信毋宁说是一厢情愿的理想,对于市场自律机制、声誉约束机制的怀疑和加强外部监管的呼声越来越强[14]。对市场主体及其私人秩序不能过分信任,尤其是在金融流动的场合,市场主体本身存在认知局限、过度狂热甚至自欺[15]。但是,如果以维护市场安全为金科律令毫无底线地严防死守任何金融创新,监管行为就将失去它应有的内容效力。尤其是证监会牢牢把控全国证券监管的核心细节,对于证券市场的创新行为和融资活动报以审慎审查态势,并不利于市场活跃。研究者认为,对于一个强大的证券市场来说,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是:一个国家的法律和相关市场制度必须为中小投资者提供(1)评估公司价值所需要的信息;(2)确信不会被公司内部人员欺骗的信心[16]。交易所对于实现这两个目标具有最敏锐的洞察力和实现可能性。
在证监会面临普遍质疑的背景下,下放其监管权限,加强交易所监管就成了必由之路。在行业自律监管方面,交易所因承担二级市场的监管重任,应保持相对独立的监管地位,而证券业协会不应仅仅作为协调内部成员的无牙老虎,在相关的事权安排上需具有话语权[17]。对交易所而言,监管功能是交易所为追逐获利而必然提供的服务内容;外部竞争的压力有助于克服交易所监管功能的缺陷。因而,产权结构和充分竞争是交易所有效履行监管功能的基础,而其中保证交易所面临充分的竞争压力最为关键[18]。监管功能并非来源于行政机关的授权或委托,而是出于对自身存在价值的释放所采取的必要手段。交易所提供的上市服务,其实可以被分解为四个组成部分:(1)流动性;(2)监控证券交易活动;(3)标准的公司合同格式;(4)交易所的信誉附加。*关于这些部分的具体分析,参见Jonathan Maeey&Hideki Kanda,The Stock Exchange as a Firm:the Emergence of Close Substitutes for the New York and Tokyo Stock Exchan8es,75 Cornell Law Review 1007(1990),pp.1011-1025.这些因素都有助于吸引投资者从事证券交易,从而扩大交易规模。交易所实现盈利的方式是通过吸引公司上市与投资者进场交易,收取诸如上市费用、交易手续费、信道费等。在监管压力下,交易所必须在吸引更多公司上市与确保所上市公司本身投资价值可靠性之间进行适当平衡。
2.放宽事前监管要求,加强事中监管与事后执法
根据监管的时间维度和过程视角来看,证券监管严格的说可分为事前监管(ex ante regulation)和事后执法(ex post enforcement)[19]。前者指在市场交易行为发生前进行预先的控制、批准、审查,如发行审核、收购审核等,而后者指对已然发生的违法行为的责任追究。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如美国证交会的事前审批很少,但事后执法相当突出[19]。而中国证监会却把事前监管作为工作重点。证券法通过事前监管的严格准入限制,将不具有优质资产和发展前景的公众公司排除出去,从而保障市场融资能力的畅通和融资目的的正当。这种目前对证券市场监管的诟病很大程度也在于对产品、业务、机构和人员的行政许可上,繁多的事前监管使证券市场主体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消耗在市场之外的事项上。*陆泽峰、李振涛: 《证券法功能定位演变的国际比较与我国〈证券法〉的完善》,载《证券法苑》第5 卷(上),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1 页。有的公司为了上市会选择粉饰业绩,而要达到财务报表的合规要求,不得不通过复杂的业务设计、分拆甚至组织体本身的结构性调整,这种大费周章的运作下来,一方面无法真实反映该企业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甚至因业务调整导致其缺乏竞争力。除此之外,频繁的寻租活动渗透在事前监管的“大浪淘沙”过程中,为了寻求上市,企业不得不长期来往于所在地和北京,不得不疏通各种关系甚至铤而走险逾越官商交流的基本界限、违背官商沟通的根本伦理,造成官商勾结、寻租频仍。这种事前监管的范式及理性愈发受到挑战和越来越多的批评。
所以就过程视角的监管以观,在权力内涵上,监管重心从事先审批向事后监管转移、减少大量的不必要的审批(审核)权仍然是完善我国证券监管权力制度的一个重要方向[20]。在证券发行注册制改革的逻辑下,结束现有以行政干预与事前审核为主的制度安排,将新股发行交还给市场,符合注册制精神和市场化要求[21]。事实上,除了事前监管和事后执法之外,事中的持续信息披露等监管方式也是重要的一环,证券市场高度自由的美国强化了被监管对象事中信息披露的责任意识,所以并不特别重视事中维度的考量。但在中国证券市场守法意识淡薄、违法现象盛行的制度背景下,强调事中信披自律是非常关键的环节。
3.中央监管权限下放,地方加强监管
下放中央监管权力,加强地方监管是监管竞争理论的逻辑结果,同时也符合中国幅员辽阔、市场丰富、地域分层的基本格局。美国的经验证据指出,各州之间的竞争没有使美国公司法的标准越来越低,相反“好”的公司法是各州之间监管竞争的产物。*史蒂芬·崔:《法律、金融和路径依赖:发展强大的证券市场》,载吴敬琏(编):《比较》第8辑,中信出版社2003年,页129。开放式的竞争环境(不管是产品、监管和市场)对于促进国际间规则的交流和产品创新成果的普及均有促进作用。
学者们早就证明,在竞争的压力下,监管才能更为有效[22]。目前从中央到地方、从证监会到交易所、从发行到上市交易,一系列的监管都维持在一个基本的分工配合和统筹操作,监管竞争的格局并没有得到良好的释放。2004年,深圳交易所开设中小板块,流通股本规模相对较小的中小企业股票将在这个板块挂牌上市。在这种安排下,深圳交易所创立中小企业板块,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之间形成了一个层次化的市场格局:上海交易所将定位为中国股市的主板市场和蓝筹股市场,深圳交易所则定位为中小企业筹资的主要场所,最终发展成创业板市场。在这种股市结构的安排下,显然两个交易所之间的竞争将大大减弱,而分别服务于不同规模的上市公司和不同需求的投资者[23]。
加强地方监管有利于促进上市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强化交易所竞争。根据我国特有的地理格局,上市公司资源分配并不均衡,地区差异较大[24]。按照目前的中央统一监管来看,中央严格控制上市公司数量,把控上市名额,数量控制的直接结果是导致部分优秀企业无法顺利融资从而寻求海外上市。监管竞争的目的是为了通过竞争实现上市资源的有效配置。
四、结语
本文的中心任务在于通过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解重新配置证券监管权限,从中央与地方、自律与他律、发行与上市(事前与事后)等不同维度构思证券监管的应然状态,这对于深化认识政府权力的运作场域及其与市场权力的碰撞具有重要意义。证券监管权的运作事涉证券市场稳定和实体经济的增长,如何规范其运作流程、强化责任归属、妥善管控风险、激励商事主体融资,是《证券法》的核心主题。注册制改革背景下,释放市场化运作的信号需要构建对市场与政府关系的制度化调整,中国法下证券监管权限的分配逻辑和重构路径应循既有的成就以及国际先进经验,将能构筑中国证券监管的防火墙。
参考文献:
[1] 维托·坦茨.政府与市场——变革中的政府职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2.
[2] HAYEK F A.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45, 35(4): 519-530.
[3] 兰迪·西蒙斯.政府为什么会失败[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4.
[4] 霍尔库姆.公共经济学——政府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228.
[5] 黎江虹.知识论视阈下政府与市场关系之辨思[J].中外法学,2010(1).
[6] 梁上上.公共利益与利益衡量[J].政法论坛,2016(11).
[7] 廖凡.竞争、冲突与协调——金融混业监管模式的选择[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
[8] 丁建臣,等.试论我国证券监管理论面临的现实挑战[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6(1).
[9] 蒋海,刘少波.金融监管理论及其新进展[J].经济评论,2003(1).
[10] 奥利弗·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69.
[11] 道格拉斯·诺斯.交易费用政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3.
[12] 蔡长昆.从“大政府”到“精明政府”: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逻辑[J].公共行政评论,2015(2).
[13] 张守文.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法律调整[J].中国法学,2014(5).
[14] PRENTICE R A. The Inevitability of a strong SEC[J]. Cornell Law Review, 2006, 91(4): 775- 839.
[15] QUINN B J. The failure of private ordering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2008[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09(5).
[16] BLACK B S. The legal and Institutional preconditions for strong securities market[J]. UCLA Law Review ,2001, 48(4): 781- 855.
[17] 高建宁.我国证券监管的制度变迁与模式选择[J].经济体制改革,2005(5).
[18] 彭冰,曹里加.证券交易所监管功能研究——企业组织的视角[J].中国法学,2005(1).
[19] COFFEE JR J C. Law and the market: the impact of enforcement[J].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2007, 156(2): 229-311.
[20] 高西庆.论证券监管权——中国证券监管权的依法行使及其机制性制约[J].中国法学,2002(5).
[21] 李小加.A股为什么需要注册制[EB/OL].http://finance.caixin.com/2014- 02-28/100644693.html
[22] ROMANO R. Empowering investors: a market approach to securities regulation[J]. Yale Law Review, 1998, 107(5).
[23] 彭冰,曹里加.证券交易所监管功能研究——企业组织的视角[J].中国法学,2005(1).
[24] 程金华.中国公司上市的地理与治理[J].证券法苑,2010,3(2):55-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