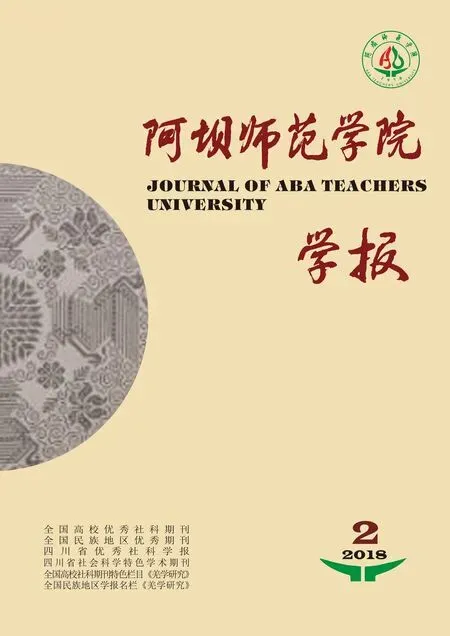汶川灾后建设中的文化价值重建
于佩丽
中国处于全球现代化进程之中,社会面临多重转型,各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汶川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地震灾害,原有的发展进程被打断,十年重建,各种现代化元素迅速涌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多种因素交织,形成新的“历史的合力”。现代与传统并非二元对立,要促进汶川城乡均衡发展,实现人的幸福生活,应根据文化的不同层次、功能,探索汶川文化重建路径。考察汶川文化特质,动员政府、社会和个人力量,为汶川发展提供文化价值指引,提供更具文化适应力的生活方式。
一、文化分层与文化价值
生活是整全的,文化是人们获得善好生活方式的途径。人类为谋求生存、获取慰藉、凝心聚力构建起一整套价值体系。按照社会学家费心通先生的观点,“文化是指一个团体为了位育处境所制下的一套生活方式”。“成套的原因是:在团体中个人行为的一致性是出于他们接受相同的价值观念。人类行为是被所接受的价值观念所推动的”[1]。
“位育”有“适应”的含义,体现的是人和团体、自然相互适应以达到生活的目的。生活在一定自然状态中的人,在生产实践活动中组成团体、社群,创造生产、生活所需要的文化,反过来,也受到所属团体文化、价值观念的约束、影响。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发展并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一种双向互动过程。
特定人群在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历史条件中采取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形成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但具有地域特点、民族特色的文化并不是与整个人类文化相对立、相孤立的文化孤岛。在与外来文化或多或少的交流互动中,本土文化会产生速度或快或慢的变革。在不平衡的发展进程中,文化会表现出吸纳积极、进步因素的方向性。
文化价值体系服务于人的生活目的,为人的行动赋予意义,提供指引。现代工业社会以经济为目的,经济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作用凸显。文化与经济二者的关系不应对立。汶川处于中国当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整体环境之中,通过对当地文化的考察,可以发现因民族融合所呈现出的丰富性、多元性。传承至今的文化遗产并不单纯服务于经济目的。非经济因素往往取代经济因素,在区域特色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对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重视文化教化和整合的作用,强调社会稳定和价值体系的维系。汶川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审美情趣、价值理念已沉淀出更具稳定性的文化传统。富有羌、藏、回、汉等多民族融合特色的文化符号、文化遗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既出于“日用伦常”考虑,也服务于社会事务管理需要,还体现出不同宗教信仰对客观世界的超越,满足不同精神文化需求。
汶川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当地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社会变迁具有丰富性、复杂性。“社会内在发展机制的强弱,取决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机体中多元因素能够获得多大的活动空间,这是内部孕育的渐变力量能否壮大的重要条件”[2]59。社会固有的社会矛盾不会因地震自然灾害而消失,灾后重建如不能适应当地居民的生活习俗和文化心理,有可能加剧社会矛盾,已经取得的经济成果也容易丧失。改善人们的生产水平、生活方式,改变人们的精神文化面貌,既要考虑历史文化传统,也要以现代化进程为参照。
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应“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形象地指出了文化其实具有不同层次、不同功能以及共同的核心价值。“作为一种整体的文化或者文明,主要有三层结构组成,可以分为工具、审美和价值信仰三个不同层次。外围系统是工具系统、认知系统,是文化的第一层工具部分。文化的第二层结构是审美系统部分。一个民族,一个种群,他的情感的型,特定的型,很多时候无关乎先进落后,好坏优劣。文化的第三层结构,是最内核的系统——价值信仰系统。这更难以用先进落后、正确错误、优劣高下去评价”[3]10。汶川的城乡文化传承与保护可以从中获得启发。
第一,从文化系统的工具层面看,为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人的要素和技术要素应成为汶川社会变迁和新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为适应中国现代化潮流和世界潮流,汶川的器物、制度层面可以通过学习、创新,不断追赶先进,与时俱进。
第二,从文化系统的审美层面看,为满足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应充分保护和积极培育汶川长期积累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活起来、活下去,需要考察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状态,抽取多层次文化样本,通过政府引导,调动社会力量构建“名城、名业、名人、名景”四位一体的“名城保护体系”,通过传承、保护、发展有形与无形的文化载体,实现城乡文化变迁中农业文化、工业文化、信息文化的有序“继替”。
第三,从文化系统的价值层面看,文化价值是文化的核心。人是生产实践活动和文化创造活动的主体。建筑、器物、制度是文化的承载形式。在中国社会的多重转型中,如果没有稳定的文化价值体系指引,支持社会长久发展的动力系统就会发生紊乱,社会转型也会发生断裂、失范、失序乃至变异。
汶川作为羌、藏、汉聚居区,各族在漫长的历史交往过程中,形成具有地域适应性和内在稳定性的信念、信仰、理想、价值文化系统。汶川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受中华文化的浸润、滋养,也不断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汶川在重建过程中,城乡与外界的联系将更加紧密与广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将呈现多元化趋势。
对汶川现代化进程起稳定、导向和催化作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需要确立、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人本理念,仁爱思想有利于现代社会人与人、人与社会秩序的建立。传统文化也需不断创新发展。中西文化中所蕴含的高度理性化因素与强烈的成就动机,是汶川现代化发展的有利因素。汶川城乡的现代化建设应关注人的尊严,保护人的生活热情,需要构建体现区域特色、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做出符合当地实际的文化调适,凝聚力量创造汶川“美好新生活”,形成中华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多元一体格局”。
二、汶川文化重建的内外条件
汶川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依赖于当地的现实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以及生产关系的优化、调整。二者共同为汶川发展提供基础。按照大致划分的社会生产力类型来看,自然形态的生产力、农业(畜牧业)生产力、工业生产力与信息生产力在历史上循序渐进发展,受各种因素制约,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并不可能均衡、充分发展。汶川经济、社会与文化表现出原生、次生、再生的复杂层次,加之地震灾难之后因家园毁损、亲友丧失等严重打击产生的精神改变,社会结构易出现分层加剧乃至断裂的危险,亟待教育和文化的双重整合,价值观重新确立。
在汶川重建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传统“乡土社会”如波纹一样一圈一圈推出去的“差序格局”叠加出纵横交错的“立体网络连接状态”。汶川城乡中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人,经济利益诉求和文化理念并不相同。传统社会结构沉淀出的价值观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为社会恢复秩序、争取发展机会创造了条件,但其中的消极因素也应剥离、剔除。
为弥合社会变迁中的分层和断裂,在赈灾的特殊语境下,政府成为建设的主要规划者和推动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指导作用,社会与民间的资本和技术力量成为最活跃因素,助推汶川重建与发展。但从长期发展考虑,必须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为汶川可持续发展提供内在动力。
首先,在规划、建设、建成的城市新区应尽可能完善城市的不同功能,为满足人的多样性需求创造条件,使传统的精神文化和现代的生活方式通过公共空间的营建得到沟通,使人们的精神获得慰藉。“想要理解城市,我们必须完整地涉及到城市不同用途的结合或混合用途,而不是单纯处理这些用途”[4]131。其次,通过文化与科技融合,利用现代通讯手段的便利,快捷的水陆空交通网络,内地与沿海、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空间距离大大缩短,农村对现代城市的文化隔膜与物质依赖相对减轻。
再次,汶川城乡文化重建离不开现代教育体系的支撑。城乡与地区发展不平衡,容易出现当地人才留不住、外地人才引进难的“通病”。为改变长期以来城市对乡村人才、资源的单向吸引状态,宜整合、引进中国乃至世界科研院所的优质教育资源,培育、引进并留住与汶川资源与发展阶段相匹配的文化、技术等人才,提高调动汶川社会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动员能力。
伴随中国整体经济的较快发展、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现代化教育体系的日益完善,凝结在城乡文化传统中的血缘、地缘、学缘、业缘关系,经过城市和乡村文化的“陶养”,可以通过家庭、亲属、学业、事业等发生转化,创新出具有时代特征的乡规民约或具有区域特色的社区文化内容,加速现代城乡社会的整合。
三、“以人为本”的文化价值重建
“以人为本”始终应该是汶川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政府的层面来说,发展汶川及周边地区的产业,要通盘考虑,不能只考虑经济和效率,更要兼顾社会公正、公平,尊重个体对自由和幸福的理解与愿望,动员城乡最广泛的力量和积极因素共同推动文化发展,带动乡村与城市共同发展。
只有城乡共赢,才能发挥出一个地区应有的潜力。对乡村资源、人才的掠夺式发展模式,将不能产生城乡建设的良性互动关系,地方建设就会失去最可靠的基础,社会的功能将会失灵,社会有机体也会遭到严重破坏。传统社会中,城市是在文化上享有优越地位的一方,但对于以农村占据国土广大面积的中国来说,不能对乡村的文化需求视而不见甚至歧视、漠视。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受到外力入侵与冲击而阻断,经过近百年以来的工业化努力,使得中国城乡在同一生产中逐渐有分工、有合作。
“中国现代化在20世纪下半叶才进入了真正的大转变时期。在新时期,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解体了,而来自苏联与美国的不同影响也都在损坏着民族文化传统并增添许多新的因素。在这种新形势下,传统与变革的关系与启动时期已大不相同。由于现代化的大环境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文化中受到制度与结构压抑的许多合理性因素才得以变成促进变革的条件;或转换原有的功能,变成现代经济增长的助力”[2]415。汶川在城乡建设中,城乡安置性建筑会改变原有社区和乡村的人口结构。在城市产业升级、转型和人才、技术、资金引进过程中,城乡文化要素通过生产、生活方式的互动,重新熔铸。城乡的权力结构、治理方式影响人口的行为方式和流动方向,文化移植与本土化冲突明显。需要从个人的行为选择变化、国家政策变迁、技术引进影响方面讲清楚汶川文化发展的根脉和变迁轨迹。
要解决因为个性的冲突而导致的矛盾,需要不断扩大社会分工合作的范围,以安全、繁荣的共同价值信念凝聚群体。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和技术“体用相连”。“一个健全的和能平衡的文化必须站在有机循环的基础上”[5]24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推动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现代技术不断重组,影响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文化随之发生改变。文化在新的社会格局中传承、创新、发展,要产生的社会认同,仍然要以人为目的,确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在费孝通先生提出的“美好社会”概念中,群体性生活不可缺少的意念“表现为诸如神话、传说、宗教、祖训、哲学和学说等多种多样形式的价值信念”,“体现了组成群体的各个人生活上追求的人生导向,而且也是群体用社会力量来维护人跟人相处的规范。它是个人的主观意识和群体社会律令内外结合的统一体”[6]126。面对复杂的社会变迁,现代化生产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人的“异化”会破坏社会有机体的完整,需要传统和现代文化、制度、法治的调控和保障,提高社会和个人的文化自觉。
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文化一方面要启蒙、教育个人对团体、社会的责任,一方面要教化、整合社会,强调对人的尊严、价值的肯定,加强人权保护。费孝通先生提出“活动、生活、社会三者要能结合得起来”。“在完整的社会里社会所要个人做的事,个人会认真觉得是自己的事”[7]241。
在文化价值体系确立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文化认同,形成最大限度的共识,有助于增强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巩固汶川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汶川羌、藏、回、汉各族对生命、自然、土地、社会、国家的认识,作为一种文化联系,维系着社会有机体的良性循环。与地理气候密切相关的生产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交往方式应得到传承和延续。至今依然起作用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应该被重新认识,并通过甄别、筛选加以创新、转化。具有地域、民族特色的习俗、乡规民约等应该得到尊重与保护,使之更适应人的情感需要,并能为经济发展创造一定的物质条件,使人的完满德性与幸福所依赖的外界条件得以匹配,使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条件。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费孝通江村经济[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
[2]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3] 周熙明.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意识形态创新//文化回归与价值重建[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
[4] [加拿大]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金衡山,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6.
[5] 费孝通.损蚀冲洗下的乡土//江村经济[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1.
[6] 费孝通.对“美好社会”的思考//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
[7] 费孝通.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乡土重建[M].长沙:岳麓书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