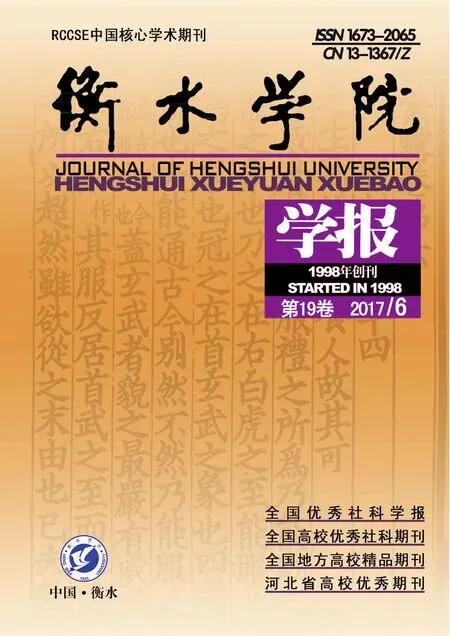董仲舒与汉代灾异理论的建构
鲍有为
董仲舒与汉代灾异理论的建构
鲍有为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董仲舒结合先秦以来的知识与理论,总结出了一套完整而有体系的灾异理论。董仲舒对“灾异”概念的诠释,不仅具有一定的逻辑抽象性,还把对灾异的诠释上升到了伦理学以及哲学的高度。灾异在董氏天人理论的支配之下,即是为了让人君意识到“天之不可不畏敬”,又是人君政治权利乃天授的显现。而他加入的阴阳学说,使得灾异不再是简单的违背自然客观规律的异象,而是天的意志对人的不满。然而灾异“偶然性”的出现,并未能打破这种认识,反而使人们更加注重对自身道德的关注。
董仲舒;春秋学;灾异;汉代
一、董仲舒与《春秋》灾异概念的界定
古人对灾异现象的关注,在先秦就已经出现,就连文字简洁的《春秋》经中也不乏天地灾异的记录,而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左传》中不仅记录灾异,更详细记录了时人对各种灾异现象的分析与研究,灾异的诠释方式很多已经与汉人相似。比如占星学的运用,灾异诠释的思维,与汉人有很多相似处,而且在诸多方面都体现出对灾异的重视。
当然,人们重视灾异现象的情况出现很早,但对“灾异”概念进行理性界定则相对较晚。应该说《穀梁传》《公羊传》是较早对灾异概念有所关注的。《穀梁传》《公羊传》中重视对《春秋》经灾异记录的阐释,这已经说明了传习者受到当时观念意识的影响,觉察到了灾异的重要,而且对灾异的探讨也具有了一定的抽象性。如《穀梁传》:
成公十有六年经:“春,王正月。雨木冰。”传:“雨而木冰也,志异也。传曰:根枝折。”
宣公十五年经:“冬,蝝生。”传:“蝝,非灾也。其曰蝝,非税亩之灾也。”
昭公九年经:“夏,四月,陈火。”传:“国曰灾,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闵陈而存之也。”
庄公十一年经:“秋,宋大水。”传:“外灾不书,此何以书?王者之后也。高下有水灾,曰大水。”
《穀梁传》中对“灾异”概念的界定比较模糊,“灾”“异”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别,当然很可能当时已经意识到灾异的不同,或由于语言的简洁导致文本中并未明确出现。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此时出现了对“灾”的概念性质的界定。昭公九年“国曰灾,邑曰火”,庄公十一年“外灾不书”这是从概念范围的大小来讨论的。相对于《穀梁传》的简洁,《公羊传》的诠释则比较清晰。最明显的就是《公羊传》对“灾异”的概念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如:
定公元年经:“冬。十月。陨霜杀菽。”传:“何以书?记异也。此灾菽也,曷为以异书?异大乎灾也。”
这里明确了“灾”“异”间的区别,即在文本的描述中,“异”所承载的意义要重于“灾”的意义。这种理解在传文他处有所运用,如:
文公二年经:“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传:“何以书?记异也。大旱以灾书,此亦旱也,曷为以异书?大旱之日短而云灾,故以灾书。此不雨之日长而无灾,故以异书也。”
据此可知,《公羊传》中对“灾异”概念的理解上升到了抽象性高度,但其在具体的文本叙述中,并未能真正贯彻这种理解。因此,“灾”“异”概念混用的情况非常多,如:
庄公十八年经:“秋,有蜮。”传:“何以书?记异也。”
僖公二十年经:“五月,乙巳,西宫灾。”传:“西宫者何?小寝也。小寝则曷为谓之西宫?有西宫则有东宫矣。鲁子曰:‘以有西宫,亦知诸侯之有三宫也。’西宫灾?何以书。记异也。”
哀公三年经:“五月,辛卯,桓宫僖宫灾。”传:“此皆毁庙也,其言灾何?复立也。曷为不言其复立?《春秋》见者不复见也。何以不言及?敌也。何以书?记灾也。”
桓公元年经:“秋,大水。”传:“何以书,记灾也。”
另外,我们从《穀梁传》以及《公羊传》中能够得知“灾”“异”概念所蕴含的天地现象并不单一,凡风、雨、彗星、雷电、动物、昆虫、大水、旱、火灾等天地间的各种现象都有可能成为“灾异”体现的载体。
其后董仲舒承续《公羊传》的理解,结合公羊学,阐述了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一套学术体系,其中对灾异概念的把握也远比《公羊传》《穀梁传》深刻。其在上武帝的对策中便对灾异产生的先后顺序作了简单的区分,他说: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1] 2498
又在《春秋繁露》中对灾异概念作了细致的分析,其云:
其大略之类,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2]259
此段文字是董氏灾异理论的精华,详细界定了“灾异”的概念。灾异根属于天地之物,其出现是为了体现天意之仁。很显然,董氏认为灾异是连接天人关系的一种方式,只不过这种方式并不惹人喜爱,他的出现让人敬畏。由此我们就会明白凡天地之物皆可与灾异产生关系。当然,“灾”“异”的区别董氏沿袭了《公羊传》的解释,即“异”大于“灾”,但同时董氏把“灾”“异”诠释成是天意的隶属,故在其天人感应的思维模式下,“灾异”被赋予了神秘性,让人敬畏。同样,灾异代表了天的意志,而天之意志的表现被诠释成为儒家的仁义,所以“灾异”又与人事间的道德伦理有密切关系,人们只有遵守这套道德标准,才不会遭致灾异的谴告。
当然,除却董氏的理解,我们还必须看到与董氏不同的说法。比如《洪范五行传》云:“凡有所害谓之灾,无所害而异于常谓之异。”[3]《公羊传·襄公九年》疏引《五行书》云:“害物为灾,不害物为异。”[4]此与董氏的理解完全不同,着重以“害物”作为区别灾、异的标准。另外,《白虎通·灾变》引谶纬曰:“灾之为言伤也,随事而诛。异之为言怪也,先发感动之也。”[5]268都与董氏的理解角度不同。当然,相较来说,这些只言片语仍旧无法与董氏的诠释相提并论。
因此,我们认为董氏对“灾异”概念的诠释,不仅有了一定的逻辑抽象性,而且还把对灾异的诠释上升到了伦理学以及哲学的高度。可以说,汉人对“灾异”的理解并未逃脱出董氏的思想范畴。如:
臣闻师曰,天左与王者,故灾异数见,以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惧,有以塞除,而轻忽简诬,则凶罚加焉,其至可必。[6]3359
臣伏思诸异,皆亡国之怪也。天于大汉,殷勤不已,故屡出祅变,以当谴责,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6]1999
我们根据《汉书》与《后汉书》等史料,可以判断出,汉人眼中的“灾异”涵括的内容十分多样化,不仅有日月星辰等天文星象,还有所谓的大气现象,比如云、气、虹、风、雷、雾、雪、霜、雹、霰、露等。这些都可以说是古代占星学的内容。另外,还有自然现象,比如草、木、石、山、飞禽走兽等。总之,凡天文地理皆可与灾异有关,这与《春秋》经中的灾异种类既有雷同,也有所增加。而且在汉人看来这些天地间的现象与人事具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他们格外重视日常生活中出现的一些异象。他们对灾异的理解并未脱离董氏的思维模式,皆注重灾异与人事的关联。如以谶纬为例,云:
凡异所生,灾所起,各以其政。变之则除,其不可变,施之亦除。(《易·稽览图》)[7]143
凡天象之变异,皆本于人事之所感。故逆气成象,而妖星生焉。(《春秋·元命苞》)[7]634
人合天气五行阴阳,极阴反阳,极阳生阴。故应人行以灾不祥,在所以感之。(《春秋·考邮异》)[7]986
二、灾异与天人关系
就公羊学来说,最早对灾异诠释的是《公羊传》,由此开启了公羊学诠释灾异的历史。具体来说,《公羊传》在理解灾异时,已经有很明显的天人感应观念在里面。我们可以举例子来说明。
僖公十五年经:“己卯,晦,震夷伯之庙。”传:“震之者何?雷电击夷伯之庙者也。夷伯者,曷为者也?季氏之孚也。季氏之孚,则微者,其称夷伯何?大之也。曷为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
此处意在说季氏专权,卑公室,故天降灾异以警戒季氏。
昭公二十五年经:“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传:“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众以逐季氏也。”
此即云以灾异与现实政治相附会。因此可以说《公羊传》已经突显了天人感应的观念,所以对灾异的理解要么说成是天之告诫,要么说成是天对人事政治的反应,天人之间的关系通过灾异得以展现。只是《公羊传》并未明确灾异背后的思想与理论,也没有形成所谓的系统。
当然这种天人关系支配下的灾异观念,很明显战国后期已经出现,比如《墨子·尚同中》说:
夫既尚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者,则天灾将犹未止也。故当若天降寒热不节,雪霜雨露不时,五谷不孰,六畜不遂,疾灾戾疫,飘风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罚也,将以罚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
《墨子》认为人当敬畏天命,否则会降下灾异。而为了避免灾异,就当遵守天意。因此很明显《墨子》的天人关系十分密切,而且与《公羊传》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基本上是一致的。另外,《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中有关时令的讨论,也是这种天人关系的体现。“这种思想认为,天子的政令应该配合自然界的四季运行,如果违反这种规则,就会导致灾异的发生”[8]。
这种天人相关论已经对灾异的诠释做出了理论上的指导,此指导意味着灾异这种所谓的自然天象并非是完全机械化的,而是在天、人发生关系后的产物。
另外,我们前面提到了儒家的天命观,这种天命观注重人的主体性以及能动性,也就是作为人必须自我主动地追求善,追求儒家道德伦理,从而合乎天命,顺应天命。而到了汉代的董仲舒,他在整合前人天人理论的基础上,重新诠释了天人关系。董氏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即是所谓的天人感应论。这种天人感应的理论,所探讨的仍不外乎是天道与人事的关系。而在讨论天、人关系时,董仲舒确立了天在这种关系中的神圣性与主导性,所谓神圣性是一种具有神秘主义倾向的天道观念,具有宗教的意味,这应是先秦早期天命观的遗存。
董仲舒在上武帝的对策中云: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
此文中所谓的自然现象并非是机械的存在,乃天命之所使,即在天的命令之下而出现的符应。这些受命之符,代表了具有意志且神圣的天。另外,对策又云:“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1]2515,这种唯有圣人可行天命的口吻,正是维持了天之神圣性的形象与观念。
而天的主动性在于这种意志的天对于人事之变化会做出相应的指示。这种指示,可以说就是天命的传递。所以董氏说: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1]2498
这里即是说天具有仁爱之心,即承认天包涵了人事间的道德伦理,如果人君不能遵循这种天道,就会必然遭到天的惩戒。当然,这种主动性的惩戒就是灾异的出现。这里董仲舒并未简单化灾异,而是进一步深入诠释了天道与灾异的密切关系。前面我们探讨了灾异概念的定义,即是这种性质的讨论。他说:
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
据此可知灾异的发生不仅是对人事的反映,还具有一种动态的过程,即灾异会随着人事的变化而变化。对于人君来说,行为越严重越恶劣,那么灾异的惩罚程度也越深。此体现了“天”的意志以及在此意志下对人事不满的主动性的反映。
董氏从这两方面奠定了天人关系中天的神圣地位,这种观念稳固了天的地位,确立了天的权威性,让人产生敬畏。所以董仲舒反复说道:
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1]2515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1]2501-2502
天人关系中,人处于次于天的等级地位,所以人必须敬畏且遵守天的旨意。在董仲舒看来,人并非是指所有人,而是特指帝王。帝王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遵循上天的意志。而上天的意志反映到帝王的身上,就是对帝王道德伦理、政治行为的关注。为此,董仲舒强调了天有教化人间的作用,他说:
性之名,非生与?如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性者,质也,诘性之质于善之名,能中之与?既不能中矣,而尚谓之质善,何哉?……性如茧、如卵,卵待覆而成雏,茧待缫而为丝,性待教而为善,此之谓真天。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2]291-300
在此董仲舒认为人性本非善,而为使民向善就必须依照天的旨意进行教化,那么为了实施这种教化,董氏便把帝王拉出来作为天意的授权者,这时的帝王便是神圣权威以及道德伦理的代表,他的出现是为了教化人民,引导人民向善。帝王被赋予执行人间教化的职责,因而帝王也就必须自己首先遵循天意,也就是说人君必须在道德和政治上做好人民的榜样,这样人民才能在人君领导之下向善。
总之在董仲舒天人关系的理论下,人君处在关键的环节,因此董仲舒针对帝王的行为进行了相关的探讨。正如《隋书·经籍志》所说:
然则圣人之受命也,必因积德累业,丰功厚利,诚著天地,泽被生人,万物之所归往,神明之所福向,则有天命之应。
人君之受命,必须积德累业才能上顺天道,下应民生。此点在《尚书大传》中也有很好的体现。据皮锡瑞的《尚书大传疏证》卷三记载,武丁时有飞雉升鼎而鸣,武丁问祖己,祖己曰:“雉者,野鸟也。不当升鼎,今升鼎者,欲为用也,远方将有来朝者乎?”故武丁内反求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编发重译来朝者六国。此即强调政治上修德便可应对灾异的出现。而如果人君做不到受命所应具备的要求,也就不能够遵守天意,那么灾异就成了制约人君的手段,通过灾异来劝谏和警告君主,天意不可违。
董氏以灾异作为劝告人君向善的方式,但灾异对人君的谴告有一个过程。就是当帝王违背天意时,意识到了灾异的警告,如果及时悔改,那么帝王将会继续享受天赋予的权利,继续统治国家。如果灾异降下后,并未自我约束自我改造,那么天将继续对帝王发出警告,最后如果人君一意孤行,“亡大道”,则将在天的意志下丧失手中的权力。董氏反复向帝王诉说灾异,意在“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因此董氏并非是借助灾异来恐吓人君,灾异的存在只是一种谴告,实质上对帝王的权利并没有本质上的伤害。所以董氏在上武帝策中提到了灾异,意并不在灾异,而是在说人君被赋予天之仁心,帝王作为万民的统治者,不仅承担教化,更是民心之体现:
传曰:天生之,地载之,圣人教之。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故君民者,贵孝弟而好礼义,重仁廉而轻财利,躬亲职此于上,而万民听生善于下矣。[2]320
人君的权利乃是上天的意志,面对天的提醒——灾异,君王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要时刻谨慎行事,以维护权利、稳定统治。然而董氏的灾异理论并非是顽固不化,灾异出现的层级性,不仅在明天之仁心,更是间接说明帝王在面对天意时,自身的主动性非常重要,只要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不当,自我悔改即是这种主动性的体现。“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响之应声。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饬身正事,思其咎谢,则祸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1]1273。对于人君“饬身正事”的主动性结果,上天便会出现“自然之符”,那就是灾异的反面——祥瑞。故董氏云:
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汉书·董仲舒传》)
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佑之,为生贤佐,后世称诵,至今不绝。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汉书·董仲舒传》)
灾异在董氏天人理论的支配之下,即是为了让人君意识到“天之不可不畏敬”[2]396,又是人君政治权利乃天授的显现。所以有学者说:“天道的作用完全没有抑制君主的权力,而是倾向于处于世界之外的作为思想家的分身的君主对万民的统治。”[9]80
三、灾异与阴阳
董氏在构建天人理论时,融入了所谓的阴阳五行学说,以阴阳五行作为天的构成,以与王道政治相一致而彼此影响。然天人感应的理论即是二者的理论核心,所以探讨二者须依据此理论展开。前面我们讲到了灾异是天的意志的体现,那么董氏把阴阳五行的概念引入到天道的建构中,从而体现天的意志,也就是说所谓的“人格的天(天志、天意)是依赖自然的天(阴阳、四时、五行)来呈现自己的”[9]150,董氏通过这种建构,把自然现象与天的意志结合起来,自然的客观规律成为天意的隶属,而对于人来说,人的道德伦理、政治制度乃至人的形体都是天通过阴阳五行的手段在人间实施的。如此一来,人事与自然相关联且相互影响,构成一个在天的意志下相互平衡、和谐的整体。这点在《淮南子》中也有所反映,其《要略》云:
天文者,所以和阴阳之气,理日月之光,节开塞之时,列星辰之行,知逆顺之变,避忌讳之殃,顺时运之应,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顺而不乱其常者也。
时则者,所以上因天时,下尽地力,据度行当,合诸人则,形十二节,以为法式,终而复始,转于无极,因循仿依,以知祸福,操舍开塞,各有龙忌,发号施令,以时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从事。
灾异作为自然现象,在这种理论下,就成为代表天意的阴阳五行与人事不和谐的产物,这种产物虽然仍是天的意志,但却是通过阴阳五行学说这一层面来推演的。因此我们便看到了汉人诠释灾异的一种独特现象,那就是以阴阳五行学说去阐释灾异现象,其中运用阴阳理论的现象尤为突出。可以说董氏运用阴阳五行理论构建的天人关系,突出了自然现象的重要性。而灾异作为特殊的自然现象,在儒家思想与阴阳五行论结合之后的天人感应观念之影响下,让人了解到了灾异对人事的警告,因为此时的灾异不再是简单的违背自然客观规律的异象,而是天的意志对人的不满。正如学者李泽厚所说,董氏的特点在于“相当自觉地用儒家精神改造了、利用了阴阳家的宇宙系统”[9]161。阴阳家本来就重视时令与人事的关系,这点《史记·太史公自序》已经说道: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这里司马迁总结了阴阳家利用自然规律,使人拘而多畏,可知此说在当时对人来说是有一定的约束效力的,而灾异可以说即是所谓的“逆之者不死则亡”的自然异象。董氏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了阴阳家的学说,正是借鉴了阴阳家对时令的强调。在董氏的天人理论下,“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变得更加重要,失去了,轻者有灾异的出现,重者便会亡国。《春秋繁露》云:
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气也,故生;秋,怒气也,故杀;夏,乐气也,故养;冬,哀气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有其理而一用之,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故为人主之道,莫明于在身之与天同者而用之,使喜怒必当义而出,如寒暑之必当其时乃发也。[2]341
因此对人君来说,灾异成为他们不可忽视的异象。而对于统治下的士大夫来说,灾异不仅是评判人君统治的“晴雨表”,更是自我抱负展现的一种手段,他们借灾异以评判时政,袒露自己对帝王乃至国家社会的见解。
四、灾异观念的紧张性
虽然按照董氏的理论,人君“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汉书·董仲舒传》)。但有时一些灾异现象并不能按照此理论来诠释。董仲舒针对此问题做了解答,他说:
故圣王在上位,天覆地载,风令雨施,雨施者,布德均也,风令者,言令直也。……禹水汤旱,非常经也,适遭世气之变而阴阳失平,尧视民如子,民视尧如父母,《尚书》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四海之内,阏密八音三年。”三年阳气厌于阴,阴气大兴,此禹所以有水名也。桀,天下之残贼也;汤,天下之盛德也。天下除残贼而得盛德大善者,再是重阳也,故汤有旱之名,皆适遭之变,非禹汤之过。毋以适遭之变,疑平生之常,则所守不失,则正道益明。[2]348-349
《白虎通》沿袭了董仲舒的理解:
尧遭洪水,汤遭大旱,亦有谴告乎?尧遭洪水,汤遭大旱,命运时然。[5]270
后来王充在其《论衡》中便把灾异分为政治之灾与无妄之灾。《论衡·明雩》云:
问:“政治之灾,无妄之变,何以别之?”曰:“德酆政得,灾犹至者,无妄也;德衰政失,变应来者,政治也。夫政治,则外雩而内改,以复其亏;无妄,则内守旧政,外修雩礼,以慰民心。故夫无妄之气,历世时至,当固自一,不宜改政。”[10]671-672
所谓政治之灾即是董氏所强调的灾异,而无妄之灾即是董仲舒所说的偶然性的灾异。《孔丛子》也有此论:
建初元年大旱,天子忧之,侍御史孔子丰乃上疏曰:“臣闻为不善而灾报,得其应也;为善而灾至,遭时运也。陛下即位日浅,视民如伤,而不幸耗旱,时运之会耳,非政教所致也。昔成汤遭旱,因自责,省畋散积,减御损食,而大有年。意者陛下未为成汤之事焉。”天子纳其言而从之,三日雨即降。转拜黄门郎,典东观事。[6]3278
严遵《老子指归》也涉及了此论:
遭遇君父,天地之动,逆顺昌衰,存亡及我,谓之遭命。
谷神子注:“偶然所遇,非常定也。”[11]可见汉人虽然注重灾异的出现,但他们在灾异的理解上并非顽固不化,这里面很明显也有一定的变通性。当然变通性理解是在违背常规思路的基础上展开的。如果一旦在向善的情况之下,灾异还会出现,这就违背了灾异出现的正常模式,此时人便会产生疑虑。《后汉书·儒林传》曾记载一事,云:
时县连年火灾,昆辄向火叩头,多能降雨止风。徵拜议郎,稍迁侍中、弘农太守。先是崤、黾驿道多虎灾,行旅不通。昆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负子度河。帝闻而异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为光禄勋。诏问昆曰:“前在江陵,反风灭火,后守弘农,虎北度河,何行德政而致是事?”昆对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质讷。帝叹曰:“此乃长者之言也。”顾命书诸策。乃令入授皇太子及诸王小侯五十余人。[6]2550
这种所谓的偶然性,是建立在以道德伦理作为评判标准的基础上。而董仲舒等汉代的知识分子接受了流行的灾异观念,这种观念强调道德伦理的重要,所以一旦所谓的异象发生在现实中具有仁善德性的人身上时,正常的灾异观念便失去了诠释的效力,因为这与世人的灾异观念发生了冲突。而在当时的思维状态下,人们不会运用科学的思维去解释,但仍然会寻求一个答案,而解答的方式仍是转移到天命上来,也就是孔子以来的儒家所强调的天命,面对天命的不可知,唯有敬畏。因此对于无妄之灾,也是命运之使然,与现实无关。所以,在汉人的眼中,这种偶然性的解读,并非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纯粹的自然现象,而仍是一种神秘主义的解读。通过这种解读,方可缓解这种观念的紧张性。所以王符说:
凡人吉凶,以行为主,以命为决。行者,己之质也;命者,天之制也。在于己者,固可为也;在于天者,不可知也。[12]301
司马迁在其《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道: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太史公在以一种较为理性的思维来评判各家学说,即他看到了这种学说背后的不合理性。这种不合理性即包括阴阳学说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就是过分夸大了违背自然后的惩罚的严重性,所以说“未必然也”。可以说正是在阴阳学说的影响之下,汉人普遍接受了“逆之则亡”的灾异观念。在此观念支配下,对于自然现象,总要关联到人事上。如此一来,灾异的出现便会让人“拘而多畏”。而士人所谈到的灾异现象的偶然性,其实正是太史公所强调的“未必然也”。在太史公看来,所谓的自然时令,不过是顺应自然以合乎天道,而天道便是人所应当效法的,是治理天下的纲纪。因此,作为人君亦当遵守天道,以明天道乃天下之人效法的准则。太史公对于阴阳学说逻辑下的惩罚性后果,给出了很好的解释。而灾异观念有时让人产生了过度的敬畏,从而会导致人们对于所谓的自然现象产生了过度的敏感。在司马迁看来,他认为我们应该关注“天下之纲纪”,遵守天道,对于那些所谓的异象,不要过分关注,但这并不能代表他不重视自然异象。其实司马迁与后来的士大夫们一样,并未能直接解答灾异的偶然性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对于自然的理解有一个思维定式,那就是天人关系的发生是靠自然现象来传达的。所以,在此思维定式之下,这种灾异观念的矛盾与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但他们不会如同今人一样说这是纯粹的自然现象,他们总要把这种矛盾溯源到天命的高度,如此一来就会得到所有人的赞同,因为毕竟天是神圣而令人敬畏的。所以在汉人对天人关系的无比重视下,他们给出的答案却总是如此的一致,我们也就不必奇怪了。
王充虽然把灾异区分为政治之灾与无妄之灾,但他对于无妄之灾的理解却不同于当时的主流观念。其《论衡·自然》云:
诰誓不及五常,要盟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五伯。德弥薄者信弥衰。心险而行胆,则犯约而负教;教约不行,则相谴告;谴告不改、举兵相灭。由此言之,谴告之言,衰乱之语也,而渭之上天为之,斯盖所以疑也。[10]784
在这里王充把人们所认为的谴告观念,说成是衰乱之言,也就是说谴告只是时人争斗的利用工具,而与所谓的天道无关。因此据此思路可知,所谓的灾异观念支配下的对人事的谴告,也有这种功利性的倾向。可见王充以辩证理性的角度,看到了灾异观念的盲目性,这种盲目不仅出自人对天的敬畏,更是在利益驱使下,用神道设教的手段去蛊惑人心。然而汉代出现的道教典籍《太平经》却给出了一个较为圆融的解答,其云:
凡人之行,或有力行善,反常得恶,或有力行恶,反得善。……力行善反得恶者,是承负先人之过,流灾前后积来害此人也。其行恶反得善者,是先人深有积蓄大功,来流及此人也。能行大功万万倍之,先人虽有余殃,不能及此人也。[13]
道教以承负说劝人行善德,从而免除灾异,以求福报。而对于现世中人行善而反得恶报者,归因于先人之过错大于现世中人的行善,只有当现世中人所行之善超过先人之过时,才会有所谓的福报。当然,相反,现世所行之恶未能超过先人之行善大功,也不会遭来灾害报复。
儒家虽无此说,但仍旧是会把灾异的探讨聚焦在人的善恶德性上来。比如东汉的王符认为若要求福,人之自身的德义才是最重要的:
巫觋祝请,亦其助也,然非德不行。巫史祝祈者,盖所以交鬼神而救细微尔,至于大命,末如之何。……不若修己,小心畏慎,无犯上之必令也。故孔子不听子路,而云“丘之祷久矣”。孝经云:“夫然,故生则亲安之,祭则鬼享之。”由此观之,德义无违,鬼神乃享;鬼神受享,福祚乃隆。故诗云:“降福穰穰,降福简简,威仪板板。既醉既饱,福禄来反。”此言人德义美茂,神歆享醉饱,乃反报之以福也。[12]302
总之,一旦出现不同于常规灾异思维的现象,人们都会采取各种方式去弥补这种矛盾的观念,但并不能够给出较为理性的解释,因为他们对灾异的理解的出发点是神秘而非理性的,所以汉人无论怎样解释,都无法摆脱这种矛盾的困境。
[1] 班固.汉书[M].北京 :中华书局,1962.
[2]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
[3] 李昉,李穆,徐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3876.
[4] 贾公彦.春秋公羊传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492.
[5] 陈立.白虎通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4.
[6]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7]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8] 沟口雄山,小岛毅.国的思维世界[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58.
[9]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10] 黄晖.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2.
[11] 樊波成.老子指归校笺[M].北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1.
[12] 彭铎.潜夫论笺校正[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3] 王明.太平经合校[M].北京:中华书局,1960:22.
(责任编校:卫立冬 英文校对:吴秀兰)
Dong Zhongshu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alamity Theory in the Han Dynasties
BAO Youwei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321004, China)
Dong Zhongshu summarizes a set of complete and systematic calamity theory based on the knowledge and theories since the Pre-Qin Period. His interpretation of calamity not only has some logical abstraction but also has risen to the height of philosophy and ethics. Under the domination of Dong Zhongshu’s the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ven and man, not only does the calamity theory make the rulers realize that Heaven can not be defied, it also embodies that the political rights of the rulers are given by Heaven. And according to his Yin-Yang theory, calamity is no longer the simple unusual phenomenon that goes against the objective natural law but the dissatisfaction of the will of Heaven with human beings. However, the “accidental” calamity does not make people eliminate such kind of understanding but make them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ir own morality.
Dong Zhongshu; studies on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calamity; the Han dynasties
10.3969/j.issn.1673-2065.2017.06.005
鲍有为(1986-),男,山东济宁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浙江省哲学社会规划课题(18NDJC269YB)
B234.5
A
1673-2065(2017)06-0029-08
2017-0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