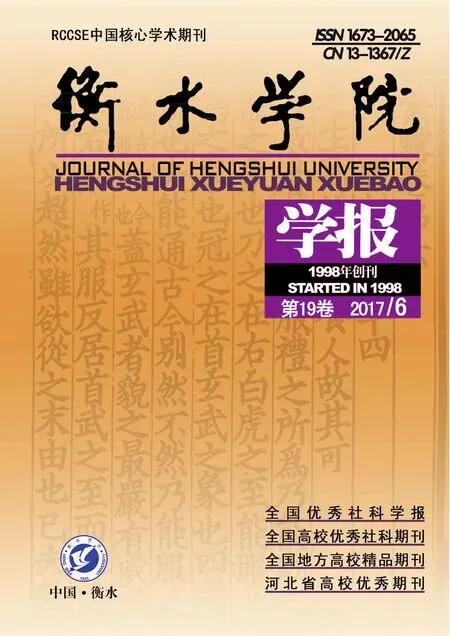董仲舒的心学:以其引《春秋》与《诗》为基础的探讨
张丰乾
董仲舒的心学:以其引《春秋》与《诗》为基础的探讨
张丰乾
(中山大学 哲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董仲舒作《春秋繁露》,对《春秋》大义做了多重阐发,并多次同时引用《春秋》与《诗》,其论说方式既注重文辞词意的追溯和引申,亦注重义理原则的推演和阐发,颇值得仔细考究。此种论说方式并非简单地引经据典或断章取义,而是和董仲舒的思想基础——心学息息相关。董仲舒仔细分别“心”比之于“礼”,“志”比之于“物”的重要性和优先性,重申了“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提出了“尊礼重信”,基于“良心”“察视其外,可以见其内”“贱其无人心”。认为自然灾异使人警醒,同样体现了“天心之仁爱”,认为《春秋》无通辞、无常辞的根本原因就是要分辨和判断当事人的用心。凡此种种,都和孔孟思想一脉相承而又在多方面做出了发展;同时他的论述又和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评价结合起来,构建了新的思想体系。
董仲舒;心;志;《春秋》;《诗经》
一、世道衰微,《春秋》屡被采编引用的背景
孟子有言:“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这说明了孔子作《春秋》是出于忧患和不得已而为之,而依据礼法,作《春秋》是天子之事,故而孔子断定理解他和怪罪他的原因都是因为他所编修的《春秋》。但孟子显然是拥护孔子的,他指出了孔子作《春秋》的背景:“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其中的“《诗》亡”并非指《诗》的文本的消失,而是在诸侯争霸、大夫专权的情形下,《诗》的规约和教化功能消失殆尽,孔子一方面在民间坚持“以《诗》《书》《礼》《乐》教”,同时修《春秋》,其效果是“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认为这是与“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相提并论的功绩(《孟子·滕文公下》)。但如前文所引孟子之言,多个诸侯国都有类似于鲁国《春秋》的史书。司马迁对于《春秋》一书的写作背景有更系统的介绍:
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呜呼,师挚见之矣!纣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襃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可见,在多种《春秋》之中,以孔子所编修的鲁国《春秋》影响最大。孔子最杰出的弟子群体“七十子之徒”以为《春秋》所蕴含的批判精神如果形成文字可能会招致危险,所以口耳相传;但左丘明又担心众弟子意见分歧且在传授过程中添加私意,所以根据孔子所参照的史书,编写了《左氏春秋》。此后《春秋》在楚、赵、秦诸国都有被各取所需,另行编排的情况;而著名的思想家们也往往摘引其中的内容来构建自己的体系,直至西汉,董仲舒成为其中的集大成者。
董仲舒以“目不窥园”的精神研习经典,在担任上大夫时,演绎《春秋》所蕴涵的意义,著成系列作品,尤以《春秋繁露》一书流行于世。该书内容丰富,思想深刻,条理清晰,奠定了董仲舒在学术上成为儒者领袖的地位①。
尽管孟子业已指出“《诗》亡然后《春秋》作”,但董仲舒的视野并非仅仅局限于《春秋》。在《春秋繁露》中,读者很容易发现董仲舒《诗》与《春秋》并引的论说方式——此种论说方式并非简单地引经据典或断章取义,而是和董仲舒的思想基础——心学相关。
二、“尊礼重信”,基于“良心”
《春秋·昭公十二年》记载:“晋伐鲜虞。”《穀梁传》解释:“其曰晋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与夷狄交伐中国?故狄称之也。”鲜虞是北狄的一支,但和晋一样,也是姬姓,却受到晋国的侵犯。《春秋》对鲜虞给予同情而谴责晋国,超越了种族差异,引起论者的疑问:
《春秋》曰:“晋伐鲜虞。”奚恶乎晋,而同夷狄也?曰:“《春秋》尊礼而重信,信重于地,礼尊于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疑礼而死于火,齐桓公疑信而亏其地,《春秋》贤而举之,以为天下法,曰礼而信。礼无不答,施无不报,天之数也。今我君臣同姓适女,女无良心,礼以不答,有恐畏我,何其不夷狄也?!公子庆父之乱,鲁危殆亡,而齐桓安之,于彼无亲,尚来忧我,如何与同姓而残贼遇我?《诗》云:‘宛彼鸣鸠,翰飞戾天。我心忧伤,念彼先人②。明发不昧,有怀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晋不以同姓忧我,而强大厌我,我心望焉,故言之不好,谓之晋而已,婉辞也。”(《春秋繁露·楚庄王》)
董仲舒认为,“尊礼重信”是《春秋》所推崇的重要原则,即坚持认为信用比土地更重要,礼仪比生命更尊贵。宋恭公的夫人伯姬因坚持“妇人之义,保傅不俱,夜不下堂”的原则而被火烧死③;鲁庄公三十年,齐桓公把汶阳这个地方让给鲁国并在柯邑(今山东东阿)签署盟约④,这些行为具有典型意义;而“尊礼重信”的根源在于“良心”。文中的“疑”为“定”‘止’“凝”之意[1],亦即“固执”之意。董仲舒举例说鲁国遭受庆父之乱而处于危机之中,齐桓公和鲁国没有亲缘关系尚且能够帮鲁国分担忧患,去除内乱,安定内政[2]。以此观照,怎么可能发生是同姓却加以侵犯的事情?他阐释说晋国之作为令人厌恶,而鲜虞的遭遇则令人同情。何休《春秋公羊学解诂》持同样观点:
谓之“晋”者,中国以无义故为夷狄所强。今楚行诈灭陈、蔡,诸夏惧。然去而与晋会于屈银,不因以大绥诸侯,先之以博爱,而先伐同姓,从亲亲起,欲以立威行霸,故狄之。(《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二十二)
《左传》对于经文中的“伐”没有异议。可见《春秋》三传的注疏者们立场一致,都是突出对晋伐鲜虞的谴责,其中超越种族的感情基础就在于由《诗经·小雅·小宛》所引发的“与我同忧”的同情心。董仲舒基于“人皆有此心”的理论预设,批评晋的作为不仅没有同情心,还以自恃强大而忘记同姓相助的伦理,是违背礼俗,没有良心的做法。但《春秋》的记载用了“伐”和“狄”这样的贬义词来委婉地表达了对晋的不满。后代学者更把这一论题演变为民族国家的认同问题[3],但却忽视了董仲舒对于“良心”及“人皆有此心”的突出,而董仲舒所引诗句“念彼先人”和“明发不昧”则是强调执政者应该不忘祖先,觉醒发悟⑤。
三、“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论事重“志”
董仲舒主张“深察名号”,他指出《春秋》之中的不同形式的提问和应答成百上千,都是可以演绎援引进行类比的:
《春秋》赴问数百,应问数千,同留经中,翻援比类,以发其端,卒无妄言,而得应于传者;今使外贼不可诛,故皆复见,而问曰:“此复见,何也?”言莫妄于是,何以得应乎?!故吾以其得应,知其问之不妄;以其问之不妄,知盾之狱不可不察也。夫名为“弑父”,而实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为“弑君”,而罪不诛者,逆而距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语盾有本,《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无邻,察视其外,可以见其内也。(《春秋繁露·玉杯》)
董仲舒以赵盾被冠以“弑君”的例子来说明个人的责任会被别人推理出来,不能逃脱。同时,如余治平所言,类似的事例频频发生,“《春秋》一定会再以另一种属辞方式灭之、绝之”[4]。何以如此?董仲舒引用《诗经·小雅·巧言》“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之句作答,以说明万事万物都有邻近的东西可以类比,观察其外在的表现,可以知道其内在的属性。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的另外一种情况是“贱其无人心”:
《春秋》讥文公以丧取。难者曰:“丧之法,不过三年,三年之丧,二十五月。今按经:文公乃四十一月方取,取时无丧,出其法也久矣,何以谓之丧取?”曰:“《春秋》之论事,莫重于志。今取必纳币,纳币之月在丧分,故谓之丧取也。且文公以秋祫祭,以冬纳币,皆失于太蚤,《春秋》不讥其前,而顾讥其后,必以三年之丧,肌肤之情也,虽从俗而不能终,犹宜未平于心。今全无悼远之志,反思念取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讥不出三年于首而已,讥以丧取也;不别先后,贱其无人心也。”缘此以论礼,礼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节具,则君子予之知礼;志和而音雅,则君子予之知乐;志哀而居约,则君子予之知丧。故曰非虚加之,重志之谓也。(《春秋繁露·玉杯》)
“贱”这种“春秋笔法”也用于批评“无善善之心,而轻救民之意”的行为,哪怕是面对夷狄和中国的分别,也要坚持这个原则:
《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至邲之战,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夫庄王之舍郑,有可贵之美;晋人不知其善,而欲击之,所救已解,如挑与之战,此无善善之心,而轻救民之意也,是以贱之,而不使得与贤者为礼……”(《春秋繁露·竹林》)
董仲舒强调善良之心如果没有得到推崇,爱民之意如果没有得到重视,即便是晋国这样的“中国”,也会被轻贱。
《春秋》一般被当作是鲁国的史书,以记事为主,但董仲舒强调指出:“《春秋》之论事,莫重于志。”“《春秋》之好微与,其贵志也。春秋修本末之义,达变故之应,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极者也。”(《春秋繁露·玉杯》)鲁文公虽然没有在为鲁僖公居丧三年(实际时间二十五个月)期间办理婚娶,但是婚娶的前奏纳币却是在居丧期间办理,而且又赶在秋天集中办理祭祀,随即在冬天举行纳币之礼,都是过早行事。董仲舒认为《春秋》评论事件,最看重的是行事者的心志,居丧三年也未必能使哀痛之心平复,而文公全然没有追悼先人的志向,反而惦记婚娶之事,是《春秋》特别痛恨的。董仲舒还解释说,《春秋》所讥讽的“不出三年”,是指该事件的起始时间,而没有区别事件发生的先后次序,是出于当事人没有人心而轻贱他。此处的“人心”指子女对于父母的追思哀悼之心,此种人心要体现在守丧三年的具体礼仪上。
董仲舒进而指出,根据《春秋》记事最看重当事人心志的方式,可知礼仪所看重的也是心志。恭敬、平和、哀痛的心志用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就会被君子评价为“知礼”“知乐”“知丧”。董仲舒还用“质”和“文”的关系来论述“志”和“物”的关系:
志为质,物为文,文着于质,质不居文,文安施质;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文质偏行,不得有我尔之名。俱不能备,而偏行之,宁有质而无文,虽弗予能礼,尚少善之,介葛卢来是也;有文无质,非直不予,乃少恶之,谓州公寔来是也。然则《春秋》之序道也,先质而后文,右志而左物,故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亦宜曰:朝云朝云,辞令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引而后之,亦宜曰:丧云丧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贵志以反和,见其好诚以灭伪,其有继周之弊,故若此也。(《春秋繁露·玉杯》)
董仲舒认为“质文两备”是礼仪得以完成的条件,如果有偏颇,“你”“我”这样的名称都不能使用(以保持双方均衡);如果非要施行,则宁可有质朴而没有文饰,虽然不能评价为“能礼”,但尚且可以稍加赞许,如用“来”,记叙东夷介国国君到鲁国的事情;而用“寔来”(这个人来了)记叙州国国君到曹国的事,是因为州国国君借用“朝”的名义来指责曹国。但这些都是特例,就总体原则而言,《春秋》讲述道理还是“质”优先于“文”,“志”优先于“物”。
董仲舒仔细分别“心”比之于“礼”,“志”比之于“物”的重要性和优先性,和孔孟思想一脉相承;同时他的论述又和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评价结合起来,构建了新的思想体系。
四、《春秋》之旨,精心达思者能知
“春秋无义战”为读者所熟知,孟子有言:“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孟子·尽心下》)然而免不了“总有正义之战”的质疑。董仲舒以《春秋》所记的灾异之中,虽然田地里有零星的庄稼,还是用“无麦苗”来记叙为例,说明《春秋》的言辞是根据所记述对象的不同而有变化,总体的原则是“敬贤重民”:
曰:“……秦穆侮蹇叔而大败,郑文轻众而丧师,《春秋》之敬贤重民如是。是故战攻侵伐,虽数百起,必一二书,伤其害所重也。”问者曰:“其书战伐甚谨,其恶战伐无辞,何也?”曰:“会同之事,大者主小,战伐之事,后者主先,苟不恶,何为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恶战伐之辞已!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旧,意在无苦民尔;苦民尚恶之,况伤民乎!伤民尚痛之,况杀民乎!故曰:凶年修旧则讥,造邑则讳,是害民之小者,恶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恶之大也,今战伐之于民,其为害几何!考意而观指,则《春秋》之所恶者,不任德而任力,驱民而残贼之;其所好者,设而勿用,仁义以服之也。《诗》云:‘弛其文德,洽此四国。’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亲近,而文不足以来远,而断断以战伐为之者,此固《春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难者曰:“《春秋》之书战伐也,有恶有善也,恶轴击而善偏战,耻伐丧而荣复雠,奈何以春秋为无义战而尽恶之也?”曰:“凡《春秋》之记灾异也,虽亩有数茎,犹谓之无麦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战攻侵伐,不可胜数,而复雠者有二焉,是何以异于无麦苗之有数茎哉!不足以难之,故谓之‘无义战’也。以无义战为不可,则无麦苗亦不可也;以无麦苗为可,则无义战亦可矣。若《春秋》之于偏战也,善其偏,不善其战,有以效其然也。《春秋》爱人,而战者杀人,君子奚说善杀其所爱哉!故《春秋》之于偏战也,犹其于诸夏也,引之鲁,则谓之外,引之夷狄,则谓之内;比之轴战,则谓之义,比之不战,则谓之不义;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谓善盟;战不如不战,然而有所谓善战;不义之中有义,义之中有不义;辞不能及,皆在于指,非精心达思者,其庸能知之?!《诗》云:‘棠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由是观之,见其指者,不任其辞,不任其辞,然后可与适道矣。(《春秋繁露·竹林》)
董仲舒反复申论《春秋》爱人而反战的原则,言辞激切地指出苦民、伤民、杀民的行为危害性均难以接受。《春秋》所特别痛恨的事情是德行没有亲和力,文化缺乏吸引力。他认为《诗经》中所云的“弛其文德,洽此四国”⑥,也是《春秋》所赞扬的。虽然在具体战斗中“义”与“不义”相互包含,但判断战争的性质,还是要像孔子论《诗经》时所说的要返回头去,重新审视思考,“精心达思”,以揭示其宗旨。
“精心”一词,出现于西汉,“精心达思”即“精心致思”,心思专精、思维通达之义,汉武帝即位后下诏:“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在向汉武帝的对策中还引用过。
五、惨怛不忍之心,《春秋》大之
有人以楚国司马芈子反在内把持政权,在外侵夺君主美名却被推崇为例,质疑《春秋》褒贬人物的原则。董仲舒指出了芈子反恻怛仁爱等值得推崇的品行;而问者不肯罢休,又进一步指出与芈子反相同的行为都被谴责,芈子反不应例外。董仲舒也具体阐发说《春秋》之道,“常”和“变”应用的对象不同,其侧重点也不一样:
“司马子反为君使,废君命,与敌情,从其所请,与宋平,是内专政,而外擅名也。专政则轻君,擅名则不臣,而《春秋》大之,奚由哉?”曰:“为其有惨怛之恩,不忍饿一国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远之为大,为仁者自然为美。今子反出己之心,矜宋之民,无计其闲,故大之也。”难者曰:“《春秋》之法,卿不忧诸侯,政不在大夫。子反为楚臣,而恤宋民,是忧诸侯也;不复其君,而与敌平,是政在大夫也。湨梁之盟,信在大夫,而《春秋》刺之,为其夺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夺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闲也。且《春秋》之义,臣有恶擅名美。故忠臣不显谏,欲其由君出也。《书》曰:‘尔有嘉谋嘉猷,入告尔君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此谋此猷,惟我君之德。’此为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今子反去君近而不复,庄王可见而不告,皆以其解二国之难,为不得已也,奈其夺君名美何!此所惑也。”曰:“《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变用于变,常用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今诸子所称,皆天下之常,雷同之义也;子反之行,一曲之变,独修之意也。夫目惊而体失其容,心惊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于惊之情者,取其一美,不尽其失。《诗》云:‘采葑采菲,无以下体。’此之谓也。今子反往视宋,闻人相食,大惊而哀之,不意之至于此也,是以心骇目动,而违常礼。礼者,庶于仁,文质而成体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着其礼,方救其质,奚恤其文,故曰:‘当仁不让。’此之谓也。《春秋》之辞,有所谓贱者,有贱乎贱者,夫有贱乎贱者,则亦有贵乎贵者矣。今让者,《春秋》之所贵;虽然,见人相食,惊人相爨,救之忘其让。君子之道,有贵于让者也,故说《春秋》者,无以平定之常义,疑变故之大,则义几可谕矣。”(《春秋繁露·竹林》)
董仲舒引用《诗经·邶风·谷风》“采葑采菲,无以下体”之句说明诸子所主张的理论,都是普遍适用的原则,而芈子反的行为则是个别的变通做法,不能拘泥于一般原则去评判。如周桂钿先生所论:“在这里,董仲舒把仁爱的原则看得高于君和政。只要确实符合仁爱原则,专政、轻君都无不可。不但不应贬抑,而且还要赞扬。”[5]
“惨怛”即“恻怛”,犹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董仲舒认为这是《春秋》所看重的原则。董仲舒还以“当仁不让”为由,说明在特殊情况下,不能以约定俗成的原则来怀疑真正符合仁义的行为,尤其是涉及发生人道危机以至于人吃人的情况下。
六、“天心之仁爱”与取向“圣化”
董仲舒在给汉武帝的《对策》中,同样注重《春秋》和《诗》《书》的相互发明,并特意突出自然灾异使人警醒,同样体现了“天心之仁爱”:
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本人就是“目不窥园”“强勉学习”的典范。他引用《诗经·大雅·烝民》中“夙夜匪解”的诗句和《尚书大传·周传》中所记周公之言“茂哉,茂哉”来说明“强勉”的必要。
对于“六艺之学”,在《春秋》和《诗》之外,董仲舒并不是轻视其他四个方面,而是对它们各自的优长做了阐发,并明确表示了自己的价值取向:
君子知在位者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能兼得其所长,而不能遍举其详也。故人主大节则知闇,大博则业厌,二者异失同贬,其伤必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齐时蚤晚,任多少,适疾徐;造而勿趋,稽而勿苦,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劳,而身大成,此之谓“圣化”,吾取之。(《春秋繁露·玉杯》)
从中也可以看出董仲舒的远大抱负。
《史记·儒林列传》记载:“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缪西王。’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脩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瑕丘江生为《穀梁春秋》。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可见,董仲舒治《春秋》以公羊氏为宗而成一家之言,并影响到了《穀梁春秋》。
《春秋繁露》之中,分别引《春秋》与《诗》,及《春秋》与《诗》共同引用的例子还有几处,都体现了董仲舒价值追求的高远与论说方式的周密,值得进一步仔细探究,从而对董仲舒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重新予以估计。董仲舒的著述,非常重视文辞意涵的追究和引申,但是他更为看重的是言行文辞的用心所在。董仲舒所主张的“常”,根源就在自觉主动、良好仁爱的“心”。
在心志方面,董仲舒还特别强调“强勉”:
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习,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汉书·董仲舒传》)
“强勉”在这个语境中是一种高度的自觉。但劳思光先生认为:“孔孟儒学,原以心性为主。……汉儒昧于心灵之自觉义,只在一粗陋宇宙论架构中处理哲学问题;故心性论问题在汉儒手中遂裂为两问题,而各有一极为可笑之处理。”“心性论所涉及之价值问题,在汉儒学说中,化为‘天人相应’的问题。”[6]殊不知,董仲舒既讲述人心,又注重天心,其人性论更是影响深远。而董仲舒引用《诗》《书》所突出强调的“强勉”既包括主动努力的“学习”,也包括主动努力的“行道”,不正是“心灵自觉”的全面落实吗?劳先生所界定的“心性”,未免过于狭隘了!
正如冯达文先生所评论的:“劳思光先生只认孔孟心性之学为唯一判准,而傲视其他思想派别,所强调的则是自己认定的主体的至上性。”劳思光之前,“牟宗三先生就称,董仲舒是宇宙论中心,他把道德基于宇宙论,要先建立宇宙论,然后才能讲道德,这是不行的,这在儒家是不赞成的。依此,牟先生实际上把董仲舒开除出儒家行列。徐复观先生三卷本《两汉思想史》对思想个案研究做得非常细致,但是在评价上亦说,董仲舒以及两汉思想家所说的天人关系,经受不起合理主义的考验。”⑦
现当代一些著名的学者之所以对董仲舒有偏见,也出于一种狭隘的理性观,特别贬低他的宇宙论。然而,如冯达文先生所论:“世界上许多大的宗教,都是靠神话传播信念,有的还靠权力支撑起来。比较之下,董子没有创世纪,也没有编织许多神话故事。他引入宇宙论,以为我们依一年四季的变迁付出努力,就可以成就价值,这其实是很理性的。”⑧
同时,在宇宙论之外,董仲舒的心学也是值得探讨的;除了打破沿袭已久的“前识”以外,对于董仲舒著作的精细研读和系统把握也很有必要。我们还需要注意到董仲舒《诗》与《春秋》等经典并引的行文特点——他也不是狭隘的公羊学家。其心学与人性论的关系问题则需要另文讨论。
[1]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6.
[2] 何休,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946.
[3] 李帆.“夷夏之辨”之解说传统的延续与更新——以康有为、刘师培对《春秋繁露》两事的不同解读为例[J].近代史研究,2011(6):93-101.
[4] 余治平.董仲舒《春秋》辞法十举[J].衡水学院学报,2016(3):2-9.
[5] 周桂钿.周桂钿文集·秦汉思想研究:五[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272-273.
[6]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16-17.
(责任编校:卫立冬 英文校对:吴秀兰)
①刘向评价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刘歆虽然不认可这一点,但也承认:“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汉书·董仲舒传》)《汉书·五行志》亦言:“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
②“念彼先人”,《毛诗》作“念昔先人”。
③《列女传·贞顺传》。宋伯姬之死载于《春秋公羊传·襄公三十年》。
④今本《诗经·大雅·江汉》作“矢其文德,洽此四国”。
⑤《春秋公羊传》评论说:“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仇,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⑥《新书·先醒》:“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辟犹俱醉而独先发也。故世主有先醒者,有后醒者,有不醒者。”《汉书·邹阳传》:“邹阳发悟于心。”
⑦冯达文《重评中国古典哲学的宇宙论》,该文部分内容刊载于《孔学堂》2015年第4期;全文发布于微信公号《解释》2017年9月10日。
⑧同①。
Dong Zhongshu’s Theory of Mind: On the Basis of His Reference toand
ZHANG Fengqia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Zhongsh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China)
In his, Dong Zhongshu makes a multiple elucidation of the righteousness ofand cites fromandat the same time for several times. His way of elucidation not only pays attention to the original meaning and extended meaning of the words, but also pays attention to the deduction and elucidation of the righteous principles, which is worth studying carefully. It is not simply a way of quotation or interpretation out of context, but is closely related to Dong Zhongshu’s theory of mind, which is his ideological basis. He elaborates that “mind” is more important than “etiquette” and that “ambition” is prior to “object” and reiterates that “the mind of others, I can fathom”. He suggests that people should have a high regard for etiquette and credit, understand one’s mind based on his or her conscience and behavior, and despise those who have no conscience. He also believes that natural disasters can make people alert, which shows the benevolence and love of God. He holds that the key reason why there are no standard words or common words indistinguishing and judging one’s intention. All of this is of the same lineage as Confucius’ and Mencius’ thoughts and has been developed in many aspects. Besides, his elucidation, which is combined with the evaluation of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events and people, constructs a new ideological system.
Dong Zhongshu; mind; ambition;;
10.3969/j.issn.1673-2065.2017.06.002
张丰乾(1973-),男,甘肃古浪人,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哲学博士。
中山大学“三大建设”专项资助
B234.5
A
1673-2065(2017)06-0008-07
2017-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