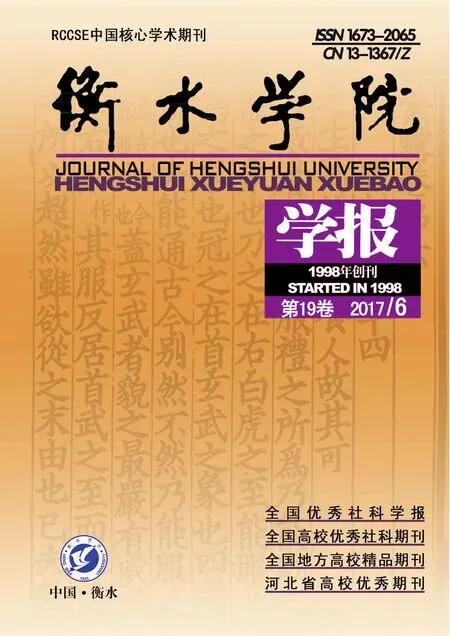“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价值导向研究
王宏海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价值导向研究
王宏海
(三亚学院 跨文化研究中心,海南 三亚 572022)
由于不同时代、不同区域学者的认知水平、文化背景、学术语境、信仰、时空观念不同,研究者的技术路径依赖,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造成了“百家争鸣,众说纷纭”的局面。从媒体历史学的角度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争论不仅仅是其存在与否的问题,而在于作为媒体主题引发儒学价值融合与创生的问题。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题引发的文化情境分析,既可以是对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分析,也可以是在此基础上对《儒林列传》董仲舒的分析;还可以是对班固及其《董仲舒传》的分析,甚至对当现代学者及其研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分析。从媒体历史和文化情境论分析就会发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仅仅是一种文化隐喻,它所获得的价值和意义取决于特定历史时代、特定的主体。
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媒体历史学;文化情境论
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研究综述
自东汉①以降,作为政治话语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长期受到政治家、学者的关注,它之所以令史学界、哲学界、法学界学者重视,一方面其代表了中国古代政治的转向,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中华文化儒学意识形态政治话语权的初步确立。随着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认识的深入,人们对其是否是董仲舒所出,处于何时,是否真正存在等等问题长期研究、讨论。由于史料不足,该命题所引起的纷争不断,各有所取,各有不足。概而言之,该命题主要涉及五个方面,即汉武帝是否实行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独尊儒术的原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间问题;谁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首倡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作用[1]。究其缘由,一是汉代久远,社会情境模糊;二是研究者所处文化情境不同;三是方法论不同;四是相关性的时代课题变化不断。
大多数学者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源于《汉书・董仲舒传》之“天人三策”及班固对董仲舒的述评。该传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武帝纪赞》曰:“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二文互证,被近代学者解读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1979年4月徐光烈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了《论汉武帝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标志着学界重开以科学的态度研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认为“汉武帝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是中国历史的一件大事。从此,儒家思想在文化思想领域占了统治地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长达二千年之久”“董仲舒独尊的儒学,已非当年孔孟儒学的旧物,而是经过他杂糅儒、法、阴阳等家学说,把传统儒学加工改造过的新儒学”“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绝不是完全摒弃其他学派的主张”“汉宣帝对太子说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这句话说出了汉武帝各项政策措施的真谛”。邹学荣则进一步说明:“从现存的资料看,秦汉之际历史和逻辑的发展要求当时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以一家为主,融合百家’,以形成地主阶级的新型哲学理论,而不是采取独尊或者是把各家思想机械地结合起来的方式建立统一的思想。”“董仲舒的哲学既不是‘独尊儒术’,也不是‘杂采百家’,而是‘以儒为主,融合百家’而形成的新理论”[2]。于传波对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论断提出了质疑,他说:“董仲舒对策之前就已经走上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道路的这一历史原貌被掩盖了,歪曲了。”因此,于先生要考证“天人三策”出自哪一年。于先生认为:“在董仲舒对策之前,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步骤:1)建元元年举贤良方正时,丞相卫绾奏道:所举贤良中有‘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之政,请皆罢,武帝批准了。这就罢黜了法家和纵横家。2)几个月后,卫绾病免了,窦婴任丞相,田蚡任太尉,赵绾任御史大夫,王藏任郎中令。他们全都‘隆推儒术,贬道家言’。黄老派的最有权势的代表窦太后心中不满,寻事把他们全罢官了,启用黄老派的许昌、庄青翟任丞相、御史大夫。3)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4)建元六年窦太后一死,汉武帝立刻罢了许昌、庄青翟的官,最典型的崇儒人物田蚡当了丞相,大力招揽儒家人物,推行儒术。5)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6)元光元年下五月举行贤良对策,董仲舒参加的就是这次对策。”[3]施丁几乎与于传波持同样观点,认为董仲舒不应该被贴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标签[4]。岳庆平总结、考证了关于董仲舒提出“天人三策”的时间争论点,认为:“作于元光元年五月,但又不否认董仲舒在建元元年对过策。”[5]孙景坛全面否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发展的历史,认为应该用“绌抑黄老,崇尚儒学”代替之[6],甚至还认为班固伪造了天人三策,董仲舒不是儒家[7]。值得令人思考的是孙景坛的文章尽管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所质疑,可是一是没有回述史学界的研究成果,缺乏学理基础,实质上是做重复工作;二是文章的一些观点失于片面,如“绌抑黄老”明显地限于狭隘,事实上还有“绌抑”法家、纵横家等。即使东汉的班固有心造假,也不敢造皇帝的假,而汉武帝和董仲舒的问答决定了汉武帝策问为真,董仲舒之应答必不能为伪,这是基本常识。何况班固与司马迁不是同一时代的历史学家,他们选择关于董仲舒的史料的立场不同,再自然不过了。司马迁不用的史料不一定不存在。确切值得思考的是,据刘桂生考据,自20世纪初以来,梁启超之《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邓实的《古学复兴论》、翦伯赞的《秦汉史》、郭沫若的《中国史稿》以及章太炎、刘师培、胡适、冯友兰、侯外庐、刘大杰、陈定闳、杨荣国等许多学者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和董仲舒造成的儒学专制,“禁绝和摧毁了儒学以外的百家诸子,以至中国文化学术日衰,国运日蹙”[8]。而对此质疑的学者则认为“这类说法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如许之衡的《读<国粹学报>感言》(《国粹学报》1905年第6期),刘诒徵的《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史地学报》1921年创刊号)认为这种论断是“诬古”,失于“武断”。管怀伦发表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学”确有其事》一文与孙景坛商榷,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一个过程,经历了六个阶段,理论分析多于史事陈述[9]。由此形成了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学术研究热点。2013年郝建平发表了《近30年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研究综述》做了较为详细的学术梳理[1]。
二、从媒体历史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价值
媒体历史学就是从媒体制作、媒体主题、媒体表达、媒体阐释等媒体文化演变的过程研究历史文本的学问。媒体制作是指历史学者或者历史人物书写、制作的历史文本,如《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论语》等都是经作者加工成为媒体的,由此,单个作者或者某个群体都可以成为媒体制作人。媒体主题就是历史媒体中的某事件、某观念成为媒体制作人叙述的对象,而在制作、叙述某个主题时,就需要各种技巧、表达形式、表达语言,就称之为媒体表达。媒体阐释就是媒体在传播过程中,同一主题经过不同时代的人们用口传或书写的形式进行注疏评价。在媒体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出现了传统文化价值与媒体价值的融合与创生[10]。所谓的融合和创生不是谁融掉谁或者谁合并谁,而是历史主体的选择和创造。这个过程意味文化创造,可以称之为创生。这种融合和创生是由文化情境决定的[11],因此,通过文化情境理解某种文化现象可以更好地理解古今话语的转化和跨学科、跨文化、跨视域的对话。由此,历史是媒体价值不断创造的过程,是个体价值与时代价值相互作用的结果。
从媒体历史学的角度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争论不仅仅是其存在与否的问题,而在于作为媒体主题引发儒学价值融合与创生的问题。对于该主题的认识,首先是关于董仲舒的文本的认知,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史记・太史公自序》:“故汉兴于五世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第六十一》有较完整的叙述:“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今上即位,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瑕丘江生为谷粱《春秋》。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褚大至粱相。步舒至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而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以上媒体所表达的信息是:1)董仲舒属于儒家。2)董仲舒治《春秋》公羊学,是春秋学传人,瑕丘人江生通过比较选择了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3)董仲舒弟子众多,人才济济,既有学者也有官员。4)董仲舒性耿直,不聚财,懂礼好学,以教书、做官为生。5)董仲舒的儒学融化了阴阳家思想,创生新儒学。司马迁感慨汉武帝执政后的政治变化,当概述自孔子及西汉儒学演化之路后,说:“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尽管司马迁认为董仲舒只是治《春秋》者之一,然而,儒学在政治媒体上取得的话语突破是显而易见的,而这种变化也是值得记录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话语作用以及影响力。
司马迁没有想到的是至东汉时,董仲舒的影响已经超越其他儒者,班固专门为其立传,且增加了“天人三策”“仲舒所著”以及史学家刘向祖孙三代对仲舒的评价。班固写《汉书》时距司马迁去世已有150余年,况且班固先因私修国史入狱,后得明帝支持,才得以继续。班固又怎敢拿汉武帝和董仲舒的对答作伪呢?这就是当时的语境。《汉书・董仲舒传》作为媒体所表达的意义是:董仲舒不是作为不得志的官员,而是受人尊敬的教育家而值得立传的,因为他伟大的政治思想而立传的。班固为董仲舒立传这个事件标志着以董仲舒儒学为核心的政治思想主流化和正统化。这种儒学意识形态化,经历了魏晋玄学“名教是否出于自然”以及隋唐佛学“明心见性”的浸染,转向了宋明理学。这个过程呈现了媒体价值及其表达的历史与媒体在特定历史视域的融合与创生。
无论是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对董仲舒提出“天人三策”时间的修订,还是今人对班固是否作伪的讨论,都无法回避“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价值和媒体价值。究其历史价值而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应时代之发展变化而出现的,其历史价值就在于清末民初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反思。这种反思是建立在特殊的文化情境中自然而然的、具体的、历史的呈现。当司马光赞扬董仲舒时,他看到的是董仲舒对政治一统的作用,然而董仲舒的“大一统”政治思想又与司马光所处时代的现实不相符,它与宋代政治理念冲突不断的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近代以梁启超等为核心的学者群体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批判,其历史价值不在于历史上的本真如何,而是在于传统对清末民初的社会究竟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的问题,“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表达的媒体信息就是专制概念。如何改变这个专制的社会才是问题的关键。
这种历史价值和媒体价值的合流与统一,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发展到了极致,纵观该时期发表的论文,千篇一律的是以儒法斗争为主线批判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当时的事实是,学术被意识形态固化,历史被固化。
而近30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研究同样呈现出媒体快餐化、碎片化的研究,个体话语阻断——自说自话的现象。如孙景坛的《董仲舒非儒家论》《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等文,不顾司马迁、班固等历史学家约定俗成的学术派别划分传统,运用自我设定的话语逻辑解释历史,这种媒体解释已经超越了历史本身,而是自我限定、自我修正的命题式逻辑分析。
综上所述,从媒体历史的角度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司马迁撰文始,就意味着它作为媒体主题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充满了前意识的暗示,这种暗示表明了媒体制作者的价值和立场以及他们对社会观念反映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投射——媒体解释。
三、从文化情境论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价值
文化情境论是用文化因素解释、理解媒体制作者对历史文本如何解读的。换言之,任何个体对文本的解释都是由其所处的文化情境决定的。媒体文本的历史价值和媒体价值在特定的具体的历史时代呈现为主体的价值,这种价值也只能由主体决定。而这种媒体解释又是由主体及其文化情境决定的,由此,人类社会有群体组织发展的主体文化认知和传统。文化情境的决定因素包括个体的认知能力、传统影响(家庭、社区和学校)、信仰、思维方式、时空观念以及技术路径依赖。这些因素既有先天本性,也有后天学习获得的习性。如个体生物性决定主体认知能力成长的可能性,智障人和思维健全者的区分是显而易见的,认知能力因个体差异及其阶段性发展而有所不同。传统影响是指个体生活境遇给予自我的影响。信仰是个体成长中根据自我认知建立起来的终极精神依赖。思维方式是个体在生活中形成分析问题的模式。时空观念是个体感知存在对象的深度、广度和长度,时间和空间感知力和想象力。技术路径依赖是指个体在解决问题时,因受认知能力、信仰、思维方式、时空观念影响而形成解决问题的方法和习惯。概而言之,这些要素形成主体决策和选择的文化语境,这个语境即是文化情境。用这个模式分析文化现象即文化情境论。
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题引发的文化情境分析,既可以是对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分析,也可以是在此基础上对《儒林列传》董仲舒的分析,还可以是对班固及其《董仲舒传》的分析,甚至对当现代学者及其研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分析。
回归文本,再次审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媒体历史和文化情境论分析就会发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仅仅是一种文化隐喻,它所获得的价值和意义取决于特定历史时代,特定的主体,同样是在清末民初,它对梁启超与许之衡呈现的价值意义就有很大的不同。梁启超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中认为:“秦始皇焚百家之语,坑方术之士,而思想一窒;及汉武帝表章六艺,罢黜百家,凡不在六艺之科者绝勿进,而思想又一窒。自汉以来,号称行孔子教二千余年于兹矣,百皆持所谓表章某某、罢黜某某者,以为一贯之精神,故正学异端有争,今学古学有争。言考据则争师法,言性理则争道统,各自以为孔教,而排斥他人以为非孔教,于是孔教之范围益日缩日小。濅假而孔子变为董江都、何邵公矣,濅假而孔子变为马季长、郑康成矣,濅假而孔子变为韩昌黎、欧阳永叔矣,濅假而孔子变为程伊川、朱晦菴矣,濅假而孔子变为陆象山、王阳明矣,濅假而孔子变为纪晓岚、阮芸台矣。皆由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如群妪得一果,跳掷以相攫,如群妪得一钱,诟骂以相夺,其情状抑何可怜哉!夫天地大矣,学界广矣,谁亦能限公等之所至,而公等果行为者?无他,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其有稍在此范围外者,非惟不敢言之,抑亦不敢思之,此二千年来保教党所成就之结果也。曾是孔子而乃如是乎?孔子作《春秋》,进退三代,是正百王,乃至非常异义可怪之论,阐溢于编中。孔子之所以为孔子,正以其思想之自由也。而自命为孔子徒者,乃反其精神而用之,此岂孔子之罪也?呜呼,居今日诸学日新、思潮横溢之时代,而犹以保教为尊孔子,斯亦不可以已乎!”(《新民丛报》第二号)
梁启超长期尽心于传统文化,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后追随康有为,投身维新变法。通过为学、从政、讲学等方式,深刻反思儒家文化,留欧考察,深感中国儒家文化思想专制的束缚,于是解释中国儒家思想史有了鲜明的反专制的思想价值取向。
同时代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在日本留过学的许之衡,则从学术和信仰层面认为:“若在野而倡国粹,则一二抱残守缺之士,为鸡鸣风雨之思,其志哀,其旨洁,是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欧化者自欧化,国粹者自国粹而已。与执政之主持,殆不可同日而语。”又说:“孔子之为中国教,几于亘二千年,支配四百兆之人心久矣。而忽然夺其席,与老墨等视。夫老墨诚圣人,然能支配四百兆之人心否耶?夫以孔子为非宗教家,徒以其乏形式耳。孔子之不立形式,正其高出于各教,使人破迷信而生智信也。除形式外,殆无不备教主之资格者。囗(梁)氏‘保教非尊孔论’一谓束缚国民思想,再谓有妨外交,又谓今后宗教必衰颓,其辟宗教也至矣。而其‘宗教家与哲学之长短得失’一篇,又谓无宗教思想,则无统一,无希望,无解脱,无忌惮,无魄力。其‘佛学与群治之关系’一篇,则谓今日之世界,其去完全文明,尚下数十级,于是乎宗教遂为天地不可少之一物。其言前后歧舛若是,则孔子非宗教家一语,又可信乎?”又指出:“若谓定一尊则无怀疑,无怀疑则无进步,因以希腊诸学派,律周秦诸子,而谓自汉武罢黜百家之后,学遂不竞。日本人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此而囗(梁)氏益扬其波者也。夫以今日群治之不竞,而追咎古初,亦知今日犹未为生番椶夷者,即此定一尊之效乎?亦安知今后之必无进步乎?且彼言希腊,夫希腊学风之盛,流衍遍于欧西,而今日无一存者,徒供历史研究之资料。”(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国粹学报》1905年第6期)
许之衡认为一国之宗教信仰是不能够人为地消除的,且孔教如国魂不得不保。他说:“国魂者,立国之本也。彼英人以活泼进取为国魂,美人以门罗主义为国魂,日人以武士道为国魂,各国自有其国魂。吾国之国魂,必不能与人苟同,亦必不能外吾国历史。若是则可为国魂者,其黄帝乎?近日尊崇黄帝之声,达于极盛。以是为民族之初祖,揭民族主义而倡导之,以唤醒同胞之迷梦,论诚莫与易矣。然黄帝之政治,犹有可寻,黄帝之道德,则书阙有间矣。今之标民族主义者,于道德多置未论,识者方为前途惧。抑知民族主义,有重要于道德者乎?愚谓黄帝而外,宜并揭孔子,而国魂始全。盖黄帝为政治之纪元,孔子则为宗教之纪元。种族不始于黄帝,而黄帝实可为种族之代表;宗教不始于孔子,而孔子实可为宗教之代表。”(《国粹学报》1905年第6期)
许之衡既看到媒体历史在不同时代、不同空间的转化,又深感欧亚之不同,西化并不能解决中国问题。靠否定古人并不能解决今日的问题。同时,他也看到梁启超在面对当下问题时的理论困境以及文章的内部矛盾,他们彼此都没有从学术研究中得出指导中国道路的思想是什么。
当代学者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研究同样深受当下文化情境的影响,且就技术依赖路径而言,如孙景坛之《董仲舒非儒家论》则出于哲学概念定义、逻辑推理的结果,他与其他学者的多次商榷,均没有超越静态概念的局限性,更没有上升到过程哲学和价值哲学的高度;也有学者一而再、再而三地考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出的时间点及其意义,但是重复性工作较多,且没有考察这一媒体主题的学术历史,无论是从哲学、历史学、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学科方面的研究,还是从解释学、语义学、考据训诂等子学科方面的研究,都需要对该主题进行更充分的话语解释与动态分析,就当下而言,一些对该主题的研究表现为学术功利性、学术泡沫化的现象。
四、结论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所谓“文化专制”的内涵源于清末民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学者群体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尽管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对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没有记载,但是对董仲舒开馆设教、社会影响却有明确记载。《汉书·董仲舒传》证明了董仲舒政治思想的巨大影响,创新儒学是历史必然,董仲舒儒学的影响表明了儒学、儒者政治地位的提升和超越。在这个过程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含义是儒学成为“学而优则仕”的主要途径;其他诸子逐渐失去了入仕途的优势,如兵家仍然能够通过举荐或科举获得官位。这个过程是由汉到明清逐步加强的过程,这个过程受到了官方主流话语的深刻影响。今人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研究表现出现代学科专业化的学术技术路径依赖,人们能够从多元文化比较中获得该主题的历史价值和媒体价值。从文化情境论看,可以较好地认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媒体历史的发展演变过程,超越所谓历史人物评价的“对错”二元论。
[1] 郝建平.近30年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研究综述[J].古籍整理学刊,2013(4):103-107,42.
[2] 邹学荣.董仲舒哲学思想的形成及其历史作用[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6(3):17-27.
[3] 于传波.董仲舒对策年代考[J].学术研究,1979(6):30-31.
[4]施丁.董仲舒天人三策作于元光元年辨——兼谈董仲舒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创始人[J].社会科学辑刊,1980(3):90-99.
[5] 岳庆平.董仲舒对策年代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3):114-120.
[6] 孙景坛.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中国近现代儒学反思的一个基点性错误[J].南京社会科学,1993(6):102-112.
[7] 孙景坛.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J].南京社会科学,2000(10):29-35.
[8] 刘桂生.论近代学人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曲解[J].北大史学,1994(2):116-132,263-264.
[9] 管怀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学”确有其事[J].南京社会科学,1994(6):13-18.
[10] 王宏海,石斌,徐艳.历史视阈中传统文化价值和媒体价值的转换与融合[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52-56.
[11] WANG Honghai. The meaning of life and self-actualization:Understanding ASEAN,Provision of Social and Humanities Science(Tailand)[J]. 2014 (May-August):1-18.
(责任编校:卫立冬 英文校对:吴秀兰)
①西汉时期的司马迁仅仅在《史记》卷一百二十一之《儒林列传》第六十一简要介绍了董仲舒的生平事迹。而东汉时期的班固在《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二十六则叙述了“天人三策”,并说“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是董仲舒说的。由是,本文认为:自东汉以降,才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核心话语之辩。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Abolishment of All Other Schools in Political Ideology but Confucianism Adopted Valid”
WANG Honghai
(Research Centre of Cross-Cultura, University of Sanya, Sanya, Hainan 572022, China)
Due to the differences of the cognitive level, cultural background, academic context, belief and concept of time and space of the scholars in different times or different regions, the researchers’ reliance on technical ways changes the phase of “the abolishment of all other schools in political ideology but confucianism adopted valid” into that of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 and public opinions are diverg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 history,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abolishment of all other schools in political ideology but confucianism adopted valid” is not the issue of whether it exists or not but the issue that, as the theme of media, it causes the integration and originality of Confucian value. The analysis of cultural context that is caused by the theme of “the abolishment of all other schools in political ideology but confucianism adopted valid” can be that ofby Sima Qian,by Dong Zhongshu and Ban Gu as well asby him, even that of modern scholars and their studies on “the abolishment of all other schools in political ideology but confucianism adopted valid”. Analyzing “the abolishment of all other schools in political ideology but confucianism adopted vali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edia history and the theory of cultural context, we may find that it is only a kind of cultural metaphor, and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that it may get depend on specific historical period as well as specific subject.
Dong Zhongshu; “the abolishment of all other schools in political ideology but confucianism adopted valid”; media history; theory of cultural context
10.3969/j.issn.1673-2065.2017.06.004
王宏海(1968-),男,河北沽源人,三亚学院跨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历史学博士。
B234.5
A
1673-2065(2017)06-0023-06
2015-0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