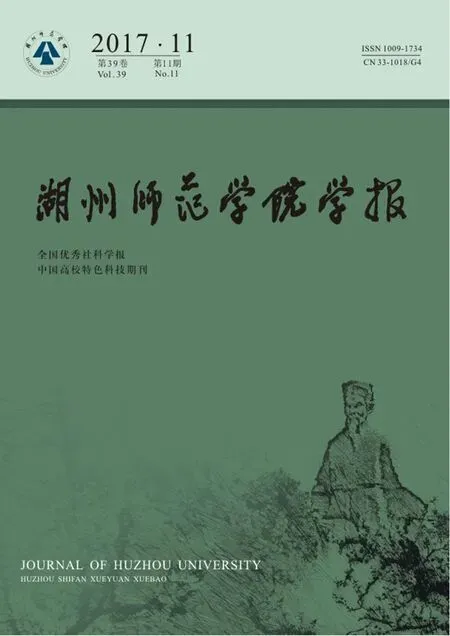谈“牡牝”之造字原理*
高新凯
(湖州师范学院 国际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谈“牡牝”之造字原理*
高新凯
(湖州师范学院 国际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关于“牡牝”类字的造字原理一直颇有争议,有形声、会意、合文等说法。文章通过《说文》保留的“麀”及文献中表动物雄雌专名的形声字推断“牡牝”类字乃是会意字,并由“芈”“牟”和东巴文等确认它们是专名而非异体字。“土、匕”是字中的偏旁,是生殖符号的象征但不具备独自表“雄、雌”的语义,“牡牝”绝非合文。“土”本是“社”字的假借,取象于祭社的“社主”象征物——木、石,乃是男根的象征。
牡牝;会意;形声;合文;土
一、关于“牡牝”的争议
学界对于“牡”字的造字原理一直很有争议,千百年来未有定论。自甲骨文中发现一系列的“牡牝”类字后,这种争议就更明显了。
《说文解字》:“牡,畜父也。从牛,土声”,许慎认为“牡”是形声字。段玉裁在注说中意识到“牡”与“土”的古音“求之叠韵双声皆非是”,他甚至认为或者“土”本为“士”,“士”有“夫”意,且“士”“牡”古音相近,如此则“牡”既是形声字又是会意字。罗振玉、王国维等人赞同“牡”字从“士”之说[1]( P1517-1518)。朱骏声、苗夔等人也认为“牡”与“土”古音差距太大,但不同意段注,而认为“土”是省声[2](P189)。朱芳圃认为“土”是“矛”的异文,“矛”与“牡”谐音相同[1]( P1520)。郭沫若把“牡”中的“土”解释为牡器符号,认为“土、且、示”都是牡器之象形,从字的本形解释“牡”为会意字[3](P271-292)。
赵诚不赞成改动字形以牵强附会,但认为《说文》关于“牡”为形声字的解释完全正确,人们之所以否认“牡”从“土”声,是因为“固执地”认为上古音有一个统一的系统,而“牡”与“土”的古音在这个系统中不合[2](P189)。因时代和地区差异,上古音可能存在多个语音系统,但这样臆断也难以服众。
至于“牝”字,《说文》:“牝,畜母也。从牛匕聲”,它是与“牡”相对的字,但因为“匕”与“牝”古音相合,所以没有引起多少争议。相反,它倒使人们更多地思考“牡”的偏旁“土”的表音性以附会其为形声字。
于省吾发现甲骨文中有几例卜辞写作“匕牛”,所以他推断“匕”是“牝”字的初文,“牝”是“匕牛”的合文。于先生较谨慎,因没发现“土牛”的写法,特说明“牡”字不能以此为例[4](P329-331)①于省吾《释牝》一文也认为“牡”字应是从“士”的,但后来在主编《甲骨文字诂林》作按语时已赞同“牡”也是“合文”的说法。(文章提到学者较多,此文失礼,都直呼其名而未加尊称)。。张秉权持相同的见解,但认为“牡”字也是合文变化来的[1](P1523)。洪笃仁也认为二字是由“合文”合成单字的看法最合理[5](P63-70)。

本文认为“牡牝”既非形声字,也不是合文,而实在是会意字。只是人们没弄清“土匕”偏旁的原始涵义。
二、“牡牝”类字并非异体字
但是关于这些字究竟是同一个字的异体还是各有所指的不同的字又出现了争议。


杨逢彬撰文《论(羊土)塵(豕土)(马土)(犭土),(羊匕)麀(豕匕)(马匕)(犭匕)等字不能与牡、牝二字通作》[10](P71-75)支持杨树达观点。此文列举了许多人类学的证据证明古人原始思维的特殊性,如盖捷特在《西南地区的克拉玛特印第安人》所说:“我们力求准确清楚地说,印第安人则如画一般地说,我们分类,他们则各别化”。 斯皮尔金在《意识的起源》中指出,在南非的苏鲁人那里,红的、白的、黑的等各种颜色的母牛都有特殊的名称,但却没有一般种类的母牛的名称;公绵羊,牧羊犬以及鸟等各类动物的尾巴都有具体的名称,但对“尾巴”却缺乏一般的称呼;对狗眼狮眼豹眼以及人眼都有各自的称呼,却没有抽象的“眼睛”一词……还列举了一些卜辞等证明甲骨文中这种原始思维的遗留。
我们非常赞同这一点,古人思维与后人颇有差异,古人重视“具象”,事物大小颜色形状不同往往各有专名,这从《说文》《尔雅》中保留的对牛、马、鹿等动物的细分也可以得到证明。倘若这不是一种原始的遗留,那就很难解释它们存在的理由。杨树达《释追逐》一文考释出甲骨文中逐兽用“逐”、逐人用“追”,而后人使用则不区别,这也可以看出古人造字用字的具体性与特殊性。闻宥《释年》一文指出“同样是‘去势’,对马称騬,对牛称犗,对羊称羯,对豕称豮,对犬称猗……这些文字虽然后起,但这些词语必是早有的”[1]( P1520)。我们后人对语言文字的发展则是倾向于抽象化、分析化,而不再是造“专名”。

另外,东巴文*东巴文是纳西族先民自创的文字,比较原始还不完善,绝大多数不能完整按语词记录语言,在文字的发展阶段上比甲骨文还要古老。中也有这样的例子。东巴文绵羊,读bv33;山羊,读h55;捲角羊,读n21。黄牛,读mu21;水牛,读i55;牦牛,读br21;犏牛,读dz21。同为牛羊,不同的种类则有不同的音读。但不知何时,语言中又抽象出类属的表达,如牛又读为33,黄牛为n2133,水牛为i2133[11](P181-183)。这便可以明显看出名词语音正经历一个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
所以,甲骨文中出现的“牡牝”类字绝非异体字关系,而是各有所指的“专字”。
三、形声与会意之别
杨树达据《尔雅·释兽》“鹿牡麚”释塵为麚,据“豕牝豝”释为豝,据《释畜》“(马)牡曰骘,牝曰騇”,释为騇。那未见甲文之,当为“骘”。据“羊牡羒,牝牂”,释为羒,羊匕为牂。*《说文》中有异,解释两字都为牡羊。《尔雅》中又有黑羊牡牝之分:羖、羭,《说文》又全解释为牡羊。《段注》据《尔雅》作了改动。其实,据《说文》“豭,牡豕也”,又可以释为“豭”。加上《说文》本有的“麀”的异体字:,我们可以总结一个对应表:
牡——特?*据《说文》“朴特,牛父也”,也可以释牡为“特”。我们认为公母牛也有对应的形声字,并且应与“牡牝”的读音不同。牝——?



这里有一个“化石”级的字“麀”(这是后世文献于以上字群中除“牝”外唯一保留“匕”旁的字),可以帮我们破解它们之间的关系。据《说文》“麀,牝鹿也,从鹿从牝省。,或从幽声”的解释,可以明显看出许慎以“麀”为会意造字(应从“匕”,而不是从“牝”省),“”为形声造字*许慎没见到甲骨文中那些同类的字形,否则他就知道定“麀”为会意,定“牝”为形声就是自相矛盾了。。
由此,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上表中横线左边的在甲骨文中使用却几乎不见于后世文献中的字都是会意造字,而右边的字则是形声造字。一个词既有会意造字同时也有形声造字在汉字中是常见现象。只是随着形声字的兴盛发达,后来它们相应的会意字逐渐被废弃了。

上表横线右边的形声字还有声旁表意的特点,体现其命名的理据性。如牝鹿之为“”,得于它的叫声“呦呦鹿鸣”[12](P470);牡鹿和牡豕用“叚”作声旁,而“叚”有“大、有力”之意*我们单从《尔雅》中一些相关的记载也可以看出这一点:《释诂》:弘、廓、宏……嘏、丕、假、京……,大也。《释木》:櫠,椵。郭璞注,椵为柚属,“子大如盂,皮厚二三寸……”《释草》:荷,芙蕖,……其叶蕸……《释鱼》:鲵,大者谓之鰕。《释兽》:罴,如熊,黑白文。郭注,“似熊而长头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树木,关西呼之曰貑熊”。《释畜》:(牛)绝有力,欣犌。详见:胡奇光,方环海.尔雅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骘”本得音于“陟”,与“叚”音有相通之处*《尔雅·释诂》:骘、假xia、格、陟、跻、登,陞也。。由此可以推测,其余的表动物“牡牝”的形声字也应是各有借声表意的理据的*语言的约定的同时也应是理据的开端。《说文》中保留那许多马牛等字的详尽分类的字声旁也应多是表意的,倘没有理据的存在,很难想象这些会不会超出人类思维的记忆能力。。
四、不是“合文”
至于甲骨文中出现了两三例“匕牛”的卜辞就断定“牝”是合文,未免略显草率。合文起码要满足两个条件:首先合文是一个词,组成合文的各个单字(简省部件的字可以明显看出并补出原形)是有独立意义的,此合文的意义是单字的语言意义组合,即各自独立意义按语序组合表达的意义;其次,读音要保持原来多音节的读法。
甲骨文中虽出现了“匕牛”,但从没有证据证明单字“匕”能表示“雌性”的意义,那么“匕牛”在字面意义上不能理解为“牝牛”,这于合文的第一个条件就不能满足。而且甲骨文中没有发现“土牛”的表达。那么“牡”、“牝”曾经被读作“土牛”、“匕牛”是无法证明的。后世文献中也只有“牡某牝某”的表达,而从没有“土某匕某”的痕迹。
当然,于先生的意见是它们最初是“合文”,但后来合成了一个“字”。这种情况在现代汉字中是有的,如“不用”合成“甭”、“勿要”合成“覅”。至于古文字是否有这样的情况还有待证明*濮茅左说这是常见情况,并举例“洹”为“亘水”的合文。我们认为值得商榷。“洹”本是“标类”形成的形声字,不知为何判定为“合文”?详见: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M]. 北京:中华书局,1996:1524.。于先生认为“匕”是“牝”的初文,“牛”是“牝”的形符,那又相当于认为它是合文形成的形声字,这种造字法怕是罕见。洪笃仁没有强调语音上的联系,只是认为这样的“合文”与会意、形声同是造字法*至于洪笃仁举的先公先王合文的例子,它们一直是读多音节的,一直是合文,并没有成为一个单音节字。而表二十、三十之“廿”“卅”一般认为渊源于结绳记事,它们是先有单音节读音还是后来“二十”“三十”合成的读音还是存疑比较妥当,古人未必不是一个整位数有一个“专名”表达。所以,这些例子并不能证明“牡牝”类字是“合文”合成的字。。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如果认为它们是合文,那前提就是承认了“土、匕”是表示抽象的“雄、雌”的语词,这一则无法证明,再则何必要在合成了这类字后又进行“二次抽象”出“牡、牝”?也就是汉语至少部分语词经历了一段由抽象表达到合成“专名”再到在此基础上重新抽象的过程。这种循环发展怕是可能性不大。倘按于先生曾经的看法,因为是合文,那关于“牝”类的其他的字“匕鹿”“匕羊”“匕马”等必然表示“专名”,它们同时还是形声字,又得读相同的“匕”音,且不说于语音上该如何区别,单是后世保留的“麀”字读作“幽”就无法解释。
我们认为“土、匕”只是字中的一个偏旁,在这里并不能单独表义。“匕”字之所以能单列,我们猜想当时关于动物公母的“牡、牝”在语言中应该已经抽象出来了,如同上文中举的东巴文的例子那样,抽象的词与具体的词处在一个并存的阶段,而因“牝”与“匕”读音相同,所以用简单的字形“匕”临时假借了“牝”*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误解了卜辞。。
五、“土、匕”的意义
许多人不肯承认“牡牝”类字的会意性,而且甲骨文和后世文字中“牡”都从“土”旁,而总有人试图“修改”它,主要还是因为没搞清楚其中“土、匕”的真实涵义。既然我们认定“牡牝”类字是会意字,那它们所从之“土、匕”究竟代表什么?


六、结 语

“牡牝”类字并非异体字关系,杨树达的观点是正确的,它们依然是表示“专名”的字。倘若它们是同一字的异体,那就无法解释甲骨文中这些字同在一条卜辞中的现象。
《说文》中保留的“麀”字,让我们找到了突破,“牡牝”类字实际是会意造字,它们在后世文献中有对应的形声字。“土、匕”本是有生殖象征的字形符号,在这里不具备独立的意义,“牡、牝”自然不是“合文”。“土”旁乃古代“社主”的象形,是“男根”符号的象征。至于“牝”之与“匕”音同,大抵只是巧合。
[1] 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M].北京:中华书局,1996.
[2] 赵诚.甲骨文字学纲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9.
[3] 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郭沫若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4]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M].北京:中华书局,2009.
[5] 洪笃仁.卜辞合文商榷[J].厦门大学学报,1963(3).
[6] 季旭昇.说牡牝[C] // 古文字研究.2002,第24辑.
[7]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
[8] 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说·耐林庼文说·卜辞琐记·卜辞求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9] 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0] 杨逢彬.论(羊土)塵(豕土)(马土)(犭土),(羊匕)麀(豕匕)(马匕)(犭匕)等字不能与牡、牝二字通作[J].江汉考古,1992(4).
[11] 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
[12]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
[13] 容庚.金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4] 王元鹿.普通文字学概论[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
ThePrincipleofMupinCharactersFormation
GAO Xinkai
(International College, Huzhou university, Huzhou 313000,China)
There is always an argument among phonogram, associative and co-character about the principle of mupin(牡牝) characters formation. This article proves they are associative compounds through the character you(麀) inshuowenand phonograms which express the male and female retained in ancient classics. They are proved proper nouns not variant characters through characters mi(芈) and mou(牟) and dongba characters. They are not co-wen either because the components tu(土) and bi(匕) do not express the meaning of male and female independently. The tu(土) is phonetic loan character of 社, it comes from the image of sacrificial wood and stone, and it is a Symbol of penis.
mupin(牡牝);associative;phonogram;co-character;tu(土)
H12
A
1009-1734(2017)11-0068-06
2017-09-15
国家社科重点基金项目“世界记忆遗产”东巴文字研究体系数字化国际共享平台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2AZD11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字与南方民族古文字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0BYY04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华民族早期文字资料库与《中华民族早期文字同义对照字典》”(项目编号:11JJD740015)。
高新凯,讲师,博士,从事比较文字学研究。
[责任编辑铁晓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