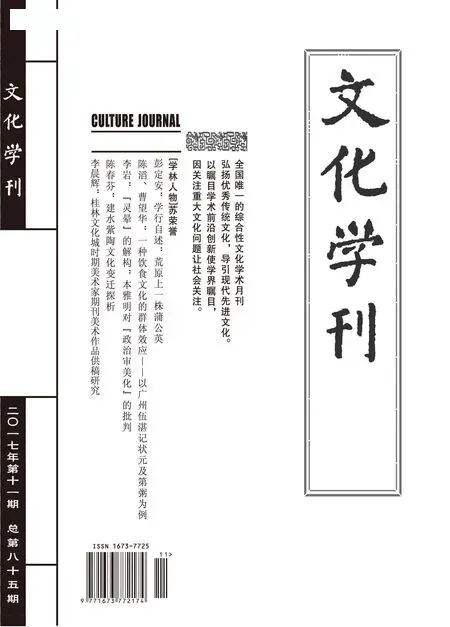叙事视角下《慈悲》中丽贝卡女性话语权的建构
武少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基础部,山西 阳泉 045000)
叙事视角下《慈悲》中丽贝卡女性话语权的建构
武少燚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基础部,山西 阳泉 045000)
本文借助申丹教授提出的叙事视角理论,以选择性全知视角为切入点,分析《慈悲》中丽贝卡为颠覆男权制和建构女性话语权所做的挣扎和努力,进而解读叙事视角对建构女性话语权的作用,彰显莫里森普适的女性主义观。
叙事视角;《慈悲》;丽贝卡;女性话语权;建构
一、叙事视角及《慈悲》
叙事视角是后经典叙事学中文本阐释的一种重要方法,国内外学者对其进行了不同的分类。在《小说的叙事视角》一文中,诺尔曼·弗里德曼提出了叙事视角“八分法”:两类有无“作者介入”的全知叙述;两类“第一人称”叙述;两类“选择性全知”叙述和两类客观叙述。热奈特在《叙述话语》一书中将叙事视角分为三类,即零聚焦(叙述者>人物)、内聚焦(叙述者=人物)和外聚焦(叙述者<人物)。
在弗里德曼和热奈特的基础上,国内叙事学领域的权威申丹教授进行了新的分类:观察者处于故事之外的外视角和观察者处于故事之内的内视角。选择性全知视角是指“全知叙述者选择限制自己的观察范围,往往仅揭示一位主要人物的内心活动”[1],因此,这种叙事视角属于外视角。
在莫里森的大部分作品中,黑人女性一直是其塑造的经典形象,但《慈悲》,莫里森将叙事视角转向殖民地初期生活在黑人文化圈中的白人女性——农场女主人丽贝卡。《慈悲》中体现的是蓄奴制形成之前,白人女性和黑人女性遭受的创伤。在这部作品中,莫里森表现了对女性生存的普适性关怀,将笔锋直指下层白人女性,以丽贝卡为代表的白人“他者”不但因为阶级地位的悬殊,而且因为性别原因处于他者地位。“《慈悲》描写了各色人等扛着灵与肉的枷锁和他们的解脱之道。”[2]种族不再是他者产生的原因,白人女性需要跨越性别政治进行自我救赎,而丽贝卡的救赎之道是颠覆宗教传统。
长期以来,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处于他者地位,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所说:“他是主体,是绝对,她是他者”[3]。这种无法言说的精神创伤使女性不得不内化这种他者地位,因此逐渐失去了话语权。丽贝卡出生于英国下层阶级家庭,父亲急于让女儿出嫁来减轻经济负担,而雅各布恰好在寻求这样一位妻子,因此,在父权制的迫害下,丽贝卡独自坐船从英国来到弗吉尼亚,成了名副其实的“邮购新娘”。尽管她是一名白人女性,但其生活在黑人文化圈中同样遭受着种种压迫,她的失声亦即她话语权的缺失。婚后,她成为了以雅各布为代表的男权文化的附属品,更加剧了她话语权缺失的窘境,因此,对丽贝卡来说,建构女性话语权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以申丹教授的叙事视角为理论框架,以选择性全知视角为切入点,对小说中刻画丽贝卡形象的叙事视角进行分析,进而诠释丽贝卡为建构女性话语权做出的挣扎和努力。
二、选择性全知视角下的丽贝卡
叙述者采用选择性全知视角来展现丽贝卡对雅各布的内心情感。选择性全知视角是指“全知叙述者选择限制自己的观察范围,往往仅揭示一位主要人物的内心活动”。[4]叙述者选择限制自己的观察范围,将丽贝卡作为全知叙事的见证人,仅仅从丽贝卡的角度揭示雅各布所代表的男权给她带来的创伤。
“雅各布大概认为,给她一个与帕特丽仙年龄相仿的女孩,会让他开心。可事实是,这侮辱了她。什么都无法取代,亦不应取代最初的那一个。”[5]雅各布试图用弗洛伦斯来医治丽贝卡失去女儿后受伤的心灵,可他未曾想到,丽贝卡的创伤更多的是由父权制下的男权社会所带来的,她的生命轨迹中一直充斥着像雅各布或她父亲式的人物。作者在表现贝利卡同雅各布关系恶化的同时,也表达了贝利卡对父权制的厌恶。丽贝卡关于邮轮的回忆同样表现了这一点。在前往弗吉尼亚的邮轮上,丽贝卡和她的船友们被束缚在黑暗中,看不到天空,承受着男性权力的空间规训,话语权的缺失剥夺了她们的女性立场,一群社会弃儿相互鼓励着来抗争“他者”。在丽贝卡看来,“女人是属于男人并为男人而存在的,但在那些短暂的时刻,她们二者皆非”[6]。
在雅各布的农场上,已“升级”为女主人的丽贝卡依然没有获得认同感。她的白皮肤带给她的不是好运,而同样遭受着同农场上其他奴隶一样的歧视和压迫。在失去四个孩子和丈夫之后,无儿无女的阴云与孤独的袭击使丽贝卡未能禁得起撒旦的诱惑,开始信仰基督教。“作为白人文化的内在基石,基督教是统治阶级用来束缚被统治者的精神手段,固化了信仰者的思想观念,是实行精神殖民的必要形式。”[7]丽贝卡找到了自己精神上可依赖的另一个“男性主体”。对于自己受到的折磨和精神的绝望,她联想到了约伯的故事,但是在丽贝卡眼中,约伯的痛苦只是想引起上帝的注意。独在异乡的她同样也需要上帝的关心和怜悯,但上帝却让她失望了,对于她们这些女约伯来说,“救赎是被拒绝的”[8]。上帝虚假的安慰并没有让她走出创伤,“我认为上帝并不知道我们是谁。要是他知道,我觉得他会喜欢我们的,不过,就我看,他并不了解我们”[9]。丽贝卡对上帝的失望衍射了小说主题“慈悲”的含义。莫里森的大部分作品和《圣经》中的爱和关怀有关,例如《宠儿》和《所罗门之歌》,但这部小说中提及的上帝却没那么的和蔼、友善,正如弗洛伦斯的妈妈所说,“这是人类施与的慈悲”[10]。
小说中,叙述者通过颠覆基督教传统来表达丽贝卡的女性主义立场。丽贝卡的父母无论对待彼此还是子女都表现得麻木而冷漠,却把火一般的热情全都留给了宗教事务,但讽刺的是,她对上帝的理解却十分模糊,认为“那是由某种奇妙的憎恶点燃并维持的一团火焰,对陌生人的点滴宽容都威胁着要浇灭那团火焰”[11]。所以当她和另外七个“白人他者”被分配到“祈祷”号轮船的船舱底层时,她并没有因为要只身远赴外国去嫁给一个陌生人的害怕和恐惧而向上帝祈祷,而是和她们凑在一起,谈笑风生,并且慷慨地把自己的奶酪和饼干与她们分享,短暂的“姐妹情谊”为旅途平添了不少轻松和愉悦。共同的他者命运使这些女性之间产生了一种无形的凝聚力,因此在丽贝卡病重时仍然在梦境里见到了当年与她同舟共渡的那份“姐妹情谊”。
叙述者选择从全知叙述者的角度透视丽贝卡的内心活动,彰显了莫里森高超的叙事技巧,同时表现了丽贝卡艰难并坚定的女性主义立场。
三、结语
女性话语权的建构是莫里森作品的普遍主题,她笔下的女性隐忍而坚强,在黑暗中找寻自我之路,建构自我主体。莫里森在《慈悲》中表现了她在种族书写上的协商意识,关注的焦点从底层黑人女性转向底层白人女性,直接描写了白人女性的他者空间,更突出地表现了她普适的女性主义观。由于丽贝卡的解脱之道建立在性别政治束缚的基础上,因此,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关于女性话语权建构的方式还有更多的思考空间。
[1][4]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95.95.
[2]王守仁,吴新云.超越种族:莫里森新作《慈悲》中的“奴役”解析[J].当代外国文学,2009,(2):43.
[3]西蒙娜·徳·波伏娃.第二性[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9.
[5][6][8][9][10][11]Toni Morrison.A Mercy[M].New York:Vintage Books,2008.96.85.92.80.167.74.
[7]王丽丽.走出创伤的阴霾——托妮·莫里森小说的黑人女性创伤研究[M].黑龙江: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97.
【责任编辑:王崇】
I712.074
A
1673-7725(2017)11-0011-03
2017-09-05
本文系山西工程技术学院校级基金课题“托尼·莫里森近期作品中女性话语权的建构”(项目编号:201706001)的研究成果。
武少燚(1989-),女,山西太原人,助教,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汉 长生无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