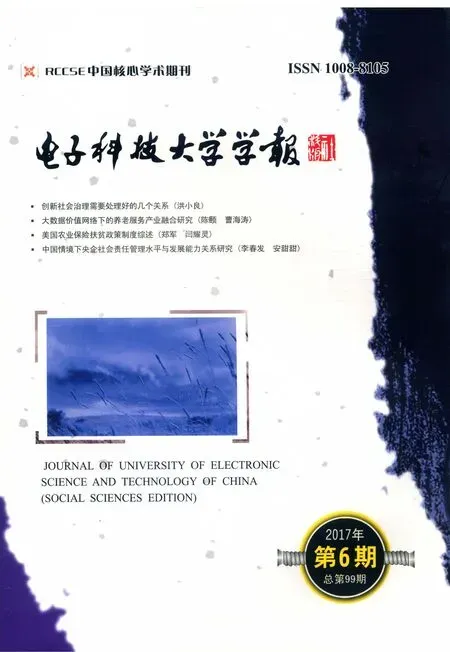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优化:国家的视角
□李力东
[浙江理工大学 杭州 310018]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优化:国家的视角
□李力东
[浙江理工大学 杭州 310018]
在当前中国经济逐渐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劳动关系领域的矛盾冲突有所加剧,这就需要发挥包括工资集体协商在内的劳资关系调节机制的作用。研究认为,工资集体协商在实践中的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的关键在于国家在其中的作用发挥还不到位。因此,国家需要在工资集体协商中厘定与资方、劳方的关系并对双方进行有效的协调。国家在工资集体协商中不应再扮演主导者的角色,而应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劳资矛盾的协调者和裁判者、公共利益的维护者。面对“资强劳弱”的总体态势,国家应主要通过立法支持劳方并规范约束资方,以实现劳资之间的适度均衡,这样才能促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优化和劳资关系的有效治理,从而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步入新常态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
经济新常态;工资集体协商;国家;资方;劳方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及其对劳动关系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快速增长,目前经济总量已位居全球第二。但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也不断累积,产能过剩、结构失衡、资源依赖、环境破坏、创新不足、内需乏力是突出的体现。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质量和效益还比较低。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呈逐年下降态势,从2011年的9.2%降到2016年的6.7%。从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历程看,中国经济的这种降速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也表明我国开始超越简单的“GDP主义”,而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从而逐步进入经济增长的一种“新常态”[1]。
所谓经济新常态,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的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了其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2]可以看出,中国经济新常态体现在增长上的主要特征就是结构性减速。不过,这种因结构变化引起的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的下降,同时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总体质量和效益向中高端水平的迈进[3]。中国经济质量提高最显著的体现是劳动力、资源等生产要素从传统制造业向以服务业为主转移,这即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这一过程势必伴随着传统产业的激烈竞争与优胜劣汰[4]。
中国经济向新常态的迈进既提供了广阔的发展机遇,也对很多企业特别是传统制造业的生产经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前,我国的很多地区特别是经济比较发达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出现了企业招工难、工人就业难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困难并存的局面。一方面,企业招工难现象的出现,一是由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非农就业岗位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比例逐渐提高,中国经济的第一个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5],工人工资水平不断上升,导致企业用工成本提高,利润率下降,一些经营状况相对较差的企业被迫裁员甚至倒闭;二是由于劳动力供需中存在着结构性矛盾,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劳动力过剩,而技术型、有经验的劳动力相对不足。另一方面,工人就业难现象的出现,一是由于企业裁员或关闭导致的总体或局部就业岗位减少,很多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因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被迫返回家乡;二是有些地区的有些企业存在拖欠工人工资的现象,如笔者调查的山东省某市,有些企业拖欠工人工资2个月到半年。
在上述两难并存的局面下,一方面企业要确保正常的生产经营,这就可能对工人的工资福利甚至就业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工人有就业需求,其工资也要保持合理增长,这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提出了一定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生产经营与工人就业、工资之间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就很有可能导致劳资双方发生矛盾甚至形成群体性事件,富士康公司员工跳楼事件和广东南海本田汽车工人停工事件就是典型的例证。可见,在我国经济逐渐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我国的劳动关系更加复杂化,劳动争议特别是集体劳动争议有所增加。据统计,各级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和仲裁机构受理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数从2011年的131.5万件增加到2015年的172.1万件①。在这种情况下,要尽量减少劳动争议的发生,就需要在劳资之间建立起良好的协商机制,让双方能够了解对方的情况和诉求,从而实现劳资之间一定程度的利益平衡。当前,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就是劳资协商的一种重要制度形式。
二、我国工资集体协商的发展状况与国家主导的基本特点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是在西方国家比较成熟而在中国还处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调整劳资关系的制度形式。所谓工资集体协商,就是工人组织与雇主或雇主组织就工资、福利、工作条件等问题进行协商并确定相关标准的过程[6]。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工资集体协商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非常迅速。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出台,我国的工资集体协商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据统计,截至2013年9月底,全国签订工资专项集体合同129.8万份,覆盖企业364.4万个,覆盖职工1.64亿人[7]。以浙江省为例,截至2016年9月底,全省签订工资专项集体合同12.17万份,覆盖企业38.98万家,覆盖职工1623万人,其中签订行业性工资专项集体合同443份,覆盖企业3.41万家,覆盖职工126.6万人,区域性工资专项集体合同8084份,覆盖企业26万家,职工596万人[8]。随着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推行,它的社会经济效益也逐步显现出来。在工资集体协商开展比较好的地区,形成了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劳资矛盾大为缓和,劳资纠纷也大为减少,企业的效益和发展也从这种和谐的劳动关系中受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职工权益、企业效益和政府公益“三赢”局面的实现。
虽然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应该看到,中国的工资集体协商还处于发展过程中,在实践中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总体来看,工资集体协商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形式化现象严重,协商过程中谈判环节缺位,集体合同照搬法律或政府提供的范本,内容千篇一律,缺少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导致该制度仍然没有成为一项实用和有效的制度[9~11]。这一问题的出现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因为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涉及国家、工会、普通职工、企业主及其协会等多个主体。就工会方面而言,中国的工会组织特别是企业工会缺乏代表性和独立性,依附于政府或者企业管理者,不能真正代表工人利益与资方进行协商[6,12~15]。就企业方而言,一些企业特别是非公企业经营者认为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容易形成对立,因此有抵触情绪,不想开展协商;一些企业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认为开展协商增加工人工资会挤占利润,不愿开展协商。笔者的调查发现,甚至在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开展较好的温岭市新河镇,有的企业主也认为开展集体协商费时费力,并表达了不想继续开展的意愿[16]。就普通职工而言,他们对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认知度还比较低。以笔者承担的2016年杭州市某区总工会职工满意度第三方测评项目为例,如表1、2所示,与工会的其他工作相比,职工对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认知度相对较低,只有3.2%的职工认为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是工会最重要的工作。事实上,职工的认知与工资集体协商的开展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工资集体协商开展得不理想,所以职工的认知度低,反之亦然。
依上分析,工会、企业方、普通职工三个主体在工资集体协商中都存在一些问题,导致工资集体协商不能有效开展。而且,很多问题单靠其中某一方是无法真正得到解决的,比如工会的独立性问题、企业方的协商意愿问题等。这就不但需要各主体间自发自觉地相互协调,同时也需要某种“外力”的推动来促使相关协商主体更好地履行职责,这一“外力”即是国家。国家在我国的工资集体协商中能发挥重要作用,这是由我国工资集体协商的特点决定的。西方的集体协商是劳资协约自治模式,集体协商的过程是劳资双方谈判和博弈的过程,政府很少干预;而党和政府在中国的集体协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从促进劳资和谐进而稳定社会秩序的角度出发自上而下地推动工资集体协商,因此,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是中国工资集体协商实践的基本特征②[9~11,17~21]。然而,工资集体协商的国家主导模式在实践中容易产生问题,如果国家在集体协商中的角色定位不清,职能行使不当,会对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效果产生更大的消极影响。国家主导下地方党政的越俎代庖导致工资集体协商的两大主体—工会方和企业方无法很好地履行各自职能。在国家主导下,指标管理成了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核心,而地方政府和工会则使用“软硬兼施”和“偷梁换柱”的策略来完成上级的指标考核,导致集体协商有协商但无博弈、有合同但合同法条化、重合同签订但轻合同履行[20]。因此,中国的工资集体协商要健康发展,需要国家在集体协商中有合适的角色定位,需要国家处理好与资方、劳方的关系,需要国家协调好资方与劳方之间的矛盾。

表1 职工对工会工作的认知度排序

表2 职工心中工会最重要的工作
三、工资集体协商中国家与资方的关系
资方是工资集体协商中代表企业主利益的协商主体,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资方的配合或者至少是不反对,工资集体协商才能顺利开展。然而,资本的天性是追逐利润,凡是影响到利润最大化的因素都会遇到资本本能的抵制和反对。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提升工人的权益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要分享资本的利润,所以资方自然不会主动地建立和发展工资集体协商。而且,在当前的中国,相比于劳动力而言,资本是更为稀缺的资源,绝大多数地方政府都把招商引资作为其工作的重中之重。资本的稀缺性带来资本的强势性。更有甚者,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越来越强,越来越不受限制。资本正从民族国家所实施的约束和监督中脱离,潜入一个“无人地带”,这里几乎没有规则限制、约束或妨碍资本的自由,甚至成为一种“外在空间”,齐格蒙特·鲍曼称这一过程为“第二次巨变”,以区别于卡尔·波兰尼所论述的资本脱嵌于社会的“第一次巨变”[31]。资本流动性的增强意味着其对劳动的依赖越来越弱,导致工人罢工变得越来越难,而资本却可以“罢工”,近年来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中国向东南亚等工资更低国家的转移就是明显的例证。“资本罢工”不但导致就业岗位的缺失,也意味着政府税收的减少[32]。一言以蔽之,全球化时代资本的流动性加剧了资本的稀缺性,从而进一步增强了资本的强势性。
全球化使民族国家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因其一方面要保障工人工资的合理增长,另一方面又要吸引资本以保证税收,而这两者之间无疑存在着矛盾冲突。因此,在工资集体协商中,国家在处理与资方的关系时,首先要看国家有没有动力和意愿去推动集体协商工作,其次才是采取什么措施促使资方配合集体协商的问题。从我国的具体情形来看,由于地方政府普遍把招商引资作为政府的首要工作任务,影响到招商引资工作的会受到地方政府直接或间接的抵制。因此我们看到,虽然各地政府也把工资集体协商作为一项重要工作,集体协商的数量也大量增长,但多数地方政府更多的是从应付上级政府指标考核的角度对待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这是导致该项工作“有量无质”的重要原因。基于这种状况,我们的国家首先要做的就是改变原来“GDP至上”的发展理念,向更加协调、共享的发展模式转型。事实上,中央已经意识到原来发展型国家的问题并提出了适应时代需求的新发展理念,只是这些理念被各级政府接受并得到贯彻落实需要一定的时间,而这也需要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内容和方式不断地进行调整和优化。因此,在工资集体协商中,国家特别是各级地方党政不能再因招商引资而纵容资本的无理要求,而要推动工资集体协商成为保障工人工资合理增长的有效制度。
国家特别是地方党政有了推动工资集体协商的真实意愿,才能把资方引导到配合协商的轨道上来。当前,资方出于各种原因(影响企业利润、怕麻烦、害怕因不能兑现而出事)对工资集体协商有抵触态度。比如杭州市某区总工会主席在访谈中提到:我们工会方发出要约后,有时候企业根本不来协商,另一种情况就是让工会弄个东西,然后看看没问题就签一下,而不是大家坐下来平等地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放在桌面上通过博弈的方式达成共识③。要转变资方的此种态度就需要国家出面。第一,各级党政和各级总工会④应通过宣传渠道使资方特别是中小私营企业主认识到资方和劳方长远利益的一致性。应该承认资方和劳方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但是两者之间显然不是零和博弈的关系,他们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实际上是一致的,国家应通过宣传使资方认识到,工资集体协商虽然看似拿走了企业的一部分利润,但是可以通过留住工人并激发工人的工作积极性而带来更多的利润,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在这方面,浙江省近年来推行的企业关爱职工、职工热爱企业的“双爱”活动⑤是一种可行的思路。第二,国家应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规制企业的用工行为,用法律手段推动工资集体协商的开展。目前我国已有的关于工资集体协商的法律法规存在立法层次低、刚性不强的问题,很难对资方行为形成有效约束。因此,应加强工资集体协商的立法,要提高立法层次,尽快制定《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法》;要增强法律的刚性和强制力,对违反工资集体协商相关制度的企业,明确其法律责任和惩罚细则[34]。此外,还应通过不断完善政府的劳动保障监察职能规范企业的用工行为,实行劳动保障监察机构省以下的垂直领导,减少同级政府对劳动保障监察机关的干预,并适度赋予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对违法违规企业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35]。
四、工资集体协商中国家与劳方的关系
在工资集体协商中,工会代表工人与资方进行协商。如前所述,资方在劳资关系中处于强势地位,而劳方则是劳资关系中的弱势一方,因此只有团结起来成立工会才能实现劳资之间一定程度的均衡。正如英国学者韦伯夫妇所言:“工会者,乃工人一种继续存在之团体,为维持或改善其劳动生活状况而设者也。”[36]工资集体协商就是工会维护工人权益的一种重要方式,甚至在有些国家特别是工会多元化的国家,工会组成和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集体协商,不能代表劳工进行集体协商的工会不被看作工会,而是被看作是一种政治团体。因此,工会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成为企业或行业内与资方协商的代表。需要注意的是,从历史上看,工会的成长和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支持。自19世纪以来,为应对市场“脱嵌”于社会而进行的反向保护主义运动中,国家通过各种形式的立法发挥了重要作用[37]。英国工会在《1871年工会法》制定之前在法律上处于一种极不稳定的状态之中,该法的实施消除了工会在民法上的非法地位,并且授予他们在法律诉讼方面的豁免权,从而为工会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38]。在美国,1935年颁布的《国家劳动关系法案》为工会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法律支持,集体协商逐渐成为美国劳资关系调整的首要制度[39]。可见,国家对工会在工资集体协商中作用的发挥提供了重要支持。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由于企业工会存在“制度性弱势”,所以在工资集体协商中存在“不敢谈”“不愿谈”“不会谈”等突出问题,这就需要国家—包括各级党政和各级总工会,采取多种措施以提高企业工会的地位,促进企业工会的职能转型,从而更好地代表工人与资方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第一,各级党政和各级总工会应尊重和鼓励企业工会的创新意识,不过多介入企业工会的具体协商过程之中。浙江温岭的羊毛衫行业工资集体协商之所以能取得较大成效,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是自发生成的。在制度形成的整个过程中,虽然党政部门也有介入,但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参与者而不是主导者,主要扮演着推动者、规范者、监督者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有为”而不“越位”,从而为该制度的发展完善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16]。因此,地方党政和各级总工会在推动工资集体协商的过程中要适度“超脱”,把更多的制度创新自主权交给企业工会,更要抛弃为求数量而采取简单的指标考核的方法。第二,国家应从法律、制度、政策等多方面支持工会在工资集体协商中的作用发挥。法律层面,如果说国家更多地需要用法律来约束资方的话,对工会则应提供更多的法律支持,通过法律手段保障工会以及工会干部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合法权益。制度层面,国家要支持企业工会实行工会主席直选、工会主席专职、工会会费的会员交纳等制度形式,从而保障工会能够真正代表工人与资方展开集体协商。当然,这些制度的建立和实施离不开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政策方面,国家需要设立企业工会干部权益保障金,加大工会干部关于工资集体协商的培训并为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提供政策支持,从而解除企业工会干部开展集体协商的后顾之忧并提高其协商能力。
在工资集体协商中,除工会外,国家与工人的关系也是国家与劳方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实践中,虽然由工会代表工人与资方开展协商,但是工人对与工资集体协商有关的工会工作的参与情况无疑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集体协商的效果。如前所述,我国的普通工人对工资集体协商的认知度还比较低,对集体协商的参与也比较有限。面对这一问题,第一,国家要通过立法保障工人的集体行动权,要转变“权力治理”的劳资关系调整模式,正面看待工人的集体行动。在我国当前“资强劳弱”的总体态势下,工人的集体行动具有暴露劳资矛盾、启动集体协商的积极作用,各级地方党政和总工会对此应有充分的认识,对工人的集体行动采取积极斡旋的态度,推动劳资双方通过协商解决纠纷,而不能仅仅从维稳的角度出发压制工人的集体行动。通过工人的集体行动自下而上地推动协商正成为启动工资集体协商的一种重要形式[40]。当然,工人的集体行动并不是毫无规范的群起而闹事,集体行动同样需要在法律框架内进行,而我国目前还缺少关于工人集体行动的法律法规。因此,国家应加强工人集体行动(或罢工权)的立法,这既是对工人权利的保护,也是对资方利益的支持,因为真正的工人集体行动并不是为了要激化矛盾,而是为了实现劳资之间的适当均衡。第二,国家应为工人参与工资集体协商提供支持,提高工人参与的效能感。根据阿尔蒙德等人的研究,公民的主观效能感对公民的参与有正面影响,主观效能感高的公民的参与度也比较高,同时对决策结果和政治系统的支持度也更高[41]。当前的工人群体参与工资集体协商的热情之所以不高,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缺乏这种主观效能感,认为即使参与了也起不到什么效果。因此,国家应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工人的参与效能感,使其真正参与到协商过程中。在这方面,一个基本的方法是国家要保障工人直接选举劳方协商代表,除工会干部之外,还要保障工人选举来自企业基层的代表,这样才能保证集体协商具有充分的代表性,从而最大限度地代表工人开展协商。
五、工资集体协商中国家对资方与劳方关系的协调
资方和劳方是工资集体协商的两大主体,前者倾向于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后者则希望自己的工资水平不断提高,因此双方在协商过程中存在矛盾实属正常。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无疑能够在协调劳资矛盾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处理劳资矛盾时,国家不能简单地进行压制,而是要做好劳资矛盾的预防机制,并在出现矛盾时进行合理的疏导,或者依法对矛盾做出裁判。
一方面,国家对工资集体协商中劳资矛盾的协调需要建立劳资矛盾的预防机制,尽可能从源头上预防劳资矛盾的发生。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政府、劳方、资方构成的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是预防劳资矛盾的主要形式,我国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建立三方协调机制。目前,我国县级以上行政单位中的多数已建立起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根据《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法律的规定,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研究解决有关劳动关系的重大问题,包括参与劳动法律政策和重要劳动标准的制定和实施、促进劳资双方开展集体协商、参与劳动争议处理等方面[42]。就工资集体协商而言,三方协调机制虽然也参与处理劳动争议,但更多的是通过法律法规、政策、制度来预防集体协商中可能出现的矛盾。在我国的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中,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代表政府,各级总工会代表劳方,而资方的代表多为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或工商联合会。在三方协调的实践中,资方代表的多样性带来了一定的混乱,导致其代表性不足,即使通过了相关决议也难以对企业形成有效的约束,这在县级以下的三方协调中表现得尤为突出[43]。而且,由于我国各级总工会的准政府机构特点,导致三方协调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两方协调”。因此,国家应不断推动完善三方协调机制,建立健全三方协调的相关机构并保持常态化运行,提高协调人员的代表性,通过三方协调机制不断完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从源头上预防劳资矛盾的发生。
另一方面,对于工资集体协商过程中已经发生的劳动争议或矛盾,国家需自身或推动相关方面通过相应的制度机制予以解决。为了更好地处理劳动争议,我国于2007年出台了《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该法提出的劳动争议处理方式主要有协商、调解、仲裁、诉讼四种。按照当前法律的规定,协商和调解不是劳动争议处理的必经程序,而仲裁是必经程序,当事人双方可以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不服的,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对劳动争议双方而言,协商显然是成本最低的争议解决方式,但是协商不可能总是成功,这就需要其他处理方式。就调解而言,我国目前的劳动争议调解机构包括企业调解委员会、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和乡镇、街道设立的具有劳动争议调解职能的组织。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企业的调解委员会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基层人民调解组织的专业性不强,更多的是靠个人的权威和魅力;而乡镇、街道调解组织的独立性、权威性较高,公信力较强,因此,由这类组织进行的行政调解应成为劳动争议调解的基本形式[44],特别是像工资集体协商这样发生集体劳动争议的领域更应如此⑥。就仲裁而言,虽然我国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由劳动行政部门代表、工会代表和企业方面代表三方组成,但政府无疑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再者现行法律规定仲裁是诉讼的必经程序,所以我国的劳动争议仲裁呈现出明显的行政化、诉讼化的特点,因此有学者提出我国的劳动争议仲裁应该去行政化、去诉讼化[45]。笔者认为,劳动争议仲裁去诉讼化⑦很有必要,这样才能体现仲裁相比于诉讼成本较低、规则灵活、程序简单、处理及时的优点,更有利于劳动争议的解决;但劳动争议仲裁去行政化却没有必要,在“资强劳弱”的总体格局下,需要由政府主导做出客观公正的仲裁。就诉讼而言,劳动争议的诉讼必须从整体上遵守民事诉讼的规则体系,利用好诉讼程序严谨、复杂、一视同仁的优点,确保劳资双方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能因为所谓的“民意”“弱势群体”等借口而损害司法公正,扭转当前“司法政策化”的倾向[46]。
六、总结
在当前中国经济逐渐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企业招工难、工人就业难两难并存,导致劳动关系领域的矛盾冲突有所加剧,这就需要发挥包括工资集体协商在内的劳资关系调节机制的作用。作为调整劳资关系的一项重要制度,工资集体协商在中国虽已普遍建立,但是其实施效果却很不尽如人意。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与工资集体协商的相关主体如工会、工人、企业都有关系,但是在笔者看来,更为关键的因素是国家在工资集体协商中没有发挥好应有的作用。
事实上,资方、劳方等主体在工资集体协商中作用的发挥也离不开国家的引导、规范、支持和协调。首先,国家与资方的关系方面,国家在面对资本的强势性时应有恰当的立场,这就需要国家特别是各级地方党政从“GDP至上”的发展理念转向更为协调、共享的发展理念;再者,国家应通过宣传渠道促使资方认识到资方与劳方长远利益的一致性,并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劳动保障监察制度,规范资方的用工行为,促进工资集体协商的开展。其次,国家与劳方的关系方面,由于企业工会存在“制度性弱势”,国家应从法律、制度、政策等多方面支持企业工会在工资集体协商中的作用发挥,并尊重和鼓励企业工会的创新意识,不过多介入企业工会的具体协商过程之中;再者,国家要通过立法保障工人的集体行动权,支持工人通过集体行动自下而上地推动集体协商,国家应为工会干部之外的工人参与工资集体协商提供支持,提高工人参与的效能感。最后,从国家对资方与劳方关系的协调看,国家应不断推动完善三方协调机制,并借此出台劳资关系领域法律法规、政策和建立相关制度,尽可能从源头上预防工资集体协商中劳资矛盾的发生;对于集体协商中已经发生的劳动争议或矛盾,国家需推动各方通过相应的制度机制予以解决,特别是需要不断完善劳资矛盾的调解、仲裁和讼诉机制。
工资集体协商作为一种重要的劳资关系调整制度要有效发挥作用,需要在国家、市场、社会三者之间实现合理的平衡。就我国的情况而言,国家在工资集体协商中不宜再起主导作用,而应该是法律法规的制定者、劳动争议的调解者和裁判者、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国家特别是各级地方党政和各级总工会不应介入工资集体协商的具体过程,不应采取考核、奖惩等行政手段推动工资集体协商的开展。而在面对市场和资本的强势地位时,国家应支持社会进行反向的保护行动,这更多地应通过立法来实现。也就是说,鉴于“资强劳弱”的总体态势,国家应侧重于通过制定法律来约束资方,同时通过制定法律来支持劳方,以期实现劳资之间的适当均衡,这样才能促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优化和劳资关系的有效治理,从而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步入新常态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
注释
①数据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网的历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②不可否认,中国的工资集体协商在实践中也有自下而上的“社会化模式”,这种模式又体现为多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由企业工会发起的,特别在有强有力的企业工会的条件下,这种形式的集体协商能够成为现实[22~23];第二种形式是雇主、工会、工人共同发起,通过雇主和工人在劳动关系中的互动而“自然生成”集体协商制度[16,24~25];第三种是集体行动的形式,在工人采取罢工等集体行动后,地方工会、企业工会组织工人与雇主进行集体协商[26~28];第四种是“草根”非正式的集体协商,比如植根于乡土习惯和草根组织的具有地方特色的集体协商[29],比如东南沿海帮工队“厂内赶工”的非制度化集体协商[30]。虽然有这些自下而上的协商形式,但“国家主导”仍然是中国工资集体协商的基本特征。
③2016年12月28日对杭州市某区总工会主席的访谈记录。
④中国的各级总工会实际上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基本组成部分[33],因此本研究将其纳入“国家”的范畴,并把各级总工会与以企业工会为代表的工人组织区别开来。
⑤2014年2月,浙江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浙江省“双爱”活动推进计划(2014~2017年)》,深入推进“双爱”活动。
⑥需要提及的是,仲裁调解、诉讼调解也是劳动争议“大调解”的重要形式。
⑦仲裁去诉讼化需要改革当前的仲裁强制前置制度,应区分个体劳动争议和集体劳动争议,前者应实行仲裁自愿,而类似工资集体协商等集体劳动争议仍然实行强制仲裁。此外还应建立实质意义上的仲裁终局效力。
[1] 金碚.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5(1): 5-18.
[2] 习近平.谋求持久发展 共筑亚太梦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N].人民日报, 2014-11-10 (A02).
[3] 李扬, 张晓晶.“新常态”: 经济发展的逻辑与前景[J].经济研究, 2015(5): 4-19.
[4] 齐建国, 王红, 彭绪庶, 刘生龙.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和形成机制[J].经济纵横, 2015(3): 7-17.
[5] 蔡昉, 王德文, 都阳.中国农村改革与变迁: 30年历程和经验分析[M].上海: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6] 李力东.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完善路径—工会转型的视角[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2012(2): 52-57.
[7] 《中国工会年鉴》编辑部.中国工会年鉴(2014)[Z].北京: 《中国工会年鉴》编辑部, 2014: 110.
[8] 王海霞.我省启动新一轮工资集体协商“要约行动”[N].浙江工人日报, 2017-2-9 (1).
[9] 程延园.集体谈判制度研究[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10] 郑桥.中国劳动关系变迁30年之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J].现代交际, 2009(2): 64-73.
[11] 冯同庆.近年来工资集体协商取向的正误分析—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结合[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2): 180-185.
[12] CLARKE S.Post-socialist trade unions: China and Russia[J].Industrial Relations Journal, 2005, 36(1): 2-18.
[13] 冯钢.企业工会的“制度性弱势”及其形成背景[J].社会, 2006, 26(3): 81-98.
[14] 许晓军.工资集体协商需要解决的若干问题[C]//颜辉.中国工会·劳动关系研究(2011).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
[15] 林燕玲.中国集体协商制度的发展及其前景[C]//颜辉.中国工会·劳动关系研究(2012).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
[16] 李力东, 钟冬生.多中心治理视角下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以浙江温岭行业工资集体协商为例[J].晋阳学刊,2014(5): 75-81.
[17] CLARKE S.Collective Consultation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China[J].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2004, 42(2): 235-254.
[18] 黄任民.中国工资集体协商的特点及工会的作用[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 2009, 23(5): 53-57.
[19] 谢玉华.工资集体协商: 能否走出协调劳动关系的“第三条道路”?[J].社会主义研究, 2011(3): 99-102.
[20] 吴清军.集体协商与“国家主导”下的劳动关系治理—指标管理的策略与实践[J].社会学研究, 2012(3):66-89.
[21] 潘泰萍.新世纪中国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的转型研究[M].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
[22] 石晓天.工资集体协商的条件与实现路径—从南海本田等个案比较的角度[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 2012,26(2): 38-43.
[23] 杨正喜, 杨敏.论转型期自下而上式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基于深圳先端的个案分析[J].广东社会科学, 2013(4):180-188.
[24] 徐小洪, 张俊华.《劳动合同法》实施状况与前景展望——来自浙江省的实证调研[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25] 闻效仪.集体谈判的内部国家机制—以温岭羊毛衫行业工价集体谈判为例[J].社会, 2011, 31(1): 112-130.
[26] 常凯.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与政府劳工政策的完善[J].中国社会科学, 2013(6): 91-108.
[27] 石秀印.集体协商的广东模式与江苏模式: 以全球化为背景[C]//颜辉.中国工会·劳动关系研究(2013).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4.
[28] 段毅.行政型劳资协商与行动型劳资谈判—两种模式的分析与比较[C]//颜辉.中国工会·劳动关系研究(2013).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4.
[29] 关彬枫.泊头: 一种植根于乡土习惯、草根组织的市场化的不一样的工资集体谈判[C]//颜辉.中国工会·劳动关系研究(2012).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
[30] 甘满堂.“帮工队”与非正式集体协议工资——来自福建泉州制造业的案例[C]//颜辉.中国工会·劳动关系研究(2013).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4.
[31] 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M].郇建立, 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59-61.
[32] 冯钢.转型社会及其治理问题[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118.
[33] 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M].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 79.
[34] 杨冬梅.平衡与和谐——转型期工会与劳动关系问题研究[M].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 98-99.
[35] 肖进成.我国劳动保障监察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6): 93-101.
[36] 韦伯夫妇.英国工会运动史[M].陈建民,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9.
[37]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 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钢, 刘阳, 译.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38] 琳达·狄更斯, 聂尔伦.英国劳资关系调整机构的变迁[M].英中协会, 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99.
[39] 托马斯·寇肯, 哈瑞·卡兹, 罗伯特·麦克西.美国产业关系的转型[M].朱飞, 王侃, 译.北京: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8: 17-18.
[40] 李琪.从争取权益的集体行动到利益博弈型的集体谈判[C]//颜辉.中国工会·劳动关系研究(2011).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2.
[41] 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 西德尼·维伯.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M].徐湘林, 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9: 258-284.
[42] 乔健.中国特色的三方协调机制: 走向三方协商与社会对话的第一步[J].广东社会科学, 2010(2): 31-38.
[43] 王长城.中国现行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及其改进[C]//颜辉.中国工会·劳动关系研究(2013).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4.
[44] 李雄.我国劳动争议调解制度的理性检讨与改革前瞻[J].中国法学, 2013(4): 158-168.
[45] 王蓓.我国劳动争议仲裁制度的缺陷与完善[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3): 75-82.
[46] 董保华.论我国劳动争议处理立法的基本定位[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08(2): 148-155.
编 辑 刘波
Optimization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System on Wag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New Normal: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tate
LI Li-dong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the Chinese economy has been stepping into the new normal, the contradiction and conflict in the field of labor relations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serious.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play the role of the labor relations adjustment mechanism, including collective bargaining on wage.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the practice is not satisfactory and the key reason is the role of the state is not in place.Consequently, the state needs to define its relations with labor and capital, and carry out effective coordination between two sides in collective bargaining on wage.The state should not play the leading role in the collective bargaining on wage, but should be the maker of the rules, the coordinator and referee of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and the defender of public interest.In the face of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quot;strong capital and weak laborquot;, the state should mainly through legislation support for the labor and regularize and restrict the captital,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proper balance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so as to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collective bargaining system on wage and the effective governance of labor relations, and thus provide a stable social environment for Chines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stepping into the new normal.
economic new normal; collective bargaining on wage; the state; the capital; the labor
F249.26
A
10.14071/j.1008-8105(2017)06-0035-08
2017-10-08
浙江省社科规划“之江青年课题”研究成果(16ZJQN042YB),浙江理工大学521人才培育计划资助.
李力东(1980-)男,博士,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