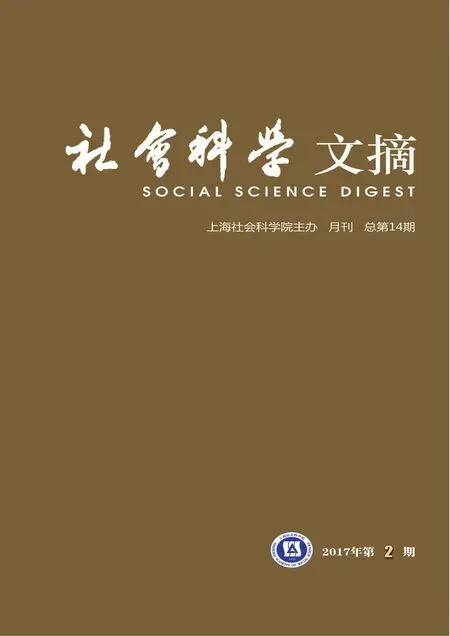交易成本、城市发展与新市民住房制度调整
文/孙斌艺
交易成本、城市发展与新市民住房制度调整
文/孙斌艺
作为人口和物质在空间上集中的一种形态,城市是现代经济、社会、文化、技术、行政等各方面力量的交汇点。城市有助于发挥生产和分销体系的规模经济效应,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深度分工情形下的协作效率。由于城市道路、桥梁、公用设施、住房等具有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的性质,这种公共品具有生产上的非竞争性和消费上的非排他性,由此会导致市场机制无法有效提供这类物品,即市场会出现失灵。于是,必须由政府运用行政管理手段提供这些物品,促进城市的持续发展。
在人口和物质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中,人们交往更为频繁,分工更为专业化,交易规模和频率急剧增加,交往集聚现象出现,交易成本水平变化,尤其是像我国在较短时期大规模城市化,原有协调城市内部各种关系的内在和外在制度不敷使用,城市交易成本大幅度提高,极大地限制了城市绩效水平提升,阻碍了城市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人口迅速向城市集聚,整个城市经济体系经历了巨大的重塑过程,新进入城市的人口不断融入城市。较短时间集中进入城市的人口与原有城市人口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形成城市原有市民与新市民的冲突。本文所称的新市民,是指由人口的机械增长形成的某一城市的新增人口,这类人口与所进入城市原有市民拥有不同的亚文化特点,实际生活中表现为城市的外来人口尤其是未获得所进入城市户籍的人口(如新近毕业未达到进入城市落户条件的大学生)、农民工等等。新市民融入城市首当其冲的就是“住”的问题,各种制度失衡、不协调和冲突集中反映在新市民的住房问题方面。
制度、交易成本范式和城市交往集聚
制度在现代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中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制度可以分为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内在制度有习惯、内化规则、习俗和礼貌以及正式化内在规则。外在制度主要表现形式是国家法律。由于城市的复杂性,城市的发展过程与外在制度的日益细化和繁琐联系在一起。由国家出面建立的各种法令、法律、规章、政策和标准等都是外在制度的表现形式。例如,土地所有制、金融制度、户籍制度,以及由国家制定的反映在各种规章中的制度类型。在某种意义上说,我国城市中出现的一些行政机构负担过重是与外在制度缺乏内在制度基础联系在一起的。
表征城市特点的关键因素在于人口规模以及带有不同制度烙印的群体差异,人口数量的急剧膨胀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相关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突出表现在相邻关系、交通状况、城市内人群分工、空气、噪音和光污染、城市生态环境、人们交往距离与居住距离的分歧等方面。
当人口和各类物质要素在空间上集中时,集中程度越高,人口密度越高,人们对交通、基础设施等的需求也会提高,人们之间的各类交往(包括各种交易)水平越高,从而对协调人们行为的制度的需求水平越高。当制度有效时,由于交往集聚所带来的城市交易成本水平会趋于下降;反之,城市交易成本水平会趋于上升。其中,城市居民的居住状况是集中反映交往集聚水平和状况的重要表征,也是城市各种冲突的聚焦点。尤其是在我国,由于历史原因,城乡分隔在持续了几十年后,在较短时间内放开,新近拥入城市的居民与原有居民在遵循的制度规则方面存在巨大的落差,这种城市内冲突更加明显。
城市发展中新市民住房问题的制度限制
城市发展中新市民进入城市、融入城市面临着一系列的制度限制,新市民直接感受到的各种住房方面的“歧视”,导致城市发展中交易成本大幅上升,大大抵消了城市集聚带来的成本节约。同时,由于新市民与原有市民内化的制度规则不一致,人们在经济交往中无法形成稳定的预期,或出现预期错配,从而使这些问题更加突出。主要体现在:
1.户籍制度
我国的户籍制度是限制新市民融入城市最大的制度障碍,尤其是对新市民具有巨大吸引力的一线城市,往往对新市民采取强制性的行政限制,制定了进入城市长期居留的较高门槛。这对于只具备初步劳动技能甚至只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们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存在户籍制度限制时,劳动力流动会受到阻滞,导致城市劳动力布局存在结构性失衡,提高了城市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固化了劳动力市场运行,从而使新市民的住房选择范围无法与其就业相匹配。
2.土地所有制、土地流转制度及金融制度
当新市民试图进入拟长期居留的城市时,往往会发现由于我国的土地制度、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等制约无法实现资产流动,资产固化的限制导致其拟购买或租赁城市住房时缺乏必要的启动资金,如新市民中的农民工原有的集体土地资产无法进入市场变现,从而抑制了新市民改善居住水平的条件。
另一方面,在城市“匿名社会”的条件下,资产固化无法使其市场价值显性化,导致新市民在购买住房时往往缺乏足够的资产作为担保获得金融支持,大大抑制了其购房支付能力。
3.与身份相关的公共服务制度
长期以来,人们的身份与其户籍所在地的公共服务捆绑在一起,新市民身份通常也意味着只能享受所进入城市的一部分公共服务,或者同等情况下被迫付出较大的代价才能享受同样的服务,通常涉及到子女就学、医疗、福利保障等各个方面。当新市民无法享受这些公共服务时,他们就无法做出合适的住房决策。
这种状况反映了目前城市的各种公共服务制度改变了新市民的住房决策条件,增加了其合理决策的交易成本,间接地也使城市集聚所带来的正向效应被抵消,加剧了新市民的居住困难。
4.就业、创业和产业政策
我国一线城市往往视小而散、低资本密集高劳动密集型产业为落后产业,在产业政策方面施加了许多限制性条件,直接或间接地抑制了这类产业的发展。然而正是这类产业能够吸纳大量的劳动力,而其提供的各种产品和劳务正因其分散、灵活才为城市所必需,才能满足城市对这些规模小、分布广、需求波动性大的产品和劳务的需求,抑制这类产业会极大地损害城市的协同发展。
当新市民就业受制度性限制无法稳定下来时,那么相应的居住安排就会转化为临时性决策,由于缺乏对制度的长期稳定的预期,因工作调整频繁导致居住地不断搬迁,增加了新市民的实际居住成本。
5.惯例、习俗和伦理规则的冲突
每个新市民尤其是成长期处于不同地域的人群,往往在成长过程中内化了相应的习俗、处理事务的惯例或习惯、与周围人群和社会相处的伦理规范,这些内在制度隐含在新市民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带有本能的性质。由此,新市民群体(地域群体)与相隔距离较远的所进入的城市之间存在紧张的文化冲突,体现在居住方面就是严重的不信任,居住中相邻关系复杂,容易诱发各类社会矛盾。
受这种亚文化性质的制度吸引,来自同一地域的新市民往往具有在所进入城市的特定区域集中居住的趋势,当集中居住地某些负面活动达到一定水平时,由此将产生严重的城市病,提高了城市发展的交易成本。
促进城市发展、有效解决新市民住房问题的制度调整方向
促进城市健康发展且能有效解决新市民住房问题的合理制度框架,要求各类制度具有降低城市交易成本、具有正向激励作用、鼓励不同形式创新性试错的作用,具有在住房问题上激励其进行长期决策、提升其总体经济福利的效能。因此,促进我国城市发展的新市民住房制度的调整方向应当包括:
一是改革农村土地所有制,允许农村土地实质性流转,单个农民可以将土地在市场上自由交易,农民转化或不转化为新市民由其根据自身条件自由选择。土地实质性自由流转,可以促使土地资产的市场价值显性化,新市民尤其是工作波动较大的农民工可以藉此支持获得进入城市的初步保障和启动资金。
二是改革户籍制度,将目前的户籍制度与公共服务制度分离,剔除公共服务的身份限制,依照人们的纳税情况享受相应的公共服务,消除对新市民的身份歧视,使其住房决策只需考虑其经济承受能力和自身偏好。
三是在强化对各类金融机构规则性、普适性监管的条件下,放开各类金融机构的微观性贷款限制,允许其与各类主体包括新市民自由协商金融条件,新市民可以根据自身条件获得金融机构不同的金融支持,满足其购买或租赁住房的需要。
四是取消各类创业、就业限制,允许企业和新市民自由竞争、自由择业,取消各类执业资格对新市民的限制。
五是取消各种住房市场的限制条件,允许新市民基于自身条件购买城市任意数量和品质的住房。
结论
我国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新市民住房问题能够通过制度调整予以解决。城市人口导入,会提高城市交往集聚水平,交易成本水平可能上升也可能下降,与之相适应的城市内在和外在制度都具有降低城市交易成本的特性,提升城市发展水平,反之,无效的制度会导致城市发展受挫。我国现阶段由各种制度性因素导致新市民住房问题日渐严重,亟待通过制度调整以化解制约城市健康发展的冲突和协调失灵。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副教授;摘自《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