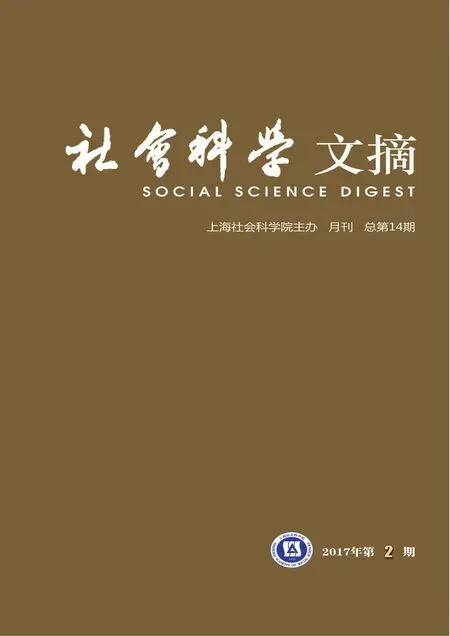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及其法律规制
文/王志祥 刘婷
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及其法律规制
文/王志祥 刘婷
网络恐怖主义犯罪概念的界定
关于“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存在狭义说和广义说之争。狭义说认为,网络恐怖主义犯罪是指恐怖分子对计算机系统、网络和信息设施发起网络袭击,引起实际的损害或制造恐怖氛围,以此实现其政治或社会目的。狭义说在本质上属于“目标型网络恐怖主义”。而广义说认为,所有利用互联网或计算机策划、组织和完成恐怖活动的行为,不仅包括前述的网络袭击,还包括利用网络实施的其他恐怖活动,例如筹资、勘察、交流和宣传等等,都属于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广义说在本质上属于“工具型网络恐怖主义”。
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并非网络空间与传统恐怖主义的简单结合。作为恐怖主义犯罪的表现形式之一,网络恐怖主义犯罪不论体现为对计算机系统、网络数据等进行网络袭击,还是将网络作为实施恐怖活动的工具,其都是通过对现实世界施加影响,例如威胁、恐吓政府,破坏计算机系统控制的基础设施,制造恐怖氛围和社会恐慌等等,以此实现恐怖活动的终极目标,而对这种非暴力的网络恐怖活动如果不加以防范和打击,也会对现实社会产生与暴力性恐怖活动相当的影响。因此,在当下恐怖分子广泛利用互联网作为袭击目标或利用工具的情形下,对网络恐怖主义的内涵采用广义说,更为全面、更为合理,即凡是以制造社会恐慌,威胁政府,或引起社会或环境损害为目的发动的网络袭击,以及以网络作为媒介实施的恐怖活动,都属于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范畴。基于此,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应当包括两类:一是网络恐怖袭击,即以控制关键基础设施的计算机系统和储存重要数据的互联网程序实施袭击;二是网络空间利用,即利用社会网站、网络软件等实施煽动、招募、筹资、策划、培训等恐怖活动。
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表现形式
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可以分为目标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和工具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两大类。而这两类网络恐怖主义犯罪根据恐怖活动的具体内容可以表现出多种形式。
就目标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而言,主要是指网络恐怖袭击。与普通的网络袭击相比,网络恐怖袭击虽然在行为人、方式、影响等方面具有很大程度的重合或交叉,但这并不表明二者不能从这些因素上区别开来。工具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即以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作为恐怖势力开展活动的重要工具,是目前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主流。
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国外立法现状
在刑法规制方面,英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家都针对网络恐怖主义犯罪进行了相应的规定。对于网络恐怖主义犯罪,英国、德国和俄罗斯的刑事立法呈现出如下特点:首先,对工具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和目标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分开立法。不同的是,英国对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采取专项立法模式,尽管工具型和目标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属于不同的规制体系,而德国和俄罗斯则通过修订刑法典,将具有公众威胁的网络恐怖主义行为纳入刑法调整范围。其次,就工具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而言,英国、德国和俄罗斯的立法都倾向于将利用网络实施的恐怖主义活动的教唆、预备和帮助行为入罪化,提前刑法介入的时间,实现法益的前置保护。在立法特征上,一是打击范围由现实世界延伸到网络空间,由实行犯扩大到非实行犯;二是从实害犯扩大到危险犯,刑法调整化被动为主动,着重刑法预防功能的发挥;三是从作为犯扩大到不作为犯,强调在风险社会下,特定主体对打击和预防网络恐怖犯罪具有的责任和义务。最后,关于目标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英国、德国和俄罗斯都没有对其进行特别的规定。在没有对网络恐怖袭击和普通的网络犯罪进行区分的情况下,对网络恐怖袭击犯罪就仍然比照适用普通的网络犯罪条款进行处理。由此可见,与工具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相比,英国、德国和俄罗斯对目标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立法相对滞后,这说明尽管遭遇多起网络恐怖袭击事件,上述国家对打击网络恐怖袭击犯罪的力度和重视程度仍有待提高。
我国对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立法规制
根据《反恐怖主义法》第3条的规定,恐怖主义是指通过暴力、破坏、恐吓等手段,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财产,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以实现其政治、意识形态等目的的主张和行为。按照该规定,恐怖主义既可以是一种主张,即通过口头、书面或其他方式表达的思想,也可以指某种行为,即主张的实践方式,二者具有发展程度上的递进性,但它们的共同点在于——恐怖主义理念和目标根植其中。关于恐怖主义的目的,《反恐怖主义法》将其规定为“政治、意识形态等”。在此,虽然以一个“等”作为打击恐怖主义的兜底保障,但可以看出,我国反恐立法仍然将“政治性”作为恐怖主义的主要或必要特征,这就可能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将恐怖主义犯罪的定性局限于政治犯罪的做法成为普遍现象。由此,恐怖主义犯罪的“非政治化”并没有在此次立法中得到体现。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恐怖主义犯罪的动机与其侵犯的法益已经呈现出新的变化:即以追求政治秩序的破坏转向追求社会经济秩序的损害。并且,这种经济恐怖主义犯罪通常表现为以攫取非法经济利益为目标的经济恐怖主义、以破坏经济秩序为目标的经济恐怖主义以及恐怖主义融资与洗钱犯罪等多种形式。传统的政治恐怖主义犯罪逐渐演变为新兴的经济恐怖主义犯罪,恐怖主义犯罪的“政治性”已不再是其必要特征,恐怖主义犯罪的目的呈现出政治、经济、宗教等多元化趋势。政治目的或动机并非是恐怖主义的必要特征。因此,未来的反恐立法应对此进行调整,将经济目的作为恐怖主义追求的目标之一。这样,当恐怖主义犯罪追求政治秩序的损害时,就将其定性为政治恐怖主义犯罪;而当恐怖主义犯罪的目标旨在破坏经济秩序时,就将其定性为经济恐怖主义犯罪,以此减少国际社会将恐怖分子视为政治犯而“不引渡”所带来的尴尬困境。
就恐怖活动而言,根据《反恐怖主义法》第3条第2款的规定,是指恐怖主义性质的下列行为:(1)组织、策划、准备实施、实施造成或者意图造成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公共设施损坏、社会秩序混乱等严重社会危害的活动的;(2)宣扬恐怖主义,煽动实施恐怖活动,或者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的物品,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戴宣扬恐怖主义的服饰、标志的;(3)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的;(4)为恐怖活动组织、恐怖活动人员、实施恐怖活动或者恐怖活动培训提供信息、资金、物资、劳务、技术、场所等支持、协助、便利的;(5)其他恐怖活动。根据该条款的规定,恐怖活动包括恐怖活动的教唆行为、预备行为、帮助行为以及实施行为,即从恐怖事件的策划筹备到实施完毕的整个过程的行为都被认定为恐怖活动。虽然恐怖活动的教唆、预备和帮助行为不具有像着手行为那样对法益造成的现实、急迫危险,但其本身具有恐怖主义性质,具有法益侵害的抽象或具体的危险,而且这种危险具有不确定性、扩大性、难以预测性,必须采取相关手段进行提前遏制,以免这种抽象或具体的危险转化为现实损害。在互联网与人类生活紧密结合的今天,恐怖主义分子在掌握和运用互联网技术方面的能力超乎我们的想象,上述恐怖活动的教唆、预备和帮助行为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线下实施方式,而是可以通过网上串联的方式加以完成。从打击网络恐怖主义的范围来看,《反恐怖主义法》第3条第2款主要适用于工具型网络恐怖主义行为,网络恐怖袭击等目标型网络恐怖主义行为在此次立法中并未得到重视。虽然第(5)项规定了“其他恐怖活动”的兜底条款,但通过联系上下文进行解释,“其他恐怖活动”也应当是指具有宣扬、煽动、筹备、招募、协助等工具型网络恐怖主义性质的其他行为,而并非指将网络当作攻击目标的恐怖主义行为。
在《刑法修正案(九)》通过之前,我国刑法分则中规定的专门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罪名屈指可数,恐怖活动犯罪的法网不够严密,对涉及恐怖活动犯罪行为的罪名和法定刑设置存在疏漏,刑法难以充分发挥预防和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功能,大量的恐怖活动分子由此得以逃脱刑法的制裁。基于此,《刑法修正案(九)》坚持从严打击恐怖活动犯罪的立场,结合我国当前恐怖活动犯罪的新特征和司法实践的经验,借鉴国内外的反恐立法,对恐怖活动犯罪的刑事立法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这主要表现为刑法分则相关罪名的完善和涉恐犯罪类型的增设。《刑法修正案(九)》关于恐怖主义犯罪的规定,在总体上具有法益保护早期化、处罚范围扩大化与处罚程度严厉化等特点。其关于恐怖主义犯罪的立法修订,丰富了我国刑法分则的反恐罪名体系,尤其在信息化时代,对惩治利用网络实施恐怖犯罪的教唆、预备和帮助等行为极具现实意义。然而,伴随着恐怖主义犯罪新特征、新方式的出现,现行反恐罪名体系的缺陷将逐渐显露。
一方面,现行反恐罪名体系无法包容“独狼式”等个体型恐怖主义犯罪。这些个体恐怖主义分子相互之间可能并不认识,不具有意思联络,也没有组织、领导或参加任何恐怖组织,但可能受到恐怖主义思想的蛊惑或者其他恐怖分子的煽动,或者浏览恐怖主义网站而萌生恐怖主义动机,进而自发策划和实施恐怖活动,即恐怖主义动机的产生、准备和践行都是由恐怖分子个人自行完成的。目前,“独狼式”、“自杀式”等个体型恐怖主义犯罪已经成为恐怖主义犯罪的主流,并具有分散性、隐蔽性、不可预测性等特点,通常自行策划对网络系统的袭击,或者线下制造恐怖事件,其造成的现实损害并不亚于恐怖组织犯罪。从现行刑法规定的反恐罪名来看,对实施恐怖活动犯罪的刑事制裁无法兼容个体型恐怖主义犯罪。这是因为,刑法分则对恐怖活动犯罪的规制模式是以行为人组织、领导、参加相关恐怖组织为前提的。根据《刑法》第120条第2款的规定,“犯前款罪并实施杀人、爆炸、绑架等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据此,司法机关在对实施恐怖活动犯罪进行评价时,如果行为人客观上还具有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的行为,那么就按照实施的恐怖活动触犯的具体罪名与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进行数罪并罚;如果行为人并未组织、领导或参加任何恐怖组织,那么就将行为人实施的具有恐怖主义性质的行为按照普通罪名进行定罪处罚。由此可见,刑事立法在设置恐怖活动罪名时进行了一个预设:即恐怖活动犯罪是有组织犯罪,行为人要实施恐怖活动犯罪,必定会组织、领导或参加某个恐怖组织;行为人组织、领导或参加恐怖组织,必定会实施一定的恐怖活动犯罪。因此,以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和其他具体犯罪,例如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等严重犯罪,进行数罪并罚,能够给予恐怖分子最严厉、最恰当的刑事评价。然而,当大量个体型恐怖主义犯罪出现时,上述预设的适用空间和效果将大打折扣。这是因为,个体型恐怖主义犯罪已经不再以有组织形式出现,无法再以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进行定罪处罚;按照现行刑法规定,只能根据其行为性质适用普通的犯罪罪名。这样一来,恐怖分子实施的犯罪行为虽然具有恐怖主义性质,却无法按照恐怖活动犯罪进行评价。由此,就不仅模糊了恐怖活动犯罪与普通犯罪之间的界限,淡化了犯罪的恐怖主义性质,还将导致恐怖活动的社会危害性在刑法上得不到应有的评价。虽然《刑法修正案(九)》将恐怖活动犯罪的教唆、预备和帮助行为予以实行行为化,对单独实施这些外围行为的恐怖分子能够按照恐怖活动犯罪的相关罪名进行处罚,但仍然不能包容着手实施恐怖活动犯罪的个体型恐怖主义分子的恐怖行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借鉴《俄罗斯刑法典》和《法国刑法典》的做法,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中增设“实施恐怖活动罪”,将具有恐怖主义性质的犯罪行为,例如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放火、决水、投放危险物质等,单独以“实施恐怖活动罪”定罪处罚,从而与其他普通犯罪区别开来。与此同时,对实施恐怖活动罪必须结合行为人的主观动机和行为性质加以认定,以避免将打击恐怖活动犯罪的触角肆意延伸到其他普通犯罪。
另一方面,现行反恐罪名体系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某些外围行为缺乏应有的关注。《刑法修正案(九)》对诸如参加恐怖训练、招募恐怖成员、协助恐怖组织等恐怖犯罪的外围行为予以实行行为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上述外围行为具有高度的潜在危险性,并且能够用具体罪状加以描述。然而,在上述外围行为之外,还存在诸多具有恐怖主义性质并存在“明显而即刻”危险的行为。比如,发布赞美或者辩解恐怖主义的公开言论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抹杀或淡化恐怖主义犯罪或者恐怖主义分子的恐怖性质,甚至可能诱导社会公众对恐怖主义产生错误认识、加入恐怖组织或自发实施恐怖活动等等。这种间接煽动造成的社会后果并不亚于直接煽动。立法上在将“赞美或辩解恐怖主义”纳入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罪进行打击时,应同时对“赞美”和“辩解”作出补充性规定或解释,明确指出何种性质的言论或行为构成对恐怖主义的赞美或辩解,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构成对恐怖主义的宣扬或煽动,从而在打击恐怖主义与保障言论自由之间划清界限。
《刑法修正案(九)》对目标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规制主要体现在对计算机网络犯罪的立法完善方面。从总体上看,《刑法修正案(九)》对计算机犯罪的立法修正,仍然以保护计算机系统和数据为主,并重点打击利用计算机和网络实施的相关犯罪。无论在《刑法修正案(九)》通过之前,还是之后,对网络恐怖袭击犯罪都没有作为计算机犯罪的特殊类型进行专门规定。从立法完善的角度而言,刑事立法应当对网络恐怖袭击犯罪和普通计算机犯罪予以区别对待,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之下增设“实施恐怖活动罪”,以对目标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网络恐怖袭击犯罪进行定罪处罚。
(王志祥系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刘婷系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硕士生;摘自《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