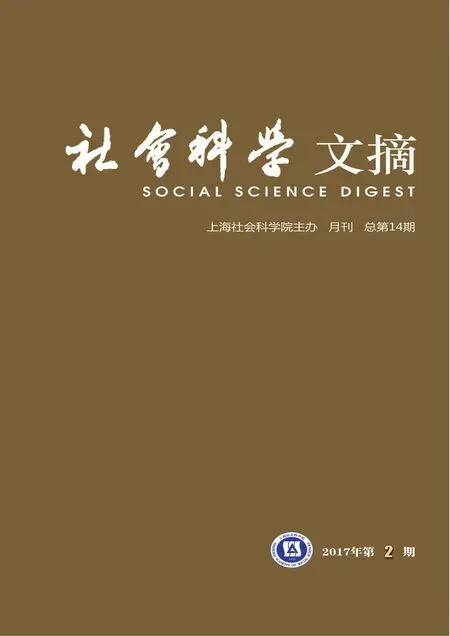两面结盟现象的再思考
——兼评《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
文/周方银 王旭彤
两面结盟现象的再思考
——兼评《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
文/周方银 王旭彤
2015年第5期《当代亚太》发表了曹玮、杨原的《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两面结盟”之谜》(以下简称《盟》)一文,讨论了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反常识现象,即一个国家如何能与两个彼此敌对的国家同时结盟。
两面结盟是此前国际关系研究中一个不太为人们关注的现象,深入的探讨相对缺乏。《盟》文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盟》文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但难以做到尽善尽美,其中的理论解释和历史案例分析还有值得改进之处。本文希望通过对《盟》文相关内容的探讨,进一步深化对两面结盟现象的认识。
古代东亚之盟与今日之盟的差异
关于同盟的界定问题,是探讨两面结盟现象的基础和出发点。《盟》文将同盟界定为至少有一方负有为另一方提供军事支援义务的双边或多边合作安排,认为,在古代东亚朝贡体系中,一些核心成员与中国的宗藩关系就属于同盟关系。这样的认识,涉及两个值得讨论的方面。
一是朝贡关系本身是一种演化中的,强弱程度有很大变化余地的关系。北宋时期朝贡关系的性质和内容颇为复杂,朝贡关系大多没有相互提供军事支援义务的含义。二是对谁是朝贡体系中“核心成员”的认定。人们一般认为,朝鲜是中国古代朝贡体系中藩属国的典型。这样的说法,在明清大一统政权稳定时期大体成立,但在此之前,特别是在南宋及以前,难以成立。据统计,宋代来朝贡较多的国家包括:占城56次,交趾45次,高丽41次,大食40次,于阗34次,三佛齐33次。这些国家与北宋之间几乎都没有相互提供军事支援的义务。
对朝贡关系与同盟关系两者进行有效的相互匹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即使到了明清之际,中国与朝鲜的关系能不能作为同盟关系来理解,也颇值得商榷。在中国人包括当时朝鲜人的观念中,这一关系主要是一种宗藩关系,是一种上下级关系。即以宋辽时期而论,辽国认为自身与高丽是上下级关系,以至辽国还对北宋表示:“高丽乃我奴耳,南朝何以厚待之?”在这样的观念结构下,作为宗主国的中国,很难产生和接受自身与朝鲜是一种同盟关系的观点和思维。在上下级关系中,即使存在一定军事支援义务,双方关系的性质也不太适合作为同盟关系来理解。
关于辽、后金与高丽之间同盟关系的存在性,涉及对东亚国际关系的理解,有几个值得探讨的地方。
(1)兄弟之盟是不是同盟?《盟》文认为,“兄弟之盟”同样具有军事合作的属性。但在东亚古代国家关系中,“兄弟之盟”“叔侄之盟”往往没有同盟含义。古代中文语境中“盟”的含义源于古代的会盟,这不同于同盟之盟。宋辽、宋金在战争之后缔结的盟约,其含义大体相当于现在的战后和约,如“澶渊之盟”中,宋辽约为“兄弟之国”应该就是这样。如辽宋这样的兄弟之国,它们之间的外交礼仪被称为“敌国之礼”,敌国之礼的重点在于强调双方的对等性。隆兴元年,南宋兴兵北伐失败,次年双方达成隆兴和议,约为“叔侄之国”。但这里的“兄弟之盟”“叔侄之盟”都不是同盟关系。“叔侄之盟”中的“叔侄”话语表述的不是双方关系的亲密性,而是双方关系的不平等性,它也是一种南宋一直念念不忘、希望去之而后快的表述。
(2)强迫订约建立的关系是不是同盟关系?如《盟》文所述,1627年,后金发兵攻打朝鲜,朝鲜很快被后金征服。在此情况下,双方约为“兄弟之国”,即所谓“兄弟之盟”。这实际是在后金强大军事压力下签订的一个不平等和约,根据和约,朝方被迫入质纳贡。盟誓后,后金军队仍占领了平壤和义州等地一段时间。朝鲜对此十分不满。在朝鲜政府心目中,并没有把1627年的“兄弟之盟”视为同盟关系。从后金的角度,和约更多体现了对朝鲜的单方面约束。
此外,一国希望另一国出兵相助,也不一定意味着双方之间就有军事援助义务或同盟关系。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有很多一国在战争中向他国求救的事例,如公元前506年,吴、蔡、唐联合攻打楚国,一直攻下郢都,在此情况下,楚国申包胥去秦国搬来救兵。又如公元前354年,魏国伐赵国,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用围魏救赵之计,在桂陵大败魏军。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但在楚国和秦国之间、赵国和齐国之间,并没有同盟关系的存在,即使派出救兵,也主要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的政策选择。在古代东亚国际关系中,严格意义上的同盟关系实际上是并不多见的。
两面结盟的实例分析
《盟》文对历史上中国与朝鲜(高丽)两面结盟的历史进行了详细分析,确定了三个存在两面结盟现象的时间段。我们分别对这三个时间段两面结盟现象的存在性,进行一个简单的再分析。
(1)历时最长的第二个时间段(1071~1116年)
自1031年到1070年之间,高丽与北宋之间并没有朝贡关系,两国往来处于停滞状态。1071年,高丽遣民官侍郎金悌等110人来北宋,并献方物。高丽与北宋的朝贡关系正式恢复,但双方并未因此建立同盟关系,高丽与北宋多年的往来,在政治、军事领域并没有什么实质性成果。北宋朝廷不少官员包括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苏轼等,甚至主张断绝与高丽的朝贡关系。
如果我们退一步,接受朝贡关系的建立即意味着同盟关系的建立这一逻辑,则会带来另一个麻烦,即北宋与辽国之间的朝贡关系。1004年,宋辽签订“澶渊之盟”,宋真宗与辽圣宗约为兄弟,两国约为兄弟之邦,此后双方维持了约百年之久的长期和平关系,双方之间的相互聘问十分频繁。据统计,从1004年到1121年的117年间,双方相互遣使贺生辰、贺正旦、祭吊共达643次。在1120年宋金海上结盟之前,宋辽关系长期维持在一个很高水平,且明显在宋丽关系之上。
按照朝贡关系即同盟关系的操作化方法,则宋辽在1004~1119年之间已经是同盟关系,而且是比宋丽更紧密的同盟关系。在此情况下,即使高丽同时与宋辽结盟,也不过是三个国家互相结盟,从而并不符合两面结盟的要求。
(2)高丽与宋辽的两面结盟(986~993年)
相比辽国,高丽总体上对汉族政权更为认同。高丽太祖王建在临终前告诫其子孙:“惟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遵其制。……契丹是禽兽之国,风俗不同,言语亦异。衣冠制度,慎勿效焉。”981年前后,高丽与立国尚不久的北宋关系颇为密切。相比之下,这一时期的辽丽关系则颇为紧张。先是983年,辽圣宗在即位第一年,检阅东京留守所总兵马,摆出欲亲征高丽的姿态。然后是985年,辽国准备大举进攻高丽,但由于辽泽水溢,道路不通而取消行动。之后,辽于993年大规模入侵高丽,迫使高丽向辽称臣。
期间,还发生了986~989年的宋辽大战。在宋辽大战的同时,高丽乘机北进,不断对鸭绿江沿岸的女真人进行征伐,建城筑塞,加强边防。至992年,高丽已将鸭绿江下游南岸的女真人基本驱逐到长白山以北地区。高丽不断扩张的态势引起辽国不满,这也成为后来辽国征讨高丽的口实。
《盟》文认为,辽国986年遣使到高丽请和,虽然和议内容在史籍中缺乏详细记载,但可以认为高丽与辽国结成了军事同盟。实际上,此次请和,只能说辽丽达成了一项暂时和议,而远远谈不上两国结成同盟关系,甚至可以说,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颇为对立的。
(3)朝鲜与明朝和后金的两面结盟(1627~1636年)
该阶段朝鲜与明朝颇为紧密的关系毋庸讨论。我们主要考察朝鲜与后金的关系。
在这一阶段,后金先是于1627年进攻朝鲜,朝鲜无力抵御,在江都议和,结为兄弟之盟。但和约的内容谈不上友好,双方的一致之处不过是停止战争。朝方在誓文中说,“若金国仍起不良之心,违背和好,兴兵侵伐,则亦皇天降祸”,显示朝鲜对后金继续对朝用兵有很大的担心。更有甚者,后金在其简短的誓文中还说,“若与金国计仇,整理兵马,新建城堡,存心不善,皇天降祸”。双方不仅不是军事上的协作关系,反而誓文中有明确限制朝鲜加强自身武装的含义。
对于兄弟之盟,我们不可从今天的视角简单地从字面上理解。在1627年的谈判过程中,朝鲜内部对“兄弟”关系的说法也是颇有想法,只是为了避免在和议过程中节外生枝,而勉强接受。1632年,后金遣使赴朝鲜,要求将前已签订的“兄弟之盟”改为“君臣之盟”,并大量增加朝鲜的岁贡要求。1636年,后金更是调集10万大军攻打朝鲜。从双方关系的实际情况看,可以说不仅不是同盟关系,而且带有非常强的敌意。
综合来看,《盟》文讨论的三个两面结盟案例,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弱国在两个敌对大国之间的两面结盟。
在较为宽松的意义上,特别是按照与《盟》文一致的处理方式,把古代东亚国际体系中的一些盟誓行为、朝贡行为理解为同盟关系的话,其他两面结盟的例子也是存在的。如公元前598年郑国与晋国、楚国的关系。以及鲁文公时期,蔡国、陈国这两个国家分别与晋国、楚国的关系。
在错综复杂的欧洲国际关系史上,也存在两面结盟的情况,这特别体现在俾斯麦精心编织的复杂同盟网络中。1881年6月,德国、奥地利、俄国签订三皇同盟条约(第二次三皇同盟),在这个同盟框架内,奥俄关系实际十分对立,特别是两国在巴尔干地区长期存在激烈争夺,最终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此外,在俾斯麦的推动下,德国、奥地利、意大利于1882年5月签订三国同盟。三国同盟通过定期续订一直延续到1915年。在三国同盟内,奥地利与意大利的关系长期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
1887年,俾斯麦通过外交操作在欧洲建立了一个复杂的同盟体系,其内容包括1887年2~3月英国、意大利、奥地利的第一次《地中海协定》,1887年德奥意三国同盟条约的续订,1887年6月德俄两国签订的为期三年的《再保险条约》,以及1887年12月在奥地利、英国和意大利之间签订的第二次《地中海协定》。俾斯麦促成的同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除法国外的所有列强纳入一个彼此密切联系的网络,其最大弱点则在于,同盟网络内的国家相互之间矛盾重重。这不仅是两面结盟的事例,而且是多个存在复杂相互对立关系的国家,通过一系列特定的安排被整合在一个同盟网络中。
在二战后的国际关系中,我们可以找到两面结盟更为典型的实例。1945年8月,苏联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双方建立同盟关系。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与美国保持着更为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双方存在事实上的同盟关系。1946年之后,美苏关系逐渐恶化,美国的外交政策逐渐转向在全球遏制苏联势力的扩张,美苏彼此成为最大的对手。从1945年到1949年,中国国民党政府与美苏同时保持了结盟状态。另一个例子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个时期中,巴基斯坦与中、美两国的关系。此外,20世纪60年代,越南与中、苏两国的关系,也符合两面结盟的情况。在1964~1974年间,越南民主共和国同时与中、苏处于结盟状态,中苏都努力为越南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支持。但在这一时期,中苏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双方还于1969年兵戎相见,发生了珍宝岛冲突和铁列克提冲突。这或许是一个弱国与两个敌对大国同时结盟的最契合且有效时间较长的例子。
对两面结盟的理论解释
《盟》文认为,两面结盟现象的出现需要具备以下条件:一是小国至少有两种重要且仅靠自身无法满足的需求,而两个大国分别只能满足其中的一种;二是两个大国处于彼此均无必胜对方把握的僵持状态,从而可以抑制某一大国对小国采取单方面的强制手段。
从《盟》文所举案例来说,在案例与理论的契合方面存在不足。以高丽与宋辽的关系而言,高丽是否必须通过与北宋结盟来满足其合法性需求存在疑问。在1031年到1070年之间,高丽与北宋之间并未建立朝贡关系,但高丽政权依然能够十分稳定存在,说明与北宋的紧密同盟关系并非高丽政权合法性所必须。
其次,雍熙北伐失败后,北宋的对辽战略由进攻转为防御,两国军事实力的高下已然清晰,辽国占有相对明显的优势。这就使论文的推理出现一定问题。在北宋与辽国对于辽军事优势具有共识的情况下,北宋的存在本身,并不足以抑制辽对高丽采取严厉的强制措施。
《盟》文通过理论分析所提出的两面结盟的两个基本条件,既不是两面结盟发生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其必要条件。这一点,在巴基斯坦与中、美两国的两面结盟,以及越南与中、苏两国的两面结盟的实例中表现得颇为明显。在巴基斯坦与中、美的同盟关系中,巴基斯坦并不需要通过与中、美某一国结盟来确保自身政权的合法性需求,在相当程度上,中美两国都满足的是巴基斯坦的同一个需求,即在面临印度巨大军事压力下的安全需求。在越南与中国、苏联两面结盟的案例中,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处于主导地位,同时与中国相比,其在军事安全领域具有明显的优势,从理论上说,苏联有可能同时满足越南的合法性需求和安全需求。但来自中国的军事援助对越南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越南更希望的是取得“鱼与熊掌兼得”的结果。
由此,对于《盟》文提出的经验困惑,即一个国家怎么会与两个彼此敌对的国家同时结盟,特别是对此作出的理论解释,值得进行进一步的思考。
从巴基斯坦与中、美,以及越南与中、苏两面结盟的案例来看,导致两面结盟出现的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1)弱国希望通过与体系中更多大国结盟,获取更多可资利用的战略资源。弱国面临的安全威胁越严重,其寻找更多大国作为盟友的动机越强。在两个大国严重对立的情况下,弱国会在两个大国之间采取较为灵活的策略,努力避免大国之间的对立延续到它们与弱国的同盟关系中。(2)两面结盟的难点在于,大国能够容忍弱国在与本国结盟的同时,还与自己的敌手结盟。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同盟关系形成的态势,以及大国争夺对中小国家影响力的方式选择。在越南与中苏两面结盟的案例中,中、苏两国都试图通过提供大量援助的方式争取越南,而越南则在大敌当前的背景下,努力避免在中、苏之间决定性地站队,由此在较长时间内维持了政策层面的平衡。在巴基斯坦与中、美的案例中,中、美两国主要是从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关系以及南亚地区的大局考虑出发,并不十分在意巴基斯坦与其他大国的关系。这使得这一双重结盟关系可以以更小的代价持续更长的时期。
这里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弱国与一个大国的同盟关系,不是针对与弱国结盟的另一大国。即弱国A与敌对的B国、C国结盟,只要AB两国的同盟关系不针对C国,以及AC两国的同盟关系不针对B国,这样的同盟关系在理论上就是可以想象的,在现实中也是能够实现的。
(周方银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王旭彤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硕士生;摘自《当代亚太》2016年第4期;原题为《两面结盟现象的再思考——兼评<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两面结盟”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