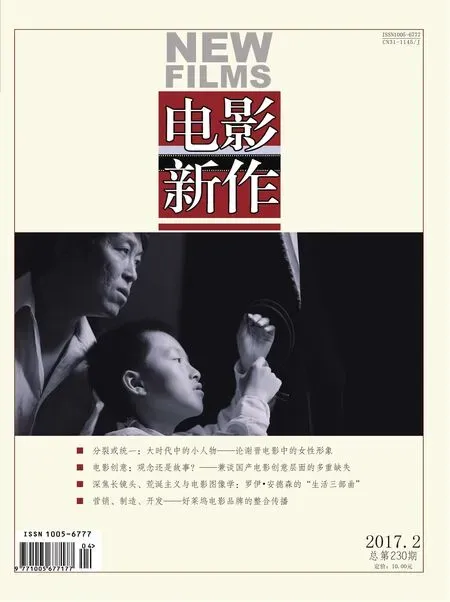在漂泊中寻找
——西奥・安哲罗普洛斯“沉默三部曲”
陈蒙蒙
在漂泊中寻找
——西奥・安哲罗普洛斯“沉默三部曲”
陈蒙蒙
西奥・安哲罗普洛斯被誉为“希腊电影之父”,他不仅领导了“新希腊电影”运动,而且也以其独特的作者电影风格立足于世界电影史。拍摄于80年代的“沉默三部曲”是他转型探索个体生命情感与自由的集大成之作,这三部作品以“寻找”为主题,用悲剧性的叙事空间、长镜头的拍摄手法以及“去戏剧化”的情节安排呈现了个体在历史社会大环境下漂泊疏离的生命形态,揭示了个体生命在“寻根”过程中隐含的“无根”忧思。
“沉默三部曲” 寻找空间影像
“希腊电影之父”西奥・安哲罗普洛斯(以下简称安哲罗普洛斯)是世界级电影大师,从第一部作品《重建》,他就开始了对希腊历史政治、群体命运以及个体存在精神生活近乎偏执的关注,长镜头记录下的悲剧化影像和灰色的叙事基调在其一系列作品中贯穿。拍摄于80年代的“沉默三部曲”(《塞瑟岛之旅》(1984)《养蜂人》(1986)《雾中风景》(1988))是安哲罗普洛斯对个体存在和精神生活的哲学思考,三部影片均有着公路片“在路上”的类型元素,但影片中“所谓‘公路’特色其实只是安哲罗普洛斯进行哲学思考的‘载体’,他是依托诸如码头、海岸线、公路、落寞的村庄、千疮百孔的城市等广义的公路元素来进行心灵探索的哲学思考。”①他以悲剧性的叙事空间、长镜头的拍摄手法以及“去戏剧化”的情节安排完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变奏,从而使他的作品成为充满人文主义的“欧洲式公路片”。
一、漂泊:在寻找中失去
李・R・波布克在《电影的元素》中说:“任何一部影片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主题。如果观众抓不住影片讲的是什么,那就很难指望他们去评论、分析和研究它。如果影片制作者不知道他要说的是什么,他就不可能制作出一部能起交流作用的艺术作品。”②主题是一部电影作品的灵魂和精华,体现了创作者的世界观、价值观和艺术观。
在安哲罗普洛斯“沉默三部曲”中,“寻找”成为共同恪守的主题意象:《塞瑟岛之旅》中曾被流放苏联的老革命分子努力回归故土;《养蜂人》中孤独的中年养蜂人寻找着精神的共鸣体;《雾中风景》中年幼的姐弟则被“父亲”二字牵引,执著地奔向德国。然而“寻找”的旅途却是以不断“失去”为代价完成的:老革命分子被故土拒绝后“乘桴浮于海”③;养蜂人用自己的蜜蜂结束了生命;年幼的姐弟则以惨痛的经历完成成人礼。“寻找”与“失去”的矛盾对立共同构建了悲剧化的影像世界。
(一)寻找即是寻根
“沉默三部曲”中反复纠缠、挥之不去的“寻找”意象,其实亦是“寻根”旅程的表达。《塞瑟岛之旅》中的老革命分子史派洛在被流放35年后重新踏上陌生又熟悉的故土,生于斯长于斯的他在经历了“无根漂泊”后,寻找的不仅是亲人、朋友、归属感和身份认同,他的行为更是对家和“根”的渴望。《养蜂人》里的养蜂人史派洛在女儿婚礼结束后带着蜂箱独自踏上“寻找”之途,人至中年的他寻找的是填补心灵空虚的精神共鸣,同时是生命最原始的纯真状态,他试图以流浪的方式重建生命个体的存在价值,漂泊途中他遇到了爱情:年轻而有活力的少女给予的关爱带给他无尽的想象,在经历了与妻子、女儿和朋友的分别,少女成了他最后的依靠和生活的动力。流浪与漂泊对于渴望“根”的老游击队员和寻找生命存在价值的养蜂人来说是人至暮年的一次生命确认,而对于孩子来说却是一段未知的成长之途,《雾中风景》中年幼的姐弟以流浪的方式表达着对“父亲”执著地追寻,母亲的形象在这里变成了深夜归来的一双脚,父亲形象的缺失更是让“家”这个意象空洞化,寻“父”不仅是填补现实的空缺,也是姐弟俩对生命根源的诉求。此外,在三部影片中,“父亲”作为寻找的主体和被寻找的客体不断被提及:“父”的归乡、“父”的流浪以及寻“父”。“父亲”形象的出现与安哲罗普洛斯童年的经历密切相关,1944年希腊内战爆发,父亲史派洛被极左激进组织“解放希腊人民军”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此后又被莫名释放,期间安哲罗普洛斯与母亲在乱尸堆寻找父亲尸体的经历令他印象深刻,父亲的这段经历成为他多部电影里的情节,“史派洛”这个名字也作为“父亲”的象征出现在他一系列作品中,这样的记忆影射不仅仅是安哲罗普洛斯作为子一代对父辈的缅怀,更让我们看到他以“父”为主体对历史与民族的哲学反思、对生命存在价值形而上的思索和以“父”为客体探讨子一代对父辈的追寻之途。
(二)寻根亦是无根
三部影片里,无论是被流放后重踏寻“根”之途的老革命分子,还是主动以流浪漂泊之态寻找生命存在价值的养蜂人和寻找“父亲”的年幼姐弟,他们的“寻找”之旅都是以不断“失去”为代价完成的。《塞瑟岛之旅》中的老革命者史派洛曾遭遇历史迫害流放异国,时隔多年的归家途却再次变成了离家路,儿女的冷淡、家庭聚会上的格格不入,因其反对政府征收土地,家乡人开始了对他的讨伐,在村民的眼里,曾被政府四次宣判死刑并流亡在外多年的史派洛没有权利搅乱他们现在的生活,村长在门口高喊:“手里拿着枪在山里到处跑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你是死人啊,在军事法庭上有四次被判死刑……你还有把村子搅乱的念头吗?你给我走吧……”流亡数载,故乡变为异乡,史派洛真实存在,身份却被否认,最终与妻子在浓浓的冷雾中“乘桴浮于海”,寻根变成无根,他成了时间车轮下的牺牲品。《养蜂人》里的校长史派洛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死亡,结束了他的“寻找”,昔日好友被病痛折磨、妻子与女儿的冷淡让他的旅途充满孤独和伤感,在遇到年轻而富有活力的少女以后他孤独的心慢慢敞开,少女对他的关爱更是带给他无尽的遐想,已至暮年的他甚至采用暴力手段——用卡车撞咖啡馆玻璃门来占有/夺回少女(生命的存在),然而在荒废戏院的舞台上,史派洛的性无能彻底瓦解了这段暮年爱情,少女离去以后他在阳光下掀开蜂箱,用蜜蜂的毒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寻找生命却断送性命,他在寻找自我中迷失。《雾中风景》里,寻父之旅变成了年幼姐弟二人残酷的成人礼。旅途中,两人不断碰到类似“父亲”形象的角色——舅舅、火车乘务员、巡警、流浪艺人、卡车司机等,这些角色以不同的方式推动了姐弟二人的成长:舅舅以成年人视角残忍地打破姐弟两人的“父亲梦”,并做出了“抛弃”的选择;流浪艺人给予了姐弟两人温暖和关爱,然而同性恋的他让姐姐乌拉萌发的爱情变成泡影;卡车司机则以极端冷酷的方式强暴了姐姐乌拉的身体,展示了人性极黑暗冷酷的一面。最终姐弟二人躲开了枪子,越过边境走到了一棵树下,此时“父亲”象征的美好乌托邦成为带给子一代精神和肉体双重折磨的无望终点。
安哲罗普洛斯曾经在访谈中这样说,“旅行意味着改变,每一次都是新的开始。我很喜欢塞非里斯的诗句‘从一开始就是旅行’。在旅行中,你会更好地认识你自己。我一直在旅行,在我内心的世界中,我喜爱旅行,却是为了对归乡的渴望。”④安哲罗普洛斯用旅行的方式探索了希腊历史和社会环境以及人的生命与精神生活,让观众跟随影片中的角色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心灵旅程,传达了他的哲学思考。
二、空间:心灵之路的外化
电影是时间与空间综合的艺术,这也是电影作为一门独立艺术的依据,空间和时间的变化共同推动故事情节发展,构成了银幕上流动的影像空间,“这正是电影叙事的重要条件和基本特征。画面是片断的,依靠剪辑技巧构成完整的时空复合体,创造一种非连续的连续性,画面又是整体展现,能指和所指呈共时性存在,空间词语成为主要语言手段。”⑤让观众能够通过银幕叙事空间来建构故事空间的意象。
《塞瑟岛之旅》《养蜂人》《雾中风景》三部影片故事发生的环境即是多样性的又有着高度的相似性:阴冷潮湿的天气,雾气伴着雨水下的灰色破旧建筑,人烟稀少的马路,昏暗的旅馆,寂静的车站,海岸边的小饭馆等等,这些的环境共同构建出电影故事里阴暗沉重的物质空间,这样的物质空间在镜头和音乐的作用下成为安哲罗普洛斯叙述话语的载体,也在某种程度上转化为了象征型空间即人物的心理空间/心灵空间,成为人物心灵之路的外化。
《塞瑟岛之旅》的故事空间主要设置在码头、男主角家里、村庄、荒原、海岸等,在这些空间里男主角史派洛遇见了儿子、女儿、妻子、亲人、老友、村民、警察等人,他试图表达自己对故乡的思念与留恋以融入自己的土地,但却与每一个空间和空间里的人发生不愉快的摩擦,最后仍然以漂流大海结尾。史派洛第一次出现是在影片17分钟处,他乘船而归,随着轮船扶梯的缓缓降落进入画面,立在巨轮旁边的陆地上,儿子与女儿则并排站在屋顶与父亲构成俯视视角,此时镜头从儿子女儿身后向前推,父亲慢慢出现,位置处于两人中间,三人构成一个斜面等腰三角形,轮船的巨大与俯拍镜头映衬着史派洛的渺小,儿子女儿处于前景与轮船平视,显得无比硕大,镜头继续往前推变成了二人从高处看向父亲的视角,史派洛则以与镜头相对的方向径直上前,轮船与儿子女儿出画,史派洛由小变大,后景变成潮湿的水泥地。这是父亲归来后与儿子女儿首次碰面的场景,轮船、大海、灰色的天空、潮湿的地面构成了这一段落的物质空间——阴冷、潮湿、无根性,儿子女儿与史派洛的站位以及画面设计构成了人物的关系空间——陌生、疏离、不平等,物质空间与关系空间共同作用于叙事空间,原本属于史派洛的地方对他的排斥性显露无遗,这也预示着他之后回归的坎坷与失败。在接下来的故事叙述中,导演不止一次地运用空间设计来传达人物关系、心理与命运走向:史派洛在家门口下车步行见妻子的几分钟,在横向移动的镜头中,我们看到了人物背景环境由洋楼、柏油马路慢慢变成断壁残垣、坎坷泥路,史派洛“近乡情怯”的感情也逐渐显露无遗;在儿子带着父母和姐姐开车回老家的途中,周围的环境由清晰的高速公路变成雾气缭绕的崎岖山路和群山环绕的土地,史派洛曾生于斯长于斯,这里是他生命的起源,但在这个空间里,辽阔土地、雾气缭绕的群山将史派洛挤压成一个小点,小木屋的燃烧、村民的驱逐与警察的阻挠让史派洛从城市到农村,再次归乡失败。最后史派洛携妻子离开时,导演选择了大海作为空间背景,与史派洛归来时呼应,只是交通工具由游轮变成了一块浮木,相对清晰的天空也变成了朦胧的雾气,这一空间设置暗含了史派洛的心理空间:他带着对故乡的思念和留恋满怀希望而归,但却经历了一次次的驱逐与拒绝,最后只能狼狈逃离。
《养蜂人》的故事依然延续了安哲罗普洛斯一贯的灰色基调与悲剧性主题,灰色建筑、阴冷潮湿的天气一直存在。故事主要发生在便利店、废旧剧院、空旷广场等有着孤独感的场所,在一路的行走中,二人之间的感情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其中便利店、旅馆和废旧剧院是二人发生情感转折的主要空间。史派洛在路边便利店给无处可去的少女买食物并做短暂停留,无意间看到了少女随歌曲舞动,在人迹稀少的公路旁,这样的活力是一抹亮色,吸引了孤独沉默的史派洛,尽管在之后的旅行中他中途放下了少女,但之后还是默许了少女住在他的房间;旅馆是史派洛对少女情感转折最大的空间,也是拉近二人距离的场所,在这期间,史派洛一直对少女有着近乎神话般的忍耐:她的喋喋不休,她拿他的钱出去买烟,她带士兵回房间过夜……但当他看望老友后满怀感伤地回来到旅馆,这种忍耐逐渐转变成了依赖,少女为他细心剃须,旅馆的寂静衬托出少女的热情活力,于是我们看到了当史派洛在妻子那受到冷落后,像热血少年一般,用卡车撞坏饭店玻璃门,打破少女与别人的聚餐并带她离开;最后两人有了肉体的接触,但却是发生在废旧剧院的舞台上,这样的空间安排使得这场爱欲就像是没有观众的现场演出,史派洛的性无能无法满足少女——二人的关系就像戏剧里人物角色一样短暂和虚假,这场戏成了压倒史派洛的“最后一根稻草”。
《雾中风景》再次回归到《塞瑟岛之旅》中的雾气朦胧、阴雨潮湿的灰色故事空间,阴暗的环境与灰色的基调依然贯穿始终,在不同空间遇到的不同人和事推动了姐弟二人的成长。第一次在火车上因没有票被警察带到舅舅那里时,长镜头下巨型的机械和建筑把人物压得无比渺小,这样的工业环境让人变得自私冷漠——舅舅表示无法为两个孩子负责,只能把孩子交到警察手中。随着姐弟二人的继续前行,影片的叙事空间也变得越来越灰暗、沉重,如夜晚两人走在满是积雪的空荡大街,遇见一辆车拖着一匹濒死的马,姐姐蹲下凝视不语,弟弟嚎啕大哭,背景却是一场新人婚礼过后宾客从饭店出来的嬉闹,一悲一喜,衬托了小姐弟俩处境的艰难;姐姐乌拉惨遭强暴一场,导演将其安排到公路边的一辆卡车里,卡车占据了画面的大半,旁边是公路上来来回回的车辆,整个过程在车厢里进行,无声无息,只有画面外弟弟对姐姐的呼喊。施暴过程的沉静与公路上来来回回的车辆形成画面上一静一动的鲜明对比,简单而有力的呈现了环境对姐弟二人的压迫。影片最后,导演将姐弟二人的目的地设置成一个满是童话意味的空间:迷雾渐散,一片绿色的广阔草地上有一颗树,两人缓缓前行,像拥抱亲人一样拥抱了那棵树。这个场景设置是导演做的一个理想的空间想象,在经历了亲人的遗弃、工人的强暴、边境警察的射杀等一系列磨难以后,两个孩子在一棵树上找到了安全感,暗示了成年人世界的冷漠与残酷,“父亲”象征的美好乌托邦成为带给子一代精神和肉体双重折磨的无望终点。
三、影像:长镜头与音乐的二重奏
叙事空间是电影故事存在的载体,是导演传达其电影观念的桥梁,环境作为电影人物的活动空间需要在视听语言的辅助下才能完成现实空间到影像空间的转换。安哲罗普洛斯电影的视听语言最有风格的是长镜头和音乐,在“沉默三部曲”中,长镜头和音乐的完美融合不仅完成了独特的叙事空间设置,而且营造了安氏作品无所不在的悲剧性气氛,更为重要的是,长镜头与旅行都具有不断前进的感觉,两者都是经过缓慢的时空位移而产生新的发现,这种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使得“沉默三部曲”的内涵更为深厚。
安哲罗普洛斯从影以来,始终坚持对长镜头和远景构图的青睐。“长镜头是一种保持现实多义性和时空连续性的现代电影手段,在展现完整现实景象方面有其优越性。”⑥而远景构图又能呈现出一种客观的凝视感,两者结合不仅是安哲罗普洛斯结构电影的一种方式,还达到了“去戏剧化”的效果,更特别的是,他的长镜头并不只出现在个别场景中,而是贯穿所有影片的始终,达到高度的一致性。
《塞瑟岛之旅》中,父亲史派洛从游轮上下来与儿女的对望,镜头从儿子女儿所在的位置慢慢向前推,形成了二人从高处看向父亲的视角,史派洛则以与镜头相对的方向径直上前,轮船与儿子女儿逐渐出画,史派洛由小变大,后景变成潮湿的水泥地。这个单一的镜头一气呵成,但却传达出这个流放多年的老父亲与儿子女儿的陌生与疏离,以及这片土地对老人的排斥。而在史派洛回到曾经居住的村子中后,为了表达对市政府要收购土地的不满,他从小木屋拿起铲子刨地,此时镜头以中远景的方式拍摄,前景是处于画框左侧的小木屋,中景是刨地的史派洛,后景则是反抗示威的村民,再后则是雾气缭绕的群山,在看到史派洛刨地以后,人群开始涌来,其中一个最先走到他跟前,俩人开始扭打,这一过程中,机位始终没有变化,将史派洛对故土的留恋、村民像大山一样对他的压迫排斥表露无遗。这样的长镜头和远景构图也出现在《养蜂人》中,史派洛与少女在分别时,摄影机用长镜头记录了二人在铁轨旁长长的拥吻,并做了往后拉的镜头运动,然后一列火车经过,阻隔在镜头和两人之间,但镜头依然继续,我们可以在火车车厢的接口缝隙看到二人拥吻的状态。这一场景设计充满诗意却亦凄凉,火车作为“旅行/离开”的象征,阻断了呈现拥吻的连续镜头,也带走了少女——拥吻过后,便是少女的离开和史派洛的死亡。《雾中风景》里,警察带着姐弟俩找舅舅的情节中,在工厂外,是一个远景的镜头拍摄,巨大的工厂建筑和机械占据大半个画面,人物走在建筑下十分的渺小,在走进工厂后,安哲罗普洛斯使用了30多秒的长镜头记录了姐弟二人在警察的陪同下上楼梯的画面,这样的画面中,电影人物纤小的身体与巨大的工业环境产生强烈的对比,带给观众视觉震撼,同时也暗示环境对姐弟二人的压迫,后面舅舅的遗弃以及姐姐惨遭工人强暴即验证。另外,在三部影片的结尾,安哲罗普洛斯均使用长镜头记录了人物的结局:《塞瑟岛之旅》中史派洛携妻子漂泊在雾气浓重的海面,《养蜂人》中史派洛将蜂箱全部掀开死于蜜蜂毒针,《雾中风景》则是以长镜头构造出一幅童话十足的理想画面:雾气渐散,姐弟二人在青青草地上拥抱着一棵树。
安哲罗普洛斯用长镜头和远景构图静静的凝视人物和环境,完美地呈现了在历史大环境下人们的精神迷失和对生命的困惑,背景音乐的配合又使得影像整体富有诗意和哲理思辨色彩。“沉默三部曲”的三部作品配乐均出自著名作曲家艾连妮・卡兰德若,她的音乐充满浓厚的历史感和哲学思索的韵味,与安氏作品诗意般风格十分匹配,两人的合作营造出一个个充满诗意、富有哲学思辨色彩和悲剧性的影像空间。
《塞瑟岛之旅》中,大提琴演奏出来的主题乐低沉悲伤,出现在影片的几个场景中:史派洛在下车后见到等候他的妻子时,音乐响起,史派洛步伐缓慢,镜头跟随他的脚步横向移动,此刻他内心的激动混杂着陌生与不安,在音乐的衬托下传达给观众,令人动容;在史派洛遭到村子里的人驱逐的时候,他带着妻子行走在茫茫雪山,背后是巨大的山脉,面前是厚厚的积雪,年迈的夫妻在风中艰难行走,音乐将人物此时处境的艰难和凄凉化成声音配合画面呈现出来,暗含安氏对历史的批判。《养蜂人》以萨克斯风配上卡兰德若所创作的音乐,融合电影中蜜蜂嗡嗡的声音,整部影片充满淡淡的哀愁,使得影片画面上的悲剧性延伸到听觉层面。大提琴为辅音的管弦乐是《雾中风景》的主题曲,大提琴的辅音低沉而具有穿透力,管弦乐急促且悲伤,与姐弟俩在旅途中的悲惨遭遇完美融合,共同营造出一个悲剧化的世界。
艾连妮・卡兰德若曾经在访谈中说:“他的电影承载着有关希腊民族的文化记忆,充满诗意,我们是在互相欣赏对方的创作。而我们的合作——关于电影与音乐的结合,又往往引发出一种很特别的火花,很特别的,就好像能够述说出一些文字也难以表达的东西……很有力量。”⑦艾连妮・卡兰德若的音乐,使得安氏影片独特的时空观念和充满哲理性的故事内容有了牢固可靠的依托,将安氏作品中阴郁压抑的影调与对历史和生命在哲学上的探索展现得淋漓尽致,两人作品完美地融合,带给观众充满诗意与哲学思辨色彩的银幕视听盛宴。
结语
作为安哲罗普洛斯关注个体存在和精神生活的集大成之作,“沉默三部曲”以悲剧化的影像呈现了流放归来的老游击队员、中年养蜂人以及年幼姐弟的“寻根”之旅,影片在视听语言上成功运用长镜头,与主人公内外交织的“旅行”状态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在音乐配合下与环境融为一体,营造了符合影片主题的悲剧化叙事空间。结合他早期和90年代之后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安哲罗普洛斯穷其一生都在对历史和生命做哲学上的探索,一直在为艺术电影拓展疆界,坚持着自己“作者电影”的创作风格,作为世界电影大师,安哲罗普洛斯就像他电影里的主人公一样:一直在电影的旅途中行走,寻找电影的生命之根,以一颗悲天悯人的心剖析社会历史,关注个体生命。
【注释】
①薛澈.生命漂泊中的永恒求索——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世界(硕士论文)[D].保定:河北大学.2007.
②[美]李・R・波布克.电影的元素,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8):102.
③出自《论语・公冶长》,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④河西.专访安哲罗普洛斯——旅行是对故乡的渴望[J],《外滩画报》,2007.4.11.
⑤郦苏元.中国早期电影的叙事模式[J].当代电影.1993(06).
⑥赵春霞.西奥・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研究(硕士论文)[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7.
⑦本文原刊于台湾《电影欣赏杂志》,2005年10-12月期,来源于http://blog.iweihai.cn/.
陈蒙蒙,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