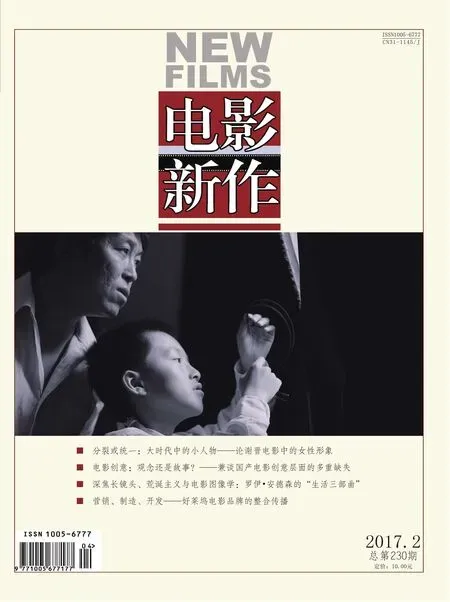黑泽明电影《乱》的佛教视野和美学思想
郑绍楠 郭小丽
黑泽明电影《乱》的佛教视野和美学思想
郑绍楠 郭小丽
黑泽明的电影《乱》是由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改编而来,导演将故事背景置换为古代日本,并以佛教视野来观照乱世中的众生相。他在原作基础上增添了三个人物来代表人类对待苦难的三种态度——复仇、美和佛教的宽恕。在此视野下,他看到仇恨是“乱”不断循环的根源;而乱世中的美除了安慰苦难者,还担负“天问”的责任。《乱》中所持的美学不是日本避世的恒在美学,也非安住现世的无常美学,而是企图借美沟通接近救赎彼岸的宗教美学。
《乱》 宽恕 复仇 佛教视野 美学
黑泽明拍摄了日本的《李尔王》——《乱》①,两个几乎一样的故事,但一个来自西方,一个来自东方,他们的思考会有什么不同呢?更重要的是他们看待问题、思考问题视野又是如何呢?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基督上帝始终没有正面出场,但是却始终在场。这种上帝没有出场的在场所呈现的恰恰是莎士比亚在写作《李尔王》或自觉或不自觉的神性观照人性的视野。在此视野之下,他超越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人的伟力和人性高贵的一味讴歌,他看到了人性背离神性之后自我膨胀所显露出更为根本的处境——人的渺小和平庸、卑鄙和疯狂,更重要的是,人在背离神性之后,并没有强大到身处存在的深渊而无须神圣之爱的地步。而当人类背弃神圣的时候,其实也背弃了这种圣爱。当李尔失去象征圣爱的考地利亚,神性之光就此熄灭了。他再也找不到活下去的希望和理由,发疯和死亡变成了他最好的救赎和解脱。那么在具有“电影中的莎士比亚”之称的黑泽明的电影《乱》,这一东方版的《李尔王》里,导演又持何种观照的视角呢?他在这种视角看到了什么呢?
一、李尔与秀虎、《李尔王》与《乱》
莎士比亚的剧本中的李尔没有过去可言,他只有在剧本里的当下,当下选择,当下承受,因此莎士比亚写了李尔的不幸,没有写李尔的恶,他有过错,但这过错配不上那样巨大的惩罚。如仓央嘉措所说的,“一个人需要隐藏多少秘密,才能巧妙地度过一生。”②莎士比亚不描述李尔的秘密,不描述他安然度过世间的动荡,双手沾染的是什么。秀虎在黑泽明的作品里不止愤怒和任性,手上的血腥和灵魂的邪恶,才是黑泽明着力体现的。秀虎在“人”之外还是“罪恶的人”,李尔仅是单纯的“人”和当下的人,他没有过去,这是不同之处。黑泽明在这位年老的主角身上添加的丰富意蕴,这使《乱》这部作品有了与《李尔王》不同的走向。如果说莎士比亚作品的基督教视野的观照是不自觉的,那么佛教视野的观照就是黑泽明很自觉地提出来的。在关于“乱”的平息上,莎士比亚以考地利亚这个天使般的人物,提出了“人间的或天上的爱的救赎”。黑泽明则提出了关于“乱”的平息的不同方案,而这些面对“乱”的不同反应和表现,都是他关注的重点。
我们先具体考虑引起“乱”的要素。《李尔王》中是两姐妹的自私、欺骗、嫉妒,哀德蒙的野心、贪婪,李尔的受蒙蔽,最终引起的义或不义的战争;《乱》除了这些要素还特别加上了“复仇”。正是从“复仇”出发,或者说是从对秀虎的罪恶的“复仇”出发,黑泽明开掘了与《李尔王》不同的故事层面——“乱”的“平息”。秀虎既是乱的制造者,又是乱的承受者,既是杀戮者,又是被复仇者。复仇是对罪的报复,复仇作为一种行动,是实施者面对仇恨的极端方式。之所以极端,是因为复仇又制造了新的仇恨,它是使仇恨滋生繁殖、无限衍生的行为。然而实施者却是将复仇作为“平息”内心仇恨的一种手段在使用的。既有了乱,便有仇恨,既有仇恨,便有平息。复仇作为“平息”仇恨采取的其中一种方式,是无法让人接受的,它更大程度上使“乱”更猖獗,这又何来真正的“平息”呢?这让我们思考了平息仇恨其他的方式,如逃避、原谅等。这些方式,包括复仇,黑泽明在他的作品里利用阿枫、阿末和鹤丸提了出来。因而,从这里开始,我们要引入《乱》在《李尔王》的基础上所添加的一些人物的分析,即引入黑泽明在莎士比亚的“乱”的基础上试图做的“平息”的努力的分析。
二、复仇与宽恕
在电影《乱》中,持“复仇”态度的人物是阿枫。持“宽恕”态度的是阿末。我们先来分析这两种方式和这两个人。“复仇”之所以是关键性的要素,是因为它把“乱”循成了一个环。杀人掠城的秀虎参与制造了乱世的“乱”,阿枫的复仇,使事态回到了混乱的起点。以乱报复乱,由乱到乱,成为一个循环、一个轮回,并且永无止境。对比《李尔王》的“乱”,乱既是祸由又是结局,果又转成因,人堕入永世轮回,令人心怵——面如此悲惨的世间,我们不禁会这样想:人为什么会堕入永世轮回?这样的因果相循有终止的一天么?或者它可以靠什么来阻断呢?在现世里人能否自救?如果能够自救,那他也就不会一次次重蹈覆辙,历史也不会一次次陷入纷争和混乱。如果不能自救,那么我们能够从哪里寻求解救的办法呢?关于这些答案,我们在这里还是不得而知。
我们再来具体分析阿枫这个人物。阿枫是个生命活力强大的女人,野蛮,残酷,一个仇恨浇铸的女人,心中容不得佛。她太清楚生存的残酷和生存之道,她知道战场上的厮杀,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战场如此,情场也不例外。她杀害阿末只是为了独占整个的生存空间。但是究竟是什么令她感到阿末的威胁了呢?若是为了她在次郎身边的位置,她不必采取这样极端的手段,她完全可以牢牢把握住次郎的心。何况她心里只想利用次郎,而并不在乎他身边有什么人。那么她所感到威胁的是阿末面对仇恨的另一种解决方式么?只能这么推断。她并不原谅阿末面对仇恨的另一种方式,若一切都如阿末所说的是前世宿缘,那不就承认了她所承受的与阿末一样的苦难有合理的依据么?亲人白白地被杀害,城池白白地失去而无法归咎,一切只是“前世宿缘”而已。且面对面前的仇人她所采取的报复行为也被否定了。她把整个生命的意义都托付在复仇上,而阿末和阿末所信仰的佛否定了复仇,也就否定了她的生命意义。因而她争夺的不是生存空间,而是托付于复仇行动的整个生命意义。她要杀掉阿末,原因是容不得阿末或者说佛对罪孽的原谅。仇恨的双方,即阿枫和秀虎,都容不得佛,是出于同一个原因。我们理解了阿枫对于阿末的态度,我们接下来可以分析一下秀虎对阿末的态度,会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仇恨的双方,即罪人和复仇者对佛是一样的态度。
秀虎对阿末说,我宁愿你恨我,“我要你仇视我,这样我较不难过”。秀虎无法抹掉他所犯下的罪孽,他对幸存者的亏欠无法用什么来补偿。他的歉疚只能在他收取仇恨,也就是在遭受人的仇恨的惩罚中才能减少自己的罪恶感。也只有受到惩罚了,才能稍微减轻他的罪恶感。对他来说,这种惩罚就是别人对他的仇恨。因此即便他受到心灵折磨,认为他自己罪孽深重,却还是在理智上赞同相互残杀。他知道罪恶不能减少,一直深重,他必然要背负罪孽,但是阿末并没有对他的罪孽做什么,她并不用仇恨来惩罚他,因而他只能双倍的自责。他能对阿末做什么呢?他能对佛做什么呢?所以他说,“这世上没有佛”,承受不幸的人恨那制造不幸的人才是正常的。他知道自己的罪孽不可原谅,拒绝佛对他的原谅,“这是不需要佛的时世”。相互残杀相互仇恨才是扯平。在这样的相互仇恨——仇和报仇中现世取得了一种平衡,有了存在的可能,甚至是存在的合理。既然是我们自己承认了相互仇恨相互厮杀的历史的合理,我们还能奢望在这种合理之下,人类能够有治乱平息的一天么?然而秀虎一直拒绝的,或许正是黑泽明想给出的解答。我们无法依靠“复仇”,我们或许只能从彼岸世界、从现世之外,寻来解救的办法。阿末已经制止了一场混乱,然而最悲观的结局是,阿枫还是杀了阿末。人类丢掉了佛,罪恶仍在肆虐。在黑泽明《乱》的剧本中这样写道:“佛陀的画像被撕成了碎片,夜幕降临,它在夕阳下的最后一抹余晖中,闪耀着金色的光芒。佛陀的脸看起来十分悲伤。”③而目盲的鹤丸,象征着人类的无助和无明。
作为幸存的人,鹤丸是值得分析的人物之一。在三人中,只有他幸存了下来。我们其实可以说导演刻画了三个女人,阿枫和阿末之外,鹤丸其实是被设计成能剧中的经典角色“疯女人”的形象④,他穿的是女人的衣服。一则是能剧的角色,二则笛子在鹤丸的生命历程中的重要性,那么,鹤丸象征着的,应该是艺术是美。阿枫对应的是复仇的人,阿末对应的是宽恕的佛,而对应鹤丸的,是另一个超越层面——艺术和美。
三、美之救赎
接下来我先分析一下日本的“美”的传统,然后再联系至这部作品,我想这样也许能让我们更明白作者的用心。
《源氏物语》里引有《古今和歌集》中的句子:
为爱春花好,心常住野边。
但教花不落,我欲住千年。⑤
花之美,月之好,人们希望永远沉醉其中才好。
《徒然草》里却有这样的句子:
倘若无常野的露水和鸟部山的云烟都永不消散,世上的人,既不会老,也不会死,则纵然有大千世界,又哪里有生的情趣可言呢?世上的万物,原本是变动不居、生死相续的,也唯有如此,才妙不可言。⑥
万物因变动不居,才妙不可言,世界和人生,因而才有趣。它讲究一个生的情趣,如蛙之跳入池塘⑦,“生”要打破静寂;如鱼之浮游沉潜,见首不见尾,无常理、无恒真,才成就无常之美。虽然现世的确是无常,但在作者的态度中似乎有给人“故意”“自觉求此”的感觉。不无常才不美呢,人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自觉求美,变成了对无常的心安理得。
前者为自己构造一个幻美之境,在这个世界里,人不会老去,心常而物常。潜义是,人为无常烦恼,因而常有逃遁野边的意趣,往往向往着此世之外的美之净土。⑧这其中没有忧世,因为我们难以想象贵公子会有这种意识,他们只是在美的不恒在中生发对现世的排拒意识,表现出对美的一味沉浸。对他们而言,也许美的不恒在就是他们所体会的苦难。他们当然也饱尝人生,但人生的失落与否,是以美为标准的。因此若说他们饱尝人生也是不假的,他们饱尝人生之美绽放的喜悦与凋零的失落。因此他们很有可能在现世之中虚构出一个云上世界。后者中,人已经摆脱这种烦恼,并不向往净土或来世,不向往此世的另一世,此刻的另一刻。浮生观、现世的享乐思想、珍视无常的观念,似乎与前者相比是一种更为积极的人生态度。但从他们的表现来说,也是一种对美的沉浸。只是这种美因易逝而更显珍贵。因美的存在,似乎一瞬有着永恒的力量。就人生的过程而言,因为世间之物善于变化,又有“变”之情趣。就像一味静寂的池塘,蛙的一跃一跳,是禅意,是生趣,让人感觉生命的那种新鲜跃动的感觉。然而这种态度,很不可靠,除非是隐居,除非是不介入,除非是旁观,不然不能超然。这种对现世的审美,是无根基的,是以跳脱人生之外为代价的审美。这两者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自觉求美,自觉以美的视点来观照世界。心可能“纯洁”无比,却无视现实。
对于日本这个“审美就是日常”的民族我们在小津的电影中也有更多的体会。审美弥补了无常成为日常,这似乎是很多人向往的境界。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小津的电影《宗方姐妹》中,节子与宏道别后,见了满里子,把心里的想法告诉满里子后,两人走出户外散步。
节子转身,看到京都的山,便问:“满里子,京都的山为什么看上去都是紫色的?”
满里子答:“真的,真的是紫色的,像是红豆糕的颜色。”
红豆糕这样的比喻,令人觉得不可思议,可是仔细一想,发现无论红豆糕还是京都的山都是美的,足可处于相等的地位。把美比作日常之物,其实很适宜,也让人感叹,这感叹是对于京都的山,还是对于红豆糕,都给人初惊讶而又回归淡定的感觉,红豆糕一样的京都的山啊。美是日常,人们见美,起先是心惊,世上有如此美物,仿佛它是天上才有的东西,然后发现它自然地与人们记忆的习惯的日常连接了起来,所以又继而给人一惊后又心安理得的感觉。美总是有距离的,是身外之物,但连接到日常,却可私有,是属于人的生活的,这是很微妙的体会。在日本,富士山是极美的象征。林夕的歌词“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⑨,这对于日本民族来说倒是有可能的。这种美,又让人想起茶道,因为茶道里浸透着人情,所以也使人发自内心地感到美。茶道的繁复,像是一种珍重的仪式,专注贯一,身心都在里面,因此从仪式之中能感到一种心灵的境界。在日本的许多“道”中,形式和心灵,是融为一体,是不可分的,形式绝不是外物,形式的美也绝不是外物。⑩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在日本似乎是人生的一种标准,美又是那么容易能够触及到人生的终极。在日本,美触及到最日常的人生体会——美是日常,人生的终极问题又是在日常生活中疑惑而生发,所以美作为标准和价值之物,也参与了这些问题的解答,而且通往解答的路径似乎尤为便利,所以无论是避世的爱美者,还是现世的享乐者,都从美这个字眼中找到了家园。
大致了解了美在日本人民的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之后,我们就进入正题。在电影《乱》里,鹤丸这个人物身上,惨痛的人生与笛声天籁交织,惨痛和美交织。而这在上述几个例子中似乎都没涉及,小津的电影体现的往往是日常的无常,是种无奈的感受。但是黑泽明的这部电影中,痛苦的极剧以及人生的残酷给人的是感觉是极震撼的。那么,对于鹤丸来说,美是否是救赎呢?如同那些避世爱恒在的美,或旁观于人生之外沉浸于无常之美的。在如此惨痛的人生背景下,美是否仍然是救赎?或说,若仍是救赎,那么这种救赎与前有何区别?
大概很多人都思考和感受着《乱》的电影画面的最后定格:鹤丸站在古老的城迹之上,丢失了佛的画像,在远处的笛声是他不能遗忘的天籁,然而笛声并不来自天上。没有笛,没有佛,一个孤瘦伶仃的人,在永恒的黑暗无明中无助而不幸。我们悲痛地看到:黄昏中,鹤丸孤零零地站在城墙上,迎接人间的黑夜,他一直身在其中的黑夜,或许还迎接着白日,如同黑夜一样的白日。
笛子对鹤丸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无法想象在之前所有的日子里,在狭小的木屋中,他是怎样度过那些漫漫长夜的。那笛子,为何会发出那样凄厉的旋律,使人听了骇然惊惧。他是靠着姐姐送给他的笛子度过这些时日的,然而他说:虽一直努力去作,无日忘此恨。鹤丸忘却不了仇恨,但在笛声中他得到了某种安慰却是事实。我们从影片中得到的关于鹤丸的笛声的印象,是这笛声让人惊骇。这区别于美的事物给人以美妙的感受印象。鹤丸的笛声大概听起来像凄惨的哭声,对痛苦的不平的哭声,所以才会给人惊骇的感觉。鹤丸并没有超然于痛苦,但是痛苦以“美好”的形式表达了出来。这样的笛声是给谁听的呢?孤独度岁的鹤丸希望谁能听见呢?
在哲学家海德格尔看来,伟大诗人的职责在他的作品中自觉采纳“神性的尺度”以度量自身和万物、是在无神性的黑夜时代寻求重建与神圣者的联系。也就是说,真正的诗人,正如荷尔德林一样,“在神圣的黑夜中,走遍大地”,真正的诗人有一种“天问”的精神。在无神的黑夜里,诗人必是那个以“祈求的人”的形象,行遍大地的人。
孤独留下来的鹤丸,黑泽明让他留下来,就像是作为导演自己的化身,那无助的影子,是否是在“天问”呢?看过电影的,大概都会给出肯定的回答。我们大概也很容易想到,他的笛声,是此岸与彼岸的交流,来自此岸的哭声因而到达彼岸,来自人间的哭声因而悲悯于神佛。黑泽明为人类丢掉佛感到悲痛,同时留下了人类在永恒轮回里受苦的哭声,以表达这样的渴望:这个破碎的生命需要求全于佛。
我们希望如此,旁观的你我,都看到了导演的用心,希望破碎的既定事实能够得到弥补。但是,同时我们确实无法直接得出鹤丸的笛声和孤弱的影子是在求全于佛这个事实。我们无法忽略的是,鹤丸忘不掉仇恨。他自然需要救赎,但是他似乎没有阿末的性格特质,他也似乎并不完全理解信仰佛的阿末。鹤丸或许是廖伟棠提到的“在河底仰望河水的人”。既渴望超越痛苦,但还是一味沉浸于痛苦,虽然他自己不愿如此痛苦下去。只通过艺术形式表达痛苦的鹤丸,审美世界为他提供了什么呢?笛声仅是表达痛苦的途径或出口,而不意味着其他什么吗?在宗教视野的观照下,笛声只是来自此岸的受苦的哭声吗?我认为确实如此。而导演表达到此就已足够。答案该由我们自己得出。正如廖伟棠的那番话所言:
“纵然你不需要救赎,救赎依旧在为你预备着。诗歌亦然,在河底仰望河水的人,必然因为河水里流淌的这些短歌望见更高处的世界。”
黑泽明是把鹤丸作为“在河底仰望河水的人”来塑造的。鹤丸必然会因为河水里流淌的这些短歌望见更高处的世界。如此痛苦的鹤丸,这个形象本身就传达出渴望救赎的祈求的意味。纵然鹤丸以为自己不需要宗教的救赎,但鹤丸总是在寻求着其他的救赎,寻求其他救赎的同时,宗教的救赎依旧在为他预备着。黑泽明当然不希望仅仅“望见”而已。但是望见总比望不见好。借由诗歌,正如导演借由电影,鹤丸借由笛声,让我们望见并渴望那个更高处的世界,这样已是伟大。
因此在这部电影里,美并不是救赎的方式,是渴望救赎的哭声。相比于一味回避痛苦的享乐主义者和避世者,在笛声中一直痛苦下去的鹤丸,是更“趋向”于佛的。佛虽超越痛苦,但却是一直痛苦下去的人,因为这世间的苦难无法超越。在对待世间苦难的态度上,或说在对待痛苦的态度上,平凡的人类总是想讲求更有效率的方式,回避、绕道而行,包括以苦为乐的石头心肠也是其中一种,但这是很难让人尊重的态度。
结语
《乱》中对待仇恨和不幸的三种态度,分别是仇恨、美与宽恕。我们通过分析阿枫和阿末,通过宽恕与仇恨的对比,更从电影里看到,恨只能使混乱的事态更乱。但是失落的佛像,似乎已经失落了,这是悲观的结尾。然而这结尾里还有一个羸弱的幸存者,这个幸存者曾经靠着笛声度过了黑暗痛苦的岁月。这里的笛声不像是逃避的忘忧乡,更像受苦的人的哭泣,这受苦的哭声,是来自人间,而上达天听的,是天问,是渴望救赎的哭声。因此,在《乱》里,美并不是作为一种超越苦难的方式,而是作为渴望救赎的哭声而存在的,导演表达出这样一种趋向,这哭声是趋向于佛,趋向于信仰的。
因此,我们能够得出,莎士比亚对爱的思考,黑泽明对宽恕、恨与美的思考,都是在宗教的视野下进行的。基督教的爱的观念,似乎是从原本充满苦难的人生中另辟一条蹊径,苦难是不得不承受的,但爱是更高的意义,爱是通往幸福的唯一途径,爱帮助人们到达苦难的另一端。苦难在人生中的比重不断加大,然而爱能与之抗衡,在这种抗衡之中,爱通向的幸福因而与苦难处于平等的地位。而佛教,似乎有一种直面的凌厉。悲悯世间众苦的同时当头棒喝,点破人类的盲目无明。人类自食恶果,自然是要直面自己的无明,这其中有一种自省的力量。也因此,宽恕的意义是对于整个人类的,对于别人的宽恕也是对于自身的。也正是借助于这一佛教的视野,黑泽明使其电影美学超越日本传统的避世的恒在之美学,和安住现世日常的“无常美学”,而形成一种独特的宗教美学。
【注释】
①[黑泽明.乱[Z].东宝国际公司发行,1985.]
②苗新宇,马辉.仓央嘉措诗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54.
③[美]唐纳德・里奇.黑泽明的电影[M].万传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0:309.
④[美]唐纳德・里奇.黑泽明的电影[M].万传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0:306.
⑤[日]紫式部.源氏物语[M].丰子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517.
⑥[日]吉田兼好.日本古代随笔选[M].周作人,王以铸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337.
⑦[日]松尾芭蕉,与谢芜村,小林一茶.日本古典俳句诗选[M].檀可译.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88:12.
⑧邱紫华.东方美学史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050.
⑨林夕.富士山下[Z].香港:新艺宝唱片,2006.
⑩邱紫华.东方美学史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098.
郑绍楠,华侨大学中文系讲师。
郭小丽,集珍文化有限公司编辑。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华侨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审美主义研究”(项目编号:13SKBS218)阶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