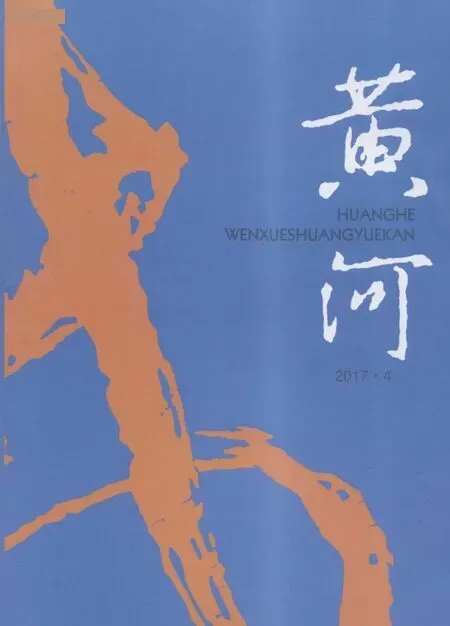黄河边墙(之三)
岳占东
E:桦林堡的落叶
一
如果将历史比作一片飘零的落叶,那么当落叶离开树梢,洋洋洒洒飘向大地时,我们无异于是站在树下的孩子。叶落归根是世界的法则,我们张开迷茫的双眼看到的却是一个落英缤纷的世界。
站在桦林堡古旧的城墙下,我很想找到那片白桦树曾经飘零的落叶。那片叶子轮廓分明,叶脉清晰,金黄色的叶面上有婴儿般稚嫩的绒毛。落叶飞舞在黄河岸畔的山岗上,在秋日的阳光里像太息的目光迷离地看着这个纷乱的世界。我知道,在这仄仄的街巷里,四百多年前的落叶早已化作了一粒微尘,只有眼前这座残缺不全的营堡像一位久经风霜的老人,为我们默默诉说那片桦树林曾经有过的美丽。
翻开地方志,关于桦林堡的记载只有寥寥数语:桦林堡,明宣德四年(1429年)建堡,后因套虏攻而废。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兵使赵彦修复,二十九年(1601年)包砖,周1里零72步,高3丈5尺。几句简单的言辞,简单得让人有点窒息。黄河边墙从老牛湾沿河一路南下,到桦林堡这儿才算建起了一座真正的营堡,而史家却惜墨如金,犹若那片曾经有过的白桦林,留给世人一个美丽的背影,让人在落叶的五彩缤纷中追寻这处山岗之上曾经有过的景致。
据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和明代《皇明九边考》记载,从宋代太平兴国年间到明朝初年三百多年的时间里,这里依然是林木繁茂的山岭。高大的树木合抱入云,低矮的灌木密如切栉,而且虎豹出没,人迹罕至,是地地道道的原始森林。到了明朝中叶,朝廷在这里颁布禁伐令,但据《明经世文编》记载:(伐林者)百家成群、千夫为邻,逐之不可、禁之不从。林区被延烧者一望成灰,砍伐者百里如扫。到明朝后期偏关守关将领才宽在 《巡边赋》中感慨,(黄河边墙一带)已经是“天高愁涧壑,荒边无树鸟无窝”的荒凉景象了。应该说,在宣德四年,那片白桦林依然挺拔在这处黄河岸畔的山岗之上。
沿边一带之所以发生大规模砍伐林木的现象,与这里增加了屯田戍边的常住边民不无关系。拓荒种地,大规模放火烧山,成了原始森林被毁的主要原因,而且边关狼烟骤起,行军打仗林密草长骑不能入,也成了放火烧山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据《明宣宗实录》记载,宣德七年(1432年)九月,就连镇守山西都督佥事李谦都上书朝廷,请求初冬调拨大同宣府兵马在黄河边境要冲之地烧荒,因其“草木茂盛或有寇盗往来难于瞭望”。至于百姓伐木建房,砍柴烧火却成了最平常不过的事情。沿边修筑边墙营堡,砍伐高大的树木建成厚重的栅栏,用于军事防守更是明代最早采用的防御办法。像明初的大边就是一道长长的木头栅栏,还有黄河对岸的马栅,都是用高大的树木修成围栏,防御蒙古铁骑入侵的工事。到宣德年以后,黄河两岸的山岭基本上是沟壑纵横黄土裸露满目疮痍的景象了,沿河烽台十里八墩,炊烟袅袅,村舍与烽台成了继原始森林之后最为密集的物体,林立于苍宇之间。
山西都督佥事李谦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爬上桦林堡这处山岗的,与周围光秃秃的沟壑相比,这处山岗在丽日的阳光下显得特别静谧,高大的白桦树东倒西歪遮蔽了整个山岗,树枝横斜相插,脱落的桦树皮斑斑驳驳,微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愈发显得整个黄河岸畔宁静而悠远。
作为统揽山西军政要务的封疆大吏,在爬上这处山岗前,李谦已沿着晋陕峡谷的黄河东岸巡视了一圈。着手北方边务几十年来,他从最初负责督建烽台的都司指挥同知,到辅助山西都督管理全省军务的都督佥事,在他的眼里沿河十里八墩的烽台原本已是固如金汤。那些蒙古鞑子的骑兵孤军深入内地流窜侵袭,寻找的都是最为薄弱的关隘,沿河一带只要狼烟四起,喊声震天,凭借黄河天险,就足以能让入犯的鞑子兵望而生畏,闻风丧胆,临阵脱逃了。因此几十年来,黄河一带的军事防务一直相安无事。可自从宣徳皇帝朱瞻基登基以来,北方游牧民族各个部落之间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退居漠北的元廷,西北部的瓦剌都在困顿中悄然崛起,就连原来归顺大明帝国的兀良哈三卫也开始蠢蠢欲动。朱瞻基几次申饬兵部大臣说:“天下尽管无事,边防却必须严格管理,尤其是西北的要害处更为重要。这些地方军官和士卒共同戍边日久天长,一旦有逃跑的士卒,军官可能鉴于情面不好严加管理,因此五军都督府要及时会同六部衙门议处此事,严加考核边务。”尽管如此,但边关的局势日渐紧张,逃跑的士卒也日益增多。当他被朝廷任命为山西都督后,这种现象更是与日俱增。在宣德三年,仅太原右卫15076名士卒中,就有1713人逃跑。发生这种现象,对于生死存亡的边疆来说,是天大的事情,士卒逃亡绝不亚于战场上全军溃退而更加影响士气。因此,作为都督他必须亲临烽台关隘,实地察看原因。
在沿河戍守烽台的士卒那里,他了解到士卒之所以逃跑,大都是因为边将不体恤士卒造成的。克扣军粮,随意使唤士卒,甚至鞭打责罚士卒之事时有发生,更令士卒恐惧的是,随着鞑子兵侵袭频繁,几处烽台几个堠围已完全无法阻挡敌人的弓弩,因此为了活命士卒不得不冒着被诛连九族的危险结伙逃跑。当他听完士卒的话,才突然想起前不久皇帝下诏让边将体恤士卒的旨意,看来皇帝下诏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皇帝朱瞻基早己察觉到了边关的实情。上谕的原话是这样的:国家餋军士,惟在抚恤,有素得其心,然后得其力,比闻各卫军多逃亡,皆由将领者不能存恤,夫军士在行伍,一有征调朝令暮行,不敢辞劳。所以朝廷餋之,惟恐不至月支粮饷,岁给布絮尤虑其失,所为将领能体此心,平素善加抚恤,临敌之际协力同心,必能成功。为将而不达此,不悯其劳,又虐使之,甚至减克粮赏,以致饥寒切身,无所告诉,不逃何俟?如此,国家何望得军士为用,尔即榜谕武臣,务存恤军士,不许生事虐害,违者罪之。
皇帝的旨意和沿河士卒所告的实情让李谦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站在桦树林的山岗上,遥望黄河对岸黑森森的山崖,他觉得蒙古部落的势力是不能再小觑了,也许有朝一日对岸的山崖上,就会扎满蒙古部落的毡房,这从近年来大同总兵屡屡向山西都司借兵就能察觉得到。大同总兵郑亨,一个牛皮哄哄的人物,自以为是一个侯爷,又领衔边关要害之地大同行都司的总兵,屡屡拿着兵部的虎符向山西都司借兵,最多一次借去13000名的兵马,让山西沿边一带无兵可派。要不是他冒死上书朝廷要回大部分兵马,就是沿边士卒不再逃跑,山西的守卫也会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后来发生的无数历史事件证实,宣德三年(1428年)山西都督佥事李谦巡边直接促进了沿边营堡的建设。这处长满桦树的山岗,从李谦注视它的第一眼开始,就注定将成为一个营堡所在,那片片飘零的落叶,将伴随着大明戍边士卒走过一个又一个秋冬。边关的所见所闻深深地触动了李谦,在那一年逃跑的士卒中,他只是象征性地处罚了领头的几个人,让其戴枷示众一月,然后按律全家发配甘肃充军,而对其他士卒则令其返回原地不予追究。在宣德四年,朝廷在偏关设立山西镇,由李谦兼任山西镇第一任总兵官。也就是从那一年起,沿河的营堡在光秃秃的黄河岸畔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水泉堡、滑石堡、桦林堡、楼子营、灰沟营、唐家会营、保德营等十几座营堡相继筑成。至此黄河边墙的格局,由烽台时代进入了营堡时代,戍边的士卒终于有了赖以守候的营城。
桦林堡建成后,李谦派驻一名守备统领营堡,领兵735名,骡马70匹,分守数十里的河岸墩台,其中烽台42座,大小隘口33处。一处原本落叶飘飘的山岗成了战马嘶鸣的兵营,而那些高大的白桦树成了掩护营堡的天然屏障,站在黄河对岸,也许能听到风吼马叫的声音,但莽原苍苍,一座营堡却被深深地锁在桦林丛中。
二
当鞑子兵第一次冲上这处山岗,眼前的营堡在树叶沙沙的声响中温馨得像一处鸡犬相闻的家园。要不是周围的烽台狼烟弥漫,山沟里喊声动地杀声震天,他们还真以为在这处桦树林掩映下的山岗必定是一个村庄,里面有牛羊、粮食,还有女人。
这是大明成化十九年(1483年)的盛夏,距营堡落成已经过去半个世纪。这一年,鞑靼首领小王子率领3万骑兵,东西连营50里,浩浩荡荡一路南下,大有始祖成吉思汗气吞山河的阵势。半个世纪以来,无论大明帝国的内部,还是北部的蒙古部落都发生了许多令史学家大书特书的事情。明英宗的“土木堡之变”,于谦的“北京保卫战”,景泰皇帝的“夺门之变”都是影响一个王朝根基的大事件。蒙古部落中的阿鲁台、脱欢和也先父子、脱脱不花、达延汗、满都海和小王子巴图孟克夫妇都是那个时期叱咤于草原之上的风云人物,在他们的不断征战讨伐下,蒙古草原各个部落之间,分分合合,风起云涌。也先父子统领时代是瓦剌强盛,到满都海和巴图蒙克夫妇统领时,鞑靼又从草原上崛起,可以说整整半个世纪,蒙古草原像一块块不断漂移的浮萍,马蹄的践踏和圆月弯刀的挥舞就从来没有消停过。此次小王子巴图蒙克率兵南下,正是鞑靼部落崛起后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也预示着,曾经兵患不断的北部边疆将进入又一个战乱迭起的时代,桦林堡等沿河营堡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桦林堡的守将们一直在为提高营堡的军事防御能力而构筑各种工事。他们加固各个隘口的壁垒,增加沿河烽台的数量,将沿河烽台由黄河下游的阳沔堡一直修到桦林堡东部偏头关的山岗上,只要一有敌情,营堡之间的烽台就会狼烟四起相互传递信息。作为沿河烽台与东部烽台的连接点,桦林堡附近的烽台担负着由西到东,由南到北的信息传递任务,只要狼烟升起,山西镇总兵便能根据狼烟升起的方向迅速判断敌情,然后集结各营堡的兵马对被敌军围困的营堡实施援助。据《偏关县志》记载:宣德七年(1432年),兀良哈由段家村入犯偏关,李谦设伏黄草梁,擒其酋长。十年(1435年),兀良哈再犯偏关,指挥江梅、千户包让等战死。虽然史料记载简略,但从中可以看出,兀良哈部落入犯两次,结果却一胜一负大不相同,其中缘由多出自救援及时与否,而救援的首要条件是来自烽台的预警狼烟。据《三晋古近代战典》记载:景泰元年(1450年)5月,瓦剌军进犯河曲东南,杀虏人畜甚众,尔后,瓦剌军专攻河曲东南方向的神池义井屯堡。明军指挥佥事刘守安等两名指挥率军迎敌,遭致全军覆没,附近守军坐视不救,瓦剌大掠而去。这次瓦剌专攻义井屯堡,有意避开了山西镇沿河营堡烽火预警组织救援的军事部署,没有直接入犯沿河其他营堡,致使偏头关的指挥中枢没有接到沿河预警,附近守军自然是不敢贸然出战。由此可见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尽管来自沿河的战事并不多见,但桦林堡分设的42座烽台仍旧承担着沿河烽火预警的重要任务,营堡内的绝大多数士卒要轮流守候烽台和各个隘口,只有休息下来的士卒能在营堡附近的山坳里开荒种地,能放松身心呼吸一番桦树林里的清新空气。
到成化二年(1466年),当总兵官王玺准备修筑沿河边墙,进一步提高沿河营堡的防御能力时,桦林堡所管辖的关河西口、寺沟都成了修筑边墙的险要地带。修筑夯土边墙需要大量的木材来做墙板,沿河所剩无几的粗壮树木在那一场工程浩大的修筑边墙的工事中,大都消耗殆尽了。桦林堡及其它营堡的士卒,都成了修筑边墙的苦力。虽然没有详尽的文字资料记载修筑边墙的具体细节,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此浩大繁重的工程都是分段完成的,桦林堡所辖的沿河边墙,都由七百多名戍边士卒赤膀上阵来修筑。可以想象到,在空寂的黄河岸畔,桦林堡的士卒个个生猛如黄河之蛟龙,他们欢快地举着石硪,和着悠扬的节奏,一齐唱着打夯号子:太阳滚滚落西山,鸟投树林虎归山。行路客人都住店,千家万户把门关。士卒们完全将自己的兴致融入到了愉快的劳作中,这种看似简单的劳动比起蹲烽台守隘口固然繁重,但是堪破生离死别的士卒们一旦走到一起便分外觉得红火热闹,比起冷冷清清的烽台和隘口,尽管修筑边墙需要出力流汗,可他们潜意识里更愿意凝聚一起以彰显生命活力。他们的这种豪情同样感染了居住在营堡内外的家家户户,可以想象这样的场景:姑娘们一遭一遭地往河畔跑,说是到护宁寺上香还愿,眼睛却老往那些筑墙的年轻士卒身上瞟。她们年老的父亲或许便会狠狠地瞥女儿一眼,女儿不理会,继续寻找一个似曾熟悉的背影。老父亲便狠着声骂:脸比桦树皮还厚!剥了一层又一层!随姐姐同来的小儿子头上戴着桦树枝条编成的凉帽,一眼看到了挖土的父亲,便高喊:大大!大大……大大是鞑子人留下的称呼,士卒们修筑边墙阻挡鞑子人入侵,可他们却阻挡不了鞑子人在他们祖祖辈辈身上留下的印迹。
从成化二年(1466年)王玺第一次修筑黄河边墙开始,鞑靼和瓦剌犯边的次数便逐渐频繁起来。成化元年(1465年),瓦剌军兵犯河曲阳沔堡;二年(1466年)鞑靼由大同犯边;三年(1467年)二月鞑靼毛里孩部入犯大同、朔州,三月玛拉噶部入犯大同,五月再次入犯大同;五年(1469年)鞑靼入犯延绥;六年渡河入犯河套……到最后干脆直接住在了黄河对岸的绥远,直到成化十九年(1483年)鞑靼首领小王子巴图蒙克率军大举犯边,再次攻克沿河营堡阳沔堡,让沿河烽火由南向北一直烧到偏头关城。
这一次大规模的战乱对于沿河营堡的确是一次生死考验。鞑靼军沿着河岸一直左右突袭,到桦林堡的山岗上时,眼前的营堡让疲于作战的鞑靼兵不禁为之振奋。只见桦林葱茏,壁垒森森,一座营堡在树木的掩映下酷似世外桃源的村庄,树林外面的山坡上梯田层层叠叠,山路纵横交错,一派夏日田园的勃勃生机。凭着多年征战的经验,鞑子兵一看便知道这是一处肥富的兵营,堡内的粮食牲畜自不必说,就连堡内躲藏的女人,也一定面若桃花。鞑子兵按捺不住的抢掠欲望,让他们变得异常勇敢。那一天的攻城,双方打得非常激烈。自从成化二年偏头关设立御守千户所以来,关内凭添了几千名士卒,各个营堡内兵力大增,而且从正统年间开始,山西镇又增设了整饬兵营的兵备道,从营内的武器配备、兵卒的日常操练,甚至防御和作战方案都加强督促力度,使得营堡的防御能力明显增强。
那一天的战役究竟结果如何,史料未予明确记载,但可以想象得到,堡内堡外一定火光四起,营内的士卒除了引箭,已经广泛使用火铳,关城内架设的火炮是否也被抬到了这处山岗也未可知,因此堡外的桦树林在战火中也许就在劫难逃了。至于这处营堡,在鞑子军异常勇敢的攻击下,城破是再所难免的,《偏关县志》所记载的“后因套虏攻而废”,也许就发生在那一次重大的战役中。
那一年的战乱整整持续到次年开春才稍稍平息。鞑靼军先后深入大同境内,纵兵焚毁代王朱成錬的庄园,攻克朔州、应县等地,设大营于马邑,攻占雁门关北口。同时攻克偏头关以北的水泉营、滑石涧堡,以南北夹攻之势攻占山西镇沿边营堡。据资料记载,仅超过千人的战役就有10次之多,攻克大同的夏米庄之战中,杀死士卒586人,伤1101人,杀死战马1070匹,在其它战役中沿边百姓被掠走的人口、牲畜更是不计其数。
一座曾经美丽的山岗和营堡,随着那一片桦树林的消失,在光秃秃的黄河岸畔已与其他地方别无二致。沿河的边墙仍旧岿然不动,营堡破了仍旧可以重修,但永远无法找回的却是那一片郁郁葱葱的生命和黄河岸畔曾经飘荡的打夯号子的声音。
三
桦林堡再次出现在史学家的视野中,是在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
《读史方舆纪要》载:桦林堡在偏头关西二十里。万历二十七年建堡,二十九年增修,周一里有奇。西去黄河三里,与套寇东西相望,边外红漕等处,即贼巢也。
此时的桦林堡那种曾经落叶飘飘的景象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桦林堡因被套虏所废,边墙上的所有防务直接归属偏头关直接管理,直至隆庆二年(1568年),下游的河保营驻守山西岢岚道河保路守参将,黄河边墙才开始分段管理。偏头关分管桦林堡以北的边墙,护宁寺寺前墩(护宁寺为元代建筑,明代一直香火不断)以南的边墙由河保营管辖。隆庆五年(1571年),史上著名的“隆庆议和”后,边墙上的战事基本上偃旗息鼓了。沿边一带建立互市,偏头关北边的水泉堡,黄河对岸的麻镇、皇甫川堡等地都互开马市,边墙和各营堡的防务由此转入建设阶段。
万历年原本是明朝的中兴时期,尽管后来的史学家在研究明朝没落的原因时,认为崇祯皇帝的悲剧从万历时就开始埋下了伏笔,但万历一朝的兴盛却是不容质疑的事实。据《明史》记载:万历十年(1582年)是明朝最为靖昌的时期,太仓里的积粟可支用10年,国库余银多达400余万两。出现这种政绩炳然的局面,其功劳当属以首辅张居正为核心的内阁集团施行的“万历新政”。也正因为此时的明朝国力鼎盛,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万里长城,才会岿然不倒地屹立在各处的山岗之上,当然也包括这处被鞑靼军毁坏的桦林堡,才有机会重见天日。
谈到万历朝,张居正和戚继光这两个曾经影响明朝内外大局的肱股之臣是无法绕开的关键人物。他俩一文一武,虽然彼此在朝中地位不可妄加评判,但张居正的“万历新政”直接奠定了万历年间国家兴盛的基础,也正因为有了这种国库充盈的局面,戚继光在建立新军,围剿倭寇,修筑边墙上面才能得以大展宏图。因此说,张居正内阁集团励精图治的改革,让万历年曾经出现昙花一现的中兴迹象,戚继光大兴土木修筑长城(边墙),也让大明帝国的北部边疆呈现出固若金汤铜底铁帮的赫赫国威。可惜这种盛极则衰的规律,犹如老牛湾“乾坤图”的魔咒,让我们这些后人在嗟叹之余,不得不多了几分思考。
据《明史》记载,张居正的改革有着雷厉风行的手段。他先从改革吏治入手,所谓“治国先治吏”应该是百试不爽的经验,提出“考成法”制度来提高各级官府的办事效率。“考成法”是监督官员办事效率的办法,简单地说就是各级官员将每一件需要落实的政务都书面呈送朝廷,落实了一件,消除一件,落实不了的朝廷都要追究责任。这样一来,朝廷政令畅通了,各级官员也不敢消极怠工了,出现了“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的局面。吏治有了成效,张居正便开始改革赋税,从经济上治理国家。万历元年(1573年)冬,他主持裁撤冗官冗费,并开始限制皇室费用。万历五年(1577年),他建议清查丈量全国土地,使土地面积由弘治年的400多万顷,增加到700多万顷,整整增长了300多万顷。在此基础上,开始实行“一条鞭法”,在税赋方面推行新制度。其内容主要涉及四个方面:一是统一役法,对人口众多的田庄大户实行“摊丁入亩”,不再区别银差和力役,一律征银;二是田赋及其土贡一律征银;三是以县为单位计算征收赋税;四是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张居正的“一条鞭法”直接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为以货币为核心的“资本化经济”提供了土壤,这也就是为什么万历年间的中国社会会零星地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原因。
可以肯定地说,货币化了的经济对于戚继光修葺长城(边墙)有着极大的好处,无论是雇佣劳力,还是生产建筑材料,都能达到社会化的最大化程度,让如此庞大的工程成为货币化驱使下的军民共建工程。据史料记载,戚继光在修葺边墙时,墙身加高加宽,以砖石包砌,墙上两侧建女墙,垛口以尖砖修砌,垛墙下有悬眼,墙上建空心敌楼,墙内侧修筑登墙小门,并建驻军老营,墙外侧修牛马墙或铲斜坡、挖品坑,有的地段还修筑重墙,使边墙建设达到顶峰。这样细致入微工艺极高的要求,绝不止仅凭苦力能完成的,应该是天下的能工巧匠都汇集到了长城脚下。
桦林堡作为废弃了的营堡,能重新被确定为恢复修葺的老营,与黄河边墙分段管理不无关系。桦林堡虽然距偏头关城仅二十里,但从防御体系上看,桦林堡属于从老牛湾到石梯子的沿河营堡,而且桦林堡作为黄河边墙北段最后一个营堡,堡外有边墩15座,火路墩7座,边口12处,需要一座集中驻守士卒的营堡来管理。
于是这处曾经落叶飘飘的山岗再次成为人马鼎沸的地方。负责营城修筑的是岢岚道兵备副使赵彦,他组织潞泽二府征调来的三千多名士卒,再一次让桦林堡的高墙屹立在黄河畔的山岗上。白桦树消失了,林涛声声还回响在当地人的耳畔旁,落叶消失了,片片如飞的蝶影还隐隐闪现在人们的眼前。桦林堡一个美丽的名字,在刀光剑影的铁血边关再次破茧而出,为沿边士卒留下了一缕暇想的惬意和温馨。
桦林堡的山岗呈不规则的正方形,东西长约186米,南北长约198米,四周全是陡坡深沟,只有东北一角于东面的山梁相连。新建的营堡东西北三墙各有马面两座,用于防御敌军攀爬。堡墙四角都有角楼,只留有一座南门,门外有方形瓮城,瓮城为东门,外有影壁。营城的结构仍旧承袭了“葫芦城”的形制,将东西北三面最为坚固的部分朝向了边墙。站在西面的城垣上,沿河边口尽收眼底,黄河对岸历历在目。史家称其为雄踞河岸,看来不假。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以后,桦林堡设操守1员,中军1员,领旗军300名,马骡10匹,分管沿河边墙46里。清初置防守1员,军200名,隶偏头援兵营。后设都司1员,千总1员,外委2员。同治时制千总1员,外委2员,隶偏关营。在明朝后期,边墙和营堡上的一些附属设施,逐渐演化成沿边居民聚集居住的村庄,如担水沟、寺沟等村庄都是与边墙和营堡同年代留传下来的地方。像庄窝、梨园等村庄都是后期发展成村落以后,由沿边居民生产生活的场所演变而来的。
桦林堡,一座曾经保留了黄河岸畔勃勃生机的营堡,历经岁月风尘,留给我们一段空灵的遐想。走进桦林堡,我们的眼前仿佛有数不清的落叶簌簌地飘下,耳畔仿佛仍旧能听到树叶随风而起的沙沙声响,还有那种草木馥馨的芬芳仿佛沁入我们的心脾。而面对古堡,我们更多地听到的是那一段战马嘶鸣的喧嚣,看到的是滚滚烽烟下,相互搏杀的如蚁的人群。
F:石城口的梵音
一
很多年以后,当石城的百姓说起石崖下的石洞,仿佛还能隐隐听到黄河对岸那个放羊娃的吼声。那声音稚嫩而悠长,在两岸的石崖上回响不绝。最早听到这吼声的究竟是石城的百姓,还是石城口戍边的士卒,人们无从知晓。可当人们听到那一声稚嫩的吼声后,石城所有的人才知道在他们的脚下绝壁上,裂开了一个深不见底的石洞,石洞里居然出现一尊栩栩如生的佛像。
如果没有这个怪诞的传说,祖祖辈辈居住在石城的百姓无论如何想不明白,在百丈高的黄河石崖上怎么会平白无故出现一个深不见底的石洞,而在通往石洞的绝壁上又咋会出现一条鬼斧神工开凿出来的石径?在石城百姓的意识里,只有那一声放羊娃的吼叫,最符合他们冥冥之中对未解之谜的臆想,也只有在这种臆想里,那一尊端坐在石洞里的佛像才会寄托他们对人生的无限遐想。
关于那个放羊娃的吼声,在石城的百姓嘴里有多个版本,其大概的意思是说:黄河对岸有一个放羊娃,每天在崖畔放羊。一天,他听到黄河峡谷里传出一声雷霆般的喊声:我出来呀!空谷回音久久不绝。放羊娃站在崖畔上寻找人影,对岸石崖上却空无一人,峡谷之内除了涛涛河水,也无舟弋通过。这样奇怪的事情一连三天,天天如此。放羊娃很是惊奇,回村后便和村民说起这件奇怪的事情。村上有人指点他说,再听到喊声你就回应,看看到底是何物。第四天,放羊娃又来到石崖畔放羊,果真那一声雷霆般的喊声又从幽谷里传出。放羊娃便仗着胆子高声吼道:你出来哇!吼声刚落,黄河对岸的石崖下便“哗啦”一声巨响,山崖崩塌,石洞显现,一尊金身弥勒佛腆着翩翩大腹笑嘻嘻地端坐在石洞之内。
放羊娃的吼声是不是真有其事,人们无从考证,一尊弥勒佛现身石洞,想来也仅仅是传说罢了。可石城之下的石崖都是如刀削一般齐茬茬的绝壁,石崖崩塌石块滑落时有发生,所以放羊娃吼声过后,石崖崩塌显现石洞倒是合情合理的事情。
当大明帝国的总兵官王玺精神抖擞地骑着快马来到黄河岸畔,实地勘探边墙修筑的地势时,护宁寺里悠扬的钟声已经为这道平静的山坳罩上了祥和的色彩。石城的百姓在晨钟暮鼓中看鄂尔多斯高原上云起云落,听黄河峡谷内浪涛鸣溅,间或有驮水的毛驴喘着粗气从河畔狭窄的石板路上爬将上来,驴蹄敲打石板发出的“嘎登嘎登”的声音清脆而悠长,愈发显得整个黄河岸畔空阔而又宁静。王玺铿锵有力的马蹄声搅扰了石城的平静,石城百姓真以为有什么祸事波及到了他们这处原本僻静的山坳。多少年来,石城北边的桦林堡不时地有遭受鞑子人袭击的消息,也时不时地有躲避战乱的百姓从黄河下游的楼子营、灰沟营逃难到他们石城,可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身着银光闪闪盔甲的将领骑着高头大马将他们的石板路踩踏得震天响的阵势。
百姓的惊慌让王玺的脸上留下了一丝淡淡的微笑,可当他听说黄河岸畔全都是悬崖绝壁,就是鞑子兵长上翅膀也无法从悬崖上爬上来时,他那一丝淡淡的微笑一下子化作了轻松的长吁。那一刻他突然明白为什么护宁寺的钟声那么从容而镇定。
为管制冗长的军事要塞,王玺虽没有在石城的黄河畔修筑边墙,但还是于成化二年(1466年)在护宁寺与石城遥相呼应的隘口处修筑了规模盛大的边口。这是黄河边墙26个边口中较大的隘口,口上的堡垒全部由石城当地石头修筑而成,是名副其实的“石城”。堡垒呈拱形环绕河岸,分上下两层,下层修筑边门,顺着石崖上的羊肠小道能直达黄河峡谷底部。上层修筑有营房,可供戍守士卒居住。石城口戍边的职责由下游的楼子营守备负责,戍守的士卒每到换防时,楼子营所辖十处边口和墩台一齐轮换士卒,从楼子营周围最近的马连口、沙口、饮马口到山区的董家梁墩、石城口、牛角尖口、吴峪口、董家庄墩、井角尖墩、高峁墩等地,五十名士卒由营堡出发,按照编制名额分赴各个军事要塞。边口最多的十人,最少的墩台仅两人,石城口居于二者之间,只有五名士卒戍守。应该能想象到,一对五十人的队伍,从楼子营高大的城门口出发时,还浩浩荡荡,像一支有模有样的武装部队,可随着各处分散,一支队伍最后完全变得七零八落了。石城口离营堡最远,他们五名士卒沿着黄河畔逶迤前行,队伍的形制已经没有了,他们慢慢腾腾行走在河畔的羊肠小道上,手中的兵器已经和下地劳作的普通百姓肩头上的锄头没有多大区别,要不是一身的戎装闪烁着猎猎寒光,谁会想到他们就是大明帝国北拒胡虏戍边的士卒?
走在空旷的黄河岸畔,脚下是崎岖不平的山崖,崖下是滔滔不绝的河水,百丈崖壁犹如刀削一般陡峭笔直,看着都让人头昏目晕,仿佛踩在浮云之上而令人心惊胆寒。再看两岸的山峁,焦黑的岩石跌宕起伏,低矮的蒿草稀疏零落,河风吹过,一种宛若铜韵一般的声响丝丝地从耳边掠过。抬头望北去的苍穹和幽深的峡谷,满目的荒凉和悠远尽显其中。那一刻,行走的人便渺小起来,总感觉到自己像飘零在塞外的一片落叶而无所依着。
士卒的心情也许并没有这么低沉冷落,他们每天巡回于石城的堡垒上,对岸就是蒙古铁骑的行营,偶尔有飘忽不定的旌旗出没在对岸的荒草丛中,伴随着低哀的号角声仿佛一刹那间就要横冲过来。士卒们知道那些鞑子兵是在虚张声势,这一溜烟的黄河绝壁还没有谁能创造单枪匹马冲过来的神话。听石城的百姓讲,自从一个远游的和尚在这黄河绝壁之上建起护宁寺以来,就从来没有两国交战的兵马光临过他们石城。士卒们看着旌旗飘动的鞑子兵,就高声挑衅:过来哇!有本事你给爷飞过来呀!喊出的话被穿河的大风撕得粉碎,不管鞑子兵听到与否、听懂与否,他们都抱着长矛哈哈大笑,将一肚子的寂寞无聊肆无忌惮地抛撒向了对岸的敌人。
没有鞑子兵的身影,他们更多的时间是默默地聆听从护宁寺里传来的钟罄的声音,间或也有琅琅诵经的声音随着穿河风飘进他们的耳朵。经文的内容没有人能听得懂,可诵经悠扬的旋律却令他们如痴如醉。在这战马长嘶的边关要塞,一曲绵长的佛音犹如天籁之声让他们孤寂的心灵有了片刻安宁。士卒们都是见过生死的人,北边的桦林堡,下游的楼子营、河保营不时地有蒙古铁骑狼奔豕突的身影,鞑子兵每一次袭击,都是血流成河横尸遍野,边墙内的百姓自不必说,就连他们营堡内的弟兄也死伤无数。能驻守石城口这样没有战事的堡垒,他们从内心感谢上天的眷顾。护宁寺里下河驮水的和尚路过他们石城口时,也时不时地向他们讲经说法,佛法的缘由他们听得糊里糊涂,可他们记着和尚的一句话:谁信谁好!
他们是该相信和尚说的话,护宁寺所在的这段边关要塞千百年来奇迹般地成了一片净土。自元朝建寺以来,在古寺重修碑记中从未有战火的记录。寺中的碑文这样表述石城口所在的地势:……崖岸陡立,如手臂而环划者,然所少者,巨灵之掌迹耳。河至峡中,束伏安帖,不得施,其排奡(傲)之势而出龙口……这处陡峭的黄河峡谷,犹如巨灵神的手掌劈开一般,就连咆哮怒吼的黄河流到此处都服服帖帖。大自然的造化庇佑了这里的安详和宁静,也让这里的人浮想翩翩,于是一种宗教情怀便飘然而至。人们在忽生忽死欲弃不能的两难境界寻求一种精神寄托,他们幻化了大自然的杰作,将万物注入了灵性,所谓天地人神鬼都在冥冥之中相互通灵。
当有一天,石城口不远处的那一声放羊娃的吼声再次伴随着护宁寺的钟声响彻黄河两岸时,一座石径禅寺便在石洞的悬崖边上开始香火缭绕,再次昭示了黄河边墙之上宗教情怀的张力。
二
明代兵部尚书阎鸣泰于崇祯五年(1630年)巡游“三关”时,为宁武关庙宇撰写《重修五岳庙碑记》云:楹宇宙皆气。气以其灵者虚,而为神秀者育,而为人厚者重,凝结为山岳,无两物也。然神栖无象,每籍境以耀其光,境室有形,援神以彰其胜。所为斡旋有无之间,以佑神而福民,则人力重也。……夫鬼神明昭祸福之应,而示人以劝以惩;佛祖秘握神鬼之机,而令人自造自化。……尝考五岳,分掌世界一切山川人物之理,其神最显,惟与天齐,独秉人生寿算福禄之权,其功无巨。而大德好生,则天仙圣母与观自在、如来所称。上同诸佛慈心,下合众生悲仰者等一化育。……从此,神气相依,精诚昭格,凝釐衍庆,祝圣寿于万年,殓厉除氛,巩皇图于亿万。愈久愈远,弥炽弥昌,必知有共天壤而无极者矣。
崇祯年间的宁武关已经是山西镇总兵官的治所,偏头关、雁门关、宁武关长城内“三关”都在其统领之下,黄河边墙属于外长城的延伸部分,自然不在话下。作为军事最高指挥官,阎鸣泰的观点无不弥散着一种宗教的情怀与力量。应该说,从成化二年(1466年),到崇祯五年(1630年)一百六十四年的时光中,大明帝国北部边疆的形势已经经历了由对峙到交融的历史阶段,边墙之上的营堡和关寨大都修葺了庙宇,无论是道家的道观,还是佛家的寺院都一起青烟缭绕法器轰鸣,边墙内外的善男信女无不跪拜在神龛之下诉说着自己的愿望,就连边墙之上的将士也开始神神叨叨,大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架势。
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一个朝代发展的趋势。
宗教情怀是人性缺憾的一种弥补,在人性无法企及的地方,宗教的力量总是默默地发挥着一种无法替代的作用。朱元璋来自佛家的寺庙,自然深谙宗教的力量。据明朝徐学聚编著的《国朝汇典》记载,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以城隍显灵助明军取胜的理由,赐封城隍为“监国司民灵护王”,从此城隍一步一步被确立为大明帝国的神祗之一。城隍庙作为明朝府、州、县大小城池主要的庙宇,成为上至官方要员下至黎民百姓顶礼膜拜的祭祀场所。据朱元璋在洪武四年(1371年)的一次祭祀上指出,他之所以大兴城隍庙,就是“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因为在道教的神祗中,城隍是城池的守护神,人在阳间的所作所为,在死后都要经历城隍的审判。作为开创大明帝国的君王,朱元璋的这一宗教思想一直影响着整个明朝的宗教兴衰,也得以让宗教信仰在帝国各级官员和黎民百姓中深深扎根。
在黄河边墙十八处营堡和二十六个隘口的军事要塞之中,大大小小的庙宇星罗棋布不下百座。虽然从碑记上看,一些庙宇重新修缮于清朝,但其实际建立时间却远远早于庙宇的修缮时间。所谓“明修长城,清修庙”,其实清朝时期修缮庙宇的地方,在边墙之上大多是明朝的关隘营堡,而这些曾经驻军的地方,在大明帝国与北方对峙的时候,已经是香火缭绕了。明朝的军队在自己戍边的地方不仅需要修葺阻挡蒙古铁骑南下延绵不断的边墙(长城),还需要修葺自己心灵归宿的庙宇。
石径禅寺从石城口“崖崩洞现”那一天起,就注定会成为延绵百里的黄河边墙之上的一个诡异的传说,这也是它之所以成为宗教场所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百丈高的悬崖上,一条石缝在层叠的岩石之间形成一条时断时续的石径,石径直通石洞,石洞内的石像呈弥勒佛形态,洞府故名“弥佛洞”。石径在悬崖断开的地方,如若悬空而置,只有借助树木之类的横木才能通过,故而起名“悬空界”。佛家的禅理总在有形与无形之间为信徒们设置秘而不宣的感觉,在朝圣的路上,万象奇异,崖石峥嵘,已经让信徒们感觉到佛的无所不至了。
天生而成的“弥佛洞”仿佛聚缘了黄河岸畔超自然的灵性。对岸的蒙古铁蹄只能望“崖”兴叹另辟蹊径了,彼岸的戍边士卒在石城的边口,默想人生繁华,玄幻来生宿命,梦里的情景定然有江南水乡的橹声。南来的士卒在边墙上苦守岁月,他们内心的憧憬有如这石崖一般坚不可摧,他们相信这从天而降的弥勒佛定然会庇佑他们实现夙愿,一座石径禅寺装满了大明帝国戍边士卒一份沉甸甸的心思。
三百多年以后,当我走入这处仍然称为“石城”的村庄,伸手触摸着这座已经破败了的古刹时,在这异常荒凉的黄河岸畔,我仿佛仍旧能听到那一声放羊娃的吼声。那吼声应该是一种来自心灵的召唤,是戍边的士卒和永居石城的百姓面对塞外长河从心底里发出的声嘶力竭的吼声。吼叫凄厉却转化成了乐呵呵的应答,于是在这历经百年的古刹里仍旧能找到大明帝国经久不绝的印迹。
首先是“兜率宫”,这是道家始祖太上老君炼丹的地方。道教在明代是被广泛世俗化了的宗教,特别是在嘉靖年间,道教不仅在民间广泛流传,明世宗朱厚熜甚至将其定位“国教”,而在皇宫大院举行斋醮活动。荒芜了的石径禅寺虽然是在近代的民国初年由佛教弟子真空和尚重修,但寺庙的格局仍旧承袭了明清时期的形制。禅院的上下两层分别建有佛教和道教的庙宇,像如来佛祖、地藏王菩萨、太上老君、城隍、土地、财神等佛道两界的神仙都云集于此,接受众多善男信女的顶礼膜拜。而至今遗留在门楣之上“兜率宫”的字样仿佛告诉人们,即使在佛祖显身的崖洞之上,被皇帝奉为“国教”的道教始祖仍需分得一碗羹。
其次是在城隍庙或者土地庙前 “叫夜”的习俗。边墙脚下的村镇至今保留着明代流传下来的丧葬习俗,亡人安葬前一天夜里,亲友孝子都必须敲锣打鼓到村口的五道神庙或者土地庙前“叫夜”(也称“叫庙”),意思是将亡人的魂魄从庙里叫回,以便第二天安葬以前送出,让亡人的魂魄随遗体的安葬进入冥界。这是朱元璋当年赐封城隍遗留下来的一项丧葬习俗的重要仪式,城隍负责审判世人在阳间所犯的所有罪孽冤屈,五道神和土地神都是其下属。世人亡故后,其魂魄都要被索命的黑白无常带到城隍庙或者村口的五道神和土地庙里进行审判,一般为期七天,七天以后审判后的魂魄才能根据审判的结果进入冥界,继而决定来生轮回。如果世人在阳间作恶多端,审判的时间会更长,第一个七天仍需“叫夜”,孝子需要多备贡品,以此通融小鬼,让亡故的亲人少受折磨。如果病故时间是春节前或者病故的日期正好“犯七”,亡人在阳间的罪过将更大,“叫夜”时孝子需要准备与亡人岁数相同的白色三角小旗,从灵柩前一直沿路插到庙宇前,以防止亲人备受折磨的魂魄找不到归家的路。即使安葬后,在“过七”的祭日里,孝子仍需准备小旗,从灵柩曾经放置的地方一直沿路插到坟茔,好让亲人的魂魄能顺利进入冥界,重新投胎做人。石城的百姓至今仍旧恪守着这种丧葬习俗,尽管在“叫夜”仪式上由于年代久远,与边墙沿线其它村庄多有不同,但大致的丧葬步骤基本一致。
石城戍边的士卒应该是践行这种宗教仪式的第一人,他们修筑了庙宇,将自己活着时的愿望寄托于祭拜神灵的袅袅青烟中,将死后的灵魂安放在神灵的累累牍案下,尽管他们曾经手握嗜血的兵刃,但活人就要活得敞敞亮亮,死也要死得明明白白。这种大大咧咧的性格,与苍凉的塞外大漠,粗犷的莽原丘陵,咆哮的滚滚黄河相应对。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沿袭几百年的宗教情怀奠定了北方边墙沿线居民特有的性格特征。
三
黄河边墙之上的寺庙,从护宁寺开始沿河一字排开,成规模的寺院除护宁寺、弥佛洞、石径禅寺外,还有吴峪洞、香山寺、岱嶽殿、禅房寺、三官庙、海潮庵等。这些寺庙都依傍边墙之上的营堡或者隘口,从古至今都是人群聚居的场所。可以想象得到,自古以来,黄河两岸都是兵戎相见的地方,当自然的干旱和战争的峰火让荒山秃岭大漠孤烟成为这里自然环境的常态后,一拨一拨来此戍边和打仗的人、或者是被朝廷流放到这里的人,当他们面对这块荒凉之地,内心的恐惧、慌张、忧郁和希望该往哪里存放和寄托。当大自然以诡异的方式为这里生活的人雪上加霜时,是谁又能拯救他们极其脆弱的心灵?寺庙自然而然地作为通灵的场所进入黄河两岸的隘口和营堡,进入每一个被强权、战争、自然挤压得无法喘息的内心深处。
纵观这些寺院,无论是最初的道观,还是佛家的寺庙,他们在宣扬自己教义的同时,无不与风水勘與、测字算命、作法道场等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活动相联系着,到最后连庙里的道士和和尚也分不清,究竟哪一项活动是出自道家,哪一项活动是来自佛家。加之佛道之间的相互交融与渗透,及其善男信女对诸神的顶礼膜拜,一座原本单纯的庙宇便成了佛道融合的场所,殿内所供奉的神像也不再分清佛道之间的区别,完全成了神仙大聚会。
吴峪口是石城口下游的边口,这里同样有佛家的洞府,只不过吴峪洞不像弥佛洞那样由崖崩洞显自然形成,它是北魏年间由人工开凿出来的石洞。石洞的天工巧成和洞内的深邃幽暗,同样为宗教的传播增添了神秘的力量,当从楼子营分道而来的戍守的士卒走上吴峪口,远远看着如墨的洞口和缕缕升腾的青烟,他们的内心世界会呈现出何种状态呢?他们会想到佛家的缘生缘灭吗?会想到因果报应吗?会想到六道循回吗?守着吴峪洞的和尚和戍守吴峪口的士卒,在黄河岸畔的群山之中同顶一块蓝天,他们一个恃刀而立,一个教化众生。应该说兵家和佛家是殊途同归,他们都致力于社会秩序的建立,只不过一个是以暴制暴,一个是以德报怨。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是佛家的叹息;所谓兵者生死存亡之道也,这是兵家的本义。在佛家那里,生和死只不过两种形式的转化,在兵家眼里却是荣誉与耻辱的天地之差。吴峪洞的开凿承载了两千多年前北魏王朝的梦想,也似乎是专门为这个兵戎相见的地方贴了一块标识。戍守的士兵每天守在敌人随时可能出现的边口上,手中的刀枪尽管可能被鲜血染红,可耳畔隐隐飘来的佛音,还是让他们内心深处有了某种坚守和奢望。
躲在唐家会营堡东北向阳山坡上的岱嶽殿仿佛比佛家的洞府更具某种力量。因为这是一处道家的庙宇,其主神是道教的东岳天齐仁圣大帝。民间传说姜子牙助武王灭纣后,敕封诸神,黄飞虎为东岳天齐仁圣大帝,总管天地人间吉凶祸福,领地在五岳之首即东岳泰山,又因东岳大帝被加敕一道执掌幽冥地府十八重地狱,而泰山别称“岱宗”,“嶽”又为“岳”的异体字,有山中之狱的意思,因而将此庙称为“岱嶽殿”。
在大明帝国,岱嶽殿的力量是不言自明的,这当然与朱元璋敕封城隍有关,因此,尽管这处道家的庙宇建于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天会十二年(1134年),但据史料记载,在洪武六年(1373 年),正德四年(1509 年),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均有修葺。岱嶽殿面朝黄河,河对岸就是陕西延绥镇边墙的起点,沿岸的边墙与对岸的边墙正好交汇在岱嶽殿的山脚下,加之有唐家会渡通衢两岸,这里便成了人烟辐辏的所在。在一处黄河岸畔的山岗之上修筑一座供奉东岳大帝的庙宇,道家最初的用意颇有点处心积虑。因为岱嶽殿里所供奉的神祗是最为包罗万象的,被道家称为“七十二司”的神祗,在岱嶽殿的庙宇里均能找到。“七十二司”的神祗执掌着人间的七十二种俗事,这种与世人生活的密切相关,对于道教的传播远比洞府的神秘更为有效。按照明清以来道家的说法,东岳大帝不仅主宰幽冥地府的十八重地狱和世人的生死贵贱,而且还执掌天下“七十二司”。因此,岱嶽殿里一般都建有七十二司神祗庙,像“速报司”和“福寿司”分别由包拯和岳飞执掌、“僧道司”由和尚执掌。这种包罗万象的“造神”运动,使得岱嶽殿成了道士和尚都能包容的庙宇,自然也成了世人趋之若鹜求神拜佛的最好去处。边墙上的士卒及他们的后代,在岱嶽殿的晨钟暮鼓中,逐渐让自己的内心日趋平和,宗教教化的力量在岁月的长河里,仿佛比营堡壁垒的厚度更加坚不可摧。所谓文化,也许就是在这种教化的浸润中一点一滴积累了下来。
正统四年(1509年),也就是岱嶽殿在明朝第二次修葺的那一年,朝廷下诏在边关隘口修建关帝庙,并且在关公像的两侧同时塑造南宋忠臣岳飞和陆秀夫的神像,以便一同祭祀。朝廷之所以如此兴师动众地以国家的名义在全国大兴关帝庙,与当时“北虏南倭”外族入侵的局势不无关系。因此,自正统以后,朝廷对忠义精神的弘扬与日俱增。到万历年间,关公正式取代姜太公,入主武圣庙,并且和文圣孔子一起享受世人祭拜。万历皇帝曾三次给关公加封,称号从王爵一直升到帝位。
朝廷的重视让边关要塞一下子冒出了许多关帝庙,在沿河边墙的关帝庙上就有这么一幅楹联: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历朝加尊号,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皈依。楹联的内容尽管是颂扬关公的,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大明帝国的边关上,儒释道三家都频频向历朝历代的英雄豪杰伸出橄榄枝,也正因为如此,儒释道在战乱频发的边关隘口才得以真正融合。
抚叹大明帝国五百多年前的边墙,这里有险峻、有玄幻、亦有数不尽的世道人心。无论是那位放羊娃的吼声,还是石径禅寺的玄妙,以及吴峪洞的神秘、岱嶽殿的森严,都让这个荒凉的黄河畔出现了一丝文化的力量。而这种来自宗教的力量,让昔日的边疆不止有黄河,有长城(边墙),亦有一道隐隐传播的梵音。边墙残破了,而黄河却奔腾不息,那道隐隐的梵音也传播不止。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站在石城的悬崖上,看峡谷里流淌的河水,我的心中突然响起这么一种声音。我知道,这应该是来自穿越两千多年时空的儒家的余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