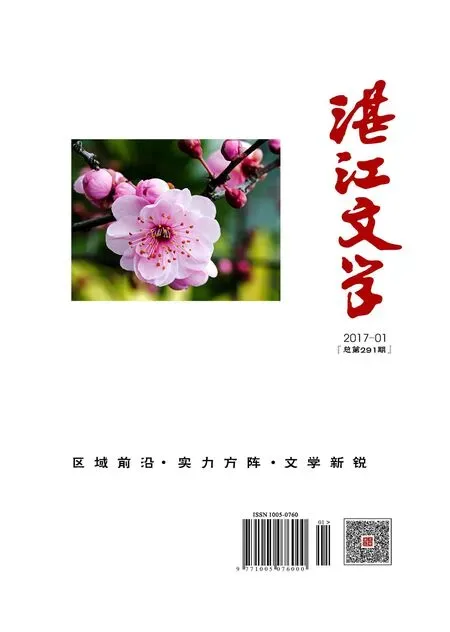鲍勃·迪伦与“文学”的边界
※ 王士强
鲍勃·迪伦与“文学”的边界
※ 王士强
2016年10月13日,瑞典文学院宣布201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美国人鲍勃·迪伦,以表彰其“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开创了新的诗性表达。”这一消息颇为出人意料,引起了热议,它甚至对某些文学界的人士构成了冒犯。在人们通常的印象中,鲍勃·迪伦主要不是一位文学家、诗人,而是音乐家、歌手,他在音乐领域的成就和影响有目共睹,但在文学、诗歌方面似乎更多的是附属、业余、“玩票”性质的。而一直以来坚持严肃文学、纯文学本位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这样一位并非从事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写作的人,不能不让一些人大跌眼镜。实际上,从鲍勃·迪伦获诺奖出发,的确可以对我们的许多已成“常识”的文学观念形成冲击,许多基本的概念、观念都值得进行重新考量。
作为诗人的鲍勃·迪伦
鲍勃·迪伦的诗很大程度上与其歌词是重合的,他的文字作品更多的是被作为“歌词”而不是“诗”来接受的。歌词一般被认为是大众的、流行的、浅显的,而现代诗则往往被认为是小众的、精英的、复杂的,两者之间如果不说存在鸿沟的话至少也是泾渭分明的。而鲍勃·迪伦的作品则冲击了这种固有观念,它一方面具有明白晓畅、通俗易懂的特征,同时也有着思想性、先锋性、异端性,在浅易和通行的面孔之下有着严肃的内心和深沉的关切,它是有内在的诗性的,本质上是诗的。鲍勃·迪伦的诗/歌连接了古老的民歌、民谣传统,有着久远的历史积淀和广泛的民众基础。而更重要的,它有着新的变化,与时代生活有着密切的关联,表达了一代人的心声,其表达技巧、审美取向、价值观念都是非常现代的。很大程度上鲍勃·迪伦是以现代诗入歌的,这一方面为歌这种形式增加了思想性、冲击力和丰厚内涵,而同时也为现代诗这种形式增加了“歌性”、乐感、吟唱性,使其更易懂、易诵、受众面更广,这实际上形成了“双赢”:歌具有了诗性,诗具有了歌性,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诗歌”或“歌诗”。
鲍勃·迪伦最重要意义之一,就是以通俗、传统的形式包容了新锐、前卫的思想观念,将诗歌的人文性推广、传布到大众层面,推动实现了价值观念和美学范式的更新,就此而言,其功莫大焉。当然,鲍勃·迪伦的作品非常丰富,风格多样,变化多端,既有抒情性、个人性的,也有精神、思想性的,还有时事、社会性的,风格上既有至情至性、柔情缱绻,也有剑拔弩张、冷酷到底的,表达上有清晰、明澈的,也有象征、隐喻的,其作品的内涵与外延都足够复杂、立体,构成了一个庞大、幽深的世界。无论就文本的成就还是影响而言,诺贝尔文学奖选择鲍勃·迪伦作为获奖者,实际上都不应构成一个“事件”。
“纯文学”“纯诗”及其限度
但是仍然会有许多人发问:歌词是文学吗,是诗吗?这实际上牵涉到了一个文学的基本问题,即何为文学、文学的边界在哪里?
这显然也是一个说不清楚、见仁见智的问题,不可能有一个所有人都认同的答案。如果联系现代文学、现代诗歌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一些问题或许可以看得更为清楚。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之一是分工的细化,现代文学同样是往专业化、细分化、类型化的方向发展,注重艺术性的纯文学、严肃文学与注重商业性、娱乐性的通俗文学、大众文学之间的分野渐趋明显,并形成了一种高下有别的等级制度。纯文学被认为是真正的、具有永恒性的文学,而通俗文学则等而下之,是追逐利益、注重当下因而意义不大的文学。这在一定程度上当然是成立的,但是关键的问题是,两者之间的界限在哪里,有没有互相转化的可能?两者之间是否一定是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的?进行一番追问,我们会发现许多固有的观念可能是未经考辨、经不起推敲,甚至包含了傲慢与偏见的。
纯文学包含了以文学为本位,反对文学的工具化、政治化、商业化,注重艺术性、审美性、不媚俗、非功利等的内在要求和特征,它是一种高度自律、高度“清洁”的文学形态。纯文学有着对于语言的高度敏感和着力经营、对于艺术的纯粹性与完美性的极致追求,以及对于人的生活世界与精神疆域的自由探索,如王国维所说是“游戏的事业”“可爱玩而不可利用”,它以整体性、审美性、超越性的方式对人的生存进行观照,实现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其价值意义自不必多言。纯文学在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其形态、意义等各有不同,需要具体分析,但应该注意“纯文学”之“纯”并不意味着它就一定是值得提倡的,不意味着它不会出现问题和偏差。纯文学有一种自我规范、自我约束的特征,这种封闭性取向可能影响其向复杂变化的生活世界的敞开,隔断其与外部的社会现实的关联,从而更多的成为一种“炫技”和语言游戏,长此以往,文学便成为了一种越来越小众化、封闭化、精英化的存在,成为了“小圈子”中的游戏,而不再与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和广大的社会公众发生密切关联,其疆域变得极其窄狭。
在诗歌领域,与此相关的是“纯诗”问题。“纯诗”理论与实践肇始于西方,强调“为诗而诗”“为艺术而艺术”“唯美”“纯美”“最高的美”等,在中国百年新诗的历史上“纯诗”也是一种重要的是个形态,总体而言绵延不绝,从未真正绝迹,尤其是在新时期以来的近数十年获得了长足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创作流脉。这里讨论的“纯诗”我们取其广义,并不仅仅指作为创作流派和美学追求的“纯诗”,而是指专注于诗歌“内部”和“自身”,强调诗歌的独立性、审美性、纯粹性的写作趋向。纯诗在一定程度上使诗歌从工具化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注重自身建设,恢复了诗歌之为语言艺术的本位,提高了诗歌的自主性和品质。但同时,“纯诗”本身也是理想主义的产物,如梁宗岱所说诗的“绝对独立,绝对自由”很大程度上只能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乌托邦梦想,不可能真正实现。正所谓“水至清则无鱼”,过于“纯”的诗很容易与时代境遇、社会现实相脱节,而仅仅成为个人的空想、呓语以及语言的游戏、修辞的练习。现代诗作为一种与现代社会相伴而生的艺术品类,其本身即有复杂性和晦涩的趋向,纯诗作为“语言的炼金术”,注重语言和修辞的锤炼与磨砺本也无可厚非,但另一方面,却也不应因而遗忘了“初心”“本心”,不应丢失了诗人应有的情怀、关怀。现实之中,许多的纯诗写作确实步入了误区,专注于语词的打磨却忽略了格局的开拓,沉迷于个人化的趣味之中而缺乏变化和自我的超越,向内的收束有余而向外的打开不足,作品语言看起来很奇异很精致但内在却空洞无物不知所云,如此等等。这样的写作貌似有专业性,很“高大上”,但实际上却是虚假、无效甚至自欺欺人的,它造成了诗歌与大众之间的隔膜甚至对立,使得诗歌的影响力和受众愈益萎缩。现代诗在当今社会所遭遇的窘困,与“纯诗”的某些负面影响恐怕是不无关联的。
文学是什么?
纯文学、纯诗在相当程度上都体现了一种边界意识和精英意识,通过区分文学与非文学、诗与非诗来提高其自身的纯粹性和专门性,保持一种“高端”的自我设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当然是必要的,非如此不足以形成其自身的独立疆域,建构其自身的价值体系与范式。然而,这种“边界”本身却也是值得时常审视与反思的,对文学而言,追求自由、无拘无束正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边界”意味着隔绝、封闭甚至等级,一定程度上正是文学所质疑甚至反对的对象。理想状态的文学不应该是自我设限的,而应该是无限敞开的,它应该有强大的胃,足以容纳和消化生活中的一切,它应该有宽广的视野,宇宙之大、粒子之微、人心变幻、地老天荒,无不在其关注的范围之内,这种开放性对于文学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文学、诗歌就其本性而言,它不应该是拒绝、排斥现实的,而应该是关注、包容现实的,它不应该是傲慢、高高在上、与大众无关的,而应该是谦卑的,应该拥抱每一个生命个体、胸怀全人类、直面生命中的残缺与悲剧。鲁迅曾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句话对于文学而言同样是恰切的,文学关注的是全世界,是每一个人,是“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过于“纯粹”和“纯洁”实际上意味着对于日常生活和普罗大众的轻慢与忽略,意味着自我的封闭和“源头活水”的丧失。应该说,对于纯文学、纯诗,的确需要对其封闭、固化的特征有所警惕,应该努力恢复其与更为丰富、广阔的存在的关联,如此才可能使其更具活力、更富可能性。文学应该是原生的、粗砺的、直面现实的,它是泥沙俱下的河流,是长于野地的花朵,过分的精致、过分的雕琢,可能使其失去“地气”与“生气”,使其失去强横、蛮野的生命力,失去与天地万物的血肉关联,变成温室里的花朵和人造的盆景。这无疑是值得警惕的。
鲍勃·迪伦之获诺奖的确可以成为一次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文学的基本问题、基本概念的契机:我们的文学观念是否已经过于封闭、保守,已经过于固化、僵化?我们是否需要打破此前的若干观念,重新回视过往,重评经典,是否需要俯身查看当前丰富而新异的文学现场,发见其中真正有价值、成长性的新生力量?我们的文学评论、文学评奖,是否已经形成一种独立、开放、稳定的价值体系,对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予以扶持和奖掖,甚至,如果我们也有自己的鲍勃·迪伦,我们是否可能给他颁发一个文学奖?……一句话,文学到底是什么?当我们谈论文学时,我们在谈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