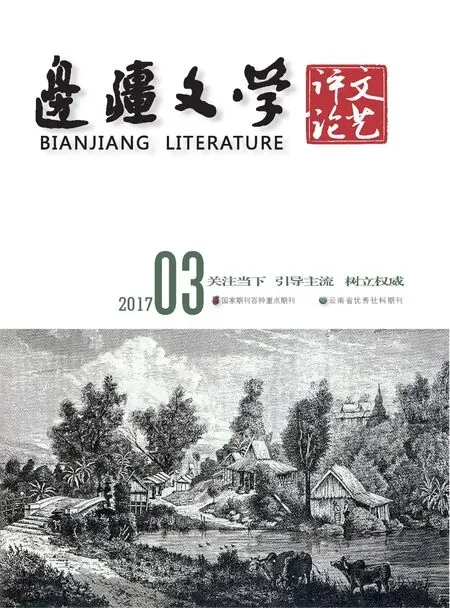论《白鹿原》中黑娃的文化心理
鲁文菲
学人观点
论《白鹿原》中黑娃的文化心理
鲁文菲
·主持人语·
已故的著名作家陈忠实凭借长篇小说《白鹿原》,奠定了他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大家地位。有关《白鹿原》,学界已有不少论述。青年学子鲁文菲从文化心理的角度论述黑娃形象,为我们理解这部著名长篇小说的人物塑造增添了新的内容。论文对黑娃文化皈依之后的心灵困境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思考儒家文化的现实意义。
彝族学者纳张元在研究之余,致力于文学创作,他的散文多抒写自己的生命家园彝山的自然之美与文化风姿。农为平的评论着力阐发纳张元文学书写的情感内涵,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蕴含的文化隐痛。通过对纳张元的个案研究,为我们理解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书写”提供了一个颇有价值的视角。(胡彦)
长篇小说《白鹿原》奠定了陈忠实在当代文坛的地位。《白鹿原》一书以白、鹿两家的权力之争为主线,在展现清末民国间完整社会运行机制的同时,以“文化心理结构论”为依托塑造了丰富的人物形象,其中寄寓了作家陈忠实在时局的变迁和历史的激荡中对儒家文化命运的观照与思考。文本中,黑娃是人生经历相当丰富的人物,是陈忠实“通过把握心理结构及其裂变过程”写活的一个人物。
一、叛逆、豪狠的性格
小时候的黑娃呆呆的有些傻气却又不乏灵气,是天真活泼很接近儿童天性的一个人。黑娃生活在贫困的长工家庭,父亲鹿三没有读过书,朴实憨厚却又十分倔强,鹿三简单、直接、粗暴的教育方式极易促成黑娃叛逆性格的形成。白鹿村学堂修好后,在白嘉轩的提议下鹿三带着黑娃来到学堂拜见徐先生,黑娃给徐先生鞠躬时,肩上的板凳不小心滑下来砸到先生的脚背,“鹿三顺手给了儿子一巴掌”,鹿三这种粗暴的教育方式给孩子带来的是心灵上的创伤和畏惧,也促成了黑娃反叛倔强性格。对于完全没有接触过“温文尔雅”的文化气息的黑娃来说,读书是另外一个陌生的世界,是一个他不曾接触也没有丝毫认知的世界。所以,一开始黑娃和这个看似威严、崇高的读书世界格格不入。本与知识世界紧密相连的毛笔在黑娃的世界里所能引起的联想和触动与毛笔原本富含的文化意义全然无关,毛笔紫红的笔头对应着的是有着相近颜色的曾被黑娃上山割草时不小心误伤的小狐狸,当班上其他同学拿着毛笔听先生讲课习字时,黑娃便沉浸在自己联想的世界中去了——“他一直在想那个狐狸的腿好了没有”。黑娃的世界是自然的、童真的、善良的,他没有接受任何一种文明教育的“污染”,他的心灵是纯净的,在所有孩子中,黑娃是唯一和大自然紧紧融合的一个人。这种自然的天性表现在他对白家父子自然而然的疏离和与不是那么严肃又随和可亲的鹿家父子的亲近上。在黑娃看来,白嘉轩是“神像”,意味着权威、不可违抗性,小小的白氏兄弟在黑娃眼中也像是庙里的神像,一副时刻准备着接受别人叩拜的正经相。白嘉轩给黑娃起了官名——鹿兆谦,想让他变成“谦谦君子”,孩子们还是叫他黑娃,只有白氏兄弟每次正经地叫他的官名,黑娃对白家兄弟只有敬重,对鹿氏兄弟却有着亲切的自然接近。
黑娃的叛逆性格自小极为明显,从黑娃对冰糖由喜爱到憎恨丢弃再至备受侮辱最终得到后毁灭的情绪转变上可见一斑。首次吃到冰糖的黑娃“浑身颤抖起来”,第二次拿到水晶饼“全身颤抖”后“便扔到草丛里去了”。冰糖给黑娃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好又痛苦的回忆,他愈来愈清晰地意识到只有买一袋冰糖才能解除这种痛苦。后来黑娃和兄弟们打劫时候虏获了一桶冰糖,黑娃“往装满冰糖的洋桶里浇了一泡尿”。此时的黑娃看似战胜了曾经因冰糖带来的自卑、恐惧的心理,实际上自出生便看着父亲在白家熬活伴随而来的自卑灰暗心理一直萦绕在黑娃心头,直至“学好为人”的鹿兆谦跟随朱先生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有了文化根基和经济基础以后,这种情绪才真正从黑娃心头消散。这一观点将在下一节对黑娃人生历程的剖析中得到印证。从对美好事物曾经的无限向往转而变为得到后的亲自毁灭,实际上是自我化解自卑情结的精神救赎。
黑娃带着鹿兆鹏、白孝文帮徐先生砍柳条,三人在街上看到白兴做牲畜接种忘了时间,回到学堂被徐先生责罚。鹿三唯恐黑娃带坏了白孝文不想让黑娃念书,白嘉轩坚持“知书达理”的信条,拽着黑娃走了。年纪小小的黑娃无力挣脱代表着白鹿村绝对权力和权威的白嘉轩,白嘉轩留给黑娃“复杂的难忘的记忆”,这记忆里一定有黑娃对白嘉轩所代表的价值体系和权力系统的恐惧,也必然伴随着自己无力抵抗的无奈和身小力薄的认知。尽管黑娃或许隐约知道白嘉轩让他念书是为他好,但不可辩驳的是黑娃对此的本能反应是不喜欢甚至是抵触的、反抗的。这里是否夹杂着作者陈忠实的这样一种思考——以白嘉轩为集中代表的儒家文化对人的本能的忽视甚至无视以及强制性的文化绑架?这一点在文本中更加鲜明具体地表现在违背现实文化统治秩序的田小娥和鹿冷氏的悲剧命运上。
黑娃始终难以承受白家整个家族强势文化的重压,所以对周围人十分认可的白灵认自己父亲鹿三为干爹一事不置可否,在长满十七岁完全“能当个人使”的时候毅然回绝了鹿三让自己在白家继续熬活的提议,只因为嫌白嘉轩的“腰挺得太硬太直”,实际上黑娃在白嘉轩面前始终自卑得抬不起头来,他不知道怎样和白家人相处,白家自白秉德起带给自己家太多的物质上的利益与牵扯,尽管实际上鹿三始终被白嘉轩当作白家的一口人,但深深的自卑感仍让黑娃对白家敬而远之。此外,两家不同的文化结构是黑娃心理上一直难以逾越的鸿沟,尽管两家本质上都是农民,但“知书达理”的白家以及白嘉轩至高无上的族长地位,使黑娃相比之下始终难以消除白家给自己造成的从物质到文化层面几乎是全方位的心理重负。与此同时,黑娃与同样在学堂里接受教育的鹿兆鹏相交甚欢,那么就又回到文化性格上来,鹿家兄弟带给黑娃的是完全没有在白家的物质联系和精神负担,鹿家人整体上比较随和让黑娃倍感亲切。相比而言,白家人却普遍比较严肃,白嘉轩又直又硬的腰杆给人带来的紧张更在于作为族长的神圣权威不可侵犯,白家人“正经八百”“等着人膜拜的神像”的形象的深层含义不仅代表着礼仪、规范、标准,白家更是白鹿村上层精神建筑的监督者,是刑罚的具体实施者,白家人所代表的严肃的、目的与手段合二为一的功利色彩相当浓厚的儒家文化是年纪轻轻、不希望被任何束缚、渴望自由的黑娃所反感和逃避的。因此,当黑娃终于长大有机会逃离长期以来一直压制他本性的白鹿村的时候,渭北一个完全陌生没有任何负担、监督和束缚的环境当然成为他最好的选择。
全然释放天性且日渐成熟的黑娃逃离束缚身心的白鹿原,伴随着性意识的萌芽,在郭财东家干活时,遇到年龄相近的田小娥的勾引,自然也就毫无顾忌的随着性子让此事发展下去了。此时的黑娃并没有考虑到自己和田小娥行为的后果,只是“及时行乐”,田小娥成为黑娃释放自己天性的第一个出口,黑娃只沉浸于当下与田小娥的两性关系中,甚至没有想过今后两人将何去何从,因此,田小娥提出的两人一起私奔并没有得到黑娃或同意或反对的任何回应。直至此事被郭财东发现,被赶走的黑娃想方设法找到被休的田小娥,带着田小娥回到白鹿村的黑娃此时才把自己从天性的随意释放中带回到有着层层禁锢的现实生活中来。明确田小娥来历的白嘉轩拒绝了两人进祠堂的要求,鹿三甚至与黑娃断绝了父子关系,白嘉轩甚至以自己负责给黑娃重新找媳妇、操办婚事为诱饵,试图说服黑娃“丢了这个烂女人”,在道德批判和利益诱惑的双重重压下,黑娃依然没有放弃田小娥,两人在村头的破窑洞里忍不住相拥而泣,虽然两人无家可归,无处可去,生活拮据,却又几乎同时获得了心灵上的解放与释然,黑娃和田小娥有着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惺惺相惜又相濡以沫的深情。
黑娃和田小娥的结合实际上只是本能生存欲望的驱使而并非鹿兆鹏所说的“自由恋爱”,尽管黑娃对此完全没有概念,但在全村人都不认同他和田小娥关系的情况下,鹿兆鹏对两人关系毫无条件的认同和称赞无疑让黑娃有了极大的心理安慰,黑娃从“知书达理”的鹿兆鹏身上获得了对于自身行为难能可贵的认同感,这给在白鹿原上长期以来不得认可的黑娃和田小娥提供了生存下去的极大希望和动力。黑娃和鹿兆鹏情感上的亲近和立场的趋同为后来黑娃参加革命做了铺垫。黑娃在鹿兆鹏的游说下烧了白鹿仓的粮台,在“农讲所”受训后在白鹿村里开讲习班,发展积极分子,创办农民协会,斩了三官庙的“老骚棒”和尚,“淫魔”碗客,砸了祠堂和刻着《乡约》的石碑,批斗了包括田福贤、鹿子霖在内的十个乡约。北上革命失败,国民党大肆抓捕共产党员,鹿兆鹏、黑娃惊慌逃跑。按照鹿兆鹏指示,在习旅长所在的营地任职的黑娃对各种枪类得心应手,黑娃天生果敢、干练的性格特质使其在“刀光剑影”中一展所能。一次战斗中一营全部牺牲,黑娃侥幸逃跑,不得已当了土匪。“心眼耿直”、“手脚利索”的黑娃很受大拇指赏识,在土匪兄弟中声望很好,很快升为仅次于大拇指的土匪老二——二拇指。黑娃深夜潜入白嘉轩的卧室替死去的田小娥报仇,进入白家大院的黑娃儿时进入这个院子的“紧张和卑怯又从心底浮泛起来”,投靠土匪的黑娃显然无力对抗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儒家文化,也必然无法冲破白嘉轩所代表的上层权力话语系统。鹿三也因承认自己才是杀害田小娥的真凶一事与儿子黑娃彻底决裂。
土匪黑娃被白孝文抓获,白孝文在大拇指的血腥威胁下给了监狱里的黑娃一根钢钎,黑娃成功越狱逃跑。土匪兄弟们因黑娃追查杀害大拇指的真凶相互猜忌,无力扭转分崩离析局面的黑娃在白孝文的游说下携土匪兄弟们归服保安团。自此黑娃便开启了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图景,拉开了回归传统儒家文化的序幕。
二、文化的皈依
与高老秀才的女儿高玉凤的结合是黑娃回归儒家文化的关键,“混沌”半生的黑娃诚挚地认识到自己“需要个知书达理的人”管教一番。婚前按照高老秀才要求历时五天五夜成功“戒土”的黑娃顺利迎娶高玉凤的同时,也因“戒土”过程中对自己的豪狠在整个县城名声大噪。新婚之夜,在“知书达理”的新娘面前十分卑怯的黑娃开始了对自己整个前半生的反思,“他想不起以往任何一件壮举能使自己心头树起自信和骄傲”,之前不管是与田小娥的结合,还是与黑、白牡丹的“龌龊勾当”都是不被世人接受,不被周围人认可的,都是只能躲在阴暗角落里苟且而万万见不得光的,唯独现在与高玉凤的结合是“光明正大”的,高玉凤在此成为一种文化的象征,高玉凤所代表的是为人人所接受的、所认可的社会秩序、主流价值观和文化统治秩序,从这个层面上讲,黑娃与高玉凤的结合可以说是一向叛逆、一向背离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黑娃对当时整个文化统治系统的妥协,只不过这种妥协就黑娃而言不仅十分心甘情愿,甚至愿意将自我真切地融入到当时的文化体系里并默默地、自觉地成为构建、维护这种文化秩序的一分子。这在黑娃的整个生命历程中可以说是脱胎换骨的转变,作者陈忠实将这一心理过程很贴切地概括为“裂变”。深究这一“裂变”背后的原因,或许我们可以看到作者陈忠实这样的思考——“闯荡半生、混账半生”的黑娃并非仅仅是为了满足现实需要,以获取整个文化系统对自身的认可为最终目的,而是真正意义上想通过“念书求知活得明白,做个好人”。新娘对黑娃毫无条件的包容和理解及饱受文化熏陶的新娘本身沉静、安然、贤淑气质正是黑娃欠缺又久久渴望的,他想从以往混乱的生活中把自己解救出来,回归到儒家文化的坚实怀抱,这位知书达理的新娘正是黑娃回归的切入口,在这种“和平宁静”、“刚柔相济”的文化气息里,逐渐向儒家文化靠拢的黑娃终于领受新婚之夜的“全部美好的同时也感到可靠和安全”。在妻子高玉凤的支持下,黑娃跟随朱先生学习,开始真正脱胎换骨的修身,其言谈举止也因文化的滋养变得儒雅而有气度。有了文化归宿、政治地位及经济基础的黑娃此时才有勇气向朱先生提出回乡祭祖一事,朱先生是白鹿原上绝对的精神力量支撑和学习榜样,一旦此提议得到朱先生同意,黑娃回乡树立焕然一新的形象也必然被全村人认可,黑娃年轻时犯下的过错也必然能够被全村人尤其是族长白嘉轩及自己的父亲鹿三原谅,黑娃对此心知肚明。因此,明知道在白鹿原上有对手的黑娃在和朱先生一起回原时,才会安心坦然到不带一兵一卒,三人坦荡回到白鹿原。
以“拘谨谦恭的布衣学士”形象出现在白鹿原上的黑娃,看到以“白鹿村最高规格的迎宾仪式”在祠堂门口迎接自己的白嘉轩,黑娃“紧走几步扑通一声跪下了”,面对曾对自家有无限恩情又自小害怕的白鹿村族长白嘉轩,黑娃内心必然是有愧的,其所有的愧疚凝练为“知罪”二字。黑娃给母亲上坟后回到村子里,挨家挨户上门为曾经的所作所为表示歉意,深受征粮征丁折磨的村人并不在意黑娃的歉词,只关心身为营长的黑娃是否能够扭转当前沉重赋税带来的生活困难的局面。黑娃的愧疚心理在道歉对象(村人)那里没有得到预期中的回应,预期回应的缺席转而在睡了十几年的炕上、以新婚妻子弥补亡母在自己内心位置以及自身内心文化根基的建筑上得到稀释和弥补。晚上和妻子一起睡在亡母炕上,黑娃“颤着声羞怯怯地说:‘我这会真想叫一声妈’。”这里与朱先生死前依偎在妻子怀中时想叫妻子一声“妈”的想法不谋而合,“妈”在这里不仅仅指自己的生母,是一个给予自己生命的伟大存在,更是潜移默化影响着数代人“怎样做人”的传统儒家文化。没有了母亲的黑娃觉得自己的生命源头突然不见了,自身生命的最原始的那一部分不存在了,文化源头在当下社会环境中也不再那样清晰可感,当儒家文化不能够真正解决人们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以致幡然悔悟回归人们数千年信仰的文化之后仍然无法弥补自己心理空缺的时候,黑娃实际上像曾经没有皈依儒家文化时一样再次茫然了。黑娃这种顿然的“生命领悟”既是对现实生活中的亡母的悼念,也是对自身生命源头的追悼,更是孕育这片土地、养育数代人而又渐行渐远的儒家文化的追悼和祭奠。
黑娃在鹿兆鹏的提议下成功策动保安团起义,却被白孝文抢了功。多半年后,黑娃沦为白孝文谋取更辉煌政治图景的工具,黑娃被捕,与岳维山、田福贤一同被执行枪决,半生糊涂的黑娃皈依曾经十分畏惧又不屑一顾的儒家文化并没有挽救他的命运。儒家文化在新的政治话语体系下失去以往的绝对统治权威,传道者朱先生的离去、单纯的最后文化阵地的坚守者黑娃的悲剧命运似乎为读者勾勒了本深深扎根于人们心理深层、潜移默化作用于整个社会秩序的儒家文化如何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一步步无奈地退出历史舞台,人们的深层文化心理怎样逐渐被新的社会秩序解构与重塑的。
【注释】
[1] 陈忠实.接通地脉[M].作家出版社,2012: 146.
[2] 陈忠实.梅花香自苦寒来:陈忠实自述人生路[M].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111.
(作者系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杨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