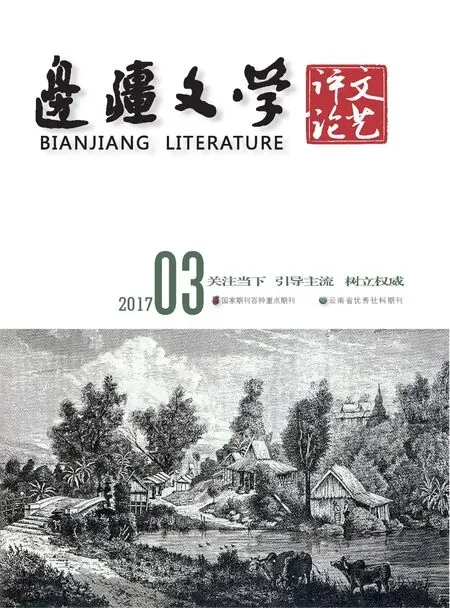悔改的时候到了
——读窦红宇的小说《青梅了》
孔莲莲
悔改的时候到了——读窦红宇的小说《青梅了》
孔莲莲
2016年,窦红宇的首个中篇《青梅了》熟了,先是在《十月》发表,很快又被《小说选刊》和《作品与争鸣》相继转载。这个作品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如文坛的一丝亮光,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这是我接下来想探讨的问题。
上
在说窦红宇的小说《青梅了》之前,先来一起回顾一段文学史吧。
二十年前,准确的时间段应该是在1993年之后,中国文坛发生了变化,市场经济和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学关系亲密度加强,很多自由作家成为文学市场的独立个体,个人意识空前增强。之后,1998年,一群被文学批评家命名为“新生代”的作家在文坛上掀起了一股文学浪潮, 首先是《北京文学》发表朱文主持的问卷调查,题为《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继之,韩东的《备忘:有关“断裂”行为的问题回答》(载《北京文学》,1998.10)也发表了“断裂”的声明。这次集体行为声势不小,他们表示要超越他们的文学前辈,在文学的路上率性而为,扬弃所谓的道德和宏大叙事,走一条“个人化”写作之路。这是一次年轻人对老一代作家的集体反叛。“新生代”作家大多是6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比如韩东,邱华栋,朱文等人,当然还包括一些女作家,比如陈染,徐坤,海男等。
这群作家在以后的创作中果然表现出与前辈作家的不同。首先是他们的创作适应了时代精神。20世纪末的中国被消费文化刺激得到处弥漫着力比多的气息,连带着铜臭之气。这两种味道在这些“新生代”作家的文学作品里混合着,以鬼魅之态呈现出来,强烈地吸引着文学消费者。实际上,这时候起来的年轻作家们都不同程度地适应了市场经济的需要,他们的小说在市场的春风下,如鱼得水,销量甚好,再加上出版商适时地炒作,使得很多新生代作家的作品称为畅销书。比如当时新生代女作家陈染的长篇小说《私人生活》出版的时候,封面设计得如春宫图一般。其次,这些作家本人往往以严肃作家自居,创作主旨意在打破传统形而上的精神文化,在整体的价值趋向和伦理规范上,体现出对传统文化的反叛精神和对后现代文化的认同或者矛盾态度。他们的作品在表现两性关系、父子关系,甚至母女关系时,表现出惊世骇俗的勇气。比如女作家林白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被评论界认为是女性主义文学中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说一个男作家个人化写作的例子,朱文的小说《我爱美元》。这个作品最初发表于1994年的《大家》杂志,1995年,朱文将他的其他作品结集出版小说集《我爱美元》,借着1998那一年韩东、朱文、邱华栋等人在文坛起事,朱文的这部小说集成了“新生代”文学创作实绩的代表作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我爱美元》,题目就像当年海男出版的《我的情人们》一样惊世骇俗,同时又显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即中国市场经济与世界接轨后中国人大胆的形而下追求。
这个故事呈现的是一段后时代的新型父子关系。父亲因为出差,顺便来城里看“我”和弟弟,“我”当时刚好和情妇床事未完,被父亲生生打断。弟弟是一个想辍学搞流行音乐的叛逆大学生,“我”一边带着父亲寻找弟弟,一边和父亲游走在城市的各种娱乐场所,和父亲讨论性、文学、金钱、女人、情妇,甚至找舞女请父亲消费,怎奈小姐要价太高,“我”和父亲只能作罢,最后,没办法,“我”请求“我”的情妇陪父亲一晚,被情妇愤怒地扇了耳光。
小说中,父亲和“我”持有不同的价值观。父亲认为“性不能是当饭吃,而应该是当菜吃的事情”,而“我”则认为,应该好好的享受性生活,“我”甚至同情地认为“父亲是个性欲旺盛的人,只是有点生不逢时”。父亲和儿子的传统伦理关系因为“性”价值观念的变迁而被解构。传统宗法制下的“父父、子子”关系,是建立在性的传宗接代功能上,而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性”的消费功能被强调。父子二人一起消费舞女,甚至要共同使用同一个情妇,这完全抹杀传统有层级有性禁忌的父子伦理,使得父子关系走向一种平等和无禁忌。请注意,作者朱文让“我”这个小说中的儿子,用性和金钱的方式表达的是对父亲的“爱”,“爱”是一种人类的普适性的情感,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说法很不一样,中国讲的是子对父的“孝”。可见,朱文对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刻意的抵制。
另外,小说借儿子与父亲讨论文学,表达了与父辈完全不同的文学观。父亲认为“我”的小说里只有性和金钱,价值观有问题,“我”则认为“我”的小说里民主、自由、理想等等都有,只是不同于前辈的表达。“我”很坦白“我”写作的目的:
“他们(指如朱文一样的新生代作家——笔者按)是为金钱而写作的,他们是为女人而写作的,所以他们被认为是最有希望的。 但是其中若干角色支撑不了多少时间就精疲力尽了,他们的肾有毛病,谁也帮不了他们。
“因为我就是这样一个廉价的人,在火热的大甩卖的年代里,属于那种清仓处理的货色,被胡乱搁在货架的一角,谁向我扔两个硬币,我就写一本书给你看看。
“我已经准备好了,连灵魂都卖给你,七折或者八折。
“不过别忘了,我要的是他妈的美元。
“所以,我们要尊重钱,它腐蚀我们但不是生来就为了腐蚀我们的,它让我们骄傲但它并不鼓励我们狂妄,它让我们自卑是为了让我们自强,它让我们不知廉耻是为了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本身就是这么不知廉耻。”
稍长一点的作家简平这样评价《我爱美元》:
“对于这样满是流氓腔的下流、无耻的文字,竟有文学评论家欣欣然为此击掌欢呼,称一代‘文学新人’正以新的姿态在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到来, 不仅为其打出所谓的‘新状态’的文学旗号,还煞有介事地用各种玄乎的新名词为之作理论上的提升和包装。令人费解的是,具有很高声誉的作家出版社也来推波助澜,还堂而皇之地在封底打上标签,宣称这是‘现代人结束精神流浪的悲壮努力’,其谄媚、恶俗和麻木昏庸非但使人震惊,更使人愤慨。 ”
从这段评价文字里,我们真正看到了新老作家的“断裂”。60年代出生的人,在很年轻的时候经历了中国的改革开放,那时他们年轻气盛,那时他们认同金钱、性和物质。他们认同名利。他们是一群“犬儒主义者”,他们是一群中国的“雅皮士”。
下
扯了那么多,现在言归正传,谈谈窦红宇的中篇小说《青梅了》。
窦红宇和朱文是同龄人,经历了二十年的浮躁人生之后,当年的年轻人经历了岁月的磨炼,到了不惑的年龄。中国的社会也在渐渐地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和物质丰富,变为整体上的“软着陆”。时代在变,人在变,文学变了没有呢?
《青梅了》也是在讲一个父子关系的故事。窦红宇用他惯有的“土匪”和“莽汉”口吻,深情、幽默、又骂骂咧咧地讲述了父与子在同一段路上交叉的故事,他很狡黠地将父辈故事和“我”辈的故事纠缠在了一起,在弄清历史真相的悬疑和警察追捕逃犯的惊险中,完成了故事的讲述。这种口吻,正是新生代的作家们独有的,是他们性格中的犬儒精神的体现。而在追求故事的好看性上,我们依然能看出60后作家对读者和市场的尊重。以上两点,窦红宇与朱文们如出一辙。
所不同的是,这个故事关乎人性,关乎悔过,关乎救赎。
罗青梅显然是这篇小说要凸显的女人:她是一个和父亲同时代的女性,是父亲心目中的“女神”。罗青梅逆时代而行,在五十年代末,选择一个曾经做过国军上校的男人为丈夫,并且为了这份爱情,不惜用计策陷害了父亲的朋友陈启民。也因此,父亲替罗青梅背了黑锅,一直招陈启民的记恨,直到老年二人都是冤家。接着,为了赎罪,罗青梅告别城市,在大山里一呆就是几十年,教书育人,传播文化,保住了自己的爱情,也实现了道德完善。想来,这个女人的人生选择有几个过人之处:坚守爱情,不惜背弃家人、时代、组织和道德。面对内心道德谴责,她又自我放逐到偏远山区,和爱人厮守,共同培养大山里的孩子。这个唱歌动听,长相美好的女人,不能算是一个道德上的完美主义者,她是一个人,是一个不完全的人,但是她知道自己的不完全,并通过自己的赎罪选择实现了自我的完全。小说最后,赵小西看到罗青梅牵着丈夫的手,在阳光里离开,“老夫老妻,老嘴老脸,他们恩爱如初,他们步履蹒跚,他们一路搀扶……”她最终赢得了爱情。
与此相对的是赵小西的爱情。赵小西为了满足爱人张春的私欲,透露标底,挪用公款。表现出为了私欲不惜放弃公共利益,为了爱情不惜违法的莽汉主义倾向。在情感问题上,赵小西与罗西梅的选择似乎颇有相似之处,但是在面对情理平衡的问题上,赵小西和罗西梅则有天壤之别:一个是精致缜密的至情主义者,一个是粗糙愚昧的莽汉主义者。赵小西因为情感私欲触犯理法后,不敢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选择逃亡,他躲避警察,躲避法律制裁,希望能推卸掉法律责任。赵小西养尊处优的生活蒙蔽了他做人的良知和智慧,他的出手阔绰和本能的心软确实让他赢得了风尘女子的感激、同情甚至帮助,这让他的出逃行动颇不寂寞,还有这些女子为伴,但是,到底谁成了谁的垫背?当他在走投无路,不得不接受董小囡充满讽刺和揶揄地救助之时,赵小西真正感觉到了他成了这个女孩的陪玩和垫背。一路担惊受怕,一路被羞辱,一路尊严丧失,也是一路拨开云雾寻找历史真相,他在重走父亲和罗青梅当年外调之路时,更是在和当年父亲的一次对话。终于到达大山深处,见到罗青梅,阅读了父亲的信,了解了真相,赵小西也完成了一次对自我罪性、贪性和惰性的对话和审视,以及因着审视和本能的良知而获得的灵魂重生。
窦红宇笔下的赵小西,与朱文《我爱美元》中的“我”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可以想象,赵小西应该是从90年代的“新生代”中走过来的“大叔”,他经过了欲望的时代,和轻慢的“审父”期,对金钱热爱无比,甚至他对张春的爱是源于张春对他长期的经济供给。然而,一次生活中的失足,在父亲有意的安排之下,他重走了一次父亲年轻时候走过的路。于是,在历史与当下的相遇和对比中,在罗青梅的抉择里,在父亲对他的期许和担忧中,他真正感受到了他们这代人的缺失。小说的最后,赵小西在深夜里独对高山,反省逃亡经历,他竟然感到父亲如上帝一样在观望着自己,恢复了对父辈的敬畏。这一次重走父辈之路的经历,让他真正从迷失的人生轨迹中得以归正。有谁说,赵小西不是《我爱美元》那个轻视父辈,追慕金钱,缺少责任的“我”呢?二十年的积习,“我”果然误入迷途,触犯法律,而最终因为对父辈的回望,让他们在悔过中迷途知返,投案自首。
与《我爱美元》中的“我”爱父亲的方式不一样,赵小西对父亲的爱体现在他听从了父亲交给他的使命,帮助父亲完成历史遗留问题,还父亲清白。这种做法中国的名字叫作“孝顺”,小说反复提到这个中国字眼。因此,“父父子子”的传统伦理是被作者认同的。
还要说一说《青梅了》中的两性关系,或者更“本质”的说,是性观念。父亲对罗青梅是有情愫的,但和罗青梅一起出差外调,二人清清白白,甚至生病互相照顾都未有肌肤之亲。以至于赵小西在听父亲讲这段故事时,竟然不相信地问了一句:“你们没发生点什么?”对于儿子赵小西来说,虽然一路颇不寂寞的行程,虽有年轻女孩不断骚扰,甚至是性诱惑,赵小西还是难能可贵地保持着对张春感情和身体的忠诚。所以,在窦红宇的这个小说文本里,“性”,不是一个消费概念,而是一个与严肃爱情相关连的概念。而且,当赵小西发现更年轻一代的董小囡等女孩,她们生活的要义是金钱消费和游戏人生时,作者借赵之口真切地表达了痛惜之情,那句深情的歌词是:“姑娘,你的头发一甩,我就疼了……”所以,我们在窦红宇的这个作品中看到的是生命的重量,爱情的重量。而这,恰恰也是在二十年前的小说作品中缺失的重量,或者是他们有意规避的重量,商品时代,他们追求的是金钱,以及能用金钱买来的性快感。性和爱无关,性只关乎感官,只关乎消费。由此,我们看到了60后作家文学精神向度的回归。
还可以说说作品中那若隐若现的对政治的讽谏。在那个政治狂乱的年代,一个子虚乌有的反革命指标会让本来善良的人蒙受罪责,让正直的人背负良心的谴责和人格上的迷失;而当下这个追求政治效率的年代,政治官员的急功近利和不守承诺也会造成私人领域欲望的膨胀和道德底线的崩溃。上行下效就是这个意思。没有完善的政治环境,人性的完善就缺少保证。窦红宇具有稳健和中正的政治觉悟,不偏激,不越位。这个作品,他在宏大而又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展露出人性的脆弱与坚守,暗淡与辉煌,堕落与救赎。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2016年的中国文坛,许多作家不约而同地关注起了共和国的历史,比如方方的长篇《软埋》,关注的是土改,胡性能的中篇《消失的祖父》,关注的是地下党人在共和国时期的命运。作家们对共和国的政治史再掀关注热情,是有胸怀大担当的体现。再次说明了作家们真的走出了“自我”,走向了宏阔。
所以,我们是否可以说,窦红宇的这个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个当下文学的集体隐喻。迷失的路最终是要找回来的。曾经的“新生代”们迷途知返,重新回归了文学的传统。《青梅了》体现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文学讯息。实际上,对于当年的“新生代”作家而言,窦红宇小说体现的回归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个整体现象,看一看如今写散文随笔《挑灯看剑》的邱华栋,看看写出诗集《忧伤的黑麋鹿》的海男,以及歇笔了的朱文与陈染们,再看一看当年曾经为新生代作家摇旗呐喊,如今却写出了《90年代文学整体批判》这种反思性论文的作家兼批评家葛红兵,就知道,“新生代”在自我的小圈子里走到了尽头,他们又回到了大文学传统里来了。
这是为什么?我想,那是因为,在文学之外,在形而下的物质之外,有一个自在永在的上帝守望着人类,以至于不让人们在偏斜的路上迷失太久。
(作者系曲靖师范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万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