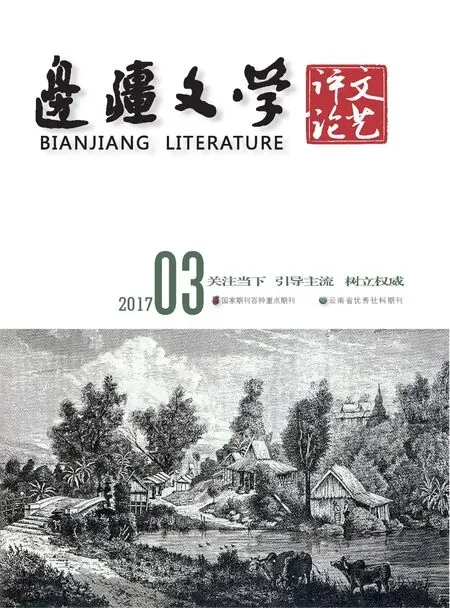滇中奇士周良沛
王海东
滇中奇士周良沛
王海东
“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刘劭将“中和”视为人之最佳品质,是成才的基石。它孕育着一切美好的人格。《中庸》誉之为本与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故而,此质为人之根本,乃成大器之胚芽。否则,不过落为偏才、鬼才之流,甚至是落入凡夫道。今见耄耋老人周良沛先生,给人以此感!
此公名号早有耳闻,因曾是文学少年,囫囵吞却不少作品,尤喜新诗,故而常见“周良沛”所编诗作。那时轻狂,未曾关注这位苦心孤诣的编者;后又沉溺于哲学,也就淡忘了。直到不久前,蔡毅先生跟我提及此公,尘封的记忆被打开,惊叹于人世之妙——原以为遥不可及的他,竟然与我同在一城,且能与之面谈文学。不觉有几分惊愕,亦是欣喜顿生。
于是,数人结伴,往而见之。电梯敞开,老先生下楼迎接我们,动作敏捷、声音洪亮、笑容可掬,望之不似耄耋!
我们鱼贯而入,依次而坐,周先生不仅忙着和我们聊天,还不断拆递各色零食。俨然,有宾至如归之象。而严肃的访谈也就在这种温馨的场景中悄然展开。
苦难人生:化为创作之源
苦难是人生的刀梯,每行一步,则苦痛增一分,而每一分苦痛,也能促使心智的成熟,增益其能。所以孟子劝喻:“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周老未能例外,亦饱尝人间疾苦。
1933年出生的周老,系江西井冈山永新人。抗战时,他是难童,曾随学校四处流亡,后栖身于教堂孤儿之中,从小受过西方文化影响,求学之路在硝烟里中断。1949年,加入解放军,随横渡长江的大军南下,之后剿匪、戍边、修路,同时勤奋自学。19岁起,便在《文艺报》与《人民文学》等报刊发表作品。随之,从连队进入文化部门工作,渐渐又干起了编辑工作。
然而,好景不长,1958年,周先生被错判为“右派”,劳改了二十年。在十年动乱期间,关押他的牢房,竟然成了“禁书”搁置地——扫“四旧”而缴获的旧书多得无处可放,警察们便将之堆放于牢房。可谓因祸得福,劳动之余,他便专心读书,不仅可以光明正大地读马列主义著作,还可以痴狂地读各种禁书。渊博的学识,积累于此。单调的改造生活,反倒使其有充足的时间自学和思考。为他后来完成十大卷《中国新诗库》等系列工程奠定了基石。以至于台湾有学者称其为“奇人”,实为荒诞之日的荒诞之“奇”。
这样的荒诞剧,竟然在一个民族不断上演,荒诞中的荒诞,便是周先生不但没有被彻底摧毁,尽管他的身体遭受摧残,腿也摔断,但他的精神却日益强大,文学的造诣更为深厚,匪夷所思。更为奇特的是,在整个谈话之中,周先生不但没有埋怨时代,也没有怨恨领袖,反倒十分平和,与通常的“右派”们不同,他却怀有感激——那种独特的境遇,虽然带来无法抹去的灾难与苦痛,但却间接地玉汝于成。
那个时代的痛、苦、恨与灾难,并没有摧垮他,反倒成为他笔下的素材,成为他创作的宝藏。他已经将苦难转化为创作的经验,升华为对时代与人性的思考,以宽容之姿与世界和解!
诗就是诗:为诗正名
随着改革春风席卷大地,平反工作不断推进,到1978年,周先生才从劳改队直接调到北京,结束苦难生涯,回归正常生活。而此时的他,已是知天命之年,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已经浪费。时不我待,一出狱,他就迅速开展自己的文学事业,不辞辛苦,南北奔波,竭力恢复新诗运动的历史真相,选编出不少诗集,其中就有徐志摩等人的诗。在巴金等人的帮助下,使《徐志摩诗集》《胡也频诗稿》和《戴望舒诗集》等新诗集得以问世。
新时期,思想大解放,周先生突破禁区,推进新诗研究,随之又陆续编辑、编选了“五四”后及港、台、海外作家、诗人的全集、选集,共有一百五十多位名家及新人的百多部书。他所编的书,大概有二百多部,主要是“五四”后诗家的诗选集、全集,有《中国新诗库》《旧版书系》《云南文学丛书》《抗战诗钞》《中国新诗百年选读》等。难怪,我等后生所读新诗,总难以忽视“周良沛”这个名字。而今,算是解开心中疑惑。他举一人之力,选编如此之多的文学作品,实属罕见。
如此而论,外人以为周先生就是一个编辑,其实远不止于此,他还是一位硕果累累的诗人与作家。在编书的同时,他笔耕不辍,六十余年,著有诗论、诗选集、长篇传记、散文、随笔和杂文等多种文学作品。出版的书有三十多本,其中诗集七八本,散文四五本,评论三本,余者为杂文、回忆录和长篇传记等。新时期复出后,他身兼数职,为国际笔会中国中心成员,世界华文文学联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联络委员会委员,北京《诗刊》编委及香港《海岸线》执行编委等,工作至今仍未间断。其创作作品洋洋大观,令人叹为观止!
与此同时,周先生持续地关注新诗的动态,发掘新的诗人,探寻新诗的发展方向,不仅有诗集问世,还有系统的新诗评论集。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维度上,探索诗歌的真谛。《诗歌之敌》便是其理论思考的结晶。他要回答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也是新诗的命脉所在,那就是到底何为诗歌?
当人们正苦恼于如何对诗歌进行定义时?周先生却反其道而行,从否定的视阈,排除什么不是诗歌。显然,这是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语言哲学就有此妙,对于那些无法定义的概念,则无需定义,必须得换一个视角,才能说清楚。诗歌,是一个无法定义的概念,无法从形式逻辑的层面,对其进行清晰的界定。只要通过理性的判断,就可以知晓:诗歌不是政治,诗歌不是庸俗社会学,诗歌不是意识形态,诗歌也不是口号……如是而行,便可削掉假冒伪劣的诗作与诗学,进而描述出诗歌的本相。
因此,周先生提出诗歌无需定义,“诗就是诗”的看法。“诗最根本的就是思想与情感的结晶,是具有诗思之诗美,并具相应的艺术方式所表述之作品”。他曾表明:“每一首真正的诗,都应该是诗人一次新的艺术创造,是自我,也是诗的一次崛起。创新,就像人体的血液循环一样,在沸腾艺术的生命”。创造与诗性,就是诗之为诗的东西。
但是在文学的汪洋之中,事态复杂,鱼龙混杂,恐怕找不到纯粹的艺术,也无纯粹诗歌。事实上,即便是诗歌,也会带有时代的气息,甚至是政治的印迹,也就是找不到完全隔离时代与生活的纯诗。而时代性、民族性、政治性和现实生活,并不是降低诗歌的因素,有时还是必不可少的元素,伟大的诗歌都与时代密切相连,都与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其关键在于,寻到诗歌与现实的平衡点,既不依附时代,亦不抛却时代,诗歌与政治的关系也是如此。“诗歌艺术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政治也不能等同分行抒写的自身,但它对于为诗者的成败,却有撇不开的作用。这和我前面反对运动中用政治口号的配合、堆砌,图解政策,取代文艺的态度是一致的。那样,只能用所谓的‘政治’葬送艺术,用所谓的‘艺术’庸俗化了政治。我们要防止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这便是他所致力的一个诗学要点。
在现实与艺术之间,为诗歌寻找栖身之地,既不堕落为庸俗的政治物,亦不超然于世外,而是在关照人间的过程之中,回到诗歌自身,正如聂鲁达所言:“诗人之敌,莫过于他自己没有与同时代的最被忽视、最受剥削的人们找到共同语言的能力”。诗歌是时代的精神标志,是连接上帝的楼梯!他竭尽全力,还原诗歌的真谛。
拒绝遗忘:平淡中的奋进
时光的步伐,未曾因为苦难而停留,它默默地流逝,悄悄地抹去痕迹。许多曾经饱受苦难的人们,而今已作古,他们已经化为无名氏,不能言说。在大时代面前,他们已经悄无声息,逐渐被人遗忘,甚至还可能被粉饰,一代人的劫难,就这样进入无痕的黑暗。这既是历史的无情,也是人性的悲哀!谁能铭记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深重灾难?
当我们问及周老今后的学术计划时?他坦言,没有明确的计划,不过是随遇而安。的确,人生到了84岁,谈何计划呢?连明天的太阳能否见着,都没保障,计划何从谈起?对于声名远播海外的周先生而言,他选择偏居一隅,安心做自己的事情。在平淡之中,尽一己之力,为中华的文化事业续写华章。然而,他并没有因为高龄而懈怠,反倒有老骥伏枥之势,每天伏案工作十余小时。先后学会电脑,发送邮件,打印复印,还会用录入笔输入材料,不得不令人拍案叫绝!而他却又自嘲是不会用手机的“老笨蛋”!
这一智一愚,所显现的正是智慧,因为电脑网络能够为其节省宝贵的时间,而手机恰恰会浪费时间。他不愿将有限的生命耗费在琐碎事情之中,而是集中精力写作,编书和研究新诗,以此面对真实自我。他珍惜上苍所赐的光阴和机会,顺天道而行,正值新诗诞生一百年之际,便选编了《中国新诗百年选读》,同时还写了二十来万字的介绍与评述,既有总结与梳理之意,又有示于后人之用,“对新诗百年的历史,我们需要好好总结,千万不能患上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健忘症”。
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最可怕的是不断重蹈悲哀的命运。而这样的悲剧,在我国历史上,尤为突出,每个王朝都摆脱不了“革命的悖论”——从革命者转变为执政者,然后又被革命,一次次的血腥杀戮,并没有唤醒沉睡的人们,悲剧依然还在上演!由此足见,整个民族的集体遗忘症有多么严重和可怕!
而周先生的努力,就在于通过研究新诗的历史,以抗拒整个民族的遗忘症。百年来,新诗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关联一体,它是民族命运的映射。“因为近百年的新诗运动,无论是创作实践或理论,每前进一步,都因时因地无法不遇到不同之‘敌’的干扰、破坏,不正视它就无法向前”,因而通过系统的研究,消除各种恶敌,才有新天地。“战胜和清除了各种诗歌之敌,诗应能阔步前进”。而不应漠视新诗的命运,忽视新诗的历史,放纵新诗的敌人,否则灾难还会再次降临!
为了抗拒集体遗忘症,周先生在平淡之中日以继夜地奋进,不仅要书写新诗史,而且还要撰写他们那一代人的苦难史,即将出版的散文集《人在天涯》便是这种苦难的书写与证明,以文学的形式铭记历史,拒绝遗忘!他渴望“诗歌和文学成为建设我们新生活的钢铁与面包”,那时人间就会充满善良的天使,真善美才会漫山遍野!
周老仍宅在自己的居所,仍以中和平正之心耕耘着自己的事业,不知老之已至,虽处边地,却心系天下,仍举一人之力,干着经天纬地之大业!边地有此翁,不再是“疑城”!
(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万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