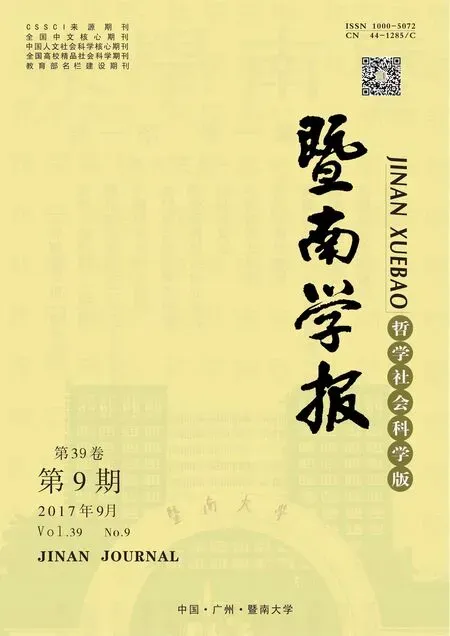《诗经·颂》与《圣经·诗篇》中美颂传统的比较研究
匡迎辉
(暨南大学 广东省高校女性发展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632)
《诗经·颂》与《圣经·诗篇》中美颂传统的比较研究
匡迎辉
(暨南大学 广东省高校女性发展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632)
“美颂”是一种超越时代和地域限定的人类共同的文化精神。《诗经·颂》和《圣经·诗篇》是人类早期美颂行为的主要呈现,虽然还带有一定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但已具有比较成熟的精神内涵和审美价值。论文通过对《颂》和《诗篇》中美颂内容、载体及功能的比较,从源头上分析中西方美颂传统形成和发展中的异同,肯定美颂精神在文艺作品中的意义与价值。
《诗经·颂》; 《圣经·诗篇》; 美颂; 文化精神; 文化差异
从满足生存需要的功利性实践活动,发展为理性的精神教育再到审美,“美颂”是一种超越时代和地域限定的人类共同的文化精神。早在人类社会的原始时期,先民们以颂神的形式求助神灵、驱除内心对大自然的恐惧,产生了基于原始宗教的美颂活动。然而作为一种以精神性为主体的理性行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颂》可算是我国 “美颂”文学的始祖;追溯西方文明之源,属于“二希文明”(希腊—罗马文明与希伯来—基督教文明)之一的《圣经》中的《诗篇》,堪称西方早期“美颂”文学的总集,据传是耶和华真正敬拜者大卫所记录的一辑受感示的诗歌集,在希伯来文中,该书名即是“西佛·透希尔林(Se’pherTehil·lim’)”,意即“赞美之书”。
《颂》诗分《周颂》三十一篇、《鲁颂》四篇、《商颂》五篇,共四十篇。“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据陆银湘《“诗经”颂诗的研究》分析,《颂》诗基本上是朝廷宗庙用来歌颂、祭祀祖先或神灵的歌舞曲,……具有庄严肃穆的宗教特色。作为一种祭祀先祖、歌颂英烈而得以流传的体式,从形式上来看,它除了有歌辞的性质外,还具有音乐、舞蹈的功能。《诗篇》包含圣诗共150首,表达了对耶和华的崇拜,一般用音乐伴唱,在圣殿礼拜时使用。英文卷名所用Psalmoi的单数形式,指用弦乐伴唱的歌,其词根可单指“歌唱”或“赞美”。
《诗经》在中国文化史上拥有崇高而独特的历史地位,深深影响着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的发展。《圣经》虽然由早期希伯来文明与希腊文明撞击结合而成,但通过基督教的广泛传播,对西方各国人民的思想心态和文化色彩产生出全方位的影响,成为西方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是影响西方思维模式的经典,也是西方思想、宗教和艺术的根。作为人类初期的主要艺术思维成果,两部圣著是人类文明进入自觉的标志,其记录的美颂行为虽然还带有一定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但已具有比较成熟的精神性内涵和审美特征。本文拟通过对《颂》和《诗篇》美颂内容、美颂形式及美颂功能三个方面的比较,探寻两种文化中美颂传统的形成和发展。
一、内容:以现实关切为旨归与以上帝为中心
宗教的要素包括宗教信仰、宗教情感以及与这种信仰和情感相适应的宗教仪式和宗教组织。以此来观照《诗经》中的颂诗,它具有非常明显的宗教性特征。颂诗中颂赞的对象有上天、社稷、山河、祖先,当中尤以颂赞祖先为最多。先民们视祖先为神,基于对先祖艰辛创业的崇拜,祭祀并颂扬其功德,带着一种宗族血脉的天然情感,这种虔诚和由衷的礼赞,上升到精神层面则是一种宗教的祟拜与信仰。诗中记录的祭祀活动,有主祭、助祭者和执事者,气氛肃穆、场面庄重,有着严整的组织和仪式。例如, 《清庙》中有“于穆清庙, 肃雍显相”、“济济多士, 秉文之德”,《雍》一章中有“相维辟公, 天子穆穆”等,文辞均呈现出庄重肃穆的宗教仪式感。
《诗篇》以丰富的内容,繁复的题材,表达了对神的信仰、感恩和颂赞,是以色列人敬拜神的重要内容,在以色列民被掳归回重建圣殿之后,才被正式收集成书,供崇拜时使用。它是犹太人会堂中的颂诗集和祈祷书、希伯来人圣殿和会堂仪典上的宗教颂诗,后来被基督教直接继承下来,成为基督教会的赞美诗。《诗篇》在基督教中的传播也是通过礼拜诵读来实现的,在圣典崇拜中,一个重要的仪式就是诵唱《诗篇》由专门的圣诗班轮唱,或由唱诗班和会众以应启形式吟唱。宗教性是《诗篇》的本质和固有特征。
然而,《诗经》为儒教的圣典、《圣经》为基督教的神典,《颂》诗和《诗篇》的宗教基本内涵和性质是不一样的。
《诗经》的宗教观指向“多神”,其美颂行为主要为“尊天”和“敬祖”。《颂》中多处表现出对“天”的信仰,如“秉文之德,对越在天”,“维天之命,於穆不已”,“不显成康,上帝是皇”等。周人通过对茫茫苍天的冥思、玄想,将其神化,认为它无所不包,无所不含,掌控着世间一切事物,自然、社会一切事物的运动由它指挥操控,赋予“天”以神性。在先民看来,“天”是与人世间相通的,是具有意志的格神。这里的“天”作为至上神具有质的规定性,为信仰之天,可感、可视、可听,可以赐福,也可以降祸,具有超自然的巨大神力,掌控自然与社会的一切事物,唯有对它顶礼膜拜才能获得它的眷顾与保佑。随着等级社会的出现,人世间的统治者借天的威力来巩固王权,认为自己“君权神授”, 自称为“天之子”。《周颂·时迈》篇“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中的“天子”即指周代最高统治者。另外,由于整个社会建立在以亲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族集群和宗法制度上,“祖先崇拜”也是周人的重要宗教观念。“从宗教的意义来看,祖先崇拜以祖先的灵魂作为崇拜对象,相信自己血缘祖先的灵魂永远存在,他们的灵魂对自己的血裔后代的生产、生活活动具有相当大的作用,……为了报答祖先的造福与赐与,祈求祖先不要降祸作祟,从而虔诚地祭祀。”《周颂》中有大量祭祀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庙堂乐歌,如《维天之命》、《载见》、《执竞》等。作为宗族的代表,祖先是整个宗族的精神核心和象征,在这种祭祖仪式中,人们得到了一种血统认证与归属感的满足。“君权神授”和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维护了血缘宗法组织和家族、国家的统治秩序。
“尊天”和“敬祖”的宗教观念又延伸出 “明德”和“重孝”的伦理观念,对“德”“孝”的颂扬是《颂》诗美颂精神的重要特征。“德”是沟通“尊天”和“敬祖”的桥梁,《诗经》中的“天”有着明显的道德内涵,它爱憎分明、善恶明辨,而上天选择“天子”的依据是道德,辅助的是有德之君,“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以德配天”、厚德善政是对统治者品行的一种内在规定。《颂》诗中的主要祭祀对象并非周人历代祖先,而是那些盛德茂行、爱惜人民,为周部族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而作为“王”的祖先。“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丞民,莫匪尔机。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是《周颂》中颂扬周人始祖后稷功德的诗句;“于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颂扬了周文王的高洁德行。“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王国维认为西周“文化上的巨大变革,即在于将‘德’的范畴融入‘天’的观念中……殷周之兴灭,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故克殷之后,尤以德治为务”。和“德”一样,“孝”也成为《诗经》中反复强调、使用的概念,“孝”在道德上是和祭祖敬宗的观念密切相关的,周人祭祀祖先既是为了获得祖先神的保佑和赐福,同时也表达了对祖先的孝敬, “以祖为宗,以孝为本”。如《周颂·载见》“率见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寿,永言保之,思皇多祜”。故此,在“明德”与“重孝”中,“尊天”和“敬祖”的宗教目的已经被增殖进道德意义。从宗教到伦理的延伸,《诗经》颂的内容已经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政治功能。
通过作诗来表达对贤明君主的赞美与企盼是《诗经》中许多作品的主旨,《颂》诗中的“神”其实是具有“神格的人”,宗教外衣下所关注的仍然是充满人情的现实世界。与《诗经·颂》在内容方面相比较,《圣经·诗篇》歌颂对象是神,是对神崇拜敬畏情感的抒发:赞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赞美圣父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奇妙大能,和对圣子舍身流血施行救赎的宏恩,上帝是《圣经》中描述的唯一的神。从以色列人的上帝到全人类的上帝,这个耶和华,是一个具有“人格的神”,而不是部落首领、国王或其他。一方面《诗篇》是神的话,它描绘神对诗人的看顾、施恩,以不变的爱和无条件的恩典侧耳听人的祷告;另一方面,《诗篇》也是人的话语,它记载了诗人向神的倾述,及对神的信靠和祈求。在对上帝神恩和救赎的颂赞中,获得的启示是爱天下所有的人,行神人约法之义,即神的道德要求是“爱”和“义”,通过“爱”和“义”见证神的荣耀,激发人努力向上,这是《诗篇》的最高价值。它不仅是见证人心渴念神的过程,也是见证那些找到神的心灵获得的安息和满足。因此《诗篇》不是说教的典籍,它是表达人类心灵深处宗教的渴望。《圣经》的宗教性是纯粹的,它将自然和人类产生、变化和发展均纳入以上帝为中心的信仰体系,神的属性、权能和地位是启示的主体和信仰的根基。现实中难以解决的问题,逐渐从人生存的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向精神空间转移。《诗篇》很少涉及现实政治,偶有涉及的篇目,也多是向神认罪,其所关注的人,不是非现实中的、哲学意义上的“人”。
如果说《诗经》以现实社会、政治礼教为主旨,《诗篇》则强调耶稣基督信仰的救赎观和公义的伦理观,以宗教神谕为根本,以希伯来人的内心宗教经历为中心,寻求人类与神的沟通,表现出一种追寻超自然、超世俗的精神奥秘的倾向。
二、形式:以文学为方向与以音乐为载体
无论中西方,早期的美颂都表现为诗乐舞结合的艺术形式。“在文明未开化的远古时代,人类的文化即在宗教,人类的一切活动皆与宗教有关。”美颂和宗教同样密不可分,原始社会初期的宗教产生了以侍奉、献媚和祈求的姿态出现在神灵面前的另一种巫术——颂神,而“礼乐就是祭神的仪式与音乐歌舞,是原始宗教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用乐歌、乐舞、美言祀秦神,以求得到赐福和庇佑。例如《葛天氏之乐》“昔葛天氏,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中,先民们岁末祭祀,歌咏祖先的由来、歌咏草木、五谷的生长,企盼丰收。当然,“他们歌颂神灵时候的原始乐舞还只是一种非理性的巫术形式,更多表现出了迷狂的色彩”,但他们论述和记录的是诗乐舞最初的本于一体。《礼记·乐记》有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汤姆森在《论诗歌源流》中也说:“舞蹈、音乐、诗歌三种艺术开头是合一的。”
然而,从发展结果来看,中西方却选择了不同的艺术呈现倾向:中国的美颂青睐文学形式,纵观我国历史上的作品,多数以吟诵的形式活跃在中国文坛;西方的美颂主要与音乐结合,体现为“宗教颂歌”,这反映出中西方不同的艺术思维。事实上,这种思维差异的原生性基因,早在《诗经》的“颂”篇和《圣经》的“诗篇”中已经存在。
首先,美颂对象决定着沟通的方式。西方颂赞的是神,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本身微妙、神秘和复杂。作为一个非实体性的精神存在,神与人之间的情感属于灵的交融,为了达到精神的彼岸,人需要用心灵来与神沟通。黑格尔认为:“通过音乐来打动的就是最深刻的主体内心生活,音乐是心情的艺术,它直接针对着心情。”音乐的抽象性特征及无限、超越的本质,决定了唯有音乐能最好地引领人与神灵进行精神对接。著名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有言:“歌曲能够激励一种虔敬的感情,音乐与我们精神情感之间惊人的相似激发人们对上帝的渴求。”这源于对音乐和谐性和有序性的认识。确实,音乐是一门适合表达情感的艺术,它所表达的情感几乎涵盖了人类的全部精神,内容丰富,包括人的思想、情感、灵魂、意志、甚至潜意识,事实上,《圣经》从一开始就选用了音乐作为它首要的传播途径。《诗篇》150 篇第3节到第5 节中说道:“要用角声赞美他(耶和华),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响的钹赞美他,用高声的钹赞美他。”人们演唱颂赞歌就是在与上帝进行交流和沟通,同时表达对造物者最真切的崇拜和渴求。
而在“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语境中,美颂从诗经时代,已经开始与政治结合,“天”与“祖”的宗教外衣下颂赞的其实是“人”。从表达和接受两方面看,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思想、情感具象清晰,中国的文学以汉字为符号,对于实际存在的具象内涵具有强大的表现功能,因此文学最终成了主要的美颂形式。《周礼·太师》郑玄注: “颂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可知《颂》以诗为载体,具备“诵”的音乐节奏,是在宗教礼仪场合中出现,作为祭祀用的歌舞曲。颂诗尚声,具备宗庙祭祀的特点,在祭祖的同时,证明现实政治的合理性,因此,中国雅颂自产生始,就重在“美盛德之形容”的情感内容和内在的文化内蕴。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虽然会通过乐官演奏或演唱《诗经》的某些篇章,但对其乐调的欣赏为次,看重的是歌词内容的展示。对情感内容而言不仅仅是情感本身的追求,最终影响了后世美颂朝着文学形式的发展趋向。汉朝文学就直接继承了雅颂的美颂传统,如杨雄的《赵充国颂》、傅毅的《显宗颂》、刘充的《高祖颂》等,在语言形式上以整齐的四言句式居多,成为汉代文学的主旋律。
其次,诗的文意及表现手法影响了其音乐的表现空间。《诗篇》150篇是对世界创造者——神的称颂和赞美,是心灵之呼喊,诗人充分利用生活中熟悉的具体事物来表达神的属性,文意曲折而深邃,修辞手法多隐喻,“王”和“牧者”这两个隐喻频繁甚至交替出现,用来赞美神性的王权和人性的慈爱。正是因着形象的隐喻,《诗篇》语言凝练、意象丰富、抒情且富有生命力,也正是因为抒情的需要,音乐成了其表达的主要手段,因为抒情就是音乐的本质特征。早期基督教音乐主要以人声颂歌直接向神表达崇拜、感激和赞美,用音乐情绪来烘托出神圣、庄严、肃穆的气氛。《颂》“作为宗庙祭祀之乐章演出,当是采用载歌载舞,有声有色,美先人之盛德而形容之形式”。然而,由于雅颂是朝廷之歌,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反映的是社会现实,美颂的对象是人,《颂》偏向于采用“赋”的表现手法。所谓“赋”就是以叙述为主,记言叙事、长于铺陈、繁于文彩,对表达先人功德和社会人际的内容很有优势。但“赋”说史味浓,句子散文化而缺乏形象性,适宜于诵而不宜歌,因此中国的美颂虽然也未曾离开音乐,但与文学更亲密。
再次,诗与乐的依存和制约关系决定了美颂传统在艺术载体上的发展方向。远古诗与乐的产生孰先孰后,或同时存在已很难考证,但《诗经》风雅颂是依据音乐形式的不同而区分的,这为目前学界大多数人所认同。后来“颂”成为一种相对固定的曲调,以辞配乐、依曲填文,“乐”部分日趋僵化,“颂”呈程式化的趋势;且西周礼崩乐坏,诗摆脱乐的束缚,从音乐领域拓展到文学语言领域,以至于最后雅乐消亡,“颂”只存留在文学领域。直到十九世纪末,随着近代中国合唱艺术的兴起和发展,美颂再一次在特殊历史时期选择以音乐作为主要载体,在西方音乐技法和民族音乐元素的融合下重现生机。
《诗篇》始终是以文为本体,依文而成曲。随着时代的演进,或者是以《诗篇》整篇诗歌为歌词、或者以其中的诗句为主题,诗篇成为音乐创作永远的源泉,从巴赫、亨德尔到20世纪的许多作曲家,包括门德尔松、李斯特、德沃夏克等都有过与《诗篇》相关的创作。可以说《诗篇》及颂赞歌的演唱成就了格里高利圣咏,成为西方音乐的奠基石,对世界音乐的发展起着恒久的影响。虽然西方的美颂后来也走向世俗,但音乐永远是美颂最主要的载体,而且在世俗的美颂中仍含有一种宗教的精神。
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来语言文字一脉相承,美颂传统一经形成,就在文学形式的表达中得以传承;基督教在西亚至整个欧洲的传播中,语言文字有其局限性,更具共通性的音乐语言成了承载美颂精神的首要媒介。当然,自诗乐舞原生综合的《诗经》和《圣经》始,文学和音乐分中有合,离而不散,承载着人类共同的美颂精神走向审美和理性。
三、功能:一致的“和合”教化
如果说历史流变下,中西方在美颂内容和形式方面,更多地表现于不同发展方向,关于美颂功能,两者却始终体现出一致的“和合”教化思想。先民时期的这种教化思想尤为突出,是一种伴随宗教意味的道德教化。《说文解字》解释“宗,尊祖庙也”,中国“宗教”的含义即为“祖先崇拜”,这“祖”的概念除了世俗的政治指向,同样具有宗教的神学意义。《诗经·颂》主要是祭祀祖先时候的祭文,洋溢着无数对先祖创业功绩的颂扬,《礼记·祭统》:“祭者,教之本也已。”同样,《圣经·诗篇》展现的是对上帝施恩和救赎的赞美,其内容是以虔诚的宗教情感和信仰为基础,对“德”的肯定和宣扬。《诗经》颂篇和《圣经》诗篇在道德教化功能上具有一致性。
首先,二者颂赞的前提都是德和爱,颂赞的旨归都意在对自身行为的规范。颂篇中敬的是祖,重在赞颂先祖仁爱之德,希望这种仁德能在宗族血脉的方式中得到延续。 “修德配天”、“敬德保民”,是颂赞对象具备的重要品质。例如《周颂》崇拜赞美了从周始祖后稷到文王、武王的德业勋烈,体现了周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精神追求;《鲁颂·宫》更是把“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并举,表明了周人重视德行修持的王政理想。《诗篇》颂赞的也是上帝的德,基督徒十分看重上帝的品格,在他们心目中,上帝是全能而至善至美的。基督教以上帝的品格作为其伦理道德的基础,爱人人是上帝的准则,人互爱是上帝的要求,这种追求平等的爱,与中国的仁爱有内在相通性。《诗篇》中还多次体现祈求和平安宁的教化思想,例如第122篇中有 “你们要为耶路撒冷祈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第128篇中 “看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在这些对祖和上帝的称颂中,不仅有对被颂赞者的敬畏,还有对自身行为的规范。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早期宗教祭祀活动客观上实现着对祭祀参与者、后人、信众的教化。祭祖仪式中强调先祖功业的继承和发扬,尊祖,在伦理观念上延伸为重孝,此血统认证的表象下是归属感的满足,有着极大的内聚张力。后世毛传以及朱熹对诗经“颂”的篇章的评价均有论及由这种血缘认同性而形成的对祖“德”的延续力。基督教亦追求善德,他们专注于救赎,认为只有按照上帝的指引行善事,才能洗清自己的罪责以求来世通向天堂。基督教认为应该爱人如己,爱是其精髓,正是这种爱的教义使基督教成为人们心中的信仰,从而把神和道德紧密地联系起来,产生一种上帝能够监管其行为的内在约束力,构筑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和道德城墙,去维护他们所认知的善。
其次,二者皆通过仪式在诗乐舞的审美体验中实现。在“明堂”“郊庙”或是“教堂”,《诗经》的“颂”和《圣经》的“诗篇”,分别为商周祭祀、礼乐仪式和基督教礼拜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前文所言早期的宗教祭祀仪式是以诗乐舞的综合形式呈现的,因此颂赞时无论文辞还是音乐皆宏大浑厚,旨在符合当时庄严肃穆的仪式氛围,最大限度上体现祭祀者的虔诚和崇拜。纵看颂篇,多次使用赋的手法歌颂先祖功德,文辞拖宕铺陈,乐则以洪亮而稳重的浊音为主,诗乐中蕴含着先祖之“德”的浩然之气,以及浑厚质朴、雄健浑融的精神品格。如《思文》一诗,文辞不厌其烦详述后稷功德,在盛大庄严的礼乐中,对颂赞者的崇拜情感逐渐内化为对自身品德的要求。西方的颂赞由于颂赞对象为共同的神——上帝,而“上帝”对于人来说,是一种绝对的精神实体,是人所难以把握和不可企及的,因此言辞注重使用隐喻手法,音乐平直、柔和、理性,表现出对“有限性”的超越,对上帝 “无限性”的追求,让人感受到的是心灵的净化和精神的震撼。在集体礼拜的虔诚中,唱诗的过程营造出强大的宗教氛围,对上帝的情感和归属意识被升华,于庄严和神圣中走向崇高。“听到这些神圣的歌词通过乐曲唱出,比了不用歌曲更能在我心里燃起虔诚的火焰,我们内心的各式情感,在抑扬起伏的歌声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音调,似被一种难以形容的和谐而荡漾……”
教化总是与伦理相结合,所谓伦理,即人们处理相互关系时应遵循的行为准则也,此“理”规范的是“伦”(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关系)。《颂》和《诗篇》均以“和合”为最终目标,在颂赞中进行道德伦理的教化,但是两者也有一定的差异性,主要表现为道德伦理的实践路径。汉字“教”字,结构上是“孝”与“攴”的组合,“教化”,便是以“孝”之文化去“化倒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推到本质便是“孝”。在讲求宗族血脉的汉文化中,家为父子、国为君臣,“孝”是维护稳定的关键因素,也是社会得以延续的重要保障,通过宗法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理”,族群和社会的团结得以实现。由此看来,中国的教化重在外向的修行,在群体制约中实现社会的中和。
与中国汉文化不同,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和合”伦理教化思想,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人与上帝关系的基础上。上帝是伦理道德的典范——慈爱、圣洁、善良、怜悯、公义、信实,上帝与人签订契约,要求并监督跟随他的人,效法其美德完成对善的追求。因此,西方的教化重在个体自身的修炼,个人通过自我约束实现道德的崇高感,最终达到社会的和谐。中国的“孝”对应西方的是“契约”,“孝”倾向于情感,“契约”却更偏理性;“孝”是对外的,“契约”是向内的;也就是《颂》所追求的“德”通过与他者互动而得以实现,而《诗篇》颂扬的“德”,通过个人理性约束自己符合上帝的立法而达到。
结 语
本文对标志人类文明进入自觉的两部巨著《诗经》和《圣经》中美颂行为的比较,意在梳理中西美颂传统形成初期的特征,分析其对后世文化传统及文学艺术的影响。综上:无论是保持着对神的超世俗性颂赞,还是将美颂对象拉回到现实中的“人”,无论是以诗乐相伴的形式,还是更多地通过诗文来颂赞,美颂在中西方历史上都曾发挥着“和合”人心,从而整合社会力量、凝聚思想、巩固社会制度的重要作用。美颂传统既不是某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精神思想,也不是某个人的情感流露,而是整个民族的性格、心理、意识的反映,甚至已成为一种极其稳固的文化结构和心理力量,跨越时空存在于整个中西文化史。作为一种亘古的文化精神,基于“德”和“爱”的美颂,在中国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昂扬奋发的精神力量,以及爱民族、爱祖国、爱生活、爱生命的人文情怀,在西方,同样是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得以形成的基础。
伴随着宗教的颂赞,西方的文学、音乐、绘画,甚至建筑艺术曾达到艺术的顶峰;美颂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至近代,更是在合唱、绘画、戏剧等领域,扩展到对祖国、民族、自然、英雄等的深情讴歌。事实上,艺术无论使用何种语言,音响、色彩和文字都是一种艺术符号,记录的是现实生活,表现的是真实思想和情感。艺术符号有技术和审美的高低,但艺术不能停留于对符号本身的把玩。萨特的介入理论就充分肯定了文学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主张文学要介入生活,作家要有社会责任感,文学创作要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重大问题。
优秀的文艺作品必须是价值取向与艺术追求的统一。比较中西美颂传统的异同及成因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肯定大雅正声的历史感与传统美颂精神中“德”的社会价值,关怀文学艺术的思想性和精神力量,以切合时代发展的需要。
2017-01-17
匡迎辉
(1972—),女,江西九江人,文学博士,暨南大学广东省高校女性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I206.2
A
1000-5072(2017)09-0086-07
[责任编辑
池雷呜
责任校对
闫月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