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虚名终底事
杨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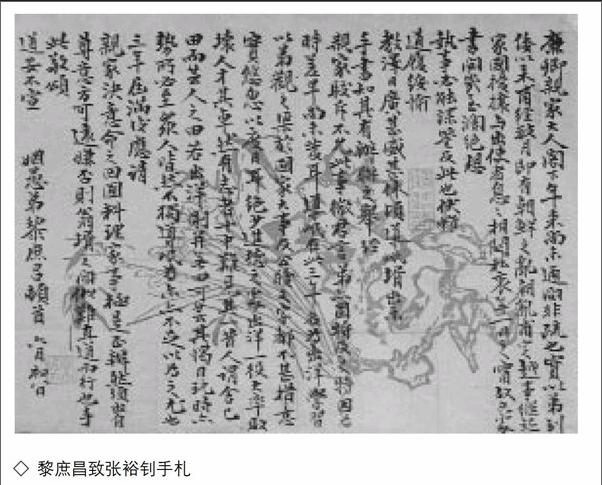
张裕钊(1823-1894),字廉卿,号濂亭,湖北武昌人,与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并称曾门四弟子,以古文与书法煜耀于世。曾国藩对其尤为称赏,赞其“好学不倦,作古文亦极精进。余门徒中,望有成就者,端推此人”(曾国藩:《求阙斋日记》)。吴汝纶亦盛赞:“清代足与文章之事者,姚鼐、梅曾亮和曾国藩后,惟张裕钊而已。”(吴汝纶:《与吴季白》)张氏性严介,寡交游,“尝数月不出户庭,与人对坐,或移晷始一语”(张沆、张浍:《哀启》)。道光三十年(1850年),张裕钊考取国子监学正,授内阁中书,在北京渡过了一段拍张跳荡、饮酒诙嘲的生活,但性非所好,志不在此,1852年毅然辞官归里。见知于曾国藩,入其门下,淡泊仕宦,一心向学。先后主讲武昌勺庭,江宁凤池,直隶莲池,武汉江汉、经心及襄阳鹿门等书院,成就后学者众。张氏一生谨言慎行,持身约甚,穷毕生之力治文事,读后人传记评语,无不对其甘守寂寞、覃心向学的品格大加赞赏,给人留下一位在纷纭乱世中,甘愿独处书斋,不食人间烟火的大儒形象。
果真如此吗?
近读张裕钊家书,语多家常,近乎白话,与选入文集中的碑传铭序、论学书札等应酬文字端着架子说话,遣词造句小心翼翼,文采风流迥然不同。这些私密性的信札语及家庭琐事,友朋交谊及世态人情等毫无顾忌,信笔直书,一反其惯常刻板谨严的形象,呈现出另一番面目。
张裕钊有一兄,名张锴,长裕钊三岁,其上还有一姐,男女共排,故信中多称二兄;有二子,张后沆、张后浍,后改名为张沆、张浍。现存家书多为写给以上三人。张裕钊一生游幕,辗转多地,朋友圈皆一时名流,师事曾国藩最久,与吴汝纶性情最为契合,与黎庶昌又有亲家之谊,故与以上三人的信札往来也较频繁。
1889年2月,在武汉江汉、经心书院讲学的张裕钊写信给张浍:
天下事但当务实,不必鹜名,声闻过情,往往败露,实至则名自归。我生平从不张皇,此次返鄂后,亦仍守故辙,然数日以来,微闻此间上下皆甚倾服,是其明验。当时张裕钊因李鸿章一纸逐客令,已离开河北莲池书院,回到武昌。经此变故,他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有了更深的体悟,愈发坚定了自己与世无争的处世之道。信中不忘叮嘱儿子与人交接时,收敛锋芒,低调行事。然后言归正传:
王文泉文已撰就,今寄去,孔刚介文亦将续行撰就寄至。去年孟芾臣所说,不知是作墓表,是作家传?我一时忘却,恐说是家传。汝等但云家传不如墓表之合体裁,倘渠必欲作传,则将原稿略加窜改,再行邮寄亦可。但文稿已就,润笔自先可交,不必再待改稿,此一定之理势。此文我颇自喜,如它日刊入文集,则彼已经讨大便宜。万一彼欲得我书上石,必更送三百金不可。
碑传墓志为旧时重要的纪传文体,传主往往可借此流传后世,要把传主平淡无奇的一生点染得摇曳生姿,鲜活感人,对写作功力要求极高,寻常人家也以能得到大家亲笔作传为荣。因此文坛名家传世文集开篇即为传、记、书、表等,张裕钊也不例外,为人作文写字也是其重要的经济来源。此处的孟芾臣(孟黻臣)即孟庆荣,河北永年人,光绪十六年进士,曾任学部左参议及右丞,在河北学界亦有声望,张裕钊主讲莲池时,两人过从甚密。但张氏私下对其评价不高:“其敦笃似查冀甫,学问少逊,而晓畅世事过之。”(张裕钊:《致張锴》)在他看来,孟之学识平平,敦厚如其弟子查燕绪,但明事理而已。孟托张裕钊为王文泉作家传,但张氏记忆有误,写成了墓表。但他并不打算重写,而是教儿子将原文略加修改交差,且须先付酬金,美其名日墓表比家传更合适。而且还颇有不甘,说这篇文章如果将来收入文集,付梓刊印,那对方可就占了大便宜(后来查燕绪确将《定州王君墓表》及《孔刚介祠堂碑记》收入《濂亭文集》)。如果想请他书写刻石,则明码标价,需奉送三百金!着实令人瞠目。很难想象,轻薄事利的张裕钊如此看重润笔酬金,即使好友托办,也不讲情面。
张裕钊为何对自己的书法这么自负,一篇三百余字的碑文竞开价三百金,看他怎么说:
我近日作书,益有得心应手之乐,自度竟欲突过唐人,即使不能,亦当与欧、褚诸公并驱争先。此事我胸中已确有把握,殆非妄言。(张裕钊:《致张浍》)
客观地讲,张裕钊的书法个人风格鲜明,汲取了北派碑体之大成,融而化之,字体结构里圆外方,方中带圆,精气内敛,风韵独具,被誉为在近代书坛上别开生面的“张体”或“南宫体”(因其代表作《重修南宫县学记》得名)。张裕钊对自己的文章还是有所保留,但书法则不遑多让:“古文吾亦犹人,书法当独有千古。”(《清史稿·张裕钊传》)康有为一贯尊碑抑帖,故而对得之北碑精髓的张裕钊书法极为推崇:“其书神韵皆晋宋得意处,真能甄晋陶魏,孕宋梁而育齐隋,千年以来无与比。”(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张裕钊自视甚高,求字除一律收润笔外,对用纸亦特别讲究:“宣纸必玉版宣,杂色纸惟冷金笺、雨雪宣、大红蜡笺三者差可,他色纸不能写。”(张裕钊:《致吴汝纶》)他还曾对吴汝纶说:
近世金石刻稀少,吾书虽工,世不求,无所托以久,恐身死而迹灭。吾将归于黄鹤楼下,选坚石良工,书而刻之……千百世后,必有剖此石壁,得吾书者。
可见他苦心经营书法,是将书法作为传诸后世,以求不朽的名器。张氏书名重当时,时人得其片纸只字尽宝之,汪士铎称其“寻常一字值百金”,并非妄言。张裕钊在家信中对文章书法的率性自矜,毫不掩饰,也就不难理解了。张氏书法流播甚广,在日本也很受推崇,弟子宫岛相伴多年,得其衣钵,回国后创立书院,对传播张裕钊的书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张裕钊于咸丰二年(1852年)八月辞官南归,是年十二月,太平军攻克武昌,剑指南京,大清帝国国势日溃,如丸走坂。张裕钊文名虽盛,但无一官半职,乱世中终归要有落脚处以谋生计,无奈之下只得求助曾国藩及其同僚。1853年夏,应安徽巡抚江忠源之聘,张裕钊主讲武昌勺亭书院。是年底,江忠源战死,张裕钊重回曾国藩幕中。1859年2月,应湖北巡抚胡林翼邀请,他再赴武昌参编《读史兵略》。但编书并非长久之计,1864年11月,迫于生计,张裕钊致书曾国藩,请求推荐存身之所,甚至情愿委身盐局当差以糊口:endprint
既顷,湖北书院已无可谋者……欲肯夫子寓书杜小舫观察,于汉口盐差局为别置一地,每月可三十金,乃稍足自给。(张裕钊:《与曾国藩》)
不过这次曾国藩以“从前盐务冗费多端,新立章程概从删汰,并无干修之例,碍难措辞”婉拒了他的请求。但曾国藩还是经常接济他,并致信李翰章等人,礼遇张裕钊,设法为其谋职。1871年3月,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聘张裕钊主金陵凤池书院讲席,直至1882年年底。1883年冬,李鸿章聘其任保定莲池书院山长,至1888年卸任。除此之外,十几年问,他曾辗转湖北钟祥编辑《钟祥县志》、武昌崇文书局司理校雠、湖北通志局编《湖北通志》等,可谓席不暇暖,辛苦异常,这些事务一部分是人情往来,但更多的还是为衣食计。已在莲池书院执教的张裕钊写信给兄长张锴,述说谋生糊口之不易:“大抵谋馆难,而干修则尤属万难,必大有力、大情面乃侥幸可以办到,然荐者及主者稍有移易,即立行辍止,只有取得一年算一年,断断不可常恃。”(张裕钊:《与二兄书》)书院生活远非想象的那样优裕从容,虽然有李鸿章等大员推荐延请,但薪水也只能一岁一议,且岁无定数,不能保证一以贯之,实在艰难。张裕钊虽然每至一处均被奉为座上宾,但毕竟不能自立,有寄人篱下之感。友人也多有劝谏,“胡不振翅凤池上,对扬奇木歌灵禽”(汪士铎:《赠张廉卿舍人》)。
不过文字虚名终底事,衣食生计乃是最现实的事,不可一日无之。正是出于这种辗转颠沛、处处求人的切身体验,他虽不喜举业,但对张沆、张浍还是寄予厚望,希望二人能走科举正途,谋得出身而后自立。于是在课业教学之余,“仍督令(二子)温习旧业,为科举之学”(张裕钊:《致吴汝纶》)。无奈二子“时文工力皆至浅薄”(张裕钊:《致吴汝纶》),无法继承自己的文章志业,难堪大任,只能托朋友故旧勉强在地方衙门里谋个差事。他曾在信中向吴汝纶吐露内心苦闷:“大小儿于去秋得一厘差,差足补苴目前。但秦中章程,一岁即当瓜代,苦不能久耳。”(张裕钊:《致吴汝纶》)这些小差使顶多勉强糊口,而且只是权宜之计,让张裕钊操碎了心。张裕钊与黎庶昌不仅同为曾门弟子,且为儿女亲家,1876年,张裕钊长子张沆娶黎庶昌长女瑞荪为妻。1881年,黎庶昌奉命出使日本,张沆随同赴日。张裕钊既然无力为孩子谋得更好的出路,便寄希望自己的亲家着意提携。他又推荐杨守敬随同黎出使日本,并写信给杨守敬,请其多加管束,可谓用心良苦。张沆赴日之后,张裕钊经常写信给张沆,除互通声讯、殷勤叮嘱外,也希望其多来信:
汝以后必须勤于寄信,得汝一函,不独我心内释然,即举家亦皆喜慰不可言。能一月两函乃更佳耳,虽数行亦可,得数行便如获珍宝也。(张裕钊:《致张沆》)
言辞温厚深挚,一改平日正襟危坐的严父口吻,父子情深,令人动容。
张裕钊虽性情狷介,不谙奔走逢迎之术,但有时也不得不低首下心,如桔槔随人俯仰。黎庶昌在日本搜辑“古逸丛书”,为学界瞩目。时任直隶通永道的沈能虎知张、黎二人的关系,便辗转向张裕钊求书。张知沈为李鸿章亲信,虽不胜其烦,但也不敢得罪,只得写信给张沆,请亲家黎庶昌再寄一部《玉篇》来,赠其了事。
张裕钊对张沆寄予厚望,可惜的是张沆非笃志向学之士,难堪大任,1884年7月,黎庶昌致信张裕钊,直言不讳地告知张沆在日情形:
导岷在此三年,名为出洋学习,以弟观之,渠与国家大事与公牍文书都不甚措意,实悠忽以度日耳,绝少进德之虞。出洋一役,大率敗坏人才,其卓然有志者十中难见其一。众人皆然,不独导岷为尔,亦不足为之忧也。三年届满后,应请亲家决意命之回国料理家事,极是正办,然须出自遵意方可远嫌,否则翁婿之间似难直道而行也。(黎庶昌:《致廉卿书》)
张沆出洋三年,不思进取,虚度时光,连岳父黎庶昌也难掩失望之情,认定他实在不是这块料,希望亲家出面做女婿的思想工作,免得翁婿生隙。这对张裕钊来说确是极大的打击。所以1887年黎庶昌第二次奉命使日时,张裕钊听从了亲家的意见,劝阻张沆再次出洋,为了打消其出洋之念,他甚至搬出曾纪泽英年早逝一事来提醒张沆,出洋是不祥之兆:“出洋一节,且可暂置……劫侯之逝,或亦不应出洋之一机也。”(张裕钊:《致张沆》)张裕钊连续写信,苦口婆心地劝诫他,详陈出洋与谋差之利弊,告知其时任陕西布政使的陶模和陕西巡抚的鹿传霖都是好友,完全可以施以援手,助其谋得一待遇优厚的差事,而大可不必去选择变迁无常、难可逆料的出洋苦差。1890年7月,他再次致信张沆,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
揆之情事,衡之义命,斯为至顺,断无一旦舍此,更谋出洋之理。外则有负上官优渥之意,内则举家之中言及汝欲出洋,无一人愿意者。此事便作罢论也!
真可谓恩威并施,好话说尽。后来张沆也听从父命,安心当差,并与弟弟张浍一起继续攻读。
二子并无特出之才,且无专心一力之志,无法继承其衣钵。张裕钊不再奢望张沆靠科举飞黄腾达,只求其读书明理,平淡生活即可。张裕钊开创莲池文风,桃李满天下,但自己的孩子却寂寂无闻,这也是一代名师的尴尬和无奈。
1884年7月,中法马江一役,清朝福建水师全军尽墨。以文人典兵事的张佩纶,身败名裂,被褫职发配。1888年,张佩纶获准回京后,李鸿章爱其才,招致幕中,并将幼女李鞠耦许配给其作续弦。为给乘龙快婿谋一教席,李鸿章举贤不避亲,有意以张佩伦取代张裕钊执掌莲池。为不得罪张裕钊,李鸿章修书一封,殷勤致意,措辞颇为迂回:
顷接奎乐山中丞来书,以江汉书院讲席虚悬,鄂中人士延企名德,欲回几杖,还式粉榆。燕赵诸生,久亲教泽,岂于中路夺我儒宗?敝处气谊素洽,倚助良多,闻信之余,怅惘阖极!独是执事楚国耆旧,儒林大师,况以贵乡文史之渊,重以阖部士民之望,情词如此,恐难靳辞,弥念高年,亦便故里。(李鸿章:《致莲池书院山长张》)
李鸿章搬出湖北巡抚奎乐山(奎斌)作为挡箭牌,力邀张裕钊返乡执教,并表示出对江汉书院“横刀夺爱”的不满和惋惜,但因张裕钊本为楚地大儒,故里士民想望其返乡也是名正言顺之事,而且还将其与近世名家一体尊之,最后才道出欲聘张佩纶继掌莲池的真实意图。话虽说得冠冕堂皇,但实际上不过一纸逐客令。此时张裕钊再次显示了其孤傲清高的秉性,遵命卸任,并慷慨致书李鸿章:“闻拟延张幼樵学士接主此席,可谓得人,莲池诸生亦皆有所依归矣。”(张裕钊:《复李傅相书》)言辞端正,不卑不亢,但其私下在与吴汝纶议及此事时则颇有怨言:endprint
顷得李傅相书云,接奎乐山中丞来函,以湖北江汉属余明岁讲席需人,欲招弟返鄂为之承乏,并称弟如许诺,拟延张幼樵接主此席云云。观此情词,不言而喻……而此间官僚人士,同声怅恨,物议颇为纷然,书院诸生尤怊然若失,其隽异之士愈益眷言衰朽,彷徨莫释,异日并拟散去。(张裕钊:《六月初八日与吴先生书》)
可见张裕钊对李鸿章的意图是很清楚的,莲池诸生对自己的挽留和眷恋也让他颇为感动,“征鸿念畴侣,欲去犹回睐”(张裕钊:《留别莲池诸生》)。决意南归途中,张裕钊还惦念莲池书院的情况,写信询问吴汝纶:“张幼樵已传为傅相乘龙之选,曾闻之否?外问咸称莲池一席,渠已改计不就,此言虽无确据,然十八九其信。又传有王壬秋(王阎运)主讲莲池之说,此语或亦不妄耳。”(张裕钊:《致吴汝纶》)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莲池的眷恋关注和对李鸿章徇一己之私的不平。
时在冀州的吴汝纶,也竭力挽留张裕钊:
目前深冀两州读书之士,意欲挽留在北,由此两州醵金为寿,亦如莲池之数。虽由省城下至外州县,俗人以为左迁,而大贤固不屑校论此等。缘恐从者南返,北士从此失师,不复能振起,非有他意也。执事倘见许,望密赐一复示,二州人当自上书傅相乞留,续自具书币造门请谒,于上游决无妨碍,于执事亦无轻重,不过于北方学者有无穷之益。
吴汝纶以北方学术大业为重,愿从中斡旋,只要张裕钊愿意,他可以出面,让师生上书李鸿章,加以挽留。张裕钊去意已决,婉拒了吴的好意。李鸿章得张裕钊信后,很快回复,对其南下返乡就职表示敬意,并奉上川资。不过他低估了张裕钊的影响力,毕竟张已主莲池6年,开河北学界新风,不仅培养了范当世、查燕绪、贺涛、张謇等文坛才俊,而且日本宫岛勖斋、冈千仞等人也慕名前来,学习古文书法,其声名已远播至海外。此论一出,诸生哗然,自发联名抵制。迫于舆论压力,张佩纶最终未赴任,李鸿章改聘吴汝纶接任,一来平复众议,二来吴张本是挚友,张裕钊想必也能接受。
离开莲池书院后,张裕钊旋就职武昌江汉、经心书院,1890年又赴鹿门书院短暂执教,1892年,因年迈体衰,精力不济,由张沆接至陕西西安草场巷养老。张在西安曾入荣禄幕中,后任职陕西三原书院。此时的张裕钊已七十二岁,经过这样一番颠沛辗转,身体每况愈下,很快罹患风寒,饮食骤减,夜不成寝,如秋叶凋落,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正月十四日溘然逝去。吴汝纶对老友张裕钊境遇颇为同情,叹惋无已:“辗转关中,流落以死。贤人末路,其可悲如此。”(郭立志:《桐城吴先生年谱》)离开莲池确是其人生境遇的转捩点。张裕钊在古稀之年,毅然以老病之躯自谋生路,维护了他孤傲清高的气节,但也在迁转流离中耗尽心力,安稳闲适的生活一变而至老无所依,一代大儒,终至陨落。
张裕钊虽名满天下,要立足谋生,也只能靠师友照拂,一生身如飘絮,难觅安身之所,年七十因无术自给,以老病之身被迫入陕谋生,郁郁而终,可谓晚景凄凉。在微言大义的正史传记中,只有表彰其学行文章的文字,其心迹曲折却难觅踪迹。其弟子友人所作传记文字中,总有为逝者讳的初心,只记其言述其行,未审其心,只记其圭璋特达、迥异尘俗的风采,略去其心境凄苦、潦倒困窘的一面,这也是传统评传文字的通病。
张裕钊文名虽盛,但《濂亭文集》所选文章多为墓表、祭文、寿序、碑传等应酬文字,不乏遵命代笔之作,所谓代人悲喜而强效其歌哭,不足传而弃之者多矣,真正發自内心的传世佳作并不多。倒是在为数不多的诗歌遣兴中,略可体味其牢骚与心酸。只有阅读日记、书信这些私人文字,才能体会其真性情,得悉其不为人知、不可为外人道的真面目。“万事悠悠无可说,一心耿耿有谁同?”(张裕钊:《百年》)正道出他内心彻骨的孤独和悲凉,也是其一生侘傺不遇、自伤自放的真实写照。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