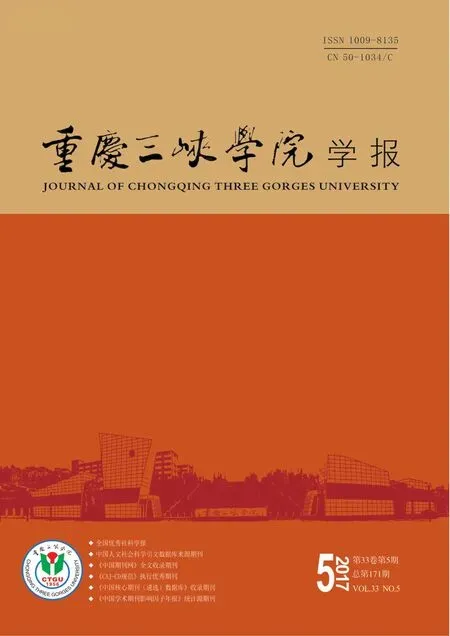章太炎的翻译——以《论进境之理》为例
王 诚
章太炎的翻译——以《论进境之理》为例
王 诚
(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汉语史研究中心,浙江杭州 310058)
章太炎与曾广铨合译的《论进境之理》涉及不同的学科,介绍了斯宾塞的进化思想,内容基本忠实于原作,删改了冗繁的论述,增添了必要的诠释。译文的表述工具是文言,遣词造句相对平易,但又不失古雅,将文言对于现代思想的涵纳能力做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堪称“新理络绎,妙义环生”。这次翻译使章太炎接触到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观点,对其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影响。
章太炎;翻译;斯宾塞;《论进境之理》
章太炎(1869—1936)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革命家、学者,师事经学大师俞樾,为乾嘉学派殿军。身处新旧更替、中西交汇的时代,他的学术恢弘博大、深厚精湛,不但在小学、经学、史学、哲学、医学等国学诸领域有总结和创发,而且广泛涉猎西方的哲学、社会学、宗教学、语言学、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等科学论著,走在时代的前沿。他不仅积极吸取西学的科学精神和营养,早期还身体力行,投身于介绍、传播西学和思想启蒙的行列,在翻译上也具体实践,作出一定的贡献。
1897年秋,他和一批志同道合者在上海创办了译书公会,计划采译欧、美、日等国家的政治、法律、教育、矿务、商务、农学、军制等“近时切要之书”介绍给中国民众。是年11月,担任《译书公会报》周刊的主笔[1]23,作《译书公会叙》,指出公会的任务是“紬五洲书藏之秘,以左政法,以开民智”,强调译书的迫切性:“五大洲之册籍,吾不能博发而扬诩之,吾则瞀矣。且新理日出,岁无留故,一息炭养(氧)更,其事立变。若乔木之移阴,若蛇蚹蜩翼之移壤,而吾犹守旧译,以成世之暗㫚,其焉能与之终古?”他还以邻国为鉴,认识到译书的长远价值:“独尝借观于邻国,日本得王仁以《论语》《千字文》传,其后经术艺文,遂什伯百济。泰西政艺,各往往取诸希腊、罗马,而文明远过其本。然则是译书会者,安知不如微虫之为珊瑚,与蠃蛤之积而为巨石也。”
1898年章太炎与曾广铨合作翻译《斯宾塞尔文集》部分章节,连载于《昌言报》。1902年章太炎翻译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一书,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当时的《新民丛报》评价为“译者于祖国学术博而能通,其所定名词,切实精确,其译笔兼信、达、雅三长,诚译坛中之最铮铮者也”,称之为“译界一明星”[2]。
一、《论进境之理》的译文特色
《论进境之理》是章、曾合译《斯宾塞尔文集》卷一的第一论,连载于《昌言报》第一至五本[3]。曾广铨为曾国藩之孙,早年跟随曾纪泽在英国多年,精通英、法、日、德语及满文。合作采取曾广铨口述、章太炎笔录的形式,故译文首栏题有“湘乡曾广铨采译,余杭章炳麟笔述”,此论译自《进步:法则及其原因》(),这是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早期的一篇阐述进化观念的重要文章,1857年4月初载于Westminster Review[4],1858年收入斯宾塞的论文集Essays: 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论进境之理》的原作底本是1868年由英国伦敦Williams and Norgate公司引入重印的“铅印版”斯宾塞论文集[5]。从总体上看,章、曾的译文是对原作的直译,甚至连尾注都以按语的形式译出,但增删之处也较常见。译文刊载后,严复随即在天津《国闻报》上撰文《论译才之难》,以译文首段为例提出批评,认为“《昌言报》一述一受,贸然为之,无怪其满纸唵呓也。西书可译而急用者甚多,何必取此以苦人自苦?吾愿后生以为戒也”。然而,正如王天根所指出的,“平心而论,章、曾译文确实比严译文逊色许多”,但“严复对章太炎译文批评,其文人相轻的情绪化色彩要远大于公正的学术评判与商榷”[6]。
《论进境之理》首段以意译为主,个别语句确实欠妥,比如,把“altering the temperature, and perhaps the chemical state, of the surface it covers”译成“而化其固有的面积”,不但遗漏了主要信息,而且连句意也不通。但总体来看,并未背离原文所要表达的意思。略举几例,如:用“探隐索微”的“隐”“微”来对译原文的“internal modifications”;把“the nature of these changes”译为“变化之理”;末句“以是知凡事当得其比例而后可考其进境何如也”,“比例”对应原文的“the law”(古汉语中“比例”是法律术语,常与法令连言,所以可引申指规律、原则)。这些都体现出译者的用心。
除去首段,通读全篇,译文精彩之处颇多,反映了章太炎的西学知识和章氏翻译的特色。严复在《论译才之难》一文中说:“按斯宾塞氏此篇之论,乃其少作,为天演先声,全书嚆矢。其旨欲牢宠万化,并为一谈。读其书者,非于天地人、动植、性理、形气、名数诸学尝所从事,必不知其为何语也。”其本意在于“暗中奚落章太炎虽精湛国学,却不懂科学,远不能和自己出身理工科的科班相比”[6],但也说明理解斯宾塞原作并非易事,然而章、曾的译文在对天文、地质、生物等学科内容的阐释并无破绽,反而表现出译者在自然科学方面较好的修养。章氏在诂经精舍时已治西学,其时撰写的《膏兰室札记》就曾利用西学著作所提供的科学知识,诠解疏证周秦典籍。他引用赫士《天文揭要》、雷侠尔《地学浅释》、韦廉臣《格物探原》等书,借助于它们所介绍的天体运动、星球演化、生物进化、分子原子与物质结构、光的运动、化合与分解、地层与考古等学说,对古书中一些疑窦难解或众说纷纭的文句作出新的解释。其后他还撰写了《视天论》《菌说》等专门论文,更反映出他对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最新成就的关注和吸收[1]306-307。对西学的广泛涉猎为他翻译斯宾塞的论文作了知识上的准备,反过来说,或许这也是他选择“牢笼万化,并为一谈”的《论进境之理》为第一论的原因。
尽管如此,章太炎毕竟是从旧学中出来的,青年时代大部分岁月是在研习“稽古之学”中度过的。虽然他并不持“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之见,但当中西两种学问相遇之时,他不可能不基于已有的知识结构和储备,去理解和吸纳外来的新知,他往往借用传统的思维和语汇来表达西学的概念和事理,带有一些格义的味道。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原文叙述物体碰击之后发生缩合反应而生热:
Yet more, this condensation is accompanied by the disengagement of heat. In some cases a spark--that is, light--results, from the incandescence of a portion struck off; and sometimes this incandescence is associated with chemical combination.
章氏的译文为:“伏火在藏,有迎而与之枝格者,则其火必大泄,或熠熠可指示,而物移其故质矣。”“伏火”是一个中医的概念,“伏”是潜伏之义,“火”即体内阳盛有余,治疗“伏火”宜升散宣泄,所谓“火郁发之”。章太炎将其移用来指物质所含的热能。两物相击,产生热量,发出光亮,所以形象地说是“伏火大泄”。这样的比喻出自精通中医的章太炎自不足怪,但显然不能算是科学的表述,因为热量并非伏藏着的,而是由动能转化的。
用中国古典的话语系统来传达西方近代的科学思想,其难度可想而知。钱钟书说,翻译的最高境界在于“化”。严复的翻译文字典雅,“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庶几臻于化境。章太炎的外语能力没法与留学西洋的严复相比,但要论文笔的古雅,则章氏有过之而无不及。

表1 译文中出现的部分古语及其出处
这种以旧瓶装新酒的翻译风格折射出译者的旧学功底,对照章氏一贯的文风不难猜想,这些古语多半是在自觉不自觉之间流露出来的,而不必如严复那样为刻意求古而苦心经营,为寻觅陈词雅句而“旬月踟蹰”。这种古雅的风格还表现为行文的简洁,比如下面一段话:
For a long time there connate forms of government—civil and religious—continue closely associated……For many ages religious law continues to contain more or less of civil regulation, and civil law to possess more or less of religious sanction.
译文仅用了“刑治、教治,其行若比肩”九个字,其意立现。译文对于繁琐冗长的叙述还适当地裁剪和删略。比如在讨论哺乳动物的进化时原文引了Dr. Carpenter和Professor Owen的大段意见,而译文则以“专家论是者,其文实繁,余不敢儳言”一笔带过。
二、《论进境之理》译文对原文的增补
如上所述,章太炎的译文风格古雅而简洁,但是,翻译这样一篇理论深刻、涵括广泛的学术文章,一味的求简必然无法传达应有的信息,所以《论进境之理》的译文为了使内容更加明晰充实和贴近中国读者,增添了不少原文没有的文句,大致可以分为五类。
(一)补出上下文之间缺漏的过渡环节
“教化的演进”(progress of civilization)一段中间明显多出几句话:“久之则战者不得战,渔猎者不得渔猎,操作者不得操作,无他,便于此者必不利于彼,故不能交相为用,而民有揭林木以争斗者矣。斗则弱者为俘虏,而强者必为酋长。”此段上文讲原始人自给自足(self-sufficing),喜欢离群索居(live apart from the rest);下文讲早期的部落(a nomadic tribe)形成,出现治与被治(the governing and the governed)。二者之间缺乏过渡,显然是原文的缺失,而上述增补的文句正好提供了中间环节。又如,原文论述胎儿的心脏(foetal heart)是各组织器官的始源,因为血液供给组织生长所需的养料(nutrition),同时,心脏产生的废料(waste)则促使排泄器官(excretory organs)的形成。但是,原文没有说明心脏为什么会产生废料,对生理学不甚熟悉的读者难免会发出疑问,为此,译文补充了一段原文所没有的话:“其血日以销铄,心尝佂伀,而血又有所损,若是则吾形内之川渎,将涸竭以至于绝流乎,是故水谷者,为血餫饟者也。”原来血液的制造需要水谷的营养,所谓心脏产生的废料其实是指食物消化后剩余的残渣。
(二)对原文观点进一步展开和阐释
“手工业的分化”(division of labor)一段,原文只讲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出现分工和技术的专业化就结束了,译文特意增加了一段话:“则考工始精,而器用之良窳,物产之美恶,必睨一国以为鹄,一国澶漫,则又睨一郡一邑以为鹄,其市列之有声者,于此又为其上选,而粗工无所鬻其技矣。”进一步阐述分工导致技术的进步和优胜劣汰。又如,原文提到生物体的发展(organic progress)是渐变的(gradual),因为不显著(unobtrusive),故不易察觉(difficult to detect)。译文在其后增补一段:“今夫日之昃昳,表随而向之,葵花随而蔽之,而人不能求其端者,其变渐也。蚕易形而为蛹,蛹易形而为蛾,而人不能求其端者,伏于茧中,其变暗也。夫人兽植物之变也,其渐且暗,亦若是矣。”用时间推移和蚕蛹变蛾的例子说明何谓渐变,使读者有具体、形象的认识。
(三)译者对原文内容所发的评论和感慨
原文讲到不同地域的气候、地质等条件各异,非各科学者的研究所能穷尽,译文在其后增了一句:“呜呼!以大圜之奥博,视吾生微眇,曾不黍子若,而欲写其形求其义,亦可悲也已。”这句类似“吾生也有涯,吾知也无涯”的感叹表达了译者对浩瀚宇宙、寥廓自然的敬畏之情。又如,原文指出,以前被认为只存在鱼类的地层,现在发现存在更高级的爬行类,而以前被认为只存在爬行类的地层,现在则发现有哺乳类。译者由此评论道:“人贵积思,学问始于广闻见,今世学者,其讹谬诚众矣,抑非专家之咎,其咎乃在闻见之不广也。”表明学者博闻广见的重要。
(四)联系本国历史或当前局势增补事例、发表议论
原文指出文字、绘画和雕塑都是建筑的附属,与神权统治有关。译文加了按语:“《尚书》旧说曰,五世之庙可以观怪,又禹铸鼎象物,屈原观楚寝庙作《天问》,知古者中国亦如是。”说明不但国外如此,古代中国也不例外。又如,原文叙述蒸汽机的出现促发了人类生产生活的一系列变革,由此说明一个小小的发明会引发无数的反应,译文于此宕开一笔,联系时局发议论道:“夫当一千五百年时,粤海有事,其为英利害特毫末耳,而今乃若切肤,然则事变之来,始不过蚁穴,而踵之起者其纷如是,可不察欤”?这番议论显然和原文无关,只是随机引发,提请读者关注时事,警示世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五)添加譬喻以增强表述的形象性
译文形容散布的原子相互吸引(the mutual attraction of the atoms of a diffused mass)为“萃而若粟之穗”。原文谈到新形成的地球开始减温(cooling),地核收缩(shrinking),导致地壳倾陷而成褶迭之形(wrinkles),用“瓜果之属,内瓤已枯,皮亦缩朒”来比喻,同时,译文在原文之外增加了一个譬喻:“譬老人肌肉日消,则肤革为之肿啥”。有凹陷必有凸起,有低谷必有高山,原文只形容了一面,译文补足了另一面。诸如此类为原文增色的譬喻还有不少,不再一一举例。
三、《论进境之理》和章太炎的语言学研究
章太炎和曾广诠合译的《论进境之理》是中国学者引介西方社会学(主要是社会进化理论)的最早译作之一,在翻译史和社会学史上有一定的贡献[7],同时,对于章氏本人而言,《论进境之理》中关于语言起源和发展的论述对其语言文字学研究有一定的影响,值得研究者关注。
章太炎在学术上的一大贡献是使“小学”真正摆脱经学的附庸地位,发展出一门独立的语言文字之学[8]328。十九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和社会学有不少相通之处,存在密切的关系,二者都接受进化的观点,并且侧重于实证的研究。斯宾塞在其文中就以语言文字的起源和发展为例论证社会进化的观念,因此可以说,翻译《斯宾塞文集》是章太炎接触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开始。另一方面,章氏所译的《论进境之理》大概是最早向国内介绍相关语言学观点的中文文献之一,其中涉及的一些语言学思想在章氏后来的相关研究中都有所体现。例如,斯宾塞认为语言最原始的形式是感叹。章太炎在其《语言缘起说》中讲到命名时指出:“物之得名,大都由于触受……其无所噩异者,不与特名,以发声之语命之……施之兽类者……形性相似,则与之发声之名……施于人类者……种类相似,则与之发声之名……人自称与最亲昵之相称,亦以发声之词言之。”所谓“发声词”就是感叹词,章氏的观点显然受语言起源“感叹说”的影响。又如,斯宾塞论述词类和语法发展的一段话,章氏的译文中涉及一系列语言学术语,如“动静”和“名物”就是动词和名词,其中“动”指主动,“静”指被动,“虚实”分指抽象和具体,将情态(mood)表述为“气之缓急”,时态(tense)为“时之先后”,数量(number)为“物之盈歉”,格(case)为“位次”,“助动静”就是助词(auxiliary verbs),“附动静”盖为副词(adverbs),“代名词”即代词(pronouns)。上述术语基本一一对译。1898年正是《马氏文通》问世的时间,当时,西方语言学的术语并不为人所熟悉,甚至“文法”“语法”的概念都还未通行,章太炎只能借用传统虚字研究中的“辞气”来指称西方的grammar。
斯宾塞所述的语言学观点中对章太炎影响最大的应该是语族(families of words)的思想:“求语言之源,复有一术,凡字同而义异,与义同而字异者,卮言日出,莫可名状,然就其支离,可以深求其理。人初有语言也,固不能遍包众有,其形色志念之相近者,则引申假借,归之一语,俄而聆其言者,眩惑如射覆矣,乃不得不为之分其涂畛,而文字以之孳乳。至于末世,有数字之义,祖祢一字,而莫能究其原者,非覃思小学,孰能道之。”这段文字中的第二、三句被引用在章太炎后来所写的《訄书•订文》中[9]48。他在《自述学术次第》中也说:“转复审念,古字至少,而后代孳乳为九千……字虽转繁,其语必有所根本。盖义相引申者,由其近似之声,转成一语,转造一字,此语言文字自然之则也。”章氏在治小学、读《说文》的过程中已经对这一理念有了感性的认识,而在斯宾塞的阐述中则进一步得到理论的印证。约十年后章太炎开始撰写词源学著作《文始》,其中就用了“语根”(primitive root)的概念,探讨“数字之义,祖祢一字”现象的根源,显然是受这一理念的指引。此外,斯宾塞还详细讨论和列举了文字的起源和发展,该段译文也被章太炎全部引述于《訄书•订文》[9]47-48。
四、结 论
章太炎的翻译基于他深厚的国学功力和对西学的了解。《论进境之理》一文“新理络绎,妙义环生”,除了原作本身的因素之外,在一定程度上还得益于章氏的译笔和文采。这是章太炎初次涉足译林,从事实际翻译,也是他仅有的一次参与翻译英文文献。尽管严复对其提出了较为苛刻的批评,译文中确实也有不妥甚至误、漏的地方,但不带偏见地看,《论进境之理》涉及天文、地质、生物、人类、社会、语言、艺术等不同学科的知识,比较好地传达了斯宾塞的进化思想,译文基本忠实于原作,只是删改了一些冗繁的论述,增添了一些必要的诠释,而表述工具则是中国读书人用了近两千年的通行话语——文言,遣词造句相对平易,但又不失古雅,将文言对于现代思想的涵纳能力做了最大限度的发挥。
值得一提的是,在斯宾塞关于文字发展的论述中,章太炎特别注意到一点:“今英语大数,无虑六万言,言各成义,不相凌杂,盖自书契之作,斯为最广矣”。他认为汉字常用字仅两千,两相比较,差距甚远,因此,他在《訄书·订文》中指出:“今自与异域互市,械器日更,志念之新者日蘖,犹暖暖以二千名与夫六万言者相角,其疐便既相万,及缘傅以译,而其道大穷”[9]49。近代西方新事物、新思想层出不穷、纷繁复杂,文言体系在应对西方文化时已显出力不从心。可以想见,这次实践使他对翻译有了具体的认识和实际的体验,上述这番感慨应该就是他的经验之谈。章太炎关于翻译的论述不多见,但在题为《论语言文字之学》的讲演中曾提到:“译书之事,非通小学者,亦不为功。所以者何?通行文字,所用名词,数不逾万,其字则不过三千而已,外来新理岂能以此包括?求之古书,未尝不有新异之名词,可相影合,然其所涵之义,究有不同。呼鼠寻璞,卒何所取?若非深通小学,何能恣意镕化”[10]10。由此可知,章氏非常重视译者的小学功底,即本国语言文字的修养,认为只有“深通小学”,掌握丰富、准确的词汇,才能恰当地表达西学的各种概念,才有可能达到“恣意镕化”的境界。
除了在翻译史上的价值之外,《论进境之理》一文在近代引进和传播社会学特别是进化观念方面也有一定的贡献。对于章太炎本人来说,这次翻译是他接触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开端,使他在治传统小学、研习《说文》时注意到的语源和孳乳现象得到了理论上的印证,其中的一些思想和观点一直贯穿于他后来的语言文字学研究。
[1] 姜义华.章炳麟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 张超.从“群学”到“社会学”:近代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形成与演变[J].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2012(1):57-72.
[3] 昌言报馆编.昌言报:一—五册(光绪二四年七月—八月)[M].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三十三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
[4] Herbert Spencer. 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s[J]. The Westminster Review, 1857(67):445-465.
[5] 彭春凌.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原作底本问题研究[J].安徽大学学报,2017(3):67-77.
[6] 王天根.严复与章太炎社会学思想的对峙与交流[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49-54.
[7] 韩承桦.斯宾塞到中国——一个翻译史的讨论[J].编译论丛,2010(2):33-60.
[8] 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
[9] 章太炎.訄书 初刻本 重订本[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10] 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于开红)
On Zhang Taiyan’s Translation: Takingas an Example
WANG Cheng
Zhang Taiyan and Zeng Guangquan has co-translated. It is an important essay of Herbert Spencer, which expatiates his theory of evolution. Although the first paragraph gets harsh criticism of Yan Fu and there are indeed some errors in it, the translation in general is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version with necessary deletions of redundancy and additions of explanation, and widely considered as one exuberant with novel ideas and fresh thoughts. This piece of work is a good reflection of Zhang’s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as well as his unique translation style. It is also his first meet with 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which influenced him a lot.
Zhang Taiyan; translation; Herbert Spencer;
H059
A
1009-8135(2017)05-0094-06
2017-06-10
王 诚(1982-),男,浙江上虞人,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讲师,博士,主要研究语言学。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5JJD740012);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清末启蒙运动中章太炎的翻译活动研究”(Y20143147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