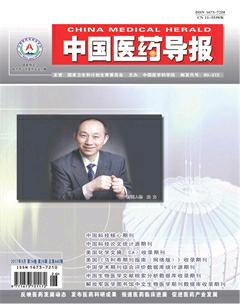从中成药的不良反应报表浅谈合理用药
王欢++朱青霞++原永芳

[摘要] 目的 分析2014年1月~2016年12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北部)(以下简称“我院”)中成药不良反应发生的情况,为临床应用提供合理用药依据。 方法 导出2014年1月~2016年12月我院上报的中成药不良反应报表明细,包括患者年龄、性别、原患疾病、怀疑药品、给药途径、报告人以及不良反应名称等,并将资料进行分析。 结果 2014年1月~2016年12月共上报中成药不良反应1360例。原患疾病以呼吸系统疾病最多,占48.63%。发生不良反应的人群以2~<11岁儿童最多,为34.12%;其次是61~<71岁老人,占14.90%。使用中成药后导致的不良反应累及系统-器官,以皮肤及其附件反应最高,占40.27%,主要以皮疹、瘙痒为主;其次是消化系统,占25.6%,主要以胃不适为主。 结论 应重视中成药不良反应的监测,更要合理、规范地使用中药,以减少中药不良反应的发生。
[关键词] 中成药;不良反应;合理用药
[中图分类号] R28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7)09(b)-0177-04
Analysis of rational drug use based on the adverse reaction report of Chinese patent medicine
WANG Huan ZHU Qingxia YUAN Yongfang
Department of Pharmacy, Shanghai Ninth People's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1999,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occurrence of adverse drug reaction (ADR) induced by Chinese patent medicine in Shanghai Ninth People's Hospital (North),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for short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4 to December 2016,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ational clinical drug use. Methods All reports of ADR induced by Chinese patent medicine in our hospital were export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by using tabulation, including age, gender, original disease, suspect drug, administration route, the reporter and the name of ADR. Results The ADR incidence of respiratory system as original disease was the highest, which make up 48.63% of 1360 reports. The incidence of ADR was the highest in children aged 2 to 11, accounting for 34.12%, followed by 61 to 71 years old, accounting for 14.90%. ADR involved organs with the highest response to skin and accessories, accounting for 40.27%, mainly with rash and pruritus, followed by the digestive system, accounting for 25.6%, mainly with stomach upset. Conclusion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monitoring ADR induced by Chinese patent medicine. Rational and standardized u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of greater importance to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ADR.
[Key words] Chinese patent medicine; Adversedrug reaction; Rational drug use
随着医疗保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我国的中药应用越来约广泛,食品、化妆品中也不乏中药成分[1]。然而随着中药现代化进程的展开,亦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关于中药药物不良反应的报告[2]。为更好地了解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北部)(以下简称“我院”)中药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选取2014年1月~2016年12月我院上报的中药不良反应数据进行整理分析,为我院临床合理应用中药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资料来源于不良反应上报系统网站www.adrs.org.cn。在“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系统”首页“个例药品不良反应报告管理”项中点击“报告表检索”,即可查询所有上报数据。
其中,时间类型为“国家中心接收时间”,时间为2014年1月~2016年12月,报告类型全选(包括严重、一般、新的严重、新的一般);药品类型为“怀疑药品”;剂型为“中药”(说明:本院上报ADR的網站中,中药并不包含中草药,均指中成药)。
2 结果
2.1 中成药不良反应上报情况
我院2014~2016年共上报药品不良反应1360例,其中中成药不良反应255例,占18.75%。255例中成药不良反应中,新、严报表数为132例,占中成药不良反应总数的51.76%。见表1。
2.2 中成药不良反应给药途径情况
2014~2016年中成药不良反应给药途径情况表中,静脉滴注的构成比最高,为49.22%;其次为口服,构成比为46.88%,外用最低,为3.91%。见表2。
2.3 中成药不良反应报告原患疾病情况
中成药不良反应原患疾病以呼吸系统最多,构成比为48.63%;其次是心脑血管系统,构成比为12.94%。见表3。
2.4 中成药不良反应性别与年龄情况
从性别看,每一年的构成比,女性均大于男性。从年龄看,2~<11岁儿童的构成比最高,为34.12%;其次是61~<71岁老年人,构成比为14.90%。见表4。
2.5 中成药不良反应报告累及系统-器官情况
中成药不良反应报告主要累及以皮肤及其附件,为40.27%。见表5。
3 讨论
3.1 中成药不良反应现状
2014年1月~2016年12月,我院共上报药品不良反应1360例。其中,中成药的不良反应上报数为255例,占比18.75%。在255例中成药的不良反应中,新的、严重的例数为132例,新严占比51.76%。
我国原卫生部令81号文第二十条:“新药监测期内的国产药品应当报告该药品的所有不良反应;其他国产药品,报告新的和严重的不良反应。进口药品自首次获准进口之日起5年内,报告该进口药品的所有不良反应;满5年的,报告新的和严重的不良反应。”说明新的、严重的药品不良反应病例,对及时、有效控制药品风险,保障公众用药安全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
而中成药说明书缺项较为严重[3],其中的“不良反应”项,一般较简短,某些中成药(多为口服药)只有“尚不明确”四个字。所以,一旦发生药品不良反应,这份报表类型较大概率是新的,也可以验证这一点。
中成药的新严发生率较高,除了重视其不良反应的监测外,做好中成药上市前的药理毒理分析和药物试验,是减少新的不良反应发生的关键[4]。
3.2 中成药不良反应的患者情况
本研究结果显示,连续3年女性中成药不良反应情况都高于男性。
从年龄构成比看,排第一的是2~<11岁的儿童,其不良反应发生率占比为34.12%,约占总数的1/3。郑新勤[5]认为,儿童肝微粒体酶系代谢和结合能力较成人弱,肝肾功能发育不完全,部分药物消除慢,易造成药物短时间在体内蓄积,增加ADR发生的危险。另外,儿童无指征用药、药物滥用、缺乏儿童专用药和儿童药物临床试验开展难度大等问题,导致儿童的用药风险比成人高2倍[6]。
其次是61~<71岁的老年人,其不良反应发生率占比为14.90%。王悦之等[7]认为,老年人生理功能的退行性改变,对药物的敏感性和耐受性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另外国外有报道,在社区居住的老年人,通常使用2.8~5.0种药物治疗。由于与年龄的变化及药物的相互作用,增加了药品不良事件发生的风险[8]。
本研究结果提示,需关注老人、儿童等特殊人群的用药安全。
3.3 中药不良反应的用药情况
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年度报告2016年度:涉及的药品给药途径分布中,静脉注射给药占59.7%、其他注射给药(如:肌内注射、皮下注射等)占3.4%、口服给药占33.7%、其他给药途径(如:外用、贴剂等)占3.2%。与2015、2014年相比,总体给药途径分布无明显变化。
本研究结果显示,我院2014~2016年中成药不良反应给药途径中,构成比最高的是静脉滴注(49.22%);其次是口服(46.88%);外用占3.91%。给药途径分布与国家不良反应监测年度报告的前后顺序一致,但注射剂与口服药的占比差距较大。
这可能有以下的原因:一是国家的年度监测报告中,静脉注射的品种包括化学药、中药、生物制品,而不是本文单指的中成药。二是可能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陆续公布的警惕中药注射剂的严重不良反应有关:从2006年鱼腥草注射液事件,到2012年药品不良反应信息通报第48期“警惕喜炎平注射液和脉络宁注射液的严重变态反应”、2013年药品不良反应信息通报第52期“警惕红花注射液的严重不良反应”等,中药注射剂的安全性问题越来越引起大家的关注。我院是一家以西医为主的三甲医院,鉴于上述通报,医生相对较少开具这类中药注射剂。
本研究结果显示,2014~2016年中成药不良反应报告原患疾病情况中,呼吸系统疾病占首位,為48.63%。呼吸系统疾病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除去吸烟等人为因素、人口老龄化等自然因素,很多研究表明,空气污染对人体健康存在影响[9]。2013年1月北京、天津、河北的PM2.5日均浓度高达718 μg/m3,该区域人群因PM2.5短期暴露导致超额死亡2725例,其中呼吸系统疾病超额死亡人数846例、循环系统疾病超额死亡人数1878例[10]。
本研究结果显示,导致皮肤及其附件反应的不良反应数高居首位,为40.27%,主要以皮疹、瘙痒为主,与多数文献报道相符[11-12]:皮肤及其附件损害是最主要的系统/器官损害,这与皮肤反应的临床表现易于发现且容易诊断有关。部分中药制剂进入人体后易产生变态反应,导致皮疹、药疹的出现。其次是消化系统,占25.60%,主要是胃肠道反应,涉及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因连续三年我院出现不良反应的群体以10岁以下儿童、60岁以上老年人居多,而儿童脏腑娇嫩、老年人代谢缓慢,故累及消化系统的不良反应也不少。
3.4 中成药不良反应的影响因素
涉及中成药不良反应的因素有很多:年龄、性别、个体差异、药物本身等,文献报道亦很多,为此不再赘述。笔者主要分析可能的人为因素:
3.4.1 中药制剂的使用还不够规范 与亢卫华等[13]的报道有类似情况:在我院,中药注射剂医嘱也多由西医师开具,他们没有经过系统化的中医药理论培训,大部分按照中药的现代药理学的研究来开具药物,完全违背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
为贯彻落实中西医并重的方针,进一步加强我市非中医类别医师系统学习中医药知识和技能工作,2017年4月,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举办西医学习中医在职培训班,具体委托上海中医药大学继续教育实时培训。培训周期为两年半,一年理论学(半脱产形式集中面授结合自学),一年临床跟师学习(每周2~3个半天)。最后完成所有学习计划、考核合格者,经市卫计委审核后,颁发统一格式的结业证书。这是上海市政府推进中药制剂更规范使用的有力举措。
3.4.2 中西药联用方案的增多 现在,越来越多的医生尝试使用中西药联用的方案治疗疾病[14]。田晓亮[15]曾对该院两个月门诊中西药联用情况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中西藥联合用药5727例,其中不合理1227例,占22.30%,主要不合理类型有重复用药、理化禁忌性的联用、可引发药源性疾病的联用、药理作用拮抗性联用。而随着中成药和西药联合疗法在临床治疗中越来约普及,其所致的不良反应也逐渐增多[16-17]。
目前,临床有关中成药的研究较少,因其药性较为复杂,研究难度增加,导致药物动力学、药理学研究不够完善,因此无法为临床提供客观依据,这就加大了中药西药联用合理性分析难度,从而导致临床中西药配伍使用的盲目性[18]。再加上不熟悉中医中药理论的西药师开具中成药,更加大了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中西药联用方案的合理也是国家倡导“合理用药”的重要一环[19-20]。
3.4.3 患者对中成药不良反应的认识不足 在中成药的服用过程中,部分患者出现不适后,常常认识不到可能是药物引起的不良反应。他们不仅不会停用,还会继续定时服用,直到不适症状持续至再次就医时,才会遵医嘱停用。因此,我院每年都会进行关于合理用药、药物不良反应的宣传,让患者了解不仅仅西药有不良反应,中药包括中成药、中药饮片都有不良反应。
综上所述,中成药的不良反应监测和积极上报值得重视;尤其需要重点关注老人及儿童等特殊人群的使用;中成药应该根据患者病情辨证施治;对患者需加大不良反应宣传的力度等,使中成药更规范、更合理地使用,为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 黄萍.中药不良反应的研究和监测[J].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1998,9(1):54-55.
[2] 杨立平.中药不良反应报告分析[J].中国全科医学,2011, 21:2459-2460.
[3] 杨洁江,马鹏辉.92份中成药说明书和61份药品不良反应报告表的调查分析[J].中国医院药学杂志,2008,28(2):148.
[4] 秦庆芳,陆卫英,谭柳英,等.2010-2012年1237例中成药致不良反应报告分析[J].中国医院用药评价与分析,2014,14(3):262-264.
[5] 郑新勤.门诊儿童218例静脉滴注不良反应分析报告[J].临床与实践,2015,19(14):1917-1919.
[6] 张伶俐,李幼平.基于风险与责任,促进中国儿童合理用药的思考[J].中国循证医学杂志,2011,11(9):983-984.
[7] 王悦之,张玉.老年药物性肝损伤的研究进展[J].临床肝胆病杂志,2016,32(4):821-824.
[8] Bakken MS,Ranhoff AH,Engeland A,et al. Inappropriate prescribing for older people admitted to an intermediate-care nursing home unit an hospital wards [J]. Scand J Prim Health Care,2012,30(3):169-175.
[9] World Health Organizatin. Outdoor air pollution a leading environmental cause of cancer deaths [M]. Geneva: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13.
[10] 张衍燊,马国霞,於干,等.2013年1月灰霾污染事件期间京津冀地区PM2.5污染的人体健康损害评估[J].中华医学杂志,2013,93(34):2707-2710.
[11] 支敏倩.145例中成药不良反应报告分析[J].中国药业,2014,23(24):91-92.
[12] 罗茂玉,黄庆水.某院2013年599例药物不良反应报告分析[J].光明中医,2015,30(9):2023-2025.
[13] 亢卫华,平贯芳,崔李平.196例中药制剂不良反应分析与原因探讨[J].中成药,2016,38(8):1878-1880.
[14] 李哲,罗晓,史丽敏,等.中成药与西药联合使用的现状、问题及建议[J].临床药物治疗杂志,2015,13(4):65-69.
[15] 田晓亮.1277例中西药不合理联用分析及对策[J].中国药物滥用防治杂志,2009,15(5):305-307.
[16] 房伟.我院中成药和西药配伍不良反应的报告及原因分析[J].中国卫生标准管理,2015,6(20):117-118.
[17] 赵小刚,王淑香,陶强,等.某县级医院中成药临床合理使用分析探讨[J].河北医学,2016,22(6):1021-1022.
[18] 赵熙婷.我院中成药与西药配伍不良反应报告及原因分析[J].中国处方药,2016,14(11):30-31.
[19] 陈勇,杨燕,陈霞,等.临床合理应用抗肿瘤中成药的评估及干预措施分析[J].河北医学,2017,23(3):495-498.
[20] 沈绍清,李外,任浩洋,等.我院开展"合理用药月"活动对用药监管的成效分析[J].中国医药导报,2016,13(29):123-126.
(收稿日期:2017-05-27 本文编辑:李岳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