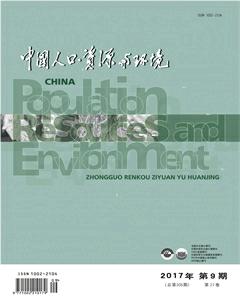中国省际间绿色发展福利测量与评价
钟水映+冯英杰
摘要 在绿色发展理念下,对绿色发展福利进行测量和评价比传统的GDP评价更能体现发展的质量。本文基于生态绩效理论,将绿色发展福利增长速度推导为脱钩指数与GDP增长速度的乘积。首先以人类发展指数作為绿色发展福利的判别标准,根据脱钩指数理论,以数值0和0.1为界线,将2002—2014年中国31个省份的绿色发展福利水平划分为“负福利增长”、“绝对低福利增长”、“相对低福利增长”三类。其次,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及Malmquist指数测度兼顾期望产出(GDP)与非期望产出(生态足迹)的绿色经济增长,并对中国省际绿色经济增长效率进行分解,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为技术效率变动、技术变动、纯技术效率变动和规模效率变动,以探讨影响中国绿色发展“C”模式的关键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大陆31个省份的脱钩指数均小于0.6(两个省份的脱钩指数小于0),处于低福利增长状态,但是整体上省际间脱钩指数与GDP增长速度呈现正相关关系,省际间人类发展指数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公平的教育机会与收入分配差距两个方面。对中国大陆31个省份绿色经济增长速度的分解表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得益于技术效率变动、纯技术效率变动、规模效率变动指数的提高,且每个时期三者的贡献率均在1左右波动。检验期间,北京、上海、广东、天津四个省份作为“创新者”共同推动产出朝着最优生产前沿面外移。最后,为了构筑中国绿色发展“C”模式,认为应该以绿色发展福利水平的提升为导向,在依据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同时,应注重教育公平与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减。同时,应积极发挥创新者省份绿色发展的示范效应,带动非创新者省份共同发展。
关键词 生态足迹;绿色经济增长;绿色发展福利
中图分类号 F205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7)09-0196-09DOI:10.12062/cpre.20170364
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完成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加快,黑色发展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导致资源损耗与环境资源压力持续加大,生态足迹已经大大超过生态承载能力,并且出现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脱钩”的低福利式经济增长现象。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绿色新政和绿色经济迅速兴起,发展模式将由工业文明的“黑色发展”转变为生态文明的“绿色发展”。按照多纳圈框架[1],绿色发展是实现生态文明的新型模式,即基于环境容量和生态承载力的制约,通过资源合理高效利用和经济适度发展,使得社会福利不断提升。绿色发展模式包含两大门槛:一是在自然系统资源供给能力及对污染吸收、降解功能阈值的制约下,经济系统的物质增长规模受其制约,被称为“生态门槛”,二是经济增长是否能够带来社会福利持续提升的“福利门槛”,社会福利的持续增长既来自经济系统的人造资本,又依赖于自然系统的自然资本,由于自然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制衡互补作用,导致经济增长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改进生活质量,超过这个范围,将导致生活质量退化[2]。中国的绿色发展模式,是从多纳圈的内圈到中间圈的“C”模式[3],即在生态门槛内跨越福利门槛,以生态可承载的方式实现社会福利的持续增长。本文基于多纳圈理论框架,以绿色发展福利提升为导向,立足于中国各个省份绿色发展福利的演化情况,利用Tapio的“脱钩”指数研究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失衡情况,并采取DEA方向距离函数和Malmquist指标研究绿色经济中兼顾期望产出(经济增长)提高与非期望产出(生态足迹)减少的影响因子,以探讨中国绿色发展“C”模式的驱动因素。
1 相关研究及进展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自然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福利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证方面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理论研究方面,新古典经济学完全脱离了自然系统,利用市场和价格机制研究预期目标下稀缺性资源的配置机制,并将福利与效用概念等同,认为其取决于人们的需求,可以通过商品和服务的买卖实现[2]。但是,以“效用”揭示人们对市场商品和生产利润偏好的同时,暗含了非市场物品和非市场交易活动对福利没有任何贡献。在认为经济增长没有物理极限的前提下,主张帕累托有效配置的效率标准实质是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只能使自然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福利三者之间越来越难以协调。自1987年可持续发展概念进入学术界以来,环境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迅速兴起。环境经济学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识到福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系统功能,并受外部性的影响,但是通过庇古税、科斯产权界定等赋予污染和自然系统服务市场价值,仍然是从经济增长范式中的效率层面解决环境问题,想当然认为经济增长能提高社会福利,因此其也被称为“弱可持续发展”,即强调自然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福利三者的总和,认为只要经济增长能抵消环境问题和社会福利损失,就是可持续发展。生态经济学,也被称为“强可持续发展”,认为生态系统是封闭的,通过自然资本供给(源)与环境调节支持功能(汇)与经济系统相联系,强调关键自然资本如地球生态服务等的非减化,单纯依赖经济增长无法弥补关键自然资本和社会福利的损失,即使有很大的经济增长,也不是可持续发展[4]。经济系统在有限的不增长的自然系统里持续不断增长,最终将导致“满”的世界,而我们已经处在这样一个满的世界经济当中[5]。社会福利不仅来自人造资本的服务,而且还来自自然资本的服务,忽视福利研究的经济系统研究只是一种将资源转化为废弃物的愚蠢的机器。
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是当前绿色发展研究自然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福利三者关系的重点,按照指标体系内容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绿色经济。该词由皮尔斯在1989年提出并用于强调生态环境的安全性[6]。2002年,牛文元在世界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峰会上用“绿色 GDP”的理论来解释可持续发展,即在GDP核算中考虑环境容量、污染治理和生态恢复等成本,形成能够反映经济增长代价和质量的指标[7]。2008年联合国提出用绿色新政拯救金融危机,然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编制《绿色经济报告》和《迈向绿色经济:通往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各种途径——面向决策者的综合报告》[8],并倡导将绿色经济融入可持续发展战略。绿色经济演化成强调如何将环境挑战化为经济发展机会,因此绿色经济是指投资于自然资本的经济增长,是避免生态退化的经济发展。第二,绿色发展指数,侧重于研究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增长的关系。2010年以来,李晓西等人构建并逐渐完善了“中国绿色发展指数”,公开发布了中国绿色发展指数省际比较的年度报告。该指数包括中国省际绿色发展指数和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指数两套体系,分别由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环境承载潜力和政府政策支持度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60个三级指标组成,2012年增加了“绿色发展体检表”和“城市绿色发展公众满意度调查”的报告[9]。第三,生态绩效。也被称为“生态经济效率”,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减轻生态环境压力。1992年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首次提出生态效率,指出生态绩效是指“通过提供满足人类需要和生活质量的竞争性定价商品与服务,同时使产品生命周期内的生态影响和资源强度降至与地球承载力一致的水平,以实现环境与社会发展目标”[10]。2001年欧洲环境署(EEA)将生态绩效定义为单位经济活动的环境数量。该概念通常被用来分析宏观经济活动,也被用于研究政府、企业和其他组织的微观经济行为[11]。endprint
第四,生态福利绩效,是福利水平与生态资源消耗量的比值,被用来衡量单位资源投入所带来的福利水平的提升,强调了深绿色发展中公平的意义。Daly最早将其表示为服务与吞吐量的比值,服务指人类通过经济系统所获得的来自自然系统的效用,吞吐量指人类从自然系统中获取的低熵的资源和向自然系统排放的高熵的废弃物的综合[12]。诸大建在此基础上,结合人类发展指数(HDI)和生态足迹(EF)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公式进行了拓展[13]。
鉴于此,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拓展:①以生态足迹、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指数为切入点,综合考虑绿色发展理论下自然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关系。②绿色发展福利的提升,是绿色发展的最终目的。以福利提升为导向,发展绿色经济是要在保持人类发展水平不降低的同时重点降低生态足迹。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绿色经济增长效率进行分解,以考察中国绿色发展“C”模式的驱动因素。
2 兼顾生态足迹与经济增长绿色发展福利提升的模型、指标和数据
2.1 绿色发展福利模型
根据Daly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定义[5],可以将生态福利绩效(EP)表示为:
其中,EG表示经济增长,EF表示生态代价,WB表示获取的福利。诸大建在此基础上,结合人类发展指数(HDI)和生态足迹(EF)[14],将生态福利绩效(EP)定义为:
在此基础上可以将绿色发展福利增长速度用公式表示为:
式(3)中,%ΔHDI表示历年人类发展指数的增长速度,%ΔGDP表示历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ΔEF表示历年生态足迹的增长速度。式(4)暗含了生态足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比如4/3×3的经济增长速度与4/1×1的经济增长速度在数值上具有相等性,但是从绿色发展角度来看,显然后者更有利于促进经济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协调发展。根据索洛经济增长模型,考虑生态足迹因素, 可构建一般化的t期索洛绿色经济增长模型:
式(5)中,L、K、R、A、θ分别代表劳动投入、资本利用、土地投入、技术进步因子、效率因子,α、β、γ分别代表劳动、资本与土地投入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且0≤α、β、γ、θ≤1,α+β+γ=1。两边取对数,那(5)式可转化为:
可以看出,绿色发展不仅仅是追求GDP增长速度的提升,同时应注重生态足迹增长速度的下降。本文中要素投入部分考虑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及不同类型的土地要素投入,产出部分考虑经济增长期望产出和生态足迹非期望产出。根据Tapio脱钩指数模型对人类发展指数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福利脱钩指数[11]如下:
根据式(7),可以将绿色发展福利增长速度公式(3)转化为:
因此,通过研究脱钩指数与绿色经济增长的效率分解,可以探讨影响绿色发展福利的因素。
2.2 基于DEA的方向距离函数和ML指标
为了从要素投入生产率角度分析绿色经济增长速度情况,采用基于方向距离函数的ML指数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根据Chung 等对环境技术集的定义[15],假设存在k(k=1,2……K)个生产单位,在t(t=1,2……T)期使用n种投入要素X(X=x1,x2…xN )生产出m种期望产出Y(Y= y1,y2…yM)和i种非期望产出Z(Z= z1,z2…zI)。通过DEA可以将环境技术集定义为:
式(9)中,λtk为第t期第k个投入产出观测值权重。根据Chung等提出的方向函数为:
βn:指方向距离函数值,即为达到有效的产出水平,第n种要素的期望产出的提高和非期望产出同比例缩减的比例,βn值越小,表明生产决策单元越接近生产前沿面,生产效率越高,当生产决策单元位于生产前沿面时,生产完全有效率,这时β1=β2=……βn= 0。
式(10)表明能够在实现期望产出增加的同时,同比例降低非期望产出(可以参考图1),即兼顾绿色经济增长的期望产出(经济增长)与非期望产出(生态足迹)。对于生产决策单元的既定产出观测点A,根据方向距离函数得出的最佳产出极限是C,C点处于生产前沿面上,是有效率的,但是由于生产条件等的限制,目前所能得出的产出极限是B。方向距离函数要求A按照向量g =(βgy,-βgz)增加y,减少z,从而达到B点。由在此基础上,借鉴Chung等的研究[15],同时考虑期望产出(经济增长)与非期望产出(生态足迹)的t期到t+1期的Malmquist指数可以表示为:
式(11)中,MLTECH表示技术进步率,MLEFFCH表示技术效率变化。结合史丹、王俊杰[16]对于生态效率EFE(GDP/EF)的DEA-ML拓展,可以得出:
即EFE=ML×SUB(SUB表示要素投入足迹的替代),因此GDPt/GDPt-1=ML×SU(SU表示要素投入量的替代)。GDP的增长速度和GDPt和GDPt-1之比变化方向一致,ML可以反映期望产出(经济增长)与非期望产出(生态足迹)双重目的之下的生产效率,因此可以利用上式分解绿色发展中GDP增长的关键因素。本文基于DEA 的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L指标,以中国省(市)k(31個)作为生产决策单位构造t(12年)期的生产前沿边界,并且将GDP增长和生态足迹变化量纳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框架中。
2.3 模型指标与数据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问题,本文以中国31个省份(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台湾、香港、澳门没有包括在分析范围之内)。作为生产决策单位采集面板数据,时间跨度为 2002—2014年,所有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人类发展报告》、《中国环境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国家统计局网站系统数据。绿色发展福利模型变量的选择以及数据来源界定如下:
(1)人类发展指数。HDI由预期寿命指数(LEI)、教育指数(EI)和GDP指数构成[17]。endprint
采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预期寿命数据估计2002—2010年的预期寿命指数,采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预期寿命数据估计2011—2014年的预期寿命指数。采用6岁及以上上过学的人口与6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代为估计成人识字指数。采用每年人均GDP与当年平均汇率进行购买力评价估计GDP指数。最后,依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通用的国际HDI阀值对三个分项指数进行差分调整(表1),并根据人类发展指数的地区差异,将其划分为四个区间级别(表2)。
(2)绿色经济增长速度。采用各地区的亿元GDP作为期望产出指标。由于无法获取关于劳动时间与劳动报酬方面的准确数据,采用各地区年末就业人数估计劳动投入,单位为万人。由于无法准确获取各地区资本存量数据,选取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指标进行估计,单位为亿元。土地要素投入采用征用土地面积指标进行估计,单位为万hm2。为了测试以生态足迹为主要内容的非期望产出,依据国家生态足迹账户,生态足迹计算需要考虑6种类型的土地利用,即耕地、林地、草地、建设用地、渔业用地和化石燃料用地,并利用Wackernagel等价因子对各种土地进行权重调整[16],如表3所示。其中,建设用地用建筑业施工土地面积进行衡量,单位为万hm2;渔业用地足迹采用渔业总产值指标进行衡量,单位为亿元;化石燃料用地足迹采用燃料油消费量指标进行衡量,单位为万t。由于生态足迹计算所需数据不完整,难免产生误差,不过本文在进行DEA分析时,将生态足迹作为非期望产出,只需研究各个省份2002—2014年生态足迹的增长程度,这样的转化处理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误差。
3 绿色发展福利测算及评价
3.1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现状
中国在人类发展指数领域是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已于2011年迈入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行列(图2)。中国人类发展指数的提升在预期寿命指数(LEI)、教育指数(EI)、GDP指数各个方面得到了体现,具体表现在:预期寿命由2002年的71.4岁上升至2014年的74.83岁,婴儿死亡率由2002年的29.2‰下降至2014年的8.9‰,成人识字率和毛入学率分别由2002年的88.4%、89.8%上升至2014年的95.1%、94.6%,人均GDP由2002年的9 324元上升至2014年的46 354元。
通过对2002—2014年中国31个省份人类发展指数进行计算发现,省际之间的人类发展指数存在较大差异(图3)。以2014年为例,北京的人类发展指数(0.92)最高,比最低的西藏(0.65)高出41.5%。由于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尚未普及,及义务教育设施和教育质量的省际、城乡差异,“择校”现象影响省际间的毛入学率,同时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机制下的高等教育收费、大学生就业等制度,使得经济发展先进与落后地区间的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也促使了EI指数的差异。根据Branko Milanovic整理的2002—2012年世界166个国家基尼系数数据库ALG,中国的收入差距整体呈扩大趋势,在2008年和2009年达到0.49[17]。这种收入差距还表现在省际、城乡之间,2014年上海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是排名后三位的贵州、甘肃和西藏的4倍左右[17]。虽然自2010年以来,随着一系列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实施,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有所下降,但是2014年基尼系数高达0.47,仍然处于高位。因此,省际间人类发展指数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公平的教育机会与收入分配差距两个方面。
3.2 脱钩指数测算及评价
DI指数通过对人类发展指数增长速度和GDP增长速度进行对比,来描述福利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同步性。根据式7,并测算出我国31个省份人类发展指数增长速度以及GDP增长速度,从而计算出2003—2014全国及31个省份的脱钩指数。
根据计算结果,本文将DI分为三种情况:①当(2个年度及以上)DI≤0,表示绝对脱钩,说明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福利增长出现倒退,即“负福利增长”。②当0≤(5个年度及以上)DI≤0.6表示相对脱钩,说明福利增长速度慢于经济增长速度,即“低福利增长”,并以0.1为界限,将0≤(5个年度及以上)DI≤0.1称为“绝对低福利增长”,将0.1<(5个年度及以上)DI≤0.6称为“相对低福利增长”。除了西藏(2004,0.505)、安徽(2013,0.367)、江苏(2006,0.426)、新疆(2009,0.399)之外,2003年以来我国其余各个省份的脱钩指数都小于0.3,并且一些省份的脱钩指数(山西2014,-0.034;上海2013,-0.003;安徽2005,-0.073、2012,-0.16;海南2005,-0.016;重庆2004,-0.019;四川2005,-0.077;贵州2005,-0.046;云南2005,-0.067;西藏2003,-0.36、2005,-0.052、2012,-0.075、2013,-0.125;宁夏2005,-0.000 5、2006,-0.033)出现了负值。这说明了我国的福利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上是脱钩的,即人类发展指数的增长速度低于GDP的增长速度,甚至会出现绝对脱钩,即人类发展指数在GDP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出现了倒退。
在31個省份中(表4),安徽、西藏和宁夏处于负福利增长水平,安徽出现负福利增长状况是由于其2005年和2012年人类发展指数相比2004年和2011年有所下降,同理,西藏(2003、2005、2012、2013年)和宁夏(2005、2006年)出现类似情况。处于绝对低福利增长的8个省份中,除了湖南省2014年人均GDP排名第17位,其余7个省份2014年人均GDP均排名前11位,由于过快的GDP增长速度,导致福利增长速度相对较小,即脱钩指数较小。其余大部分省份处于相对低福利增长状态,而这些省份的相对低福利增长并不是因为其福利的迅速增长,却是因为GDP增长速度相对降低。由此说明,我国整体上处于“低福利增长”的状态,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福利的相应幅度endprint
增长,居民在预期寿命、教育、生活水平等领域中的福利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GDP的增长。
为了进一步探讨GDP增长速度、HDI增长速度与脱钩指数变化之间的关系,绘制三者2003—2014年度的增长均值折线图(图4),通过图形可以发现:除了河北、黑龙江、海南、四川、云南、西藏、甘肃、宁夏、新疆由于人类发展指数增长速度缓慢,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导致脱钩指数在GDP增长的情况下反而降低,其余省份脱钩指数与GDP增长速度呈现正相关关系,即在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情况下,虽然各种民生问题凸显,但是GDP的大幅度增长依然能促进人类发展指数水平的提升。因此,如何使得绿色经济发展的同时,并相应程度满足人们福利需求是中国绿色发展“C”模式转型所面临的严峻考验。
4 中国各个省份绿色经济增长效率分解
为了寻找自然系统和经济系统中促使绿色发展福利提升的关键因素,此部分计算了考虑非期望产出(生态足迹)的Malmquist指数与不考虑非期望产出Malmquist指数,以对全国及31个省份的2003—2014年间的绿色经济增长进行分解。
在考虑生态足迹的条件下,2003—2014年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表5)。“十五”规划以来,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出台,使得经济发展迅速扩张,从而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十五”规划末期,根据省际劳动投入量的统计结果可以發现,由于老龄化现象的日益严重,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导致劳动投入逐年下降,加上钢铁等高能耗、高排放的重污染行业过度发展,“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使得考虑生态足迹影响的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下降[16],传统的经济增长动力正逐渐减弱。随后,国家在“十一五”期全要素生产率变动TFPCHGDP增长间提出“节能减排”目标,所以,2006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又出现了回升。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投资需求缩减,导致 2007—2009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下滑。中央政府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及时推出了扩内需、保增长等措施以实现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推动了2010年以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回升。而表5中2003—2014年省际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起伏的不稳定状态,2005年、2009年出现低值。因此,实现经济发展动力由依赖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到依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关键。
如表5显示,在不考虑生态足迹非期望产出的情况下,我国的技术效率变动均值为0.96,技术变动效率均值为1.031,纯技术效率变动均值为0.963,规模效率变动均值为0.997,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均值为0.99,而考虑生态足迹非期望产出的情况下,我国的技术效率变动均值为0.955,技术变动效率均值为1.026,纯技术效率变动均值为0.963,规模效率变动均值为0.992,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均值为0.98,即除了PECH指数,在考虑了生态足迹产出之后,EFFCH指数、TECHCH指数、SECH指数均有所下降,但整体接近于1,反映了中国省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保持着良好态势,表明效率状况稳定。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由SECH、PECH、EFFCH和TECHCH构成。通过回归分析可以发现,在不考虑生态足迹产出时,Malmquist指数中各个分指数对GDP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依次为:SECH>PECH >EFFCH >TFPCH >TECHCH,在考虑了生态足迹产出之后,Malmquist指数中各个分指数对GDP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依次为:SECH>EFFCH>PECH>TFPCH >TECHCH,其中技术效率变动与纯技术效率变动的影响程度地位发生改变。可以发现,规模效率变动始终是影响经济增长效率的关键指数,而技术效率变动是衡量绿色发展的关键指数,其影响生态足迹非期望产出,并对经济增长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考虑生态足迹非期望产出情况下,EFFCH仅下降了0.485%)。而技术变动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均小于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说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得益于技术效率变动、纯技术效率变动、规模效率变动指数的提高。
根据以上分析,省际间技术效率变动、纯技术效率变动、规模效率变动指数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源泉,且在每个时期均在1左右波动。为了分析每个时期是哪些省份作为“创新者”推动产出朝着最优生产前沿面外移,根据Fare等和 Kumar的判断标准[18-19]:
两个约束条件分别表明,最优生产前沿面沿着SECH、EFFCH、PECH方向向量向外移动,用t+1期的投入及第t期的技术不可能生产出第t+1期的产出,创新者省份必须在最优生产前沿面上[20]。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则该省份是推动最优生产前沿面的外移的创新者。根据测算结果,整理可得各时期创新者地区,如表6所示。2003—2014间每年至少有3个省份共同推动最优生产前沿面的外移,创新者地区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天津等省份。其中,北京(12期)、上海(11期)、广东(11期)作为主导创新省份推动了生产前沿面的向外扩张,与其在经济发展中的领先地位相吻合。从区域来看,各时期的创新者地区东部区域表现尤为突出,中部和西部所占省份比例有限。因此,中部和西部区域作为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相对落后地区,应进一步加强与东部区域的技术合作与交流,缩短与创新省份的差距。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Daly与诸大建对于生态福利绩效定义的基础上,拓展了绿色发展福利的评价公式,将其划分为脱钩指数与GDP增长速度两部分。并将生态足迹所对应的不同类型的土地作为投入要素,将生态足迹作为非期望产出,以分解绿色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通过研究发现:
(1)绿色经济的发展是缓解绿色发展过程中低福利发展现状的关键。中国各个省份的人类发展指数增长速度和GDP增长速度在长期内基本上是脱钩的,福利增长的速度远远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处于不同程度的“低福利增长”状态,因此福利的提升是绿色发展的关键。本文通过对省际脱钩指数的实证研究发现,福利和经济发展整体上呈现正相关关系,因此绿色经济发展是提升绿色发展福利的关键因素,同时在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注重现行经济增长模式、资源配置方式等是否满足了人们对于生活质量中环境、空气等自然福利的需求,是否满足了人们对于教育公平与收入差距缩小的社会福利的需求。endprint
(2)绿色发展要注重教育、收入差距等的公平配置。绿色发展中,无论是自然系统、经济系统还是社会系统,每个人有发展的机会与自由,而且这种自由不应该被剥夺[21]。因此,在注重经济发展效益、提升经济增长效率的基础上,更应当注重资源及生产要素的合理分配,在测算省际人类发展指数的过程中发现,教育公平及收入分配合理是影响绿色发展福利的关键因素。以教育为例,在教育资源初始分配时应体现公平,即无论是否贫困、社会地位如何,每个人都享有对于知识获知的权利;在再分配的过程中,应通过经济制度、社会安排等进行约束和指引,防止教育资源仅仅聚敛于经济发展先进地区,促使其实现公平。
(3)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绿色经济发展的新动力。通过探讨生产要素投入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发现传统的依赖生产要素投入促进经济增长已经不适应绿色发展,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绿色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资源的充分自由流动是实现省际间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前提,规模效率、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是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不仅依赖于市场机制对于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且得益于技术的创新驱动。中部和西部区域作为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相对落后地区,应进一步加强与东部区域的技术合作与交流,缩短与创新省份的差距。
(4)自然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要相互协调,形成复合可持续发展系统,同时应积极发挥创新者省份绿色发展的示范效应,带动非创新者省份的共同发展,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绿色发展的转型。本文以生态足迹、经济增长、绿色发展福利为三大系统的切入点,分别通过脱钩指数与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分别,探讨了三大系统的协调关系。自然资源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基础,经济增长是实现绿色发展的手段,而社会福利是实现绿色发展的目的。北京、上海、广东、天津等作为创新者省份,在推动最优生产前沿面的外移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但是仅仅依靠创新者省份,难以实现中国绿色发展模式转型,应发挥创新者省份的示范效应,带动各个省份的绿色发展转型。因此,中国的绿色发展“C”模式,是关于自然系统、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协调发展的模式,也是创新者省份带动非创新者省份,实现深绿色发展的模式。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RAWORTH K. A safe and just space for humanity [R/OL]. Oxfam International, 2012. https://www.oxfam.org/sites/www.oxfam.org/files/dpasafeandjustspaceforhumanity130212en.pdf.
[2]诸大建.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如何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J].学术月刊,2013,45(10):79-89.[ZHU Dajian.Beyond growth:what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conomics and neoclassical economics[J].Academic monthly, 2013,45(10):79-89.]
[3]诸大建.从“里约+20”看绿色经济新理念和新趋势[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22(9):1-7. [ZHU Dajian. New concept and trend of green economy emerging from ‘Rio +20[J].China popul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12,22(9):1-7.]
[4]赫爾曼·戴利.生态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DALY H E.Ecological economics: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M].Beijing: China Renin University Press,2014.]
[5]DALY H E.Economics in a full world[J].Scientific american,2005,293(3): 100-107.
[6]曹东,赵学涛,杨威杉.中国绿色经济发展和机制政策创新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22(5):48-54. [CAO Dong, ZHAO Xuetao, YANG Weish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and policy innovation of Chinas green economy[J]. China popul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12,22(5):48-54.]
[7]牛文元.中国GDP质量指数[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1,26(5):516-525.[NIU Wenyuan. The quality index of Chinas 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 [J].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2011,26(5):516-525.]
[8]诸大建.绿色经济新理念及推进中国绿色经济的思考[N].文汇报,2015-03-13(T13).[ZHU Dajian.New concept of green economy and consideration of green economy studies in China [N].Wen Hui Daily,2015-03-13(T13).]
[9]关成华,李晓西,潘建成.面向“十三五”:中国绿色发展测评[J].经济研究参考,2016(1):4-20.[GUAN Chenghua,LI Xiaoxi,PAN Jiancheng. Oriented 13th FiveYear Plan: the assessment of China green development [J].Review of economic research,2016(1):4-20.]endprint
[10]WBCSD.Ecoefficient leadership for improved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R].Geneva: WBCSD,1996:3-16.
[11]杨爱婷.基于可持续发展和福利增长的经济绩效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3:73-74.[YANG Aiting.A study on 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welfare growth [D]. Wuha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2013:73-74.]
[12]HERMAN E D.The world dynamics of economic growth: the economics of the steady state[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4,64(2):15-23.
[13]诸大建.生态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和管理学[J].中国科学院院刊,2008,23(6):520-531.[ZHU Dajian. Ecological economics:economins and managemen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J].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2008,23 (6):520-531.]
[14]诸大建.生态福利绩效与深化可持续发展的研究[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5(5):106-115. [ZHU Dajian.Ecological wellbeing performance and further research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Tongji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4,25(5):106-115.]
[15]CHUNG Y H, FARE R, GROSSKOPF S. Productivity and undesirable outputs: a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 approach[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1997,51(3):229 -240.
[16]史丹,王俊杰.基于生態足迹的中国生态压力与生态效率测度与评价[J].中国工业经济,2016(5):5-21.[SHI Dan,WANG Junjie.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of Chinas ecological pressure and ecological efficiency based on ecological footprint[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2016(5):5-21.]
[17]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16[R]. 2016.[UNDP.Chinas human development in 2016[R]. 2016.]
[18]FARE R, GROSSKOPF S, PASURKA C A. Environmental production functions and environmental directional[J]. Energy,2007,32(7):1055-1066.
[19]KUMAR S.Environmentally sensitive productivity growth:a global analysis using MalmquistLuenberger Index[J]. Ecological economics,2006,56(4):280-293.
[20]王维国,范丹. 节能减排约束下的中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演变趋势与增长动力[J].经济管理, 2012(11): 142-151.[WANG Weiguo,FAN Dan.Evolution trend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regional of China under energysaving and emissionabating and dynamic analysis of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J]. Economic management journal,2012 (11):142-151.]
[21]SEN A. Development as freedom[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