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味道
电影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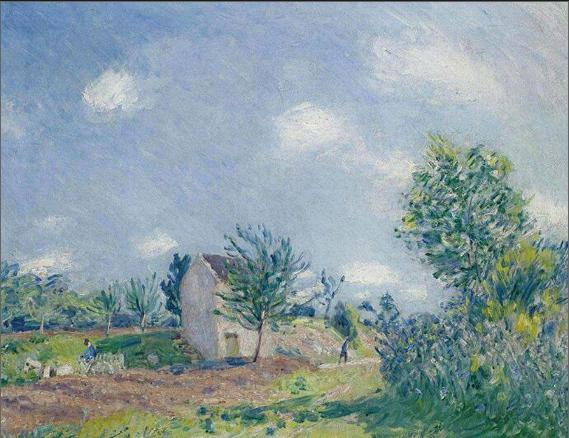
我的儿时记忆是从八十年代初开始的。那个年代虽然物质匮乏,但我经常忆起的美食总是那个年代母亲给我做过的。
那时,元宵节过完,春节就算是过完了,亲戚就不会再来走动了。刚过完春节,家里会有或多或少的猪肉留存下来,母亲会用锅把这些肉熬化成猪大油。那时植物油农村人吃不起,这些猪大油就是家里几个月的食用油了。
母亲把肉切成小块,在沸腾的锅里不断翻炒。时而用漏勺把榨干油的肉干捞出,然后她把新的切成小块的肉放入锅里。我看着母亲刚刚捞出的被榨干油的肉干垂涎欲滴,忍不住伸手去抓几块肉干放到嘴里。那酥脆、香喷喷的感觉,让我忍不住又要去抓,却总会被母亲严肃地喝止,我很不解。
等母亲把所有猪肉炸完,拿来一个小碗,抓几把肉干放在碗里,放上酱油搅拌均匀:“小馋鬼吃吧,如果不放酱油没有咸味会吃伤的。”
母亲欣慰地看着我狼吞虎咽,满脸笑意。酥脆、香喷喷的肉干对于我来说是春节后的第一道美食。吃过香喷喷的肉干后,蔬菜成熟还至少要等到夏天,我又回到天天吃窝头饼子和咸菜的日子。
不记得在春节后的哪一天,母亲突然端出一个小碗放在饭桌上。仔细一看,小碗里整整齐齐地摆着已经扒过皮的咸蒜。看着晶莹剔透中挂着些许红色的蒜瓣,我食欲大开,小盘里的蒜瓣很快被我“赶尽杀绝”,那淡淡的蒜香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每当看着母亲在秋天腌制咸蒜的时候,我便充满了对来年的憧憬。
春天很快来了,树发芽了,我最爱吃的榆钱长大了。
母亲带着我来到村口的榆树林子里,挑选榆钱最大、最均匀的树枝,用一端绑了镰刀的竹竿把树枝割下来。我边捡树枝边捋下榆钱往嘴里塞,慢慢嚼碎,丝丝香甜。那副不用掩饰的贪婪模样,把母亲逗得哈哈大笑。
等割够一定数量,母亲和我每人拖一捆带回家里,然后把榆钱从树枝上捋下来,装到簸箕里。母亲把榆钱洗干净,放到已经放有面粉的盆里,搅拌均匀后放进锅里蒸。等蒸熟掀开锅,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扑面而来,于是我便甩开腮帮子大吃一番。
盛夏到了,美味的金蝉来报到了。
我每天放学后,回家放下书包,拿上镊子、罐头瓶子,和小伙伴们去村口的小树林捉金蝉。金蝉白天是不出来的,到了傍晚才从土里往外钻,爬到附近的树上去蜕壳,羽化成知了。我们小心翼翼地、聚精会神地扫视树下的每一个小洞。发现小洞里的土在慢慢蠕动,我们用手指伸进洞里一挑,就会看到金蝉在洞里的脑袋了。然后,我们用镊子轻轻地夹住金蝉,轻轻地把金蝉拖出洞,往罐头瓶子里一放,一只金蝉到手了。
吃过晚饭,我就拿上手电筒在树林里搜寻每一棵树。每天能找到少则十几只,多则三五十只金蝉。带着金蝉回到家后,母亲把金蝉放到咸水里腌制起来。
等积攒到几百只,吃饭时母亲就突然端出一盘金灿灿、香喷喷的金蝉。不舍得一口就把一只金蝉吃掉,我总是一根腿、一根腿地吃,慢慢品味。在那個吃不饱饭的年代,在我眼里没有比金蝉好吃的美食了。
秋天快过去了,地瓜熟了。
那时候农村生活窘迫,除了所谓的人民公仆,没有人舍得去买地瓜吃。母亲带着我去翻地瓜,地瓜的主人已经收获完毕,我们再把土重新翻一遍地,看看地下有没有漏下的地瓜。经过一天的劳作,我们一般会翻到三五斤地瓜。
回到家,母亲会挑选一块比较顺溜的地瓜洗净让我生吃,那甘甜、那脆声的感觉让人难忘。母亲把地瓜洗干净,用刀从中间一分为二,贴到锅壁上慢慢蒸熟。看着灶膛里的火焰映红了她的脸颊,我觉得母亲是世界上最美的人。
地瓜熟了,看着锅壁上黄澄澄的地瓜,我猴急得抓耳挠腮,却不敢上前,因为太热了。母亲用铲子把地瓜从锅壁上铲下来,轻轻地放到簸箕里。吃着用语言难以形容的美味,脸上、脖子上全是地瓜渣,我都顾不上了。后来我才发现,母亲做的蒸地瓜类似后来流行的烤地瓜的味道。
冬天很快到了,庄稼地里只有茫茫白雪。
村边的小河沟结了一层薄薄的冰,鱼也不那么活跃了。当时村里就有小学,下课以后我带上捞鱼的小抄网,来到河沟边把冰打碎。用小抄网捞一个傍晚,我总能捞个七八两小鱼。
母亲把小鱼洗干净,把鱼内脏去除,在鱼身上裹上面粉,在锅里炸熟。然后,她赶紧重新刷锅,再用葱、姜、蒜炝锅。水烧开后,母亲把炸好的小鱼倒进去,再放入些许面粉。不久,鱼汤就新鲜出锅了。我喝着鲜香的小鱼汤,感觉真香。
几十年过去了,我现在时常想起儿时的美食味道。成年后,我在外面吃过很多比母亲做的精致得多的饭菜,却再也没有那种垂涎欲滴的感觉。
可能这就是母亲的味道吧!
(北京诚百东方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