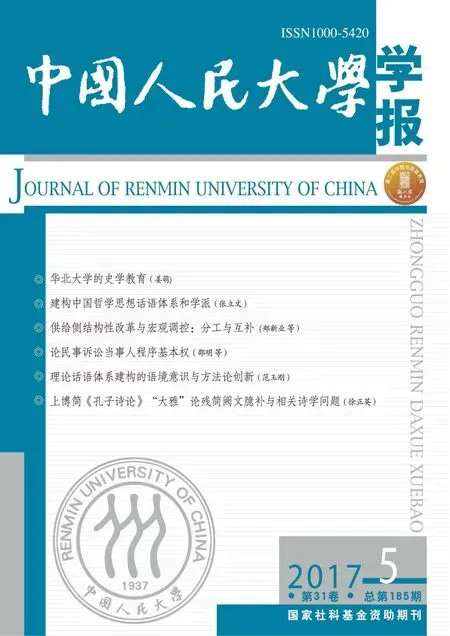国际传播理论及其发展的主要阶段与反思
刘 琛
国际传播理论及其发展的主要阶段与反思
刘 琛
从公元前5世纪的波斯帝国到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国际传播在研究和处理国际问题中的重要意义一再得到历史验证。国际传播理论发端于西方,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很多理论观点需要进行重新梳理和评价。与大众传播等其他传播形式相比较,国际传播的突出特点是涉及国家核心利益,带有鲜明的战略目的,追求改变效果,是国家间、地区间综合实力的新的展示方式。国际传播理论的发展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既有国际传播理论成果的突出贡献是立足现实需要,提炼了国际传播的若干重要的一般规律且形成了体系;存在的局限性主要是受到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过于强调竞争,对融通与互鉴重视不够。面对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国际传播理论需要具备更加宽广的视野,才能有所突破和创新。
国际传播;概念;理论;阶段;反思
在全球化态势下,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建构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世界各国,尤其是迫切期望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需要更为全面而深入地认识国际传播的历史进程和变化规律,辨析现有国际传播格局的形成原因,从而尽可能准确地把握未来发展的着力点。
本文以历史为视角,对国际传播理论中主要流派的核心思想、实践效果和产生的影响进行批判性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对未来发展做进一步思考。
一、国际传播的概念
根据历史记载,国际传播活动最早可追溯至横跨欧、亚、非的波斯帝国[1](P11)大流士一世(Darius I,the Great,公元前558—公元前486年)时代。国际传播在出现之初就已深刻地影响了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样貌。 对此,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指出,古代波斯、罗马和希腊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帝国,是因为它们的传播观念重在“走出去”,不断地尝试尽可能扩大信息到达范围的方法,因此是“倚重空间”(space-dependence)的传播。[2]就传播观念而言,中国等文明古国更强调把信息“传下去”,青睐“倚重时间”(time-dependence)的传播。传播理念的不同造成了社会样貌的差异。进一步说,一个国家如果选择“倚重空间”的传播更可能成为帝国,而选择“倚重时间”传播的国家即使文明达到很高程度,也难以拓展出恢宏的版图。
此后近千年中,世界范围内涌现出若干经典的国际传播实践,也凸显了国际传播理念的差异。西方的国际传播更多倾向于征服,东方的国际传播则注重建立联系。与古罗马帝国公元前47年裘利斯·恺撒(Julius Caesar )征服小亚细亚的吉拉城宣告“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Veni!Vidi!Vici!)相比较而言,古代丝绸之路(前202—公元9年)、玄奘西行(628—645年)、鉴真东渡(751年)、郑和七下西洋(1405、1407、1409、1413、1417、1421、1431年)等典型事例却体现了中国与西方不同的国际传播观。
1837年,电报的发明开启了现代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不再只是跨越国界和民族的信息传递。相反地,它可以将一国的内政问题扩展为国际范围的讨论,甚至能够引发外力的干涉和介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年)可称为第一个经典案例。当时,借助电报技术,英国的《泰晤士报》(The Times)和路透社(Reuters)、法国的哈瓦斯社(Havas)以及德国的沃尔夫社(Wolff)都参与了南北战争的报道。其中,《泰晤士报》积极协助英国的亲南方派发表了大量反对北方的文章,结果在1864年险些导致汉密尔顿·林德赛(Hamilton Lindsay)提出的应介入美国内战的动议被英国议会通过。相比较而言,这一时期国际传播仍处于摸索和经验积累阶段,尚未出现专门性研究。
20世纪,广播、电影、电视和互联网等电子媒介的相继问世和不断发展逐渐提升、深化了国际传播在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影响。因此,国际传播的内外因素变得更为复杂。相应地,理论研究也随之深入。从时间上看,传播学在“20世纪的40到60年代,才形成了自己的基础学术流派并初具规模”[3](P13)。与之相比较,国际传播的理论体系建构稍显滞后。
20世纪70年代,德里克·菲舍(Heiz-Dietrich Fischer)和约翰·梅里尔(John C.Merrill)对国际传播进行了定义,认为国际传播不是简单的信息跨国流动,而是政府间的信息交换,因此少数几个大国控制了传播秩序。[4]这个解释初步明确了国际传播的三个根本特征:第一,国际传播是一种跨国界的传播。第二,国际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发生在政府之间,而不像大众传播以民众、市场为主体。第三,国际传播是处理国家间关系和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直至20世纪90年代,国际传播的定义仍处于讨论之中。学者们基本上都认同菲舍和梅里尔对国际传播核心特点的总结,但是逐渐将国际传播的概念拓展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军事等更多层面。*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对国际传播进行概念定义的学者及其论著主要包括:Robert S.Fortner.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History, Conflict and Control of the Global Metropolis.Belmont, Californi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1993;Cees J.Hamelink.The Politics of World Communication: A Human Rights Perspective.London: Sage,1994;Hamid Mowlana.Global Information and World Communication: New Fronti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nd Edition).London: Sage,1997。美国传播学者罗伯特·福特纳(Robert S.Fortner)概括出国际传播的六大特征——目的性、频道、传输技术、内容形式、政治本质和文化影响。[5](P6-11)这为界定国际传播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框架。
综合国际政治、国际经济、社会学和传播学的相关论述*相关代表性学者主要有:国际政治学领域的Daniel Lerner,Bernard Cohen,Joseph Nye等;发展经济学领域的Rafael La Porta,Daron Acemoglu, Simon Johnston, James Robinson等;社会学领域的Anthony Giddens等。,本文尝试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传播进行定义。与大众传播等其他传播形式相比较,国际传播的突出特点是关乎一国的发展格局,涉及国家核心利益。它的战略目的是夯实民意基础,建构有利于己的国内外舆论环境。在当前时代条件下,国际传播已经成为一个国家乃至地区影响力展示的最主要的途径。总体上,国际传播的内涵和外延主要可以从四个维度加以把握:
第一,国际传播是鲜明的目的性传播。从一开始,国际传播就服务于国家间的竞争和之后的更为尖锐的意识形态斗争。逐渐地,国际传播的影响覆盖了国际关系中几乎所有主要方面,并且越来越有能力改变这些领域的议题和运行方式。因此,国际传播已经成为关乎一国发展空间的重要因素。
第二,国际传播是超越信息发布和交换的传播。国际传播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远远超越了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大众传播。它的内容遴选标准集中于能否尽可能地影响对象国,乃至国际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判断标准和行为范式。可以说,与常规的大众传播相比,国际传播的内容具有更为鲜明的社会学指征。
第三,国际传播是途径多元的传播。其中,政府是最主要的渠道。从目前的态势看,智库、企业、媒体、国际组织等民间或半官方力量在国际传播中日趋活跃。
第四,国际传播是国家间、地区间综合实力的展示与竞争。国际传播能够产生强烈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这一点凸显了国际传播与大众传播之间的差异。在政治影响方面,福特纳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国际传播都带有政治色彩。可以公开带有政治性质,也可以隐含政治色彩。”[6](P8-9)在经济影响方面,国家形象(Nation Branding)概念的提出者、英国政策顾问西蒙·安赫特(Simon Anhalt)融合经济学原产国形象(Country of Origin)*1965年,美国学者罗伯特·思科勒(Robert D.Schooler)提出了原产国理论,指出消费者在选择和评价品牌时,会将品牌原产地作为购买依据。20世纪80年代,针对荷兰、意大利和美国等国消费者的实证分析,进一步证实原产国形象确实会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图。等理论,深入分析了国际传播可能产生的巨大经济影响,认为“国家的形象(image)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对其他国家的看法,那里的人,那里的产品,那里的服务。这虽然看似不公平,可却是事实”[7](P1)。在文化影响方面,新帝国主义研究(Neo-imperialism)等流派已经做出了较为充分的讨论。大量的经验性研究都证明国际传播必然会产生深刻的文化影响。
综合这四个主要维度,可以得出结论,国际传播的效果是分层级的。首先,它是信息的交流与传递。因此,传递效果是基本的效果。其次,国际传播既是对传播者自身形象的展示,也是对他者形象的某种塑造,因此解读效果是国际传播要实现的第二级效果。国际传播希望达到的最终效果是改变对方,因此改变效果是最高层级的。
综上,国际传播的概念具有构成性和发展性等突出特征。发展性特征意味着它具有较强的张力,而且适应性和应用性突出。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互联网等新媒体的迅速崛起,国际传播的传递效果、解读效果和改变效果不断增强,并日益成为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必须审慎对待的议题。以国际传播对美国总统与媒体关系的经验性研究为例,“卡特总统由于认识到传媒不是提供信息,而是筛选信息,因此在很多外交决策中显得犹豫不决。相反,里根总统和老布什总统却十分善于利用国际传播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国际认同铺路”*上述研究结论总结自Edwin Diamond.Sign Off: The Last Day of Television.Cambridge,Massachusetts: MIT Press,1983;Robert J.Spitzer(ed.).Media and Public Policy. Westport:Praeger, 1993等。。更近期的代表性案例是1999年,科索沃战争爆发。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料被披露,显示美国介入此次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遏制刚诞生的欧元,防止其对美元构成威胁。然而,通过系统的国际传播部署,美国支持战争的行为却以捍卫和平与保护人权的形象出现,从而有效地引导了国内外舆论。
由此可见,国际传播的特性决定了其双刃剑的特征:一方面,它是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它也是制造和左右舆论的有力推手。当前,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进一步增强了国际传播发展的不确定性。面对国际传播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共时性存在的特点,如何改善现有国际传播秩序、建设一个更为公正和科学的国际传播环境,使之与全球化发展水平和发展中国家的诉求相适应已经成为突出议题。这些工作如果完成得好,实现国际传播的健康、良性发展是可以预见的。
我们以国际传播改变效果的实现为主线,依据代表性理论和历史性事件等标准,将国际传播理论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冷战时期、全球化时代。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传播理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人们注意到在战争、冲突或处于紧张局势等特殊情况下,国际传播是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在这个阶段,美国国际政治学者、记者李普曼(Walt Lippmann)及其著名的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研究是代表性理论成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李普曼负责宣传工作。这个经历让他发现传播的作用极为重要。他将媒体比喻为“民主的《圣经》”,谁写“这本书”,谁有权裁决善恶。李普曼对国际传播一般规律的总结与当时的政治学理论观点显著不同。根据政治学理论,是制度或机构而不是政治活动中的人[8](P172)决定结果,李普曼却指出“在现代国家,决策是通过互动和交流完成的。也就是说是舆论在发挥作用,而不是国会”[9](P172)。
1917年十月革命,宣告维也纳体系(1815—1914年)结束。欧洲作为国际政治的中心,实力逐渐下降。英国、法国和德国等欧洲主要国家由于战争的拖累,对于继续主导国际事务已经力不从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影响力大幅提升。以此为背景,国际格局进入凡尔赛—华盛顿体系(1918—1939年)。随着力量对比的变化,美国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这极大地激发了对国际传播的需求。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李普曼开始关注“本质极为复杂、意义极为重要并且容易引发强烈情绪与争议的事件”[10]是如何被国际传播解读和建构的。他与《纽约世界》(TheNewYorkWorld)副主编查尔斯·默茨(Charles Merz)合作开展研究,以《泰晤士报》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报道为对象,从超过1 000篇的样本中,测试舆论形成与变化的规律。在遴选记者时,李普曼的标准是其报道是否与其他媒体的报道有所矛盾。在他看来,这类记者的稿子不能被视为新闻,而是一种宣传。1920年,两人合作的论文《新闻的测试》发表。同年,他与默茨合著的《自由与新闻》出版。通过研究,李普曼认为传媒比较容易操控舆论,尤其是给公众提供虚假信息的时候。从立意、方法论和研究结论等方面看,李普曼对西方媒体视域下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报道研究是最早也最全面的国际新闻研究,是最早分析媒体如何影响舆论的学术成果,具有标志性意义。然而,它却长期未能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李普曼的这项研究应为最早的批判性话语分析,但语言学界却一直将诺曼·费尔克劳(Norman Fairclough)的《语言和力量》(Language and Power.Essex: Pearson ESL,1989)作为批判性话语分析的开端。参见Gunther R.Kress.Linguistic Processes in Sociocultural Practic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Gunther R.Kress.Reading Images.Victoria: Deakin University Press, 1990; Ruth Wodak, Rudolf de Cillia, Martin Reisigl, and Karin Liebhart.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0;Veronika Koller, and Ruth Wodak.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Public Sphere.New York: De Gruyter Mouton, 2010。国内对李普曼的研究通常将《新闻的测试》之后的《自由和新闻》作为他最早的新闻研究成果。参见叶青青:《李普曼新闻思想反民主立场的由来》,载《新闻爱好者》,2012(24)。
李普曼对于国际传播如何在特殊情况下影响舆论的研究贯穿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1939—1945年)。他的研究假设是:“如果公众没有获取信息的渠道,那么所有的人最终都会变得无能、盲目、迂腐、丧失忠诚、恐慌并最终酿成舆论灾难。”他的结论是“没有新闻和消息,明智的公共舆论难以形成”[11](P1)。李普曼的《公众舆论》(1922年)和《幻影公众》(1925年)相继出版。这些研究的主线是公众舆论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它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变化?最终,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理论,认为电报、广播等现代传播技术的普及不仅使国际传播成为可能,而且正在塑造出一种虚拟的现实。这些信息是由媒体构筑的“幻象”,并不是外面世界的原貌。李普曼在《外面的世界与我们脑海中的图画》[12](P3-32)中,指出由于人们直接获取外部世界信息的渠道是有限的,因此需要“媒介”,然后根据所获得的各种“意象”(images)逐渐形成对自己不能亲身观察的外部世界的“先入之见”(preconceptions),甚至是偏见,直到最后被固化成刻板印象,进而形成舆论。因此,媒介更有能力塑造国家意愿或社会目标。
历史地看,李普曼的视角与当时的国际政治、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有着显著差异。他分析的是在矛盾冲突等特殊状态下,传播是否能够履行“为培育公共舆论而提供信息的最高职责”[13](P2)。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普曼的研究代表了一个独立派别,他的研究不仅填补了其他学科的空白,而且率先发现了在国际传播条件已经具备的情况下,一国的事件乃至整体形象是可以被设定的。以李普曼论著为代表的这些研究成果使新世界格局中的列强认识到了国际传播的战略意义。
与美国取得的国际传播理论成果相比,英国、法国、德国等主要欧洲国家在这一阶段没有出现系统研究。值得一提的是此时刚成立的苏维埃政权尝试建立了有别于资本主义体制的传播制度,即韦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等所总结的共产主义媒介理论。[14]但是,该理论流派主要观点的形成与确立是在冷战时期。在亚洲,绝大多数国家仍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没有国际传播话语权。所谓的国际传播媒介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商人以及学者等经营的外文报刊,也包括少量的使用当地语言的刊物。因此,也没有出现任何与此有关的经验性研究。然而,日本作为当时亚洲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了国际传播实践。例如,在华盛顿会议(1921—1922年)期间,日本代表团注意到美国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的观点得到广泛响应,这是“休斯每天会见言论界人士,说明美国目的的结果……休斯每天会见100人左右的各国记者代表,详细说明美国的态度,在这一点上,休斯的战术是不战而胜。我们饱尝了没有舆论支持的痛苦。在这次会议中,我们感受最深的就是没有舆论的支持,在国际性交涉中不能达到任何目的”[15](P109)。
总之,以李普曼的研究为节点,国际传播理论发展进入初始阶段,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中心主义对西方国际传播理论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
三、冷战时期的国际传播理论
冷战时期(1947—1991年)是国际传播理论迅速发展的历史阶段,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流派。所谓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成为强有力的助推器。
根据肖恩·帕里·吉尔斯(Shawn Parry-Giles)的观点[16](P448-467),以美国为代表,冷战时期的国际传播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纯真期(naivete period)”(1947—1950年)。在这个阶段,美国人乐观地认为美国模式会自然而然地超越和战胜共产主义。作为此观念的产物,美国之音(VOA)开播。按照1948年的《史密斯—蒙特法案》,美国之音是“国际宣传媒介,禁止向美国居民播出”[17](P185)。
第二个阶段是“歇斯底里期(hysteria period)”(1950—1953年)。在这个时期,美国的国际传播策略发生了改变,开始极力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塑造成破坏世界自由与和平的危险力量。
第三个阶段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即“心理战略期(psychological strategy period)”。代表性的事例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成立了整合国际传播资源的协调行动委员会(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 OCB)以及杜鲁门总统提出的“第四点计划”。这些策略重点面向第三世界国家,通过“以黄油代替枪炮”的方法实现美国文化的输出。
历史经验表明,心理战略期的国际传播从之前直白、恶意的对抗转向了强调策略性、协调性和战略性。在此背景下,国际传播开始融入国家的整体外交构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极大地推进了相关理论体系的建设。
在对流派进行界定时,我国学者从大众传播的角度进行过分类。在国际上,英国传播学者图苏(Daya Kishan Thussu)等曾经提炼过主要的国际传播理论,但没有就这些理论的立意或者在实践中的作用进行批判性分析。在此,本文以图苏等概括的国际传播重要理论为基础,对这一历史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学理思想做学术流派划分,将其归纳为发展传播学研究、新帝国主义研究和批评性研究三大类。这些流派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是系统分析法、国际比较研究、实证分析、经验性分析、案例分析、历史分析、心理分析和行为分析等。可见,正是在冷战时期,国际传播的方法论体系得以建立和丰富。
发展传播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教授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1950年至1951年,他在土耳其、黎巴嫩、埃及、叙利亚、约旦和伊朗等中东国家进行了规模较大的实证研究。勒纳在《论传统社会的消失:中东的现代化》一书中,提出了现代化理论。勒纳认为借助国际传播,西方的政治与经济模式会传递给第三世界,进而带来文化改变,最终量变引发质变,与西方道路不同的所谓传统社会就会消失。在他看来,“现代化向东方和西方提出了同样的挑战。随着西方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精神的输入,与此相背离的伊斯兰文化毫无招架之力”[18](P120)。
现代化理论极大地肯定了国际传播在文化变革方面的特殊作用,为杜鲁门的“替代枪炮”的外交新战略给出了落实路径,即通过提升传媒参与度增强政治参与度。对此,勒纳明确了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国际传播主要任务,即解决好两个关系:一是接触传媒的程度与预期程度之间的关系;二是大众传媒的国际传播能力与政治意识之间的关系。
在勒纳之后,韦尔伯·施拉姆是发展传播学派的又一个代表性学者。20世纪60年代,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资助下完成了有关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发展与国际传播的关系研究。与勒纳的研究思路相似,施拉姆继续关注国际传播对个体行为变化的影响。例如,如何改变第三世界人们对成功和幸福等话题的认知以及促使态度改变的要素等。1964年,施拉姆的《大众传媒与国家发展》出版,推动发展传播学进入更富实践性和操作性的阶段。
总体上,勒纳与施拉姆都坚定地认为,大力发展国际传播能够有效地且渐进式地影响第三世界的人们,通过产生移情,最终实现社会转型。
新帝国主义学派的形态较为丰富,共性特征是都非常关注包括国际传播在内的各种力量是如何替代了坚船利炮式的传统殖民方式。以此为线索,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社会学文化帝国主义研究(Cultural Imperialism)、知沟理论研究(Information Gap Theory)以及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研究(Development Economics)等。以国际传播概念的构成元素为依据,加尔通(Johan Galtung)的结构帝国主义理论(Structural Imperialism)和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等人提出的霸权主义理论(Hegemony Theory)等都比较具有代表性。
相比较而言,更能够延续和拓展20世纪60年代发展传播学理论的是结构帝国主义研究。该理论的基本立足点是提出了两类国家模型。加尔通试图分析“为什么一个北海的小小雾岛(英国)能够统治四分之一的世界”[19]。他的答案是帝国主义并非一成不变,相反地,它可以被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等不同历史阶段,每个时期都有其鲜明的特征。就新帝国主义而言,国际传播的结构化导致了“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分野,进而形成了最有利于中心国家的国际传播秩序。如果在国际传播中保持“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分化,那么“中心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而“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不和谐的,“边缘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和谐的。因此,这种国际传播格局对于“中心国家”来说是最有利的。
关于国际传播的批评性研究深受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核心议题是国际传播对公民意识的影响。其中,以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赫伯特·马尔库斯(Herbert Marcuse)等为代表的文化工业研究,剖析了意图占领全球市场的传媒资本巨头如何将文化演变成流水线一般的商品,进而诱使民众对“使用与满足”(uses and gratifications)的理解产生深刻变化,最终使西方文化成为全球流行文化,压缩和抢占边缘国家的文化空间。
德国社会学家尤金·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的公共领域研究分析了20世纪资本主义如何瓜分全球国际传播的份额,认为由于受到资本的操控,18世纪发端于英国、法国等国,可供公民平等参与并就社会重大问题进行讨论的公共领域不仅没有扩大,反而萎缩了。这些理论洞察了当时国际传播秩序存在的若干重大问题。
然而从实践来看,这些批判没有产生太大作用。举例来说,20世纪70、80年代提出的“国际信息新秩序”和著名的《一个世界,多种声音:麦克布莱德报告》提出了打破“中心”和“边缘”的倡议,却因发达国家的冷落而不了了之。同样,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最初出自他的德文著作(1962年),1989年被译成英文出版。*这部著作的德文版是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Untersuchungenzueiner Kategori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Berlin: Suhrkamp Verlag,1962;英文版是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into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Cambridge,Massachusetts:MIT Press, 1989。直到此时,他的研究才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由此也反证了他所担忧的国际传播的“再封建割据化”(refeudalization)会导致世界文明发展空间缩小已渐成事实。
综上所述,冷战时期尖锐的意识形态斗争激发了对创新外交战略的迫切需求,也由此带动了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的突破性发展。在这一时期,权力理论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心议题。在讨论如何显示权力、维持权力和拓展权力等突出问题时,国际传播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路径。也是因为这个历史性原因,国际传播理论与权力竞争产生了密切联系,甚至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增强权力的基本模式之一。因此,这一时期国际传播理论研究的许多领军人物都与政府关系紧密。例如:勒纳所在的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是由美国政府于1952年建立的。美国传播学奠基人施拉姆是联邦调查局(FBI)的信息员,并自“1942年起,为美国军方的战略服务局*战略服务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的一个指导游击战、实施潜入作战的机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和中央情报局(CIA)担任顾问”[20](P186-187)。此外,国际传播的一些主要研究机构,如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等是“美国国会建立的教育和研究机构”[21](P186)。
四、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传播理论
1991年,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时期结束,全球化逐渐成为时代大势。在这一趋势下,国际传播理论被推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越来越呈现出鲜明的跨界融合的特征。
从一般的国际传播认识论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批评研究是一个标志性的理论成果。该学派在理论基础上与批评性研究基本一致,都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从研究对象看,传播政治经济学批评研究更多地聚焦于媒介融合、跨国传媒集团以及国际组织的作用。这一学派关注了由美国掌控的全球电子经济对国际传播造成的巨大影响,同时也认为苏联的解体、中东欧国家的剧变以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等都意味着马克思主义遭遇了挑战。
此外,在过去的近20年时间里,国际传播理论越来越深入地渗透或融入其他学科的理论。其中,软实力(Soft Power)研究、形象(Image)研究和全球传播(Cosmopolitan Communications)理论是三个突出表现。
“软实力”概念由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1990年提出。面对美国发展遭遇的困惑,奈尝试论证“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不仅是以传统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为指标,还有第三个维度——软实力”[22](PXII)。在他看来,“软实力”是指“如果一个国家在世界政治中可能会得到预期成果,是因为其他国家欣赏它的价值观、效仿它的案例,希望能够达到它的开放与繁荣程度——并(因此而)愿意追随它”[23](P5)。可见,当一个国家具备足够的软实力时,这种软力量会通过夯实民意基础转化成合理合法的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等多领域的硬实力。就软实力的主要维度,奈概括为三个要素,即“一个国家的文化(吸引其他国家的地方)、它的政治价值观(处理国内外事务时所履行的原则)以及它的外交政策(成为其他国家所认可的依法且有道义的权威)”[24](P96)。软实力理论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认识和实践空间。很快地,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深入研究适合自己的软实力建构形式。在这一过程中,国际传播的重要性充分显现,并被赋予了若干具有迫切性的研究命题。
然而,从“软实力”角度开展的国际传播研究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基本立场的差异。部分观点以西方零和式有限原则哲学观为理论基础,认为软实力的国际传播是竞争性关系。此类研究的共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研究思路上,更加注重各国、各地区在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上的差异,甚至有意夸大和渲染这些不同。第二,在研究立场上,经常会与发展传播学派一致,将西方模式甚至美国模式上升至普世的高度,而对不同于此的文化、政治、外交思想进行批判。第三,在解决方案上,有时会比较激进,对他者的独立性和合理性不能给予足够尊重,对互鉴共赢等理念表示质疑。
2007年,西蒙·安赫特在《竞争性身份:国家、城市和地区的新形象管理》一书中提出了国家形象六角模型(见图1)[25](P28)。安赫特以自己的理论模型为依据,主持发布了国际上第一个国家形象指数报告。

图1 国家形象六角模型图
安赫特率先提出的形象理论对国际传播研究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随之出现了一些处于发展之中的理论模式①代表性学者及其论著主要包括:Wally Olins.“Branding the Nation:The Historical Context”.Journal of Brand Management,2002(4):241-248;Simon Anholt.Brand New Justice: The Upside of Global Branding.Amsterdam: Butterworth-Heinemann,2003;Simon Anholt.Competitive Identity:The New Brand Management for Nations,Citiesand Regions.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7;Keith Dinnie.Nation Branding: Concepts, Issues, Practice.Oxford: Butterworth-Heinemann, 2008等。,例如研究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作为一种变量,对一国的发展空间有何种影响等。
然而,与软实力研究相似的是包括安赫特本人在内的大多数西方学者都认为形象的建设与展示也是一种竞争性关系。安赫特指出:“当前,世界已变成单一市场。快速推进的全球化意味着每个国家、每个城市和每个地区必须通过竞争才能赢得国际媒体、其他政府和其他国家民众的关注和尊重。”[26](P1)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这种局限性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形象评估中普遍存在。以形象排名为例,分析《联合国全球幸福指数报告》(WorldHappinessReport)、《全球国家经济活跃度指数》(GlobalRetailDevelopmentIndex)、《英国〈经济学人〉全球城市排名报告》(ASummaryoftheLiveabilityRankingandOverview)、《美国科尔尼公司全球城市指数报告》(A.T.KearneyGlobalRanking)以及《世界经合组织全球经济城市竞争力报告》(OECDTerritorialReviewsCompetitiveCitiesintheGlobalEconomy)等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与形象相关的排名报告,可见联动、互通和合作发展类的指标并未包含在内。相比较而言,西方主导的关于形象的排名,其指标体系和工具更加符合西方国家的文化理念和特点。在应用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时,这些模型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局限性。
2009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碧芭·诺里斯(Pippa Norris)和密歇根大学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根据他们所主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的经验性数据,提出了全球传播理论模型,认为全球传播由生产、分配、内容和受众影响等四个主要部分构成。具体说来,是国际格局、技术和经济变革改变了传统的传播模式,带来了全球传播的兴起。在全球传播中,美国等西方国家由于占据着全球文化贸易的主导地位,因此全球传播最可能产生三种改变结果,即其他文化与西方文化融合、其他文化与西方文化形成对抗、其他文化消融。[27]
全球化浪潮成为国际传播理论研究的巨大推动力,同时也促使国际传播理论研究与其他学科相互融合,并要求其分析视角更为宽广,理念更为科学,立场更为客观,尽量克服冷战思维。然而,辩证地看,国际传播理论长期存在的问题并未解决。因此,当前国际传播理论研究的迫切任务是如何更好地适应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形态,以建设性的态度引导国际传播,为处理好日益复杂的国家间和地区间的关系做出积极贡献。
在这一时期,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渐具备了参与国际传播的条件,也迫切期待通过加强交流,消除疑虑和误解,探索“零和”以外的关系模式。分析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发布的各类文件,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成为高度关切的问题。
针对当前时代面临的结构性和阶段性等问题,中国提出了有别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文明互鉴”等思想。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体现了这些新思路。从历史与国际比较的视角看,这些理论与实践探索有望弥补以往国际传播理论研究的不足,为新形势下国际传播更好地服务于维护和平、促进理解和走向共建提供了启示。
五、总结
从历史的角度看,始于西方的国际传播理论研究深受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这与西方的哲学思想关联密切。从17世纪时维科(Giambattista Vico)、孟德斯鸠(Baron Montesquieu)和赫尔德(Johann Herder)等人提出文化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到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提出民主思想,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始终存在。例如,维科认为:“每个社会都拥有自身的思想范式与生活理念,而且基本上不能与其他社会融合。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和理念无法适用于其他社会。一个社会所界定的美德、文学、艺术和英雄主义在另一个社会往往得不到承认。荷马(Homer)和阿基里斯(Achilles)只属于希腊,绝不会在别的社会中再现。”[28](P123)孟德斯鸠提出精英创造文化的论点,认为文化是由天才所创造的。一个社会需要有这样的人才能洞察文化要义,而精英们也具备领导力,带动社会接受并遵守所设定的法的秩序。后来的赫尔德在很多方面超越了维科和孟德斯鸠,承认是“人民”创造了文化,但他的“文化花园”理论却仍然是从西方社会的文化环境出发,对人类社会的文化规律进行整体判断。由此,他认为文化花园中的各色花朵必然是截然不同且独立发展的,因此不具备文化意义上的交流与学习的可能性。[29](P55)
在全球化时代,这类理念仍未完全改变。借助全球化浪潮,最近三四十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进步显著,国际格局的多元化趋势逐渐显现,这引发了部分老牌强国的忧虑,出现了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必有一战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等理论观点。以此为背景,发达国家对国际传播内容的主导和资源分配的控制越来越全面,试图进一步改变其他国家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观念。令人担忧的是部分发达国家为了促使西方文化理念和实践成为全球文化的核心,而强势依据所谓的文化价值观,分类制定对外政策。例如,2011年埃及爆发骚乱,国内局势动荡。美国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在表态时指出:“在做出外交决定时,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原则和价值观,要考虑美国的利益,要考虑我们所接触的人是否跟美国一条心。”[30]
总之,在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下,全球化已经进入更高发展阶段,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困境。面对问题,不同国家提出的方案是有差异的。中国的立场是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面对新的条件、环境和任务,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需要突破和创新,在新的历史节点下担负起时代的使命。
[1] Daya Kishan Thussu.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ContinuityandChange.London: Arnold, 2000.
[2] Harold Innis.EmpireandCommunicatio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3] 胡正荣:《传播学总论》,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
[4] Heiz-Dietrich Fischer, and John C.Merrill (eds.).Internationaland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2ndEdition).New York: Hastings House Publishers, 1976.
[5][6] 罗伯特·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7][25][26] Simon Anholt.CompetitiveIdentity:TheNewBrandManagementforNations,CitiesandRegions.New York: Macmillan, 2007.
[8] Ronald Steel.WalterLippmannandtheAmericanCentury.New York: Basic Books, 1980.
[9][12] Walter Lippmann.PublicOpinion.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Howe, 1922.
[10] Hanno Hardt.“Reading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the Journalism of Lippmann and Merz”.MassCommunicationandSociety, 2002, 5(1):25-39.
[11][13] Walter Lippmann.LibertyandtheNews.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Howe, 1920.
[14] Wilbur Schramm,Fred S.Siebert, and Theodore Peterson.FourTheoriesofthePress.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6.
[15] 山田文雄:《日本大众传媒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6] Shawn Parry-Giles.“Rhetorical Experimentation and the Cold War, 1947—1953: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ternationalist Approach to Propaganda”.QuarterlyJournalofSpeech, 1994(80):448-467.
[17][20][21] Umaru Bah.“Cold War Propaganda and U.S.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 Historical Critique”.JournalofThirdWorldStudies, 2008(Spring).
[18] Daniel Lerner.ThePassingofTraditionalSociety:ModernizingintheMiddleEast.Glencoe III:Free Press,1958.
[19] Johan Galtung.“A Structural Theory of Imperialism”.JournalofPeaceResearch, 1971,8(2).
[22][23] Joseph S.Nye, Jr..SoftPower:TheMeanstoSuccessinWorldPolitics.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24] Joseph S.Nye Jr..“Public Diplomacy and Soft Power”.TheAnnalsoftheAmericanAcademyofPoliticalandSocialScience, 2008(616):94-109.
[27] Pippa Norris,and Ronald Inglehart.CosmopolitanCommunications:CulturalDiversityinaGlobalizedWorld.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28] Isaiah Berlin.AgainsttheCurrent:EssaysintheHistoryofIdeas.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29] Bhikhu Parekh.RethinkingMulticulturalism:CulturalDiversityandPoliticalTheory(2ndEdition).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30] 察哈尔学会:《美国智库盘点:2011年最应关注的11大变局》,http://blog.ifeng.com/article/16355684.
html。
Abstract: From the Persian Empire in the fifth Century BC to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study and addressing of international problems has been repeatedly verified by history.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riginated in the West. However, in the new era, many theoretical viewpoints need to be re-evaluated. Compared with other forms of communication such as mass media, the most notabl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re that it concerns core national interests, has distinct strategic objective and pursues change of effect, which is a new mode of displaying comprehensive strength among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 Based on the above-mentioned core featur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or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main stages. The remarkable contribution of the established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is the refining of a number of important general law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actual needs, and further forming the theory into a system. The limitations are that they are mainly influenced by Western centralism, with too much emphasis on competition, and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accommodation and mutual learning. Facing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era and the practice requests,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theory calls for broader vision, and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have breakthrough and innovation.
Keyword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oncept; theory; stage; reflections
(责任编辑林间)
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Theories:MainDevelopmentStagesandReflections
LIU Chen
(School of English & International Studie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刘琛: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基地加拿大研究中心主任(北京 10008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海外智库中的中国文化形象研究” (16ZD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