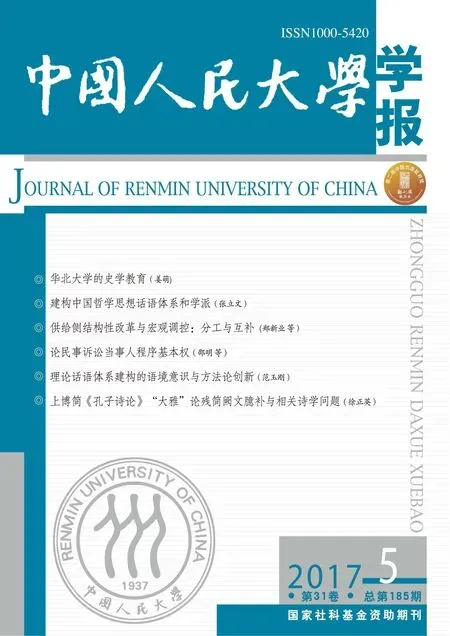德译《中国童话》与《西游记》学术探究
王 燕
德译《中国童话》与《西游记》学术探究
王 燕
1923年,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一文中提出孙悟空形象来自印度神猴哈奴曼,这是20世纪孙悟空形象研究的一大突破,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学术观点。根据1914年出版的德译《中国童话》,最早将孙悟空与哈奴曼联系在一起的并非胡适,而是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同时,胡适认为《西游记》是一部“童话小说”,这一观点与卫礼贤的相关论述也有着惊人的相似。因此,卫礼贤的学术观点在《西游记》研究史上具有开启先河的重要意义。只是由于胡、卫二人“个人才性”的不同,以及当时中西方“文化转向”的差异,致使胡适在发表相关观点时,没有彰显卫礼贤的学术贡献。
胡适;卫礼贤;孙悟空;哈奴曼;童话小说
孙悟空是《西游记》塑造的最成功的人物形象,关于其艺术原型,历来众说纷纭,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两种观点:一是鲁迅提出的“无支祁”说,一是胡适提出的“哈奴曼”说。两相对比,学界不但对后者更为倚重,而且还把“孙悟空形象哈努曼说”的最早提出者毫不犹豫地放在了胡适的名下。实际上,根据目前发现的最新资料,德国传教士、汉学家卫礼贤(或尉礼贤,Richard Wilhelm)早在1914年,就在其译作《中国童话》(ChinesischeVolksmärchen)中提出了这一观点。只是由于该作最初以德语发表,后被转译为英文,至今未被回译为中文,故长期以来在中国学界湮没不闻。
本文结合第一手外文文献,对相关问题做了系统梳理,提出卫礼贤才是“孙悟空形象哈努曼说”的创始者。此外,胡适认为《西游记》就其主题而言,乃是一部“童话小说”,这一观点与卫礼贤在《中国童话》中的相关论述,也有着惊人的相似。本文结合胡、卫二人“个人才性”的不同,以及当时中西方“文化转向”的差异,分析了上述观点产生的文化语境,以及胡适没有彰显卫礼贤学术发现的根本原因。这不仅更正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学术观点,而且对于反思胡适的小说研究,以及拓展《西游记》的研究格局,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孙悟空形象哈努曼说”的提出
1923年,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一文中提出“孙悟空形象哈努曼说”。他说:“我总疑心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一件从印度进口的。”又说:“因此,我依着钢和泰博士(Baror A.von Sta⊇l Holstein)的指引,在印度最古的纪事诗《拉麻传》(Rāmāyana)里寻得一个哈奴曼(Hanumān),大概可以算是齐天大圣的背影了。”[1](P251)此说一出,虽遭到鲁迅的驳斥,却得到不少大家的回应。1930年,陈寅恪在《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一文中,肯定了《西游记》人物形象与印度佛教故事密切相关的观点。1939年,郑振铎在《西游记的演化》一文中说:“孙悟空的本身似便是印度猴中之强的哈奴曼(Hanuman)的化身。哈奴曼见于印度大史诗拉马耶那(Ramayana)里,而印度剧叙到拉马的故事的,也多及哈奴曼。”[2](P268)
1978年,季羡林在《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一文中,有意对胡适、鲁迅的观点进行了调和,他说:“我的意见是,不能否认孙悟空与《罗摩衍那》的那罗与哈奴曼等猴子的关系。那样做是徒劳的。但同时也不能否认中国作者在孙悟空身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把印度神猴与中国的无支祁结合了起来,再加以幻想润饰,塑造成了孙悟空这样一个勇敢大胆、敢于斗争、生动活泼的、为广大人民所喜爱的艺术形象。”[3](P177)
在几位学术泰斗的论说下,“孙悟空形象哈奴曼说”广为人知,小说研究及文学史上的相关引用比比皆是;中外学者在肯定这一论断的同时,也把这一重要学术发现放在了胡适的名下。比如,美国汉学家夏志清在其《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说:“面对(《西游记》)这样一部伟大的创作,学者们一直寻思:究竟哪些民间传说和民间文学中的人物做了孙悟空的原型呢?既然他同唐朝或更早的古典传说中几个猴子形象有相似之处,胡适提出《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努曼是最可能的原型。尽管胡适实际上没有试图考察这个印度史诗对中国民间传说和民间文学的影响,但直到现在,对他的这一假设还没有人提出异议。”[4](P132)这一学术观点之影响深远,由此可见一斑。
实际上,最早将孙悟空与哈奴曼联系在一起的不是胡适,而是德国传教士汉学家卫礼贤。1914年,卫礼贤把100篇中国民间故事译成德文,题名《中国童话》,作为“世界童话”(Die Märchen der Weltliteratur)系列丛书中的“东方童话”(Märchen des Orients),在德国耶拿(Jena)出版。从序言落款可知,翻译工作早在“1913年4月”就完成了。“孙悟空形象哈奴曼说”就出现在这部《中国童话》中,这一著作的诞生,比胡适修订于1923年的《西游记考证》要提前十年之久。只是由于这一重要学术发现最初以德语发表,故在中国学界长期无人知晓。
《中国童话》的最后一篇《心猿孙悟空》(DerAffeSunWuKung)译自《西游记》,是对《西游记》前七回内容的简介,这或许是德语世界最早的《西游记》译文。卫礼贤从石猴出生、入山学道,写到他大闹天宫,最后被如来佛祖压在五行山下,完整交代了孙悟空的不凡来历及神通广大。《西游记》自第八回开始才逐步讲述唐僧取经故事,前七回内容相对独立,主要围绕孙悟空展开,卫礼贤将自己译介的这部分内容恰切地题作《心猿孙悟空》。此处之所以将德语的“Affe”回译为“心猿”,而非“猿猴”或“猴子”,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西游记》文中明确表示:“猿猴道体配人心,心即猿猴意思深。”[5](P46)陈洪先生解释说:“孙悟空被称为‘心猿’,是取的‘心猿意马’的含义,而作者通过孙悟空的经历,以‘猿’喻‘心’,是要表现‘心灵’修养的主张的。”[6](P147)又说:“《西游记》大量使用‘心猿’是其行文的突出特征。”[7](P152)故此,将德译文题目回译为“心猿”,显然比“猿猴”或“猴子”更能体现《西游记》前七回的要旨。二是卫礼贤在这篇译文的文末“注释”(Anmerkungen)中说:Der Affe ist das Symbol des Herzens,意谓:“猿猴象征着人心。”由此可见,他对“Affe”的象征意味同样心领神会。所以,将“Affe”回译为“心猿”更能传达卫礼贤的本意,以及他对《西游记》宗教文化的深切领悟。
“孙悟空形象哈奴曼说”同样出现在卫礼贤为《心猿孙悟空》所做的文末“注释”中。他说:“这个故事,很像《天路历程》(Pilgrim’sProgress),是个寓言。尽管具有讽喻性特点,但其中却蕴含了大量童话理念。孙悟空这个形象让人想起哈努曼,即罗摩(Ramas)的同伴。”[8](P404)卫礼贤之所以知晓哈奴曼,与19世纪《罗摩衍那》的欧译密切相关。[9](P124-125)《罗摩衍那》在欧洲很早就出现了多种译本。1829—1838年间,施莱格尔(A.W.von Schlegel)翻译了拉丁文节译本;1843—1858年间,戈雷西奥(Gaspare Gorresio)翻译了意大利语节译本;1853年,帕里索(Valentin Parisot)翻译了法语节译本;1854—1858年,福谢(Hippolyte Fauche)翻译了九卷本法语全译本《罗摩衍那,蚁垤的梵文诗》(Ramayana,poèmesanscritdeValmiki);1870—1874年,格里菲斯(Ralph Thomas Hotchkin Griffith)在印度的贝拿勒斯(Benares)和英国的伦敦同时出版了五卷本英译本;1892—1894年,达特(Manmatha Nath Dutt)在印度的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了七卷本英译本;1897年,德译本姗姗来迟,古典文献学者门拉德(Joseph Menrad)翻译的《罗摩衍那 罗摩王的抒情歌曲》(Rmyana,dasliedvomkönigRma)在慕尼黑(München)出版。以上译本,均有助于卫礼贤从多种渠道了解《罗摩衍那》所塑造的神猴形象——哈奴曼。
二、卫礼贤与《中国童话》的学术影响
将孙悟空与哈奴曼联系在一起,是20世纪讨论孙悟空形象的一大突破,但这一重要学术发现却出现于卫礼贤德译《中国童话》的文末“注释”中,或许很难引起学界重视,由此,如何评价其学术影响也成了一大难题。我们不妨从两方面做些尝试:一是考察卫礼贤的学术影响;二是探索德译《中国童话》的传播情况。由此间接地分析这一学术发现有可能对胡适产生的启发。
卫礼贤是德国新教同善会的一名传教士,1899年来到中国青岛传教。虽曰传教士,却不以传教为主,反以治学为重。在华二十多年间,他竟不曾发展一名教徒,甚至还颇为自得地对著名心理学家荣格说:“我没给一个中国人洗礼,这真是太叫我欣慰了。”[10](P352)
其实,更令卫礼贤欣慰的是他的中国典籍翻译。1910年,德语文学界最著名的出版社——迪德里希斯出版社(Diederichs)决定出版卫礼贤翻译的系列中国典籍,这套丛书被称为《中国的宗教和哲学》,原定10卷本,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没能出全,但陆续出版的《论语》、《老子》、《列子》、《庄子》、《孟子》、《易经》等,已使卫礼贤从一名默默无闻的传教士,一跃成为德国著名汉学家,各种荣誉接踵而至。1911年耶拿大学授予他神学荣誉博士头衔;1921年被任命为德国驻北京公使馆头等参赞;1922年被北京大学德语系聘请为教授;同年,法兰克福大学授予他哲学荣誉博士头衔;1924年离开北京,到法兰克福大学出任汉学教授,并在该校建立了“中国学社”(China-Institut),为中德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一系列典籍翻译和文化活动,使卫礼贤从容跻身于20世纪欧洲最著名的汉学家之列。德国学者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说:“在著述与普及有关中国的知识方面,当时再没有其他汉学家能像卫礼贤那样产生广泛而特殊的传播效应。不仅他对《易经》的翻译和解说至今仍在全世界传播并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可,而且他对那些最重要哲学著作的翻译和解说也通过不断再版至今还对专业人士和大众的中国观具有决定性影响。”[11](P115)
值得注意的是,卫礼贤翻译的《中国童话》也是由迪德里希斯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它显然有别于《中国的宗教和哲学》系列丛书,但这本中国民间故事在当时创造的真正神话,却是它的出版业绩大大超越了卫礼贤翻译的任何一部中国经典。德国学者威廉·许勒(Wilhelm Schueler)在《卫礼贤的科学著作》一文中说:“卫礼贤在迪德里希斯出版社出版的翻译作品,几乎是当时欧洲青年人乃至成年人汲取(东方)营养的唯一源泉。”[12](P14)在这些译作中,《中国童话》的阅读最为广泛,“正如其29000册的印数所表明的,卫礼贤的作品中也许再没有别的书能在读者中创造如此可观的记录,这一记录肯定还将继续扩大”[13](P19)。
事实上,这部作品不但在德语世界广为传播,而且很快被美国人马顿斯(Frederick Herman Martens)转译为英文,题名《中国民间故事集》(TheChineseFairyBook),作为世界“民间故事系列”(fairy series)丛书的一部分,1921年由施托克斯出版社(Frederick A.Stokes Company)在纽约出版,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卫礼贤德译《中国童话》的影响。马顿斯在“序言”中说:《中国民间故事集》“几乎向美国读者呈现了目前所能提供的最全面、最多样的东方童话。”他对中国童话充满夸赞:“中国古代的民间故事和传说,与《一千零一夜》(ThousandandOneNights)一样,如同东方的黄金美玉和多彩丝缎那般绚丽夺目、光芒四射,是充满奇思妙想和超自然力的东方财富。而且它们还以自身独特的个性凸显了一种异国情调。”[14](P5)这部英译中国民间故事集问世后不断再版,至今畅销,其影响力毫不逊色于卫礼贤的德译《中国童话》。
对比两个译本,有四点值得注意:
第一,德译《中国童话》100篇,英译《中国民间故事集》转译了其中的74篇,虽然数量上有所删减,但最后一篇《心猿孙悟空》却被完整转译为英文。卫礼贤的德译文不但简洁生动地翻译了《西游记》前七回涉及的主要故事情节,而且还很好地保留了某些人物语言与动作细节。如:“那大圣收了如意棒,抖擞神威,将身一纵,站在佛祖手心里,却道声:‘我出去也!’你看他一路云光,无影无形去了。”[15](P48)卫礼贤译为:“Sun Wu Kung sprang mit einem Satz darauf.Dann sagte er: ‘Los!’ Dann machte er einen Purzelbaum nach dem andern, daß es nur so ging wie ein Wirbelwind。”马顿斯严格遵照德译本,用英文转译为:“Buddha then stretched out his right hand.It resembled a small lotus-leaf.Sun Wu Kung leaped up into it with one bound.Then he said:‘Go!’ And with that he turned one somersault after another, so that he flew along like a whirlwind”。两种翻译都再现了孙悟空的活泼灵动,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第二,卫礼贤在《中国童话》“序言”和文末“注释”中将中国童话分为七类:kindemärchen,Göttersagen,Von Heiligen und Zauberern,Natur-und Tiergeister,Gespenstergeschichten,Historische Sagen,Kunstmärchen,马顿斯在英译本“目录”中全部保留了以上七类,并逐一转译为:Nursery Fairy Tales,Legends of the Gods,Tales of Saints and Magicians,Nature And Animal Tales,Ghost Stories,Historic Fairy Tales,Literary fairy tales,回译为中文,即:儿童故事、神仙传奇、圣贤与术士故事、自然与动物故事、鬼怪故事、历史故事、文学故事。《心猿孙悟空》在两个译本中都被划归“文学故事”一类。
第三,两个译本“序言”的内容不同,篇幅短小,但对《心猿孙悟空》却都表达了格外的赏爱。卫礼贤说:“最后一篇长篇剧作,蕴含了许多不同的主题。”马顿斯则说:“半宗教性戏剧(the quasi-religious dramas)《心猿孙悟空》和《哪吒》(Notcha)达到了奇幻之巅。”这种表述自然有利于吸引读者阅读这篇以虚构见长的“文学故事”。
第四,英译《心猿孙悟空》忠实地转译了德译本“注释”,并把德译本放在书末附录中的“注释”调至每篇的文末,从而方便了读者查阅“注释”。“孙悟空形象哈奴曼说”在两个译本的“注释”中均位列第一,在德译本中表述为:“Der Affe selbst erinnert an Hanumant, den Begleiter Ramas”,在英译本中表述为:“The ape himself suggests Hannumant, the companion of Rama”。故此,通过英译本,读者也不难获悉这一学术发现。
现在,让我们回到胡适。目前学界所见《西游记考证》一文是1923年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西游记》的序言。文章开头,胡适道:“民国十年十二月中,我在百忙中做了一篇《西游记》序,当时搜集材料的时间甚少,故对于考证的方面很不能满足自己的期望。这一年之中,承许多朋友的帮助,添了一些材料;病中多闲暇,遂整理成一篇考证,先在《读书杂志》第六期上发表。当时又为篇幅所限,不能不删节去一部分。这回《西游记》再版付印,我又把前做的《西游记序》和《考证》合并起来,成为这一篇。”[16](P235)由此可见,被学界反复引用的《西游记考证》实际起笔于“民国十年十二月”,即1921年底,恰在这年德译《中国童话》被转译为英文,从而为精通英文的胡适看到这一观点提供了可能。只是到目前为止,尚无直接证据证明胡适确实看过这个英译本。
三、“个人才性”与“文化转向”
除了“孙悟空形象哈奴曼说”这一观点,胡适的《西游记考证》与卫礼贤的《中国童话》最大的相通之处,在于对《西游记》主题的认识。《中国童话》书末附有一份“文学作品引用书目”(Benutzte Literarische Quellen),卫礼贤将《西游记》(Si Yu Gi)置于首位,由此可见,他明确知道《西游记》是一部文学作品。在《心猿孙悟空》中,卫礼贤又反复强调其“童话文学”属性。归根结底,在他看来,《西游记》是一部“童话小说”。十年后,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中表达了几乎完全相同的观点。胡适把《西游记》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即一至七回,说:“第一部分乃是世间最有价值的一篇神话文学。”[17](P263)又说:“正如英文的《阿梨思梦游奇境记》(Aliceinwonderland)虽然还有很有意味的哲学,仍旧是一部极滑稽的童话小说。现在有许多人研究儿童文学,我很郑重地向他们推荐这七回天宫革命的失败英雄《齐天大圣传》。”[18](P264)这种关于《西游记》主题认识上的惊人相似,不得不让人揣测胡适与卫礼贤之间存在着观点上的直接继承性。
虽然这样怀疑,但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中却并未提及卫礼贤,只道自己的观点直接得益于钢和泰的启发。钢和泰何许人也?他与胡适的关系如何?在《胡适的日记》中,钢和泰一直被胡适尊称为“钢男爵”或“钢先生”,他说:“钢先生是俄国第一流学者,专治印度史与佛教史。”[19](P66)1937年3月16日,得知钢和泰去世的噩耗,胡适在日记中写道:“钢先生是一个纯粹学人,终身寻求知识,老而不倦。他从前是Esthonia的贵族,广有财产。他专治梵文藏文,往年为考迦腻色迦王的年代,他想从中国史料里寻证据,故到东方来。俄国革命后,他的财产被没收,不能不靠教书生活。民国七年,我因Sir Charles Eliot 的介绍,请他到北大来教梵文,并教印度古宗教史。他的古宗教史是我替他口译的,我们合作两年,我得益不少。我最初学梵文,也是跟他学的。”[20](P547)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胡适对钢和泰的赞许与钦慕,以及两人之间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钢和泰在学术上主要研究印度佛经,以他对梵文及印度文化的熟悉,完全有能力发现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哈奴曼与孙悟空形象的雷同,故此,胡适说他的“哈奴曼说”直接得益于钢和泰是成立的。值得注意的是,钢和泰是个语言天才,他不但精通俄语和梵文,还学过德语、英语和法语等多种语言,故此,无论是德译《中国童话》,还是英译《中国民间故事集》,他都有能力读懂,只是目前同样缺乏直接的证据表明钢和泰知晓卫礼贤的观点。
那么,同样是活跃在20世纪初期的学界名流,胡适与钢和泰是否与卫礼贤有过交集,以致影响了二人对于卫礼贤著述的接受?查阅《胡适的日记》,他确实不曾提及德、英两个童话译本,但在1921—1923年撰写、修改《西游记考证》一文期间,胡适曾两次见过卫礼贤。1922年5月3日,胡适在德国使馆结识时任“科学参赞”的卫礼贤,知道他“精通汉文,曾把十几部中国古书译成可读的德文”。此前一年还曾尝试着翻译过胡适的《哲学史》。[21](P347)6月28日,在文友会上,胡适听卫礼贤讲《易经》,认为他大旨用自己的解释,没什么创新。但卫礼贤对于胡适“太极”之“极”字的解释的赏识,却令胡适觉得颇为难能可贵。[22](P388-389)然而,两个月后,胡适就对卫礼贤的“个人才性”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不以为然,他在8月29日的日记中说:“邀钢先生和雷兴(F.Lessing)先生到公园吃茶,偶谈学术上个人才性的不同。尉礼贤对于中国学术,有一种心悦诚服的热诚,故能十分奋勇,译出十几部古书,风行德国。钢、雷和我都太多批评的态度与历史的眼光,故不能有这种盲目的热诚。然而我们三人也自有我们的奋勇处。”[23](P441)显然,在治学态度和方法上,胡适、钢和泰彼此声气相投、引为同调,他们对卫礼贤却敬而远之、不求苟同。
尽管胡适对卫礼贤漠然置之,卫礼贤对胡适却颇有些一往情深的况味。卫礼贤虽然比胡适年长十八岁,但对其哲学思想和博学多识却格外服膺。1921年结识胡适后,他不但在演讲中推介胡适的学术观点,而且还尝试着翻译过胡适的《哲学史》。在他翻译或撰写的《老子》、《孔子生平和事业》、《易经》等著作中,有不少地方显示了胡适的影响。1924年离开北京后,卫礼贤对胡适仍念念不忘。1926年10月邀请旅欧的胡适做《中国小说》的演讲时,卫礼贤亲自到车站迎候。在同年出版的《中国文学》(DieChinesischeLiteratur)一书中,他不仅采纳了胡适演讲稿中提及的最新《红楼梦考证》结论,甚至还附了一张胡适的照片。[24](P193)但这样的热忱似乎并没有改变胡适对他的看法。当他来到卫礼贤在法兰克福大学创办的“中国学社”,面对这一推动中德文化交流的重要学术机构,胡适却说:“其意在于使德国感觉他们自己文化的缺点;然其方法则[有]意盲目地说中国文化怎样好,殊不足为训。”[25](P394)
事实上,胡适所谓与卫礼贤“个人才性”的差异或许只是表面托词,他对卫礼贤的本能排斥以及卫礼贤对他的一往情深,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中德两国思想文化转向的彼此背离。20世纪初期,胡适提倡的“新文化运动”以摧毁传统文化、打倒孔家店为前提,而“一战”后以卫礼贤等为代表的德国新锐思想界却把东方智慧或孔子思想看作是拯救欧洲文化衰亡的福音。1921年,旅德学生魏时珍在日记中对两国背道而驰的文化现象有着清晰的描述,他说:“德国思想界,有两大潮流,一为新派,一为旧派。所谓新派,大都出自哲学美术与诗学者,彼辈自欧战后,大感欧洲文化之不足,而思采纳东方文化,以济其穷,于是言孔子、释迦哲学者,皆大为社会所尊重,如凯热几林,如尉礼贤,如史奔格列儿,皆其例也。所谓旧派者,仍尊崇自然科学万能,不为时潮所动摇……此两大潮流中,新派极占势力,所谓旧派者,几无声息。此种现象,与吾国适反。我国言新者大都以驳斥孔子为能,而在德国,则深以能知孔子哲学为幸,甚至以辜鸿铭为欧洲之救星。可见天下学问,其价值极为相对,合乎当时之人心,则价值便高,反乎当时之人心,其价值便低,今日国内盛称之杜威、罗素,安知几年后,其学问不为人所吐弃,而奉之者俨如上帝,此亦未免大过矣。”[26]这时在中国推崇杜威、罗素思想的代表人物恰恰是胡适等人。职是之故,在中德思想文化转向截然相反的大背景下,卫礼贤这位“德国的孔夫子”对于中国文化的大力提倡,在胡适看来必然是热情有余而理性不足,换言之,他对卫礼贤其人其学充满疑虑。
那么,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胡、卫二人“个人才性”的不同,以及当时中德“文化转向”的差异,致使胡适哪怕此前知晓卫礼贤关于《西游记》的学术发现,也未必情愿加以引用?倘若胡适的学术观点确实受到了卫礼贤的启发却不肯公之于众,也该是20世纪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值得研究的案例。无论具体情形怎样,都不影响本文申述的主要观点,即:第一个将孙悟空与哈奴曼联系在一起的并非胡适,而是卫礼贤,胡适把《西游记》看作是“童话小说”,与卫礼贤的相关认识也有着惊人的相似。在出版时间上,卫礼贤的《中国童话》比胡适的《西游记考证》提前面世十年之久,这在《西游记》学术研究史上具有开启先河的重要意义,故此,卫礼贤的学术发现确实不应被学界有意忘却或无意忽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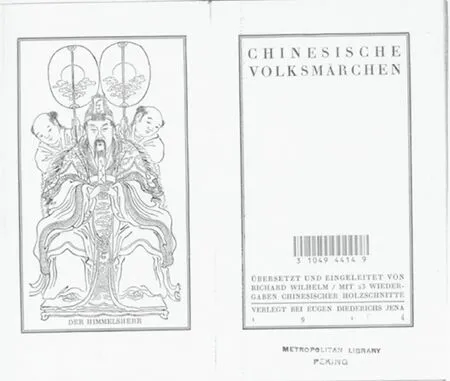
1914年版德译《中国童话》封面(国家图书馆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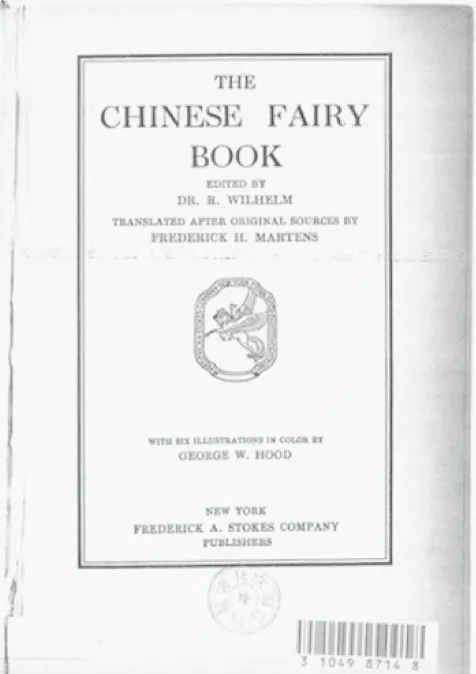
1921年版英译《中国民间故事集》封面(国家图书馆藏本)
[1][16][17][18] 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2] 郑振铎:《郑振铎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3] 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4] 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5][15] 吴承恩著,汪原放校点,胡适考证:《西游记》,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3。
[6][7] 陈洪:《“四大奇书”话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8] Richard Wilhelm.ChinesischeVolksmärchen.Jena: Eugen Diederich, 1914.
[9] K.Karttunen.“The Ramayana in the 19th Century”.In Gilbert Pollet(ed.).IndianEpicValues:RāmāyaaandItsImpact. Leuven: Uitgeverij Peeters en Departement Oosterse Studies, 1995.
[10] 荣格:《荣格自传》,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
[11][12][13] 孙立新、蒋锐编:《东西方之间:中外学者论卫礼贤》,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
[14] Richard Wilhelm.TheChineseFairyBook.New York: Frederick A.Stokes Company,1921.
[19][20][21][22][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
[24] Richard Wilhelm.DiechinesischeLiteratur.Wildpark-Potsdam: Akademische Verlagsgesellschaft Athenaion, M.B.H.1930.
[25] 胡适:《胡适全集》,第30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26] 魏时珍:《旅德日记》,载《少年中国》,1921,3(4)。
Abstract: The viewpoint that “Sun Wu Kong coming from Hanuman” was put forward by Hu Shi in theTextualResearchonJourneytotheWestpublished in 1923. This point of view was regarded as a great breakthrough of the study of Sun Wu Kung in early 20th century. But according to Hu’s article, the first researcher who associated Sun Wu Kung with Hanuman was not Hu Shi himself but rather Richard Wilhelm, a German sinologist who proposed the assumption inChinesischeVolksmärchenin 1914. Meanwhile, Hu Shi thought ofJourneytotheWestas a “fairy tale novel”, which also bore a striking resemblance to Richard Wilhelm’s point of view. Thus, Richard Wilhelm’s related statements aboutJourneytotheWesthave an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the academic research history of this novel. Because of the “personal character” of the two scholars and the “cultural shift” of that time, Hu Shi did not mention Richard Wilhelm’s academic contribution when he published related views.
Keywords: Hu Shi; Richard Wilhelm; Sun Wu Kung; Hanuman; fairy tale novel
(责任编辑张静)
GermanVersionofTheChineseFairyBookandAcademicResearchofJourneytotheWest
WANG Yan
(School of Liberal Art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王燕: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2)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十九世纪中国古典小说英译资料整理与研究”(15XNI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