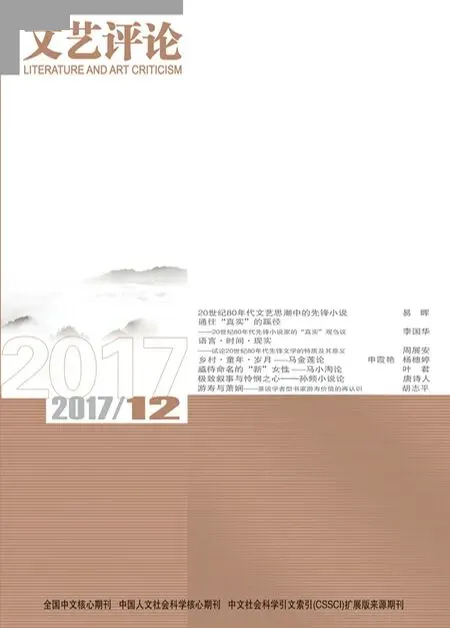通往“真实”的蹊径
——20世纪80年代 先锋小说家的“真实”观刍议
○李国华
通往“真实”的蹊径
——20世纪80年代 先锋小说家的“真实”观刍议
○李国华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真实”是一个画上了胡塞尔式的删除线的概念,不同作家的理解不仅大相径庭,而且截然相反。即使是一些现在看起来比较相近或相似的作家,他们的“真实”观也是不太一样的。比如史铁生和余华,单独看余华的《虚伪的作品》,也许会认为他们共享着一致的“真实”观;如果只看王朔在《王朔文集》上的序言,也会觉得王朔和余华具有很明显的家族相似性。但实际上,从《人民文学》1989年第3期上刊布的三篇文章来看,史铁生、余华和王朔的“真实”观,差别极大。而且,这种极大的差别,应该说在很好地显现了不同作家的“真实”观的同时,凸显了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家的独特之处。
一
《人民文学》1989年第3期以栏目“对话与潜对话”的方式刊登了史铁生《“神经内科”》、余华《我的真实》和王朔《我的小说》三篇短文,意在标识三位作家在小说观念上的分歧。史铁生的核心意思是要找到“永远变不了的东西”,“只起个名字,确实没有太大的意义”①。在他看来,小说被批评家命名为“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新潮”“后新潮”什么的,并不重要,也没有太大的意义,重要的是“真实”是否得到了确认,如同当年自己身患的疾病是否得到了确诊一样。史铁生认为遗憾的是,当年自己的病得到了各种名目的症断,但并未确诊,现在关于文学的讨论也没有找到那个“永远变不了的东西”。
余华大概不会反对史铁生对“永远变不了的东西”的相信,因为他在《我的真实》中说“在我的精神世界里面,是不存在混乱的,因为它没有时间的概念”。“变化”是和“时间”紧密相关的一个概念,“没有时间的概念”意味着没有“变化”的概念;没有“变化”的概念,也就意味着有“永远变不了的东西”。因此,余华在文中说:“一个人死了,在我的精神里却是活着的,因为我老记住他。我一记住他,就意味着他还活着。而很多活着的人我已经忘记他了,就证明他已经死了。”人死了,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但余华以记忆的方式改变了这一“变化”,并转为“永远变不了的东西”。这是余华和史铁生相通之处。不过,这相通之处并不妨碍余华走上与史铁生不同的蹊径。余华明确表示有两种不同的“真实”,一种是自己所有的创作都在努力接近的“真实”,另一种是“生活里的那种真实”,那种“实际上是不真实的”“真实”。简言之,史铁生可能不愿意花费太大力气去进行名实之辨,更希望通过某种直观的方式去把握“永远变不了的东西”,而余华对名实之辨是感到极大兴趣的,他要顽强地表达自己的“真实”观,以致于不惜将“生活”斥为“一种真假参半的、鱼目混珠的事物”。
王朔与余华刚好相反。虽然王朔也许是习惯性唱反调,但他在《我的小说》中所说的一些意见,仍然是有重要的讨论价值的。他开篇提到一个重要的批评现象:“有人不喜欢我的小说,说我的小说不是小说。其实,只不过觉得不是新潮小说罢了。”撇开字里行间透露出的王朔对于马原、余华等人代表的新潮小说赢得批评界更高赞誉的羡慕和不满不论,可以看到的是,在1989年的中国文坛上,先锋小说已经有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引起了同行的意见;而“我的小说不是小说”之类的判断则意味着先锋小说背后的小说观念已经是一种有力量的排他性的观念存在。在这样的压力之下,王朔表示:“我写东西都从我个人实例出发。而我接触的生活,使我觉得只要把它们描述出来就足够了。所以写的时候我总极力抹煞自己。我不想把自己的东西加到生活上去。而且要把生活写出来,笔力就已经承担不住……先锋的和前卫的文学当然要有,但比例应当控制,总不能搞成这样,让人家说你们都弄成同性恋俱乐部了……”虽然王朔在《王朔文集》序言中的一些说法会给人王朔颇愿成为同性恋俱乐部会员的感觉,但还是应该注意到,他自觉地站到了余华们的对立面,他的言议中也可以抽绎出几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即:
第一,从个人出发的写作,未必就是现代主义的写作。王朔甚至认为:“现代主义小说在文学史上地位很高,但总起来看还是现实主义小说地位更高。我倒承认我这是现实主义的。”考虑到近十年多来中国批评界的一些反复现象,有批评家开始重新看待18、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小说的价值和意义,王朔的意见也许不妨得到更多的肯定。那么,余华式的以个人“真实”为真的“真实”的观念,就有重新讨论之必要。
第二,生活与创作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唯一的。余华将生活视为“真假参半、鱼目混珠的事物”,这在王朔看来,可能正好是作家意识到“笔力就已经承担不住”“生活”,就退而求其次,逃避到个人的真实中去的办法。在此意义上,现实主义的反映论不是失效了,而是作家失去了直面生活的魄力和勇气。
第三,余华式的方式,可能不过是“把自己的东西加到生活上去”。所谓“把自己的东西加到生活上去”,实际上就是近些年中国批评界学步日本批评家柄谷行人反复讨论的“透视法”问题。在“透视法”的作用下,作家完成了极为重要的替代性想象,即想象自己是造物主,能够俯瞰并创造一切。这一现在被视为“现代性装置”的观念之物,在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那里,恐怕是透明的、绝对的存在,是作家们自觉追求的结果。
第四,先锋小说作为余华们的“真实”观念的形式化,表征的乃是作家承受不住生活挤压的心灵状态。易言之,不是先锋小说对生活进行了变形处理,而是生活将先锋小说挤压成变换了现实主义小说形式的形式。
当然,与其说王朔是在理论上意识到了上述问题的存在,不如说是一种作家的直觉让他努力地表达自己。而通过王朔的表达,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家“真实”观的合法性也被悬置起来。借助同时代人的目光,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的形象也变得立体。王朔在文中又说:“我觉得文学应当有两种功能,纯艺术的功能和流行的功能。”这其实指明了余华式的小说观的观念基础是“纯文学”。贺桂梅曾仔细检讨“纯文学”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说明了卡西尔《人论》将人理解为符号动物的观念以及以“现代化”取代“革命”的意识形态对“纯文学”观的根本重要性。②持此观念的作家难免敌视反映论,并且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关联的革命经验表现出格格不入的状况。因此,尽管1989年就有王朔式的反对意见,“纯文学”以其知识谱系和形式形态仍能提供足够的知识和意识形态信心,让余华们坚决地表达现代主义式的“真实”观,并在创作中自觉追求“透视法”带来的虚构的满足感。
二
所谓满足感的问题,其实马原小说《虚构》中的一句话即足以尽之,就是那句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格言的“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不过,马原安插在这句话中的深意也许并未被完全打开。至少这句话与小说开头的题记式的内容有何关系,也许还值得继续探讨。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小说家似乎是怕读者不够敏感,又或者是怕自己在小说中要表达的见解太深刻,因而习惯在小说文本中植入题记式的内容。马原《虚构》的题记式内容,可能是所有先锋小说家提供的题记式内容中最值得细读的,试引如下:
各种神祇都同样地盲目自信,它们惟我独尊的意识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它们以为惟有自己不同凡响,其实它们彼此极其相似;比如创世传说,它们各自的方法论如出一辙,这个方法就是重复虚构。
《佛陀法乘外经》③
和马原惯常的表现一样,《佛陀法乘外经》也是似真还假的,它并不存在,然而频繁地出现在马原的一些小说文本中。这虚构的经书充满反讽的意味:首先,它的语言是典型的马原式的小说语言,并没有模仿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部佛经,这表明它不仅是“外经”,而且是“假经”,虚构的。其次,它强调“各种神祇都同样地盲目自信,它们唯我独尊的意识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与“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两相对照,构成反讽的效果。“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一句本来的自信满满的感觉及所引出的后文的自信满满的叙述,似乎都可以说是一种“盲目自信”。而尽管是“盲目自信”,“唯我独尊”,创世传说却是流传下来了。这似乎隐喻着,先锋小说家马原的“自信”尽管“盲目”和“唯我独尊”,但却建立了小说叙述的基础和可能。而因为“各种神祇”“各自的方法论如出一辙”,则如此建立的小说叙述的基础和可能,也许是唯一的;就算是“盲目自信”“唯我独尊”,也没有什么办法。第三,先锋小说家的叙述行为与“各种神祇”的创世行为在方法论方面是一样的,都是“重复虚构”。小说的名字就是《虚构》,而“我写小说”,也就是说,作为先锋小说家的马原在“重复虚构”。因此,先锋小说家马原创作小说《虚构》的过程,其实就是“创世”的过程。而二者之间,也许在马原看来的确并无二致,在其他人看来,也许就是不可相提并论的,那么,滑稽的意味就出现了。第四,当作家写下“虚构”二字作为小说标题时,他也许害怕读者不明白作者已经发现神祇创世的秘密,或者说文明起源的秘密,于是特别写上一段题记式的文字,显露作者神祇式的身段。而一般来说,神祇不是在自我言说中显现自身,而是在被叙述中显现出来的。这就意味着,尽管先锋小说家马原有意与神祇相比,实际上却恰好证明了先锋小说家并不是神祇,反讽的意味在这个层面也出现了。第五,先锋小说家马原自信满满地认为自己发现了神祇的秘密就是“重复虚构”,其实则只是说出了小说叙述的秘密,对于神祇的言说因而彻底沦为一次小说的叙述行为,并不值得进行神学意义上的对待。事实上,在小说文本中,马原惯用的手法之一正是“重复虚构”,小说《虚构》也是“重复虚构”。那个已被作为标签贴在先锋小说家马原身上的所谓的“叙事圈套”,正是源于“重复虚构”。把“重复”的部分离析,马原的“迷宫”自然解体。
而尤为反讽的是,在这样的“重复虚构”中,马原建立了他小说的“真实”,或者说,马原通过“重复虚构”接近了“真实”。这就来到了余华在《虚伪的作品》中所表达的核心内容。尽管马原对通俗小说的爱好和余华对通俗小说的戏仿是在不同的方向展开的小说叙述行为,两位作家在如何通过“重复虚构”接近“真实”这一蹊径上,倒是前后同行的。而且,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批评界乐意关心马原们背后欧美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作家的身影,但也不可否认,这些先锋小说家仍然是通过自己的写作实践抵达欧美前辈开拓出来的一些路向的。这一点余华在《虚伪的作品》中表达得相当充分:
在86年写完《十八岁出门远行》之后,我隐约预感到一种全新的写作态度即将确立。艾萨克辛格在初学写作之时,他的哥哥这样教导他:“事实是从来不会陈旧过时的,而看法却总是会陈旧过时。”当我们抛弃对事实做出结论的企图,那么已有的经验就不再牢不可破。我们开始发现自身的肤浅来自于经验的局限。这时候我们对真实的理解也就更为接近真实了。当我们就事论事地描述某一事件时,我们往往只能获得事件的外貌,而其内在的广阔含义则昏睡不醒。这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窒息了作家应有的才华,使我们的世界充满了房屋、街道这类实在的事物,我们无法明白有关世界的语言和结构。我们的想象力会在一只茶杯面前忍气吞声。④
当在1989年6月表达上述意见时,余华是一位成熟的先锋小说家,已经清楚地知道并且能够熟练地表达自己的写作实践与小说观念之间的关系。他强调自己是通过写作实践来认识小说、发现小说的秘密,这就如同马原在《虚构》中表现出来的自信一样,有着切身而来的底气,是值得批评家重视的。不过,更为重要的问题是马原、余华前后同行的通过“重复虚构”接近“真实”的蹊径。当马原强调“各种神祇”都在“重复虚构”时,内含的是关于世界的不同表述背后有着同样的结构的意思,故而实际上表达的正是余华试图明白的“有关世界的语言和结构”。这也就是说,马原、余华这些先锋小说家试图越过“房屋、街道这类实在的事物”,突破“经验的局限”,找到“有关世界的语言和结构”,“接近真实”。他们相信混沌的事物背后存在“有关世界的语言和结构”,这种解构主义语言学式的对世界的理解,使他们相信通过语言的虚构行为、而不是对事物的再现行为,去“接近真实”。当然,余华的表达要比马原复杂而缠绕。在马原那里,一个“虚构”似乎足以包打天下,而余华支使了“事实”“看法”“经验”“真实”“事件”“事物”“想象力”等一组内涵或交叉、或互渗、或相歧的概念。很显然,“事实”和“真实”是同义词,也许都是“truth”的翻译,而“事件”“事物”是被“看法”和“经验”掩盖的“真实”,“想象力”可以接近“真实”,但往往受困于“看法”和“经验”。因此,所谓“事件”“事物”即意味着已被叙述过的“事实”和“真实”,已经不是其本来面目,要“接近真实”,就必须抛弃对“事件”“事物”的关注。这就是说,必须有新的观察“事实”“真实”的方法,才能接近“真实”。而“事件”“事物”作为旧有的经验之物,不能提供新的观察“事实”“真实”的方法,相对而言,新的观察“事实”“真实”的方法就显得是“虚伪”的或“虚构”的。余华在《虚伪的作品》中继续说:
当我发现以往那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只能导致表面的真实以后,我就必须去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寻找的结果使我不再忠诚所描绘事物的形态,我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实。⑤
值得注意的是“接近了真实”这一表达。如马原在小说《虚构》的结尾要表达对于刚刚结束的叙述的不信任感一样,余华在他的所有表达中也从未像现实主义者那样说自己的写作抵达了“真实”,而强调接近“真实”。余华的小说《此文献给少女杨柳》《四月三日事件》《世事如烟》《河边的错误》等,都表明作家通过“重复虚构”,试图接近“真实”,但却不能提供或抵达“真实”本身。这一点在其他先锋小说家的小说中也可以反复观察到,这里不再赘述。
有意思的是,先锋小说家们的“真实”观并未引领出一种谦卑,倒是引发了王朔的“同性恋俱乐部”的嘲讽。这里也许隐藏着某种更深的病灶。
三
早在1987年,就有论者表示:
在我国目前文学环境下出现的“纯文学”观念,具体表现为上述的“非理性”论,“纯感觉”论和“纯语言技巧”论等等。它们见于各种对其它文学观点的反驳,见于对各种具体作品的批评,也见于直接的理论阐述之中,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它们各自的具体文学主张虽有异,却都有一个共同点:力图从文学中将种种政治的、社会的和历史的内容和因素统统作为“非文学”因素而排除干净,只剩下主张者们各自心目中的那唯一的纯文学因素留在文学之中。因此,对于文学作品中的所谓“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因素的贬低和排斥,对于文学研究与批评中就作品的社会原因、社会内容、社会意义及社会效果的研究和对作家的社会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要求的淡漠与反对,就成为它们的共同态度。所以概括地说,“非社会性”便是“纯文学”论的根本要求。⑥
认为先锋小说家对“纯文学”的追求即导致“对作家的社会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要求的淡漠与反对”,肯定是言过其实的。实际上,尽管先锋小说家每每表示疏离社会政治,在小说中甚至表现一些语言中心主义的特点,但他们不过是以去政治化的方式来疏离他们所不认同的社会政治罢了,他们有他们所认同的社会良心和责任感。否则,他们在小说中处理血腥、暴力、疾病、情欲和历史的方式,他们引渡通俗小说或类型小说的叙述技巧到小说中去的匠心,都将是不可理解的。不过,相对于此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而言,先锋小说的确在现代主义“透视法”的作用之下,显得光滑而纯净,告别了“种种政治的、社会的和历史的内容和因素”,使读者不易了解先锋小说所反映的具体的社会生活和内容。即以马原《虚构》而言,读者从中即很难读出20世纪80年代中国麻风病的疫情、控制和社会心理方面的内容。相对于马原所欣赏的毛姆小说《月亮与六便士》对麻风病的描写,读者也许不能不认为,马原只是利用麻风病作为一个惊悚的符号植入小说文本中,以引发读者的好奇心;对于马原而言,麻风病完全可以是别的什么,只要能够令人惊悚并因而好奇即可。同样地,在格非的《迷舟》和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等小说中,重要的也不是小说叙述所涉及的历史内容,而是小说叙述所呈现的对于历史叙述的理解。也就是说,正如讨论先锋小说时人们所惯常注意的那样,对于先锋小说家而言,重要的不是叙述了什么,而是叙述行为本身。因此,所谓“‘非社会性’便是‘纯文学’论的根本要求”,虽然断语峻急,带着明显的批评先锋小说家的意识形态训诫,但仍然算得上一语中的,指出了马原、余华们所“重复虚构”出来的“真实”是多么地与社会现状相疏离的。
与社会现状相疏离的结果是多样的。就马原而言,他感到的是叙述上花样翻新的困难和逐渐失去读者的悲哀。而其他先锋小说家,大多是临阵变法,变成了“新历史小说”或“新写实小说”的作者,也有的是进入影视行业和大专院校。作为曾经热烈的拥趸,批评家吴亮1989年即已意识到:
纯文学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许多作家、评论家还硬要等着看小说。在非常好的小说面前,他们自己已经无话可谈了。包括我自己也这样。老调子已经唱完,新调子也唱得差不多了。还是听听现实的东西比较舒服。纯文学是在非常狭窄的范围中发展的,它已经从大众传播中退出。再也不可能进入大众传播的层次。⑦
吴亮唱衰“纯文学”的时间离“纯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的崛起并没有几年,离先锋小说的蔚然成风更是近在眼前。这也许意味着一种高度提纯的“真实”观,可能并不像余华想象的那样,既能“自由地接近了真实”,又能唤醒事件“内在的广阔含义”,反而导致的可能是“盲目自信”的“真实”幻觉,带来短暂的欢娱。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感到悲观。即使是近三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有人在守望先锋,相信“纯文学”是不死的。而且,诸如“已经从大众传播中退出”“还是听听现实的东西比较舒服”之类的说法,也不能算是从“纯文学”或先锋小说内部发展的脉络得出的观察,而是一种典型的冷眼旁观者的所得,因此也不能说是有多么大的说服力的。在一个庞大、复杂的中国当代社会系统中,容量一定比例的“纯文学”或先锋小说的存在,实际上是毫无问题的。即使如王朔所言,成了“同性恋俱乐部”,其实也略无挂碍。那么,所可断言的并不是“纯文学”的死亡或不死,而是余华们的“真实”观,确乎是在庞杂社会中另辟蹊径,而他们以为因此“自由地接近了真实”。
而因为得以在庞杂的中国当代社会系统中繁衍生息,先锋小说家们可能误以为自己所理解的“真实”即是全部的“真实”或更高级的“真实”——很显然,在他们的观念中,“真实”是存在等级的,于是就以“有关世界的语言和结构”的发现者甚至创造者自居,与神祇并列,产生了一点也不谦卑的情绪。虽然在他们的修辞上,他们使用“接近真实”而不是“把握真实”,但在行为上,尤其是小说的叙述行为上,他们表现得像是他们不仅把握了“真实”,而且创造了“真实”。因此,他们没有多少理由去谦卑。而作为一些关联性的结果是,读者发出了“还是听听现实的东西比较舒服”的反馈,先锋小说家们对于中国当代社会的理解和研究也是相对显得肤浅的。
正如马原小说《拉萨生活的三种时间》结尾所写的:
时间整个乱套了。我不说你们也看得出来,我有把条理搞得一团糟的天分。比如我先说去年十月结婚,又说三年半以前我和我老婆刚到拉萨;再比如我说明天早晨看到那个卖银器的康巴汉子,又说今天从小蚌壳寺回来就已经见过这个人;一言以蔽之:时间全乱了。⑧
不是时间真的全乱了,而是叙述者将整个事件叙述得乱套了,是作者“有把条理搞得一团糟的天分”。先锋小说家们以独特的“真实”观拼合出他们想要的“真实”,就算一切乱套,他们也是乐在其中的。
①史铁生《“神经内科”》[J],《人民文学》,1989年第 3期。下文凡引用史铁生《“神经内科”》、余华《我的真实》和王朔《我的小说》时的出处与此相同,不再注明。
②贺桂梅《“纯文学”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文学性”问题在1980年代的发生》[J],《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③马原《虚构》[J],《收获》,1986年第 5期。
④⑤余华《虚伪的作品》[J],《上海文论》,1989年第5期。
⑥秦人《“纯文学”与文学的社会性》[J],《浙江学刊》,1987年第5期。
⑦赵玫《纯文学与一九八八年》[J],《文学自由谈》,1989年第2期。
⑧马原《拉萨生活的三种时间》[J],《解放军文艺》,1986年第9期。
同济大学中文系)
——以纯文学在近代和八十年代的两次现身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