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与中国文论感觉体验性话语的建构
吴中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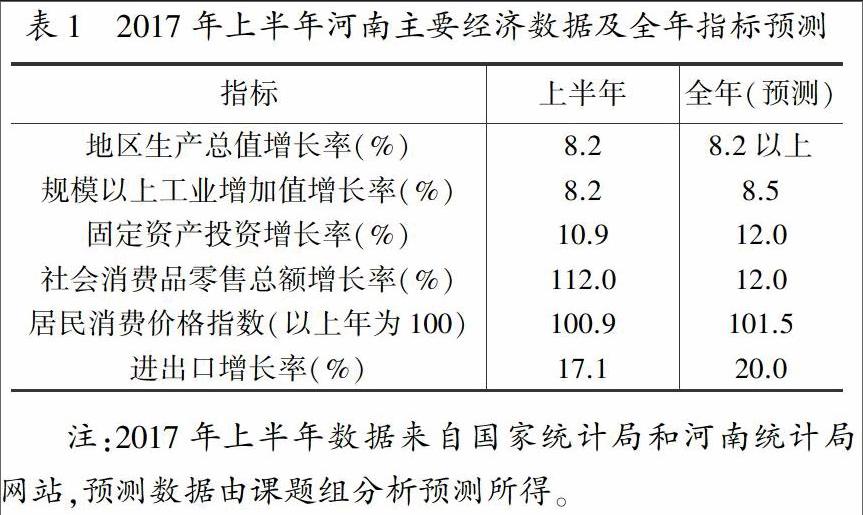
摘 要:根植于深广的诗性文化,中国文论喜欢用五官的日常体验去比拟文学,从而延生出大量的富于感官体验的直觉性文论范畴和概念。以《文心雕龙》“视、听、味、佩”说为代表的感觉性文论话语,大量运用于从文学创作到阅读欣赏的一系列过程的描述,从而从最根本的意义上决定其文论思维特征的体验性。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成熟期的中国文论,从范畴概念、话语方式到思维方式,都具有的感觉体验性,建构起一套富于民族特色的感觉体验性的文论话语。这套感觉性的文论话语对于后世文论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文心雕龙;感觉体验;话语建构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8-0135-07
中国古代的文论家们以五官的日常体验去比拟文学,从而延生出大量的本来是用来表达人的感官体验的直觉性文论范畴和概念。建立在大量直觉性范畴概念基础上的古代文论,对文学从生产到阅读的一系列过程的描述都是富于直觉体验的,从而从最根本的意义上决定了古代文论思维特征是感觉体验而非逻辑推理。正如列维—布留尔所说:“与其说他们在思维,还不如说他们在感觉和体验。”①关于古代文论感觉用语的援用,汪涌豪先生有专门论述。②我们认为,这不仅仅是“用语的援用”,用语毕竟是表象,真正起支配作用的是其内在的思维,大量感觉用语的援用是中国文论诗性思维的生动反映,是中国文论感觉性话语建构的具体体现。中国文论成熟时期即魏晋南北朝时期就非常注重感觉性话语的建构,《文心雕龙》就是一个值得个案分析的经典文本。一般认为,《文心雕龙》是古代文论中逻辑性最强的著述。多年来的龙学研究也更重视其逻辑性的分析,有意无意地遮蔽其最富民族特色的感觉体验性。实际上,《文心雕龙》无论从范畴概念、话语方式到思维方式,都有很强的感觉体验性。《文心雕龙·总术篇》云:“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这里的“视”“听”“味”“芬芳”等概念,原来是人的视觉、听觉、味觉、嗅觉的用语,今引之以论文,似乎文学也视之有色,听之有声,品之有滋味,闻之有香臭。这种五官感觉用语的化用及其思维的体验性最富于原始感觉,也是最富于诗性特征的。
一、视之则锦绘:诗性视觉
眼睛是人的最重要的感觉器官,眼睛虽小,却能看到整个世界。亚里士多德说:“此于五官之中,以得之于视觉者为多。”③美国学者韦勒克说:“诗歌不仅是写给耳朵听的,也是写给眼睛看的。”④钱钟书也说:“人于五觉中最重视觉(the primacy or privileged position of the sense of vision)。”⑤外部大部分信息是通过视觉被人感知的,所以人对外界的视觉观感类概念也比较多,比如形状、大小、颜色、高低、疏密、肥瘦、远近、方圆等等,都是视觉类概念。在维柯看来,视觉体验是人类许多思想观念的基础,“人类的思想开始是从用肉眼观照天象所产生的”,先民们“在世界中第一個观照的对象就是天空”⑥。这跟《周易·系辞上》所说的先民们通过仰观俯察来认识世界的道理是一样的。刘勰正是通过观察天文地理悟出文学之道,《文心雕龙·原道篇》就是通过“丽天之象”和“理地之形”来体悟“道之文”,这也是刘勰所谓的“形文”(《文心雕龙·情采篇》),这是基于视觉体验的文象。天地万物千变万化,人的视觉体验也丰富多彩。基于道通万物的诗性思维,先民们自然把对万物的视觉感受转移用来比拟文学,于是文学也有形有色、有疏有密、有肥有瘦。
不同时代人们的视觉审美趋向各不相同,所谓“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文心雕龙·通变篇》)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视觉审美爱好,所谓“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文心雕龙·明诗篇》)但人们的视觉审美也有一些共同的地方,往往比较注意醒目、突出者。鲁道夫·阿恩海姆说:“视觉是选择性的”,“在它们最喜欢选取的东西中,最多的是环境中时时变化的东西”⑦。所以出类拔萃的作家、作品自然引人注目,评论家们也往往褒奖有加。例如,刘勰多处用“颖”一词称道作家。如“根盛而颖峻”(《文心雕龙·隐秀篇》)、“贾谊才颖”(《文心雕龙·才略篇》)、“锋颖精密”(《文心雕龙·论说篇》)、“陆机断议,亦有锋颖”(《文心雕龙·议对篇》)、“颖出而才果”(《文心雕龙·体性篇》)、“才颖之士”“颖脱之文”(《文心雕龙·通变篇》)、“瑰颖独标”(《文心雕龙·才略篇》)等等。颖,就是事物最突出的部分。《说文解字》:“颖,禾末也,从禾,顷声。《诗》云:‘禾颖穟穟。”《说文解字注》:“浑言之则颖为禾末,析言之则禾芒乃为秒。”⑧可见,“颖”一词是农耕文化背景下的视觉经验积累。
鲁道夫·阿恩海姆说:“视域中的某些永不变化的因素,如阳光照射时那种永不变化的色彩,很容易从意识中消失。”⑨多彩亮丽的颜色往往招人喜欢,所谓“辩丽本于情性”(《文心雕龙·情采篇》)。这里我们以《文心雕龙》“丽”一词的运用来作些分析。尚丽意识是魏晋南北朝文论的一条主脉。曹丕《典论·论文》云:“诗赋欲丽”。陆机《文赋》曰:“嘉丽藻之彬彬”“清丽芊眠”。到《文心雕龙》,“丽”一词更是频频出现,并专门有《丽辞篇》。《体性篇》中所谓“八体”之中就有“壮丽”一体,其尚丽意识是显而易见的。具体用例有“丽天之象”(《原道篇》)、“古诗佳丽”“景阳振其丽”(《明诗篇》)、“文丽而义暌”(《杂文篇》)、“赞序弘丽”(《史传篇》)、“淮南泛采而文丽”(《诸子篇》)、“丽于黼黻文章”(《章表篇》)、“公干笺记,丽而规益”(《书记篇》)、“商周篇什,丽于夏年”“新进丽文”(《通变篇》)、“岂营丽辞”“崇盛丽辞”“丽句与深采并流”(《丽辞篇》)、“各竞新丽”(《总术篇》)、“李斯自奏丽而动”(《才略篇》),这里除“丽辞”“新丽”稍有贬斥之意,其他“丽”字多为褒义。当然,刘勰推崇“丽”是有原则的,他提倡“雅丽”“清丽”“丽则”,如“圣文之雅丽”(《征圣篇》)、“文辞丽雅”(《辨骚篇》)、“清丽居宗”(《明诗篇》)、“丽词雅义”(《诠赋篇》)、“清文以驰其丽”“雅丽黼黻”(《体性篇》)、“商周丽而雅”(《通变篇》)、“羽仪乎清丽”(《定势篇》)、“诗人丽则而约言”(《物色篇》)等。刘勰反对过度的“丽”,即所谓“淫丽”“巧丽”“靡丽”“绮丽”“缛丽”“诡丽”等,如:“宋发巧谈,实始淫丽”“词必巧丽”(《诠赋篇》)、“魏初表章,指事造实,求其靡丽,则未足美矣”(《章表篇》)、“韩非云艳采辩说,谓绮丽也”“绮丽以艳说”“为文者淫丽而烦滥”(《情采篇》)、“辞人丽淫而繁句”(《物色篇》)、“李斯自奏丽而动”“子长纯史,而丽缛成文”“搜选诡丽”(《才略篇》)等等。与“丽”一词相似还有“采(彩)”一词,也是视觉体验,如“郁然有彩”“符采复隐”“光采玄圣”(《原道篇》)、“夫子风采”“秀气成采”(《征圣篇》)、“风人辍采”“采缛于正始”“各有雕采”“俪采百字之偶”(《明诗篇》)、“铺采摛文”“时逢壮采”(《诠赋篇》)、“镂彩摛文”(《颂赞篇》)、“其才清采”(《铭箴篇》)等等。与“丽”一样,刘勰对于“采”也要求适度,所谓“符采相济”(《宗经篇》)、“符采相胜”(《诠赋篇》)是也。与“丽”类似的词还有“艳”,如“中巧者猎其艳辞”“艳溢锱毫”(《辨骚篇》)、“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诠赋篇》)、“艳词动魂识”(《杂文篇》)、“观其艳说”(《时序篇》)、“洞入夸艳”“景纯艳逸”(《才略篇》)等等。刘勰同样不喜欢过度的艳,如“侈艳”“巧艳”“夸艳”:“楚汉侈而艳”(《通变篇》)、“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定势篇》)、“洞入夸艳”(《才略篇》)等。从日常体验来说,好颜色招人喜欢,但色彩过度则适得其反。以这种视觉体验评文学,则要求创作文采飞扬但又不失章法,否则则为瑕、为俗。刘勰强调文章的“丽”“采”和“艳”,顺应魏晋六朝人的时代审美情趣,同时也是视觉审美基本经验的体现,也是其“文而不侈”(《奏启篇》)、“唯务折衷”(《序志篇》)写作原则的具体体现。
除了颜色之外,还有方圆、疏密、远近、明暗、长短等,也是视觉体验。如《文心雕龙》多处用“圆”一词,汪涌豪先生有专文揭示其思想资源。⑩据王先霈先生统计,“《文心雕龙》全书中‘圆字凡17处,除开《原道》《定势》《隐秀》三处为‘方圆之圆,系指形状而言,没有什么感情色彩,其他各处分别有周全、完整、丰满、成熟等含义,全都明确无误地用作褒语。”?在我们看来,所谓周全、完整、丰满、成熟正是“圆形”视觉体验的具体表现。王先生称这种文论思维为“圆形批评”,也是视觉体验的精妙概括。文学的视觉体验有远、近:“鉴远而体周”“远近之渐变”(《诸子篇》)、“其来远矣”(《议对篇》)、“其神远矣”(《神思篇》)等,八体之中有“远奥”(《体性篇》)、“响逸而调远”(《体性篇》)、“涯度幽远”(《才略篇》)等。又有明、暗:“博明万事”“明乎坦途”(《诸子篇》)、“赞者明意”(《论说篇》)等。还有长、短:“修短有度”(《镕裁篇》)。更有疏、密,《文心雕龙》有大量用例:“密而兼雅”“辞高而理疏”(《杂文篇》)、“疏阔寡要”(《史传篇》)、“慎到析密理之巧”(《诸子篇》)、“辞共心密”(《论说篇》)、“曲趣密巧”(《檄移篇》)、“骨掣靡密”(《封禅篇》)、“理密于时务”(《议对篇》)、“密则无际,疏则千里”(《神思篇》)、“才疏而徒速”(《神思篇》)、“裁密而思靡”“虑周而藻密”(《体性篇》)、“通变之术疏耳”“近附而远疏”(《通变篇》)、“识疏阔略”(《声律篇》)、“理圆事密”(《丽辞篇》)、“暨乎后汉,小学转疏”“瘠字累句,则纤疏而行劣”(《练字篇》)、“精思以纤密”(《指瑕篇》)、“气衰者虑密以伤神”(《养气篇》)、“首尾周密”“必疏体统”“疏条布叶”(《附会篇》)、“功在密附”“精思愈疏”(《物色篇》)、“密而至”“以密巧为致”“意繁而体疏”“捷而能密”(《才略篇》)、“曲意密源”(《序志篇》)等等。《说文解字》云:“密,山如堂者,从山从宓。”又谓:“疏,门户,疏窗也。从疋,疋亦声囱,象GFDF2形。”这都是基于视觉体验的造字方法。用于文论,“密”是严密、周密,是褒义;“疏”是松散、疏忽,是贬义,都有原初的视觉体验印迹。
刘勰很重视文学欣赏的观察功夫,提出“六观”说:“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文心雕龙·知音篇》)此处“观”字,詹锳先生认为作名词用,意指“從六个方面观察”。又引饶宗颐观点,认为“六观”之法参刘邵《人物志》的“八观”说。?中国古人提倡“观”法似应更早。《道德经》第五十四:“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此“观”即指推己及人、观察体验之功夫。?如果从最本根的角度来说,“观”法来源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视觉体验。《知音篇》又曰:“圆照之象,务先博观”“观文者披文以入情”,可见刘勰是非常重视赏析文学的体验性。
二、听之则丝簧:诗性听觉
鲁道夫·阿恩海姆说:“在视觉和听觉中,形状、色彩、运动、声音等等,就很容易被接合成各种明确的和高度复杂多样的空间和时间的组织结构,所以这两种感觉就成了理智活动得以运行和发挥的卓越的(或最理想的)媒介和场地。”?鲁道夫·阿恩海姆的意思是说,人类的思维活动运用视觉和听觉的机会更多。美国学者韦勒克说,“声音的层面”“构成了作品审美效果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视觉前面说过,下面说听觉。维柯说,先民们最初惊惧地听到巨雷时,“自然相信电光箭驽和雷声轰鸣都是天神向人们所作的一种姿势或记号”,上天用这种记号来发号施令,以显示它是“最有权力者”(optimus),意思就是“最强的”(fortissimus)。?这是先民们的听觉体验,他们靠耳朵来聆听上天的旨意。刘勰也认为,大自然的百籁之声,给文学以无限启迪:“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鍠。”(《文心雕龙·原道篇》)与视觉体验相比,古代文论中的听觉体验也很丰富。这是由早期诗、乐、舞不分的局面所造成的。朱自清《诗言志辨》说:“以声为用的《诗》的传统——也就是乐的传统——比以义为用的《诗》的传统古久得多。”?《尚书·尧典》:“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声”“律”“八音”是为听觉的内容,而“依”和“谐”“无相夺伦”云云,则是听觉体验了,如以之论文,则为一种诗性隐喻的表达。这样,评乐时也在评文学,古人对文学音乐性的探讨得以不断深化。《论语·述而》云:“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余音绕梁,三月不绝,美好的音乐的确有入心入脑的奇效。刘勰也说:“乐本心术,故响浃肌髓。”(《文心雕龙·乐府篇》)这些,还是音乐之评向诗文之评的移用或者说混用。后世文论还有以音乐比文学的现象,汉代的《诗大序》几乎照抄先秦《礼记·乐记》中本来说音乐的一段话:“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郭绍虞释此“文”为“宫、商、角、徵、羽五声之调”?。曹丕《典论·论文》:“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陆机《文赋》:“譬偏弦之独张,含清唱而靡应”云云,但音乐和文学毕竟是两回事,只是道理相通而已。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更是大量地用听觉体验指文学,《情采篇》有所谓“声文”,又有《知音篇》《声律篇》专门讨论这种听觉体验。对于刘勰的听觉审美意识,我们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尚“响”意识。刘勰要求,文学作品用字造句铿锵响亮,所谓“制氏纪其铿锵”(《乐府篇》)是也。《文心雕龙》多处用“响”一词,如“结响凝而不滞”(《风骨篇》)、“攀响前声”(《封禅篇》)、“遗响难契”“剖字钻响”(《声律篇》)、“秘响旁通”(《隐秀篇》)等等。刘勰提倡所谓“正响”:“淫辞在曲,正响焉生?”(《乐府篇》)、“黄钟之正响”(《声律篇》)。什么才是“正响”呢?即黄钟大吕之音,如刘勰称赞六经“金声而玉振”“席珍流而万世响”(《原道篇》)、“譬万钧之洪钟,无铮铮之细响矣。”(《宗经篇》)“六经”传达出来的就是一种“正响”,这是一种宏亮之音,有强劲力度、有生机活力的声音;这又是大雅之音,一种充满人间正气的声音,而不是靡靡之音、俚音俗曲。提倡“正响”,这是刘勰的宗经意识在听觉审美上的具体反映。与“正响”相反的是所谓“溺音”“乖调”,这是刘勰反对的:“雅声浸微,溺音腾沸”“故事谢丝管,俗称乖调。”(《乐府篇》)刘勰还提倡“逸响”:“嗣宗俶傥,故响逸而调远。”(《体性篇》)“动心惊耳,逸响笙匏。”(《隐秀篇》)“逸响”就是一种闲放之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阮籍行为逸放,所作诗歌“遥深”(《明诗篇》)、“归趣难求”(钟嵘《诗品》语)。
其二,和韵意识。《说文解字》:“韵,和也”,认为和、韵一个意思。刘勰则认识到两者不同,《文心雕龙·声律篇》:“气力穷于和韵。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韵气一定,故余声易遣;和体抑扬,故遗响难契。属笔易巧,选和至难;缀文难精,而作韵甚易。”我们先说“和”。重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周易·彖卦》:“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国语·郑语》:“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可见“和”之可贵,即在于“生物”。人们都喜欢和谐之音,中和之音养人性情,《荀子·劝学》:“乐之中和也。”又《乐论》:“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以这种听觉体验评文学,则要求文学抑扬顿挫、节奏有序。南朝沈约提出“四声八病”之说,就是这一审美诉求的具体反映。刘勰就提倡“中和之响”:“中和之响,阒其不还。”(《乐府篇》)又提出“宫商大和”“瑟柱之和”(《声律篇》)、“折之中和,庶保无咎”(《章句篇》)、“殊声而合响”(《才略篇》)等等,都是其主张“中和之音”的具体体现。其次,我们说“韵”。“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心雕龙·总术篇》)齐梁时期,有韵无韵成为区分文体的重要尺度。后人说“韵”,多指余蕴。如听音乐,人们要求余音绕梁,三月不绝。以之评文学,则要求无声胜有声,有遗韵十足、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陆机《文赋》中说:“音泠泠而盈耳。”郭绍虞释“泠泠”为“音韵之清”?。《文心雕龙》也有多处讲“韵”,如:“结言GFDF3韵”(《诠赋篇》)、“盘桓乎数韵之辞”(《颂赞篇》)、“若乃改韵从调,所以节文辞气”“两韵辄易,则声韵微躁”(《章句篇》)、“季鹰辨切于短韵”(《才略篇》)等等。这些“韵”字指韵脚或押韵的字,而不是指审美意义上的韵味。在用韵方面,刘勰主张“切韵”,反对“讹韵”或曰“讹音”:“楚辞辞楚,故讹韵实繁”“凡切韵之动,势若转圜;讹音之作,甚于枘方。”(《声律篇》)“张衡《讥世》,韵似俳说。”(《论说篇》)此“韵”指风韵,有审美意义上的韵味之意。刘勰认为,张衡《讥世论》(已佚)文风类似杂戏搞笑表演,即缺乏韵味。在审美上,刘勰主张“流韵”“逸韵”:“锋发而韵流”(《体性篇》)、“流韵绮靡”(《时序篇》)、“偶意共逸韵俱发”(《丽辞篇》),刘勰把“韵”当作作品的审美情趣和精神情调了,这是尚韵意识的表现。
三、味之则甘腴:诗性味觉
中国的饮食文化特别丰富,历史也非常久远。《礼记·礼运》中说,太古时代,“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饮食仅为了维系生存。后来,祖先们发现并使用火,饮食不仅要吃饱而且要吃好,饮食文化也逐渐丰富。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追求饮食味道之美的理论长盛不衰,诸如《食谱》《食经》之类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丰富的饮食文化蕴育了丰富的味觉观念。其中许多观念后来移植到文学批评当中,文学也成为有滋有味的精神食粮。
在所有的味觉体验词语中,对古代文论影响最大的是“味”这个概念。《道德经》第三十五章:“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又第六十三章:“味无味。”高明以为,这两个“味”字皆作名词。(21)这里,“味”一词已摆脱日常生活的味觉体验,已上升为精神理念了。在中国文论中,以味论诗、评诗的内容相当丰富,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味”字,为中国文论增色三分。文论中的“味”范畴,把人们日常生活的饮食体验与人们品读诗文的精神体验相结合,使“味”一词既有日常生活的生动体验性又有精神体验的超越性。汪涌豪先生指出:“其含义都超越一般意义上的生理体验,而指称一种心理体验,一种有所领会的精神性活动,是显而易见的。”(22)汪先生进一步指出:“汉魏以来人论文用‘味,主要用以指主体在审美赏鉴方面的投入,所谓‘耽味‘诵味‘含味和‘玩味;同时又指作为赏鉴对象的客体所蕴藏的某种意蕴,所谓‘滋味‘辞味‘义味‘真味‘精味‘清味‘至味,乃至‘禅味‘逸味‘遗味‘余味,等等。”(23)“味”范畴主客两方面的内涵在《文心雕龙》中都有表现,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说:
其一,从创作角度来说,如何使作品有味道呢?刘勰认为,构思非常重要,构思巧妙的话,“拙辞”可以孕育出“巧义”,“庸事”可以萌生“新意”。(《文心雕龙·神思篇》)
其二,从作品本身来说,要有余味,不能太露太透。《文心雕龙·宗经篇》云:“往者虽旧,余味日新。”认为五经“旨丰”“喻远”,余味无穷。刘勰又提出“隐”这一审美范畴,其意也指余味:“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隐以复意为工。”“夫隐之为体,义主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深文隐蔚,余味曲包。”(《文心雕龙·隐秀篇》)也就是说,“隐”是言外之意、味外之味。范文澜说:“重旨者,辞约而义富,含味无穷。”(24)钱钟书认为:“《史通》所谓‘晦,正《文心雕龙·隐秀》篇所谓‘隐,‘余味曲包‘情在词外:施用不同,波澜莫二。”(25)与这种“余味”相近的还有“遗味”:“儒雅彬彬,信有遗味。”(《史传篇》)有“滋味”:“吟咏滋味,流于字句。”(《声律篇》)有“精味”:“精味兼载”(《丽辞篇》)有“辞味”:“统绪失宗,辞味必乱。”(《附会篇》)有“道味”:“道味相附,悬绪自接。”(《附会篇》)有“义味”:“义味腾跃而生。”(《总术篇》)总之,刘勰希望文学作品要涵含丰富、余味无穷,所谓“味飘飘而轻举”是也。(《物色篇》)
其三,从欣赏、品鉴的角度言,读者要认真研读、仔细体味,这样才能领会作品要旨,作品的味道才能出来。“张衡怨篇,清典可味。”(《明诗篇》)“研味李老”“味之必厌”(《情采篇》)。这里,我们还要提一下前面提到的“吟咏滋味,流于字句”(《声律篇》)。学者们多推举钟嵘《诗品》所说的“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认为钟嵘是“滋味说”的首倡者。我们认为,刘勰提出“滋味”这一概念可能要比钟嵘要早,并且他还认识到,“滋味”流淌在字里行间,读者要获得滋味要有一个吟咏推敲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刘勰提到“品”一词也有同工之妙,如:“成帝品录”(《明诗篇》)、“皎然可品”(《才略篇》)。如“咀”字,许慎《说文解字》中说:“咀,含味也,从口且声”。又“含”字,《说文解字》中说:“含,嗛也,从口,今声。”咀、含本指吃食的动作,是富于饮食体验性的词,用于文学上则指拥有、包含某种文学特色。如“俯察含章”(《原道篇》)、“含章之玉牒”(《征圣篇》)、“五经之含文”(《宗经篇》)、“叔夜含其润”(《明诗篇》)、“含飞动之势”(《诠赋篇》)、“宋玉含才”“含懿采之华”(《杂文篇》)、“含道必授”(《诸子篇》)、“气含风雨之润”(《诏策篇》)等等,这些“含”字,也可视作是口含食物的生活体验的化用。
除了以上视觉、听觉、味觉体验之外,《文心雕龙》中还有其他感觉体验。如“佩之则芬芳”(《总术篇》)、“情采芬芳”(《颂赞篇》)、“《七略》芬菲”(《诸子篇》)等等,其中“芬芳”“芬菲”就是嗅觉体验的用词。文论还经常用软、硬、细、粗、轻、重、尖、锐、钝、平等词语,这是触觉体验用语的援用。如:“魏文九宝,器利辞钝”(《铭箴篇》)、“尸佼尉缭,术通而文钝”(《诸子篇》)、“思有利钝”(《养气篇》)。汪涌豪先生认为“钝”一词“已微致贬意。”(26)与之相反,“锐精细巧”(《附会篇》)、“子云锐思于千首”(《总术篇》)、“后进锐笔”(《物色篇》)、“祢衡思锐于为文”(《才略篇》)等,其中“锐”一词应当是褒义了。
文论话语中不仅有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触觉这些单个感觉体验用语的移用,而且也有联觉(一称通感)体验的移入。比如“美”字是文学批评中运用较多的字眼,如从字源学角度来说,它就是联觉体验的移入。许慎《说文解字》中说:“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日本人笠原仲二说:“从所谓‘羊大兴起的、人们对生活和直接的意识或感情,即包涵在‘美字中和最原始的意识内容。”其中有视觉、味觉、触觉、经济等多方面,“在心理方面是包含在喜愛、愉悦、快乐之中的,可称之为生活的吉祥、幸福感吧!”(27)也就是说,美意识是一种综合的心理体验。关于中国人美意识的产生,汪涌豪先生则提出一种颇有新意的看法,他认为,“与古人的生殖崇拜更有关系”。“羊与人感觉中的美之所以发生美,也因其分娩时,通常胞衣不破,产程平顺,故古人因以为祥美,验诸《诗经·大雅·生民》之‘诞弥阙月,先生如达,不拆不副,此处‘达字通‘羍,即指羊子,此诗如孔疏所言,是说‘羊子初生之易;还有商代著名的青铜器父乙簋上,被写成形同孕妇的‘美字,可知它显然与古人的生殖崇拜更有关系。”(28)细分析起来,这一美意识渊源也是多种感觉体验的综合。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美”一词的原初义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提升为一种较为纯粹的精神体验了。如“义必纯美”“武仲之美显宗”“致美于序”“义兼美恶”(《颂赞篇》)、“遗亲攘美之罪”(《史传篇》)等。《文心雕龙》还常用“声采”“声貌”“声色”等词语来形容文学的具体情状,如“声采靡追”(《原道篇》)、“始广声貌”“极声貌以穷文”“穷变于声貌”(《诠赋篇》)、“极蛊媚之声色”(《杂文篇》)、“夸张声貌”(《通变篇》)、“豫入声貌”“声貌岌岌其将动矣”(《夸饰篇》)、“附声测貌”(《才略篇》)等等。显而易见,这些词语是听觉和视觉的联通。正如钱钟书所说:“夫文乃眼色为缘,属眼识界,音乃耳声为缘,属耳识界。‘成文为音,是通耳于眼,比声于色。”(29)其他如“视听”一词则是视觉和听觉的联通,如“以广视听”(《谐隐篇》)、“播诸视听”(《檄移篇》)等。而“声得盐梅,响滑榆槿”(《声律篇》)则是听觉、味觉、触觉的联通了。联觉体验源于人的自然本性。荀子《荀子·王霸》说:“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又《荀子·性恶》说:“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人之本性即追求美好之物,联觉体验在文学批评中的移用,反映的是人们对文学整体美的追求,即所谓色香味俱全。1981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获得者斯佩里关于“裂脑人”研究的最新成果,证实了人脑好比两套不同类型的信息加工控制系统,它们相辅相成,紧密配合,构成一个统一的控制系统。(30)这样,人感受外界信息,就必然是系统的整体的。人感受到美的整体,就从整体上从各个方面反映它。视、听、嗅、味、触觉各个感官通过不同的渠道,把有关信息输送到大脑皮层,与脑中所贮存的信息掺和在一起,就会融合成一个完整的立体的美的形象。
感觉性话语的大量涌现,是中国文论成熟时期的重要特征,不仅是《文心雕龙》,这一时期的其他几部文论也大量运用感觉性话语。如陆机的《文赋》说:“播芳蕤之馥馥”“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宜”“阙大羹之遗味,同朱弦之清汜”,钟嵘《诗品序》提出“滋味”说、“非调五音无以谐会”等等,都是五官感觉性话语在文论中的鲜活运用。
维柯认为,感觉“认识事物的唯一渠道”(31);亚里士多德《论灵魂》也说:“凡是不先进入感官的就不能进入理智。”(32)可见感觉是思想和理智的基础和前提。中国古代文论不仅由感觉而理智,而且始终保持着感觉的鲜活体验性,有别于进入抽象的理智阶段却断绝鲜活体验性的西方文论。汪涌豪先生指出:“在西方的理论传统中,官能感觉作为动物的感觉,是被排斥在美的领域之外的。”(33)“中国的理论传统则与之有明显的不同,它一般不绝对区隔视、听与味、嗅、触两者。也不执意推崇前两者,排斥后三者在审美活动中的意义。相反,认为此数者彼此感通,都有助于人对外物有认知,对美的反映。”(34)“传统文论范畴中引入感官经验之词,不仅不是取式于自然人事的范畴构成模式的粗鄙和不成熟,有时简切的字面适足体现这种模式含蕴的精微。”(35)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知,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成熟期的中国文论感觉性话语建构的体验性和精微性的完美统一。
中国文论成熟期感觉性话语的建构,是千百年来中国文化重视五官感觉体验的传承和发展。这种重感觉体验的话语建构,对后世文论产生深远影响。后世文论特别喜欢诗文的声色气味,如明代袁中道论唐人诗,称:“览之有色,扣之有声,而嗅之若有香,相去千年之久,常如发硎之刃,新披之萼。”(《宋元诗序》,《珂雪斋文集》卷二)清代顾诒禄说:“诗有声、色、臭、味。臭为先,味次之,声又次之,色更次之。声、色、臭、味具全者,佳品也。然亦有超乎声、色、臭、味之外者,此又当以天趣赏之。”(《缓堂诗话》卷上)(36)宋大樽《茗香诗论》:“或问:‘至靖节,色香臭味俱无,然乎?曰:‘非也,此色香臭味之难可尽者,以极淡不易见耳……和气之流,必有色香臭味,云则五色而为庆,三色而成矞;露则结味成甘,结润而成膏。人养天和,其色香臭味亦发于自然。有《三百》之和,则有《三百》之色香臭味;有靖节之和,则有靖节之色香臭味。”(37)都是五官感觉性话语的生动用例。
注释
①[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427页。
②汪涌豪:《中国文学批评中感觉用语的援用》,见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所主编《中国文论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67页。
③[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页。
④?[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60、175页。
⑤钱钟书:《管锥编》第4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2295页。
⑥?(31)(32)[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88、252、200、191页。
⑦⑨?[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视觉思维——审美直觉心理学》,滕守尧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5、25、23页。
⑧[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23页。
B10汪涌豪:《范疇的思想资源——以“圆”为中心的考察》,《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十五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0—51页。
?王先霈:《圆形批评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7—18页。
?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853页。
?(21)高明:《帛书老子校注》,中华书局,1996年,第89、132页。
?朱自清:《诗言志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8页。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65、184页。
?吴林伯:《〈文心雕龙〉义疏》,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22页。
(22)(23)(26)(28)(33)(34)(35)汪涌豪:《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十五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37、30、29、27、28、35页。
(24)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33页。
(25)(29)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271、103页。
(27)[日]笠原仲二:《古代中国人的美意识》,杨若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5—6页。
(30)钱学森:《关于思维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66页。
(36)张寅彭选辑:《清诗话三编》(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615页。
(37)王夫之等:《清诗话》(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第106页。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with the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of Sensory Discourse
Wu ZhongSheng
Abstract:Rooted deeply in profound poetic culture,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tends to compare literature with the daily experiences of five senses, and produces a large number of intuitive literary theories, categories and concepts which are full of sensory experiences. Sensory literary discourses, represented by "Vision, hearing, smell, and Pei" in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are widely used in literature creation and reading appreciation, thus determines its most basic experiential characteristic.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ranging from the literary concept, mode of discourse, the way of thinking to the feeling experience, has built a traditional sensory literary discourses, which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later literary theories.
Key words: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Literary discourse construction experience; the building of litera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