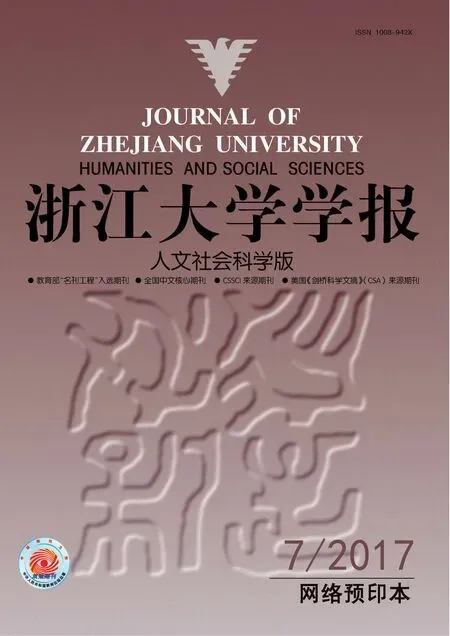教育史是什么?
陈露茜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北京 100875)
教育史是什么?
陈露茜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北京 100875)
所谓教育史,是指研究者依托教育方面的史料来建构关于教育的过去及其解释,研究者的“崇高理想”是对教育历史的解释能够尽可能地接近教育的史实,即遵循历史主义的检验,这是教育史研究的全部目的和核心使命。而遵循历史主义的检验,并非指教育史研究要探究过往教育的全部真实、按照教育从前的样子复原过去,而是指教育史研究应尽可能保证确有其事或实有其事,并使研究者自己深入到过去的世界中去理解教育的过去,在过往的生活环境、观念、思潮、社会结构中理解前人关于教育的想法、信仰及行动。而这一切都是由教育史独特的知识范式所决定的:教育史就是教育史,它既不是科学,也不是艺术,它使用的是日常的语言和表现形式,有时借用科学、艺术的诸多概念来表达自己的含义,进而建构起教育史的大厦。
教育史; 历史主义检验; 事实/真实; 知识范式
“教育史是什么”是教育史研究的入门问题,却又是一个在学界被反复讨论的话题①。它的定义既清晰又暧昧,它不仅关乎教育史的本体,更指向教育史的目的、意义、属性、范式等一系列问题。
一、 学术研究中的教育史与应用领域中的教育史
在国内学界的语境中,对“教育史”大致有以下几种较为典型的表述方式:第一,教育史“是教育科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以人类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历史为研究对象。其任务是分析、研究各个历史时期人类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进程,总结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探讨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为解决当代教育问题提供启示与借鉴,并预示教育发展的方向”[1]1;第二,教育史“是人们创造和实践的教育的历史……是人们记录和描述的教育的历史……是人们思索和研究的教育的历史……是人们自觉地、系统地思索和研究的教育的历史”[2]6;第三,教育史“是一门具有精神陶冶功能的科目……目的应当有助于学生通过认识其他国家和民族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更好地理解人、思想、文化和传统,从而为形成一种广阔的全球和世界视野提供帮助”[3]1。
从以上表述中可以看出,当我们谈及“教育史”的时候,它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指的是作为“史实”的教育史,即过去发生过的种种与教育相关的事件,是教育的现象、实践、活动、制度、人物、思潮、观念等的总和,即那个已经消逝了的关于教育的过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存在;第二个层次指的是作为“史料”的教育史,指的是那些被各种形式记录下来的关于教育的过去的知识,包括文献、纪念物、象征等,即那些已经消逝但还未消失的教育的过去;第三个层次指的是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的教育史,指的是当下的研究者对过去发生的种种与教育相关的事件的理解和叙述,这些理解和认识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4]24。
对职业教育史研究者而言,所谓教育史,是研究者依托第二个层次的教育史来建构第三个层次的教育史,而研究者的“崇高理想”[5]74-87是使第三个层次的教育史尽可能地接近第一个层次的教育史,即遵循历史主义的检验,这是教育史研究的全部目的和核心使命。
但对一般人或者绝大部分教师而言,第一个层次和第二层次的教育史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他们既不一定有兴趣也没有必要去理解这两个层次的教育史。他们所接触到的,或者更需要的是职业教育史研究者对第三个层次教育史的准确诠释之后的“附产品”或“副产品”,即教育史的运用(或应用),用于教学、宣传、为教育的实践研究提供相关的背景信息、总结历史规律,甚至是娱乐、消费等。应用层面的教育史可以根据现实需要进行必要的选择和取舍,但这种选择和取舍不是歪曲和扭曲,真实性和准确性依然是它的准绳。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到历史的、政治的、现实因素的制约,教育史研究出现了本末倒置的现象,我们将教育史研究的附属物即教育史的运用视为教育史研究的全部目的,并以此来评判教育史研究的价值,却没有对教育史研究的本质——以历史主义为准绳,回到过去,尽可能地还原那个准确而真实的教育历史——给予足够的重视。也就是说,教育史的运用需要一个健全而健康的知识前提,即充分的教育史研究。如果我们对教育史研究是什么、它的属性和特点是什么、它的价值和意义又在何处等问题没有充分的理解和把握,就奢谈对教育历史规律的总结与把握、教育历史经验对教育现实的启迪与借鉴,其结果必然是教育史运用的混乱与盲目,以及教育史研究中的短视与功利。
二、 教育史研究中的“真实”
进一步追问,既然教育史研究的核心价值和最高目的是追求教育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真实”、要“回到过去”、遵循历史主义的检验,那么,这里的“真实”指的是什么?“回到过去”是要照从前的样子复原过去吗?或者说,复原过去是可能的吗?我们又如何验证史家复原的过去是真实的过去?这实际上又涉及历史研究中另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即真实性问题。
真实性的议题是伴随历史编纂的出现而出现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6]65这是中国传统史学对史家的道德要求,即要求史家能刚正不阿地秉笔直书。“自刘向、扬雄博及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在中国的史学传统中,“实录”的概念最早出自《法言·重黎》,与扬雄评价司马迁的《太史公书》有关;后来班固又在《汉书·司马迁传》中盛赞司马迁,再次提及“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见班固《汉书·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8页。在西方的史学传统中也是如此:修昔底德就曾要求把想象与事实严格区分开来,检验见证者的可信性[7]198。这种对客观、真实的要求在18—19世纪“历史科学”形成之时达到了顶峰,兰克史学高举“盖史之所记,如其事而实书之,不参己见,亦无偏倚”的大旗,砸烂了圣·奥古斯丁的“天城”*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拉丁教父的主要代表,是基督教拉丁教父中著述最多的人,《论上帝之城》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进入“圣坛”,成就了理性主义的“大祭司”。但很快地,随着维多利亚时代天真的自信以及对机械论进步观崇拜的终结,兰普勒希特辩论*卡尔·兰普勒希特(Karl Gotthard Lamprecht),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兰克的学生,著有12卷本《德意志史》,挑战德国历史主义传统的信条。“触犯”了以总结规律和追寻客观真实为核心的历史“科学化”的“天条”,而由此产生对“终极的历史”(ultimate history)[8]10-12的怀疑,在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和卡尔·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把具有倾向性的、有意识的阶级立场辩护为“历史科学”的合法组成部分之后,“历史科学”所谓的“真实性”在20世纪最后十年被后现代主义解构为“纯粹的幻想”。兰克所谓“一切时代离上帝都一样近”的论断本身就是虚幻的,因为事实本身不会说话,“只有当历史学家要事实说话的时候,事实才会说话;由哪些事实说话、按照什么秩序说话或者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说话,这一切都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4]5。
在简要回顾了关于真实性讨论的历史之后,我们会发现所谓的真实性实际上包括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指的是“事实”(actuality或reality),意为实际发生过的、经历过的,即那个不依赖于史家主观意志的“史实”;第二层次指的是“真相”(truth),意为符合真实情况以及事实与事实之间因果关系的真实呈现,这是建立在客观事实上的主观判断或评价也即历史叙事,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史实发生的前后顺序及归因等问题的讨论而形成的历史解释。而这两个层次之间的区别正如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戏剧中所描述的那样,“事实”像一只袋子,假如你不放进一些东西,袋子就不会站起来。
因此,教育史研究所谓的“真实”指的是教育史研究应该在充分挖掘史料的基础上,使历史叙述尽可能贴近第一个层次的“事实”,即教育史研究应尽可能保证确有其事或实有其事。正如豪斯曼(Alfred Edward Housman)所言:“精确是职责,不是美德。”[9]37但历史事实能否还原历史的真相,或者说,史家建立在史实基础上的历史解释或历史判断是否准确、是否合乎真理,则很难简单判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科特(C.P.Scott)断言:“事实是神圣的,解释是自由的。”[4]4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甚至挑衅说,“对任何历史学家而言,在他创造历史事实之前,历史事实并不存在”[10]528。也正因如此,历史是常写常新的,它必然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出现与挖掘以及史家经验的变化而变化,不断接受经验和逻辑的检验与修正。
同样,所谓“回到过去”也并非意指按照从前的样子复原过去,因为这是无法完成的——教育的历史已然湮没在时间的尘埃之中,职业教育史研究者面对的是一扇“不透明的窗户”,是“无法看见和无法面对的处于黑暗之中的某种东西”[11]258。而其使命是“从永远关上大门的过去世界中获取信息,并使之转化为今人所能领悟的历史知识”[12]19,因此要用“思想之光”[11]258来照亮它们。也就是说,对职业教育史研究者而言,回到过去、接受历史主义的检验,意指他们需要深入到过去的世界中去理解过去,在过往的生活环境、观念、思潮、社会结构中理解前人关于教育的想法、信仰及行动。正如章学诚所言,对待前人“必敬以恕”,“论古必恕……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是则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13]17。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不从历史人物的内心来看他们,不像一个演员感受他所扮演的角色一样来感受他们,把他们的想法再想一遍,坐在行动者而不是观察者的位置上,就不可能正确地讲述故事……(这一点的确难以做到)……”“但无论如何,历史学家必须把自己置于历史人物的位置上,必须感受其处境,必须像那个人一样思想。如果没有这种艺术,不仅不可能正确地讲述故事,而且也不可能理解那些重构历史所需要的资料。传统的历史写作强调富于同情的想象的重要性,目的是要进入人的内心。”[14]119-120
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史研究中真实性的问题单靠个体的教育史研究者或者某一时期、某一流派的教育史研究者是无法完成的。作为个体的教育史研究者或者某一时期、某一流派的教育史研究者只能在现有的史料和史学理论的前提下,进一步挖掘新材料、解释新材料,做到论从史出、有理有据,他们只能尽他们所能地接近史实,达到一个相对真理的阶段。而达到绝对真理应该成为作为个体的教育史研究者的“崇高理想”,成为其从事研究的职业准绳和信念底线,并成为作为集体的一代又一代教育史研究者共同奋斗的目标。
三、 教育史研究既不是科学也不是艺术
那为什么要探究教育史的真实性问题?或者说,为什么教育史研究中的真实性问题这么重要?事实上,这一系列对真实性问题的追问都扎根于我们对教育史研究所属的知识范式的判定。
在当下学界关于教育史所属的知识范式的既有讨论中,所使用的表达大多是教育史要“探索教育发展历程”“总结经验教训”“摸清教育发展客观规律”“服务当下教育实践”*诸如此类的表述可参见:王炳照等《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吴式颖、任钟印《外国教育思想通史》,(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滕大春《外国教育通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周采、杨汉麟《外国学前教育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等。等。这类表达很显然参照的是“科学”的定义。这里的“科学”既不泛指“一切形式的学问”,也不指称“一科一学”,而是作为英文中“science”的译名,指称自然科学,后逐步演化为“正确之学”“有用之学”[15]7。自然科学有对确定性的前提假设,其特点包括一致性、客观性以及因果规律性,即实际方面的直接利用和理论知识方面对因果规律的演绎。教育史的情况则是不同的。一方面,教育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分支,具有历史研究的典型特征——不确定性,对史学家而言,只有变化才是绝对的[16]67,74。也就是说,即便在史料本身不变的前提下,研究者对史料的解读也是不断变化的,因为研究者的思想是不断变化的。在历史研究中,研究者是有价值判断和立场的,“他在自己的精神中重新思考、重新建构人类集体的经验……认识过去……历史学家通过它来追寻自己……”[17]147-149因此,他是无法“抽身而出”“独善其身”的。绝对意义上的历史重复或循环是不存在的,“因为一件事本身就是许多背景的组合,其中没有一件将会再度发生”[18]200,所以“没有两个历史事件是同一的”[4]57。对历史的解释只有在当时的时空中进行综合理解才有意义,而剥离了历史条件的所谓的历史经验是不可靠的。“把历史同自然科学类比的做法,在过去三十年里错误地引导许多历史学家离开了他们的职业的正确道路。关于过去的知识里没有实用价值,也没有科学地演绎关于全体人类的行动的因果规律的方法。总之,历史的价值不是科学的。”[18]12另一方面,教育史作为教育研究的一个分支领域,也兼具教育研究中的人文气质。虽然从教育学产生那天开始,学人就自觉地用自然科学的范式来进行自我规范,认定教育、教学是有规律的,人的理性可以认识和把握这些规律,并自觉地在教育教学实践中运用这些规律,但教育研究还是一类关于人的知识。因为教育从本质上说是个体社会化和社会个性化的过程,它意味着代际经验的传递以及个体的成长是人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也就是说,关心人、研究人、塑造人,是教育的核心使命。而独尊自然科学的范式使得以人的养成为目标的教育研究陷入了两难的泥潭。因为一旦涉及人的问题时,他的出身、立场、偏好、选择、际遇、价值观等都是不可回避的,这必然要求教育要有人文关怀。因此,无论我们是从历史研究中来理解教育史,还是从教育研究上来言说教育史,教育史都不是也不应成为一门研究客观实体、把握客观规律的自然科学,它的真实性从本质上来说是无法检验的。它关注人,也必然随着人的经验变化而变化,并随时随地接受经验和逻辑的修正。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史是一门经验知识,具有人文主义的属性。
但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教育史从知识范式上看不属于科学,那属于艺术(arts)吗?中国传统史学中有“文史不分”一说,无论《论语》有云“文胜质则史”,还是陈寅恪所谓“以诗证史”,表达的都是历史研究与艺术之间的紧密联系。在西方的史学传统中也是如此。克莱奥(Clio)本身就是缪斯女神;而从荷马史诗到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从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到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文学派史学曾因生动的历史叙事让读者如临其境般地进入过去世界而在西方史学流派中占据了显赫的地位;后现代主义在充分解构了“科学的”历史学之后,也竖起了“重返米什莱(Jules Michelet)”的大旗。但“文史不分家”的传统与文学派史学的辉煌并不能回避将史学视为艺术所存在的严重问题,如“以辞害意”“缺乏严谨的治史规范”“主观投入过多”“对史料的考订不够严密,细节失误较多”[19]50等。历史研究不是艺术,历史叙事不是虚构,而是基于对史料的理解;历史研究的是过去的事实,而非抒发情感;历史研究的使命也是最大限度地贴近过去的事实,任何历史解释都应该建立在史料证据的基础之上,且应经受得起多方面资料的推敲和验证,而非纯粹的想象和审美。“写好历史并非儿戏。每一句和每一段的锤炼琢磨都必须符合许许多多的史实,这些史实之中有一些是只有作者知道的,有一些可能是他在最后一刻才发现或记起的,因而就要将他精心建造起来的艺术结构全部破坏。在这些情况下,艺术家无疑就会产生忽略史实真相中不方便的细枝末节的念头。”[18]35正如贝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所言:“历史学家在写历史时,心里必须想着那些发生于过去的事情是确实存在的,它们的存在并不以人们是否知晓为转移,只要有可用的资料,史家的工作就是描述和分析过去世界的某些部分。如果心里不装着这些东西,无论他如何具有哲学头脑,是一句话也写不出来的。”“历史写作中也有所谓‘创造性的时刻’,但这种创造性不能滑进未知的领域。”[20]74-75从硬币的另一面看,虽然我们认为教育应该摆脱科学至上主义的桎梏,关注人的情感、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中不存在科学规律——直观性的原则、循序渐进性的原则、量力性原则、因材施教原则等;也就是说,在教育中不应把科学的规律信奉为不变的教条,而是应该科学地看待理性、情感、信仰、直觉在人的养成、塑造和发展过程中的价值与意义。而否认教育学是一门纯粹的科学,也不等同于否认教育中存在一定的客观规律和主观认知规律。从这个意义上看,作为教育和历史交叉领域的教育史研究不是也不应是一门纯粹的艺术。
教育史就是教育史,它既不是科学,也不是艺术,更不是其他任何学术,“克莱奥永远凛凛不可侵犯”[21]47,或者说,教育史研究没有自己独特的知识范式。科学是体系鲜明的、表达精确的,有确定性的理论逻辑;艺术是个性化的,虽然源于生活,却抽象于生活,想象、夸张、渲染、比喻是其典型手法;教育史研究却不同,它使用的是日常的语言和表现形式,有时借用科学的、艺术的诸多概念来表达自己的含义。正如屈威廉所言,“在历史是艺术还是科学这个议论纷纷的问题上,可以说它两者都是或者两者都不是”。教育史研究有科学的任务,即“每个历史家要想成为这一行业的一个严肃的工作者都必须认真踏实从事的日常工作——史料的积累和证据的检验”;教育史研究有想象的任务,“这时他研究已经搜集的史实,选择和排比它们,并且做出他的推测和概括”;教育史研究有艺术的任务,即“用一种能吸引和教育我们同胞的形式把科学和想象的结果表达出来”,但史家们要意识到对“历史事件进行描述的构思和写作的困难和重要性,布局、谋篇和风格都不是像打字那样轻而易举的。任何一个人如果要文学供他驱使,那么除非他愿意做她的忠实助手,否则文学绝不会帮助他的工作”[18]31。
四、 结 语
综上所述,对职业教育史研究者而言,所谓教育史,是研究者依托教育方面的史料来建构关于教育的过去及其解释,研究者的“崇高理想”是对教育历史的解释能够尽可能地接近教育的史实,即遵循历史主义的检验,这是教育史研究的全部目的和核心使命。而遵循历史主义的检验,并非指教育史研究能够探究历史的全部真实、按照教育在过去原来的样子复原过去,而是指教育史研究应尽可能保证确有其事或实有其事,并使研究者自己深入到过去的世界中去理解过去,在过往的生活环境、观念、思潮、社会结构中理解前人关于教育的想法、信仰及行动。而这一切都是由教育史独特的知识范式所决定的:教育史就是教育史,它既不是科学,也不是艺术,它使用的是日常的语言和表现形式,有时借用科学、艺术的诸多概念来表达自己的含义,进而建构起教育史的大厦。
也正因如此,教育史研究的价值是不能以直接服务于行动的能力来衡量的,它应是一类不牵涉任何实际物质利益、纯粹为了实现精神满足而进行的研究。它与其他任何一门知识一样,能丰富人的认识,发展人的整体思维,进而实现人类知识的整体发展,并为其从业者带来智力的满足与身心的愉悦。这便是教育史研究的“自由价值”。它主张教育史研究者出于纯粹的学术兴趣而进行研究,而不是为了解决教育发展中的当下问题并满足教育发展中的直接需要;能够在教育所处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的真实情境中发现教育的真实问题与价值,而不是在现实话语系统中自说自话;能够更加深入、真实地了解本土或异域的历史文化,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认识他人,从而愉悦身心、充实生活,而不仅是为了“下一次更聪明一点”。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如果一门知识不能为我们生活的改进与社会的进步提供实质性的帮助,我们总会觉得有缺憾。这是实用理性给我们的惯性思维,但正是出于这种惯性思维,在我们为教育史研究寻找可具体行动的方向时,我们事实上便假定了它具有潜在价值。而即便是寄希望于教育史研究能够发挥实际用途,我们首先需要做的也是理解和认识,只有真实地发现教育的历史,才有可能为我们的现实行动提供真正有意义的思维指导。而摒弃一切外在的工具目的和功利诉求,真正地“回到过去”,以真正的历史问题为导向,发现真实的教育历史之情境,真实地再现教育的历史后,教育史研究对增扩人类思维与整体利益的自由价值便达成了,同时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教育史研究对现实教育行动的指导意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让教育史研究回归历史研究与教育研究的本质,真实地回到过去,实现教育史研究的自由价值,并为之献身,应成为教育史研究者的志业。
[1] 吴式颖: 《外国教育史教程》,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Wu Shiying,ACourseintheHistoryofForeignEducation, Beijing: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2003.]
[2]杜成宪、邓明言: 《教育史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Du Chengxian & Deng Mingyan,StudiesintheHistoryofEducation, Beijing: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2004.]
[3]张斌贤、王晨: 《外国教育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Zhang Binxian & Wang Chen,AHistoryofForeignEducation, Beijing: Education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2008.]
[4]E.H.Carr,WhatIsHistor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5]C.Beard,″Written History as an Act of Faith,″AmericanHistoricalReview, Vol.39, No.2(1934), pp.219-231.许慎: 《说文解字》,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Xu Shen,ShuowenJiezi, Changsha: Yuelu Press, 2006]
[7][德]斯特凡·约尔丹: 《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孟钟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S.Jordan,ADictionaryoftheBasicConceptsofHistoryandScience, trans. by Meng Zhongji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8]A.W.Ward, G.W.Prothero & S.Leathes(eds.),TheCambridgeModernHistory:AnAccountofItsOrigin,AuthorshipandProduction, Montana: Kessinger Publishing, 2010.
[9]M.Manilii,Astronomicon:LiberPrimu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7.
[10]C.Becker,″Detachment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TheAtlanticMonthly, No.20(1910), pp.524-536.
[11]P.Novick,ThatNobleDream:The″ObjectivityQuestion″andtheAmericanHistoricalProfe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12]李剑鸣: 《历史解释建构中的理解问题》,《史学集刊》2005年第3期,第19-25页。[Li Jianming,″Questions on Understanding the Explanations of History,″CollectedPapersofHistoryStudies, No.3(2005), pp.19-25.]
[13]章学诚: 《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Zhang Xuecheng,PosthumousPapersofZhangXuecheng,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1985.]
[14]W.Dray,LawsandExplanationin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15]冯天瑜: 《中西日文化对接间汉字术语的厘定问题》,《光明日报》2005年4月5日,第7版。[Feng Tianyu,″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Terminology into Western and Japanese Culture,″GuangmingDaily, 2005-04-05, p.7.]
[16]K.R.Popper,ThePovertyofHistoricism, Boston: The Beacon Press, 1957.
[17][法]安托万·普罗斯特: 《历史学十二讲》,王春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A.Prost,TwelveLecturesonHistory, trans. by Wang Chunhua,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18]G.M.Trevelyan,Clio,aMuseandOtherEssaysLiteraryandPedestrian, New York: Longman Group Ltd., 1913.
[19]李剑鸣: 《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Li Jianming,TheVirtuesandAccomplishmentsofHistorians, Shangha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20]B.Bailyn,OntheTeachingandWritingofHistory:ResponsestoaSeriesofQuestions, New Hampshire: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94.
[21]杜维运: 《史学方法论》,台北:三民书局,1985年。[Du Weiyun,TheMethodologiesofHistory, Taipei: Sanmin Book Company, 1985.]
What Is History of Education?
Chen Luxi
(Faculty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Nowadays, the focus on the utility of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has strongly perturbed the academic researches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It demands that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serve directly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as a discipline, to serve directly the reality, and to serve directly politics and policy-making. All of these demands originated in the uncertainty of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with the understanding that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is a knowledge based on natural sciences but not a knowledge based on the liberal arts, a type of thinking that originated in the worship of Scientism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is research tries to deny the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of education based on the simplified explanation of the scientism paradigm and to discuss history of education as an academic research field, including the paradigms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it. This means that this type of research attempts to separate the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of education as an academic research field from the field of applied knowledge. It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different meanings of ″truth″ and ″reality″ embraced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ruth″ (Wahrheit) and answer the question of ″what is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as a science (Wissenschaft).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with regard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is the historical presentation and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record of the education in the past that is constructed by the educational historians whose ″noble dream″ is to make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educational history as much as possible close to the educational reality of the past, verified by the historicism doctrine, which will be the unique purpose and mission of educational historical researches. However, when we talk about the verification by the historicism doctrine, it does not mean that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can find the truth of our educational past, nor can we recreate the educational past. It means that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should ensure that what he talked about was the reality or past actuality of education. The professional historian should delve deep into the past world to understand the past of the education, to understand the educational ideas, faiths, and practices in the context of past social circumstances, ideas, thoughts, and structures. All of this was decided by the unique paradigm of the educational history that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was neither a science nor an art. It used the daily languages and patterns of manifestation, or it borrowed concepts from science or the arts to present its own meaning and to construct the mansion of educational history. The value of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cannot be calculated by its ability to serve direct action. It should be the kind of research that is not involved in any practical interests but focuses only on spiritual satisfaction. It asks the researchers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to perform the research just for pure academic interests; to find out the real questions and values of education in the real historical, cultural,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context; to really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culture deeply, whether at home or abroad, and to help us understand ourselves and each other.
history of education; historicism inspection; reality/truth; knowledge paradigm
10.3785/j.issn.1008-942X.CN33-6000/C.2017.02.071
2017-02-07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zjujournals.com/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17-07-31 [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 CN33-6000/C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6YJC880003)
陈露茜(http://orcid/org/0000-0003-1436-334X),女,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外国教育史研究。
①目前国内相关研究主要包括:杜成宪、崔运武、王伦信《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杜成宪、邓明言《教育史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吴式颖《教育:让历史启示未来》,(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史静寰、延建林《西方教育史学百年史论》,(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李涛《百年中国教育史研究高潮的回顾与反思》,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第106-113页;郭法奇《什么是教育史研究?——以外国教育史研究为例》,载《教育学报》2005年第3期,第92-96页;张斌贤《教育史学引论》,见《教育是历史的存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田正平《老学科,新气象:改革开放30年教育史学科建设述评》,载《教育研究》2008年第9期,第7-16页;周采《教育史研究的前提假设及其意义》,载《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18-25页;郭法奇《再论什么是教育史研究》,载《教育学报》2009年第4期,第97页;李忠《建国后教育史研究取向的转换》,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88-96页;吴式颖《我们需要这样的外国教育史学建设:读〈西方教育史学百年史论〉有感》,载《教育学报》2016年第1期,第121-128页。